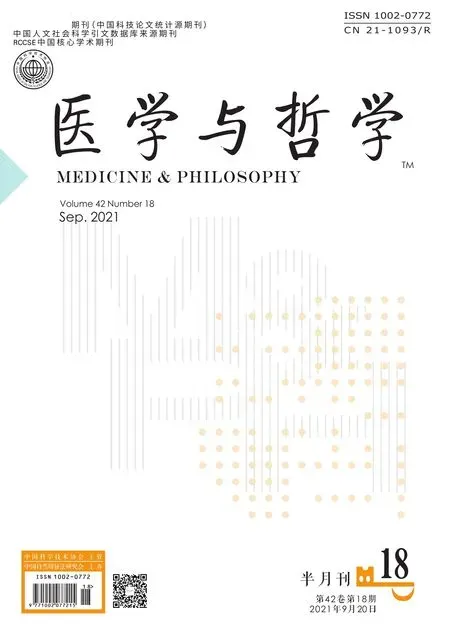他者视域下的医学暴行*——二战期间医源性战争暴行的痛苦记忆与当代反思
杨彦君
关于二战时期医学暴行的历史记忆、当代反思和社会教育,理应成为当今国际医学界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在历史与现实交相呼应中,既需要历史学界持续深入调查史证,藉以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也需要生命伦理学界在医学与道德层面不断反思,积极采取有效的社会教育实践,防止人类社会历史悲剧的再次上演。正如德国学者米勒[1]所讲:“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里,谁注入了记忆、定义了概念、解释了过去,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我们既要关注日本国内对医学暴行的历史认知,也要面对国际社会对医学暴行历史的淡忘和忽视,更要在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都积极地采取行动,促使未来的医学能够沿着人道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行。
围绕二战时期的医学暴行,笔者试以德国作为“他者”来观察,希望阐明德日两国的历史记忆和反思实践,梳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下的“互视”现状,进而在“苦难哲学”视角下体察中国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
1 纳粹医学的反思与实践
1938年~1945年,纳粹医生在奥斯威辛、达豪等集中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绝育试验、海水试验等数十种医学试验,导致不计其数的“受试者”死亡。在纽伦堡后续审判的“医学案件”中,有23名纳粹医生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根据纽伦堡法庭1947年8月的判决,16名医生被判处死刑、无期和有期徒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医学犯罪者”的公开审判,广为人知的《纽伦堡法典》(NurembergCode)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不断向前推演,《纽伦堡法典》规定的“医学试验准则”也逐步更新换代。实际上,这种大规模的医学犯罪既关乎于过去的“黑暗历史”,又影响着战后国际医学法律法规的制定,波及到当代国际社会,特别是医学界的历史认识。在《纽伦堡法典》的基础上,1964年芬兰第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通过了《指导医务卫生工作者从事包括以人作为试验者的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建议》,即《赫尔辛基宣言》,另外在1975年、1983年、1989年、1996年、2000年世界卫生大会又补充和修订了《赫尔辛基宣言》,最终确定了开展人体试验的32条基本原则。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无论是《纽伦堡法典》,还是不同时期对《赫尔辛基宣言》的修订,从其字里行间能够看到规则制定者充分汲取了二战时期医学暴行的历史教训。在2000年版《赫尔辛基宣言》中关于开展“人体试验”的规定更为精细和具体,重申了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应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意味着,二战历史上的医学犯罪作为“负面遗产”为二战之后的医学试验规则的制定带来重要影响,亦可看作是国际医学界对纳粹医学暴行的不断反思之后的具体实践。
大屠杀和纳粹医生犯罪的发生地之一——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于1947年被辟为受难者纪念馆,陈列展览就在旧址本体内进行,旧址、实物、图片和档案记录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二战结束之后,犹太人在欧洲和北美通过集体的不懈努力,利用报纸、电视、纪录片、电影等传播媒介持续揭露纳粹暴行。在推动国际社会认知的漫长过程中,如犹太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名单》在国际传播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幸存者参与了电影的拍摄、宣传和推广,使其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商业价值。《辛德勒名单》1993年一经上映,随即引起全球轰动,获得了法国凯撒奖、日本电影学院奖、美国奥斯卡金像奖、英国学院奖、意大利大卫奖等。换言之,犹太人通过电影叙事的方式让“地球人都知道”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辛德勒名单》原作者是澳大利亚人托马斯·肯尼利,他于2017年5月14日参观了七三一部队旧址后说道:“我曾经去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天又参观了七三一部队旧址,日本军国主义把年轻人变成杀人犯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七三一部队活体试验的罪恶就是东方的奥斯威辛。”肯尼利当天在哈尔滨果戈理书店见面会上还说道:“《辛德勒名单》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的纪实风格,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非虚构。”当然,文学作品和电影等媒体传播是推动国际社会认知的一种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犹太人依托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系统开展大屠杀专题研究,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普遍价值予以深入挖掘、严密论证和多维度阐释。由此,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昭示天下,使之成为了世界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今日无论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几乎无人不知这段历史,形成了具有全球认知度的历史记忆。
犹太人作为受害者不断前行,加害者德国人也做了非常重要的实质努力,这从德国领导人、社会组织不间断地开展反思与实践中即可窥见一斑。1970年12月7日,到波兰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突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面前屈膝跪下,为他的同胞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深深忏悔。这一跪,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996年,德国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1月27日定为德国的“纳粹受难者纪念日”,警示国人不能忘却这段历史。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集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德国必须直面过去,“对于纳粹罪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德国决不能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2]。
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通过不间断地历史叙事、话语传播和反思实践,作为加害者的德国政府始终将国家责任作为战后反思的主旋律,成功地将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欧洲人的历史记忆转换成全世界的历史记忆。加害国的反省与实践、受害者的反思与行动促使历史充满纠葛的双方达成了“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共识,在和平与和解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2 日本医学的反思与实践
1933年~1945年,七三一部队以“国家利益、科学研究和医学发展”的名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反人类、反文明和反伦理的人体试验。这些残暴的医生及其同谋们在战后不但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没有像纳粹医生一样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反而轻而易举地脱掉恶魔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进入战后日本医学院校担任公职。在原七三一部队成员中,有的人通过人体试验取得异于常态的知识和技术,借此取得博士学位,副教授、教授职称,有的人开设私人医院和医药公司牟取暴利。这些“医生”和“专家”跻身于日本医学界上层,不难想象,他们从未公开提及战争责任、医学伦理和职业道德,直接影响到整个日本医学界对此没有反省和反思,医学暴行的历史事实被掩盖下来,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虽然1951年日本医学会加入世界医学会时曾发表“公然指责战争时期对敌国人进行的残酷行为,并谴责那些曾经对患者的残酷行为”声明。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听到日本医学组织发出类似反省和反思的声音。不难想象,“医学暴行”关联者无一例外地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自不会公然指责他们过去的犯罪行为。正如德国学者多因(Doering)[3]所讲:“与德国相比,日本一直在更长的时间内继续生活在禁忌和谎言中。”
进入21世纪以后,相较于医学界主流声音的消寂,一部分医学者摆脱了束缚不断发出反思之声,集体沉默和个体反思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学者森冈正博(Morioka)[4]发出的声音最具代表性,他在文章中写道:“西方的生命伦理学始于对纳粹人体试验的反思,那么日本的生命伦理学应该从反思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开始。”华裔知名学者聂精保[5]呼应了森冈正博:“这对于当今日本和中国的医学伦理,乃至全球生命伦理学都具有多方面、多维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莇昭三[6]在《十五年战争中的医学犯罪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课题》一文中写道:“我认为日本医学界此时此刻需要深刻反省,对被敷衍过去的战争时期的医学犯罪,重新自问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知道石井部队在做什么,即共有公开的秘密,如果这就是他们始终沉默的理由,那么他们的沉默就是犯罪。”
不无遗憾的是,日本医学者略显微弱的反思之声并没有促进日本政府像德国政府一样采取积极行动,日本政府仍然固执地坚持不接触、不理会、不回应的消极态度。不过,学界的反思也偶尔映射到日本医学组织的集体行动。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展出了1945年活体解剖8名美军飞行员的历史资料,这是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第一次站在加害者的视角公开展示战时日本的医学犯罪。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个令人期望的发端,也可能是日本医学界直面历史、记忆和未来的开始。
历史记忆是当代是否反思、如何反思、是否行动、如何行动的前提和基础。二战时期,加害国与受害国、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通过战争、野蛮和屠杀来书写彼此历史与集体记忆,而处于和平时代的后人如何面对这些历史与记忆,又会怎样看待先人留给他们的“负遗产”?来自东京的调查问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
2010年10月,日本民间团体“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在东京发出调查问卷,调查“医学生对七三一部队和奥斯威辛的社会认知状况”,调查对象是东京相关医学院校的在读大学生和研究生。问卷中:“是否知道七三一部队”,统计结果是:17%的人知道,21%的人听说过,62%的人不知道。问卷中:“是否知道奥斯威辛大屠杀”,统计结果是:68%的人知道,27%的人听说过,5%的人不知道。围绕七三一部队问题,问卷中的“认为医学界应该表明证实与谢罪”,结果显示:应该的占69%,不清楚的占25%,不应该的占6%;问卷中“历史问题是否影响到现在”,回答“是”的占75%,回答“不清楚”的占19%,回答“不是”的占6%。
上述问卷发放的范围囿于东京一地,其调查对象是知识群体集中的医学院在读学生,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同对奥斯威辛的认知状况相比,他们对七三一部队的社会认知程度普遍偏低。试想,如果连在东京从事医学学习和研究的人都不清楚七三一部队的事情,那么对于日本其他区域、其他群体,对于七三一部队的认知程度当会更低。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常识,如果没有基本的历史认知,就不可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过,这份调查问卷也显现出相对积极的一面,作为医学院的学生还是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日本医学界,认为“应该表明证实与谢罪”,并且多数人能够认识到,历史上发生的医学暴行影响到今天日本的对外关系。
实质而言,关于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的医学暴行,既有战时环境下国家政治、社会制度和医学制度的驱动力因素,也有社会历史、伦理道德以及作为医者主动迎合的驱动力因素,正是多种驱动力的内外结合才导致了医学暴行的持续发生。如果将其放置于历史学视域下考量,纽伦堡后续审判追究了纳粹医生的战争责任,美日秘密交易掩盖了七三一部队的医学暴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日两国在国家层面的不同认识,进而影响到了医学界的社会认知、价值判断和行为实践。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的政治家、医学者和社会学者等在汲取历史教训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并不局限于德国国内,还波及到欧洲、美洲和亚洲。反观日本,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没有在思想上进行反省和反思,也就不可能在行动上“面对历史、承担应该负起的责任”,这也成为直到今日还经常引起中韩等亚洲国家不断抗议的缘由。因为痛苦的历史记忆和理性的当代反思紧密相连且无法剥离,所以我们必须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学习和研究非人道医学行为何以大行其道;如海水试验、绝育试验、活体解剖、细菌感染、冻伤试验等医学暴行是怎样隐藏在国家制度和战时医学的背后,公共卫生、人口控制和种族差异又是如何成为政治干预医学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必将有助于我们审视、判断和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3 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
虽然战时日本医学暴行的证据链条完备,二战的硝烟也已散去了76年,但是围绕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遗留问题却仍处在否认与证实、狡辩与澄清的纠葛漩涡之中。如果日本一直无视、漠视甚至否认七三一部队医学犯罪的历史,那么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纠葛也必然给现实交往带来隐患和挑战。对中日两国来说,二战历史承载着两个国家的记忆,也同样面对着国民集体无意识的现实困境。如何看待中日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学术界关心的话题,也是我们未来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逃避和回避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现实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源于历史记忆的明显偏差以及现代叙事的迥然有别。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一贯采取不反思、不回应、不面对的消极态度,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不断强调“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双方之间既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又没能创造一个可以彼此坦诚交流的对话空间,在和平与和解的道路上看不到交叉点,问题也就持续存在且越拖越久、越来越难以解决。
那么,中国和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和反思这段历史的呢?以对七三一部队的历史记忆和当代反思为例,可以将其区分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三个层面。
从个体记忆层面来看,七三一部队秘密实施了“特别移送”,将“反满抗日志士”作为人体试验“受试者”以细菌感染、活体解剖、冻伤试验等方式残害致死。随着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公开,按图索骥访寻到大量受害者遗属,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当笔者在研究中接触这些遗属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痛苦,那是失去至亲、苦苦寻找,却没有任何线索、任何希望的痛苦。他们有的人只见过父亲的照片,有的人只知道父亲的名字,有的人只记得父亲模糊的身影,有的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悄无声息地死去,至于父亲去哪儿了、父亲是死是活,他们却一无所知,甚至因为不知道父亲去哪了,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或政治迫害。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对二战历史的记忆多已渐渐淡忘,但像王亦兵、李凤琴、敬兰芝等人体试验受害者家属,在他们的心中,战争并没有结束,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和痛苦一直存在,媒体采访和对日诉讼活动使得他们有机会发出受害者的个体声音。
从集体记忆层面来看,1996年,中国民间自发组织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为开展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诉讼案调查取证。1997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组织受害者赴日开展诉讼维权活动。2002年8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虽然驳回了原告关于谢罪及赔偿的诉讼请求,但是首次判定了侵华日军曾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并且承认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人体试验和细菌战受害者的个体记忆构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集体记忆的核心部分,并在对日诉讼活动中不断强化了这种历史记忆与群体身份。
从国家记忆层面来看,全面记录七三一部队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的“记忆空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被国家认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等,七三一部队旧址也进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多次支持七三一部队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特别是近些年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等日文原始档案影印出版,既是史证挖掘的重要贡献,也是真实历史记录的现代重现。因为历史记录是历史记忆的核心基础,所以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切割的密切关系。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站在维护历史、尊重人权的基点上,对七三一部队“反人类暴行”的历史记忆,贯穿了个体、集体、国家三个层面,诠释了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理解和对现实的期待。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仍在不断地强化,无论是面向学生群体的学校教育,还是面向全社会的具体实践,如每年9月18日的防空警报,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些国家层面的反思和实践活动都影响着中国人对二战历史的理解、书写和传播。然而,关于二战时期的医学暴行,相较奥斯威辛的历史记忆和国际传播,毋庸讳言,我们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现实差距,这需要更长时间的坚守和努力,也需要更广空间的传播和影响。不宁唯是,关于七三一部队医学暴行的历史记忆更多地局限于中国境内,对于国际主流社会的认知和触动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笔者认为,可以将犹太人和德国作为可资借鉴的“他者”,立足真实的、准确的、客观的“医学暴行”史实,首先应该影响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历史认识,其次推动欧美国家的社会认知,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最广泛的历史记忆,当是一条通向“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