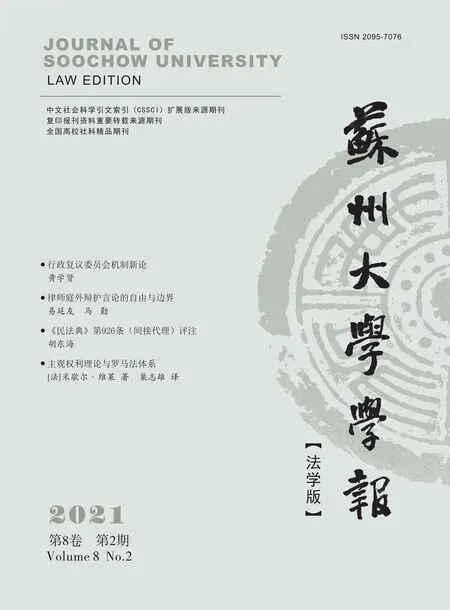刑事被追诉人阅卷权研究
邵奇聪 宋维彬
一、引言
刑事被追诉人阅卷权存在“检阅卷宗”与“证据开示”两种立法模式。前者建立的“检阅卷证权”(Akteneinsichtsrecht),乃大陆法系卷证并送制度下,辩方据以检阅控方卷宗与证物的权利。(1)参见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77页。二者均使被追诉人能在审前获悉控方证据,本质上为两种诉讼模式下,控方资讯向辩方流动的两条路径。在证据开示模式下,被追诉人是阅卷权的当然享有者;而在检阅卷宗模式下,阅卷权曾被视为辩护人的固有权,但该观点已被扬弃。目前,建立被追诉人阅卷权是各国的普遍共识。
不论何种立法模式,被追诉人阅卷权均体现三种价值。(2)Daniel S. McConkie, The Local Rules Revolution in Criminal Discovery, 39 Cardozo Law Review 59, 66 (2017).一是程序正义:阅卷权能弥补被追诉人的资讯劣势,使之有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准备辩护,因而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内涵。二是实体真实:阅卷权可提升辩方实力,促使控辩双方进行平等、充分、有效的对抗,从而揭示真相。三是司法效率:阅卷权将使负罪者意识到追诉的不可逃避,因而倾向于认罪;阅卷权也能帮助辩方明晰案件争点,减少诉讼拖延。同时,被追诉人阅卷权具有两项特性。一是兜底性:阅卷权使被追诉人不论有无律师协助,均能获悉案件资讯以自行辩护,因此是最低限度的保障。二是能动性:阅卷权可激发被追诉人的主体意识,使其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协助辩护人进行诉讼准备,亲自决定辩护的最终方案,掌握自身诉讼命运。
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能够有效提升其辩护能力,保障控辩平等对抗。因此,法治发达国家纷纷确立了被追诉人阅卷权,并且不断对权利范围进行扩张。然而我国立法却几近空白,理论研究亦有待深入。被追诉人阅卷权的价值与特性决定了其不可被替代,而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其缺失必将引发短板效应与连锁反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但被追诉人的处境始终未有改善,其诉讼权利不断增多,却又频繁被架空。实践中,被追诉人依然容易受威胁、引诱、欺骗;无力对逮捕进行争议;仍要扮演控方证人,并在诉讼中被迫成为消极待审的客体;面对控方的“打包举证、摘要宣读”,被告人不仅无法“有效”质证,甚至连获悉其被指控的证据都存在障碍,极易引发冤假错案(3)“中国冤假错案网”收录的180余起案件中有逾50起共同被告案件,其中绝大多数为法官错误采信同案犯或证人的虚假庭外陈述所致。在这些案件中,被告人因无权获悉证据和准备辩护,想质证却无能为力。。可以说,被追诉人阅卷权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障碍。鉴于此,本文将从被追诉人阅卷权的理论基础导入,重点对两种立法模式进行比较与选择,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构建被追诉人阅卷权的思路。
二、被追诉人阅卷权的理论基础
控辩平等理论、有效辩护理论与程序主体理论,是被追诉人阅卷权的理论基础。三者紧密联系、互为保障,从其中任何一项理论出发,最终均可推出被追诉人阅卷权。
(一)控辩平等理论
控辩平等理论要求赋予两造对等的攻防手段,使二者能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进行对抗与合作。(4)Brandon L. Garrett, Judging Innocence, 108 Columbia Law Review 55, 96 (2008).因此,被追诉人阅卷权也是平衡控辩资讯,促进二者平等合作的重要保障。
(二)有效辩护理论
有效辩护理论以公平审判为目标,要求赋予被追诉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以保障辩护的有效性。被追诉人阅卷权就是实现有效辩护的途径之一。其基本逻辑是:质证的有效性决定辩护的有效性,但因庭审时间局促,辩方很难在控方举证后立刻进行有效的辩护,所以要实现有效辩护,就必须为辩方提供适当的时间和机会进行诉讼准备。从理论上看,提供“适当机会”(adequate facilities)有两种方式:一是允许辩方在控方提出证据后,要求延期审理以获取准备时间,但可能导致诉讼拖延和法官心证模糊,故集中审理原则对此有严格限制,仅将其作为例外性规定。二是允许辩方提前获悉控方证据,使辩方有足够的时间发现证据漏洞,并有针对性地准备反证,此即阅卷权。鉴于被追诉人有自行辩护的需求,故赋予被追诉人该项权利,使之能自主进行辩护准备,此即被追诉人阅卷权。
(三)程序主体理论
程序主体理论要求将被追诉人作为程序的主体来对待,保障其在诉讼中的人格尊严以及在关涉个人基本权益事项上的影响力与选择权。被追诉人阅卷权就是强化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的方式之一。其基本逻辑是:被追诉人的影响力与选择权以理性认知与自愿决策为基础;由于被追诉人在不了解控方证据的情况下易受威胁、引诱、欺骗等影响,(5)参见陈学权:《论被追诉人本人的阅卷权》,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第109页。因此,要保障其程序主体地位,就必须在涉及基本权益事项的处分时,向被追诉人提供充足的控方资讯,以便其理性、自愿地处置自身利益,此即被追诉人阅卷权。程序主体理论不仅能导出该权利,还能驳斥两项经典的反对理由:一是“阅卷将影响供述的真实性”,这显然是将被追诉人作为提供证据的客体,而非行使辩护权的主体,严重违反了程序主体理论,故不成立;二是“辩护人享有阅卷权,故被追诉人无须阅卷”,这是将辩护人当作了程序的主体,并挤占了被追诉人的自主决定权,明显违背了程序主体理论,故不成立。
三、被追诉人阅卷权的两种模式
被追诉人阅卷权有两种立法形式,分别为大陆法系的检阅卷宗模式,与英美法系的证据开示模式。(6)Stefan Trechsel,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2-228.两种模式随着法系的融合而互有吸收,但并未完全趋同。为此,本文将深入考察二者,供未来我国立法选择与借鉴。
(一)检阅卷宗模式
检阅卷宗模式确立了检阅卷证权,即狭义的阅卷权。目前采行该模式的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其中以德国为代表。
1.德国的检阅卷宗模式
德国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导源于听审请求权。(7)该法第147条第7款已于2018年初废止。新修第4款在吸收原第7款部分内容后对被追诉人阅卷权进行了扩张,并配合电子卷宗的使用。即允许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自行阅卷。
就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范围,相关规定可分为:原则允许、例外限制、不得限制三个层次。
(1)原则允许。原则允许检阅的卷证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第1款所称“移送法院的案卷”与“官方保管的证据”,即通常意义上的本案全部卷证,系听审请求权的应有之义。二是依据《司法法通则》第23条请求查看的控方在调查后认为无价值而未记入卷宗的案件线索,即线索证据(Spurenakten)。(8)Vgl. Lutz Meyer-Gossner, Strafprozessordnung, 48 Aufl. 2005, § 147 Rn. 40.三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分案决定前的全部卷证,以及分案决定后形成的与本案相关的卷证,即共犯卷证。
(2)例外限制。例外限制检阅的卷证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危及侦查目的之卷证。所谓“危及侦查目的”,是指可能对侦查造成威胁,比如导致证据灭失、被追诉人逃避侦查等。该威胁不要求现实发生,但应当有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二是与第三方优势利益相抵触的卷证。所谓“与第三方优势利益相抵触”,是指对他人的隐私、人身安全,商业秘密等构成威胁,(9)Vgl. Reinhart Michalke, Das Akteneinsichtsrecht des Strafverteidigers-Aktuelle Fragestellungen,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NJW 2013, S. 2336.三是证人的住址与身份信息。对此,该法第68条规定,在危及证人或他人法益时,可以不公开证人的住址及身份;相关信息由检察院保管,仅在危险解除后装入卷宗。若有必要,该项限制不限于侦查阶段。四是卧底的身份信息。对此,该法第96条与第110b条规定,若公开身份将危及卧底及他人的生命、身体及自由,或将影响继续任用卧底,或将损害国家利益时,可以禁止公开。若有必要,该项禁止可持续适用至审判期间。由于《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规定阅卷权的起止时间,因此被追诉人原则上自侦查阶段即享有阅卷权,而实践中辩方在不同诉讼阶段的阅卷范围便受上述限制事由调整。
(3)不得限制。不得限制检阅的范围,包括特权文书与申请羁押的材料。所谓特权文书,即《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第3款规定的,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准许辩护人在场或者本应准许其在场的法院调查活动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而申请羁押的材料,系该法第147条第2款所称,对判断剥夺自由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理论上认为,控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的全部卷证都属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10)BVerfG NJW 2006, 1048 (1049); BGH NStZ-RR 2008, 16, 17.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对羁押审查中的阅卷权有较周密的保障。首先,《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0条第1款第4项将待审羁押列为指定辩护事由,使被追诉人能在律师的协助下行使权利。(11)Vgl. Werner Beulke/Tobias Witzigmann, Das Akteneinsichtsrecht des Strafverteidigers in Fällen der Untersuchungshaft, NStZ 2011, S. 254, 259.再者,司法审查随羁押状态的延续而持续进行,辩方的阅卷范围也将随之扩大。最后,控方限制阅卷还将产生类似证据禁止的效果,相关证据在此后的羁押审查程序中不得再用。
关于阅卷争议的裁决,《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第5款规定,侦查程序及程序生效终结后的阅卷争议,由检察院裁决,除此之外均由审判长裁决;若检察官在案卷中注明侦查结束后仍禁止阅卷,或拒绝提供特权卷证、申请羁押的卷证,或被追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相关阅卷争议均可申请法院裁决。该款实际上是以起诉为界,将起诉前的阅卷范围交由检察院裁量,而将起诉后的阅卷争议交由法院裁判。同时,为制约检察院的裁量权,保障辩护权,对被追诉人在押或涉及特权卷证、申请羁押卷证等内容的争议时,允许向法院申请裁判以获得救济。
德国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运行良好。通常情况下,辩方在起诉后即可全面阅卷。起诉后,由于法官需要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还会进行补充调查。因此从起诉后到开启主审程序往往会间隔数月乃至更久,故辩方有充足的时间阅卷。(12)Thomas Weigend & Franz Salditt, The Investigative St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Germany, in E. Cape, J. Hodgson, T. Prakken & T. Spronken, eds., Suspects In Europe: Procedural Rights at the Investigative St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sentia Antwerp-Oxford Press, 2007, p. 132.此外,辩方还可请求法院收集证据。总体而言,被追诉人阅卷权在德国刑事辩护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
2.奥地利的检阅卷宗模式
奥地利是法治发达国家,曾对欧洲宪政产生极大影响。该国被追诉人阅卷权也采行检阅卷宗模式,且立法水平较高。《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51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查阅提交给警察、检察机关和法院的侦查和主审结论。只要不妨碍侦查,阅卷权也包括亲眼查看物证的权利”。即被追诉人阅卷权始于侦查阶段,并贯穿诉讼全程。而阅卷权限制事由为该法第162条所称“会使证人本人或第三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完整性或自由面临重大威胁”。该国被追诉人与辩护人的阅卷地位等同,但该法第57条第2款规定,被追诉人的阅卷权由辩护人行使。值得一提的是,被追诉人通常须依申请获得案卷副本,并要支付相关费用,但对于法律援助、涉及羁押事由、鉴定结果和鉴定书的案卷副本可免费获得。此外,如果是法律援助案件,案卷将依职权送交给辩护律师。总体而言,奥地利的阅卷权制度较为成熟,从权利告知开始,及至阅卷权行使中的申请启动、限制事由、阅卷时间、阅卷方式、救济途径,到阅卷权实现后产生的保密义务等环节都有较高的立法密度。但遗憾的是,《奥地利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被追诉人与辩护人同等的阅卷地位,比德国法更先进,但还是让辩护人代行阅卷权,未彻底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性。
(二)证据开示模式
证据开示模式建立的是“发现证据权”,属于广义的、功能意义上的阅卷权。事实上,证据开示包括“控方向辩方提供证据信息”和“辩方向控方提供证据信息”两组制度,其与“控方允许辩方查看卷宗”的阅卷权存在制度结构上的差异。同时,英美法系的检察官并不制作卷宗(Akten)而是持有案件档案(case files),即证据信息载体与阅卷权制度也不相同。但在以德国2017年修法为代表的欧洲电子司法改革之后,阅卷权概念已经从传统的“检阅卷宗、证物权”扩张为广义的“查看以电子数据等为载体的证据信息权”。(13)德国刑事司法系统将于2026年彻底停用卷宗,目前仍处于过渡期。在2018年生效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阅卷权条款中,被追诉人查看电子文件已是原则性规定,而查看卷宗副本属于例外情形。因此,证据开示制度中的“辩方发现证据权”可以被纳入阅卷权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考察。
目前采行证据开示模式的有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日本等,其中美国是证据开示制度的代表国家。从名称来看,证据开示似乎是一项义务性规范,但这是我国学者翻译了“Disclosure”(开示)的结果。而实际上美国学者通常使用“Discovery”(发现)一词,并习惯从“Right of Discovery”(发现证据权)的角度展开研究。(14)Ion Meyn, Discovery and Darkness: The Information Deficit in Criminal Disputes, 79 Brooklyn Law Review 1091, 1101 (2014).“辩方发现证据权”与“控方开示义务”实为一体两面,本质上并无区别。
1.美国的证据开示模式
美国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宪法基础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15)Brady v. Maryland, 373 U.S. 83(1963).法律依据则为五十二个司法管辖区域各自的立法。但不论各法域的制度如何独立,均承认被追诉人为阅卷权的主体。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a)款规定,“根据被告人申请”控方开示证据;《俄亥俄州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A)款规定,“根据被告人的要求启动发现程序”。由于美国的被追诉人与律师之间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因此阅卷权必然属于被追诉人,律师则基于代理人身份而分享该权利。事实上,就阅卷权区分被追诉人与辩护人的做法,只可能存在于大陆法系。因为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律师负有客观性义务,需对正义负责。而英美法系“当事人至上”(client-first)的律师职业伦理,则显然排斥类似设置。鉴于美国多法域的特点,为方便研究,本文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立法模型。即《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模型,与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开示及陪审审判标准》模型。通过对比二者,可大致了解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全貌。
(1)《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模型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的证据开示范围较窄,(16)Andrew Smith, Brady Obligations, Criminal Sanctions , and Solutions in a New Era of Scrutiny, 61 Vanderbilt Law Review 1935, 1941 (2008).通过对比可知,《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所界定的“重要性”,比Brady法则的“重要性”范围略广。实践中基于Brady法则所能获悉的证据范围极小,因而美国学界对此批评不断。
除了需要开示的证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还规定了三类无须开示的证据,分别为:属于控方工作成果的工作报告、备忘录或其他政府内部文件;预期的控方证人所作的陈述;大陪审团的文件。其中“控方证人所作的陈述”仅允许在审前限制开示。该法第26.2条规定,证人进行法庭陈述后,辩方就可以在具备相关性的范围内要求开示,以便弹劾当庭证言的证明力;(17)Erwin Chemerinsky & Laurie L. Levenson, Criminal Procedure, Aspen Publisher, 2008, p. 617.假如控辩双方对相关性存在争议,还允许法官在录像存证的情况下,秘密审查证人的先前陈述,以决定是否提供给辩方检阅。
关于证据开示的争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d)款(2)项规定了四类解决方式:一是直接命令开示,或限定时间、地点、方式进行开示,或规定适当的期限和条件进行开示;二是延长同意期审理;三是禁止出示未开示的证据;四是根据情况签署其他适当的命令。其中“适当的命令”包括:宣布审判无效、(18)United States v. Rodriguez, 496 F.3d 221, 228 n.6 (2d Cir. 2007); United States v. Graham, 484 F.3d 413, 416-17 (6th Cir. 2007) .指示陪审团推定事实、判处藐视法庭罪、驳回起诉等。此外,该法第26.2条(e)款规定,对于未开示的证人陈述应从记录中删除;若检察官未执行法庭的命令,出于司法公正的需要,应宣告审判无效。
(2)《刑事司法开示及陪审审判标准》模型
美国律师协会拟定的《刑事司法开示及陪审审判标准》虽非实定法,却是许多州立法时参考的蓝本。该标准下的证据开示范围较大,是立法模型中开放的代表。该标准规定,证据开示应在审前特定且合理的时间内进行,(19)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 Discovery and Trial by Jury §11 (AM. BAR ASS’N 1996).控方的开示范围包括:被告人(含共同被告)所有的相关陈述;控方已知能就指控罪行提供资信之人的姓名、住址及其陈述;控方和准备传唤的证人的一切关系,及双方达成的任何约定;所有相关的专家报告或书面陈述,检验及测试结果,审判时将传唤的专家证人之意见、依据、预定证词之内容、个人简历等;任何与案件有关,或自被告处取得,或属于被告的实物证据,并应指明哪些将在审判中使用;被告及共同被告的前科记录,及任何与列队辨认、图像辨认或声音识别有关的材料、文件或信息;所有能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材料或信息等。此外,控方还应开示其准备使用的品格、声誉证据之内容及意图,以及与实物证据之搜查、扣押相关的文件、材料等。
《刑事司法开示及陪审审判标准》还规定了限制控方开示的五类内容:一是有关法律研究或记录、往来书信、报告或备忘录中所包含检察官或辩护人,或其他法律团队成员之意见、理论或结论;二是秘密证人的身份信息;三是开示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证据;四是开示后将导致他人受伤,或导致出现恐吓、胁迫或贿赂等实质风险的证据;五是被告任何抗辩之联络内容,或依据其他相关法律应当保密之证据。其中,第二类、第三类证据应当在听证或审判时开示。而第四类证据只有经法院权衡后方可免于开示,具体裁量标准为:开示的实质风险是否超过开示的有用性。
《刑事司法开示及陪审审判标准》规定了开示争议的裁决手段。此部分与《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基本相当,具体包括:命令开示;延期审理;禁止传唤证人或提出未开示的证据;根据情况签署其他适当的命令。
(3)全美各法域证据开示立法现状
通过对比上述两种立法模型,可大致了解美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总而言之,一般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均起始于起诉后、审判前的阶段,持续至审判阶段,不同司法管辖区域的差异仅在于具体日期。而主要的差别体现在证据开示的范围上。若将控方持有的全部证据分为两类:一是准备在审判中使用的定罪证据;二是不准备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其中,第二类内部又包括:有利被告的证据,和似乎对双方都没有意义的证据。至于不同司法管辖区域的差异,就第一类证据而言,是究竟向被告开示哪些定罪证据,比如是否开示证人、共同被告人的陈述。就第二类证据而言,是对于开示有利被告之证据有无限制,及限制程度如何,如是否要求具备“重要性”等。此外,对于“似乎没有意义”的证据,是仅规定不得恶意销毁,还是对被告有进一步的义务。若将上述两大类证据相加,总开示范围越小、控方义务越少,就越接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模型;而总开示范围越大、控方义务越重,就越接近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开示及陪审审判标准》模型。如果开示范围进一步扩张,控方有义务开示全部证据,则属于完全开示(open file)模型。最后,关于证据开示的争议解决机制,各司法管辖区域的立法基本相当。
目前,扩大证据开示的范围已是美国学界的主流共识,而将证据开示适用于更多的诉讼程序,可能是美国未来的立法方向,比如在认罪协商程序中建立证据开示制度。(20)Jenia I. Turner & Allison Redlich, Two Models of Pre-Plea Discovery in Criminal Cases: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73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285, 400-408 (2016).比如,基于诉讼策略,检察官可能会更早、更大范围地向被告开示证据,使之尽快考虑辩诉交易。
2.日本的证据开示模式
日本在二战后继受美国法并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其阅卷制度也由检阅卷宗模式转变为证据开示模式,因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日本的证据开示呈三阶构造:(1)消极开示阶段。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6条之13、14的规定,检察官应在审前整理程序中向被告人或辩护人开示其准备在审判期日请求法院调查的证据,包括证据文书、证物;证人、鉴定人、口译人或笔译人之姓名、住址、供述记录等。同条之15规定,若辩方对上述已开示证据的证明力存疑,且获悉卷证符合重要性、必要性及适当性要件时,可请求检察官开示证物、勘验报告、供述记录书等特定类型的证据。(2)双向开示阶段。同条之18规定,被告人或辩护人也应向检察官开示证据。(3)积极开示阶段。同条之20规定,辩方在符合关联性、必要性及适当性要件后,可以请求检察官开示与其主张相关联的证据。该阶段是辩方主动出击去发掘控方证据,与前述消极开示阶段大为不同。对于证据开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同条之25规定,法官依控方或辩方申请,对证据开示的必要性及可能产生的弊害进行权衡,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裁定开示证据。
日本证据开示制度与美国部分法域的立法有许多相似之处,诸如不确定的审前开示时间,检察官负有主动开示义务,对拒绝或限制开示证据的范围持限缩立场,以控辩双方自由开示为原则、以法官介入争议为例外等。日本证据开示制度的特点在于其并无明确的宪法性基础,而仅作为普通的法律制度存在;日本并不强调证据开示的互惠性,而是强调控辩双方各自开示证据对整理证据及争点的意义;日本学者也较少以防止证据突袭、维系控辩平衡等经典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理论分析证据开示,而是强调其能保障被告的诉讼防御权。(21)参见彭勃:《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四、阅卷权立法模式之比较与选择
检阅卷宗模式与证据开示模式系不同法律传统、文化及制度的产物,因而各有长短。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宜建立检阅卷宗模式,兼采证据开示模式的合理因素。
(一)模式之比较
检阅卷宗模式与证据开示模式最显著的差异在于阅卷主体、阅卷范围和阅卷时点,其背后是两种阅卷权立法模式的制度土壤、功能定位、运行方式与演化逻辑之不同。
1.阅卷主体之比较
就阅卷权的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而言,两种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检阅卷宗模式的发展可分为三阶段:(1)辩护律师固有权时期。20世纪40年代以前,阅卷权的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均为律师。(2)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分离时期。以德国1949年颁布实施《基本法》为界,阅卷权与听审权建立联系,其权利主体变为被追诉人,但行使权限仍归律师。这项改革具有进步意义,但被追诉人的处境与前一时期相同:要获得阅卷利益就必须聘请律师,若无律师则无阅卷权。(3)律师为主、被追诉人阅卷为补充时期。以1997年欧洲人权法院处理Foucher v. France案为界,(22)ECHR, Foucher v. France, Reports 1997 (II).法国被迫承认被告有权查阅卷宗副本,德国1999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允许被告在无辩护人时自行阅卷。从此,阅卷权成为能由被追诉人直接行使的权利,但仅作为律师阅卷权的补充,因为律师一旦介入案件被追诉人便不得行使阅卷权。目前多数法域处于第三阶段,我国则仍处于第一阶段。然而,证据开示模式自诞生以来便将被追诉人视为主体,律师分享被追诉人的权利,从未区分所谓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
差异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对律师的职能定位不同。大陆法系强调律师的独立地位与发现真实、维护司法正义之责任,典型如德国“独立司法机关”理论。律师的独立地位使其得到了司法系统的信任并获准查看卷宗;被追诉人因涉嫌犯罪而有串供灭证的动机,因此被禁止阅卷。英美法系也承认律师应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地位,但更强调其法律代理人地位与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由于被追诉人与律师形成了攻守同盟与主雇关系,因此律师查看控方证据的权利来自委托人而非法律授予。(23)此处所称“授予”乃法理意义上的正当性来源,实定法中往往会同时授权给被追诉人和律师。若厘清两种模式的制度土壤就会发现,以“辩护权源自被追诉人”的英美法理论批判“律师独占阅卷权”的传统大陆法理论并不太合理:大陆法系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存在冲突,因此法律允许律师阅卷但禁止被追诉人阅卷;若强行代入英美法理论求解,则不仅无法从律师阅卷权中推出被追诉人阅卷权,反而会动摇律师阅卷权的制度基础,即司法对律师职业群体的特殊信赖。
从检阅卷宗模式的发展脉络来看,律师阅卷权与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关系格局正在变化,其背后动因是两大法系交流融合、人权理论的繁荣与区域性国际人权条约对各国法的变革。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分离便是律师阅卷权遭遇法理危机转而向被追诉人寻求正当性的标志,当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亦是西方人权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因此成为检阅卷宗模式演化的重要转折点。虽然主体分离理论未改善被追诉人的处境,却首次在理论上将其确立为阅卷权的权利主体,从而为后续改革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堪称模式演化中的“惊险跳跃”。随后四十年间,欧洲人权法院处理的Kamasinski v. Austria案、Foucher v. France案、Öcalan v. Turkey案则逐步证明了阅卷权的权利主体也应当是行使主体。其中,Kamasinski v. Austria案传达的意旨是:若法律仅允许辩护人阅卷,但被告能够通过辩护人了解卷证内容,则符合公平审判条款。(24)ECHR, Öcalan v. Turkey, RJD 2005 (Ⅳ).这意味着,让被追诉人透过律师间接阅卷而禁止其直接阅卷涉嫌违反有效辩护原则,故应允许被追诉人与辩护人共同阅卷。就此,检阅卷宗模式逐步从“律师中心”走向“被告本位”。
2.阅卷范围之比较
证据开示模式的阅卷范围小于检阅卷宗模式,其原因在于:英美法系为确保法官的消极中立与空白心证而采卷证不并送制度,所有证据均由当事人在审判时提出,导致国家刑事侦查力量所获全部证据被检察官一手掌握。而当事人主义的检察官无客观义务、无公益色彩,其作为控方当事人的任务就是与辩方充分对抗,以此推动审判程序并促进真实之发现。鉴于证据开示会使辩方提前获悉控方证据并做好防备,因此检察官不愿在庭前向辩方开示证据;相反,检察官喜欢以证据突袭提高胜诉率,或是隐藏有利被告的证据来让法庭相信其指控。各方博弈之下,法定证据开示的范围较小,通常限制或禁止开示以下证据:证人身份信息;证人证言;证人前科记录;大陪审团记录;警察报告;科学检验报告;电子监视信息等。(25)Bruce A. Green, Federal Criminal Discovery Reform: A Legislative Approach, 64 Mercer Law Review 639, 639-642 (2013).
与英美法系不同,大陆法系虽承认控辩对抗的意义,但更相信法官依职权调查的结果,因此要求控方客观、彻底地收集证据并全案移送给法官,再由法官庭前阅卷、指挥诉讼、作出判决。职权主义的检察官扮演了法官助手的角色,即便其行使控诉职能也负有客观义务和诉讼关照义务,而将卷宗提供给辩方查阅便是义务之一。对此,检察官不仅无权任意限制辩方阅卷,反而要配合并提供相应的便利。再换个角度看,由于控方卷宗最终都要移送法官,因此检察官其实只是卷宗的临时占有人,即便其有意限制辩方阅卷也只能暂时为之,毕竟辩方在审前仍然可以去法院阅卷并准备诉讼。
全面阅卷比部分开示更优。日本在二战前后曾分别建立检阅卷宗模式与证据开示模式,可谓最佳例证:首先,改采证据开示模式使辩方在审前获悉的证据大幅减少,严重削弱了辩方的诉讼防御。其次,日本实务中出现了迈拉利案、大阪特搜部主任检察官窜改证据事件、足利事件、布川事件等一系列因检察官未尽开示义务甚至隐匿重要物证导致的冤假错案。最后,证据开示程序烦琐,遇上新证据就必须重启开示程序,而部分开示又容易使控辩双方互相猜忌对方是否隐匿证据,迫使法官频繁介入程序争议,导致诉讼时间延长近三四倍。对此,日本被迫修法,包括将开示时间从证据调查程序提前到审前整理程序;扩大证据开示范围;承认证据开示请求权;规定法院的证据开示命令并允许当事人复议等。(26)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62-363页。目前,日本学界意识到部分开示的种种弊端,因此正在讨论完全开示的相关议题,其改革趋势已现。
事实上,完全开示已被美国北卡罗纳州、得克萨斯州等法域采纳,并成为证据开示模式的最新动向。虽然反对派始终强调证据开示的负面影响:诸如存在毁灭、伪造证据的风险;导致证人、被害人受威胁;被追诉人已受无罪推定和沉默权之保护,而证据开示将打破控辩平衡等。(27)Andrew D. Leipold, How the Pretrial Process Contributes to Wrongful Convictions, 42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1123, 1151-1152 (2005).换言之,在阅卷范围的问题上,证据开示模式正朝着全面阅卷的方向演化。
3.阅卷时点之比较
检阅卷宗模式的阅卷时点早于证据开示模式,原因有二:第一,证据开示与检阅卷宗的职能定位不同。英美法系采陪审团审判制,为实现诉讼经济并节省陪审员的时间而建立证据开示,使控辩双方在审前交换证据信息、缩小争点范围以加速审判。换言之,证据开示是审前整理程序之一,其时点只需早于审判且足以让被告准备辩护即可,若过度提前开示只会增加被告串供、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的风险。而大陆法系由职业法官庭前阅卷、指挥诉讼、集中审理,并无英美法系所谓诉讼效率低下、更换陪审员等问题,因此建立阅卷权旨在为辩方提供获悉证据并准备诉讼的机会。相应的,检阅卷宗模式的阅卷时点较为自由,诸如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均承认侦查阶段的阅卷权。第二,证据开示与检阅卷宗的制度运行成本不同。证据开示本质上是对抗程序,控辩双方在此期间的对抗程度不亚于审判环节,若无法官介入就会陷入僵局或程序失衡,注定成本极高而只能围绕审判程序建立。相反,检阅卷宗模式得益于控方的客观义务与公益色彩,阅卷程序通常只有两步:辩方主张阅卷权,司法机关依职权提供卷宗。就此,极低的制度运行成本使阅卷权能前置到侦查阶段。
阅卷时点通常仅针对审判而言,但有阅卷必要性的其实还包括羁押审查和认罪协商程序。在羁押审查程序中,两大模式均承认被追诉人有权查看控方申请羁押的证据,以便被追诉人对羁押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在认罪协商程序中,二者差异较大:由于检阅卷宗模式的阅卷时点较早,因此被追诉人通常能在认罪前充分了解控方证据,从而自愿、理性地参与认罪谈判。相反,证据开示模式面向刑事审判构建,其法定开示时间通常晚于辩诉交易,导致被追诉人要在未获得证据开示的情况下进行“黑箱式”辩诉交易,极易引发冤假错案。(28)Lucian E. Dervan & Vanessa A. Edkins, The Innocent Defendant’s Dilemma: An Innovative Empirical Study of Plea Bargaining’s Innocence Problem, 103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1, 34 (2013).同时,证据开示模式假定所有受限制或禁止开示的证据将在审判时被提出,但案件一经辩诉交易就不再审判,导致被追诉人无从知晓自己因何种证据被定罪。以美国纽约州为例,辩诉交易解决了其97%的案件且多数发生在起诉前,导致审前证据开示几乎被架空。而研究报告显示,虽然检察官在证据充分时会自愿开示以促进认罪,但经常没等案件彻底查清就提出协商以节省时间,或是在证据不足时以大幅减刑优惠来诱使被追诉人认罪。无辜者有时为了避免卷入耗时费力的审判程序,或是为了避免审判的高风险,就很可能会虚假认罪。
鉴于传统的证据开示时间较晚而无法规制辩诉交易,许多法域尝试建立针对辩诉交易的开示制度,典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该州要求检察官必须在辩诉交易前全面开示以下证据:证人的姓名、地址、生日和陈述;被告和共同被告的陈述;警察的陈述和报告,以及所有执法人员的姓名和地址;所有大陪审团记录;所有当事人和证人的犯罪记录;任何可资辩护的事实。不难预见,随着辩诉交易在英美法系的进一步扩张,证据开示模式的重心将从审前走向认罪前。而随着大陆法系国家陆续展开参与式侦查程序改革,(29)Vgl. Wolfgang Wohlers, Das partizipatorische Ermittlungsverfahren: kriminalpolitische Forderung oder “unverfügbarer” Bestandteil eines fairen Strafverfahrens?, GA 2005, S. 11 ff.大量的辩护权被前置到侦查程序。为配合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的质证,未来检阅卷宗模式的阅卷时点也将更充分地前置到该阶段,否则简化审判的目的恐将难以实现。
(二)我国之选择
我国宜建立检阅卷宗模式,兼采证据开示模式的合理因素,理由如下:
首先,我国的制度环境与检阅卷宗模式更契合,原因有三:第一,我国是职权主义国家,采行全案移送制度,因此有贯穿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并为各方所共同使用的卷宗。而检阅卷宗模式正是以此为基础,赋予被追诉人对卷宗的查看权与检视权。第二,我国刑事诉讼强调国家主导,司法机关应向被追诉人提供辩护所需的基本条件。而检阅卷宗模式也带有显著的公益色彩,强调司法机关在辩方请求阅卷时的配合义务。第三,我国现行的阅卷权制度允许辩护人查看控方卷宗,若建立检阅卷宗模式下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则二者可以兼容。
其次,司法改革的经验表明,我国不适合发展证据开示模式。证据开示模式以起诉状一本主义为基础,而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建立的复印件移送主义,就是向该制度的转变。但我国法官主导审判并依职权调查证据的传统与之冲突,迫使1998年《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建立了庭后移送案卷制度,导致此前改革失败;2012年《刑事诉讼法》则彻底回归案卷移送主义。另外,我国也曾尝试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因为证据开示的范围较小且程序复杂,既不能满足辩方所需,又给法官造成了额外负担。而证据开示程序本质上为对抗程序,但在我国法官不愿介入,且控辩双方缺少对抗经验的情况下,制度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再者,我国建立检阅卷宗模式的资源压力较小。因为检阅卷宗模式以控方履行配合义务为主,阅卷程序相对简单。所以被追诉人能独立行使阅卷权,对律师辩护率的要求较低。而证据开示模式的阅卷程序较为复杂,且对抗性强。若无辩护人协助,被追诉人将很难获悉证据,因此要求较高的辩护率。目前我国律师资源紧缺,因此适合选择检阅卷宗模式。此外,证据开示模式要求法官频繁介入,以便对裁定内容进行个案权衡,因此对法官资源的消耗远超检阅卷宗模式。而在我国基层法院人少案多的情况下,建立证据开示模式必然加剧法官资源的匮乏,导致案件积压等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宜采行检阅卷宗模式。
最后,吸收证据开示模式的合理因素,能弥补检阅卷宗模式的不足。检阅卷宗模式倾向于限制被追诉人的行使权限,但并无充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证据开示模式允许被追诉人享有并自主行使阅卷权,更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与辩护权,对此我国应予以采纳。同时,关于阅卷权争议,证据开示模式拥有更成熟的裁判标准与裁判手段,能合理平衡各方诉求,因此值得我国立法时作为参考。
五、我国被追诉人阅卷权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但在客观上为阅卷创造了机会。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被追诉人阅卷的尝试,反映了被追诉人、律师、公安司法机关等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的态度,展现了未来我国立法的某些可能。
(一)我国未确立真正的被追诉人阅卷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即法律允许辩护律师在单独会见时,向被追诉人核实证据。由于辩护律师享有阅卷权,而核实证据必然涉及案卷内容,这使被追诉人可借此获悉控方资讯。因而有学者认为,该法条实际上承认了被追诉人的阅卷权。
但本文认为该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就立法技术而言,“核实有关证据”的规定位于《刑事诉讼法》第39条,而该条5款全部是关于辩护人会见权的。根据常理,其中不可能规定被追诉人阅卷权。(30)参见朱孝清:《再论辩护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46页。最后,就解释论而言,该款的文义是“律师可向被追诉人核对证据的真实性”,若要得出“被追诉人有权检阅案卷”,则必须对核对、证据、主被动关系等一系列概念作扩张解释,而这是值得讨论的。
退一步来说,纵然能从“核实证据”解释出阅卷权,这种权利也存在重大缺陷。因为其行使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有辩护律师;二是辩护律师已经阅卷;三是辩护律师主动会见;四是辩护律师在会见时愿意“核实证据”。然而仅以我国目前的辩护率,大部分被追诉人尚不具备第一项条件。而即使在有辩护人的案件中,律师不阅卷、不会见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尤其是“高成本、低收益”的法律援助案件。再者,“核实证据”也有风险,(31)参见韩旭:《辩护律师核实证据问题研究》,载《法学家》2016年第2期,第120页。不少律师担心控方以律师伪证罪等名义,对其进行报复性追诉,因而视核实证据为畏途。由此可见,该权利的实现高度依赖律师的个人选择,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此外,法谚有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然而“阅卷权”本身尚无明文规定,更不会有救济途径。总而言之,即便被追诉人因“辩护律师可以核实证据”的规定,在客观上获得了接触卷宗的权利,但该权利在正当性、可操作性、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被追诉人阅卷权。
(二)我国实务中有被追诉人阅卷的尝试
我国法律虽未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但实务中却有阅卷的尝试。与惯常直觉不同,被追诉人其实能通过侦查人员获悉卷证。因为在实践中,获取口供是提高破案效率、降低侦查成本的最佳方式,而多数嫌疑人不会自愿坦白,一些惯犯更是“有多少证据,认多少案子”,所以侦查人员必须披露证据使之“松口”。常见的披露步骤为:(1)出示个别证据,引嫌疑人作出陈述;(2)出示与该陈述矛盾的证据,并要求嫌疑人作出解释;(3)出示新的证据,产生新的矛盾,并要求新的解释,如此循环。在这种逐步“叠加”证据的讯问中,嫌疑人会作出多个版本的供述,其中往往有细节冲突。侦查人员常能借此破案,而嫌疑人也在讯问中得以接触卷证。此外,侦查人员有时会主动向嫌疑人核实证据,以避免错案。当然,本文并非试图将随机性披露附会为阅卷权,其本质上类似于英美法系的检察官任意性开示:不仅不是被追诉人的权利,反而是追诉手段;侦查人员披露的证据不仅零碎,甚至可能是虚假的。本文考察随机性披露的实务旨在反驳将侦查阅卷“妖魔化”的观点,即允许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接触卷证未必会有毁灭性后果;相反,在许多情形下往往能促进破案乃至认罪。
实践中,因嫌疑人接触卷证而影响侦查,或导致第三方利益受损的情况很少出现。因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特殊利益的案件基数很小,而侦查人员有丰富的披露经验,对披露时机、内容、方式等都有较好的把控。就披露范围与方式而言,物证、书证、视听资料通常可以直接向嫌疑人出示;鉴定意见会依法告知,并允许阅览;(32)参见宋维彬、邵奇聪:《对笔录证据过度适用的规制》,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22期,第79页。除非侦查时需要嫌疑人到场并签字,否则嫌疑人通常不会接触此类笔录。当然,诸如辨认笔录中的辨认结果,侦查人员仍会择情披露。总言之,虽然侦查人员披露证据是为了实现侦查目的而非保障辩护权,但也表明:在许多情形下,被追诉人接触卷证的程序阻力并非大到力不能及,因而必然存在总结侦查实践规律,并予以制度化的可能。
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直至审判阶段,被追诉人也有可能通过辩护律师接触卷证。目前我国辩护律师阅卷已经不存在障碍,并且各地看守所都设立了专门的会见室,供辩护律师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会见被追诉人。因此,实践中有些律师会携带相关案卷材料进行会见,(33)参见陈瑞华:《论被告人的阅卷权》,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第127-128页。有的被追诉人还会主动要求查看案卷材料。虽然这种尝试受地区、案件类型、控方态度、律师个人因素等影响,尚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各方形成了微妙的平衡。检察院在无翻供串供、毁灭证据、威胁证人等风险时,会默许被追诉人接触一些案卷材料;尤其是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司法机关对被追诉人接触案卷的态度可能更为宽容。而律师在执业时也会尽量降低阅卷带来的风险,比如对提供阅览的案卷材料进行筛选,或是自行整理制作会见使用的材料,对个别敏感信息采用问答的方式核实等。事实上,就北京市的法院系统来看,第二和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都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被告阅卷,以便提高庭审效率。当然,由于缺乏规范层面的认可,这种做法仍是因地而异的。
透过上述现象,本文认为:建立我国的被追诉人阅卷权,或许并非太过大胆的假设,而是司法文明的必由之路。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阅卷权的制度供应已严重滞后。对此,我国应尽快将被追诉人阅卷权纳入法治化进程。
六、我国被追诉人阅卷权之建构
我国应建立贯穿诉讼全程的被追诉人阅卷权,阅卷范围原则上为全部卷证,仅在侦查阶段允许例外限制。就阅卷权的实现路径而言,立法宜区分侦查、审查起诉与起诉后三个阶段,并根据其特征做具体规划。为保障阅卷权的行使,未来还应建立完善的争议裁决机制。而该机制的核心是裁决者、裁决标准与裁决手段。
(一)被追诉人阅卷权的阶段范围
根据有效辩护理论,被追诉人在面临重大权益的处分前,有权进行必要的辩护准备。因此,不论各国采行何种立法模式,均承认被追诉人在审判前阅卷的必要性。但就我国而言,建立国际最低标准显然不能满足实际所需,而至少应将阅卷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理由有四:首先,起诉是案件分流与认罪认罚的关键期,如果被追诉人无法提前阅卷,必然错过辩护的重要节点,还可能因威胁、引诱、欺骗而错误认罪。其次,我国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纠错能力很弱,对不构成犯罪、疑罪案件的不起诉比例长期在2%以下。(34)参见陈永生:《刑事冤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260页。对此,立法应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强化其在程序选择时的影响力,从而抑制不当追诉。再者,我国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隐含前提是侦查机关已完成调查取证工作,涉案证据均已得到固定和保全。因此,被追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不会危及证据安全,而随着我国配套制度的完善,被追诉人翻供串供、干扰证人作证等风险都会被降至最低。最后,我国已允许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实践中被追诉人也能借此接触卷证。立法差别对待二者,既无实际作用,反而有侵害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之嫌。
最富争议的是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但本文同样主张建立,理由有三。首先,就法理而言,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即享有程序主体地位,但辩护权却不足以对抗控诉权。根据程序主体理论、控辩平等理论与有效辩护理论,此时宜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以提升其辩护能力,平衡控辩实力差距,维护被追诉人的主体性。其次,就比较法而言,欧洲各国普遍从侦查阶段即允许阅卷,侦查中和审判中阅卷是限制事由宽严的差别。其背后逻辑是:阅卷范围系辩护必要性与限制必要性博弈的结果,但不论侦查阶段如何特殊,辩护必要性始终存在,因此侦查阶段必然有被追诉人阅卷的空间。事实上,若我国能抛弃控诉利益优先的旧观念,重新审视辩方的利益诉求,将发现侦查阶段阅卷的合理性。最后,就立法必要性而言,我国侦查阶段的羁押率极高,但在被追诉人无权阅卷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就羁押提出抗辩。同时,我国在侦查阶段已允许认罪认罚,但由于未建立被追诉人阅卷权,无辜者可能在秘密、封闭且缺乏辩护人协助的情况下而错误认罪。因此,出于对人身自由权与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应赋予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至于阅卷范围的具体规划,本文认为,原则上应允许全面阅卷,但必要时可作限制,同时法律应明确不得限制检阅的内容。对此可借鉴德国法的规定,将“危及侦查目的”和“与第三方优势利益相抵触”作为主要的限制事由,并对“证人的住址及身份信息”“卧底的身份信息”等予以特殊保护。同时,为防止阅卷权受到过度限制,应根据证据的稳定性与辩护的必要性,建立阅卷权的最低保障。比如规定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不得限制检阅,控方申请逮捕的材料不得限制检阅等。最后,阅卷范围宜从本案证据扩大到在案证据,即被追诉人不仅能查看卷宗,还可查看虽未附卷移送,但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材料。例如,看守所体检报告、讯问录音录像、现场执法记录、接处警登记表等材料,只要可能对案件处理造成实质性影响,均应允许被追诉人检阅。值得一提的是,若赋予被追诉人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后,律师自然也能行使该权利,且应同样适用前述限制事由,但在个案权衡时宜适当放宽要求,以便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利益。换言之,必要时律师的阅卷范围可以略大于被追诉人。事实上,德国、美国在涉及证人敏感信息等问题时均承认该做法,我国应当予以采纳。
(二)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实现路径
权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可操作性的影响。因此,对阅卷权实现路径的规划,需兼顾合理性、便捷性与保障性。其中,卷证完整度与卷证持有者的态度,是影响权利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阅卷权的实现又可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与起诉后阶段。
首先,在侦查程序实现阅卷权,必须解决如下问题:一是卷证碎片化。因为侦查是控方证据不断积累的过程,所以在侦查终结以前,证据材料处于零散和真伪不明的状态,既没有完整卷宗可供检阅,又没有稳定的证据目录供被追诉人参考,以确定申请检阅的对象。对此,立法宜同时建立依职权披露与依申请阅卷:规定侦查机关有义务及时以适当方式披露证据,并允许被追诉人申请查看其已获悉的卷证。二是侦查机关可能怠于提供卷证。由于侦查机关是卷证的持有者,因此阅卷权的实现必须由其协助。但侦查机关属于控方,与被追诉人利益冲突,难免不愿配合。对此宜明确规定侦查机关依职权披露证据的最后期限。此外,对于侦查机关申请逮捕的材料,可由检察院制作副本,在羁押后依职权主动提供给被追诉人查阅。
其次,在审查起诉阶段实现阅卷权,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安全、便捷地提供卷证。我国多数被追诉人受审前羁押,不能亲赴检察院阅卷;而检阅原始卷证是阅卷权的应有之义,但被追诉人对卷证安全又构成威胁。对此,宜使用电子卷宗或纸质副本替代原卷,(35)参见杨波:《被追诉人阅卷权探究——以阅卷权权属为基点的展开》,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第29页。并应在看守所建立阅卷室。无论被追诉人是否在押,若有必要,都应允许其在法警的陪同下检视证物。二是如何确保阅卷的有效性。根据有效辩护理论,阅卷应先于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方能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为防止实务中以先认罪、后阅卷的方式规避阅卷权,并减少被追诉人认罪后反悔的情形,宜直接规定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前有必要的阅卷时间。
最后,案件经起诉后,卷证的持有者从控诉方变为裁判方,被追诉人阅卷权能获得较充分的保障。故立法宜允许被追诉人到法院自行阅卷;对于受羁押的被追诉人则有权在看守所阅卷。此外,审判期间被追诉人应有权携带案卷副本参与诉讼,这是阅卷权的应有之义。
(三)被追诉人阅卷权的争议裁决
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容易引发争议,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裁决机制。而在制度设计时,应格外关注三项内容,即裁决者的中立性、裁决标准的合理性与裁决手段的有效性。
首先,裁决者的中立性决定了程序的公平性。因此裁决者的人选,以法官为最佳,检察官次之。目前我国在侦查阶段尚无司法权的介入,因此较务实的立法策略是:通过完善检警关系,明确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义务,加强其对侦查程序的控制力,从而在侦查机关与被追诉人出现纠纷时,扮演相对中立的裁决者角色。但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院成为卷证的持有者,此时若出现阅卷争议,便只能寻求司法救济。因此,未来立法时宜将阅卷争议作为开启程序性裁判的事由。同理,案件起诉后直至审判阶段,都应由法官担任裁决者。
其次,裁决标准的合理性决定了竞争法益能否达成平衡。阅卷纠纷实际上是控诉利益、辩护利益,以及第三方利益的冲突,是多元主体间的复杂博弈。因此,裁决标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将各方诉求均纳入考量;二是赋予不同利益合理的权重;三是遵循风险与利益的权衡原则(36)参见刘作凌、刘学敏:《论被追诉人本人的阅卷权》,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5期,第107页。。具体而言,立法对裁决标准的设置,应体现合理的价值取向,充分尊重各方权益,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尤其不得片面追求控诉利益;在法益权衡的方式上,只要阅卷产生的利益大于或等于其所造成的风险,就应允许被追诉人阅卷。其中,阅卷风险不仅包括串供灭证、干扰作证、侵害第三方利益等风险,还应考虑卷证信息被用于非刑事诉讼程序的危险,比如被追诉人或辩护人向媒体公开卷证信息作诉讼外抗争等。若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律师阅卷权将与之衔接成为完整的辩方阅卷权,但在裁决阅卷纠纷时仍应区分不同的主体:对被追诉人阅卷权的限制可严于对律师的限制,而律师对当事人权限外的证据有保密义务。
最后,裁决手段的有效性决定了辩护利益能否获得保障。各国司法实践中,阅卷争议的形式繁多,典型的有三类:一是阅卷权行使障碍,比如义务方拒绝提供卷证。对此,裁决应侧重协助性,以辅助被追诉人实现阅卷权为主。相应的,法律宜规定命令披露、限期披露、限定方式披露等裁决手段。二是阅卷权受规避,比如控方隐匿卷证。对此,裁决应侧重恢复性,以弥补被追诉人受损的辩护利益为主。相应的,法律宜允许延迟审理;对于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规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等裁决手段。三是拒不履行裁决结果,比如义务方怠于执行限期提供卷证的裁决。对此,裁决应侧重惩罚性,以剥夺司法机关的不法利益,导正其行为规范为主。相应的,法律宜建立排除规则,即规定拒绝被追诉人检阅的证据不得向法庭提出,亦不得作为定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