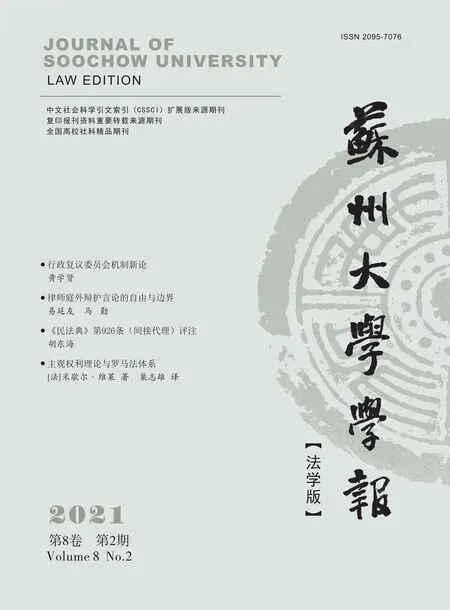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自由与边界
易延友 马 勤
引 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肖维茨曾经断言:“在权利尚未遭到侵害之前,我们总是将它视为理所当然,而当我们面临失去的危险时,我们才开始珍视它。”(1)[美]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权利本来是天经地义,但是近年来在实务上却不断遭到侵蚀,在理论上也颇有些质疑。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似乎快要失去这项权利了,尽管我们或许从未拥有过它。即便如此,本文也要不遗余力,澄清并论证它在理论上的正当性。
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更多属于刑事被追诉人辩护权的一部分。这一问题本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学术界却习惯于将其放在律师庭外言论这一更为广阔的视域加以考察。在律师庭外言论这一场域中,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职业秘密特免权、律师作为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律师不得贬损同行的职业道德义务以及律师不得做不实自我宣传的执业纪律规范等统统纳入视野。这导致一个本属于刑事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问题被与其他并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并列加以讨论。它一方面模糊了问题的核心,淡化了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也导致现有的讨论过于肤浅。为彰显问题,集聚焦点,本文仅讨论律师的庭外辩护言论,不讨论律师的其他庭外言论。
本文认为,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乃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表现,它是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律师庭外发表辩护言论的自由虽然也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但自由应当是原则,限制应当属例外。为论证此观点,本文第一部分阐明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属于宪法上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审判公开原则的必然要求。第二部分论证律师的庭外辩护言论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有一定的交叉与重合,此部分内容受言论自由原则与规则的保护与约束,但其更多内容属于辩护权的自然延伸,属于基本人权,不应限制或剥夺。第三部分是对那些以审判公正为由限制庭外辩护言论的观点进行反驳,论证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推动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第四部分在详细考察域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那些主张限制、剥夺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的观点源于对国外规则的重大误解。第五部分探讨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边界,主张按“禁区”“安全区”和“过渡区”的模式来建构规则,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选择性执法和裁量权滥用。结语部分总结全文。
一、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宪法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
(一)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界定
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基于辩护目的,为维护刑事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而在庭外发表有关其代理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司法程序等方面的言论。律师庭外言论的内容包罗万象,比如:个人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看法、对贸易战的策略、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批评建议、对司法制度的抱怨、对个别司法人员行为的指责、对法律程序或判决的不满、对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的牢骚、对同行的各种看不起,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言论中,有些属于宪法上言论自由的范畴,例如对国内外局势、大政方针、司法制度、司法公务人员所发表的看法、分析、批评和建议等。有些属于律师与委托人特免权规则调整的内容,如有关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的言论等。(2)相关法律规范如《律师业务推广行为规则》(2018)。不同的言论内容,可能属于不同的规范调整,其自由程度、约束力度等自然也就不同。
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确,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仅指律师为了刑事被追诉人的利益,出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动机,在法庭之外发表的有关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以及司法程序等方面的言论。律师基于代理刑事案件并因个案而形成的对司法制度的批评意见、对司法程序的不满、对司法裁判的失望、对司法人员的批评等,只要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发表,均属于庭外辩护言论。除此之外,律师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批评建议,以及非基于自身代理案件而发表的对司法制度、司法人员的批评等并非庭外辩护言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律师在庭外发表的称其当事人十恶不赦、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类的言论,不属于辩护言论,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
(二)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刑事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
从法理上看,辩护律师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而为其提供辩护,在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关系上,属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关系,在民法上,就是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代理人的一切行为,都要由被代理人承受后果;代理人的一切权限,也都来自被代理人。辩护律师行使的辩护权,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那些表面上只能由辩护律师享有的权利,实际上也来源于刑事被追诉人。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律师享有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这些权利本身都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由于刑事被追诉人很可能处于羁押状态,难以有效行使这些权利,法律才将这些本属于被追诉人的权利赋予辩护律师,由辩护律师本着被追诉人的利益来代为行使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未受限制,能够自如地行使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自然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妨害诉讼顺利进行、不干扰证人作证的前提下行使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至于会见权,本来就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只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将该项权利表述为辩护律师的权利而已。
如同以上所有权利一样,辩护律师在法庭内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在庭外发表辩护言论的权利,也都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由于被追诉人也许表达不够利落,或对法律不熟悉,因此,法律将法庭辩论的权利一方面保留给被告人,以方便其自行辩护,另一方面也将该项权利分配给了包括辩护律师在内的辩护人,以帮助其更好地行使法庭辩护的权利。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一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受到刑事追诉而声名扫地时,迫切需要向公众进行解释。但是,其自身的可信度已经折损,且或者身陷囹圄,或者表达能力不强,或者欠缺法律知识,因此,才将庭外辩护的权利让渡给了辩护律师,由律师这一专业群体代其行使庭外辩护的权利。无论是法庭上的辩护权,还是在法庭外发表辩护言论的权利,都来自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是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
(三)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是公开审判制度的必然要求
我国《宪法》第13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该条第一句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通常情况下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指控都是公开进行的,而公开指控就同时意味着对被告人名誉的公开贬损。在规定公开审判之后,《宪法》紧接着就规定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该原则既包含了被告人自己辩护,也包含了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无论是被告人自行辩护还是律师辩护,在公开审判的案件中也都是公开进行的。公诉机关公开指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公开辩护,就是宪法第130条之规定的完整含义。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检察官的指控既包括向人民法院的指控,也包括面向公众的指控。审判公开原则既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也包括整个诉讼活动公开。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一个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审判阶段,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则其指控就不仅起到了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的效果,而且也起到了向全体人民公开其指控内容的效果。公诉机关的犯罪指控通过在公开的法庭上宣读起诉书这一仪式化的诉讼活动得以向全社会公开。
正因为如此,律师的辩护既包括面向法院的辩护,也包括面向公众的辩护。辩护律师既要向法院尤其是合议庭法官说明其委托人并未实施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或者没有像起诉书描述的那样罪大恶极,从而争取法院的无罪判决或轻缓的刑罚;也要通过庭外辩护向全社会澄清:被起诉书描述为十恶不赦的那个被告人实际上遵纪守法、善良无辜。起诉书的内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不胫而走,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也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途径获得传播。如同检察官的战场不仅限于法院一样,辩护律师的战场也不仅限于法庭。正如一位从业多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所言:哪里有指控,哪里就有辩护;在哪里审判,就在哪里辩护;谁有权对案件作出决定,就向谁辩护。理所当然地,如果公众能够影响案件的走向,那么,面向公众辩护就是天经地义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著名的金泰尔一案中指出:“律师的职责并非始于法庭关上大门进行审判之时。他们不能无视法律程序对其委托人的实际影响。正如律师可以建议启动答辩协商或民事争端解决程序以避免审判之后可能遭受损失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一样,他当然也可以采取任何合理措施保卫其委托人的声誉并降低遭到指控这一事实对委托人的不利影响。”(3)Gentile v. State Bar of Nevada, 501 U.S. 1030 (1991).如同在其他案件中律师要维护委托人名誉一样,在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也要为其委托人的名誉而战。
刑事案件容易吸引公众眼球的性质决定了这类案件不仅是一个司法的剧场,而且也是一个司法的广场。(4)参见王露晓、张彤:《“保姆纵火案”凶手莫焕晶被执行死刑》,载《新京报》2018年9月22日,第A01版。
在法庭审判这个颇具剧场化效应的场域中,辩护律师固然要使出看家本领,拼死一搏;在面对公众这个广场化的场域中,律师更要使尽浑身解数,背水一战。如同19世纪英国一位律师所言:“辩护士出于对委托人的神圣职责,只要受理该案就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他须用一切有利手段去保护委托人,使其免遭伤害,减少损失,尽可能得到安全。这是他的最高使命,不容有任何疑虑;他不需顾忌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的惊慌和痛苦,这样做会招致的苛责以及是否会使别人毁灭。他不仅不应顾忌这些,甚至还要区分爱国之心与律师的职责,必要时就得把赤子之心抛到九霄云外,他必须坚持到底不管后果如何,为了保护他的委托人,如果上天注定必要时把国家搅乱也应在所不惜。”(5)转引自[美]艾伦·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必要时把国家搅乱也应在所不惜”的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但是利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保护委托人的说法却无疑是正确的。
二、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并不完全等同于言论自由
(一)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与言论自由权有一定的交叉与重合
穆勒在《论自由》这一名著中论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时代并不比个人更少犯错误;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意见被后世视为错误甚至荒谬,现在通行的很确定不移的意见,也将被后世所抛弃,正如一度通行的意见被现在所抛弃一样。”(6)[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律师庭外言论自由,与穆勒所赞成的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言论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是重合的。对于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有罪,是否应受法律处罚,往往也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历史上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就体现了公众对一项指控是否成立之观点的根本分裂。(7)[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人们也经常错误地认为正义虽然迟到,却从未缺席。经验却告诉我们,正义不仅迟到,还经常缺席。从这个角度来看,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不仅具有言论自由所保护的价值,并且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只不过,律师辩护言论中所包含的真理,往往不如一般真理那样幸运:一般真理可以在悠悠岁月中被人重新发现并最终成功逃脱压迫,无辜的被告人却往往在悠悠岁月中绝望地死去,而其律师庭内庭外辩护言论中所包含的关于委托人无辜的信息也将逐渐为人淡忘。
值得强调的是,很多时候辩护律师都是站在少数的立场发表对案件的看法,有时候甚至是孤军奋战。在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介入案件之前,公众——包括法官和陪审员——也许已经形成了对案件的看法。试想一下张金柱案、杨佳案、药家鑫案、马加爵案、陈建湘案、莫焕晶案……在这些案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有多少人在法院没有宣判之前已经按照自己信奉的道德准则对这些被告人判处了死刑,甚至凌迟。很多时候,律师接受委托本身就会引起非议:你看,这家伙,居然为那家伙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除了在法庭之上讲事实、摆证据、辩法律,还必须就案件在公众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偏见作出回应。即使全体公众都已认定其委托人罪有应得,辩护律师也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说出真相。那些已经在内心深处接受了控方故事的人,不能因为辩护律师讲了一个与自己已经接受的故事不一样的故事而要求辩护律师闭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也是言论自由权的范畴,受宪法言论自由规范的保护。
(二)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因属基本人权而不可剥夺
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与单纯的言论自由虽有重合,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言论自由。通常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范围更加广泛,主要涉及公民个人对政治体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以及司法机关如何运作、立法机构通过的立法等方面的看法,大多属于积极自由。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可能包括对政府执法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批评,对司法机关不遵守法定程序的做法提出纠正等。这类意见更接近于一个普通公民对政府行为提出的批评,属于公共领域,也算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权这一积极自由。但是,更多时候,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针对侦查机关侵犯委托人权利的行为提出的控告,针对公诉机关对其委托人提出的指控所作的反驳和澄清,是对案件事实提出的不同于侦查或公诉机关的看法,是针对政府可能的压迫所作的反抗,是为了保护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来自以赛亚·柏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柏林指出,消极自由回答的是“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的问题;积极自由回答的则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问题。(8)[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可见,消极自由是指个体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状态;积极自由则是指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自由。在消极的意义上,自由是一个人能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在积极的意义上,自由则是指个体成为他自己主人的愿望。
为什么说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主要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呢?因为辩护律师的身份及其职责决定了庭外辩护言论的内容主要是为委托人洗刷罪名、洗刷冤屈,主要是提出证明其委托人无罪、罪轻的事实和证据,反驳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对其委托人提出的指控,维护、恢复其委托人已经受到损害的名誉。在某种程度上,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和庭内辩护言论一样,都是为了防止其委托人遭受冤枉,维护其财产权、人身权乃至生命权等基本权利不被任意剥夺。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内容,是针对有关其委托人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向公众作出的澄清。这是一种反抗性的权利,因而是一种消极自由。但是,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也可能包含对政府执法行为的批评,甚至可能包含对司法制度的负面评价,偶尔夹杂一些牢骚或怨言,则又有可能使其言论成为公共领域,而不仅仅是对其委托人个人权利的维护。很显然,当律师只是试图指出其委托人在事实上无辜、在法律上无罪时,其庭外辩护言论的自由就属于消极自由;但当律师提出目前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例如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违反了控辩平等原则,其言论就超出了消极自由的范畴,进入积极自由的领域。由于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主要集中于政府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委托人实施了所指控的行为、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具备法律上从轻或减轻的理由等方面,而一般较少会针对司法制度本身,因此其主要属于消极自由。
为什么要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并将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大部分归入消极自由的范畴呢?这主要是因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在自由的程度上是不一样的。积极自由常常要受到更多限制,而这种限制往往具有较强的正当性;而消极自由则往往不能或者只能受到较少的限制,并且无论何种限制,都需要更强的正当性。消极自由意味着不受压迫、不受干预;不受干预的领域越广,自由的程度也就越高。当然,消极自由也有界限,只不过对其限制必须相当慎重。如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穆勒以及法国自由主义者贡斯当、托克维尔等所主张的那样,对于消极自由,应当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领域。(9)参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192页。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中有关其委托人在事实上无辜的内容,正是属于这种最低限度的自由领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应当剥夺或限制的。
平等自由主义者罗尔斯认为,作为政治自由的言论自由只有在确保宗教与思想自由的良心自由的意义上,才属于人权;而出版、结社、示威等方面的自由,虽然值得向往,却并不属于人权的范畴。因为在罗尔斯看来,人权是最基本的自由,是完全不容侵犯的自由,是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和限制的自由;当其他任何利益与基本自由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保障这些基本自由。罗尔斯提出:正义的第一原则是平等的自由原则,所有人享有同样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原则是平等的分配原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机会平等原则,二是差别原则——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必须是为了保护社会中最小受益者的最大利益。(10)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0页。正义的第一原则优于第二原则,即“自由优先”——属于人权范畴的基本自由具有优先地位,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剥夺或限制。但是,只有把基本自由的范围界定得十分狭窄、成为退无可退的权利时,自由优先原则才具有正当性,才能获得普遍接受。
因此,除了要区分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与其他言论,同时也要区分律师庭外针对案件本身的辩护言论与针对司法制度、程序、裁决的言论,从而对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不同内容给予不同强度的保护。在有些场合,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针对司法制度或司法机关的,有时是针对司法人员个人的,这些庭外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是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约束和限制的。但在大多数场合,律师庭外辩护言论都是针对案件事实、证据、所涉法律适用问题而发表的属于辩护权的内容,这些庭外辩护言论自由,就是一种消极的权利,是一种反抗性权利,是为了保护委托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任意侵犯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公民在遭受政府部门压迫时进行和平反抗的唯一武器,是无辜的被告人濒临被社会抛弃的边缘而无法获得有力救助时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自由是基本自由,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权利。正因如此,它是不容剥夺的,也是不能限制的。
三、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关键力量
长久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把维护司法公正视为限制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正当性基础。(11)参见陈实:《论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58页;杨先德:《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法律问题探讨》,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67页。这种观点既脱离了中国的司法语境,也不符合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事实上,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只要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仅不会损害司法公正,反而是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关键力量。
(一)在法官主导审判的国家,律师庭外辩护言论通常不会损害司法公正
关于庭外辩护言论影响司法公正的顾虑在于,失当的庭外报道会使潜在的陪审员形成偏见,损害审判者的公正性。这种担忧主要是在以陪审团审判为主导的国家(12)有关舆论对审判公正之影响的讨论,可参见马勤:《舆论是否毒害了一个公正的陪审团——美国诉斯基林案评析》,载《中国案例法评论》2017年第2辑,第35-57页。需要强调,这种极端情形只存在于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
我国虽然也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我国是典型的法官主导审判的国家。法官往往能够比大众陪审团更好地抵御舆论的影响。(1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这主要是因为法官接受过法律专业训练,逻辑和理性思维更强,几乎不会因媒体报道而产生偏见。即使在有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情况下,人民陪审员也很难主导案件的基本走向。合议庭的讨论过程贯穿着法官的专业化理性思维,人民陪审员存有的偏见很容易被排除。而且,根据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必须参加培训,又由于人民陪审员实行任期制,其法律思维与理性能力与法官并无本质性区别。因此,我国基本不必担忧庭外言论损害审判者的公正性。
同样重要的是,适当的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本着客观、公正、审慎的态度,不会导致偏见。这在法官审判的情况下是如此,在陪审团审判和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的审判之下亦是如此。应当区分的是,并非一切与案件有关的媒体报道都会造成偏见,法律要防范的仅仅是那些容易引起强烈偏见的言论。刑事审判活动本身是公开的,媒体有权对其进行自由报道;通常只要报道内容真实、准确,便不存在偏见性影响。(14)Reynolds v. United States, 98 U.S. 145, 155-156, 25 L.Ed. 244 (1879).显然,庭外辩护言论是为了澄清有关被告人的消极性媒体评价,本身并不会引起对被告人的偏见,自然也不会损害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二)以司法公正之名限制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实质上是妨害司法公正
以司法公正之名来限制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直接压缩了辩护权的合理范围,限制了公众了解案件事实的渠道,妨碍了人民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从而可能维持针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局面,实质上是对司法公正的妨害。
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往往是为了对抗已经出现的针对委托人的不利言论,或是为了扭转已经形成的不公正局面。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初始力量极不对等。控方有强大的国家机关作为支撑,手握更多的诉讼资源,包括舆论优势。很多时候,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还来不及委托律师,侦查机关就让电视台扛着摄像机走进了看守所,让犯罪嫌疑人面对镜头痛哭流涕认罪悔罪;等到律师介入案件时,负面报道已经铺天盖地。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指出,让犯罪嫌疑人“电视认罪”,违背其意愿,形成了定罪舆论,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15)参见朱征夫:《嫌犯电视里认罪不等于真有罪》,载《新京报》2016年3月2日,第A08版。当控方发布的信息已经对辩方造成了负面影响,公平对抗的司法原则自然允许辩方发声回应。公平的庭外言论对抗,有助于提高媒体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减少舆论对审判者造成偏见性影响。更何况,相形之下,辩方通常只是个人,势单力薄,发出的声音更微弱,发声渠道也更有限。因此,律师的庭外辩护言论应该获得更强有力的保护。在此问题上,我国对律师庭外言论的限制规则只针对辩方,控方所受限制反而更少,更应当放宽对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管制。
当律师认为委托人蒙受了冤屈,而法官却对庭内辩护不够重视时,发表庭外辩护言论是推动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法官对案件的庭内辩护不甚重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也许是私人偏见,也许是其他压力等。审判是审判者根据事实和证据而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若审判者存有偏见,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审判便不可能公正。一旦律师遇到带有偏见的法官,却无法成功申请回避,那么案件很可能遭遇不公正的审理。此时,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是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外部监督机制推动审判公正。(16)参见高一飞、潘基俊:《论律师媒体宣传的规则》,载《政法学刊》2010年第2期,第3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限制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就是在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是推动人民监督以促进司法公正
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是通过人民监督的力量来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司法公正的实现绝非自然而然、理所当然。一个具体案件,无论是程序公正还是实体公正的实现过程都可能面临重重困难。辩护律师尤其时常遭遇会见难、阅卷难。当律师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却无果时,只能通过在庭外发声来维护合法执业权利。庭审中律师的辩护意见应当获得重视。但是,法官可能出于私心,或适用法律违背了人们普遍的正义直觉,或面临政治压力等导致审判公正难以实现。此时,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是尝试激起舆论的关注,推动司法公开以促进司法公正。由此可见,只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就是推动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律师办案时直接近距离接触司法权力运行的方方面面,庭外辩护言论可以促进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并推动人民行使对司法的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从源头上抑制腐败。司法不仅关涉公民的个人自由、基本权利、私有财产等重大利益,而且涉及社会的公序良俗、道德底线、公平正义等公共利益,公民有权知悉。知情是进行讨论、监督和批评的前提。知情权不仅要求公开,而且依赖于言论自由。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有助于推动司法公开,遏制司法勾兑,抵御司法恣意,为人民监督、司法公正和民主法治奠定了基础。
四、以西方有关规则主张限制庭外辩护言论是对西方规则的误解
纵览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等,普遍在原则上保护律师庭外辩护言论,并且言论的形式基本不受限制,只在例外情况下限制言论内容。无论基于理论考量,还是域外经验,都应保护而非过度限制律师庭外辩护言论。
(一)国际普遍经验是原则上保护律师庭外辩护言论
各国法律普遍确立了司法公开的原则,因此,律师有权公布不涉密的案情。由于言论不涉及保密内容,基本不存在违反保密义务的风险。此外,律师发布的内容只是案件事实,很少会有煽动冲突的危险。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直接参与立案、庭审、执行、听证等司法活动的全过程。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工作者,当然有权公布其了解到的不涉密信息,根据个人理解来表达专业意见。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反复强调,审判活动涉及公共议题,有关审判的言论自由是宪法予以保护的核心。(17)NBC Code of Conduct for Italian Lawyers (2014), Article 17.
律师发布依法可以公开的案情,只要内容真实、无误导,便不存在恶意炒作。有一种批评的声音是指责律师炒作案件。我国2017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252条规定律师不得“对本人或者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2018年《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6条规定“律师不得利用律师身份和以律师事务所名义炒作个案”。炒作一词在社会语境中带有负面色彩。在法律层面上,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无非是为了扩大案件的社会影响,希望引起公众注意,促进民众监督司法;只要没有歪曲事实,没有夸大宣传,就不属于炒作,其行为就不应受苛责。应受谴责的是对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
(二)根本不存在“严格限制”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则模式
以西方国家有关规则为依据,主张限制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既忽视了中国的语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西方规则的误解。现有关于西方规则研究所依据的文献,除了对美国规则的介绍相对详实之外,对其他域外有关规则的考察相当欠缺。有一些出处不详、引注不明、已经过时的法律却被辗转援用,有失严谨。比如,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反复援引英国和加拿大废弃了多年的旧条文,却完全无视现行规则。
有些学者将西方规则分为“限制”和“不限制”,“严格禁止”和“底线标准”等模式。(18)关于类型的划分,高一飞等最早提出了三分法:第一种是英国的“通过禁止媒体报道隔绝律师言论模式”;第二种是美国的“不限制媒体但限制律师言论模式”,第三种是德国的“不限制媒体报道和律师言论模式”,参见前注高一飞等。陈实提出了两分法:第一种是“严格禁止模式”,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二种是“底线标准模式”,如美国;参见前注陈实的文章。这种类型化的方法意在简化,但归纳并不准确,不仅引发了争议,而且扩大了误解。美国被认为是“底线标准”模式,一般允许律师发表庭外言论,但是不得逾越底线。所谓“严格禁止模式”指的是,法律原则上禁止律师发布庭外言论,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形,比如已公开的信息或无关司法的言论等。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被误认为是严格禁止模式的代表。事实上,经逐一考察,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禁止模式”,这种误读部分由于文献疏漏,部分缘于理解偏差。
1.英国已于2013年废除了针对律师庭外媒体言论的限制规则
英国关于律师庭外媒体言论的规则在条文层面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律师执业行为准则曾对媒体评论进行了一些具体限制,但在2013年完全废除了该限制条款。英国的旧有规则绝非严格禁止,现行规则不仅远非严格限制,而且更加重视保护。
学者普遍援引的是版本不明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行为准则》(下称《律师行为准则》),该准则只更新到第八版,其最新的修正案止于2013年。在2013年以前,第709条是限制律师媒体评论的专门条款,其709.1规定律师不得对正在或预期参与的司法程序发表个人评论;709.2作为例外,规定教育或学术讨论的语境不在此限。(19)The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Bar Council: Expressing Personal Opinions to/in the Media (2014), para. 2.,不包括预期不会参与或已经结束的程序。此外,该条禁止的言论只是个人评论(personal opinion),若发布的是不涉密的案情信息,律师不作评论,则不受该规则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英国在2013年4月对《律师行为准则》进行修正时一举彻底废除了第709条,代之以英国律师协会标准委员会《媒体评论指引》作为一种建议性引导。(20)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BSB Handbook (Fourth Edition) (2019), rC15.现有的律师庭外言论规则是指引性的,原则上保障律师庭外言论自由,只是要求遵守职业伦理。
2.加拿大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则和美国规则一脉相承
有学者因不了解加拿大移植了美国规则,一方面主张美国是“底线标准”模式,另一方面反而将学习美国的加拿大规则理解为“严格限制”,实属自相矛盾。这是对加拿大规则的片面化解读,只看到限制性规则,忽视了保护性原则。
最早起源于1920年的《加拿大律师协会职业行为守则》曾是规范律师职业行为的主导规则,其第18章是关于律师公开露面和发表言论的规则,其明文指出,律师庭外言论应当遵守包括《美国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第3.6条(下称“3.6规则”)在内的规则(21)CBA Resolution on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14-01-M.
自2009年起,《加拿大律师协会联合会示范守则》颁布并逐渐被各个律师协会所援用,该守则延续了保障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在2014年已成为普遍规则。该守则明确规定:“在不损害律师对委托人、法律职业、法院或司法的义务的情况下,律师可以与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可以公开露面和公开陈述。”(22)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18), Rule 3.6 (adopted by the ABA in 1983).
3.德国、澳大利亚都在原则上保护律师的合法庭外言论
关于德国规则的理解存在重大争议,有学者认为德国规则是不限制律师庭外言论,另有学者认为德国是严格禁止。(23)The Federal Lawyers’ Act (Bundesrechtsanwaltsordnung-BRAO), §43a.
澳大利亚的规则和美国、英国都有相似之处。法律在原则上是允许律师发表庭外言论,但是要符合职业伦理,保证真实准确,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等。《澳大利亚律师协会律师行为规则》第75条禁止律师发表三类言论:一是明知是不准确的信息;二是违反保密义务;三是言论“看起来”或“确实”表达了律师对正在进行或可能发生的法律程序或程序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的意见,但是,教育或学术讨论不在此列。(24)Australian Bar Association Barristers Conduct Rules, Rule 76; see also Legal Profession Uniform Conduct (Barristers) Rules 2015 under the Legal Profession Uniform Law (NSW), Rule 77.
(三)西方各国不仅保护庭外辩护言论,而且表达形式不受限制
西方各国关于庭外言论的规则,都强调防范言论内容的有害性,而轻其言论形式。若在限制言论的法律规则中明确排除一些特定的言论表达形式,极有可能削减、压制甚至剥夺本身内容正当言论的表达权。相比之下,限制言论表达方式的正当性难以论证,必须结合情景逐案分析。因此,表达形式的自由度更高。譬如,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发布的《欧洲法律职业原则规范宪章和欧洲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律师享有发表庭外言论的自由,对言论的内容进行了规制,但明文指出言论的表达方式并无限制,包括通过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平台等。(25)NBC Code of Conduct for Italian Lawyers (2014), Article 17.
值得反思的是,我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38条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252条规定,律师不得“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此外,法律还规定律师“不得采取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众滋事,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26)《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37条;《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2017),第251条。以上规定都是针对律师庭外言论的限制性规则,明确列举了如“公开信、个案研讨、静坐、举牌、打横幅”之类的“方式”和“手段”,将特定的表达形式定为非法,实质上过度限制了律师的合法庭外辩护言论。例如,当委托人蒙冤,其他方法伸冤无果,律师通过网上声援或发表公开信为其喊冤。公开信的内容合法,其言论形式也没有给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造成损害的危险,法律欠缺对言论形式进行限制的正当性基础。
因此,只要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表达形式可以多样化。但凡表达行为本身没有达到损害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的程度,那么庭外辩护的形式就应受到保护。在规制律师庭外言论的法律条文中,不应明确列举某种言论形式,否则,不仅会让律师产生额外顾虑、心生不必要的忌惮,而且会增加发生争议的风险。
五、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的边界、越界标准、划界规则
律师享有庭外辩护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律师的庭外辩护言论完全不受约束。律师庭外辩护应当忠于事实,忠于委托人利益,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应当强调的是,律师基于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发表庭外辩护言论,其中关于委托人没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证据存在重大瑕疵、程序存在重大不公等方面的内容是辩护权的一部分,作为基本人权不可剥夺。这一部分内容,不受公共利益等因素的权衡,因为保护该项权利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必讨论其限制规则。除此之外,律师发表的其他庭外辩护言论属于政治自由的内容,该部分的言论不得损害司法公正,因此要按照“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来进行规制。
(一)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边界是“基于事实,忠于委托人,止于正义”
基于案件事实,是庭外辩护言论受到保护的基本前提。律师辩护是为了特定当事人在特定案件中的特定问题进行辩护。无论是陈述案情、展示证据,还是发表评论、表达诉求,只有立足于具体案件的事实,庭外辩护才有价值。即使是阐述法律意见,案件也是讨论法律争议产生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在法庭内外,辩护都应基于案件,不能天马行空,更不能捏造、歪曲事实。庭外辩护虽然不必像在法庭内要遵守严格的程序,但言论内容上同样应当真实客观。此外,加拿大《示范守则》第7.5-1条“评注1”指出,律师在法庭外发布言论也受到法庭言论规则的约束。(27)The Federation of Law Societies (FLSC) of Canada’s 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As amended March 14, 2017), Rule 7.5-1, Commentary [1].
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是忠诚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为委托人争取利益,是律师执业的基本出发点,当然也是庭外辩护言论的伦理基点。英国虽然废除了关于律师庭外言论的具体限制规则,但根据《律师标准委员会手册》,律师庭外言论受职业伦理约束,其中第1条便是忠于委托人的最佳利益。(28)NBC Code of Conduct for Italian Lawyers (2014), Article 18.
职业伦理规范要求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当律师在衡量是否发表庭外辩护言论,如何发表,发表什么内容时,都要本着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律师发表庭外辩护言论是为委托人争取公平对抗的机会,不得违背道德原则和正义理念。司法既是公开的,又是庄严的。美国最高法院强调,律师是案件的关键参与者,其言论会被赋予某种权威,因此,律师群体更有责任去维护司法公正。《香港大律师公会行为守则》要求,律师在发表庭外言论时应小心谨慎,不得损害司法。(29)The Legal Profession Act (Chapter 161), Legal Profession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s (2015), Rule 13(6).
(二)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否越界的判断标准应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为了充分保护律师的庭外言论自由和公众的知情权,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否越界的判断标准应当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这一标准的选择是在中国语境下对美国经验的汲取。美国律师庭外言论规则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和争论,大致形成过三种标准。(30)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1983), Rule 3.6 cmt. 2.
1.“造成严重损害的实质可能性”的标准备受争议
美国的“3.6规则”及其前身“7-107规则”都是言论自由与审判公正咨询委员会为了防范审前宣传损害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而制定的,故这两种规则确立的标准都对庭外言论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加拿大也是陪审团审判,存在类似顾虑,故而借鉴了该标准。最初的“3.6规则”有三条内容:一是一般规定,确定了限制律师言论的判断标准;二是示范性规定,确定了六种言论情形通常会被认为存在“严重损害的实质可能性”,这是考虑到衡量标准的模糊性,为适用标准提供较明确的参照;三是“避风港条款”,律师在这个范围内发表言论不必过分谨慎顾忌,明确了对律师的特定言论的保护。(31)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1983), Rule 3.6.
但是,“3.6规则”在1991年的金泰尔案中遭到强烈质疑。在一起毒品被盗大案中,金泰尔受聘担任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距离开庭还有六个月的时候,他召开了一场媒体发布会,提出办案警员有作案嫌疑,同时声明被告人是无辜的。(32)Gentile v. State Bar of Nevada, 501 U.S. 1030, 1043 (1991).
为了回应金泰尔案的判决意见,美国律师协会道德与职业责任常设委员会审查了“3.6规则”,并于1994年通过三项主要的修改意见:一是减少模糊性,对避风港条款的措辞进行修改,移除了一些模糊和争议性示范条款;二是增加回应权规则;(33)ABA Standing Comm. on Ethics &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 ABA Criminal Justice Section, Report to the House of Delegates 3, at 7 (1994); besides, a brief history of Rule 3.8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cornell.edu/ethics/aba/2001/history.htm#Rule_3.8, last visited and archived on Aug. 18, 2019.其中第二项意见如今已列入3.6(c),成为规则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这是认可了律师辩护的场所不仅仅限于法庭内,也可以延伸至法庭之外。修改后的“3.6规则”趋向于更加包容律师庭外言论。
2.我国应当采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判断标准
美国最高法院在内布拉斯加州新闻协会案中强调,如果要使用言论禁止令,为了确保其合宪性,应当满足“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之检验标准。(34)ABA Annotated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43 (1984).这正是该规则应当朝着“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去进行严格解释的原因,也正是其合宪的基础。
从司法体系背景出发,以美国“3.6规则”来限制我国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不适当的。美国以陪审团审判为主导,需要防范律师庭外言论使陪审团产生偏见的问题。但应注意,正如前文指出,我国是法官主导审判,庭外言论对司法公正更多是有益无害的。在法官主导审判的制度下,几乎不存在无法为被告人找到一个公正的审判者之顾虑。换言之,庭外辩护言论对司法公正的损害可能性是极低的,如果采用“严重损害的实质可能性”标准,会对律师庭外言论自由形成过度限制,侵害了其宪法权利。
我国需要考虑的是加强对律师庭外言论、公众知情权的保护。现有的对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规则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在实践中,有些律师的庭外辩护言论根本就达不到对司法公正造成“严重损害的实质可能性”,甚至经常连“合理可能性”的标准都达不到,即使如此,律师仍然会因为庭外辩护言论而受到制裁。面对司法实践对律师言论过分管控、肆意限制的现实,法律迫切需要明确加强对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保护。有鉴于此,我国应当采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
(三)划定庭外辩护言论边界的必要规则——“禁区”“安全区”“过渡区”
我国针对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越界与否的判断标准应当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结合我国的规则现状,通过借鉴美国“3.6规则”的立法技术,本文建议示范性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应当明确禁止的,属于“禁区”;另一类是应当明确受到保护的,属于“安全区”(或称“避风港”“安全港”)。在禁区与安全区之间的“过渡区”应当按照“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逐案判断。
“禁区”规则是禁止虚假、歪曲、误导性言论。经考察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律师庭外言论的限制,除了遵守职业伦理规范之外,都明确要求言论内容的真实、无误导。西班牙和意大利是通过明文规则禁止虚假、歪曲、误导性言论。英国、美国、加拿大则通过指引性说明、规则评注、职业伦理规范的方式禁止虚假、歪曲等言论。我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40条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258条,明文规定“律师对案件公开发表言论,应当依法、客观、公正、审慎……”(35)《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第40条;《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2017),第258条。
“安全区”规则可以给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提供明确的保护范围,减少不必要的顾忌,并防止律师享有的基本言论自由和辩护权遭到侵害,具体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公开性事实,律师可以发布公开审理的案件的事实,包括但不限于:(1)案件事实、诉求、辩护策略;(2)政府公开性信息;(3)诉讼程序不涉密事实、日程安排和结果;(4)关于请求协助获取所需的证据和资料的申请;(5)关于办案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职位的公开信息。第二类是评论性内容,律师发表对案件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司法程序、司法制度的评论,包括但不限于:(1)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对办案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评论;(2)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对司法程序、司法制度和法律问题发表评论。第三类是回应性内容,律师有权对非本方发表的负面性质的言论进行回应。回应性的内容应当具有针对性,不得超过对应事项的范围,但并不限于事实性或评价性内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我国台湾地区都规定了明确的回应权规则。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律师伦理规范”第24条第3款规定:“律师就受任之诉讼案件于判决确定前,不得就该案件公开或透过传播媒体发表足以损害司法公正之言论。但为保护当事人免于舆论媒体之报道或评论所致之不当偏见,得在必要范围内,发表平衡言论。”(36)我国台湾地区“律师伦理规范”(2009),第24条。
在禁区和安全区之间就留下了广阔的“过渡区”,需要按照“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一般标准作为指引,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进行判断。但是,在衡量的过程中,不可主观臆断、肆意评价律师言论所具有的损害危险程度和可能性。因此,“过渡区”的规则是引导性和建议性的,主要涉及在判断时应当考量的基本因素。
针对具体案件中的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否逾越了边界,英国、加拿大、美国一贯坚持逐案审查的原则。尤其是美国的诸多判例总结出了一系列应当考虑的因素。通常而言,言论内容的倾向性、偏见程度、引发偏见的可能性、发表时间、传播范围、传播次数、可能引发的后果、实际后果、律师主观上是否“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言论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等都是在逐案分析时应当综合考量的因素。
六、结语
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刑事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而在法庭程序之外发表的辩护性言论。根据律师庭外言论目的之特殊性、内容的具体性、诉求的针对性、言论情景的特定性,这些言论或明确是属于辩护权的组成部分,或明确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从而应当依据不同的原则进行规制。鉴于我国是法官主导审判的国家,庭外辩护言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以司法公正之名限制庭外辩护言论其实是妨害公正。通过考察域外经验,可以佐证对庭外言论的保护是原则,只有在言论明显有害的情况下才予以规制。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作为辩护权的庭外辩护言论属于基本人权,不应任意剥夺或施加过多限制;而作为言论自由的内容,应当按照“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对其进行规制。为了防止裁量权滥用,法律应当明确限定“禁区”规则,更重要的是强化落实“安全区”规则,并充分发挥“过渡区”规则的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