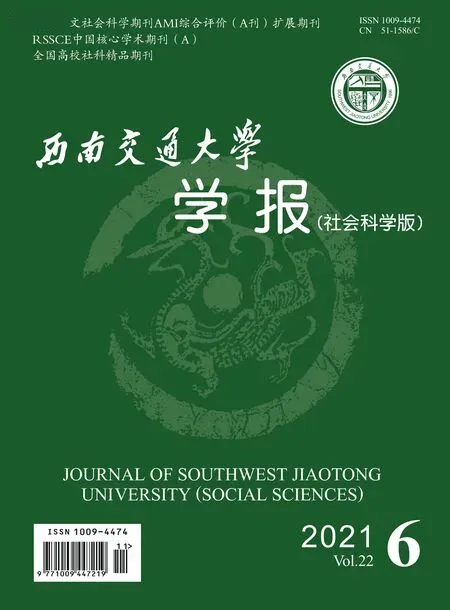《尤利西斯》汉译文本间性研究
孙建光
一、引言
艾布拉姆斯(Abrams, M. H.)认为每个艺术品都由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四个要素构成〔1〕。文学活动的文学批评也应该兼顾这四个要素,但是某一批评家或者研究者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侧重于某一要素,并围绕该要素形成对某个艺术品的界定、划分或解析,于是该要素就成为某个时期作品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文学创作不只是作家在自己的世界里言说事物,还需要尽可能地了解相关文本,并在先前的文本影响下进行言说〔2〕。艾布拉姆斯也认识到这一点,“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藉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1〕。因此他认为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方式可以分为作品与世界、作品与欣赏者、作品与艺术家和作品孤立封闭的独立研究四类。从研究的本质来看,艾布拉姆斯非常认同文学批评就是间性研究。他认为这四个要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理论,根据理论家各自特有的论证方法……在意义与功能上也随之产生变化”〔1〕。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作品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即一切可以涉及、反映或者表现某种客观状态或者相关的东西,既可以是艺术家的直觉世界,也可能是常识世界或科学世界。我们可以把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联性看成是艾布拉姆斯认为的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范畴,即某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称这为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又被译成“互文性”。文本间性的概念是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1966年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成为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标识性术语。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由其他预先存在文本的多个“交叉”片段组成,因此具有隐式引用的情况。该文本的原始语境既被召唤出来,同时又被“中立化”:互文性具有转换性特征,在这种意义上移植的文本序列获得了新的意义,也允许拥有新的意义〔3〕。通俗地说,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换,是文本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可以通过用典、戏拟、模仿、变形、转化等形态构成文本间性关系。一个文本在特定的时空中会形成某种文学或文化上的联系,或是语言间或是文化间的联系,使得该文本和其他文本形成了某种互联性。互文性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就有。宋人黄庭坚认为杜甫的诗“无一字无来处”〔4〕,而且他自己深受杜甫影响,注重在创作中用典,结合自己的创造形成了不少名词佳句。清人赵翼也评价杜甫“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不肯不典”〔5〕。杜甫在诗作中大量用典,与其他作品形成文本间性关系。事实上,历代文士无不领会到用典的妙处,只不过是没有在学理上对典故进行阐述形成理论。毫无疑问,间性理论的提出打破了文本封闭自足、独立存在的传统文学观,解放了文本,实现了文本开放性,而翻译活动无疑是最具有文本间性的特殊形式书写。
翻译本质上说是目标语对源语内容与形式的复调,需要原文与译文之间平衡、交流、共享差异才能达到融合统一的境界。翻译活动离不开译者的阅读、理解、阐释和再现,在这一过程中译作与原作的文本间性就发生了,这种间性关系不仅存在共时层面的对话,还存在历时层面的对话〔6〕。译本在某种意义上是原著变异的孪生体,两者之间有着貌合神离或者神合貌离的特质,也会有脱离原作的变异和扭曲。事实上,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以来,译者就认识到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才会有古今之争的“直译”与“意译”。无论是直译与意译,还是归化与异化,都是译者试图在差异中寻求一种平衡,处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这本身就反映了翻译的文本间性特质。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的文字材料来替换另一语言中对等的文字材料的过程”〔7〕。既然翻译是不同文本的替换,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相互指涉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对等的,也可能是不对等的。因此,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就是一种文本间性关系。与其他文本之间的间性相比,这种相互指涉程度更高,译语文本是作者意向的体现,译语文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译者个性和风格。因此我们讨论翻译的文本间性,既需要聚焦文本间的对等,也需要聚焦译文对原文的吸收与变形。为了更好地探讨文本间性这一话题,笔者以《尤利西斯》金隄译本和《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尤利西斯》汉译过程中的译文与原文、译文与引文以及译文与译文的文本间性问题,以探寻翻译中文本间性的类型及其互动关系。
二、译文与原文的间性关系
翻译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研究,它始于源语文本,终于目的语文本。从源语文本到目的语文本无论过程如何波澜壮阔,但它们之间必须要具有同源指向,要呈现原作者的意图,以实现译文与原文的互文性,互文性延续了译文与原文在内容、意义、风格等方面总体上的同源等同。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也不是硬译死译或是照套原文表达,它需要变通、重组,甚至改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文本翻译看成是译文简单地替换原文的所指。翻译本质上就是对原文的复制和再创造,事实上翻译研究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从形式上就是起于源语文本、终于译语文本的过程。有学者把文学活动看成是间性复制和间性创造,这很有道理。但是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间性复制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作者具有绝对的权威,作者的意图具有唯一性,因此源语文本的意义也是确定的,这时要求译本是对源语文本的间性复制,该观点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形式、内容、风格,甚至所指。田传茂等人就持该种观点,他认为在翻译活动中对原文本的理解需要从微观的语言文字和宏观层面上的各种间性进行把握,间性复制就是“对源语文本在宏观上的忠实”〔8〕。间性创造则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译者对原文进行创造性劳动,给予原文新的生命形式。其实,译文应该源于原文而又尽可能地高于原文,这是因为“翻译是基于原文的创造,兼具一般文本的创造共性与自身的个性”〔9〕。金隄和萧乾、文洁若在翻译《尤利西斯》过程中都遵循的是翻译的间性复制特性,并试图按照自己的诗学原则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风采,但是通过分析他们的译文,我们发现他们的译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缩、延伸和变通,进行了间性创造的运用,可见他们的翻译存在着间性复制和间性创造两种方式。为了更为直观地理解译文与原文的文本间性关系,我们结合具体译例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进行译文与原文的间性对话的。如:
No prince charming is her beau ideal to lay a rare and wondrous love at her feet but rather a manly man with a strong quiet face who had not found his ideal, perhaps his hair slightly flecked with grey, and who would understand, take her in his sheltering arms, strain her to him in all the strength of his deep passionate nature and comfort her with a long long kiss. It would be like heaven. For such a one she years this balmy summer eve. With all the heart of her she longs to be his only, his affianced bride for riches for poor, in sickness in health, till death us two part, from this to this day forward.〔10〕
金译:她的最美好的理想,并不是一个迷人的王子拜倒在她的脚下,献上一份稀罕奇妙的爱情,而是一个有男子汉气概的男子,脸上镇静而有力量,也许头发已略见花白,但是还没有找到理想中的心上人,他会理解她,将她搂在他的怀抱之中庇护她,以出自他那深沉热情的性格的全部力度搂紧了她,用一个长长的热吻安慰她。那就是天堂一样了。在这和煦的夏夜,她热切盼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全部心愿,就是要被他占有,归他独占,成为他的订了婚约的新娘,或富或贫,或病或健,相守至死,从今以后,直至以后。〔11〕
分析金隄译文与原文,发现译文很好地传递了原文的主要信息,译文与原文有着紧密的文本间性关系,而且金隄译文的一些细节处理呈现出间性创造的特征,反映出译者在文本间性中的主体性作用。原文的第一句话是倒装句,英文的倒装句大多数情况是起着强调的修辞效果,金隄并没有照着英文语序翻译,而是采用汉语的表达习惯把倒装句按照正常句序进行翻译,同时把“lay a rare and wondrous love at her feet”的意思延伸,翻译为“拜倒在她的脚下,献上一份稀罕奇妙的爱情”,类似于汉语“拜倒在某人石榴裙下”;“a manly man with a strong quiet face who had not found his ideal, perhaps his hair slightly flecked with grey ...” 该句话译文意思虽然和原文是近似的,但是句子的结构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对男子的形象进行描述,符合汉语的表达特征,然后再表达他还没有“心上人”; “For such a one she years this balmy summer eve”这句话也调整了语序,让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把时间提到了句子的前部,翻译为“在这和煦的夏夜,她热切盼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With all the heart of her she longs to be his only” 译文也进行了延伸翻译,特别是在译文中增加了“归他独占”来表达原文中的“his only”。应该说金隄的译文与原文形成了良好的间性交流,在意义上实现了很好的间性关系,实现了对原文的意义复制,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但是译文中也有一些变形,如“ beau ideal”被他译为“最美好的理想”,显然这里“ideal”翻译成“理想的人”最好,所以翻译成“意中人”“心上人”之类的效果可能更佳;“with a strong quiet face”翻译成“脸上镇静而有力量”显然也不是太到位,“strong”翻译成“有力量”似乎没有和原文形成很好的互文性,脸的表情往往是用“坚毅”而不是“有力量”。可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风格、内容上译文和原文近似度越高,说明它们的互文性越强,译文越忠实于原文,文本对话越深入。
萧译:她的意中人并不是将珍贵、神奇的爱情献在她脚前的风流倜傥的王子,他毋宁是个刚毅的男子汉;神情安详的脸上蕴含着坚强的意志,却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女子。他的头发也许或多或少已经斑白了,他会理解她,伸出胳膊来保护她,凭着他那深沉多情的天性紧紧搂住她,并用长长的亲吻安慰她。那就像天堂一般。在这馨香的夏日傍晚,她企盼着的就是这么一位。她衷心渴望委身于他,做他信誓旦旦的妻子:贫富共当,不论患病或健康,直到死亡使我们分手,自今日以至将来。〔12〕
总体上看,萧乾译文与原文的间性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句也是采用正常语序翻译原文的倒装语序,对“lay a rare and wondrous love at her feet”的翻译显得更为直接,在形式上译文与原文的互文性程度更高,但从意义上来看,翻译成“将珍贵、神奇的爱情献在她脚前”会让读者有种译文不是很流畅的感觉,显得比较生硬;“a manly man with a strong quiet face who had not found his ideal, perhaps his hair slightly flecked with grey…”这句翻译没有对原文的语序进行调整,而是采用顺译法,译文与原文之间在形式上有着紧密的互文性,意思上能近似于原文;“With all the heart of her she longs to be his only”译文采用了延伸译法,译为“他企盼着的就是这么一位。她衷心渴望委身于他”。萧译把“his affianced bride”翻译成“做他信誓旦旦的妻子”,从译文与原文的互文性程度上来看,显然不是非常紧密,而翻译成“有了婚约的新娘”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更有紧密的间性关系。
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译文和原文两者的间性关系可以从多维度视角进行,既可以是形式上的,也可以是内容上的,还可以是风格上的。毋庸置疑,两者的间性程度越高,说明原文的可译性越强,间性复制度越高;两者间性程度发生偏移或者变形,说明原文的可译性较弱,需要通过间性创造来传递原文信息。事实上,一个译本很难从头到尾都和原文有紧密的间性关系,很多时候译文或高于原文或低于原文,这时两者的互文性也会呈现出紧密性和松散性,这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表达有着很大关系。理想的“范本”离不开译者充分考虑作者的意图,尽可能地准确传递原文所有要素,同时又能考虑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13〕。理想的译本实质上是译文全方位地和原文“协商”与“妥协”,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契合度”。
三、译文与引文的间性关系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都是互文性的,文本是开放的,具有互动的生产性。在一些现代派作品或者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创作中,文本也通过用典、引用、拼贴、文字游戏和体裁转换等形式来表现与其他文本的间性关系,这种在创作中通过引入典故、变异表达等形式实现文本、意义、语言的共存交互作用,称为“引文”,是非常典型的文本间性形式。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就说:“从本相上最经常的表现为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其最明显和最忠实的表现形式,即传统的‘引语’实践。”〔14〕文学作品中运用“引文”现象非常普遍。巴特认为,引文过程(a citational process)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传承过程,是一种代码和另外一种代码的相连(1)转引自周启超《克星斯特瓦的“文本间性”理论及其生成语境》一文,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107页。。引文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有明显标记的,也可能是无明显标记的,抑或介于两者之间,标记是模糊不清的。有明显的标记如引文、套语、典故、俗语、谚语、默想和文字游戏等等,这种引文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自觉主动的创作行为,旨在通过引文隐喻某种层次的寓意,克里斯蒂娃把这种有明显标记的间性现象称为“现象文本”。没有明显标记的是一些来源已无从考证的谚语、神话或民间传说,这种引文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也可能是非自觉、无意识的创作行为,克里斯蒂娃把这种互文现象称为“基因文本”。介于两者之间标记模糊不清的引文可能会表现在体裁、主题、母题、结构等方面,这种互文现象可能是作者精心设计也可能是无意为之,但是都没有明显标记,需要读者对作品的整体把握、解读。《尤利西斯》中有各种“引文”,小说从总体框架上模仿《奥德赛》的结构和题目,大量的变异表达、典故、文字游戏以及无法确定来源的引喻构成了“引文”现象。这些引文有的有明显的标记,有的没有明显标记,但是通过一些线索能够进行溯源,还有的介于模糊状态,需要译者深入原文进行领会。例如:
...for she felt that she too could write poetry if she could only express herself like that poem that appealed to her so deeply that she had copied out of the newspaper she found one evening round the potherbs. Art thou real, my ideal? It was called by Louis J. Walsh, Magherafelt, and after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wilight, wilt thou ever?and ofttimes the beauty of poetry, so sad in its transient loveliness, had misted her eyes with silent tears that the years were slipping by for her, one by one, and but for that one shortcoming she knew she need fear no competition and that was an accident coming down Dalkey hill and she always tried to conceal it. But it must end she felt. If she saw that magic lure in his eyes there would be no holding back for her. Love laughs at locksmiths. She would make the great sacrifice. Her every effort would be to share his thoughts. Dearer than the whole world would she be to him and gild his days with happiness. There was the all-important question and she was dying to know was he a married man or a widower who had lost his wife or some tragedy like the noblemen with the foreign name from the land of song had to have her put into a madhouse, cruel only to be kind.〔10〕
在这段话中,乔伊斯引用了几处引文:“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wilight, wilt thou ever?”该句最早出现在《斯蒂芬英雄》中,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再次引用该诗,意为“在柔和的薄暮中,你会到来吗?”“Love laughs at locksmiths”也是引文,出自乔治·科曼的剧作题目,用来比喻什么也阻止不了爱情。“the land of song”是用来说明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摇篮,是美声学派及歌剧的发源地,因此通常会把意大利称为“音乐之国”;“cruel only to be kind”出自《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中哈姆雷特的台词。可以发现乔伊斯会使用来自不同作品或者不同出处的话语进行创作,构成独特的引文现象。金隄分别将这几处引文翻译为“后来还有夕阳呀,你什么时候”“爱情是锁不住的”“歌咏之邦”“残酷只是为她好”〔11〕。萧乾、文洁若分别翻译为“薄暮中,你会到来吗?”“爱情嘲笑锁匠”“歌之国”“为了仁慈,不得不采取残忍手段”〔12〕。金隄对一处引文做了标注,萧乾、文洁若对三处引文做了标注。从引文标注数量可以看出译者对引文的识别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判断出引文翻译是否准确到位,因此引文是否被准确翻译出来可以作为考察原文与译文间性关系的重要指数。金隄在翻译几处引文时并没有识别出引文,萧乾、文洁若在识别引文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并且对引文进行溯源,对读者来说,译文更加具有说服力。该段话中运用了许多具有明显标识、不明显标识的引文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引文。“Love laughs at locksmiths”“cruel only to be kind”属于具有明显标记的,“the land of song”属于没有明显标记的,倘若译者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了解引文真正所指的内容。两译本都翻译成“歌之邦”的意思,应该说从字面上讲是贴近原文的,但是如不进行注释,读者很难知道所指的具体国度。萧乾进行了注释,明确该地方是意大利。“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wilight, wilt thou ever?”介乎明显标识和没有明显标识类型的引文之间,如果没有读过《斯蒂芬英雄》,读者很难知道《尤利西斯》中该诗句是乔伊斯引自其他作品。这样的引文在《尤利西斯》中还有很多,例如“命运三姐妹、科林斯水果和忘川河水等分别对应希腊神话中掌管人的生死的三姐妹、希腊盛产水果的小镇及古希腊一宗教组织所相信的使人失去记忆的泉水”〔15〕。《尤利西斯》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乔伊斯在“隐喻、文体、叙事手段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竭尽能事”〔16〕,引文的运用是《尤利西斯》写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探讨该作品的译者处理引文的过程,可以考察出译者对引文的认知程度,一方面反映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另一方面说明引文翻译越到位,译文与原文在引文方面的间性关系越强,译文也越忠实于原文。
四、译文与译文的间性关系
德里达认为文本的流动是通过“重复、相像、重叠、复制之关系”组织的“镜像过程和折射游戏”〔17〕前文提到的原文与译文的间性关系就是一种重复与复制关系,虽然译者无法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完全对等,但是两文本存在间性关系是不容置疑的,译文是源于原文的复制、变形与延伸。一部作品在时空之旅中会出现多个译本,就是原文本的多次重复与复制。时代变迁,文化语境发生变化,作品“重译”将会持续,“最终定本”也不复存在。间性理论是开放的理论,否认文本意义的终极性,认为文本意义阐释无穷尽,为翻译领域一直存在的一本多译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根据间性理论,任何原文本都是开放的,因此翻译就无所谓“定本”。间性理论还强调语义的流变性,这就是说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确定的纯自然客体,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也会产生新的阐释,但是永远都无法洞悉原作的本真世界。因此不同译本的出现是文化语境交替的必然,就如萧乾、文洁若首先推出《尤利西斯》译本,接着金隄也推出自己的全译本,刘象愚将推出他的全译本,相信未来还会有新的译本出现。译作的诞生使得原作在异域文化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也“必然受到译入语环境中语言文化、政治权力话语、读者等要素的制约”〔18〕,因此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必然也会出现不同的风格,诸如语体风格、文化内涵、翻译策略等就有所差异,但是不管怎样译本都是根据原作翻译的,这种同源关系决定了不同译文之间的间性关系,因此,考察不同译本之间的间性关系紧密度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不同译本与原文之间的间性关系的紧密程度,从而判断译本对原文的忠实度,同时也能考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出现译文变形与延伸现象,从而观测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程度。例如:
In Inisfail the fair there lies a land, the land of holy Michan. There rises a watchtower beheld of men afar. There sleep the mighty dead as in life they slept, warriors and princes of high renown. A pleasant land it is in sooth of murmuring waters, fishful streams where sport the gunnard, the plaice, the roach, the halibut, the gibbed haddock, the grilse, the dab, the brill, the flounder, the mixed coarse fish generally and other denizens of the aqueous kingdom too numerous to be enumerated. In the mild breezes of the west and of the east the lofty trees wav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ir first class foliage, the wafty sycamore, the Lebanonian cedar, the exalted planetree, the eugenic eucalyptus and other ornaments of the arboreal world with which that region is thoroughly well supplied. Lovely maidens sit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roots of the lovely trees singing the most lovely songs while they play with all kinds of lovely objects as for example golden ingots, silvery fishes, crans of herrings, drafts of eels, codlings, creel fingerlings, purple seagems and playful insects...〔10〕
金译:在那美丽的伊尼斯菲尔有那么一片土地,圣迈肯的土地。一座高塔在此拔地而起,四周远处都能望见。有许多大人物在此安眠,许多大名鼎鼎的英雄王公在此安眠如生。这片土地委实令人赏心悦目,上有潺潺流水,水中群鱼嬉戏,有鲂,有鲽鱼。有拟鲤,有大比目,有尖嘴黑绒鳕,有鲑鱼,有黄盖鲽,有菱鲆,有鲆鲽,有青鳕,还有各种杂鱼,以及其他各类不计其数的水族。在西方和东方,高大的树木在和风吹拂之中,向四面八方摇晃着极其优美的枝叶,有飘飘然的悬铃木,有黎巴嫩雪松,有挺拔的梧桐,有改良桉树,以及树木世界的其他优良品种,这一地区应有尽有。美妙女郎在美妙树木之下倚根而坐,唱着最美妙的歌曲,并以形形色色美妙物品为游戏,诸如金块、银鱼、大筐的鲱、整网的鳗鱼、小鳕鱼、整篓的仔鱼、紫色的海宝、活泼泼的昆虫。〔11〕
萧译:在美丽的伊尼斯费尔有片土地,神圣的迈昌土地。那儿高高耸立着一座望楼,人们从远处就可以望到它。里面躺着卓绝的死者将士和煊赫一世的王侯们。他们睡得就像还活着似的。那真是片欢乐的土地,淙淙的溪水,河流里满是嬉戏的鱼:绿鳍鱼、鲽鱼、石斑鱼、庸鲽、雄黑线鳕、幼鲑、比目鱼、滑菱鲆、蝶形目鱼、绿鳕,下等杂鱼以及水界的其他不胜枚举的鱼类。在微微的西风和东风中,高耸的树朝四面八方摇摆着它们那优美的茂叶,飘香的埃及榕、黎巴嫩杉、冲天的法国梧桐、良种桉树以及郁郁葱葱遍布这一地区的其他乔木界瑰宝。可爱的姑娘们紧紧倚着可爱的树木根部,唱着最可爱的歌,用各种可爱的东西做游戏,诸如金锭、银鱼、成斗的鲱鱼、一网网的鳝鱼和幼鳕、一篓篓的仔鲑、海里的紫色珍宝以及顽皮的昆虫们。〔12〕
不同译文间性关系紧密度也是衡量译文忠实度的有效参考指数。第一句话中的“the land of holy Michan”,金译为“圣迈肯的土地”,萧译为“神圣的迈昌土地”,译文显然不一样,这就表明有一译文没有忠实于原文。分析原文我们可以译为“有一片土地,一片神圣的麦肯土地。”不难看出,萧译更加忠实原文,译文与原文的相互指涉程度更高。第二句两个译文的相互指涉性很高,对照原文,两句从整体上都忠实于原文,只是表达上存在差异。第三句两个译文相互指涉程度较弱,说明两者和原文的相互指涉程度出现了差异,主要存在的差异在“大人物”“卓绝的”表述上。如果从宏观来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两译文的总体意思是一致的,但是对照原文还是能看出哪个译文与原文互文性更强。原文是“There sleep the mighty dead as in life they slept, warriors and princes of high renown.”该句是主从复合句,主句是倒装句,主语是“the mighty”,谓语是“sleep”,表语是“dead”。因此“the mighty”译成“大人物、有影响的人”应该都是可以的。而后面的“warriors and princes”是“the mighty”的同位语,所以我们可以把“the mighty”翻译成大人物更加忠实原文。笔者把该句翻译成“那些大人物,无论是显赫的武士还是煊赫的王侯,都长眠于此,就如他们活着时一样的熟睡着”。相对而言,金译和原文互文性更加强,萧译和原文互文性稍弱些。第四句,两译文除了在鱼的名称翻译上有所差异外,其他翻译基本上一致,互文性很强。对照原文,两位译者的译文都忠实于原文。第五句的“In the mild breezes of the west and of the east the lofty trees wave...”两个译文不完全相同,金译为“在西方和东方,高大的树木在和风吹拂之中”,萧译为“在微微的西风和东风中,高耸的树……”。显然这两句的间性关系不是非常的紧密,说明其中有一个译文或者两个译文和原文的互文性不强。笔者翻译为“在和煦东风和西风中,挺拔的树林……”这样和后面的“in different directions”(四面八方)形成呼应。比较两译本发现萧文和原文的间性关系更为紧密,也更加忠实于原文。第六句两个译文互文性非常强,和原文的互文性也非常强,应该说都是非常忠实于原文。
通过上述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研究不同译文的互文性可以突破传统的译文比较研究仅局限于字词句段的微观层面的不足,从文化语境、语言风格等宏观视角也可以分析哪个译本翻译得更好。不论解构主义者如何解构原作,原文的意义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译文源于原作,因此不同译文与原文的相互指涉是相对确定的。判断不同译本是否忠实于原文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考察不同译文之间相互指涉关系是否紧密,译文间性关系越强,译文与原文的间性关系也越强,反之,可能是某一译文或者某几个译文都和原文的间性关系不够紧密,也就表明该译文不忠实于原文。
五、结语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探讨翻译的文本间性不能局限于原文和译文之间,还应包括与原文和译文发生直接指涉关系的所有文本对象〔19〕,这涉及原文、译文、引文等诸间性关系。语言层面的翻译文本研究重在对照译文与原文对字词句段的处理,考察用词是否精确,表达是否流畅,是否达到形神具备的效果,这是评判是否为“佳作”“范本”的标准。翻译文本间性研究打破了这一局限,它不仅探讨译文与原文的间性关系,也讨论引文与译文的间性关系,还讨论译文与译文的间性关系。间性关系研究为翻译的等效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译文与原文间性关系涉及意义、句型结构、风格等,它们之间在这些因素上相互指涉的程度越高,两者的等效性越强。把引文与译文引入间性研究,一方面可考察译者对引文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可考察译者对原文中的引文翻译效果,引文识别与翻译可作为译文与原文的相互指涉程度的观测指标之一,引文识别度和翻译等效度越高,说明译文与原文的间性关系越紧密。译文与译文间性关系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判断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另一方面有益于判断哪个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事实上,文本间性研究也不能完全割裂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研究,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但是,无论我们探讨文本间性还是文化间性,都离不开翻译的相关主体,译文最终是否被读者接受,离不开翻译各主体的努力,特别是译者的努力,译者要具有优秀的双语素质,还要“主动地和其他间性主体协商、沟通”〔20〕,让原作在异域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延续。那么在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如何才能实现文本间性紧密度呢?笔者认为,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要尽可能地把译文与原文的相互指涉关系最大程度地呈现出来,不能随意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避免导致译文的扭曲、变形。即便改造过的译文深受读者欢迎,如果译文和原文渐行渐远,也是不值得提倡的。间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把翻译客体(文本)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时空之中,拓展了文本研究的宽度与广度,特别是把翻译的忠实标准更加清晰化和可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