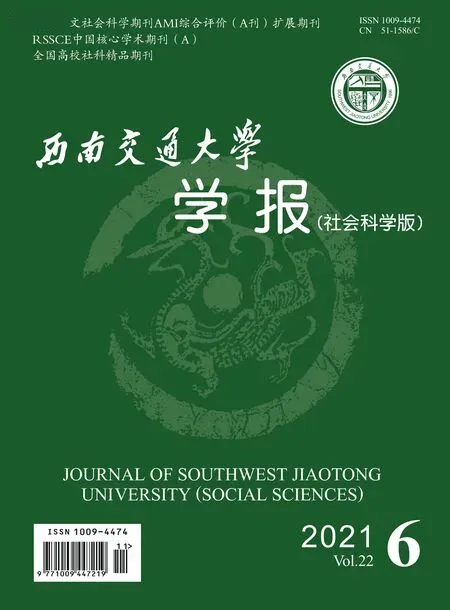纳张元文学语言风格分析
鲁湘珺
纳张元是新时期云南彝族代表作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民族作家。云南彝族山寨特殊的成长环境造就了纳张元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其文学作品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审美上都具有一种独有的味道。纳张元善于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方言俗语,以现实的笔触描写彝寨的生活现状、刻画人物形象、体悟现实生活,其作品用词用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平实的语言中充满温情、富含哲理,这种独有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是与其成长环境、创作意识及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
一、纳张元文学语言风格形成的影响因素
纳张元特殊的成长经历和生存环境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文学作品中不管是词语的使用、句子的选择,还是思想内涵的呈现都是他对家乡的观察和思索,他的文学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述。
(一)立足本民族文化反思创作意识
每个作家的成长都是有机缘性和必然性的,纳张元从小奔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童年在牛背和彝山的古歌中度过,后来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学习了一些“蚂蚁脚杆”的汉字,发现了故乡的落后。这种落后不仅是经济的落后,也是地域的落后和思想意识的落后〔1〕,作者从思想层面对家乡的落后提出了一种反思,其文学语言充满着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语言表达特点。
纳张元曾在陈思和教授组织的复旦大学开展的“那张元作品研讨会”上说:“我开始关注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外面人看我们,更多看到一些美好的方面,我倒觉得许多东西值得反思。自己写自己的民族,可以如实描写,没有顾忌。”我们在作品中会看到一些语言文字确实是他对故乡现状的一种反思,他不仅在思想上反思民族生活的现状,同时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创作理念,即“一是在语言上找到自己的个性,二是不简单流于风情描写,而致力于文化反思”〔2〕。所以说从纳张元的陈述中看得出他创作意识的建构是源于对家乡民族生活的关注,也因此形成了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语言风格。
纳张元立足本民族文化的创作意识直接影响到他的词语使用和修辞手段的选用,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充满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和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修辞使用手法〔3〕,这些文字使用手段形成了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在纳张元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人生思考不是单一的,他不仅在思考自己的何去何从,甚至还在思考家乡人的何去何从?在《山中,有梦想的天空》里他在启蒙家乡的学子,同时更多的是在诘问为什么山里人走不出家乡“酒碗”“火塘”这两个“怪圈”〔4〕,这是彝族人生活的两大日常必备,牢牢地拴住了向外挣脱的彝族乡民。通过作品中学子的思索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的人生思考,他在寻求家乡的发展之路。
(二)地域文化和成长环境的影响
云南是典型的山区地貌,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眼里除了山还是山,目光所及之处总是连绵无际的山,天空的星斗总是离人们那么近,也因此形成了人们特殊的认知方式和审美理念。纳张元从小在彝族古寨长大,他对这里的环境是熟悉和热爱的,这里的山山水水影响着他的创作,形成了特殊的语言修辞使用特点。如:
(1)千里彝山,枯瘦如柴。山里人的天地,另是一种风景。仰望高空,直到把帽子仰掉,才见窄窄的一线蓝天,七歪八扭地夹在两座枯瘦的大山之间。只有星星和月亮,每晚从东边的山顶一步跨到西边的山顶,钻进树枝,躲起来睡觉。若是雨天,两山之间就拉了一块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沉甸甸的雷声在山顶上轰轰隆隆地滚来滚去,让人毛发倒立,脊背发凉。〔5〕
在例句中作者将“彝山”比作“柴”,“彝山”和“柴”两个本体和喻体都是源于生活,作者将人们所熟悉的两个物体“山”和“柴”做出了形象的比喻,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山”的枯瘦和贫瘠;“星星和月亮”是“跨”“钻”“躲”,这样的描写将物赋予人的特性,使得山里的形象更为灵动;“拉一块黑布”“雷声滚来滚去”,几个形象的拟人化动作描写凸显了山里环境的狭小逼仄。“课堂上讲的‘天是无边无际的,地是一个圆球’”和山里人实际生活中的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山寨岁月》里,小路是崎岖和险陡的,“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细细的”“悬悬地挂在半山腰”却又是灵动的,“攀着大山”“串起山寨”。作者用“攀”“串”“悬”“挂”这些形象的词语写出了通往山寨的山路的崎岖和险峻,同时在文中还刻画了傍晚彝寨的特殊美丽景色,用“争挤”“沐浴”“等在”“站”“拽弯”“懒洋洋”“慌里慌张”“钻来钻去”等词语写出了一个鲜活的山寨形象。“倒拖着”“斜挎着”“歪戴着”写出牧羊人慵懒的形象,对撵山狗“拖一路凄婉的抱怨声”拟人化的描写,整体写出了彝寨日常生活的祥和之景。
文艺理论认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为文艺评论家的纳张元,他的文艺创作在这一点上把握得炉火纯青,在他的形象化的、艺术化的语言里,随处可见比喻、比拟等修辞表达,他的本体、喻体都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纳张元是在牧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6〕,其语言文字蕴含着放牧的情怀。如:
(2)我久违了的水牛背,你是否平稳依旧?我梦魂牵系的羊群,你是否悠游潇洒一如当年?不管这世道怎么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读书是一种受人尊敬的高尚行为。〔5〕
“我久违了的水牛背,你是否平稳依旧?我梦魂牵系的羊群,你是否悠游潇洒一如当年?”这真的是作者在问牛背,在问羊群吗?当然不是,“牛背”“羊群”的意象是作者记忆深处的意象。而这种意象激起了作者对过去自由、悠闲的放牧生活的向往,其实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无拘无束的放牧生活是生活在城里的人无法体验到的,在城市高压生活下作者想寻求一种生活的平衡,所以说这里“牛”“羊”的“悠游潇洒”可以说是作者的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感悟。
特殊的成长环境可以说对纳张元语言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用词、用语的风格,也包括修辞手法的选择等。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具有特色的作家、充满生活活力及思考力度的作家,其作品中总能感受到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二、纳张元文学作品语言风格特征
“语言风格也叫言语风格,它是使用语言特点的综合,是语言表达上特有的格调和气派。”〔7〕表现为个人风格就是以“个人惯有的选词、造句和特有表现手段以及修辞方式的运用。”〔8〕个人语言成熟的标志就是形成个人风格,个人风格的形成是长期语言使用的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文本中可发现纳张元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语词使用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
纳张元是一个很有民族文化情结的作家,他在接受大理电视台采访时曾说过他在文学创作中呈现自己本民族生活时用普通话常常会感觉到词穷,所以他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9〕,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如:
(3)叭,哒!叭,哒!两把磨得只剩巴掌大小的片锄互相挤着,挖得有气无力。一对和两把片锄一样衰老的老夫妇紧挨在一起,喘着沉重的粗气,都想尽量替对方多挖点。山地里全是膝头深的杂草,仔细辨认,才能看出在密匝匝的杂草丛中,稀疏地夹杂着几棵焦黄的包谷苗。别人的包谷三道草都薅完了,他们还头道草都没挖。
“今天太阳真辣。”男的搔了搔灰白的头发说。
“嗯,是很辣。”女的也跟着理了理同样灰白的头发。
“再挖几锄去歇歇。”
“嗯,再挖几锄去歇歇。”
“反正苦死也就这么回事。”
“嗯,就这么回事了。”〔5〕
在例句中出现了“片锄”“膝头深”“密匝匝”“包谷苗”“三道草”“薅完”“头道草”“太阳真辣”等方言词,这些方言词的使用增添了语言的趣味性,其中“挤着”(挤在一起的意思)、“薅完”(除去地里的杂草的意思),“苦死”(拼尽全力去做的意思)这些方言词的运用,增添了语言的趣味性和地域性,通过方言词语的使用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彝族山区普通百姓劳作的场景图。“叭,哒!叭,哒!”拟声词的使用凸显了劳作者有气无力的神情,在烈日的暴晒下,辛苦劳作的场景被勾勒了出来。作品中接着一系列的动作、神态、语气的描写,都凸显出劳作者的艰辛。
(4)男的用右手在脑门上搭了个凉棚,仰头缩脖,脚杆弯弯地向山梁上观看,女的也用同样的姿势手搭凉棚脚杆弯弯地跟着男人看。远远看去,包谷地里两个弯脚弯手的老人就好像两只老猴的剪影。〔5〕
“手搭凉棚”是一个方言词,意思是把一只手放在额头处用来挡光,从而向远处眺望。这个动作常常出现在劳动的场景中,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彝族劳动人民的身影。通过“弯手弯脚”“包谷地”等方言词的使用就更加形象地衬托出两个年迈的彝族老人的形象。
(5)果然,大熊开始嗅多比的脚、身子、头、耳朵,多比头皮发炸,心跳停止,几乎失去知觉。〔5〕
作者描写了一个试图用假死来蒙蔽大熊的彝族猎人形象,用词充满乐趣和紧张感,在例句里“头皮发炸”的意思就是头皮发麻,表示心里因紧张从而产生的一种身体知觉反应,作者运用一个充满感官感受的方言词突出了人遇到野兽时的紧张感,描写形象生动,贴近现实。
(6)这些猎人,谁也不是脓包,豹也打得,熊也猎得,怎就偏偏对一个麂奈何不得?〔5〕
这是作者对一个狩猎场景的刻画,彝族同胞历来都是狩猎的高手,其祖先是在与野兽赛跑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们对狩猎是充满自信的。文中“脓包”的意思是不聪明、笨的。这个词是彝寨常用的口头禅,当别人不符合自己的判断标准时,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个词语的使用突出了彝族人的一种反讽心理,意在凸显彝族同胞对自己狩猎技术的自信,同时也传达出一种思想意识,即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无法猎得麂子,而是彝寨的人们已经改变了生活方式,狩猎不再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人们开始萌生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念头。所以“脓包”一词在这里是特殊用意,即反语的用法,旨在说明彝族猎人随着社会变迁,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
方言俗语呈现在作品中会增添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读者还可以更多地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风民俗。
(二)修辞格使用的变异性
纳张元作品的风格特点还体现在他的修辞格的使用上。复旦大学钱益焦曾这样评价纳张元的写作:“我觉得他的作品特别在语言上还是很有彝族的独特色彩,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喻,这在一般汉族作家作品中是看不到的,而在他却是信手拈来。”〔2〕如:
(7)五月的骄阳像一盆火,高悬在湛蓝的天空;五月的大地像一座烧透了的砖窑,憋闷得透不过气来;五月的人们生活在炼狱里,被热情的太阳折磨得死去活来。〔5〕
作者将“五月的太阳”比作“火”,将“五月的大地”比作“烧透了的砖窑”,独具特色的比喻源于生活,形象生动地营造出彝寨五月太阳毒辣、天气燥热的气候特点。这种表达是纳张元独有的,他在出其不意中表现出幽默诙谐的效果。他的思维跳脱,打破了读者的正常思维方式,如文中“热情的太阳”,顺势思维应该是写好的方面,但是其后的“折磨得死去活来”却不是对热情太阳的享受。这样的描写既写出太阳的无辜,又表现了人们在火热太阳下的煎熬,一句话同时描写了两个意象主体,而且两个语义方向是矛盾的,让读者既哭笑不得,又觉得幽默诙谐,在笑中体会生活之艰辛。
(8)黑夜像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把平川坝搓细揉扁,五月的山风带着山汉子的醉意,在坝子四处游荡。〔5〕
将“黑夜”比作“毛茸茸的大手”,“五月的山风”拟人化为“带着山汉子的醉意”。作者用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对“黑夜”“山风”进行了狂野、狠辣形态的刻画,创设了一种危险意境,将栽秧妹置于一种危险环境中。
(9)弯弯的月儿被乌云拖进黑暗之中。文明被野蛮蹂躏,圣洁被邪恶玷污。历史在这里倒退,人性回复到远古的野兽时代。〔5〕
在这个例句中,作者描写了栽秧妹来到城里打工却遇到了危险的场景,漂亮的栽秧妹被包工头摧毁的悲剧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在这里语言的描写是极为成功的,作者不是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衬托写出这种丑恶,首先是“月儿”被“乌云”拖进黑暗之中,是借助“物”的变化和感受来衬托出人物所遭受的伤害,将“月儿”“小八妹”“央特”等同起来。“文明”“圣洁”是多么的美好,可是却惨遭破坏,“被野蛮蹂躏”“被邪恶玷污”这些语言更加体现了作者的这种不忍,其实在这里“月儿”的伤心也就是发话主体和受话主体的伤心,景物为人物而悲鸣、伤怀。作者在这里通过变异的修辞格以景写人、以人伤景,景与人产生了共鸣的艺术效果,同时烘托出丑恶的人性将文明与美好践踏得体无完肤的悲情,深沉的意境创设最终达到了一种情感释怀的艺术审美效果。
(10)这天晚上,二月妹迟迟不能入睡,直到半夜,她的心还跳得很厉害。橄榄树下野性的山歌溶化了寒冷的冬季,葫芦笙单调的旋律吹出一个不幸的春天。〔5〕
“野性的山歌溶化了寒冷的冬季”,这种变异化的修辞搭配超乎寻常,使得语言描写寓景于情、情景交融。对于二月妹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因为她遇上了心爱的人,可又是一个悲惨的夜晚,因为这个人将给她美好的生活带来灭顶的灾难。作者将两条线索交叉使用,一条是喜悦的二月妹,在她看来“今夜的歌能溶化寒冷的冬季”,“月儿是清澈透明的”;另一条是作者,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不幸的夜晚,所以葫芦笙吹出的是一个“不幸的春天”。这两条线索是作者故意创设矛盾意境,以突出人物的悲惨命运,从而达到审美的艺术效果。
(11)古朴的大山已苍老成一个深不可测的谜。火塘像一个魔鬼的怪圈拴住了一代又一代想向山外挣扎的人。“悠长的岁月像一个魔力无穷的魔术师把无数血气方刚的彝家汉子揉搓成皱巴巴的干瘪老头,一腔豪情顿时幻化成无奈而绝望的长叹,轰然一声,好汉像山一样沉重倒下,成为一段历史,化作一个传说。”〔5〕
“大山”是古朴的,并且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加上“火塘”这个彝族生活标志性的意象,阅读者感受到了彝山的重复、单调、无力的生活。作者将大山拟人化,如同人一样会苍老,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山更加充满着神秘感,这种拟人化修辞格的使用,是作者情感的一种释放,作者内心情感从奔流到沉静,体现出他对现实的一种奋力挣脱、努力超越的精神。
(三)平实语言中充满温情
纳张元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作家,其涓涓细流般的文字在平实无华中写出了真情,这种真情体现在他对女性温情的书写。在其作品中彝寨人的生活是艰辛的,特别是彝寨的女人,她们物质条件匮乏,精神也受到束缚,在艰难的环境下她们却不屈不挠地为家人、为孩子谋生活。纳张元在这种矛盾的生活中发现了母性的温柔和伟大,于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刻画了鲜活的形象,抒写了对她们的热爱,最能体现他这一语言特点的是《秋天的困惑》和《母亲的眼泪》两篇小说。
在《秋天的困惑》中“挨”“扶”“买回”“露出”“淡忘”这些单音节动词及动词词组的使用增加了语言的平实感。读者通过阅读感受到的是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彝山妇女不仅要承受劳作的辛苦,还要承受男人们酗酒后的毒打。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她们却无怨无悔,她们用善良的温情为自己的孩子筑起了一堵温暖的“墙”。“买来的花布变成了衣服穿在娃崽身上,娃崽们高兴得像一群青蛙”,在形象化的比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孩子在母爱的关怀下,甜蜜地享受这困苦生活中的温情,母亲“甜蜜的微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温情。
这种母性的温情在《母亲的眼泪》中得到了彻底的展现。《母亲的眼泪》从母亲贤淑、性格坚毅的感情基调出发,描写了母亲的三次流泪,刻画出了母亲对“我”的深切关怀及面对困难的不屈不挠。第一次流泪是因为生活的艰辛,“我”在寒冷的冬天,由于没有鞋,脚背有很多口子,走动时就会冒出血珠,这时母亲在火塘边轻轻地揉搓着“我”的双脚,洗去污垢,然后用羊油帮我擦拭,而“我”疼得在吸凉气,母亲看到这些,不由得流下了眼泪。“她像断了线的珠子的眼泪,合着羊油一起滴在了脚的裂口上。”这其实是一种爱和温情的情感展现,母亲平凡的爱通过眼泪滴进了儿子的心里。
母亲第二次流泪是因为“我”莫名其妙地病倒了,还一直没有苏醒,甚至被下了病危通知。这时的母亲很是着急,着急于儿子的生命,于是留下了关切的眼泪,“母亲凉悠悠的眼泪唤醒了我”,在母亲爱的凝视下奇迹般一天天好起来。
母亲第三次流泪是因为“我”考取了大学,家里却无法置备像样的行李。在开学的日子母亲给“我”做了糖水面条,看着窘迫的行李,想着儿子往后的校园生活,母亲又一次流下了关切的眼泪。作者用“发愁”“做饭”“捞面”这些词语来刻画人物心理,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情感。母亲为什么会担心“我”?我们在后面找到了答案,“毡条印满尿痕”,我们突然就明白了“母亲的话语”及“眼泪扑簌簌地掉进碗里的原因”,同时体会了“吃甜食吃出咸味”的心境,字里行间充满了母亲对作者的爱,也是作者对母爱的体悟和思索。母亲的眼泪化作了爱的力量,作者从一次次的泪水中感受到的是母亲浓浓的温情以及艰辛生活中的坚强。
纳张元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思索,有了对彝族山寨“母亲”的生活和情感的深切体悟。在他的笔下我们感受到“母亲”的温柔和坚强,面对生活困境,母亲永远会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孩子撑起一片爱的港湾。所以说在纳张元的作品中不管是迎着醉鬼的打骂换回布匹给娃做衣服的母亲,还是艰辛劳作后照顾孩子、用热泪唤醒昏睡的孩子、给孩子准备寒酸行李的母亲,都是充满了温情的母亲,对这种母爱情怀的抒发也形成了纳张元特殊的语言文字风格。
(四)富有哲理性的语言表达
语言文字是作家对人生的感悟和生活认知的反映,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作家的思想内涵。纳张元是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他对家乡的描写总是在娓娓道来中蕴含着深层的反思,他对家乡的深沉爱恋不是简单的赞美,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体悟、一种感知,所以语言表达上就会展示一种哲理性。
《彝山速写》是作者对家乡自然环境的思索,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时间岁月流逝的感悟。“枯瘦的山脊”“天地一缝”是作者笔下的彝山环境,在贫瘠的土地上人们在为生活而奋斗,在作者看来曾经追着猎物奔跑的日子在发生着变化,现在人们都在耕耘着土地,彝山人民的生活方式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作者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用“怒吼”“摇晃”“折腾”这些具有张力的词语将“山风”写得狂乱而又无情。“牛群、山羊、狗”几个意象构成了彝族特有的画面,这些词呈现了一种历史画面感,也给彝山增加了一种厚重感。“山羊们随着四季的更替在山沟野谷中来回奔波,肥了又瘦,瘦了又肥,不知不觉,就长了胡子,都老了。”作者用衬托的手法,以物衬人,用短句写出岁月在日常周而复始的单调生活中流逝的生活现状。
作者采用层层推进、比拟的修辞手法写出了时间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流逝的现实,同时通过“感受到时间的无奈”“孤寂中漂泊而过”“单调无聊的磨牙声”这些艺术化的语言呈现成了作者情感体验的外化形式。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思考影响着其语言创作,“太阳十分苍老”“锈迹斑驳的思想”这些蕴含着人生思索和生活哲理的语言让读者多了一份感悟。“只剩下最后憔悴的几年时,冬季的某个深夜突然一齐从沉睡中觉醒”,可以说在周而复始的单调生活中的人们觉醒了。纳张元通过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观察和思考,发现了时光在平淡无奇的岁月中一点点儿消逝,而容易被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忽视,他们总是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轨迹。作者通过具体的、贴近生活现实的意象的描写刻画,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时光流逝的残酷性,想要激起人们追赶时光、创造生活的激情。
纳张元的成长日记是对生命的沉思和对生活的执着。在《山道悠悠》中我们看到的是励志的少年形象,在艰苦的生活岁月中奋力成长的少年精神,这种精神给我们力量和情感的冲击。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苍凉狭小且逼仄的山里环境。“千里彝山”写出了山的连绵起伏,同时又是“古朴苍凉”的,视线范围内的蓝天只有“簸箕大的一片”,小路则是“攀着大山的”。就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彝家的少年却觉得迎着这些小路可以通向山外,他们奔跑在这希望的山间小道上,小道串起了彝山少年的质朴与希望;年少求学的艰难岁月的积淀,成了这些意气风发的少年的精神财富,成了他们在世事沧桑中生活的底气。也因此具备了在以后的生活岁月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生活风雨,都会有坦然面对艰难险阻的态度。这是大山赋予的灵魂和精神,在大山间的奔走历练了少年的意志。《山道悠悠》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在艰难环境中的一种不屈和抗争精神。
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情感体验的外化形式,是发话主体内心感受的主观呈现,纳张元的文字充满了这样的神奇力量,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获得了情感的一种释放,语言充满生动感和活力感。“小路攀着大山”,孩子们的“好奇希望”被“挂在”了山外,“好奇希望”能“挂在”山外吗?这种超常的语言搭配,形成艺术化的语言,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大山对山里人的阻隔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纳张元善于用形象化的描写突出人物形象,孩子们周末奔波在崎岖小路上的模样被写活了。山路艰辛,物质生活贫乏,却摧不垮孩子们的意志,反而铸就了他们乐观和坚强的性格,“那是生活对我们的一种馈赠,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艰苦的岁月成了少年时期的一种精神锤炼,从生活中获得了感悟和力量。读着这样的文字,少年求学的生动画面映入了读者眼里,积极乐观的精神感染着读者。可见语言是有生命力的,它可以激发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共情。
少年时的成长环境熔铸成了纳张元的精神财富,在艰苦的生活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获得了深层的人生思考。在《山坡上的羊群》里,“羊群”成了“我”内心最深的记忆,而爷爷的生活态度、生活思索更是成了“我”的精神财富,不断激励着远走家乡的“我”努力奋进,适应着城市的生活,所以就有了“放牧生活”和“被生活放牧”的人生思索的对比,更加清晰地摆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即在城市中追寻生活梦想的同时也要轻松洒脱,绝不会让生活现实摆布自己的精神。
三、结语
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与他们的创作意识和生存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主观到客观的联合作用,会形成不同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形式,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使用风格〔10〕。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进步,思想意识的不断深化,文学作家也会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养分,形成不同风格的语言表达形式。
纳张元文学语言风格特征的形成受到了其成长环境和创作意识的影响,其寻根意识造就了他回归故里的创作情怀。他总是对母亲充满着温情和感激,所以在他的语言陈述中就有了一种温度和情怀,在他的笔下女性是善良和坚强的,他用充满温情的文字刻画了彝族母亲的形象;他如实地描写家乡险恶的生存环境,所以语言呈现出地方特色,同时这种语言表达又富含哲理性。纳张元对家乡、人、物、景的描写和深刻体悟,最终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学语言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