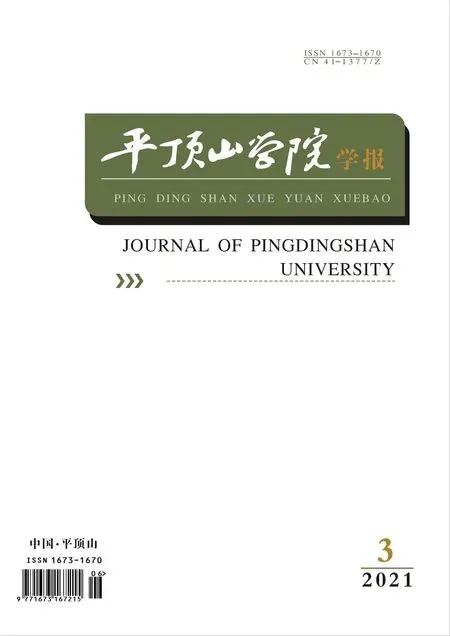清华简新见神话谫论
唐滟萍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中国神话没有形成大型的鸿篇史诗,而是以零星片段的形式散见于先秦及汉以后的古籍中,这为中国神话的研究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必须在众多的古籍中如大浪淘金一般将这些神话碎片辑录出来,然后熔铸拼接成中国神话的体系,前人学者们对此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同时,正是因为它散碎的特点,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也为中国神话的研究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新发现。清华简中所保留的神话传说内容是探索战国时期神话的时代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神话流传演变及构建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今选取其中神话色彩比较明显的三篇——《楚居》《赤鹄之集汤之屋》《八气五色五祀五行之属》展开讨论。
一、《楚居》与族源神话的发展
《楚居》是一篇与楚族起源有关的简帛文献。“竹简凡十六支……无缺简……书写工整,是典型的楚文字。”[1]180它主要是讲述楚族先祖的居住地以及迁徙过程,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战国中期,因为具有传说和史实整合的特点,其性质应该介于史书和子书之间。虽然作者在著述时固然有自己的历史观,但由于所记内容仍处于“传说和史实混而不分”的时期,因而无论是对楚族早期历史起源和楚地地理研究,还是对楚民族的族源神话研究,《楚居》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简文以“季连初降于□山”开篇,而从传世文献中可以了解到楚族的先祖一般可以追溯到颛顼,归于黄帝一脉,或有学者认为简文有缺,但清华简保存相对完整,且从竹简形制以及“初降”的文字表述看,记事应确从季连开始。这里的“降”是特指神的降临,《楚居》的作者将季连视为楚族的先祖,但因为这一时期降生神话的流行以及楚族巫文化的盛行,无法完全摆脱神话思维,因此也为其先祖赋予一层“神性”,这在早期记载国家或者宗族部落的史类文献中是常见的。与后世史书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不同,前者是一种无意识的神话思维,而后者则是统治者通过神权来强化王权的一种手段。
《楚居》一文基本完整无残缺,战国中期的楚人记述自己先祖居住地和迁徙路线以季连为开篇,而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则将楚族先祖推至黄帝之孙颛顼高阳,这与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相合。顾先生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战国中期的楚人认为其先祖为季连,而到了汉代则进一步将季连的祖先推至黄帝,这样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在传说时期,季连确实属于黄帝部落的后裔,只是这样的传说一直通过口耳相传,直到汉代才出现书面文字的记载;其二就是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原有的各氏族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使百姓产生统一的认同感,而《楚居》的成书时期仍处于“始祖诞生神话”的盛行期,大一统的思想还未形成,分封制度使得各氏族仍保留着部落的宗教信仰,因而有各自的族源神话以及始祖诞生的神话。如商民族的始祖是商契,周民族的始祖是后稷,根据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不同,其始祖的诞生神话有一定的区别。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楚居》作者在有意识地写史,是因为在描写丽季出生时,作者有意识地削弱了神话色彩。《大戴礼记·帝系》中载:“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氏,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左肋,三人出焉;启其右肋,三人出焉。”[3]而在《楚居》中则只交代了妣因难产而死,“巫并该其肋以楚,抵今曰楚人”[1]181,点明楚人之楚的来源。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已经开始逐渐将其族源神话历史化,抛去其中的神异部分,形成写实的历史记录。这对史学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同时也影响了神话传说的流传演变。
二、《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原始巫术神话
《赤鹄之集汤之屋》(以下简称《赤鹄》)是具有“小说”性质的一篇文献,与其他篇不同的是,《赤鹄》在叙事风格上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和巫术色彩,这对早期小说研究和中国神话研究、民俗研究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赤鹄》共十五支简,三道编,简长四十五厘米。全篇记载了商汤捕获了一只赤鹄,命令伊尹为之烹煮,并由此引发了一些神异之事。伊尹本是商王朝君主汤的重臣,出身低微,汤举之于庖厨之中,后助汤灭夏,因此关于伊尹的传说流传颇广。传世文献关于伊尹的传说主要见于《吕氏春秋·慎大》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吕氏春秋·慎大》篇讲述了伊尹为汤谍于夏,与妹喜交,加速夏亡的传说。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提到了伊尹母亲妊身溺死化作空桑之木,水干之后,伊尹出之,有莘因厌恶伊尹生于空桑之木,因以送女的传说。而《赤鹄》篇的内容恰恰发生在这两个故事之间,为伊尹传说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材料。
《赤鹄》一反传世文献中明君贤臣的情节,汤不再是于庖厨之中发现伊尹之贤的明君,而是因为伊尹受汤后威胁尝汤之羹而大怒,并对伊尹下诅咒的“暴君”形象。君臣反目,伊尹出逃,被巫鸟所救,并得到关于夏桀病因的指示,从而解救了夏桀的故事。李炳海先生在《清华简〈赤鹄〉的越文化属性》中认为这是因为《赤鹄》成书于刚被楚国灭国不久的越地,楚越文化并未完全融合,因此《赤鹄》虽由楚文字书写,但仍保留着越文化的属性[4]。因此叙述视角上抑商汤而救夏桀,这为我们看待《赤鹄》神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在朴素的、更接近于原始的越文化中,受巫术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神话传说。
关于《赤鹄》故事中巫乌、白兔和黄蛇的角色,从巫术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确实存在的,是自然神的崇拜和巫祝行为的实施媒介。但从神话发展的角度看,不妨将它们看作是原始社会初期的神话遗留,即袁珂先生所提到的活物论神话向万物有灵神话过渡。袁珂先生指出:“最早一批的神话,实在便是一批动物、植物故事,尤其描述禽言兽语的动物故事是神话的核心……它所续写的能言会走的动植物,在原始先民的眼光里看来,都是实有的东西,而且因有看不见的纽带和这些东西相联系,精神上还会起到一种震颤。”[5]之后巫术活动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图腾崇拜和自然神的拟人化,万物有灵神话随之而生。而《赤鹄》中说:“小臣乃昧而寝于路,视而不能言。众乌将食之。巫乌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夏后有疾,将抚楚,于食其祭。’众乌乃讯巫乌曰:‘夏后之疾如何?’巫乌乃言曰:‘帝命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之栋,其下舍后疾,是使后疾疾而不知人。’”[6]167在这段话中,巫乌虽已具有万物有灵时期自然神拟人化的特征,但尚未完全摆脱活物论时期的朴素的特点。巫乌被赋予特定的神性,在拟人的同时担任着传达“帝”的信息,成为比众乌高一等级的“神乌”,但众乌保留着动物本来的特点,只是增加了能言的属性。至于受帝命而通过巫蛊的手段作祟以害夏桀的黄蛇和白兔,从巫术的角度上看,已经因为其自然特点而成为进行某种巫术活动的工具,弗雷泽在《金枝》中记述了通过接触某物来对某人或物施加影响的交感巫术。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确有其事”的记述,但现在来看,实在是万物有灵早期神话的遗留。也正是因为越文化的朴野和巫术活动的兴盛才使得这样一篇具有活物论向万物有灵论过渡的神话文献得以保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宝库。
三、清华简关于后土神话的演变
《清华简》的《赤鹄》篇和《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篇都提到了后土。特别是《赤鹄》篇中提到的后土故事,更是丰富了传世文献中后土神话的内容,作为记载后土神话的早期文献,在后土神话研究以及土地信仰民俗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后土神话的形成来源于人们对土地的信仰。人们起初将自然界中的万物看作是和人类平等的存在,相信万物有灵,后来巫术活动兴起,对自然之灵的敬畏逐渐上升到对自然神的崇拜,产生了天神、地神的信仰,祭祀活动产生,原始先民眼中土地的“灵”逐渐转为具有“人格”的后土神。这一转变过程尚无文献可考,我们只能根据神话的发展去推测一二。
关于后土的身份和神职,在传世文献中记载略有不同,但大抵分为三类。其一是黄帝的佐臣,《礼记·月令》中提道:“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黄帝,其神后土。”[7]143-144《淮南子·时则》中亦云:“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二万里。”[8]其二是共工之子,《山海经·海内经》云:“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9]其三是幽都的统治者,《楚辞·招魂》云:“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王逸《章句》注云:“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10]
后土神的地位随着人们对土地的信仰观念经历了一个变化,形成了低级神——高级神——低级神的转变。由高级神到低级神的转变在传世文献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国语·鲁语》中说: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11]在先秦时期,“社”被人们当作土地之神来祭祀,与“稷”合称为“社稷之神”。社稷在先秦时期是与国家和人民息息相关的,因而社稷之祀是大礼,且古之世社之祀最隆重,因此,在这一时期,后土有一个比较高地位的神职。而到了汉代,人民对社神崇拜的概念逐渐淡薄了,后土也就从土地之神变为统辖幽都的神职,而土地神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地位衰微,成为保护一方土地的小地神。
而清华简正填补了后土神话早期阶段由低级神向高级神转变的文献空白。在《赤鹄》篇中,后土受帝命作祟于夏桀,使夏桀疾,“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体,是使后之身疴,不可及于席”[6]167。同时,在《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中也有交代“后土率土以食于室中”[12]。这一时期,后土已经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代表着五祀之一的“室中”,这也与他受命藏于夏桀床下起二陵屯作祟相合。室中,五祀之一,在文献中作“中霤”,《礼记·月令》:“其祀中霤。”疏曰:“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则土神也。杜注:‘春秋云在家则祀中霤……而在国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7]144可以看出,在《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篇中,后土作为社神的重要地位已经在祀礼中有所体现。而《赤鹄》篇因为受越文化属性的影响,虽然具有“率土以食于室中”的能力,参与了“使后之身疴”的巫术行为,但尚未成为受人祭祀、护佑国土的“正神”。
通过上述对三篇简文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无意识的“史影”遗留,还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抑或是巫术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崇拜,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神话流传和演变情况,即一部分在已有神话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工再创作,丰富了文本的内容;而另一部分逐渐被历史学家历史化,形成历史的一部分,其中族源神话的发展变化最为明显。而我们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神话,应先辨明这一神话传说的成书时期,然后将这一部分的新材料,归入相应的神话流传演变体系中去,填补神话流变中出现的空白,探索某一神话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分析神话传说在不断地流变中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政教影响以及民族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