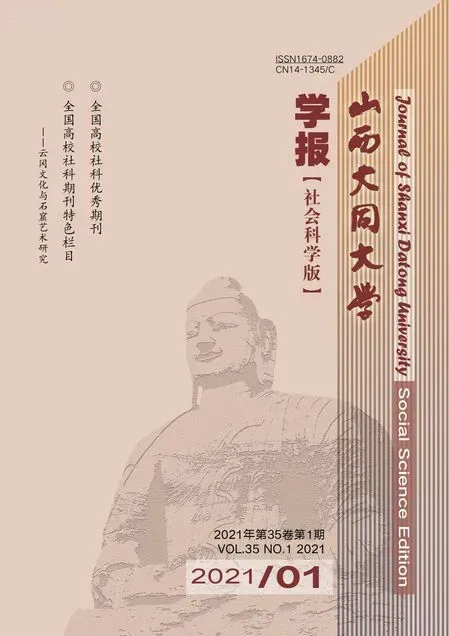“他者”的觉醒:《豆棚闲话》的新历史主义观照
王鑫昊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艾衲居士编著的《豆棚闲话》诞生于明清鼎革之后,以“豆棚”作为叙述者讲故事的场地。该篇包含文章十二则,内容涉及历史朝代变迁与社会世情乱象,其中历史题材的有第一则《介之推火封妒妇》、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与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以新历史主义视域观照该文本的他者性及他者的觉醒,能更好地揭示该文本文化语境下的文本与思想突破,打破以往文本受制于历史的限制。这对人们以多元视角重新审读经典文本、重新考虑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他者与《豆棚闲话》的新历史主义观照
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相信历史是一系列具有线性因果关系的事件,重点放在“什么是历史”的事件真假以及为人们提供了哪些信息的问题上。它以客观再现历史真实为旗帜,力求为人类知识的探索确立秩序。体现在文学领域,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以研究作品及事件产生的历史时期为基本模式,将文学的主观色彩寓于历史的客观性中。历史的发展和文学文体的时代性确立具有绝对的权威,一切与之相异的野史或新文学形式都被视为“他者”(the Other)。“他者”的概念源于西方哲学,可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录》,是相对于“自我”的差异存在,外在于自我的一切有形或无形、可感知或不可感知的事物。随着主客体间二元对立性质的确立,“他者”具有了客体性,而“客体逐渐沦为被认识、把握和征服的对象”。[1](P118-119)因此,“他者”具有了主体控制下的阶级属性,以一种附庸状态存在。
与传统正史相比,《豆棚闲话》三则历史题材的故事具有鲜明的翻案特征。依照历史主义观,三则故事的人物刻画和表达的思想不合乎史实情理,是对正史的亵渎。以此来看,历史真实性具有足够的分量,而文本的叙述风格、情节和思想是历史统摄下的变体,即历史的“他者”。因此,胡适在《〈豆棚闲话〉笔记》中曾言:“《豆棚闲话》的文章很平凡……此中十二篇都不是好小说,见解不高,文字也不佳。”[2](P540-541)依照历史主义眼光,胡适不顾该文本的艺术特色,将之视为正史内容与白话小说叙事文风附庸性的“他者”。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滥觞于20 世纪70 年代的西方文论界,吸收了新批评注重文本、反对作者意图的特点,通过对历史复杂性的觉察和历史文本化的探索,公然与历史主义传统决裂。新历史主义否定历史的纯客观性,认为所有的历史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历史学家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内,其对历史和往事的认识都会有意无意地受自身文化体验的影响。”[3](P318)例如,传统史学家对正史的编纂与热切推崇,企图为后世立下知识标准;新历史主义者则认为,所谓的正史难免是某一君王将相万千事件中被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或褒或贬的史家观点,其野史内容或外史内容也未必不可信。因此,所谓的史实具有不可论证性,一切要依从于对文本的阐释。另外,历史中的个体身份与产生它的文化相互塑造。一切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文化范畴仅是一定义问题,原则上只是体现权力话语的流动。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体身份由自我叙事构成,文化的话语流通为其提供素材。”[3](P326)例如,某一历史被编入文本,作为文学个体,因时代文化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新历史主义者不会将其看作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附庸(他者),而是看作时代文化话语的重要构成因素,体现叙事与历史的互动交流性。
在新历史主义观照下,《豆棚闲话》敢于翻案正史,借助明清易代的时代背景,观览所谓“有道之士”(如介之推、范蠡、叔齐)的伪善品行。历史的权威受到挑战,而且在叙述者与人物的故事互动讲述中,历史的真假失去了伦理意义上的评判价值,传统的人物形象遭受质疑,进而得以解构,一切成为话语阐释的一部分。另外,《豆棚闲话》将载道精神置于时代交替的话语中,对“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儒家道统精神或赞或讽,或褒或贬,表面上宣扬孔孟正统的儒学观点,实际上文本对儒家正统思想的颠覆预示着历史展示与文本阐释之间的矛盾。这样,对历史人物的精神解读也带有不同叙述者的主观色彩,历史真实不再重要,它们呈现为时代话语的流动,寓于文本阐释中。因此,所谓历史正统标榜下的文本“他者”得以觉醒,既表现出对传统历史主义的颠覆与突破,同时归于文化语境下的话语阐释,消解了边缘的个体身份特征。
二、《豆棚闲话》的历史人物形象解构
《豆棚闲话》作为一部话本小说集,在明清话本小说兴盛之际具有不同于以往话本意义上的创新性。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历史翻案性是该文本鲜明的特色,以期突破传统历史主义历史真实的限制,打破“影响的焦虑”,①对文本话语进行重构。历史传统认为介之推、范蠡和叔齐均为忠孝节义的道德典范,但在《豆棚闲话》中,作者将庄严的道德题材拉下神坛,让他们以具有鲜明弱点的反英雄形象示之,②借助不同叙述者的讲述将历史解构,赋予人物新的话语书写,打破正史中儒家楷模的典范束缚。
(一)介之推假廉惧内 正史中记载,介之推随重耳流亡十九年,一心为君,后因不受禄而归隐,足显其忠义。如《庄子·盗跖》中记载:“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4](P263)又有《左传》写道:“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5](P83)随后,经《史记》、《后汉书》等对介之推故事情节的记载,其形象均被刻画为一个隐士、一名忠臣,到明末逐渐定型。
而艾衲居士反其道而行之,将介之推描刻成一个畏惧妻子、为出山做官不惜烧死妻子的反面人物。与重耳周游,之推在随文公周行期间十分想念妻子,回国后见了面,妻子因妒忌对之推打骂不已。介之推一言不敢发,待妻子气消便打算出山做官受职。因妻子阻拦,之推便纵火欲烧妻子,但身被妻缚,双双被烧死。该故事完全颠覆了介之推廉洁尽忠的隐士形象。另外,正史中没有说明介之推有妻子之事,但介之推有无妻子,他对国君真实的内心想法,以及其母劝善不受禄之辞在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只是正史选择了介之推某些看似典型的方面来记载。从现代意义上考虑,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与历史社会的复杂性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物的优劣善恶。有人看到了介之推的忠廉,有人看到了介之推的功利。因此,历史成了可供解读的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以进行不同的合理阐释。
(二)范蠡假仁假义 传统观念认为范蠡为国家舍爱取义,乃春秋越国良臣,常与文种并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范蠡语:“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6](P638)范蠡一心为国,为博取吴王信任,不惜献妻西施入吴,为复国殚精竭虑。他与西施的浪漫爱情也广为世人称颂,两人泛舟太湖的故事至今都是一段佳话。明朝梁辰鱼传奇《浣纱记》将二人爱情寄以国家大事,两者均以正面形象示之。
《豆棚闲话》中,千古之美的西施被描述为“一个老大嫁不出门的滞货”。[7](P15)把西施作比褒姒,有“红颜祸水”之意,因先后委身于范蠡与吴王,又有了轻薄之嫌。而范蠡心怀鬼胎,阴险狡诈。原本大义为国的谋臣有了自己的心机,复国后不惜将心爱之人设为圈套,为自身利益无情地将西施葬于水中。该故事对西施的塑造和对范蠡的塑造均瓦解了传统道德对楷模人物忠诚仁义的写照。西施在隐含作者笔下并非才貌双全,为了国家勇于奉献自身,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女人的私欲和虚荣。范蠡也被塑造成一个见利忘义、贪慕名利的小人形象。由此看来,对故事的讲解和对历史道德典范的认知与传统发生了分歧,隐含作者颠覆正史,力图寻找历史的侧面展示给读者,借叙述者之口将历史视为一种笑谈。正史在隐含作者看来不再是主导文本的客观存在,而只是提供了一种信息,对信息的解读均交由不同的阐释者来处理。
(三)叔齐假忠失节 伯夷、叔齐是传统标榜的道德模范,《史记》将《伯夷叔齐列传》置于七十列传首位,以赞颂二人的忠志节气。孔子称颂二人:“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8](P56,P221)韩愈在《伯夷颂》一文里也赞誉二人:“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9](P2741)古代文人对伯夷、叔齐品行的敬仰由此可见一斑。
在《豆棚闲话》里,叔齐被刻画成一个世故变节的小人形象。伯夷、叔齐放弃王位逃亡,隐居首阳山。面对饥不择食、寂寞难耐的窘境,叔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变节下山。他遇到“忠孝节义”的猛兽和世上所谓的“顺民”,便教唆他们一起入朝,顺新寻爵。叔齐有道:“家兄是九死不渝的,我在下另有一番主意。昨日在山上正要寻见你们主人,说明这段道理,约齐了下山……一齐都有好处……所谓应运而生,待时而动者也。”[7](P56)文本中叔齐假忠变节,一反传统的忠孝节义的形象。隐含作者借对叔齐形象的颠覆表现了易代之际人们是忠于旧朝还是顺应新朝的矛盾性,即使是忠节的道德典范人物也会面临这种矛盾的抉择。因此,无论是叔齐忠节思想的变化,还是与伯夷及其他顺民思想的对立,消解了正史中单一的忠节形象,使读者对历史产生了质疑,有了独立的见解。
从三则历史故事对人物形象的解构中可看出作者对历史真实和传统道德权威的质疑。正史提供的故事为后世树立典范,而对典范故事的否定在后代成了豆棚类书场下的笑谈。读者围绕该段历史可能会作出或褒或贬或中的阐释。
三、《豆棚闲话》的儒学正统思想颠覆
陈梦熊在《儒家正统观的现代反思》中提到,“以统治者本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权承运与否作为评价标准,史学‘正统说’与儒家‘正统说’生发出紧密的联系。”[10](P25)由此看出,古代宣扬儒学正统,以统治者的道德意志为坐标,为生民立心立志。自春秋战国起,由秦、汉而下,中国倡导既符合真实历史、也对应政治生态诉求的“正统”学说。“正统”要求“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而欧公继之,标‘居正’、‘一统’之义。”[11](P75)与儒学文化相联系,“正统”以“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作为维护君权神圣性和政权正统地位的核心价值理念。正统思想成为统一万民思想的主导,历史真实标榜这一精神,具有颠扑不破的知识主导性。就传统历史主义而言,历史书写须遵循“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正统精神,对道德模范的青睐有助于教化人民和维系道德统治。在弘扬儒学正道的时代,《豆棚闲话》敢于丑化儒家道德典范,颠覆正史道统,敢于展现不同的思想倾向,实为思想界的一大突破。通过对三则故事中介之推、范蠡和叔齐的人物形象解构,展现了与正史书写截然不同的人物特点。正史书写所呈现的思想与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颠覆。文本中三则历史故事对正史思想的颠覆亦可视为其他者性的觉醒。
(一)廉义虚假 第一则《介之推火封妒妇》对介之推假廉惧内的刻画消解了儒家正统标榜的廉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也颠覆了以廉义为代表的隐士文化。就介之推归隐而言,正史中推崇的是他的无心名利,廉洁忠义;而在《豆棚闲话》中的叙述,与传统歌颂隐士闲适自得隐居生活的背道而驰,打破隐士平和安稳的生活,将妒妇的形象融入其中,是对隐士廉义思想的颠覆,也有对正统思想中提倡的琴瑟和鸣夫妻关系的质疑。
(二)仁智虚假 如果说第一则体现的是儒学正统中有廉义虚假的写照,那么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则体现为对仁智思想的质疑。范蠡为复国求荣,不惜杀害西施。西施才貌平平,为求名利,跟随范蠡。在故事书写中,范蠡的仁德和西施的才智被颠覆,传统标榜下的仁智思想成了书写中的反义成分。另外,儒家正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必要前提,但在该故事中却为反面刻画。另一方面,尽管范蠡、西施品德不高,却又能为故国报仇雪恨,立身扬名,这又体现了道德伦理与是非成败之间的矛盾。
(三)忠节虚假 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体现的是对儒家忠节思想的颠覆。和《介之推火封妒妇》相似,伯夷、叔齐和众人陆续归隐首阳山是正统的忠于旧朝的隐士的写照,而叔齐变节投奔新朝则是对隐士的打破。叔齐无意归隐,劝众变节,顺应时务,归顺新朝以图爵位。针对民众的质疑,故事最后借“齐物主”之口道出朝代更迭的天命思想,万民方答应归顺。但结果却是叔齐南柯一梦。由此可见,忠节思想在梦中(即人的无意识)遭受质疑,而且这种变节、归顺新朝的意志又披上了“齐物主”所谓的权威性的外衣。但是,结尾的南柯一梦又否定了这种归顺的可能性,进而为传统的忠节思想正名。伯夷苦心守节、叔齐假忠变节、万民思想的不一致共同呈现在文本中,一定程度上说明儒家正统的忠节思想在现实中的动摇,依文化语境的需要在文本中或合乎正史,或另立新说,具有不一致的体现。
从上述对儒家正统思想之于历史书写的分析可以看出,隐含作者敢于颠覆正史,努力寻找历史的侧面或历史可能被掩盖的一面。新历史主义认为,整一的时代精神不存在,“对历史的总体化阐释(即只用一个答案来解释某种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不充分的。”[3](P325)在历史书写过程中允许对立思想的呈现和不同文化的冲击,这样,隐含作者的思想不为正统思想所缚,文本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桎梏,实现了他者的觉醒。颠覆性的思想与儒学正统思想共同归入文本,归入话语阐释,供后人评判。
四、《豆棚闲话》历史文本化话语重塑方式
以上分析了《豆棚闲话》中三则历史题材故事人物形象的解构与儒家正统思想之于历史书写的颠覆,打破了正史对文本书写和儒学思想展现的束缚,使历史文本化,归入文化语境下的话语阐释中。而实现文本书写他者性觉醒的途径需借助历史话语进行重塑。因此,就《豆棚闲话》的历史文本化话语重塑而言,历史如何得以解构,或借助何种方式使历史话语得以重塑,同样值得关注。
(一)讽刺 《豆棚闲话》的话语书写近似于鲁迅论及《儒林外史》时提出的“婉而多讽”。[12](P137)张泽如、李淑兰将该手法解释为,“透过对客观人事的描写与叙述,使人物的表面言行和内心世界构成极大的反差,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讽刺、揭露人物的虚伪。”[13](P49)《豆棚闲话》中三则历史故事,对介之推、范蠡和叔齐等历史人物形象的解构便体现了这种讽刺手法。文本中并没有谩骂与诅咒,重点在以事论理,以人物言行前后的变化婉讽地展现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介之推表面感怀妻子之情,归隐于山林,内心却想出山受禄、封官纳爵,不惜烧死妻子,与之同归于尽。范蠡为复国不惜献妻于吴王,表面上大仁大义,但为一己私利葬西施于水中,实则玩弄西施于股掌。叔齐的初衷是与兄长一同归隐,守节于首阳山,但内心终起波澜,欲变节归顺新朝。隐含作者借助三人各自前后不一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举止对历史话语进行讽刺性重塑,使历史真实在文本阐释和众声怀疑中得以消解。
(二)含混 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含混七型》中探讨了“含混”的内涵,将其指涉为“追求意义时举棋不定的状态,或多个事物的意图,也可指意思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14](P157)就历史文本而言,如果历史发展本身出现不确定性,或与文本解读发生冲突,那么历史就具有了含混的艺术特征。以上对《豆棚闲话》中三则历史题材故事的分析,鲜明地印证了其含混性。现举一例释之,历史记载介之推跟随重耳十九载,割肉食之,也有可能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拥护文公继位后寻官纳爵,只是言谈举止中不表现出来罢了。十九年故事之概述很简单,但由此而认为介之推一直跟随文公乃牢不可破的忠义之举,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十九年中介之推的思想是否会有矛盾转变?历史又在哪里呈现?文公当政,之推归隐,又有谁知他不是为图美名而有意为之?《豆棚闲话》只是以一种可能性将该种想法展示出来,直面书写。正史选择将其廉义的英雄的道德性示之于众,或有正心明德之意,或有方便统治者统治之意,但就人性的复杂性而言,他作为普通百姓该有的情感与思想体验刻画得并不完整。对范蠡、叔齐等历史人物的刻画大抵如此。历史的含混性由此可见一斑。所以,隐含作者借助对历史的质疑与解构将介之推、范蠡和叔齐等这些儒家道德楷模拉下神坛,又通过含混历史的话语将其形象重塑,思想重塑,将历史归入文本与读者的阐释中,也印证了该文本创作的合理性。
含混历史话语的重塑消解了正史带来的权威性,历史被文本化,主体性消失。此时无所谓他者,文本中每个叙述者、人物和文本外的读者做的皆是主体性的话语阐释。
(三)复调 巴赫金(M. Bakhtin)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通过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复调”概念。“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5](P4)该类小说表现了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几个意识相互作用的自由的对话性质。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复调小说的问世标志着独白型单一叙事类型的瓦解,传统的叙事典范失去了主体的身份特征,转而与复调小说文类并驾齐驱,共同接受读者的阐释。针对正史统摄下的话本小说文类,浦安迪(Andrew H. Plaks)批判:“中国正史叙事者似乎总是摆出一副‘全知全能者’的姿态;然而,这种全知全能却只是局限在冠冕堂皇的庙堂里。”[16](P16)此说一针见血。他看到了中国正史叙事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转而提倡具有复调性质的叙事类型,突破全知全能叙事的限制,打破正史对知识的垄断和对思想的禁锢,这对中国历史题材叙事文本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推动。
《豆棚闲话》具有典型的复调性。比如,《范少伯水葬西施》中,针对老人讲范蠡与西施湖心中情事,一后生对此表示怀疑,老人便举出《野艇新闻》、《杜柘林集》、西施湾等作证。针对西施“不洁”之谈,有人举出苏轼“西湖作比”的诗句反驳。老人便从该诗中另解一番意思,印证自己的真言。最后谁也没争出个高低,各执己见,以笑结之。故事中的人物从各自角度讲解历史,对范蠡与西施的故事进行重构,一方面消解了正史中二人西湖爱情的佳话,打破了历史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人物相互间的交流体现了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之间复调式的的平等自由意志。
以该则观全篇,作者笔下的豆棚人物充当了叙述者的身份,叙述者与叙述者之间对同一事情有了不同的意识、不同的阐释,相互之间平等对话,彼此又互为叙述接受者。这里的接受者不再是全知全能叙事小说中只去倾听的“哑巴”,而是告别了固有的他者性,与叙述者一起参与到文本创作过程中。历史真实性在隐含作者、叙述者及人物的眼里变得不再重要,通过历史话语重塑,体现的是不同阐释者的思想价值。
《豆棚闲话》中对历史书写的话语重塑打破了正史对文本的禁锢,道德模范人物形象的解构与儒家正统思想之于历史书写的颠覆,使得历史归入文化语境下的话语阐释中。文本的他者得以觉醒,以历史为参照,但不囤于历史真实,不受历史禁锢,以期消解历史、包容历史。
结语
在新历史主义观照下,《豆棚闲话》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的解构、对儒家正统思想之于历史书写的颠覆以及历史文本性的话语重塑,打破了正史对文本书写与文本思想的禁锢,实现了他者的觉醒。文本不是表现作者的意图,不必关注历史真实,不再遵循固有的正统思想,不再是一种附庸性的他者身份,而是多重角色共同发声,多重思想一齐迸发,历史在文化语境下归入文本,两者共同在话语的阐释中得以表征。
注释
①“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出自美国现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书,意在表现后辈诗人在前驱诗人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压力下如何寻找方法,努力打破影响的焦虑的现象。该节意在表现《豆棚闲话》作者如何借助历史翻案特征打破正史对文本记录的限制。
②“反英雄”作为小说、戏剧、电影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并非“反面人物”。它是文学艺术将象征典雅、崇高与理想的英雄形象平民化、生活化的结果。平民生活一旦进入艺术核心,成为“主角”,“英雄”便得以衰退。具体可参照王岚《西方文论关键词·反英雄》中对“反英雄”的编写,出自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3-1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