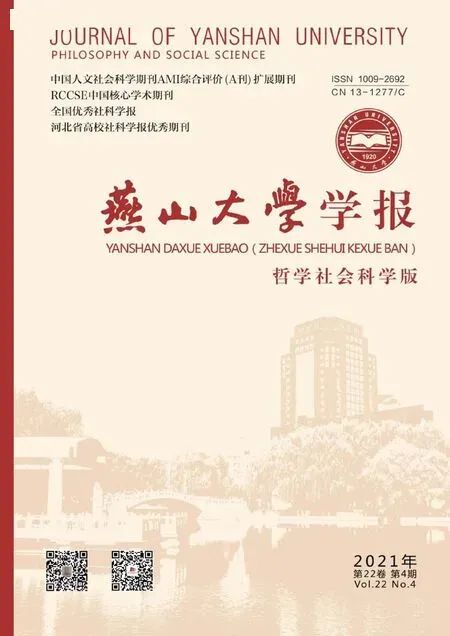认知原型视角下的《红楼梦》神话元素英译
潘桂娟,谷香娜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一、引言
神话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和各文化中,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代表着先民对世界和人类起源以及自然现象的探索。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神话从世代相传的口头故事逐渐融入文学作品,这也是神话发展的标志。[1]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生花妙笔架构了两个世界,即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他以女娲补天神话为依托,创造了“顽石补天”“木石前盟”和“太虚幻境”三个神话,籍此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覆灭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为全书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这三个神话是《红楼梦》故事的缘起,也“决定了《红楼梦》故事的走向和结局,具有命定性与先验性”[2],还“为《红楼梦》的现实世界起到了原型的作用”[3]140。
神话叙事框架在《红楼梦》中引人注目,因此在汗牛充栋的红学研究中,不乏关注神话的文献。然而,从翻译角度探讨神话元素的却寥寥无几。冯庆华曾简要指出“意译似乎是翻译包含中国神话传说的习语的最好策略”[4]150,但并未就这一主题深入探讨。蔡新乐指出了霍译《红楼梦》中对“顽石补天”神话的漏译和误译,并认为这种做法有损叙事主线,影响人物塑造。[5]张爽则从翻译目的论出发,简要对比了霍译本和杨译本在翻译神话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6]迄今为止,尚无较为全面针对《红楼梦》神话元素英译的文献。
过去两百年间,《红楼梦》已陆续有11个英译本,但其中大部分为节译本,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原著的风貌。《红楼梦》全译本仅有3个,即1978年开始出版的霍译本(由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翻译)和同年出版的杨译本(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译),以及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2004年才重见天日的邦译本(由邦索尔神父翻译)。本文将以这三个全译本中的译例为研究对象,从译者建立认知原型的角度出发,审视神话元素在其中的呈现。
二、认知原型理论
现代认知原型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一批学者对于经典范畴理论的批驳。这些学者中的代表之一是Rosch。他认为,认知原型是一个范畴内具有样本性的典型具体代表,范畴本身则围绕原型呈辐射状展开。[7]根据这一理论,当人们提到某个范畴时,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具体的原型样本。Lakoff进一步发展了认知原型理论。他认为认知原型具有抽象性,并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即由多个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简称CM)构成的抽象集合体。[8]ICM具有整体性,从心理认知角度看来,它比单个的认知模型CM更为基础和简单。ICM的获得与文化息息相关,在人们的感知体验和心理认知过程中得以完善。作为一个统一的、完形的和理想化的抽象模型,ICM是人类认识事物和建构意义的基本出发点。
上述“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认知转向,无疑对文学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9]161,文学翻译是译者针对文学文本所做的语言符号转换,也是一门实践性艺术。认知先于语言,语言背后隐含着人类共同享有的客观世界和认知规律。因此,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认知先于目标语文本的产生,而目标语文本又直接影响了读者认知原型的构建和丰富。可以说,文学翻译过程远超词句等语言单位的转换,更包含认知原型的转码、构建乃至迁移。
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理解和欣赏《红楼梦》神话部分的内涵并非易事。这些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内容,如“下凡历劫”,可能会让他们如堕烟海,不知所云。译者面对如此差异巨大的认知世界,必然会展开创造性认知活动,先作为读者去体验认知原型,再作为作者去传达认知原型。这就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认知能力的体现。采取认知原型视角来验视译本,有助于揭示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原型构建过程,为中国文化元素英译提供更多思路。
三、陌生认知原型的构建
神话故事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和发展的,它们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征,反映了不同民族和文化对世界的初步认知和理解。《红楼梦》中诸多神话的认知原型,如“女娲炼石补天”,具有深刻的寓意和隽永的韵味,但在西方文化中却不存在对等的认知原型。这无疑对翻译提出了挑战。试看以下不同的译文:
(1)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霍译: Long ago,when the goddess Nǚ-wa was repairing the sky,she melted down a great quantity of rock and,on the Incredible Crags of the Great Fable Mountains,moulded the amalgam into thirty-six thousand,five hundred and one large building blocks,each measuring seventy-two feet by a hundred and forty-four feet square.
杨译:When the goddess NüWa melted down rocks to repair the sky,at Baseless Cliff in the Great Waste Mountain she made thirty-six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one blocks of stone,each a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high and two hundred and forty feet square.
邦 译:It is said that when Nü-Kua smelted stones for the repair of the Heaven on the cliff of Wuchi on Mt Ta-huang,she smelted thirty-six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one stones,each twelve chang high and twenty-four chang square.
根据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览冥训》)英文译本读者少有或根本没有“女娲炼石补天”的认知原型,因此认知的构建需要若干细节的支撑。
霍克思在翻译过程中,应是首先觉察到了目标语文本读者的认知原型缺失,进而在译本中采取一定的策略来帮助读者完成从无到有的建构。其具体手段,就是增加了若干认知模型,对神话故事的具体情节进行补充说明,如“melted down a great quantity of rock”,“moulded the amalgam”,这种熔炼、铸造乃至修补的过程能够与读者在现实世界中已有的认知原型契合,因此能让他们构建起新的“东方神女炼石补天”的认知原型,认识到这是一项伟大的神迹,进而理解那块唯一的弃石的“自怨自叹,悲号惭愧”的缘由。这种认知原型构建和映射的过程给读者带来新鲜的认知体验,增加了阅读兴味。对比霍克思在翻译中所付出的较多认知努力,杨译本和邦译本则简洁得多。二者对“女娲炼石补天”均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并没有补充细节加以说明。这种译法不利于英语读者认知原型的构建,可能会继而影响他们对“无材补天”的顽石形象的认知。
(2) 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
霍译:“Well,well,so another lot of these amorous wretches is about to enter the vale of tears,”said the Taoist. “How did all this begin? And where are the souls to be reborn?”
杨译:“So another batch of amorous sinners are bent on making trouble byreincarnation,” commented the Taoist. “Where will this drama take place?”
邦译:The Taoist said,“And so before long some lovers in a romantic affair are also about to appear among men and pass through the world. But I do not know where it arose and where it will settle.”
如同“炼石补天”一样,“风流冤孽造劫历世”这样典型的中国神话情节在西方文化中也没有认知原型。霍译本为了帮助读者建立起相关认知原型,使用了“amorous wretches”,“enter the vale of tears”,“the souls to be reborn”等,让读者可以形成这些痴男怨女的灵魂将在尘世中得以重生,并饱受情爱折磨的认知。另外,“vale of tears”这一隐喻还与绛珠仙子还泪的故事情节暗合。而在杨译本中,“amorous sinners”和“making trouble”则具有贬义。实际上,“冤家”在汉语中是对所爱之人的昵称,形容爱极之意。“风流冤孽”意指这些恋爱中的男女,其含义与基督教中犯下原罪的罪人亚当夏娃的形象有着巨大差异。邦译本中的“lovers in a romantic affair”是将中国文化中的“风流”和西方文化中的“浪漫”等同起来,直接唤起了英文读者的认知,但“affair”一词多指不符合世俗规则的感情纠葛,与原著中宝黛爱情的主线不甚匹配。“pass through the world”的叙述则显得平淡,未能体现“造劫历世”所包含的艰辛悲哀之意。
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3) (舞女们)便轻敲檀板,款按银筝,听他歌道是:……
霍译:At once the sandalwood clappers began,very softly,to beat out a rhythm, accompanied by the sedate twang of the Zheng’s silver strings and by the voice of a singer.
杨译:Lightly striking their sandalwood castanets and softly plucking their silver lyres,they began.
邦译:The dancing girls responded and lightly struck their hardwood castanets and gently touched their silver harp’s chords. He listened to their song which said,...
太虚幻境仙女们所表演的《红楼梦》仙曲十二支,暗示了整部小说的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在全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以檀板和筝作为仙曲的伴奏乐器,营造了空灵缥缈的音乐空间,这种“鲜明、生动的音乐描写,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段,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10]154。提到仙乐,中英文读者都很难具备理想认知原型,只能在这一范畴内具备若干CM。霍克思在译文中增加了说明性的细节描写:“檀板”的作用是“beat out a rhythm”;筝所发出的声音是“sedate twang”;在乐器的伴奏下,更清晰可闻的是“the voice of a singer”。这些细节描写反映了霍克思对原文的解读和对仙曲的认知原型的建构过程,译者又将自己的认知描绘传达给读者,引导了读者认知原型的创建。比较而言,杨译本和邦译本比较相似,都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没有补充更多的细节。另外,三位译者对原文中乐器筝的译法也值得注意。杨译和邦译的lyre和harp都是西方弦乐器,其外形和音色与中国古筝差异很大。霍译则保留了Zheng的真正名称,并补充细节以说明这种东方乐器的音色是“sedate twang”,给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4) 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
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
霍译:
—Time was you lived in perfect liberty,
Your heart alike from joy and sorrow free,
Till,by the smelter’s alchemy transformed,
Into the world you came to purchase misery.
杨译:
Untrammelled by heaven and earth,
From joy and grief alike your heart was free;
Then smelting gave you spiritual perception,
And you came to this world in search of misery.
邦译:
Heaven did not arrest. Earth did not restrain.
In your heart there was not joy and there was no sorrow.
Only because after you were smelted and endowed with divine powers,
Amongst men you have stirred up trouble.
在《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神话情节与现实情节发生了一次交融。因赵姨娘与马道婆密谋作祟,王熙凤与贾宝玉身中魔魇,危在旦夕。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僧一道在凡间的化身来到贾府,手擎通灵宝玉持颂,退了邪祟。这首诗即为癞头和尚口占,追述了通灵宝玉下凡历劫的前因,也体现了贯穿于原著的道家哲学思想。对自由的追求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获得这种自由的前提就是无名、无功、无用、无己亦无情。通灵宝玉的原身是一块顽石,过着“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的生活,这正是庄子哲学中所讲的绝对自由,也是曹雪芹推崇的人生状态。也许只有凭借道家哲学的超脱,曹雪芹才能坦然面对家族衰败和今非昔比的生活。[11]154从认知角度来看,对于这种自由的状态,霍克思译为“perfect liberty”和“free heart”,较好地把握住了原文的精髓。杨译与霍译相似度很高,只是在第一句中保留了原文“天”和“地”的意象,更好地向读者传达了原文中“逍遥何所似,天地一石头”的哲学和审美意蕴,可谓更胜一筹。邦译本整首诗都是逐字直译,缺乏对原文意义层面的表述,既没有突出石头前一种生活状态的自由,也没有突出后一种生活的烦恼。不具备认知原型的英文读者很难根据邦译本构建对庄子哲学中自由和无情状态的联想。
在这首诗中,三位译者对“通灵”一词的翻译也值得关注。霍译的“transformed”似乎更加侧重从顽石到美玉的形貌改变,邦译的“divine powers”也可能会误导读者,因为通灵宝玉并不具备非凡的魔力。相比之下,杨译的“spiritual perception”较为恰切。这是因为,在道家哲学思想中,“原初状态的无知是自然的恩赐”[12]101,顺乎天然,保存本真,就会获得快乐;“而服从于人为则是痛苦和邪恶的由来”[12]94。从这个角度来说,天然、纯真和快乐的顽石一旦有了人的智识和感受,也就开启了“造劫历世”的艰难旅程。
四、已有认知原型的平移
译者在翻译目标语中不存在的神话元素时,还可以使用平移已有认知原型的方法。试看如下例子:
(7)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霍译:When first the world from chaos rose,
Tell me,how did love begin?
杨译:At the dawn of creation
Who sowed the seeds of love?
邦译:Open out the mystery,
Whoever belongs to the class of lovers...
原文中的开辟鸿蒙,指的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英语读者虽然不熟悉这个神话,却大都熟知一个与此很类似的神话,即希腊神话中关于天地起源的故事:远古时期宇宙中没有天地和日月星辰,只是混沌的一片。后来,第一个神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卡俄斯(Chaos),卡俄斯生下了“昏”与“夜”,“夜”又生下了“光”与昼。这位混沌神卡俄斯的名字,也就是英语词汇“chaos”的词源,意指混乱。中国神话中,宇宙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前所处的混沌状态与希腊神话中所描述的混沌状态相似度极高。霍克思利用了这两则神话的相似性,平移了读者已有的认知原型,将“开辟鸿蒙”译为“the world from chaos rose”,意义较为恰切。而在杨译本中,译者使用了“creation”一次,容易唤起圣经文化背景下英语读者的“上帝创世”认知原型,但这个原型与“开天辟地”神话的真实涵义有较大差异。邦译本则未使用平移认知原型的方法。
在比较三家译本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霍译本较多地使用了平移已有认知原型的译法。例如,霍译本中多次使用了“paradise”一词。英文中“paradise”的理想认知原型ICM与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密切相关,读者在这一范畴内所产生的认知包括神的居所、美丽的花园和纯洁无忧的生活等。据笔者统计,在有关太虚幻境神话的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霍克思共有6次用到“paradise”一词,与原文的具体对应如下:
遣香洞(3次) Paradise of the Full-blown Flower
宝林珠树pearl-laden trees that grow in the jewelled groves of paradise
阆苑仙葩a flower from paradise
西方宝树in paradise there grows a precious tree
从表面看,《红楼梦》中所描绘的东方仙境与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相去甚远,但二者在意义上却有相通之处。有学者指出,太虚幻境与现实封建社会形成强烈对比,它充满了平等、和谐和欢乐的氛围,恰似“中国式‘伊甸园’”[13]57。也有学者把太虚幻境和大观园进行比较,认为太虚幻境是天上的女儿国,是“清净女儿之境”,大观园则是作者设置的人间的太虚幻境。“大观园是地上的女儿国,曹雪芹的乌托邦,贾宝玉的伊甸园,大观园的最终毁灭象征着曹雪芹理想的破灭,贾宝玉现实人生的无所皈依,精神家园的丧失。”[14]10贾宝玉最终痛失大观园,红楼群芳风流云散,这种幻灭与亚当和夏娃的失乐园有着相同的内核。从这个角度看来,面对缺乏认知原型的英语读者,使用“paradise”能让他们迅速唤起已有认知原型,进而领悟《红楼梦》太虚幻境的隐喻:这个仙境虽然美轮美奂,却终将在现实中幻灭。
在神话元素集中的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霍译本中其它平移认知原型的译例如下:
邪魔:Lust(圣经文化七宗罪中的色欲)
仙女:nymph(古希腊神话中的山林水泽仙女)
琼浆玉液:nectar(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饮料)
仍以《红楼梦》第五回为例,杨译本中平移认知原型的译例有三个,具体情况如下:
琼浆玉液:nectar(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饮料)
肴馔:ambrosia(古希腊神话中的神食)
麒麟:unicorn(西方神话传说中的独角兽)
上述译例既反映了译者在阅读原文时认知原型的建构过程,又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认知原型的传达方法,由于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分析。
与霍译本和杨译本相比,邦译本第五回则没有平移认知原型的译例。考虑到邦索尔的神职人员身份,这种区分中西方神话的译法可能是译者刻意为之。邦索尔毕业于伦敦大学宗教哲学系,曾作为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且邦索尔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曾参与撰写了“伟大的东方宗教(GreatReligionsofEast)”丛书中的《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andTaoism)分册。因此,“邦索尔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所隶属的教育教学体制对于‘东/西宗教’认知、对于‘大写之神永恒在场’等‘学术信念’的影响”[15]。笔者推测,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邦索尔出于自己的宗教关怀,对中国神话元素和西方神话及宗教元素做了严格区分和界定,刻意加强了东西神话的二元对立,以维护西方神话和宗教。
五、结语
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曹雪芹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神话融入了封建社会四大家族的现实主义故事中,使得《红楼梦》中的神话与凡间的故事构成了双重叙事结构,很多神话情节预示了故事的走向。神话元素对《红楼梦》主题的揭示至关重要。
本文在认知原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红楼梦》三个全译本中神话元素的英译。一般来说,译者的任务是“努力看到作者想让他看到的画面,然后再用他自己的语言将他所看到的画面描绘出来”。[4]21
三位译者在阅读体悟《红楼梦》神话元素时,都结合自己的翻译目的,形成了独特的认知视角,也在接下来的翻译过程中付出了不同程度的认知努力。在三个全译本中,霍译本更多地使用了有助于英文读者认知的译法,如增添细节以构建陌生神话认知原型,和平移已有神话认知原型。这种译法可能与霍克思的汉学家身份有关。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他更易觉察到中西情境和读者文化认知基础的巨大差异,因而更加“重视目标语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和接受”。[16]206比较而言,受命翻译《红楼梦》的杨宪益夫妇并未明显迁就外国文化,或适应英语读者的接受力。杨译本中对神话元素的再现并不利于目标语读者构建认知原型,一些平移认知原型的译例也更像是译者信手拈来,并无刻意。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对于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读者来说,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也许更为合适”,[17]因为这种译法更贴近原著的风貌。而邦译本受译者译力和宗教信仰所限,倾向于一字一译的直译方法,在处理神话元素时鲜有出于认知考虑的翻译,使得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不够自然和灵活。这也与其他学者对此译本的评价是一致的。[18]
神话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元素。读者理解了这些神话元素,就更易于站在一个高的视角,从整体把握作品的思想。因此,神话元素的翻译是否得当,也直接影响译本读者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欣赏。神话元素在《红楼梦》其余译本,以及在其他古典文学作品译本中的呈现,值得学界进一步的探讨和关注,以期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