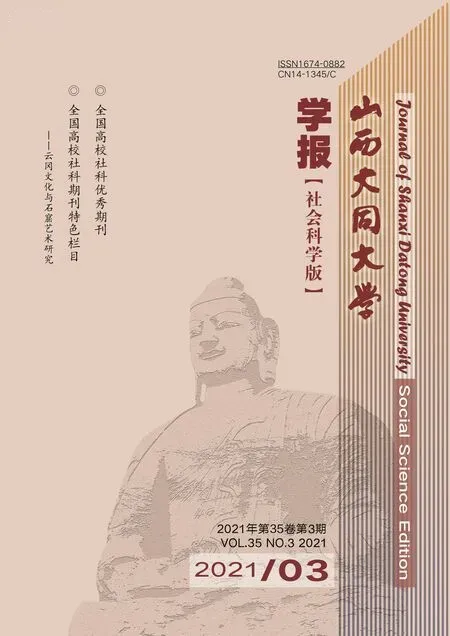疫情视角下的公安机关家庭暴力干预
——以浙江省S地区为例
沈可心,曾范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北京 100038)
家庭暴力,又称亲密伙伴暴力,是指在亲密关系中,关系一方对另一方的生理、心理和性伤害行为。家庭暴力存在于各个群体中,而女性成为最可能的受害者。但是,男性受害者也不应受到忽视,男性受害者数量的减少源于男性举报暴力的可能性降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也是影响家庭暴力的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往往更容易发生家庭暴力。然而,在当今生活和工作压力倍增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可能造成家庭暴力的发生,特别是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拥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女性被认为挑战了男性权威而面临家庭暴力的风险。失业也会增加家庭暴力的发生率。每次全球大衰退时期,高失业率成为家庭暴力的“触发点”,无力供养家庭产生的受挫感常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1]同时,童年经历或目睹过家庭暴力的人在长大后更可能遭遇或实施家庭暴力。学者Gerino将之归因于认知因素,认为有类似经历的人会将家庭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合法化。[2]学者陈月提出,施暴者因早期的经历和已经形成的扭曲性格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而导致成年后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3]
家庭暴力在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等灾难时会有所上升。以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发生时期为例,密西西比地区基于性别的暴力提升了四倍;[4]2011年新西兰基督城地震期间,家庭暴力上升53%。[5]家庭暴力发生率不仅在灾难期间有所上升,其后几年的环境恢复期仍保持上升趋势。可以说,家庭暴力不仅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展现出突发性,也具有持续性特征。
一、新冠疫情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影响
新冠疫情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因素之一。疫情发生突然,成为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为了避免病毒传播,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公共安全措施在全国至全球范围内扩散实施。然而,为了保护公共健康进行的隔离措施导致高危人群易受风险的概率上升。在可能面临家庭暴力危险的个体中,居家隔离政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据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会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家庭暴力举报数翻倍,且90%的家庭暴力与新冠疫情有关。英国卫报报道称,巴西家庭暴力事件上升40-50%;西班牙一地区政府报告在隔离前期求助热线上升20%;英国家庭暴力求助热线上升25%。[6]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称,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南非、美国等家庭暴力报道均有上升,部分欧盟国家在封锁期间家庭暴力数上升三分之一。[7]家庭暴力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因疫情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加倍。此次疫情具有突发性、高风险和蔓延快的特点,其防控难度已远超此前历次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爆发初期,病理尚未明确,各类传言此消彼长,死亡人数也急剧上升,造成人们极度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一方面,施暴者将实施暴力作为发泄渠道,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烦躁;另一方面,施暴者借机利用新冠疫情向受害者灌输恐惧与服从以达到强制性控制的目的。第二,家庭面临的经济和社交限制。居家隔离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人们外出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减少。疫情期间,大部分企业停产停业,致使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收入减少。经济收入的减少带来经济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一方对伴侣施加更多的控制。[9]同时,疫情改变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重构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相处时间的延长以及与其他人接触减少,这些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压力,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充满矛盾的紧张的家庭关系。调解机制的缺失以及原既定生活的紊乱助长了暴力行为的升级甚至犯罪。居家隔离政策使得受害者被迫与施暴者全天候24小时共同隔离在家中,为施暴者进一步实施控制提供了可能。施暴者以易被传染为由阻止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或者进行信息封锁,通过传播错误信息进一步控制受害者的行为和思想。[10]第三,受害者支持系统的弱化。家庭之所以容易发生暴力行为,是因为其内部权力的扭曲和破坏而缺乏外部群体的监督。疫情期间,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施暴者全天候的监视下,受害者既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寻求有效的帮助,潜在举报者也因缺少了解渠道而难以及时阻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二、浙江省S地区家庭暴力调研及分析
新冠疫情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改变了潜在的犯罪。以家庭暴力案件为例,由于受害者与施暴者共同生活的时间延长,为防止因警察介入而可能遭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家庭暴力的报警率可能会降低。同时,居家隔离也可能使施暴者施暴能力下降,而受害者报警率上升;或者,居家隔离使得施暴者变本加厉,受害者的报警率上升。文章选取浙江省S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疫情期间家庭暴力报警率的变化。
S地区现有人口数为84.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数为43.4万人,户籍人口数为40.9万人。下辖9个镇(街道)。新冠疫情期间,S地区于2020年1月底至2月底实施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小区封闭,非必要、非重要岗位者不出门。由于疫情防控有力,于3月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数据搜集过程中,以2020年2月至8月的报警电话为基础,参考2019年数据进行同期对比。
2020年2月至8月,S地区家庭暴力报警数为789件,同比上升16.4%。2-3月份是居家隔离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期,家庭暴力发生率在各时段均有上升。居家隔离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人们外出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减少,导致施暴者和受暴者共同生活时间延长。对于那些本就笼罩在暴力阴影下的受害者来说,居家隔离使得施暴者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在那些本不存在暴力行为的亲密关系中,随着疫情在全国至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人们承受着被感染的风险,加之工作压力和面临失业的恐惧,可能使得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加深直至爆发而产生暴力行为。此外,压力上涨会促使人们酒精摄入量的增加。酒精摄入,特别是达到有害摄入时是发生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2月,全国食品烟酒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1至8月的最高值。酒精摄入不仅使家庭暴力发生率上升,其严重程度也会加剧。从施暴者角度出发,酒精摄入会直接导致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使得个体无法通过谈判等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从受害者角度出发,在受到暴力伤害后,酒精成为个体缓解伤痛的自我治疗手段。
随着居家隔离政策的逐步放宽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人们外出时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4月客运量超过2月的3倍,约为3月的1.5倍;4月餐饮收入约为2月的2倍和3月的1.4倍。[13]外出时间的增加使得个体情绪宣泄渠道增加,施暴者和受害者共同生活时间减少,家庭暴力发生率在4月明显下降。6月初北京新发地出现确诊病例,并小范围扩散。该时期S地区家庭暴力发生率在夜晚至凌晨时段显著上升。可以推测是因在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下,北京疫情的出现导致人们夜晚外出活动减少,家庭成员夜晚居家时间延长而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率上升。
从数量上看,2020年2-8月,男性实施的家庭暴力报警数占报警总数的90.4%,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的家庭暴力报警数占比71.9%,父亲对孩子实施的占比9.9%,儿子对父母实施的占比4.9%。相比2019年同期,男性实施的家庭暴力报警数上涨6%,女性上涨25%。从反复程度上看,在报警内容中涉及“一直”、“经常”、“又”等词语的施暴者多为男性。从严重程度上看,由男性实施的家庭暴力中有87.8%属于肢体暴力,7.8%携带工具实施,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的以刀、棍、酒瓶为主,父亲对孩子实施的以衣架、木条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女性实施的家庭暴力总数较低,但其中有15.4%的女性使用了工具,且使用菜刀的占据较多数。
从报警人身份来看,受害者是最主要的报警主体,占比90%;非当事人的报警数占比9.9%,同比上升1.9%。在非当事人报警的案件中,由小孩报警的父母之间实施家庭暴力的比例为49.3%,与2019年同期相比上升10.9%;邻居报警的比例为40.3%,同比上升34.5%;路人报警的比例5.9%,同比下降29.1%;保安是今年出现的新的报警主体,其报警的比例为4.5%。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居家时间的延长改变了非当事人,特别是邻居的报警动机。在居住紧密的楼房,邻居更有机会听到或看到暴力事件的发生而导致报警数上升;而随着疫情防控期间保安巡逻的加强,保安成为家庭暴力的举报者和第一干预者。
通过上述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可以发现,疫情与家庭暴力发生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居家隔离措施带来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暴露时间”的延长、疫情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的上升、家庭成员心理压力的加剧、情绪宣泄渠道的减少、家庭矛盾的积累……种种因素加剧着个体自控能力的下降而导致暴力行为发生。家庭暴力发生后,施暴者、受害者、证人等相关人员成为行为干预的第一步。然而,由于婚姻、血缘、赡养、抚养等特殊关系的存在,为了维护彼此间的关系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受害者选择“能忍则忍”;而证人也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进行调解,其结局往往是家庭暴力行为的升级和扩散。在施暴者全天候的密切监视下,受害者只能寻找时机利用电话、网络等方式寻求救助。居家隔离措施导致潜在举报者的干预作用难以发挥实效,寻求公安机关进行干预成为受害者和潜在举报者的现实选择。公安机关如何利用公权力进行家庭暴力的有效干预,采取何种措施避免家庭暴力升级而一招制胜,成为公安机关解决家庭暴力案件的重要考量。
三、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讨论
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是指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依法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家庭暴力采取的预防、制止和处置的行政和刑事执法行为。[12]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和实施,公安机关在工作实践中有了总体的指导和规范。在接处警过程中,也更加关注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以及行使权力的规范化。但是,家庭内部本身的排外性和封闭性以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仍有一部分公安民警不愿介入家庭矛盾,对干预家庭暴力存在畏难情绪。同时,出于维护和谐家庭生活的目的,公安民警在处置家庭暴力案件过程中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相安无事的态度,不仅难以取得应有的干预效果,对施暴者也缺少震慑力而可能纵容家庭暴力,继续发生,受害者也从此丧失对公安机关的信心而可能采取极端的“自救”措施,引起社会矛盾的扩大。此外,家庭暴力并不是简单的纠纷、暴力事件,而是一系列复杂矛盾构成的社会问题,单靠公安机关一个部门是绝不能完成的。
作为干预家庭暴力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公安机关起着防范和阻止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和升级的关键作用。疫情期间,家庭暴力的隐蔽性进一步加强。在家庭成员外出和社交活动减少、施暴者全天候的密切监视下,受害者只能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寻求救助。同时,居家隔离政策使得潜在举报者“爱莫能助”,公安机关成为受害者寻求救济的主要渠道。因此,在处置家庭暴力案件中,公安机关不仅要更新执法理念,提高对家庭暴力事件的重视度,也要注意自身角色的转换,从消极的调解者身份转变成积极的行政执法者。[13]同时,也要带动社区、妇联、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参与,发挥其调解作用。具体来说,第一,未雨绸缪,及时取证。疫情期间施暴者与受害者接触亲密且持续,受害者寻求救济的机会稀缺,且往往等到暴力行为不断升级而再也无法忍受后选择报警。公安机关在接到相关警情后需要提高重视,注意报警人话语的隐蔽性,提取关键信息并及时处警。在处警过程中,受害人往往因夹杂着感情因素而选择调解,在办案民警取证时也不愿意配合做笔录、验伤,导致取证难度增加。因此,处警民警需提高取证意识,防止一时贪懒造成今后补正难、调解难、处罚难的现象出现。第二,善用“告诫”,震慑家暴。公安部门的介入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最成功的手段。[14]家庭暴力相对隐蔽,又具有反复的可能,在面对家庭暴力案件时如处置不当可能难以发挥应有的干预效果,不能有效应对受害者的求助,反而导致故意伤害的继续,甚至民转刑恶性案件的发生。2020年以来,S地区共接家庭暴力类案件789起,开具《家庭暴力案件告诫书》172份。相对于调解处理这一对施暴者毫无震慑力的处置方式,告诫手段有效阻隔了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和反复性。第三,重点走访,联动关注。社会隔离不等于社会孤立,公安机关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力量之一,不应以防控为由推诿、拖延家庭暴力事件的处置。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配合村居、社区和计生等部门,加强对发生过和易发生家庭暴力及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的家庭开展走访,做到定期动态掌控。同时,在走访过程中开展有针对性的谈话,帮助强势方端正态度,学会克制;帮助弱势方找到防范或者避免家庭暴力的方法,鼓励受害方在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捍卫合法权益。第四,拓宽渠道,事后保障。公安机关可以加设线上线下家庭暴力求助渠道,开通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报警功能,安抚并提醒报警人对现场状况、受害者伤势情况等相关证据的收集和保留。
四、结论
家庭暴力的发生是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性别、年龄、童年经历、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失业率等内部因素,也包括他人实施暴力行为的潜在影响、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社会资源和机会的短缺、自然或人为灾害等外部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影响家庭暴力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疫情不仅带来了家庭暴力事件的上涨,也改变着公安机关的工作方式。公安机关在更新执法理念的同时要注意自身角色的转换,做到事前预防、事中制止,事后保障,切实发挥家庭暴力的干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