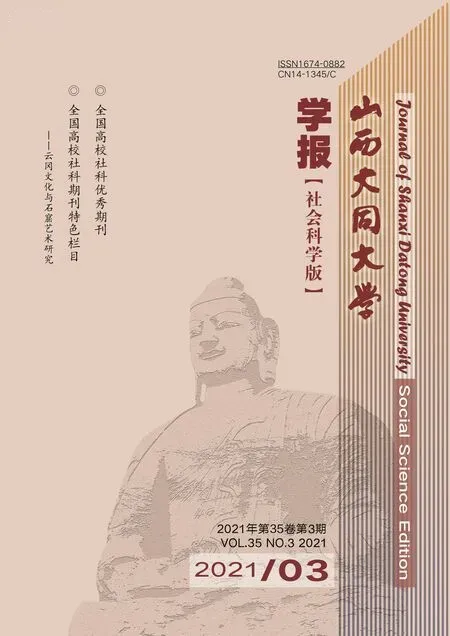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视角下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
——以《高兴》英译策略研究为例
马如桃,路东平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贾平凹是中国乡土文化和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文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之一。他在2007年出版的小说《高兴》中,生动描写了“向城而生”的社会底层民众和“流动工人”,是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深刻体现。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韩斌(Nicky Harman)在2008年甫一阅读这部小说,便萌生了翻译的兴趣。同年,她在英国的《卫报》发表部分节译,经出版商亚马逊授权后,便开始着手翻译。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直至2017年10月,英译本Happy Dreams:A Novel才得以出版。十年打磨使得《高兴》英译本问世后便引得读者热议,最终入选了亚马逊Kindle First项目。同时,Happy Dreams的海外热销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贾立平、张钰迪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索了《高兴》英译本的文化翻译。[1]史嘉维(2018)从目的论视角解读《高兴》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2]程南南等(2019)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究《高兴》中的方言英译策略。[3]可见,尽管《高兴》原文本研究已渐入佳境,英译研究却囿于语言学或文学等角度,鲜有学者从惯习与规范的互动角度解读该文本。
翻译的社会研究兴起于20世纪九十年代。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描述性翻译研究和布迪厄社会学。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和译者惯习(translator’s habitus)逐渐成为一对高频出现的重要学术话语,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均是从社会学视角描述、阐释翻译现象,既关注文本内因素,又考虑文本外因素。译者惯习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个体选择,翻译规范则关注宏观的社会层面,将二者结合即主客观结合可以更为清楚地阐释翻译行为。[4](P11-16)
一、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
(一)翻译规范 “规范是将正确与错误、恰当与不恰当的普遍价值观念转换为恰当且适用于具体情形的行为指南。”[5](P95-98)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受到社会的驱动与制约。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或民族底蕴等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对翻译的驱动与制约都必须要通过翻译规范来完成。根据图里的分类,翻译规范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预备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预备规范涉及原文的选择问题,即译者倾向选择的原文类型、影响译者选材的宏观因素和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偏好等,这些均需译者在着手翻译前思考清楚。[6]起始规范指译者对原文本采取的三种翻译策略,即以原语为依归、以译语读者为依归兼顾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操作规范涉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如命词遣意、句法结构的合理运用等。翻译规范是社会主流期待和译者个体行为之间的调和,强可近乎翻译行为的社会“规定”,弱可表达为译者的“个性特点”,既可以解释集体行为,又可以描述个体行为,从而有很强的解释力。[7](P10-14)然而,翻译规范,基于其客观的性质,往往忽视译者的主体性,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可以弥补这一空缺,使其不囿于绝对的异化和归化翻译。[8]因此,译者惯习便应运而生。
(二)译者惯习 惯习是一套深刻内在化的、促使行为产生的性情倾向系统,既为社会世界所产生,又生产社会世界,因而既具有持久稳定性和历史性,又具有可变性和建构性。惯习形成于行动者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客观社会结构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产物,与此同时,又作为一种人脑中的结构化的机制,主导着人的社会实践,从而在无形中维持或改变现有的社会客观结构。[9]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核心行动者,其对翻译的认识和翻译实践必然受社会经历、教育程度、职业生涯等的长期影响,形成颇具译者个人特色的翻译惯习。因此,译者的翻译选择并非总是有意识的、目标明确的策略性选择,而是客观社会现实在其潜意识中的内化。因此,译者惯习是被构建的个体认知结构,而内在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译者惯习,往往作为一种“前结构”的行为模式,会潜意识地调动和指挥译者的翻译方向,[10]从而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新的翻译实践的生成过程也是译者惯习重构的过程,这一同时既结构又被结构的特性是译者惯习的本质特征。而译者惯习,既因其长期受到社会客观结构的形塑而具有稳定性和历史性,又因个体社会轨迹的差异而具有个体性,会逐渐形成带有个人偏好的认知视角和行为倾向,从而影响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的个人惯习,在文本中体现为形成不同的翻译风格,包括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
(三)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的关系 惯习使规范具体化,没有规范的惯习和没有惯习的规范一样没有意义。[11]“在翻译场域中,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同时存在,翻译规范在约束翻译行为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译者惯习,而译者惯习又促成翻译规范的形成和发展。”[4]翻译规范内涵于行动者的互动中并通过互动来实现,换言之,通过不同惯习之间的互动来实现。[12]个体译者的独特惯习,逐渐形成各自的翻译风格,包括翻译策略和翻译文本的选择。在这些翻译风格中,“那些有相似风格特征、对翻译的作用和社会功能持相似态度的翻译行为构成或居于主导地位、或居于边缘地位的各种翻译规范。”[7]这些翻译规范会反过来影响译者惯习的倾向系统,促使译者不断调整翻译选择。一般来说,个体译者惯习的生成与翻译规范的更迭并非总是趋于一致。当个体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一致时,译者的翻译实践是对翻译规范和其自身惯习的融合。而当个体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冲突时,译者惯习则协调其与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协调过程中,部分翻译规范逐渐内化为译者惯习,译者惯习继而进行新一轮的重构。
二、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视角下翻译文本的选择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里,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翻译是预备规范对译者影响的结果,[13]换言之,预备规范所涉及的社会现象会逐渐内化为译者惯习,进而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材。韩斌选择翻译《高兴》与时代背景、赞助人、关注流动工人的社会惯习等密切相关。首先,受意识形态和时代背景的束缚,译者一般会选择契合当时翻译政策的作品翻译。[13]《高兴》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流动工人“向城而生”,他们的遭遇引起了译者的共鸣。[14]其次,“预备规范由赞助人决定”,[15]赞助人属于场域中的行为体之一,与译者惯习这一核心行为体在场域中形成以斗争为主的关系网络,共同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选择《高兴》作为翻译文本也是应赞助商亚马逊的要求,韩斌也谈到“Mainly,I translate what publishers offer me.”。[16]同时,“翻译行为也是主体自发的行为”。[7]韩斌幼年时,受叔叔影响,从小对中国文化耳濡目染,且热衷于中国古典名著。[17](P48-56)2011年,她辞去大学讲师一职,成为全职译者,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之中,逐渐形成了传播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乡土文学作品的职业惯习。
三、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译者选择以源语为导向还是以目标语为导向的起始规范,往往受社会背景、出版商以及译者惯习等因素的影响。韩斌在叔叔的影响下,从小就热衷于中国古典名著,之后就读于利兹大学中文系,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渐形成了热衷于研习中国文化的学者惯习。韩斌于利兹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学位后,便前往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执教,负责教授翻译理论与技巧,2011年,她辞去大学讲师一职,成为全职译者,开始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社会化过程中,译者对西方文学场域和权力场域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关照普通英语读者的译者惯习,[18]促使她在翻译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时,灵活采取替换、删简和增译等翻译策略。此外,随着《黄河边的中国》、《扎根》、《中国母亲》、《金陵十三钗》、《倒流河》等译作的接连出版,译者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本,逐渐在翻译场域中占据优势地位,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意识。韩斌曾谈到“中英文句法的不同意味着每位译者需要自己做出选择”,[19](P50-56)不仅要考虑译语读者的主观感受,也要尊重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忠实于原文,[20]使译者逐渐形成了向原文作者交际意图靠拢的译者惯习,具体体现在翻译部分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倾向于采取以原文为依归的翻译策略。在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意识,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并尽量保留源语的语言风格,成功地将《高兴》译介到西方世界。
四、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视角下翻译策略的具体运用
实际翻译过程是由译者的多个小决定组成的连续集,这就涉及到了操作规范和译者的主体性意识。韩斌认为,任何从译者的角度来考察汉英文学语言,都必须从语言本身的结构出发,两者之间存在着连续的差异,译者不仅要按单词或段落进行翻译,还要对整个文本的整体效果负责,译者应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译者主体性。[20]译者考虑到译入语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风格,没有局限于原文的形式和结构,而是在把握原文整体风格的前提下,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透过表面文字,挖掘深层次的内涵,舍形取意。《高兴》中的语言极具个性,文中方言土语的使用以及语音、语义的融合,彰显了其内在的文化素养,这些具有特色的文化作品给读者带来全新感受的同时,也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为了将文化中的异质成分化为可读的,便于译语读者理解的文本,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则要忠实于原文。下面就以《高兴》英译为例,从篇章语言规范出发,具体阐释翻译策略在文本中的运用。
(一)译语规范与译者惯习 韩斌会通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惯习和关照目的语读者的译者惯习促使她在翻译文化负载词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时,倾向于顺应译语规范,秉持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翻译原则,灵活采取替换、删简、增译等翻译手段。
1.替换 韩斌受西方文学环境的影响,会通西方诗学及各种语言风格;作为热爱、专修中国文学的学者,韩斌对中国诗学及各种语言风格也有着深度体悟。因此,在其英译过程中能够轻松自如地在西方诗学中找到对应的语言风格,比如:
例1:锅里剩下了一碗,我把它盛在盆里说明日再吃吧,五富说明日就馊了,不如我再加一下。他真的就吃了,梗了脖子,红着眼坐在那里发瓷。
译文:And he did.Then he slumped to the floor,his neck rigid,his eyes red and glassy.[22]
例2:五富说:你都三十四五了,你还弹嫌?[21]
译文:You’re thirty-five years old—you can’t afford to be picky![22]
例3:我是揭了床上的被子,用水擦净了床上的芦席,在芦席上擀,擀出了簸箕般大的一片......[21]
译文:I took the bed quilt off,wiped down the rush matting underneath,and rolled out the dough into a sheet as big as a fan.[22]
“发瓷”“弹嫌”和“簸箕”是极具方言特色的词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以译语读者为依归,避难趋易,将这些带有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替换为地道的、利于读者理解的表达方式。译者曾谈到:“她必须以一种不过于地方化的方式,将文中的文化因素传递给译语读者,将文化中的‘异质’成分化为‘可读’的,便于译语读者理解的文本”。[23]因此,译者将“发瓷”“弹嫌”和“簸箕”用简单通俗的语言翻译了出来,这种策略贯穿于《高兴》所含陕西方言的英译之中。这也是其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学者惯习、关照普通英语读者的译者惯习的外在显现。
2.删简 西方的汉英文学翻译出版社为了吸引目的语读者,倾向于将可接受性和流畅性放在首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畅销,以提高国际声誉,进而获得利润丰厚的版权合同。因此,出于商业原因,译者,尤其是出版商可能会删除他们认为不受欢迎的部分。这些因素帮助构建了韩斌删繁就简的译者惯习,在很多地方采用删简的翻译方法。
例1:西安城里的美女很多,尤其当你正走的时候,突然从某酒店出来了三四个,都是一米七以上的个头,都是瘦脸蜂腰长腿,都是鲜亮的衣着。[21]
译文:They’d burst out of restaurants as I went by,three or four at a time,all of them over five foot six,beanpole-thin and long-legged,and dressed in bright colors.[22]
例2:五富更蛮横了,说:那你掏钱,你掏钱![21]
译 文:“Then get your money out!”Wufu yelled rudely.[22]
韩斌将“瘦脸蜂腰”简译为“beanpole-thin”,既准确传达了原文信息,又避免给译文读者造成困惑。例2中,原文有意重复“你掏钱”来加强语气,译文为避免重复,选择将其省略,更简洁。同理,省译“这白癜风哪儿生不得”,避免了重复赘言,韩斌也曾明确表示:“汉语通常使用重复来表示强调,但在英语中很难用同样的手段再现原文意图,因而译者应尊重译入语的语言习惯。”[24]体现了其向目标语读者靠拢的译者惯习。
3.增译 为了实现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没有囿于原文的形式,而是侧重于语境意义的传达,比如:
我不知道挣钱不容易吗,可事情逼到这一步了,癞蛤蟆支桌子,只有硬撑着![21]
译文:Of course,I knew that money didn’t grow on trees,but once we’d gotten that far[in the ticket queue],it was like a toad propping up a table;you had to just grin and bear it.[22]
这句话出现在高兴决定买芙蓉园价格不菲的门票时说的一句话,译者通过使用“that,but”等连接词将原文的散句进行整合,适当增加“in the ticket queue”等词,使原文意义更加明晰化。此外,译者将“我不知道挣钱不容易吗”用地道的“I knew that money didn’t grow on trees”进行替换,都是向读者靠拢的译者惯习的体现。
由此可见,在翻译一些具有地域色彩的句子时,译者倾向于选择以读者为依归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降低了源语信息的陌生性、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使译语读者能够跨越文化的鸿沟,以一种更加透明的方式接近原文作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译者惯习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而且也体现在微观选词造句上。
(二)原语规范与译者惯习 韩斌认为译文既要考虑译文读者的主观感受,又要考虑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如果原文的文化负载词难以理解,或者在译入语的文化中有对应的表达,倾向于采用以译语为依归的翻译策略。但对于那些很难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且容易理解的文化负载词,译者倾向于顺应原语规范,选择以原文为依归的翻译策略,以保持其风格特点。
1.地名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英译的《高兴》一书中出现了许多地名文化负载词,笔者选取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名文化负载词进行分析,发现译者在翻译一些特色的地名时,倾向于采用以原文为依归的策略。
例1: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21]
Freshwind folk believe the spirit of someone who dies away from home has to make its way back.[22]
例2:我去看了大雁塔,去看了文庙和城隍庙,去了大明宫遗址,去了丰庆湖,去了兴善寺。[21]
I went to see the Big Wild Goose Pagoda,the Confucius Temple,the Town God Temple and the Great Xing Shan Temple,the ruins of the Daming Palace,and the Feng Qing Lake.[22]
译者将“清风镇”译为“Freshwind”,有利于读者贴近原文,了解这个小镇山清水秀的风貌以及清惠的风化。其次,译者保留原文意象,将“大雁塔”、“丰庆湖”分别译为“the Big Wild Goose Pagoda”,“Feng Qing Lake”,既保留了原文风格,又能使译文明白晓畅,无疑是译者向原文作者交际意图靠拢的译者惯习的体现。
2.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物质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主要通过物品来体现,包括食物,服装,住房,工具和交通等。[25]韩斌倾向于将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乐器和食物进行音译,比如:
例1:我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21]
译文:I can play the xiao,the flute you hold vertically.Back in Freshwind,lots of people could play the fiddle,but only I played the flute.[22]
例2:饭辰居民用四轮小木板驮着水桶都走了,五富在那里一边啃干馍一边嘴对着水龙头喝。[21]
By lunchtime,the residents with their water containers on wheels had all gone,and Wufu was sitting there,gnawing on a ganmo and drinking from the faucet.[22]
上述例子中,“箫”和“干馍”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很难在译语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且文中屡次出现,为了保留原语词汇的文化形象,译者分别采用音译加注和音译的方式,努力使译语读者能够产生与原语读者相似的情感体验,既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又可以将这种地域色彩忠实地传达出来,同时让译语读者产生了阅读的新鲜感和兴趣,也达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这也是其向原文作者交际意图靠拢的译者惯习的外在显现。
3.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语言文化负载词是反映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形态和句法系统特征的词,增加了翻译的难度。[26]汉语重意合,往往几个简单的字就能表达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汉语的歇后语。
例1:西安人三头六臂啦,是老虎吃人啦,没出息![21]
译文:It wasn’t people were man-eating tigers or had three heads.He was hopeless![22]
例2:我说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么。[21]
译文:“We are like tigers,hungry enough to eat the sky.We just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I told him.[22]
“三头六臂”原为佛家语,指佛的法相,后比喻神通广大。译语读者没有相关知识背景,但并不难以理解,因此,译者将“三头六臂”进行字面翻译,让译语读者向原文作者靠近,更能体现刘高兴嘲讽五富进城心生胆怯时的场景。其次,译者保留了歇后语“老虎吃天”这一意象,使英语读者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进一步体现了其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的职业惯习和向原文作者交际意图靠拢的译者惯习。
结语
《高兴》在西方的成功译介与韩斌熟谙中西方文化的学者惯习、热衷于传播乡土文化的职业惯习和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等密切相关。译者灵活采用替换、删简、增译、音译和字面翻译等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贯穿于韩斌译介的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策略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