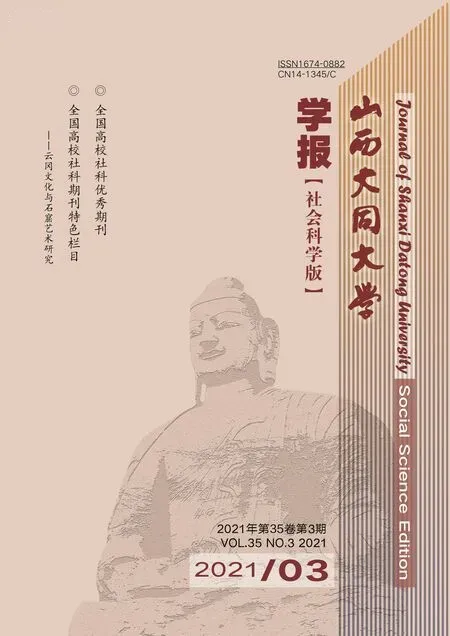论彼得·汉德克《骂观众》的元戏剧性
刘玉杰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诺奖评委给出的授奖词为:“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1]授奖词虽然短短一句话,却将汉德克获奖的理由道尽:语言学才能显然属于人类的内在体验,而外延表明的是人类体验的外在性、外围性、边缘性。汉德克戏剧的张力与魅力隐藏在这一内一外之间。《骂观众》(1966)就是一部以内(说话)索外(戏剧的边界)的元戏剧。所谓元戏剧(metatheatre),也被译为后设戏剧、超戏剧等,指“一种把主题集中于戏剧本身、亦即‘说的’是自己、‘自我再现’的戏剧。”[2]简单说就是关于戏剧的戏剧。
同样完成于1966年的《自我控诉》已经彰显出元戏剧的特征:“我来到剧院里。我听了这部剧。我朗诵了这部剧。我写了这部剧。”[3](P26)戏剧人物与剧作家的重叠构成了戏剧的自我指涉,也即元戏剧性。但《自我控诉》的元戏剧性并不十分突出,相较之下,完成于同一年的《骂观众》则充满了元戏剧性,可以看成是一出元戏剧。剧中说话者(演员)对观众说的如下台词,可以看作是全剧元戏剧性的总纲:“你们已经认识到,这个剧本是在同戏剧本身进行争论。你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主要是在否定。”[3](P49)通观全剧,说话者如何引导观众反抗、否定传统戏剧,成为《骂观众》元戏剧性的焦点所在。
一、反摹仿幻象而重本真现实
《骂观众》明确反对摹仿:“我们不会向你们展示任何东西。我们不会模仿任何东西。”[3](P69)亚里士多德却不然,在《诗学》中将摹仿看作人区别于动物的天性,因摹仿而产生了诗歌、戏剧等诗艺。他认为悲剧必然包括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等六个成分,而它们全都与摹仿有关,“其中两个指摹仿的媒介,一个指摹仿的方式,另三个为摹仿的对象”。[4](P64)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艺术摹仿其实要制造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世界,也就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构的观念世界,即戏剧幻象或者说戏剧表象。区别在于,柏拉图所论摹仿,意在突出其负面意义,认为诗歌、绘画等艺术无法真实有效地反映现实;而亚里士多德赋予了摹仿正面意义,认为艺术摹仿必然与现实不尽相同,但却不妨碍有效真实地表现现实。质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戏剧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有效摹仿,因此可以将亚里士多德的戏剧观概括为“戏如世界”。
在此意义上讲,反摹仿实质上就是反对剧中多次出现的“世界如戏”观。“戏如世界”与“世界如戏”所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是视角有所不同,前者是从戏剧出发的视角,后者则是从世界出发的视角。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如戏的观念都深入人心。莎士比亚的戏剧表述成为世界如戏观的经典表述,在其《皆大欢喜》中,剧中人物杰奎斯说:“全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世界如戏观反映出人都是演员,都在表演自己的生命,而生命一旦沉醉于戏剧幻象,就丧失了本真性。世界如戏观主张通过戏剧可以认知世界,表面看主张现实世界和戏剧世界的同构性、一致性。而事实是,现实世界与戏剧世界更常见的情况是差异性,而非同构性。两个世界的观念本质上是人类的主观构造,在原本没有界限的地方,人为地增添了界限,一个世界硬生生地被分为两个世界。
与此两个世界观相反,彼得·汉德克主张一个世界观。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即第四堵墙应该被打破。“舞台的前沿并不是界限。它并不只是偶尔才不是界限。它在我们对你们说话的整个时间里都不是界限。”[3](P42)从观演空间来看,“这舞台并不代表世界。它属于世界。这舞台的功用在于供我们站立其上。这并非与你们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3](P4)为此之故,剧中提出戏剧舞台是空的这样的观点,因为这出戏根本不需要任何实物道具,空就是最真实的舞台场景。而且这种空洞是真实世界的空洞,而不是戏剧世界的空洞,是没有任何附加意义的原始空洞。借助空的舞台,汉德克旨在反驳戏剧被赋予的象征、深度、形而上观念的沉重负担,从而将戏剧还原到现实世界。
一个世界的还原还必须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传统的观演关系是一种引导与被引导的权力关系,戏剧幻象由此产生。观众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之下,受制于演员的表演。观众的思想看似是自由的,其实只是跟着演员思考。所以观众是“没有思考”“思想不自由”“受压抑”的。而事实上,不仅仅是观众注视着演员,演员也在注视着观众,观众也是被注视者。之前的戏剧演出中,观众席往往是黑暗的,而舞台则是明亮的,这样的明暗设置,使演员处于被看的劣势,而观众处于看的优势。随着《骂观众》对明暗区分的打破,也就消散了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建立起演员与观众的平等互看关系。正是通过彼此注视的方式,演员和观众渐渐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隔绝的两个阵营,所以剧中说话者说:“我们可以不再称呼你们为‘你们’,而是共同使用另外一个称呼:‘我们’。”[3](P39)第四堵墙拆除之后,演员与观众的确成为一个整体,只有这样他们才共享同一个世界。
此外,一个世界的还原还必须打破传统戏剧的教诲观。说话者说:“我们不需要幻象才能让你们醒悟。”“你们的面前也并没有竖起什么镜子。”[3](P40)意在打破传统戏剧所赋予自身的教诲功能。暗示的显然是亚里士多德旨在借助摹仿得到知识的快感,以及借助悲剧消除恐惧和怜悯的净化论。这一教诲功能的实现是以间接、曲折的方式展开的。因此说话者将这些传统戏剧看作是具有本体和表象的“双层的”戏剧,“在它们的背后还另有东西”。[3](P65)戏剧尽管是一种表演、假扮,但却被赋予了反映真实的重任。“所有假扮出来的东西都在披露一些真实的东西。表演的目的不是戏剧,而是真实。据说你们应当去发现隐藏在戏剧后面的那个假扮出来的真实。”[3](P66-67)或者确切地说,人们被要求从假扮的戏剧里获取关于现实的真实状况。通过戏剧幻象,使人由彼及己,由表象而至本体,从而接受教诲。这样的双层戏剧被称为“不纯粹的戏剧”。尼采就明确反对这种净化观:“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激烈的爆发从一种危险的激动情绪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理解的):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6]无论是将戏剧看作幻象还是镜子,都表明艺术是一种反映真实的中介,是具有间接性的。《骂观众》则倡导并践行了一种更为现实的、直接的戏剧性,即谈话。
二、反戏剧情节而重戏剧话语
亚里士多德以来,情节一向被视为传统戏剧的灵魂和第一要素。“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4](P63、P65)一直到现代戏剧家布莱希特,都可见对情节中心论的服膺,他在《戏剧小工具篇》如是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故事(即情节——引者注)是戏剧的灵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同感。”[7]
因为《骂观众》取消了对行动的摹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戏剧人物,也就因此没有戏剧行动(戏剧情节),剧中说话者多次语气笃定地告诉观众:“这里没有那种要愉悦你们的剧情。”[3](P40)尽管说话者认为也有情节,但这决然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情节,我们且看说话者对情节的陈述:“我们在不间断地直接对你们说话,我们也借此与你们构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在一定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不称呼你们为你们,而是说我们。这意味着情节的统一性。”[3](P59)实际上就是反对传统的观演关系。表演是戏剧演员的本色,而《骂观众》中的演员却一再表明拒绝表演的立场,演员也不再称为演员,而叫说话者。相反,观众却天生就懂得如何表演,而且是模式化的、规矩的演员:“你们是纯种的演员。……你们是最强的演员阵容。你们是最理想的演出阵容。”[3](P75-76)与没有情节、没有表演相匹配的是,舞台变成没有道具的空的空间,因此也就没有道具的位置:“道具在舞台上的位置并没有被设定好。……这里并没有用粉笔标出东西摆放的位置。也不存在什么可以帮助记住人物站立位置的东西。”[3](P55)彼得·汉德克向我们揭露了戏剧行动(情节)展开所倚靠的位置标记这一细节,旨在让读者了解到戏剧行动的编排、虚构特性。
观众离开情节是否可能?或者说取代情节的又是什么?《骂观众》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观众从看客、盘观者的角色转换为戏剧焦点、中心、主题本身。如此一来,观众不再需别人演给他们看的情节,因为他们自身就处于“情节”之中。“你们不再是旁观的看客。你们就是主题。你们就是焦点。你们是我们话语的中心。”[3](P41)替代行动、情节的正是话语,所以说话者说:“我们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行动。”[3](P58)传统戏剧中非但不缺乏戏剧话语,而且戏剧话语所占分量并不太低,剧情的展开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演员之间的交谈式对话展开。与传统戏剧不同的是,《骂观众》中戏剧话语成为绝对主导,而且变成了由演员向观众讲话的陈述式话语模式。因此,说话剧的戏剧形式特别适合元戏剧所要展开的戏剧论争。
与程式化的观众相反,四位说话者是反程式的,他们随便地站成一排,说话顺序是随意的,言语彼此混合:“他们说的骂人话相互交织重叠。他们的话语搅在一起。他们从彼此那里接收单词。”[3](P35)四位说话者的话语没有条理性,而且不断重复,总体呈现出混乱与无序的戏剧效果。没有名字的说话者是没有主体的人,其全部戏剧功能就是说话。说何人之话呢?我们既可以将他们视为预言者,是某种真实状况的转述者,又可以将他们看作是疯癫者或呓语者,只是在说一些疯人疯语或者梦话而已。然而,他们身份的模糊性、说话的混乱性只是一种剧作家故意为之的戏剧修辞,四个说话者实际上只是一个说话者,即剧作家本人,说话者如此自道:“我们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意见,而是作者的意见。”[3](P58)这样一种戏剧人物的设计,本身就具有十足的戏剧张力,显示出一种隐蔽的元戏剧性。
三、反戏剧而重剧场
剧场性的刻意展现构成了《骂观众》的第三重元戏剧性。戏剧理论家汉斯·雷曼区分了戏剧与剧场的两个概念,戏剧的希腊语本意是去做,所表达的戏剧观可以用“做戏”来概括,指的是剧作家的戏剧创作,而剧场的希腊语本意是观看的场所,所表达的戏剧观主要指向了“看戏”,指的是观众的戏剧接受。雷曼指出:“戏剧诗学坚持把行动作为摹仿的对象。而新型剧场则恰恰起始于戏剧、情节、摹仿这三颗星的沉陨。正是这种三位一体使得剧场不断沦为戏剧的牺牲品,使得戏剧成为戏剧化的牺牲品,而最终使得戏剧化成为概念的牺牲品——真实在这个过程里不断撤退着。”[8]由此可见,《骂观众》所主要否定的是以亚里士多德戏剧观为圭臬的戏剧诗学。所谓冒犯观众,就是要把沉醉在戏剧诗学中的传统观众唤醒,其真正目的非但不是贬低观众,而是要提升观众在戏剧中的在场感。剧场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观众在场感、剧场环境等方面。
传统戏剧的聚焦点是戏剧情节,观众、读者欣赏戏剧其实也仅仅是在欣赏情节,情节开始前、结束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情节的背景、余续罢了。《骂观众》打破了这一传统,通过对演剧过程与观剧过程的双重展示,解构了传统戏剧的情节表演中心论。一方面,不仅关注演员的演剧行为,而且也将观众的观剧行为纳入其中;另一方面,无论是演剧还是观剧,都尽量去展示其前、中、后的整个过程,而非传统戏剧仅仅关注演剧的中间环节。
剧本台词前的舞台说明,与传统戏剧剧本的舞台说明完全不同。传统的舞台场面说明介绍的是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设计的、灯光、效果、道具、人物上下场等,是为剧情展开服务的,因而也是建构性的;《骂观众》则因为根本没有传统的戏剧情节,所以它的舞台场面说明也就没有了可资服务的对象,它只能走向自我指涉,成为解构性的舞台说明。或者确切地说,它呈现给读者的不是戏剧情节的内环境,而是戏剧情节以外的外环境,即演剧过程与观剧过程。
所谓演剧过程,指的是演员进行戏剧表演前、中、后的整个过程,而所谓观剧过程,指的是观众进行戏剧观赏前、中、后的整个过程,两者往往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开。具体来讲,《骂观众》的演剧前、观剧前的过程,旨在解构为观众营造熟悉氛围这一传统做法。比如剧中着重提到,由于舞台幕布的视觉隔离,熟悉氛围只能是听觉的,因此幕布之后必须发出阵阵响声来,以使观众产生正在布景的错觉,从而获得观剧的在场感与仪式感。甚至不惜使用录音来达到拟真的效果:“也许在此场景下,使用其他戏剧的真实录音是非常有效的,通过录音观众可以听到,在大幕拉开之前,确实有很多物体被移动过。”[3](P33)除了舞台上的这种“类型化和风格化”程式外,观众席同样如此,引座员、节目单、铃声、灯光、衣着等等都显示出熟悉的气息。而演剧后、观剧后观众的反应也被完整表达出来,从鼓掌、起立、将节目单放进口袋、相互交谈、评论戏剧一直到衣帽间穿大衣等细节都被刻画出来。反讽的是,扬声器里播放着雷鸣般的掌声和狂野的口哨声,四位说话者以此来向观众致意。
演剧观剧的前、后环节都是以观众为中心的,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演剧、观剧的中间过程却不顾观众的感受,以“骂观众”为全部内容。剧名Publikumsbeschimpfung中的Beschimpfung(英译为offending),是冒犯、责备之意,观众之所以遭到冒犯,主要原因在于观众的观剧惰性。“所有的一切还是和原来的一样。你们的期望并没有变成失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向座椅上靠去。演出可以开始了。”[3](P64)观众在《骂观众》中作为戏剧团体而存在,而非戏剧个体:“你们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个东西。你们是一个团体,在形成一定的秩序。”[3](P54)之所以说观众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团体、是东西,原因在于观众没有个性,呈现出的只有群体性,包括他们的穿着、打扮、身体姿态、目光方向,甚至观看本身也成为一种使人僵化的程序。因此,观众的主体、主人姿态必须得到冒犯,观众被说话者反主为客:“你们在这这里不是主体。你们在这里是客体。你们是我们话语客体。”[3](P48)观众因此被置于舞台之上,或者说传统舞台的范围扩展到了观众席,剧场性也由此得以凸显。
最后,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骂观众》试图否定的对象是什么?又有所肯定吗?不难发现,《骂观众》的元戏剧性总体体现在与以亚里士多德戏剧观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的对话,更确切说是对后者的质疑、否定。同时也必须看到,《骂观众》并非一味地进行否定,与《空的空间》《迈向质朴戏剧》《后戏剧剧场》等剧场性论著具有同调性,是以剧场性为显著特征的戏剧现代性的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