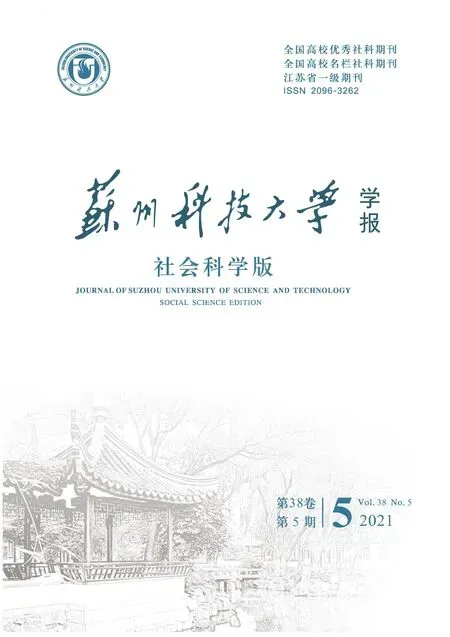知识分子的生意 *——顾颉刚与朴社的出版发展考论
董 娟
(肇庆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肇庆 526061)
1923年1月,朴社成立。这是一个由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周予同、沈雁冰、胡愈之、陈达夫、常乃德、顾颉刚等十人组织发起的出版机构,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出版社。这使得朴社从发起成立到出版经营都带有显著的“书生意气”。
一、创办缘起
1923年1月郑振铎公寓的一次聚会直接促进了朴社的诞生。顾颉刚在回忆朴社成立时提到郑振铎的倡议:
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1]124-125
因此,朴社成立的最初动机在于解决经济问题。但朴社创办的思想渊源并非始自这场聚会,而是有着更为长久的社会酝酿。
(一)社会原因:教育界窘境
晚清以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促使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职业市场取代学官体系成为知识分子生存的主要场域,治学成为一种职业。知识分子依托大学、研究所、图书馆、出版社等新式学术机构,从事专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工作,以此获取报酬维持生活,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学术研究职业化”[2]。但是,由于政局不稳,社会发育不完善,物质保障乏力,晚清至民国时期职业化的知识分子经常面临谋生困境。治生尚且困难,何以言治学?
晚清以来形成的积弱积贫的社会状况,至民国建立后仍未有实质改观,政府财政困顿,外债累累,教育经费本不充足,又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军费开支庞大,不断挤压教育经费,甚至出现教育经费被挪用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极为支绌。[3]以大学这一最主要的学术机构言之,民国时期相关章程规定的大学教师薪酬尚属优越,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中上层,但是由于教育经费不敷,薪酬标准经常不能兑现,教师群体经常面临薪资拖欠的问题。[4]
1920年6月,顾颉刚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同年12月其在致父亲的信中提到“学校薪水,仅发一月;来往盘川,须六十元,此款无从筹措”,因此与其父商量,年假不归。[5]7顾颉刚任职半年,仅获得一月薪水,以致无法筹措返乡路费,言辞之间颇显困顿之状。该信还提到其他学校亦有欠薪情况:“况政象如此,即在外省,薪水亦将欠发。得苏州同学来书,谓省立学校九月份亦未发出;……可见遍地荆棘,同有此叹。”[5]71921年6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知今天教职员到教育部讨欠债的人有一百零八人之多。”[6]2896月3日,马叙伦等到政府请愿讨薪,至新华门时被兵士殴伤。[6]2921921年冬,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介泉(潘家洵)来信,谓北京现状穷,我们寓里紧,薪水想也不要想他。他和(王)伯祥实做了寒士,因为至今不曾装炉子。”[7]187又记:“伯祥来信,谓现在穷得车钱也没有了。”[7]1881922年,任教东南大学的吴宓也遭遇欠薪,“先是校中财窘,五月与四月,均仅发半薪”[8]。这一时期,安徽、河南等地教育界也发生教职员索薪运动。于此,教育界之窘境可见一斑。
薪水拖欠,经济压力陡增,许多大学教师不得已四出兼职,东奔西走。不安定的生活干扰了治学的心境,挤压了治学的时间。顾颉刚在致妻殷履安的信中述及两位朋友的境况:
缉熙、子水在同校,可算得是用功的,可算得有学问的,然而我看他们竟说不到看书两字。他们奔来奔去的上课已算忙了,又加之以应酬交际,又加之以生活上的逼迫,一天能够坐在书桌前的时候,实是很少。[5]309
顾孟余则指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由于收入不稳定,“教职员精神不专,竟与外事。……以北大而论,教授中至少也有半数在外兼差”,以致“不欲专心求学,学问程度不能提高了”。[9]教育系统作为知识分子赖以谋生、安身立命之所在,其困顿无着、保障乏力的状态带来知识分子的仓皇与失落。
1921年12月,顾颉刚在与戚焕埙的通信中不无悲愤又悲观地说:
生活逼迫,社会困穷,只使人一天到晚只是打算生活,不能得生活以外之乐趣,做生活以外之事业。……何况现在教育经费,各处都是积欠,像北京样,现在又是三个月了。在精神上既受气,在生活上更挨饿,比了商界还不如呢!所以先生要不过矛盾的生活,专做永久的事情,非我悲观,敢说现在中国没有这种地方。[10]15
面对社会的动荡、生活的困厄,知识分子不得不另辟路径,自我筹划。
(二)知识分子的诉求:生活独立,专心学术
有感于自己与一班同人的窘迫境遇,也有感于教育界的乱象,顾颉刚强烈呼吁能有一个“专心治学”的环境。1922年4月9日,他在致《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我亦甚愿求一纯粹为学之境遇,惜终不可得。……我意,我们应该讨论一个实际问题,即是如何可以打出一个专心治学的境遇来。这不能全靠于个人意志之努力,而社会之供给资财尤为要紧。在现在的中国,不能得到这种的帮助亦自在意中,但任其迁延下去,则学术界永没有希望,岂非大可伤心之事!……我们应该如何鼓吹,使得真有学术社会出来?[10]88
李石岑颇为同情,便将顾颉刚的这封信转示学界多位同仁,以引起讨论。先后有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严既澄、常道直、常乃德、陈兼善、李石岑诸君就顾颉刚提出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些讨论的书信便刊发在《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五、六号《通讯》栏目。[11-12]
这次讨论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实的结果,然而,正是这次讨论为朴社的成立做好了铺垫。在实践中,有些学者慢慢摸索出一条新的路径:自己做资本家,供给自己研究,也就是开篇所提到的郑振铎在同人聚会中的倡议——“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1]124-125。这一倡议很快得到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周予同、沈雁冰、胡愈之、常乃德、陈达夫(兼善)、顾颉刚等人的响应。此即朴社十位发起人,其中有六位曾经参与《教育杂志》关于生活独立问题的讨论,占比超过半数。可以说,由顾颉刚引起的那场生活独立问题讨论,实为朴社成立的思想张本。
(三)直接原因:商务印书馆的“刺激”
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影响最大,被称为“现代文化的摇篮”“没有围墙的大学”,成为教育体系之外知识分子的重要聚集地。许多知识分子在学校与商务印书馆之间流动,如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先后因北大欠薪、生计不稳而入职商务。朴社的十位发起人中至少有七位(郑振铎、谢六逸、周予同、沈雁冰、胡愈之、王伯祥、顾颉刚)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叶圣陶于朴社成立后不久(1923年3月1日)[10]77亦进入商务印书馆,其他两位发起人与商务印书馆也有着相当的关联。(1)有资料显示,陈达夫、常乃德亦有任职商务印书馆的经历,但具体任职时间仍需进一步考证辨明。他们试图自立门户,另组朴社,这与商务印书馆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根据顾颉刚的回忆,郑振铎在倡议自办书店时提道:“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1]124-125由百元月薪与百万利润的对比,知识分子们看到了知识所能创造的价值,也看到了一条主导自身价值的有效门径——自己经营一个书店。他们希望能够像商务印书馆一样创造并享受到知识商品化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从而实现理想中的经济独立、潜心学术之境遇。因此,商务之于他们,既是“刺激”,又是榜样。
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业的龙头,其元老张元济先生由翰林投身商业,他的成功为新式知识分子谋生与实现理想提供了范式。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的知识分子群体后来创办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朴社群体供职商务印书馆时,正是其全盛时期,顾颉刚等由此见识到现代化的出版企业。知识商品化带来的巨额利润激发了他们自办出版社的“野心”,他们所追求的“纯粹为学的境遇”最终落实在商业经营上。这种悖论式的选择,其实是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和积弱动荡的社会中仓皇无奈的自我扶助。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顾颉刚悲悼之时慨叹,如果当时能有专门的研究机关,衣食无忧,知识分子能够恣意学术,王静安的结局不致如此。[13]可见,生计与学术之间的紧张始终是顾颉刚的心结。设若能够不愁生计,专心学术,或许顾颉刚们也不会有创办朴社的念头。从来君子不言利,而此时正是出于经济动力,朴社自商务印书馆中分蘖而出。
综上,朴社的成立根源于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生计问题,而直接受“刺激”于商务印书馆这一现代资本企业。现代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商业资本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并开始积极面对知识的商品化,进而试图在市场中掌握主动,重建知识尊严。
二、发展历程
朴社于1923年1月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其间,朴社经历了战争、总部迁移、意见分歧、成员退出等,发展并不顺利。在这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有一位成员始终坚定地支持朴社发展,也正是有赖于他的勉力维持,朴社才运营了十五年之久,此人就是顾颉刚。朴社的发展变动与顾颉刚的人生际遇、学术情境密切相关。现以顾颉刚为中心将朴社发展历程略述如下。
(一)成立初期
1923年1月,朴社在上海成立后,成员们即着手制定章程,选举职员,招募社员,计划选题。顾颉刚任会计,王伯祥任书记。[10]149议决社员每人每月公积十元,作为社费,以备出版。[1]125在十位发起人之外,先后又有潘家洵、吴缉熙、吴颂皋、俞平伯、耿济之、郑天挺、郭绍虞、朱自清、陈乃乾等人入社,一时人才济济。1923年12月,顾颉刚结束其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返京复北大职。
1924年5月,“霜枫丛书”之一《浮生六记》出版。之后,朴社又出版了叶圣陶与王伯祥点校的《戴氏三种》,影印了《古今杂剧三十种》,还陆续推出“霜枫丛书”另外三种(《初日楼少作》《髭须》《剑鞘》)。这是朴社的第一批出版物。
然而在“霜枫丛书”出版之前,朴社同人之间就朴社宣言署名问题及组织发行机关事宜产生了争议。
(二)争议
1924年2月20日,朴社在沪成员陈乃乾、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伯祥五人集议,“拟即披露(朴)社中宣言及人物”[14]23。朴社成立一年有余,一直在“秘密”进行。由于朴社几位主要成员皆为商务印书馆编辑,按照商务印书馆规定,其职员不得在馆外从事同类型的工作[15]278,因此朴社成立以来并未对外公开。此时,上海同人要求披露朴社宣言与人物,应是考虑到《浮生六记》等书目即将印行,朴社需要向外界表明身份与宗旨,从而有利于图书的推广。既然上海同人不宜公开,那么列名宣言的任务似乎理应由北京同人担任。然而,北京同人并不同意。《王伯祥日记》1924年3月6日载:“饭后乃乾来,出《浮生六记》印稿交圣陶校。因谈北京同人不肯列名宣言,认为不协作,思飘然去。”[14]29于是,上海同人决定公函敦促北京同人,“弗懈进行”[14]29,结果仍未能达成共识。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北京同人何以会拒绝?这一点并未有明确资料显示。顾颉刚这一时段的日记虽提及朴社与致上海同人的信,但都未涉及列名宣言之事。商金林先生认为顾颉刚等北京同人之所以不肯列名宣言,是因为他们“觉得朴社设在上海,他们鞭长莫及。希望能将朴社的社址设在北京,由他们来主持”[15]278。这一说法未明所本。不过,争议的结果确实是社址设在北京。《王伯祥日记》1924年3月19日载:“决定答复北京同人,社址设在北京,发行机关在上海,且略告进行组织发行机关事。”[14]35
然而,争议并未结束。上海同人在答复北京同人社址设在北京的同时,还捎去了另外一个消息,即上海同人决定朴社与上海古书流通处合开一书店作为朴社发行机关,由陈乃乾负责。[14]35结果,这一决定亦遭到顾颉刚、潘家洵等北京同人的否定。顾颉刚在致妻殷履安的信中说明了理由:
近来乃乾拟在上海开书店一所,即用朴社公积作资本。我第一个反对,因为现在我们能力不厚,难于周转,开店之后要经常费,万一亏本,不但以前积款可惜,并且所亏之钱我们也收拾不了。我主张社员私人集资开店一所,如成功,则朴社根柢已打好,从此可以进步上去;如失败,则失败者系社员,非朴社,将来朴社正式开张时亦可得一借鉴,不致复蹈覆辙。[5]405
不只北京同人,时在杭州的社员俞平伯亦不赞成开店。[14]46经过几番接洽,上海社员最终认同了顾颉刚等人的提议。[5]405《王伯祥日记》4月16日载:“决议开店不涉社事,另推人担任出版委员全权处理。”[14]48
多次协商后,最终的结论是:朴社社址设在北京,发行所设在上海,但朴社暂不开办书店,开办书店的事由社员私人进行。朴社的社址设在顾颉刚、潘家洵、吴缉熙三位北京同人的寓所(北京大石作胡同三二号);上海的发行所设在古书流通处(上海广西路筱花园口),即朴社至此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发行机关,而是附设在其他书店发行。在双方往来飞鸿协商的过程中,朴社第一部著作——俞平伯主持的“霜枫丛书”之一《浮生六记》即将付梓,双方就社址和组织发行机关事相持不下,只能以“霜枫社”的名义出版。根据留传下来的旧书,《浮生六记》版权页显示“出版者:霜枫社”。至1924年8月叶圣陶、王伯祥所点校的《戴氏三种》出版时,版权页已注明“出版者:朴社(北京大石作胡同三二号);发行者:朴社发行所(上海广西路筱花园口)”,至此社址与发行所的设置已明朗。
(三)解散与重组
由列名宣言所引起的社址以及发行机关的争议,显示出朴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大隐患。同人在事务中总有分歧:叶圣陶为朴社起草的公告,顾颉刚嫌其弱,而重新起草[7]461;俞平伯以手写序请制版印入《初日楼少作》,以示美,而王伯祥以为这是“屑碎处狡狯”的名士气[14]72;叶圣陶认为朴社诸人“不免有贪懒爱写意的毛病”[16]76。又,社费不齐,出现拖欠:朴社成立仅半年,郑振铎作为朴社第一发起人就已欠缴三月社费。[16]76不断的分歧使热心的成员开始灰心。叶圣陶很早就因感到成员涣散而忧虑朴社前途。[16]76陈乃乾则因北京同人不肯列名宣言而“思飘然去”。[14]29王伯祥更是多次表现出对朴社的悲观态度,认为大家顾虑徘徊,众说纷纭,意见庞杂,又涣散不肯负切实责任,发言人多而做事人少,前途实无多大希望,由此“侧重在退出的一条路上”。[14]38-39、42、98及至1924年9月,“齐卢之战”为朴社解散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理由。朴社上海同人以“齐卢之战”及周予同、朱自清申请出社为由,议决解散。[7]535
与同人们的悲观失望相反,顾颉刚对朴社一直寄予厚望,充满乐观。他在宽慰叶圣陶的忧虑时说:
我们的社如不幸拆散,真觉可惜。因为社中诸友办事才虽少,而在将来的出版界都很有可以占势力的希望。我们现在把可以做出版事业的人结合了,将来我们钱也有了,著作也多了,真可以做一番事业,把我们现在不定的生活安置在固定的磐石上。如此,我们对于社会的贡献自可一年一年的进步上去。[16]76
他与沈兼士言:“现在(朴)社中虽有欠缴,而一年来居然积到千四百元,觉得前途颇有希望。”[16]519与妻言:“朴社自乃乾入社后,进行甚有力量,不久要出书了。英文选由介泉、颂皋编辑一定有精彩。”[5]389
顾颉刚的坚定乐观来自他对朴社成立初衷的坚持,即希望能够在出版界打出一个地位来顾全生计,实现经济独立,进而能够专心学术。因此,当上海同人议决解散时,他强烈反对,并力主将朴社本部迁至北京,重新组织。
1924年9月上海朴社议决解散后,顾颉刚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致信上海同人不同意解散,嘱勿分款;然后发出紧急通告,稳定了一批社员;同时以经理事宜自任,使朴社有了定力,稳定了局面。[7]536-5381925年6月,朴社选举,顾颉刚当选为总干事[7]633,随后职员派定,朴社重新组织起来。
(四)北京朴社
重组后,朴社新增了一批成员,冯友兰、范文澜、刘掞藜等学者先后入社。原朴社成员俞平伯、朱自清、郭绍虞、郑振铎等先后入京执教,进一步巩固了北京朴社的实力。同时,他们注意利用北京学术网络发掘作者,开拓稿源,如冯沅君、徐炳昶、张西堂、容肇祖、罗根泽、许仕廉等学者都有作品在朴社出版。顾颉刚还向胡适、钱玄同、罗家伦、容庚等约稿,更热情邀请容庚入社。高水准的社员与作者群体保证了朴社图书的学术质量。
为推广图书,朴社与多家出版发行机构建立联系,如北京大学出版部、志成书局、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振新书社、晨报社等。朴社图书版权页上所注的分售处“北京及各省各大书坊”字样,说明朴社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朴社图书的影响力也从北京向全国辐射。
自重组至1926年,朴社运营良好。尤其是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成为朴社发展的巅峰,不仅奠定了朴社的经济基础,而且塑造了朴社品牌,提高了声誉。1926年8月,顾颉刚离京南下,成为朴社发展的转折点。
1926年前后,国奉战争使北京陷入混乱,民众恐慌,商业滞困,店铺普遍闭门歇市,军阀政府对知识界施行高压政策,加之北京国立高校长期欠薪,许多知识分子选择离开北京南下。1926年8月,顾颉刚南下厦门任教,潘家洵与陈万里亦至厦门,后来吴缉熙、蒋崇年等因故离京,此皆北京朴社操持社务的重要成员。
战乱与政治高压对出版业,尤其是新书业造成打击。一方面,军阀政府到处搜检进步书刊,北大亦被搜检,朴社发行机关景山书社曾将新出书籍藏至顾颉刚寓所,以防搜检致累。[7]738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走避他处,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北京图书生产和消费市场。从朴社人事方面来讲,朴社社员离京,不利于社务的开展与推动。后来,顾颉刚在与容庚论及朴社时,亦将“社员星散”视为朴社发展受阻的重要因素。[10]186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朴社经营陷入危机。1928年7月,冯友兰致信远在南方的顾颉刚,谓若顾“下半年不到北平,朴社将无办法”[17]190。及1929年顾颉刚返回北平,“社中所存只六十元耳”[16]124。
在此困顿之下,顾颉刚决定专力为朴社编书[17]249,以自己的学术力量挽朴社之颓势,并向友朋借三千元用以整顿朴社[17]348。自1929年回到北平至1937年朴社停办,顾颉刚为朴社主持出版了“辨伪丛刊”10种、《古史辨》第二至五册。同时,朴社还出版了许仕廉的《文化与政治》《国内几个社会问题讨论》、郭绍虞的《文品汇钞》、范文澜的《群经概论》、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书籍。这些举措解了朴社一时之急,但终未能使朴社回复到《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的盛况。
时间刚刚进入1930年代,即迎来了中原大战,接着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战乱带来学荒,同时辽西、长江流域相继出现洪灾,战争与自然灾害影响了图书销路。《古史辨》销量亦呈下降趋势。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月余销售1500册左右[7]773;1930年《古史辨》第二册出版,月余销售约800册[17]450,几为第一册销量半数;至1931年《古史辨》第三册出版,初版1500册,一年才得以销毕,顾颉刚无奈感叹“亦可怜矣”[17]707。后时局愈紧,朴社与景山书社经营愈发艰难。“七七”事变爆发后,朴社与景山书社不得不停止营业,其出版工作由开明书店接手。
三、书目分析
自1923年成立至1937年结束,在长达十五年的发展中,朴社出版图书60种以上。分析这些图书,可以看出朴社出版的几个特点。
(一)与整理国故运动关系密切
在朴社的出版书目中,数量最大的是文献整理类书籍。根据现有统计,文献整理类图书有32部,约占现知图书数目的半数。这类图书的出版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可谓“整理国故”主张的具体实践,而朴社出版的《古史辨》5册(2)1937年朴社结束后,《古史辨》后两册由开明书店出版。、“辨伪丛刊”12种皆是整理国故的实绩。除此之外,还有叶圣陶和王伯祥校点的《戴氏三种》、李笠《三订国学用书撰要》、范文澜《群经概论》等3种。这是朴社在史学领域的整理活动,其在文学领域也成绩显著。
古代文学作品整理7种:(1)《浮生六记》(俞平伯校阅);(2)《陶庵梦忆》(俞平伯标点);(3)《粤风》(钟敬文整理);(4)《歧路灯》(冯沅君、冯友兰点校);(5)《张玉田》(冯沅君校勘);(6)《聊斋白话韵文》(马立勋改编);(7)《〈水经注〉写景文钞》(范文澜编集)。这些作品从不同文体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辑校整理,为新文学建设提供了传统资源和民间资源。
古代文论整理2种:《四六丛话叙论》和《文品汇钞》。另外,朴社还校订印行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刘师培的《论文杂记》等近人文学批评著作。这些都是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过程中重要的文献基础。
专史整理3种:《建安文学概论》(沈达材)、《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和《中国文学史大纲》(容肇祖)。
朴社成立的1923年正是整理国故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该年2月,顾颉刚在邀请郭绍虞加入朴社时说:
现在整理国故的声浪极高,但大家只是喊,没有实做整理的事。我们几个人如能切实在这方面做去,每人每年标点一种书,斟酌校订的妥善,便可有永久的价值。[10]150
可见,顾颉刚自一开始就将朴社与整理国故紧密联系起来,并将整理国故作为朴社重要的出版方向。
(二)具有鲜明的丛书意识
丛书出版,作为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出版类型,至清而盛,在民国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据统计,民国时期出版丛书在6400种以上。[18]朴社虽小,但亦具有自觉的丛书意识和丛书观念,正反映出民国时期丛书出版的普遍性。
根据现有书目,朴社共出版丛书10类:“霜枫丛书”“辨伪丛刊”“中法大学丛书”“文学批评丛书”“双玉丛稿”“凡社丛书”“中法大学理学丛书”“理学丛书”“的砾丛书”“栖霞丛著”。这些丛书的规模普遍不大,数量最多者为“辨伪丛刊”,计12种;其他有的仅三四种,有的甚至仅一种。由于丛书的开放性和延续性,这些规模较小的丛书亦为续刻提供了空间。如果朴社没有结束营业,那么这些已启动的丛书都有继续增刻的可能,将为朴社更大规模的发展做铺设。
丛书具有“汇集群书、聚集知识”的特点,它能够为读者提供体系化和规模化的知识,使知识使用更为便利。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出版者都十分重视丛书出版。在朴社的出版经营中,顾颉刚亦贯彻了这种丛书思维。即使是不具丛书之名的《古史辨》,也有丛书之实。当然,作为经营者,顾颉刚在学术之外还有商业利益的考量。1929年,顾颉刚自南方返京后迅速推出《古史辨》与“辨伪丛刊”数册,目的就是试图借助这两部丛书的影响力改善朴社的经营困境。后来,朴社再次面临不景气时,其妻殷履安认为近期不宜再印新书,但顾颉刚坚持继续刻印《古史辨》第四册:
因为有了第四册,前三册也会联带有生意的。我要使研究古学的人或要得到一点古代史的知识的人不能不买《古史辨》一书,所以各方面都要编集。罗根泽是诸子方面,刘朝阳是天文历法方面,钱宾四是今古文问题方面……这样弄下去,才可收到分工合作的功效。照这样下去,古史问题一定可以在我未死前得到许多结论。就是为朴社生意着想,凡买一册的人总想买全一套,虽不懂天文历法的人也不能不买朝阳编的一册,一买就是一整套,像《二十四史》一样,生意即使不多,而数目也可观了。至于无钱的人,则零买亦无不可。总要使得这部书成为史学界的权威,朴社就不会倒了。[5]609
可见,顾颉刚的策略是以学术带动商业,将《古史辨》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都发挥到最大。
至于“辨伪丛刊”,虽为朴社中数量最大的一类丛书,但其出版数量并未达到顾颉刚的预期。通过《顾颉刚日记》我们能够看到,顾颉刚至少为“辨伪丛刊”做过两集的出版计划,其中第一集10种已出全,第二集16种仅出了2种,其他14种则随着朴社的结束而搁浅。[19]332-333
朴社推出的第一批出版物即为丛书类型的图书,是俞平伯所主持的“霜枫丛书”。在顾颉刚南下的一段时间里,朴社又陆续推出了“中法大学丛书”“文学批评丛书”“双玉丛稿”“凡社丛书”“中法大学理学丛书”“理学丛书”等,这些丛书的主持者为谁已难以稽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朴社同人具有浓厚的丛书兴趣。丛书易于形成品牌,进而带来学术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丛书思维对于朴社的发展成长具有积极意义。
(三)致力专门书
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学界对新书和专门书的需求空前迫切,但一些大的出版社对新文化和新书的反应较为迟缓和保守,这引起学界的普遍不满。顾颉刚曾批评道:“不肯出专门书”,“每虑好书不易得好销场”,以致“学者有了专门的著作不能出版,使得社会上沾不到学问气息”。[10]134此言正是针对当时学术书不易出版的情况而发。大书局踌躇的地方,正是朴社果断前行的方向。
朴社出版的图书几乎全为“高等书”。在目前所知朴社书目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各学科研究性著作,以传统文史领域为主,兼及新兴的社会学、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学等学科,学术特征明显。另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文学作品类书籍,涵盖古今中外,或者属于新文学的组成部分,或者属于新文学建设的中外资源,其作者与目标读者皆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的精英群体。朴社经营始终循着“致力专门书,服务学界”的思路展开,它的出版活动成为顾颉刚构建“学术社会”的重要环节,即通过服务学界、弘扬学术重建知识尊严,使知识分子重新成为社会重心。
(四)学术影响力大
朴社出版图书总数虽不多,但学术精品不少,有许多作品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为朴社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它的出版改变了《浮生六记》湮没不彰的命运,备受现代学界激赏。之后,《浮生六记》一版再版,至今已有几十个版本,但大多仍以俞校本为蓝本。1927年4月,俞平伯又为朴社标点了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是《陶庵梦忆》“在现代的第一个单行本”,第一次采用新式标点断句。[20]这一具有现代文本特征的版本,是俞平伯及其所代表的朴社贡献给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的重要作品。《陶庵梦忆》与《浮生六记》一起成为新文学家塑造现代散文品格的重要文本,可谓朴社的“双子星”。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文艺学领域享有盛誉,而其经典化之路亦始自俞平伯和朴社。[21]1925—1926年,在陈乃乾、俞平伯等朴社同人的努力下,原载于期刊的《人间词话》终于以单行本的样态面世,而俞平伯为该书所作的序也基本引领了后来《人间词话》研究的方向。[21]
《歧路灯》这部清人小说开始亦流传不广,至朴社付印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点校本,又有朴社同人郭绍虞、朱自清等推介评论,才引起学界关注。虽然朴社本仅出前26回,但在《歧路灯》研究史上却有开创意义。
而朴社的支柱书目《古史辨》对现代史学以及多个学科的发展所产生的轰动性影响已为人所熟知,学术地位自不待言;朴社出版的其他学科的著作,其学术贡献也经得起考证,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这些耀眼的书目是现代学术思潮的体现,朴社由此成为现代学术思潮的推动者和传播者,积极履行着其服务学界的使命。
四、总结与反思
顾颉刚、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胡愈之、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冯友兰、范文澜,朴社拥有这些光辉的名字和上述耀眼的书目,却没能跻身大书局行列,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首先,朴社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业余性。朴社成员基本有各自不同的学术追求,朴社只是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的兼职事务。按照顾颉刚的设想,“等到(朴社)将来规模确可放大了,再选几个人出来专做这件事”[10]150。在规模扩大之前,朴社始终是业余性质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朴社难以建立严格而完善的企业制度。虽然朴社在成立之初亦制定过宣言社约(文佚),但考察朴社实践,这些基础性的规章并未能保证朴社的高效运营。朴社成立最初的几个月就有社员欠缴社费,散漫之状令人担忧。后来欠缴社费现象更为普遍,顾颉刚等同人不得不提请修改社约,就缴纳社费之事“规划一种较严整的办法”,以振疲倦气象。[10]278此外,朴社可能未对社员缴费以外的其他义务做出具体规定,也未制订除持股之外的其他激励措施,这就很难调动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大家参与朴社事务更多的是凭着个人热情和责任心。朴社成立之初,顾颉刚曾描绘过这样的愿景:“若各人每年可成一种书,五年后便可有一百部书,比现在的亚东、泰东强得多咧!”[10]149-150然而,这每人每年一种书的想象并未落实为规定,亦未落实为社员义务,导致现实与理想之间相差甚远。就现有书目统计,在朴社经营的近十五年中,朴社成员编著、校阅作品数量如下:俞平伯5部,叶圣陶2部,王伯祥1部,潘家洵1部,陈万里1部,冯友兰1部,范文澜3部,郭绍虞1部,郑振铎1部,顾颉刚12部。还有许多成员并未向朴社提供书稿。也就是说,朴社的人力资源未能充分调动起来,朴社的人力资本未能全部转化为经济效益。这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缺乏调动人力资源的有效机制。
其次,朴社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朴社中“著述才”多而“办事才”少,这一偏差对经营型的机构来讲十分不利。“办事才”少,势必使朴社在管理运营、事务处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出现薄弱;“著述才”多,则坐而论道者多,容易产生争议。1924年的几次纷争使王伯祥感叹:“本社发言人太多而做事人少见,前途实无多大希望也。”[14]98众多发言人始终未产生一位最终决策者,即使北京时期顾颉刚成为朴社实际主持人,出书仍要经过全体成员通过,这种方式容易造成掣肘,错过好书。1926年顾颉刚与钱玄同书云:
《诗经通论》,自己出版,极好。惟朴社出书过于矜慎,非经全体通过,竟无办法。《古史辨》一书,因所费太多(八百余元),社员已啧有烦言,谓资本太小,不能印此大书。故“姚氏六种”,最好我们自己凑钱印而委托朴社发行。[16]559
鉴于这种情形,顾颉刚在向胡适、罗家伦、钱玄同、容庚等约稿时,皆不敢约大书,只言小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碍朴社稿源。若朴社人才配置更为合理,则当更具成效。
最后,在出版策略上,朴社放弃教科书市场,也就放弃了另一种成功的可能。朴社在发起时试图复制商务印书馆的模式来出版教科书。其成立之初,大部分社员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还有的做国文教员,有着天然的优势进军教科书市场,且上海时期的朴社确曾做过出版教科书的计划。1923年2月,顾颉刚曾邀请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等共同编辑教科书[10]77,但这一计划最终停留在设想中。时隔一年,1924年2月,上海朴社成员王伯祥、沈雁冰、胡愈之、陈乃乾等再次提议编印教科书,选注辑印《中国文学选本》作为中等学校教本或补充课本,并具体分配了编辑任务。[14]21然而,这项计划最终搁浅。北京朴社则基本放弃了教科书市场,而将注意力转向专门书出版。
鉴于北京同人的学术志向,这一转向不能说失策,只能说转向了北京同人更感兴趣和更擅长的领域;但就民国整体的出版行情来讲,放弃教科书市场,也就等于放弃了一个巨大的利润空间。事实上,民国时期名列前茅的几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皆是先占据教科书市场,通过出版教科书筑牢基础,然后才将触角延伸到其他出版领域。
作为“阳春白雪”的专门书,受众范围窄,盈利空间小。朴社在立足未稳之时,即将出版方向完全转向专门书,使其整个出版过程无法大踏步前进,只能小心地缓步前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深受影响,从而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晚于朴社创办的开明书店,深受教科书出版之惠,其创办人章锡琛总结了教科书出版之于书局发展的重要性:“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其他各小出版家,如果没有教科书或其他销数较大的出版物,往往都倏起倏灭,不能维持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更谈不上什么发展”。[22]
朴社同人所期待的经济独立最终未能实现,但其“以商养学”的思路和经营实践却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体现出他们在日益边缘化的境遇中为重建知识尊严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