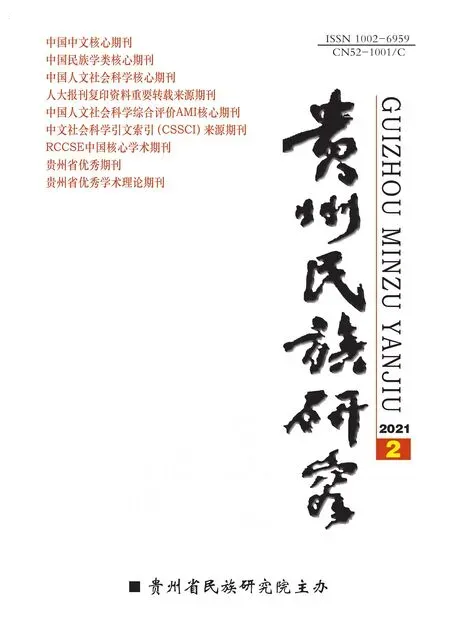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问题与再造
高春凤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城市的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社区,也是记录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的珍贵文化街区。它是拥有独特建筑文化符号遗存、鲜明民族特色和生活氛围的城市文化构成区域,承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乡愁,是解读城市悠久发展历史、表达城市有机体发展脉络、呈现特色文化意蕴的历史教科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传承意义和保护价值。本文以北京市通州南大街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为例,探讨少数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价值和意义,分析其目前面临的空间问题,提出建构空间再造的文化方案。
一、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价值
包括北京在内的世界著名城市,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主导国家民族历史,是因为它始终能够成功地代表民族文化,并将其传播后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文化自信的高度,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北京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张内蕴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保护传承利用好这张“金名片”,是首都发挥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的职责使命,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设意义。
(一) 彰显文化多元的人文品质
一个城市的人文品质是由多样性的文化凝结而成,保护北京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就是保护体现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美国城市学家路易斯·芒福德说:“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而不是机械地将大地的风光、文化的特性、社群的风格消磨掉。”[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一个文化大国保有自信的不竭动力,更是世界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是中国第四大民族,主要来源于13世纪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地来华的穆斯林,他们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节庆文化、生活方式。自元代始,回民大量涌入北京。随着明朝初年由南向北的大规模移民,北京的回民越聚越多。清初,为“拱卫皇居”,内城的汉民和回民迁到北京外城,但康熙年间,有钱的回民又迁回内城;康熙中期以来,北京回民集中聚居于牛街、朝阳门、花市、东四、西三里河、牛肉湾、扫帚胡同一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历史的变迁,回族人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除上述聚居地之外,远郊区县回民密集的村镇以通州区、大兴区居多。以本文样本——通州南大街回民聚居地最为典型。回族的居住格局是“围寺而居”和“因市而生”。一般而言,清真寺、市场、回民社区这三种生活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以至于演变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生活格局,北京的牛街就是如此。随着商业中心的转移,回民聚居区也随之转移,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清真寺兴衰史,就是这种文化逻辑演变的结果。与这种居住格局相伴随,回民清真寺风格独特的建筑、依循自然的民居建筑、职业赐予的重商传统、工匠精神、卫生习惯等,都是民族文化的形象化表达,是城市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北京要建设传承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应重视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把蕴藏在有形街区中的回民的信仰意识、性格品质、礼仪习俗、风土人情、节日庆典等文化元素挖掘出来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以此彰显北京城市文化多样性,提升城市人文品质。
(二) 彰显民族团结的城市气象
一个城市的城市气象与团结包容的民族意识密切相关,保护北京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就是践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民族团结发表重要论述,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长期以来,北京的回民群众始终站在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为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作出自己的贡献。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回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街区,由特定时期的居民参与创造,经过几代人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是承载回民美好生活的物质载体,也是体现北京城市发展文脉的重要生长肌理,不仅记录着这个民族生活区域的特色,更展现这个城市发展演变的轨迹,是非常有文化价值的历史性空间,是不可复制的珍贵文化遗产。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从事着生产生活活动和有特色的商业活动,有着基于宗教信仰的成熟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具有很好的群体文化认同和内聚力。他们与有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城市居民相互包容,团结友爱,共生融合,构成北京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就必须保护好、利用好北京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留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展现北京民族团结的恢弘气象。
(三) 彰显重信守诺的文明要素
一个城市的文明要素是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保护北京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就是留住回民以重商诚信为基础的文明要素。刘易斯·芒福德在探讨城市本质时,综合考量地理、经济、制度、政治、美学等城市文明要素,将城市描述为“一个地理网状物,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的过程物,一个社会战斗的舞台,一个集合统一体的美学象征物”[2]。在这里,城市既是一个为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服务的物质结构,又是一个为更有意义的行动以及更崇高的人类文化而服务的戏剧性场景。城市的本质既表征于经济体系之中,又内嵌于由经济体系承载的精神体系之中。回族是一个重视商业的民族,回民来到北京以后,大都以经商为生。早年京城的“三把刀”之说,就是回民从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动写照。所谓“三把刀”是瓦刀、切肉刀和切糕刀,指回族群众主要从事泥瓦匠、屠宰和小吃制作销售这三种行业。北京回族聚居区既是回民生活的文化布景,也是回民劳动的空间舞台。回民群众信仰伊斯兰教,其经典教义为《古兰经》,它倡导人们关注现实的物质生活,鼓励人们积极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充满了重信守诺的商业精神:一是倡导公平交易,正如《古兰经》所说:“你们应该使用公平的秤称货物”“你们应当用足量的升斗,不要克扣”[3](P285);二是信守契约,亦如《古兰经》所说:“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你们应当履行真主的盟约。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证者,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誓言”[3](P208)。北京的回民群众长期接受《古兰经》的浸润,形成了重视诚信,遵守承诺的文化传统,这也是如今回民聚居区独领北京小吃风骚的主要原因。北京回族聚居区不仅以礼拜寺而闻名,亦因独特的饮食文化而著称。这些被喻为“舌尖上的北京”的聚居区,洋溢着传统文化的契约精神。
二、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困境
回民聚居于北京市通州南大街始于元代,距今已600余年。该区域的最早回民有三个来源:一是成吉思汗攻北京城(时为金中都) 时,蒙古大军内部的部分回族工匠;二是蒙古大军中驻守通州军队中的回回及其家眷和后人;三是蒙古军南迁了许多在西征过程中俘虏的西域少数民族[4]。伴随回民在通州区的迅速繁衍,回民礼拜寺于元延祐年得以建立。之后,很多回民沿京杭大运河来通州寻找商机,聚居于南大街。直到今天,该地仍是回民较为集中的区域。目前,南大街由三个社区构成:(1) LHS社区。总户数2571户,总人口5070 人;其中,回族3262人,占总人口的64%,汉族及其他民族为36%。(2) WXG社区。总户数2405 户,总人口5963人;其中,回族400多人,占总人口的6.7%,汉族及其他民族为93.3%。(3) BJJ 社区。总户数2012户,总人口4914人;其中,回族944人,占总人口的19.2%,汉族及其他民族占比为80.8%。本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方法,以焦点小组和个别访谈的方式,对街道相关负责人、民族工作干部、社区居委会干部及社区居民进行资料搜集,分析该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所面临的空间困境。
(一) 居住空间质量急需与时俱进
居住空间是表征人的存在的重要载体。通州南大街回族居民的居住空间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恪守“围寺而居”的居住传统。通州清真寺,位于通州南大街回民胡同东口,建于元代延佑年间,是通州区域内回民礼拜和进行宗教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回民群众自发地围绕清真寺而聚居。这里住宅密集,人口集中,“寺坊”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构成回民社区文化共同体生成的基础。第二,鲜明的伊斯兰文化与北京传统四合院交相辉映。和北京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回民居住的四合院在窗户、墙壁等建筑细部上,雕刻有伊斯兰民族特点的文字、装饰和布置,满足了回民居家礼拜的宗教文化需求,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织就了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居住单位的联系纽带。第三,街巷文化空间具有鲜明的意向性。南大街中街与因宗教活动、姓氏、历史人物等相关联而命名的多条胡同一起,构成了南大街的街巷文化空间。流传着历史典故的十八个半截胡同(九条胡同被一条中街截分而成),蜿蜒曲折地分布于南大街这片居住区域,普遍比较狭窄,但如果以清真寺为坐标,胡同则具有较好的通达性,这是穆斯林群体的文化心理需求在空间结构上的呈现,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信仰空间,胡同均显示出了明确的“指向性”。然而,随着岁月的冲蚀,目前南大街回民聚居区现状不容乐观:一是建筑单体设施和质量堪忧。这些老宅子普遍存在着构件老化、破损严重的问题,室内缺少必要的洗浴设施和卫生间,大多数居民需要去公共浴室、公共卫生间解决清洁和如厕需求,生活缺乏便利性;二是院落环境逼仄拥挤。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院落都是多家多户混居,3~10 户居住一院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的甚至住着30多户人家。院落里,各种临建房屋杂乱无章,间隙狭小,人均、户均居住面积极小,居住密度极大。院落没有污水处理系统,私搭乱建的厨房和裸露的电线随处可见,风险院落较多;三是街区市政基础设施普遍老旧和落后。电线杆密集地分布在街巷内,多根电线悬浮在街道上空,有些竟可随手触及。路面和墙面损坏严重,鲜有公共活动空间和体育健身器材,更无公共绿化空间和停车场地,居民迫切需要生活环境质量与时俱进,但社区修复和改造面临较大困难。
(二) 商业空间功能衰败
伊斯兰教是重视商业的宗教,很多回族穆斯林从事经商活动,尤其是饮食行业。历史上,通州回族商业繁荣,是通州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研究,在南大街和十八半截胡同区域,有记录的商号就有150家,其中不乏大顺斋、万通酱园、小楼饭店等,深受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居民的喜爱。自该回民聚居区形成以来,在最重要的主干道上,至少有一条回民商业街。通州南大街的商业街(名为中街) 位于旧城东南隅,南大街东侧,靠近清真寺。街道两旁是大大小小的回民商店、回民食品店、清真饭店、牛羊肉店和其他各种商业服务活动场所。这条商业街不仅是回族居民进行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回族居民进行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是回民心理认同和民族归属的又一公共场所。商业街两边比邻或者连接着多条胡同,住在两边的居民很容易通达商业街和清真寺,这也印证了回民群众“围寺而居”和“因市而生”的居住传统。商业街两端并非“断头路”,而是又延伸出其他街区,这种构成形态也表明回民社区并不是封闭的独立社区,它与周边社区有着重要的关联。目前,这条回民商业街的情况:一是街道空间杂乱拥挤。回民商业街因为兼具经商、休闲和回民通往清真大寺的重要通道的交通功能,呈现为“三多”景象,即商户多、人流多、车辆多,又因人车混行、垃圾处理不及时,致使街道显得又脏又乱;二是建筑的民族文化特色式微。回民有着独特的饮食文化、生活习俗、信仰体系,并通过商铺的建筑结构、色彩、文字等文化符号体现出来。这些特点及其表现形式构成了硬化族群边界和凝聚族群的强大力量。然而,商业街被违规建筑商铺等非正规空间凌乱地侵入,商业文化标志大多数被遮蔽。虽然自2017年5月开始,通州区开展清除南大街违章建筑、整治开墙打洞行动,修缮街道两边商铺和居民住房外墙面,街道治理初见成效,但要恢复和兴盛这条商业街,依然任重道远。
(三) 社会空间结构松散
回族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哲玛尔提”,意为“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意译为“寺坊”[5]。“寺”是社区的核心和标志,是社区的“灵魂”“坊”是社区的整体和构成。作为回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社会组织,“寺坊”制度经历了从唐宋时期对外来者进行管理的“蕃坊”制,至元代中后期回回进行本土化过程中“哈的司”制,再到明代时期标志着回族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定型的发展过程。“寺坊”制兼具宗教组织和民间组织双重属性,是一个以教长管理数十户或数百户居民的独立组织机构。回族拥有“五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分别是“围寺而居”的地缘结构、经堂教育结构、教内婚姻结构、经济—行业结构、“寺坊”自我管理结构,其中“围寺而居”的地缘结构是回族社区的基础性结构,它使大而分散的回族在长期发展中将民族文化一脉相传、生生不息[6]。但是,调研显示,通州南大街回民聚居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因为物理空间的衰败而呈现松散态势。这也证实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相辅相成、一体两面。如今,一些回民住户搬离了社区,便捷的交通、相对繁华的商业环境和廉价的租金,使得这里成为许多外来人口的落脚地,回汉混居稀释了该民族聚居区的文化特色。另外,随着城市生活流动性的增加,一些年轻回民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改善居住质量而搬离了聚居区,老年回民成为社区的主要群体构成,社区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弱化了回民“围寺而居”基础结构,模糊了回民聚居区邻里生活的轮廓,对回族文化特色的传承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再造
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再造,不是整体性推倒重建,而是在尊重和保留原有城市肌理基础上,借鉴日常生活批判、场所精神营建、城市意象理论的有益启示,对回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有机更新,留住传统、留住文化、留住精神,在优化提升物理空间的同时,实现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繁荣昌盛,让回民群众在聚居区里有生活上的舒适感、情感上的归属感、文化上的获得感。
(一) 基于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再造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美好生活,人们留在城市,也是为了美好生活。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正在经历一个由生产逻辑向生活逻辑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通过城市空间找到自己的实现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系统阐发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认为城市的总体革命归结为日常生活革命,也就是要解决好人们“鼻子尖下面的问题”。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人必须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否则他就不能存在。他通过一系列描述界定日常生活,如生计、衣服、亲人、邻居、环境等等具有物质文化性质的东西,批判了排除日常生活的空间观念,强调关注空间中人的因素,并集聚日常生活的力量。列斐伏尔认为,这种日常生活包括生计、服装、家具、家人、邻里、环境等物质要素,并充满着价值、礼仪、习俗、传说等文化观念,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有机结合。按此理论,日常生活是城市空间的真实内容,是城市空间有机更新的活性酶。在人类日益遭遇现代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抽调或者背离日常生活,就会面临“人城分离”“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空间异化风险。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视角,思考通州回民聚居区历史文化空间再造,其策略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物质生活层面上,以政府为主导、以居民为主体,改善聚居区内居民的住房等条件,改变设施老旧、房屋破败等现状,解决洗浴等日常生活问题,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推动街巷物质空间能够承载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提高回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质量。第二,在精神生活层面上,尊重回民群众的精神信仰,维持原有的街巷空间格局,对历史上形成的街区布局进行“渐变”式有机空间环境改善,满足回民社区“向心-中分-贯穿”的拓扑关系[7]:向心——所有的路线指向清真寺;中分——以商业街为社区交往中心的作用;贯穿——中心商业街的延伸性,以清晰完整的街巷“空间记忆”承载“文化乡愁”,提高回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品质。第三,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尊重并保留社区居民已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保留原有的生活形态和空间布局,维系回族的“寺坊”结构和“四合院”院落的居住形式,完善回民群众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空间形态。
(二) 基于场所精神的协调性再造
挪威建筑学家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从建筑现象学角度阐释了场所精神。他认为,人要获得存在的立足点,必须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应该知道自己身置何处,以便在环境中认同自己。场所不仅具有一定的特性,而且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具有一定意义。舒尔茨通过场所精神的概念,深入揭示了实体空间的形式所负载的地方特性的意义,揭示了人的生活方式与所处环境的紧密关系。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突出了高楼大厦,忽略了场所精神,城市空间的和谐性遭遇干扰和破坏,城市空间的节点、路径和区域模糊了认同性,城市地标失去了社会文化意义,空间整体感缺失。以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借鉴,在推动南大街回族聚居区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时,其主要的策略选择是强调协调性。一是要保持街区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从建筑单体到“寺坊”“四合院”,再到整个历史街区,要做到建筑风格一致,建筑逻辑自洽;二是街区风貌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尤其要解决区域物质空间衰败、基础设施老旧、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消弭与周边建筑群、社区之间的反差,织补被岁月侵蚀的城市肌理。
(三) 基于城市意象的特色性再造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用城市意象理论解读城市空间,在城市的众多角色中,城市意象是人们可见、可忆、可喜的源泉,它由路径、边沿、区域、结点、地标五种要素构成。路径作为沟通城市的渠道,由大街、步行道、公路、天路、运河等组成;边沿是排除在道路之外的线性要素,意指两个面的界限,连续中的线状突变;区域主要指的是城市里中等或较大的部分,具有两维特性,常常使人产生进入“内部”的感受;结点是指城市空间中的一些要点,以集中为特征,主要指道路的交叉口、方向的变换处;地标是指城市的标志性区域或地点,比如建筑物、招牌、店牌、山丘等[8]。人们通过城市意象“五要素”来认识城市空间,即:通过路径形态完成位移过程;通过边界形态完成自我和他者的区分;通过区域形态产生进入“内部”的体验;通过节点形态获得“进入”和“离开”的感觉;通过标志物完成对空间的独特印象。回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居住格局、建筑样式、信仰体系、文化观念、生活场景,这些因素构成了回民聚居综合体和文化综合体的各种变量关系,是维系该民族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依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通州南大街回民聚居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的保留因素。要对路径、边沿、区域、结点、地标等进行有机更新,彰显建筑单体、空间聚落的民族风格、民族风貌、民族风情,增强城市文化多样的功效。
少数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是少数民族信仰体系、文化样式、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历史见证,是彰显城市人文品质、城市气象、文明要素的空间载体。像对待“老人”一样,安顿好少数民族聚居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建设主体必须完成的任务。
——以《植物妈妈有办法》一课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