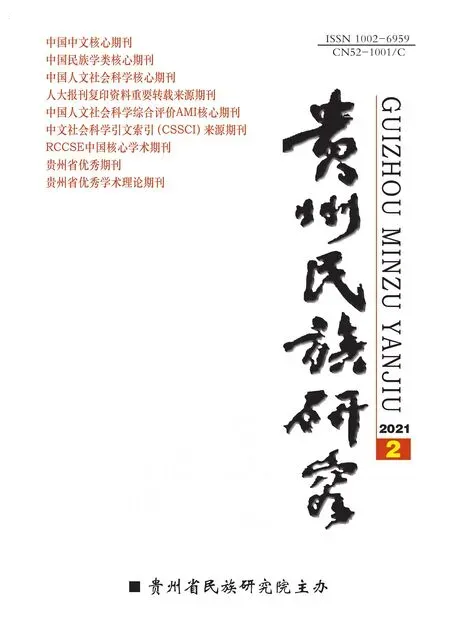府卫分制:明代行政设置中的一种特殊“插花地”
——以明代贵州为研究个案
谢景连
(凯里学院 民族研究院,贵州·凯里 556011)
明朝开国初年,地方机构设置仍依元旧制,设立行中书省或中书分省,但行中书省的长官称参知政事和平章政事,在所管辖区内具有“无所不统”的大权。这与朱元璋所要建立的高度集中权力于中央的国家体制相互矛盾。因此,需要改革这一地方行政设置。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宣布改革行省领导体制,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相互牵制,互不统属,旨在相互制衡,犬牙相制。然而,洪武年间,贵州并非独立的行省,但朱元璋为了巩固贵州地方的稳定,确保其作为云南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在贵州境内遍设卫所,旨在从军事上控制贵州地方。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正式建成为独立的行省,但境内的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偏桥卫以及五开卫仍属湖广都司统辖,永宁、乌撒、赤水等卫又寄四川永宁宣抚、乌撒军民府境内,从而出现了府和卫并非同属贵州行省统辖的现象,笔者称其为“府卫分制”现象。
府卫分制现象在明代的行政设置中较为普遍,文中仅以明代贵州为例,讨论明代贵州府卫分制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以“插花地”视角来展开分析,揭示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明确其实质。
一、通滇驿道贯通、拓修与贵州建省:府卫分制的出现
总体而言,明代从湖广经贵州通滇驿道的贯通、拓修和府卫分制的出现,是明廷经营西南战略的产物。自忽必烈偷袭云南获得成功后,包括元朝在内的其后各王朝,开始清醒并意识到,一旦云南失守,中原地区就会处于游牧民族的弧形包围圈之内[1]。从而可知,云南对于各王朝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确保中原地区的稳定,先需稳定云南,已成为明代及其后统治者的共识。
朱元璋平定中原之际,云南仍然处于元朝所封梁王的统治之下。梁王自恃地险路遥,不肯投降,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2]。为了避免蒙古汗国包围南宋的故事在明代重演,朱元璋决定用武力平定云南。但要平定云南,需要找到通往云南的最佳通道。历史上,虽从巴蜀经青藏高原东沿进入云南是一条现成的通道,但此通道容易被游牧民族所截获。因此,从中原抵达云南,最理想的路线是从湖广出发,穿贵州全境,直达云南,这样可以有效规避游牧民族的扰乱。加之当时已经有一条从湖广沅江中游出发,穿越贵州腹地,抵达云南的间道存在,只需扩展这条间道,处理好贵州境内各大土司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既可成为通滇国防大动脉。经过慎重考虑,明廷决定贯通与拓展此通道。
因资料阙如,我们无从知晓明洪武年间到底新修或拓修了哪些具体的驿道。但根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 《明实录》 《寰宇通衢》等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明洪武年间,贵州东线的驿站有:贵州驿、龙里驿、新添驿、平越驿、清平驿、偏桥驿、镇远水马驿、清浪驿、平溪驿九个驿站。再结合万历年间郭子章《黔记》的记载“自常德府至本省会城,计二十五程,共一千五百一十里。常德府:府河驿、桃源驿、郑家驿、新店驿、界亭驿、马底驿;辰州府:辰阳驿、船溪驿、辰溪驿、山塘驿、怀化驿、盈口驿、罗旧驿;沅州:沅水驿、便水驿、晃州驿”[3]。湖广段共计16驿站,贵州9个驿站,刚好对应郭子章“记二十五程”的记载。这些驿道,我们无从知晓是否都是在平定云南以前就已经开通,但从湖广辰、沅至普安的道路已经打通,为洪武十四年(1381年) 明朝大军进军云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善后经营云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贵州驿道的布局更加完善,乾隆年间,鄂尔泰等人修纂的《贵州通志》中对当时“通滇驿道”贵州东段有了更详细的记载:“自省城下至玉屏县、共十二驿”。分别是“皇华驿、龙里驿、新添驿、酉阳驿、杨老驿、清平驿、重安江驿、兴隆驿、偏桥驿、镇远驿、清溪驿、玉屏驿,共490里。”[4]
为了平定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 九月,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傅友德等既受命。朱元璋颁发诏谕,曰:“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阨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5](P20)是年十二月,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等师至曲靖,击败梁王将达里麻兵于白右江[5](P22),平定云南。但作为云南大后方的贵州不能巩固的话,大军一退,云南又成“孤悬”。朱元璋在《平滇诏书》中就明确指出了“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6]。为了加强对贵州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 正月,朱元璋设置了贵州都指挥使司,治贵州宣慰司,以顾成为使,其民职有司仍属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使司[7](卷八)。朱元璋设置都指挥使司的目的旨在利用军事对贵州加以管制,确保征滇大军后继有援和驿道的畅通。
遍设卫所,也是明廷控制贵州地方的具体举措。从洪武四年(1371年) 置贵州卫、永宁卫开始,朱元璋沿着湖广通云南驿道沿线,从东到西,设置了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偏桥卫、兴隆卫、清平卫、新添卫、龙里卫、贵州卫、贵州前卫、镇西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等16卫。其中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偏桥卫(还包括不在通滇驿道上的五开卫、铜鼓卫) 等卫隶属湖广都司。为了强化对驿道两侧纵深的控制,以及对势力强大土司的监控,明廷还陆续设置了都匀(隶属四川都司)、毕节、赤水等卫所[1](P4)。
洪武年间,贵州虽置有都指挥使司,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则缺少相应的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因此贵州还不能算是单一的行省机构。明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两大土司内讧,相互仇杀,明成祖朱棣见状,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 派兵讨平,废思州、思南宣慰使,始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贵州宣慰使司及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乌罗、新化八府,为贵州建省扫清了主要障碍,于是,贵州才得以建成独立的行省。
朱元璋在贵州设立卫所时,因贵州尚未建成独立的行省,故而,朱元璋把湘黔驿道贵州东部的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偏桥卫以及五开卫等卫交由湖广都司统辖。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后,或因遵循明太祖朱元璋“犬牙相制”祖制,或因贵州地瘠民贫,无法满足卫所所需军饷等因,永乐皇帝并未改变府卫分制现状。由此可见,府卫分制现象的出现,其实是随着明廷战略重心的转移,基于国家话语体系下而形成的,是国家政治力量介入后的直接产物。
二、府卫分制:一种特殊的“插花地”
查阅相关文献得知,“插花地”一词晚至清道光年间才始见于文献典籍中。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十一月,时任贵州省安顺府知府的胡林翼上奏“办理插花地建言书”中首次使用“插花地”一词,并将插花地归纳为三类:“华离之地”“瓯脱之地”以及“犬牙之地”[7](卷十九)。胡林翼的此种分类,是基于行政疆界的形状而进行的分类。近年来,随着插花地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在原有分类原则的基础上,相关学者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类法,又将插花地分为“传统插花地”与“现代插花地”,其中传统插花地包括民族型插花地、军事型插花地、移民型插花地、经济型插花地、政治型插花地;现代插花地包括民族自治型插花地、工矿区插花地、城市新型插花地、以及20 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因国家的计划安排及“大炼钢铁”“上山下乡”等运动而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插花地[8]。而在明代开辟西南的过程中出现的府卫分制现象,若按照胡林翼的分类,未将其纳入到插花地的范畴来。基于现有插花地的分类体系,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军事型“插花地”。
明代学者王士性载:“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故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9]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同样也有类似的记载:“而湖广都司所辖在贵州境内者,又有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卫及千户所。”“而贵州之永宁、乌撒、赤水等卫又寄四川永宁宣抚、乌撒军民府境内”等方面的记载[10]。明廷之所以将贵州东部的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等卫归由湖广都司管辖,把永宁、乌撒、赤水等卫寄四川永宁宣抚、乌撒军民府管辖等情,一是出于行政管辖中的“犬牙相制”原则所致,二是因设立上述卫所时,贵州尚未建成单一行省,故而就将上述卫交由周边的省管辖;到了永乐十一年(1413年) 贵州建省后,却又因财政困难,无法供给卫所所需的军粮以及行政开支所需经费,故而为之。且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也未改变。
文中之所以将府卫分制称之为一种特殊的插花地,原因在于,从插花地的视角来看,行政疆界需要整齐划一,行政疆界或机构的管辖权需要归属同一行政机构,若行政疆界中存在着“犬牙”“华离”或“瓯脱”等情,或行政疆界中的领域或机构未属于该行政机构管辖的,皆可称之为“插花地”。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后,若按照明代正常的行政机构设置来说,贵州省内的“府”“卫”皆应归贵州管辖,但朝廷处于“犬牙相制”“相互制衡”的目的,却将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等卫划归湖广都司管辖,把永宁、乌撒、赤水等卫寄四川永宁宣抚、乌撒军民府管辖,故而出现了上述卫虽身处贵州辖境中,但贵州却无管辖权,而贵州寄在四川的三卫,四川又无权管辖状况,那么,这种情况,自然就是一种特殊的“插花地”。
三、清理拨正:明代贵州地方官员对待府卫分制的态度
府卫分制现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因政治、军事等原因而出现的产物。产生之初,确实能解决一些政治和军事问题,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弊端日益凸显,因而,贵州地方官员不得不向朝廷奏请,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将其弊端纷纷陈述在其奏书中。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镇远知府周瑛因府、卫地近而分隶两省,不便地方管理,奏请“地方事宜疏”。
为以合府卫以却苗蛮事。
照得本府原系湖广所辖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故地。国初开创西南境土,乃设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边卫以控蛮夷,以通西南道路。永乐十一年,朝廷以宣慰司田琛等构恶,诏削其官,创设贵州布政司,分其地为思州、思南、石阡、铜仁、乌罗、新化、黎平等八府,俱属贵州。平、清、偏、镇等四边卫仍属湖广。正统十四年,本府地方苗贼生发,民兵不能独制。而四边卫以属湖广,非申报各上司不敢擅动。为因阻隔江湖,文书往返动经数月,遂致贼势滋蔓,攻城陷堡,杀戮人民,反劳朝廷遣将调兵,始克平定。后献议者以本府地方冲要,乃于清浪设镇守参将一员,及拨湖广武昌等一十三卫所官前来协守。近来苗贼入境,百姓望救,急在旦夕。主将亦以湖广为碍,不敢轻动,湖广官司或又从中而牵制之,主将未免徘徊顾望矣。臣等闻兵速则可得志,势分难以成功,主此不改,恐祸变之生,不但正统十四年而已也。夫分府、卫以属两省者,是名犬牙相制,互相犄角,指臂相使,互相运用,古人皆已行之。合无从此计议,查照洪武初年事例,将本府三司一县割属湖广,或复照今日事体所宜,将平、清、偏、镇四边卫割属贵州。庶几父子兄弟相为一家,手足腹心相为一体,缓急调度,不致掣肘,地方便益[10](201-202)。
从周瑛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明初设立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边卫的目的是“以控蛮夷,以通西南道路”,但因贵州当时尚未建成单一的行省,加之上述四边卫距离湖广行省近,故而划归湖广行省管辖。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成为独立行省,包括镇远府在内的府尽数划归为贵州管辖,但平溪、清浪、偏桥、镇远等四边卫仍属湖广都司管辖。奏书所述,明廷之所以将府、卫分属两省管辖,旨在“犬牙相制,互相犄角,指臂相使,互相运用”。这一行政格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镇远府境发生苗民叛乱,府内能调动的民兵,因势单力薄而“不能独制”,平、清、偏、镇等四边卫虽兵力雄厚,但“非申报各上司不敢擅动”,从而导致,虽有大军进驻,但无军队调用权。即使要调用的话,也需向各司申报,但“因阻隔江湖,文化往返动经数月”,延误战机,最后致使“贼势滋蔓,攻城陷堡,杀戮人民”。“近来苗贼入境,百姓望救,急在旦夕。主将亦以湖广为碍,不敢轻动,湖广官司或又从中而牵制之,主将未免徘徊顾望矣”。
周瑛的这一描述,将府卫分制的弊端暴露无遗,试图去改变这种格局,因此,奏请“将镇远府三司一县割属湖广”,或“将平、清、偏、镇四边卫割属贵州”。但因周瑛的建议,最终不符合朝廷“犬牙相制”原则,未被朝廷采纳。
隆庆元年(1567年),时任贵州巡抚的杜拯,也察觉到了府卫分制所带来的弊端,因此,会同御史王时举疏请将湖广沅、靖二州及六卫、四川三土司并黔,若能采纳此建议,便能达到“十便”的益处。原文如下:
沅、靖二州,与平、清、偏、镇、铜鼓、五开六卫之去湖广,酉阳、播州、永宁三土司之去四川,俱二千余里,遥属于二省,而兼制于贵州。服役者兴远道之嗟,莅事者无画一之轨,民情政体,甚不便也。革数州县土司专畀之贵州,其便有十:
齐民赋役自远而移之近,劳费省于旧者数倍,一便。
郡县专心志以听一省之政令,无顾此失彼之虑,二便。
军民力役彼此相济,无偏重之累,三便。
科贡悉隶本省,礼遇资谴有均平之规,四便。
司道政令有所责成,郡县不敢以他属为辞,五便。
府卫互制,悍卒豪民禁不敢逞,六便。
岁征缓急可无失程,盗贼出没易于诘捕,七便。
土酋之桀,各相牵制,不得肆其毒螫,八便。
僻远之区,监司岁至,吏弊民瘼,可以咨询而更置之,九便。
释兼督之虚名,修专属之实政,体统相安,事无阻废,十便。
臣愚以为三司所呈联近属以全经制,其说可行也。
臣等又看得各省会城府县并置,岂徒备官,要以亲民悉下情耳,乃贵州独阙焉。军民之讼牒,徭役之审编,夫马之派拨,盗贼之追捕,藩臬不能悉理,往皆委之三司首领与两卫指挥及宣慰司。夫三司首领类皆异途,操持靡定,政体未谙,指挥则尤甚矣。委牒方承,即怀私计,防缉未效,反贻厉阶。宣慰则尤矣。逞其恣睢,日事赎罚,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往往如是。是故土民争欲增建府治,而该司议程番府附省会,其说可行也[10](P301-302)。
奏疏将贵州东部府卫分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即楚属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镇远卫、铜鼓卫、五开六卫插入贵州,酉阳、播州、永宁三土司属四川管辖此等插花地的弊端。杜拯认为,若能“改隶贵州”,便能取得上述“十便”,并进而指出,“十便”想法的产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皆硕画也”。但由于杜拯当年将要离任,加之其建议还是不符合“府卫分制、犬牙相制”的原则,此疏依然未获施行。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直隶巡按御史萧重望条陈安黔五策,其中“拓疆圉”一策中指出,“黔省蕞尔单弱可虑,拟待事定,割楚之偏、镇、平、清以专黔辖,又割蜀之永宁、乌镇以拓黔壤,但版图久定,恐有窒碍,应通行三省总督详加商榷。”[5](P970)兵部复议:“列土分疆,版图久定,不加会议,犹恐楚、蜀别有窒碍。应通行三省总督、抚、按衙门详加商榷,要见所议割地之事,如果安便可行,即酌定改正,不得私意执拗。倘有未便,亦明白声言,具奏定夺。前件,臣等查得黔省本蕞尔之区,而平、清、偏、镇四卫又属于楚,永、播、乌、镇土司又属于蜀,似应割属黔中以便控制。但今地方多故,一改革间,彼此相互推诿,恐致误事。俟宁谧之日,通行三省另议。”[10](P408)从兵部的复议中,可知,因“地方多故”“恐致误事”等因,这次割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镇远卫属黔的事情又被搁浅了下来。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12月,湖广、川、贵三省总督李化龙在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后,向朝廷上奏《播州善后事宜十二事》,寻又上奏《黔省善后事宜八事》。其中在《黔省善后事宜八事》奏疏中的“一事”就是建议将黎平府、永从县改隶湖广,镇远、偏桥、平溪、清浪四卫改隶贵州。其原文如下:
楚、黔接壤、抚属错综,如黎平府永从县,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遥,反属于黔;平、清、偏、镇四卫,近黔之镇远,去楚二千余里而遥,反属于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诿。顷者,酋犯偏桥而楚不能救。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救。即黔有播患,而黎平、永从无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救助也,鞭之长不及马腹,势也。合无以黎平一府,永从一县改隶湖广,镇远、偏桥、平溪、清浪四卫改隶贵州。文武官军俸粮,岁费公用,悉仍其旧。则军民合为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谁能诿之[10](P519-520)?
李化龙《黔省善后事宜疏》中所涉及的八款都是事关播州平定后,贵州如何善后的问题,且该疏是与贵州巡抚郭子章商议后的决定,都认为“俱在可行”。疏中也将贵州辖境的“镇远、偏桥、平溪、清浪四卫”属于湖广管辖的弊端再次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酋犯偏桥而楚不能救”“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救”。且该弊端也是路人皆知的事了,但稽之旧制,或许是出于战略方面的整体考量,也未能施行。
纵观上述奏疏,府卫分制这种特殊插花地的弊端,下至地方官员,上至朝廷大员、甚至皇帝本人,都知道其弊端,尤其对地方管理甚是不利。但明廷或许稽于“犬牙相制”的旧制,或出于整体战略的考虑,一直未能有效解决贵州府卫分制的情况,直至明亡。最终,这一情形直到清代“裁卫所归并府县”时,才得以有效解决。其中,镇远卫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归并镇远县;偏桥卫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归并施秉县;五开卫于雍正三年(1725年) 归并黎平府;平溪卫、清浪卫于雍正四年(1726年) 归并思州府;永宁、乌撒、赤水三卫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分别归并永宁县、威宁县、毕节县。至此,明代贵州境内的府卫分制现象才彻底得到解决。
此外,除府卫分制这种“插花地”的弊端被明代贵州官员指出外,对明代贵州行政疆界其他类型的插花地也被当时的贵州官员纷纷指出。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巡按贵州御史萧端蒙以“贵州地方与湖广、四川、云南、广西诸省疆土参错,奸宄迭生,边圉之患,无岁无之”[10](P298)的缘由,奏请“请特建总督重臣疏”,疏中虽主在请设“湖川贵总督”,但却将行政疆界中的“插花地”的七弊一并托出,望朝廷能予以清理拨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巡抚贵州都御史郭子章在请终养之际,奏上《临代条陈地方要务疏》,其中将重安司插花一事的弊端描述得清清楚楚,“重安距黄平远,犹马之腹,即长鞭有所不及。属之清平,其近也,只犹舌之唇,唇之厚薄燥湿,舌一舐便知之。”[10](P589)
四、结语
“插花地”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古代有之,现今亦然;不仅中国有之,国外亦有。虽然“插花地”的名字迟至清光绪年间才正式出现,但据谭其骧先生考证,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存在了“插花地”现象。“插花地”现象类型多样、成因复杂,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插花地”现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立足于国家行政疆界区划的设置或调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国家行政是插花地得以出现的主导因素,但也并非唯一因素,文化生态、地方建构以及人的能动因素等皆是插花地形成的影响因素。对插花地的社会影响和利弊得失评价也是各抒己见,大部分研究认为“插花地”的弊大于利,但也有学者认为,立足于现实需求,“插花地”也有相当的益处。
文中探讨的明代贵州出现的府卫分制现象,确实是伴随着明廷经营西南的战略所致。从政治层面看,若未有明廷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与拓展,以及明代三司分制的政治制度,就不会有府卫分制现象的产生。因此,国家权力是插花地得以产生的主导性因素,可以说,“插花地”是伴随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或调整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若没有国家行政设置或调整,就不会有“插花地”的产生。对于“插花地”的评价,也是考察“插花地”时必然要关注的问题。从上文地方官员的奏疏来看,府卫分制这类插花地确实是有百弊而无一益处,但若从朝廷的整体战略角度来看,府卫分制却可以“犬牙交错”相互制衡,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我们在审视插花地问题的时候,需要从多维度的视角,给予符合其内涵和本质的解释,才能明了其内在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