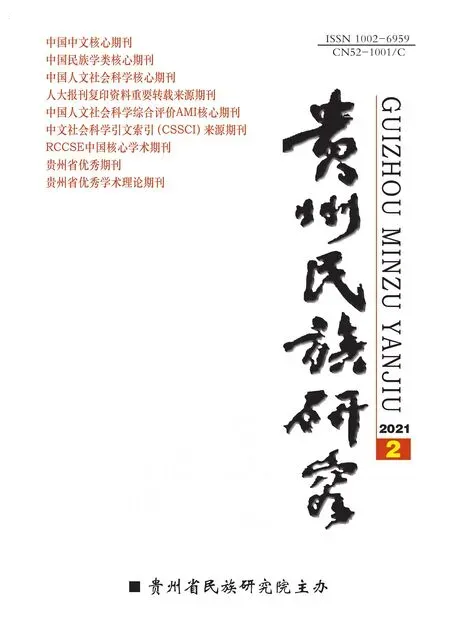费孝通对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的贡献及当代意义
蒙祥忠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中国百年民族研究大概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40年代,以学习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主;第二阶段为50—60年代,主要开展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阶段为1978年至2008年,主要关注民族社会发展、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等问题[1]。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学术历程也大致经历以上三个阶段。其中,20世纪50—60年代,他在贵州参与的各项民族工作,包括参加中央访问团、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对他影响最深[2],该时期应是他对民族理论探索的重要时期。他曾表示,20世纪50年代是他进行民族研究真正的开始[3]。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又多次访问贵州,探讨新时期民族社会发展的相关课题。费孝通的贵州民族研究工作,既是他民族理论建构的主要源泉,也是形成中国民族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对新时代民族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致力于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而开展了各项民族交流活动。党中央从1950 年至1952年陆续派出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费孝通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的实地访问工作,他在访问期间既出色地完了政治任务,也对民族地区进行了考察,探索了诸多民族研究工作理论与方法。
(一)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到千家万户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央访问团出访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并亲笔题词且制成锦旗,交由访问团送到各民族同胞手里,并要求访问团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一举一动要表现出民族平等,要与少数民族以心换心[4]。这是要求他们严格按照群众路线之工作方针开展访问。
访问团在贵州期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集中于黔中;第二阶段赴黔东、黔南和黔西。访问团每到一地并非简单机械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而是按照群众路线的工作原则与少数民族群众深度交心、交友、交情。他们了解群众疾苦并送去各种物品。费孝通回忆说:“我们看到了不少观众衣不蔽体,当场便分送布匹、衣裤,双方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相抱不放。这时真正体会到了‘以心换心’的真情实意”[4]。访问团每离开一地,均出现与群众难分难舍的感人情景。
为答谢中央访问团,很多群众也馈赠锦旗。如凯里苗族赠送的旗面内容为“中央访问团第三分团,您是民族情感的体会者,您是民族团结的教导者,朝着您指挥着的鲜明旗帜,我们快马加鞭”。当时全国各访问团受赠的锦旗就有几百面,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现珍藏有628面。这些锦旗是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深情讴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和谐”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奠立过程的历史见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财富。
访问团在贵州长达六个半月的时间里,通过与群众以心换心的交往以及把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到和落实到千家万户后,少数民族表现出了心向亲爱的祖国,体会到了作为祖国大家庭一分子的归属感。访问团也深切感到了用真情实意牢牢结在一起的民族大家庭,千秋万代都不会分离。
(二) 参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其内部矛盾仍给政权建设带来一定难度,而民族地区政权建设是各族人民平等当家做主的基本保障,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所强调的人民性和平等性的必然要求。
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内部矛盾须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这要求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为此,费孝通指导工作队伍调查了各民族土地占有和社会经济状况,形成了《苗汉经济关系的历史》 《苗族的阶级关系》 《苗族租佃关系》 《仲家(布依族) 的阶级情况及租佃关系》 《彝族土司的租佃形式》等调研报告,为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决策提供了依据[5]。在此基础上,访问团于1952年7月起草了《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问题的初步意见》[6],其主要精神是承认民族区别,不能采取一般化地进行相同的社会改革。
建立民族自治区域是少数民族真正成为新社会主人的标志。贵州在访问团的帮助下于1951年建立了凯里苗族自治区,其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选举了一名苗族干部担任县长,25人当选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委员中有11名为少数民族[7]。1956年,贵州胜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保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共同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三)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贵州在1950年就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700多人,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成立奠定了人才基础。但在成立民族区域自治之时,各民族干部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如有少数人对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能力信心不足。费孝通认为,这种认识的根源来自于大民族主义思想。民族平等是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问题,建立自治区域让少数民族参加政权是一种权利问题而非能力问题。少数民族干部表现出来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够高,那是因为他们历经长期的缺乏参加政权经验所致[6]。
在访问团帮助下,贵州从1951年初开始举行较大规模的民族干部培训班。第一批学员有138人,且选送各民族知识青年和积极分子到北京、成都等地学习。到1956年底,少数民族干部已有15496 人,占全省干部的14.05%,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干部有2642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有336人[5]。
访问团在贵州期间举办了三期培训,向学员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讲解人民与政府、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如何开展照顾少数民族工作和实施区域自治等问题[8]。费孝通强调,培养干部应包括使用和提高干部思想能力的问题,要体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互动,杜绝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6]。
二、致力于民族识别工作研究
民族平等是新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但要制定和实施民族平等政策首先是要弄清楚中国到底有哪些民族、有多少民族[11]。因此,摸清少数民族的族别情况是访问团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陆续派出识别调查小组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费孝通再次被派到贵州指导工作。
(一) 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工作原则
访问团在贵州期间初步了解和调查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有30多种,另有自报的约82种[5]。这些民族或人们共同体中,有的深受其他民族影响、有的只保留某些方面、有的正处在不断融合之过程等。这归因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历史上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少数民族要求政府承认其民族成分,这是民族自觉的表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12]。
费孝通调查了贵州各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和语言等。他认为,“弄清楚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不仅是民族工作深入一步所必需,而且已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要求。”[6]访问结束后,他完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 《兄弟民族在贵州》等论著。在识别工作中,他又带领调查组对自报的民族称谓群体进行了4 个多月的调查,形成了《贵州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 《毕节专区“蔡家”初步调查报告》等,为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费孝通等一批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情况下,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组织了8个调查组分赴各地,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性质、阶级结构及其发展特点作实地调查[13]。由吴泽霖任组长的贵州、湖南为一个组,称“贵州、湖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后因编写少数民族简史而改称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工作持续至1963 年。
1978 年,费孝通又提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的建议》,倡导以川、滇、黔三省为中心的西南民族历史、考古、语言、社会综合调查计划,并对其民族识别工作复查一遍[14]。20世纪80年代后,民族研究工作者又深入民族地区对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调查,贵州“六山六水”民族大调查也在这一背景下展开。从20世纪50 到80年代,贵州各时期民族调查资料共900多万字,不仅为民族识别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编写少数民族简史积累了基础资料。
(二) 遵循科学与主体自觉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民族识别是非同一般的民族工作。费孝通强调,一要遵循主体自觉的工作原则;二要按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指导工作。遵循主体自觉就是要在民族平等政策的基础上尊重民族的意愿,即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不能用命令主义和包办代替的方法给自报名称的民族单位确定为哪一种民族身份[15]。但是,费孝通同时提出了要尊重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即是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次的不断融合的特点。有的在形成的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而产生强烈的民族情感,其民族特征较显著,那么应鼓励他们申报为一个民族单位;有的在形成的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而主动融合到其他民族。那些人数很少、地区很小,且与其他民族在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等存在相近的,应鼓励他们与其他民族“融合为一体”。这是基于民族发展的物质基础的考虑,因为一个人数较少的群体,即使形成一个单一民族,也不利于经济发展,也难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与其他民族合为一体,利大于弊[15]。
然而,这些人数较少的群体往往缺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民族识别工作者要为他们做好历史与社会调查,给予提供分析材料,让其明白自己的历史,从而客观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民族身份。在群众工作和科学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使各民族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实现有序的融合。这一任务就是促成“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合为一体”的认同调控工作。
认同调控的重要环节是协调合并双方的感情和利益。为此,费孝通于1983年7月又一次赴贵州指导。他在给民族干部作的讲座中强调,就民族社会发展而言,并非民族数量越多越好,而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民族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确认。从50—80 年代,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已经历了一段不长不短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要求认定为单一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但80年代后,民族工作的方向是消除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现提出重新认定民族身份的,就要结合本民族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考虑[16]。
1985 年,贵州又对23种民族成分90多万人进行识别。到1996年,贵州对其开展的认同调控工作基本结束。被认定的民族大多召开了庆祝大会。如8 万多的喇叭人被认定为苗族后召开“喇叭人恢复民族成份庆祝大会”,有近4000人参加。毗邻的村寨还派出文艺队、芦笙队、唢呐队、腰鼓队参加,充满民族团结的气氛[17]。
(三)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原则
费孝通强调要学习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但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实事求是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如不能只从语言来认定穿青人和家人。居住在黔西北的穿青人为外来移民,他们过去曾有一部分人操“老辈子话”。但这一语言实为一种汉语方言,且与江西、湖北和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而非在贵州习得。根据语言来识别穿青人将面临较大困难。语言分析只能提供穿青人来历的线索[12]。
三、致力于民族社会发展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西部大开发、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以及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问题均为费孝通所关心之大事。他一系列有关民族社会发展的学术理念的支撑资料也离不开对贵州的调查研究。
(一) 消除贫富差距与民族社会发展
1983 年7月6日至13日,费孝通在贵州调研期间多次召集民族干部开座谈会并为此举行了学术报告,从民族识别工作中探讨民族发展问题。其中,《费孝通教授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报告》[16]和《费孝通教授在省民族识别审议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19]反映了他在民族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些观点。费孝通强调,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民族并非固定不变。弄清一个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而回到历史中的民族。尤其要关注当下民族的变化过程,这是民族社会发展本身所需要。中国使用“民族”两字蕴含着丰富内容。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民族,其意义在于他属于哪一个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18]。他强调从“民族”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点来看其涵义,目的是要将民族放入到整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中来考察。
而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正处在与汉族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个阶段。费孝通认为,从各民族形成的不同阶段来看,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助尤为关键。尤其是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都互相离不开。但要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最重要的是依靠智力。各民族发展的起点不同,后发的民族要通过技术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16]。经济落后的地区,其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知识、科技送到群众生活中,而知识分子要挑起该重任。这正是他所号召的以智力、劳力、财力“三力支边”的具体内容。推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还须考虑到地域民族关系问题。费孝通认为,贵州民族关系尤为复杂,汉族和少数民族呈现出互为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这决定了汉族的经济发展必然影响着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因此,分析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必须将其放进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去考察[19]。
(二) 资源开发与民族社会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是费孝通关注的另一课题。1995年8月,费孝通再次考察贵州,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且生态脆弱的毕节地区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并撰写了《毕节行》一文[20]。
费孝通注意到毕节地区水能资源、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等虽然丰富,但当地民族的经济却很落后。他归纳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生态条件差;二是社会发育程度迟缓;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最突出的是交通。致使毕节地区丰富的资源仍属于未开发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要克服这些困难,最急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且交通问题要放在首位。解决交通问题之后,资源因此被开发而变成财富,当地民族就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进入良性循环[20]。他在此已阐述了对少数民族的帮扶需要从“输血”转为“造血”模式的重要性。
费孝通之所以强调民族地区交通网络建设的重要性与其提倡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关。他在总结农村发展分三步走中,第一步是农业发展,因农业发展需得到副业的配合和工业的发展而促进了第二步的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又促进第三步的小城镇建设,因发展小城镇离不开城市和农村的配合而出现了区域发展问题,而发展区域经济最关键的是交通网络的建设[10]。
西部的现代化过程必须包含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一个历史过程。该过程也包含各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21]。社会发展滞后的西部民族地区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将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注重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平衡的问题。
(三) “人文资源论”与民族社会发展
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是费孝通晚年所关注的又一课题。在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之时,他呼吁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做好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资源也是让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2]。这是他关于经济发展后如何开展文化建设的“人文资源论”。
费孝通肯定了我国很多文化艺术都曾在西部地区得到蓬勃发展[23]。该判断来自于他长期在民族地区的调查,尤其是在贵州访问期间,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表现出来的丰富文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发展少数民族文艺,能够使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和结实[24]。
费孝通在思考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其著名的“文化自觉”等理论。他在《民族生存与发展》一文中阐述了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观点,尤其提到了保“文化”还是保“人”的重要命题。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各民族的文化正遭重大冲击,尤其是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而文化是为了人才存在的,有人了才有文化,文化是谋生之道,做人之道[25]。他表达了在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中优先保“人”的重要性,其民族文化资源论蕴含着“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的重大学术思考[26],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费孝通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的当代意义
费孝通对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的贡献,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心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民族交流活动的最鲜明特点是,以最大的诚意与少数民族深度交心、交友、交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共同体”是在各民族通过经济上的互惠、文化上的融合,以及政治上的协商后聚合而成的整体[27],而“共同体意识”则为一种归属性心灵需求和期盼性心灵要求活动。因此,各民族成员的心灵必须是相互间可以通约的,才能聚合成为一个共同体[28]。各民族之间的心灵相通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民族工作更需要树立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工作的理念。2020 年6月,习近平在银川考察调研期间强调,“做好民族团结需要我们用心,基层人员要用心、用情、用力”。人心工作既包括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心心相印,也包括领导干部与各民族之间的心心相连。是否善于同各族群众交心已成为了衡量新时代民族工作干部是否合格的标准;各族群众是否心心相印也成为了一个地区民族关系是否和谐的指标。这些标准和指标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
(二) “合之又合”的民族关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56个民族的确认,离不开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中华民族”的大讨论,也离不开20世纪40 年代以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探索与实施,更是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大调查。“民族”的概念在这过程中逐渐被磨合而形成。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中华民族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不断交融的多种情状[29]。这些情状正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特点。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有的民族根据提供的史料而选择了自己的族称,有的则是在认同调控工作中选择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尤其是在认同调控工作中,很多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实现了有序的融合。其过程充满了变通和协商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具有民族协商的传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在交往交流中,通过不断地协商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各个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实为一种“合之又合”的动态关系[30]。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的“合之又合”的特点,则体现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同化是一种自然现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也是为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走向“合之又合”的动态关系。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 世纪80年代之后,费孝通对贵州民族发展的关注和研究,充分表明了消除民族不平等的关键在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尤其是更加需要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
民族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事实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平等是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然而,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各民族都有其优长特点,这些特点的汇聚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性和发展能力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31]。然而,现阶段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距的最大法宝,仍然是坚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更是需要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给予他们更多的扶持。例如,毛南族、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就是得益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