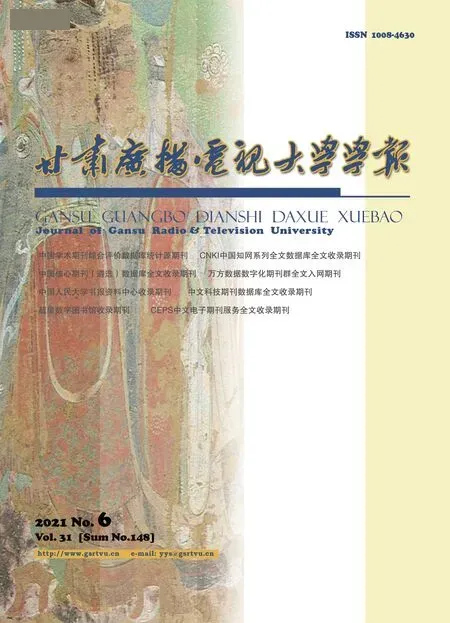从口头到文本:英雄史诗《江格尔》传播的跨媒介流变与互动探析
王晓红,施莉婷
(兰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史诗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欧洲,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到史诗的人。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指出:“史诗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说话。只是由于习惯的沿革,人们才开始将这个词与诗体写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联系起来。”[1]在我国“史诗”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期,章太炎在《新民丛报》刊登的《文学说例》一文中说:“韵文完具而后有散文,史诗功善而后有戏曲。”[2]学者刘守华等认为:“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一种专门描述民族起源、民族迁徙、民族战争、民族英雄的不朽业绩等传说或者重大历史事件的或者规模宏大的长篇民间叙事诗”[3]170。英雄史诗是歌颂人类童年时期民族英雄的传奇武功与光辉业绩的长篇叙事诗,主要描写古代民族形成过程中,氏族、部落、或者民族之间的战争,主人公都是历史转折时期的民族英雄、部落领袖和原始社会的君王,以及由他们转化而来的新兴奴隶主或封建领主[3]171。
《江格尔》的产生和形成过程类似于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它们最初大多是较为零散的口头传说和诗篇,数百年来经过民间艺人的润色和创作,才逐步形成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作为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典型代表,它所塑造的形象都是团结奋斗、肝胆相照、英勇善战、热爱自由的英雄,这是草原游牧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品格,而这种品格又内化为一种文化沉淀在他们的民族精神中。数百年来,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创作与发展凝结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崇拜和生活理想,也承载着他们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
现在流传下来的《江格尔》是由二百多部长诗组成的一部巨型史诗,除一部序诗外,其余各章都可以形成一个单独的故事。《江格尔》流传的地域不同,经过各地的英雄史诗演唱艺人的“加工”,其故事内容略有差异,但主要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统一的,基本围绕主要人物江格尔及他所带领的英雄人物的征战故事展开。
《江格尔》从产生到现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就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从传播媒介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头传播过程与传承的探究。此外,还有少数学者从推动《江格尔》的对外传播角度研究其翻译问题,对其跨媒介传播过程的梳理和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此,本文以《江格尔》传承发展的历史为线索,对其从口头到文本的跨媒介传播进行探究与分析,以期发现蒙古族文化中既满足自身娱乐需要,又能凝聚人心,实现定边安边的文化元素。
一、《江格尔》的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以语言为媒介,是人类文明中较为纵深持久的一种传播方式。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史诗演唱艺人由于生活阅历、天资禀赋的差异以及在不同场合表演方式上的特色使史诗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样态。而那些听《江格尔》的普通民众,对江格尔奇的尊重和对演唱活动的喜爱,不仅保证了《江格尔》的传播,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史诗演唱者的演唱才华和创作灵感。
(一)“一专多能”的传播者——“江格尔奇”
《江格尔》形成以前,卫拉特地区曾有许多史诗演唱艺人,这些艺人被称为“陶兀里奇”。后来随着《江格尔》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一些小型史诗逐渐让位于这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逐渐成为民间史诗的主体,出现了开始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江格尔奇。
从英雄史诗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并不是某个人在特定时期依靠个人的力量创作出来的。《江格尔》是历代江格尔奇在演唱的过程中运用古老的蒙古族神话和传说,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创作并逐步丰富的一部英雄史诗作品。可以说,江格尔奇在这部史诗的传承和传播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一方面他们是这部不朽史诗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不同时代江格尔奇的艺术再创作,赋予了这部英雄史诗新的内容。
成为一个合格的江格尔奇,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传统的师徒传授活动;另一种是家传或是有天赋的人“自学成才”。如新疆地区著名的江格尔奇朱乃最初就是通过家传学习演唱《江格尔》,他的家族中祖孙三代都是江格尔奇。因为《江格尔》篇幅较长,所以也有史诗演唱艺人通过家传然后拜师等途径学会演唱史诗的多部章节。但总的来看,英雄史诗演唱艺人的师徒传授活动是一种较为系统的传授过程,这种途径为《江格尔》的活态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演唱形式来看,江格尔奇演唱史诗的形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口传史诗的程式化模式,即严格遵守史诗中已经固定下来的规范脚本进行演唱;另外一种是在演唱过程中依据自身艺术修养即兴创作,添加一些新的内容。这种幽默机智的创作形成了英雄史诗演唱者各不相同的演唱风格。但不管是哪一种演唱方式,演唱《江格尔》都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江格尔奇们通常要熟练掌握史诗的韵律和曲调,将富于音律节奏的诗歌作为主要的唱词,其中穿插简洁的散体叙述,用不同唱腔来配合不同演唱内容。
《江格尔》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一专多能”的江格尔奇凭借着其多年的训练和艺术修养给史诗传播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一些上了年纪的江格尔奇们会深入村落演唱史诗,这种走村串户的传播会与当地的民俗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史诗的传播效果,扩大史诗的传播范围。
(二)《江格尔》的传播场景:不同文化生活中的展演
口头传播是人类最初的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人类早期信息传播最主要、最普遍的方式。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的社会经验和文化知识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获得。在蒙古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之前,他们主要依靠口头传诵神话故事和传说来表达他们对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把传唱诗歌和谚语的活动当作娱乐。口头传播的便利性为史诗演唱艺人在不同的场合的表演提供了可能。江格尔奇们演唱史诗的场合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或初五,王爷活佛、大喇嘛等比较有权势的社会上层人物在互相拜过年后,就在王爷专门腾出的蒙古包或者建起的专门的蒙古包里,请著名的“江格尔奇”说唱《江格尔》,直到月底[4]50。这种演唱活动一般在汗宫、王府、官吏的住处,在这种较为正式的场合演唱《江格尔》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最大。这时,人们把演唱江格尔看作一种慰藉心灵的情感表达活动。人们认为史诗中的江格尔是佛的化身,具有打败恶魔莽古斯的力量。在正月里演唱《江格尔》就可以驱除一切妖魔鬼怪,保护人们免受灾难的侵袭。这种认知思维源自古代蒙古族人民对自然灾害难以战胜的畏惧。只能借助于演唱《江格尔》这种文化活动来满足驱邪和祈神保佑的精神需求,这是蒙古族人民因地制宜发展出的既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又能凝聚人心的娱乐方式。
另一种非正式的演唱《江格尔》的活动,大量存在于民间,渗透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如牧民在举行婚礼后,会邀请江格尔奇来演唱《江格尔》中的婚姻长诗或念赞祝词,祈求生活的幸福美满。喇嘛念经仪式和比赛活动之后,进行祭祀时,参加祭祀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听江格尔奇演唱史诗,以告慰天地神灵。普通群众在牧场上、夜间看守马群时或在拉骆驼的驼队中,甚至是一些富人的蒙古包里也能听到江格尔的演唱。这时,人们把欣赏《江格尔》的演唱当作是一种排解生活压力和痛苦的方式。通过演唱《江格尔》来鼓励人们寻找生活的美好,激发人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勇气和信心。
此外,也有不少的江格尔奇到汉族和哈萨克人的家中演唱《江格尔》。根据仁钦道尔吉教授的记录,有个叫肖夏的汉族农民甚至为新疆的《江格尔》工作组演唱过史诗《江格尔》中的故事——《乌兰洪古尔与古南哈尔战斗之部》。《江格尔》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演唱活动,扩展了其传播的地域和范围,也使史诗成为不同民族人民沟通与交流的媒介,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彼此了解,和谐相处。
(三)双重身份的听众
热情洋溢的听众在《江格尔》的口头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没有广泛的受众,史诗的传播就难以进行。古代蒙古族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偏远的牧区,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有限。《江格尔》歌颂的是为家乡和平安定而征战的英雄人物,是一部具有爱国情怀的英雄史诗,它继承和保留了蒙古族古老英雄主义文化精神的传统,因此欣赏《江格尔》的演唱可以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以口语为主要传播媒介时期,《江格尔》的主要传播者还是听众[5]4。听众既是受传者也是传播者。这种双重身份不仅与史诗演唱活动大量存在于民间有关,还与受众听演唱的目的有关。受传者(听众)观看史诗演唱活动可能是为了娱乐享受,或者是为了获得文化知识。他们在满足自己精神文化享受后,基于日常社会交往的需要和机会,会将自己听到的故事传播给家人和朋友,形成再次传播。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受传者也加入到史诗的创作和加工之中,成为史诗新的传播者。他们向别人进行传播的过程,也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诗篇进行增减的过程。
听众的双重身份使《江格尔》的传承不会因为某一个史诗演唱艺人江格尔奇的离世而中断。在古代,蒙古族并没有专门培养和训练江格尔奇的传统和机构。大多数学唱《江格尔》的人都是听过著名江格尔奇的口头传播后,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个人天赋,反复的模仿、背诵,他们在大量的试唱后才能够独立的演唱某些章节。总之,江格尔奇、普通艺人、一般牧民,他们对史诗的浓厚兴趣为《江格尔》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江格尔》的文本传播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把人类推向了更高的文明阶段。《江格尔》在口语传播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受众,拥有良好的受众基础。但是随着史诗传播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们不再满足于从口耳相传中了解这部伟大的民族英雄赞歌。人们开始将听到的史诗演唱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复杂多样的文本形态流传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逐渐由单篇集结成册。文本传播的诸多特征也成就了这部古老史诗不朽的文化魅力。
(一)复杂多样的文本类型
文字出现之后,《江格尔》的传播媒介出现了文本。蒙古族生存于广阔的草原,山石,墙壁等物质缺乏,无法以这些固定物质为文本,这也决定了他们文化传播主要依靠流动文本。流动文本一般采用的是较为轻便的纸质媒介。这些文本类型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既有通过记录别人所演唱的史诗内容而形成的转述本,也有依靠记录者在史诗表演现场的耳听手写的记录本,还有各类手抄本。马承五先生认为:首先,传抄表现为一种流动性,它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其次,传抄显示出互递性。它可以通过人们的不断传写,不断扩充传播对象[6]。
不管怎样,文本是对口头传播的记录,而这种记录是靠着人们记忆语言的能力完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记忆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其准确性自然会受到影响。同时,转述、记录的对象不同,文本的内容也就有一定差异。
(二)从单篇到成册的传播形态
从《江格尔》文本传播发生的实际状况来看,史诗的文本最初可能只是几个单篇文本流传,经过一些人集结成册后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史诗的文本最初应该是以较少的章回结成的文本,在王公贵族、江格尔奇、文人以及比较富裕的普通牧民中间传播。在史诗文本积累到一定数量以后,集结成册被收藏或者在各种场所展示,成为经济条件和文化程度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篇幅较小的单本记录者大都是演唱史诗的江格尔奇。他们将自己会演唱的《江格尔》的部分章回以文字记录,用于师徒传授或者赠给故旧。王府有培养专职江格尔奇的传统,所以,具备集结成册条件的一般是王公贵族或者官方机构的文书。
从个别篇章的流传到结集成册,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状况与史诗本身的特征和它所依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江格尔》的篇章庞大丰富,即使是年长的江格尔奇也不能完全演唱史诗《江格尔》的全部章回。他们演唱的大多是史诗的部分章回,记录的并不全面;另一方面,《江格尔》在口头传播中的流变性,使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并没有统一固定的内容和形式。
(三)跨越阶层的传播
文本的出现意味着《江格尔》不再以单一的口头形式进行传播,使转瞬即逝的口头表演变成可以收藏、反复阅读的案头读物,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较多限制。同时,文本便携、易保存的特点,使其可以跨越阶层实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传播。
据记载,曾经做过王爷文书的图门·德琴有着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他精通经书、历史和《江格尔》故事,还将史诗《江格尔》整理成册[4]45。这种现象说明在史诗以文本的形式流传时,江格尔奇、文人们通过整理、传阅与赠送史诗文本,成为《江格尔》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们会组织文人抄录,为了鼓励这种抄录行为,甚至会对传抄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各级官员也会组织文人去记录、整理、抄写《江格尔》。在蒙古族人民心目中,他们把家里拥有《江格尔》的手抄本看作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他们认为,口说《江格尔》虽也是善行,但是对后代无益,用笔记录下来才是长久的善行,将传至后世。几乎每个识文断字的家庭都有两三个章回的《江格尔传》手抄本,很多普通牧民也都保存过《江格尔》的文本。可见,《江格尔》的文本主要是通过官方组织和民间人员经过口传记录、传抄、赠送、收藏等形式在人际间传播。
文本赋予了史诗《江格尔》比较稳定的传播形态,较好的保持了每个史诗演唱者的创作风格和原始面貌。但是文本的制作和传抄容易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以及蒙古族人民“流动不居”的生活方式,使《江格尔》在较长时间段内的传播处于缓慢发展的状况。此外,史诗的接受群体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所以口头传播《江格尔》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方式。文本只能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王府、官吏和文人之间,还有少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普通牧民家中流传,其受众面远不如口头传播广泛。
另外,从文本的接受者参与情况来看,与口传时代相比,阅读者一般不会对文本进行主观化改变,只是“搬运”,不进行再创造。除非他愿意自己动手,参与传抄。
三、从口头到文本:《江格尔》跨媒介传播过程中的变化
从口头传唱到文本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逐渐全方位地记录与呈现不同地域的社会变迁。口头传播延续了《江格尔》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活力,而文本传播则将这种文化推向了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从口头到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各自的特点促使《江格尔》在传播中出现了巨大的流变性。
(一)《江格尔》传播内容的流变性
语言和文字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媒介,其传播内容的内在规定性导致其对某一地域或民族文化传播的差异性。特伦斯·霍克斯认为: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把时间而不是空间作为主要的力量结构,后者使用空间而不是使用时间。听觉符号更倾向于象征,得到充分发挥的听觉符号,在艺术方面产生了口头语言和音乐等重要形式[7]。听觉符号在艺术方面的多样化,使口头传播成为了《江格尔》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口头传播赋予了《江格尔》不竭的生命力,文本则使《江格尔》纷繁复杂的内容得以固定传播。虽然《江格尔》有着固定的叙事结构,但其不同文本中的故事内容、情节及人物名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差异的形成源自《江格尔》早期的口头传播。
根据加·巴图那生的调查报告:19世纪末20世纪初,塔城的西·克甫都统曾邀请著名的史诗演唱艺人布拉尔演唱《江格尔》。布拉尔连着说了几个小时,西·克甫都统问他:“英雄们都征战这么久了,他们不吃饭吗?”布拉尔说了声“他们吃饭时间还没到”,就又开始演唱。过了一会,他即兴创作为史诗增添新情节,他说道:“多多地煮上鹿肉,白面和得堆成山,做好长长的拉面,现在江格尔一伙要进餐。”西·克甫都统大声称赞说:“对呀,勇士们该吃那样多的饭。”[4]45加·巴图那生报告中的这段文字生动的展示了口头传播阶段,艺人根据现场的演出状况而对史诗的内容稍作改编,以此来满足受众的需求。这种史诗口头传播中流变性的产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口头传播因人而异。《江格尔》篇幅较长,江格尔奇们在演唱史诗的过程中,也不能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他们会将口头用语和书面语言混合起来,并在演唱的过程中即兴添加自己熟悉的一些地方习俗和文学材料。这种即兴的创作,往往融入了演唱者自己的感情、经历、知识、对史诗的理解以及个人语言使用风格等;另一方面,口头传播中,面对面的传播形式使演唱者都能够即时接受到听众的反馈并据此对演唱内容和形式作出相应的调整。受众的批评和建议,能够启发史诗演唱者进行创作和修改。可见,史诗的流变性源自口头传播的频密互动和效果渲染中。
在《江格尔》以文本为主要形式的传播阶段,史诗的流变性更容易产生。《江格尔》内容庞大复杂,文本类型多样,以文本形式记录的《江格尔》数量较多。在我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克尔梅克共和国以文本形式出版的《江格尔》有170多种[5]186。在《江格尔》口头传播过程中,这种流变性更多的来自演唱者根据现场传播环境进行的即兴表演。但是随着史诗在文本传播空间的不断拓展,在不同部族或地域及不同的文化场域中,史诗的内容、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如从《江格尔》典型的婚姻故事情节来看,描写洪古尔的婚事主要的有两次,有的版本对此记述的较为详细,有的版本则非常简略。此外,在《江格尔》的文本传播阶段,人们通过记录、整理发现了同一部史诗出现了多种异文。这不仅源于早期《江格尔》口头文化的多元与多变,还与史诗文本中不同的书写传统有关。在史诗以文本形式传播之前,每一个史诗演唱艺人都有关于史诗的独特历史记忆和感悟,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讲唱方式。因此,这种多元的口传文化对文本的差异产生了影响。同时,记录者不同、书写传统上的差异,以及传抄过程中的笔误,都会对史诗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
(二)从口头到文本:史诗传播的互动性
史诗的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在诸多环节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问题。事实上,在《江格尔》从口头到文本的跨媒介传播中,这两种传播方式常常是共存的,彼此互动的。
在《江格尔》进入文本传播阶段后,口头传播也并未式微,它仍然是史诗最传统、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在蒙古族人民的眼中,能称之为“江格尔奇”的史诗演唱艺人,除了有演唱史诗才能外,还能通过文本抄写和背诵史诗来完善自己演唱史诗的技巧和内容。文本在与口头的互动传播中,使史诗的内容变得更加生动、丰富。根据仁钦道尔吉教授的调查,新疆的现代江格尔奇,可以分为口头学唱和背诵手抄本两大类[8]。与冉皮勒、普尔布加普等著名的江格尔奇不同,朱乃是个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他在口头学唱的同时借助《江格尔》的手抄本,从中学会了许多部①。这些优秀的江格尔奇们在进行口头传播的同时,借助文本增加自己演唱史诗的篇幅,提高自己演唱史诗的能力。新疆卫拉特有许多不同版本《江格尔》的手抄本,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江格尔奇,就是通过读手抄本而学会演唱《江格尔》的。这种口头与文本的互动进一步完善了史诗艺术审美。同时,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的互动并不仅限于史诗演唱艺人。从史诗传播的环境来看,对于某些固定的场合,如节庆、婚礼等,蒙古族人民更加喜欢演唱史诗,而文本适合在一些较为单一的环境中被人们传抄和阅读。有时,人们也会出于记录史诗的目的,使史诗的演唱和书写记录同步进行。因此,进入文本传播领域的《江格尔》不仅与书写传统有关,还与口头传播关系密切。它们是在同一种文化空间中的互动传播。这种现象的产生既得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源于这两种传播方式各自的局限性。
另外,当进一步探究《江格尔》的口头传播特征时,我们发现:首先,《江格尔》的口头传播较为自由,并没有统一的固定形式。演唱行为通常伴随着不同史诗演唱艺人对史诗的不同阐释和理解,从而展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其次,由于艺人演唱《江格尔》受时间限制,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在冬夜里,或者是节庆日观看欣赏江格尔奇的演唱,而且通常是中途不能停顿,至少要演唱完一章。这种现场行为对受众的接受是很大的考验。再次,《江格尔》原本就是一部篇幅较长的复杂史诗,口语传播难以保持史诗在传播中的稳定性和长久性,这也会给史诗带来“人亡歌息”的危险。因此,以语言为媒介的口头传播方式虽然能生动的保持这种说唱文学的原始风貌,但容易受到时空限制不利于史诗的系统传播和保存。而文本传播在弥补这些缺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一,文本传播不囿于口头传播的时空限制。但同时需要阅读者有一定的教育基础,起码要识字。这对于蒙古族那些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底层人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们才是《江格尔》传播过程中最广泛的受众。第二,文本记录所依靠的物质媒介具有稳定性,利于史诗长久的系统的传播。但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一般要求接受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其接受成本较高,受众面较为狭隘。因此,《江格尔》手抄本的记录者除了史诗演唱艺人,一般都是文人、贵族还有一些宗教界人士。《江格尔》文本主要还是在蒙古族社会富有的上层知识界和宗教界中传播。第三,文本传播较强的适应能力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恢复“口头记忆”,还能重建人类古朴的意识。从文本传播的形式来看,文本的存储、记录能力减轻了蒙古族人民对史诗这种民族文化的记忆负担。可见,在《江格尔》进入文本传播阶段以后,传承陷入“人亡歌息”困境。
总的来看,《江格尔》从口头传播进入文本传播,两种传播媒介的共存互动,形成较为合理的史诗传播格局。口头与文本的跨媒介互动传播也进一步拓展了《江格尔》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蒙古族人民根据自身生存环境,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一套既满足生活娱乐需要,又能传承文化、凝聚人心,实现定边安边的文化体系。
注释:
①仁钦道尔吉的文章《〈江格尔〉的传承与保护》被收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的《“史诗之光—辉映中国”——中国“三大史诗”传承与保护研讨会论文及论文提要汇编》,第93-115页。
——新一代江格尔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