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空符号中能指的缺失∗
王军 李想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苏州 215006)
提 要:在符号学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通常都是实符号,即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符号,如一般语言符号、交通标志符号和声音符号等,而对于没有形式表现但却能够表达特定意义的空符号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在国内外对空符号的研究中,经常会把索绪尔的二元符号观和皮尔士的三元符号观中的某些概念混为一谈,从而带来能指是否可以为“空”的问题。本文以语言空符号为例,通过对能指、符号载体和再现体等概念的解析,指出在索绪尔的经典符号学框架中,能指不可以为“空”,“空”的只是符号载体;空符号必须具有可识别性,其依据是结构或概念语义的完整性;语言空符号的“空”可以是形式结构层面上某一特定成分的缺失,有些情况下可以借助标记手段来提示空符号的存在,也可以是某一完整语义关系中某一环节的缺失。
1 引言
在符号学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通常都是实符号,即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符号,如语言符号、交通标志符号和声音符号等,而对于没有形式表现但却能够表达特定意义的空符号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虽然语言学中不乏表达“空”的概念,如零代词、零形式和空语类等,但这些一般都是从语言学的层面进行研究,鲜有人研究其符号学属性。与索绪尔、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研究范式不同,以皮尔士为代表的一般符号学不但关注语言及语言之外的各种类型的符号,而且特别注重对符号外在表现形式的研究。这种表现既可以有物质形式,也可以体现为物质形式的缺失,前者属于一般性符号,或称实符号,而后者属于空符号的范畴。赵毅衡(2016:25)给空符号下的定义是:“(空符号)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缺失:空白、黑暗、寂静、无语、无嗅、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等等。缺失能被感知,而且经常携带着重要意义”。在人类的符号活动中,实符号和空符号缺一不可,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韦世林2012:9)。
国内对空符号的研究多使用“空符号”(blank⁃sign)这一术语,如王希杰(1989)、韦世林(2012)、曾庆香(2017)、赵毅衡(2016)、汤文莉和胡易容(2019)等,但也有部分学者沿用国外的用法,使用“零符号”,如王东和李兵(2013)、聂丽君和李兵(2014)。国外学者在研究空符号这一现象时,并不使用blank⁃sign这一术语,而是大多使用zero sign,如Jakobson(1984)、Sebeok(1985)、Cantor(2016),也有学者使用其他类似的术语,如void of sign(Tanaka⁃Ishii 2017)。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人们不使用类似于“空符号”“零符号”这样宽泛的术语,也并不意味着人们研究的不是空符号现象,如对silence或eloquent silence(Ephratt 2008,Bilmes 1994)、pause(Hawkings 1971)、停顿(苏少波2000)、留白(李勇忠2009)等的研究。虽然在这些空符号研究中,也会或多或少涉及语言空符号的问题,但基本上没有专门聚焦语言空符号的研究。
空符号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缺少具体的形式表现,但这是否就是意味着能指的缺失呢。针对这个问题,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Tanaka⁃Ishii(2017)认为空符号的能指可以缺失,即存在“缺失的能指”(absent signifier)。Sebeok(2001)也持这一观点,他的原话是:(A)sign vehicle can sometimes…signify by its very absence,occur,that is in zero form.Linguists who employ the expression‘zero sign’…must mean either‘zero signifier’,or,much more rarely,‘zero signified’.值得注意的是,Sebeok所说的能指为空(zero signifier)实际上指的是“符号载体”(sign vehicle)的缺失,是把能指等同于符号载体。然而,其他学者(如赵毅衡2016)并不认为能指可以缺失,空符号中缺失的实际上只是符号的表现形式而已。在Cantor(2016)的研究中,两种矛盾的观点同时存在,他一方面认为空符号可以表现为人们无法感知到“再现体”(representamen)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说能指缺失就是一种空符号。我们认为,这种针对空符号中能指是否可以缺失的摇摆不定的观点,反映的是索绪尔符号观和后索绪尔符号观的冲突。
2 索绪尔与后索绪尔时代的符号观
索绪尔(1980)经典符号学思想中的能指与所指分别指的是声音形象(sound image)和概念(concept),两者均为心理实体,依靠某种规约关系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二元结合的符号。概念毫无疑问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存在,而声音形象是“声响的精神印记”(索绪尔1980:84),“符号系统只存在于言说者的精神之中”(Saussure 2002:43),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于外部客观世界的系统。然而,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常常被误解、扭曲,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把索绪尔所说的能指看作一个物质性或具有物理属性的存在,是大脑之外可以被直接感知的实体(翟丽霞 张彩霞2006,李洪儒2010,李霓2013)。针对这种较为普遍的误解,屠友祥(2013)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地追随本维尼斯特的观点,因为他反对索绪尔的心理现实性,强调现实就应该是大脑之外客观存在的事物。
事实上,不仅仅是本维尼斯特和很多中国学者错把索绪尔所说的心理现实理解成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这种思想在国外也比较盛行。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 1961)最早提出“后索绪尔符号学”(post⁃Saussurean semiotics)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就包含把能指视作符号的一种物质(mate⁃rial)或物理(physical)的形式。在探究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时,Cobley(2001:4)也是一头雾水,只是猜测说,这可能与索绪尔的唯一著作在1959年的英语译本有关,是译者对能指所指的不当处理留下的隐患。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比较牵强,甚至屠友祥认为的本维尼斯特是始作俑者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原因有二:首先,索绪尔留存于世的著作只有一部,尽管后来陆续有一些索绪尔的手稿被发现,但是人们对他符号学思想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一部著作,学者们对其中的核心观点长期产生误读的可能性极小。其次,理论与应用历来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方面,索绪尔的伟大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理论上的贡献,尤其是开拓性地提出语言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向,具有宏观研究导向和引领作用;然而在现实的语言研究及一般符号学研究中,人们更加关注应用性问题,更容易被无限丰富的可被直接感知的符号现象所吸引,这是推动符号学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因之一。索绪尔创造的能指所指二元对立的概念言简意赅,突显出关系在符号意指过程中的作用,其理论价值是任何意义研究、符号研究无法回避且必须接受的,但是这种接受并非意味着全盘接纳,而是要取其精髓,继而发扬光大。例如,尽管索绪尔所讲的能指与所指仅限于单纯词层面,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其扩充到大于单纯词的语言结构的其他层面(张德禄1997,董敏2005)。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能指的概念扩展到表示符号的物质或物理形式上去,我们甚至可以把皮尔士符号学中的再现体也视作能指(如Se⁃beok 2001:6,赵毅衡2016:95)。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所有这些针对能指的拓展、发展,都已经不等同于索绪尔的经典能指思想,只是在借用能指这个耳熟能详的术语来引入或说明其他相关概念而已。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索绪尔经典符号学的能指概念并不适合直接用来对语言空符号现象进行阐释,因为如前所述,他的能指仅限于单纯词范畴,而且是一种声音形象,而语言空符号现象往往涉及大于单纯词的范畴,在心理层面上也不太适合使用声音形象来表示。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能指看作语言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其表征对象可以是任何显性语言表达结构。这样一来,修改后的能指与索绪尔经典能指概念的共同之处就只有一点,就是它们同属于一个心理层面的实体,而这也正是我们可以使用能指这一术语讨论更广泛符号及空符号话题的根本依据。
3 缺失的能指
认为空符号或零符号的能指为“空”的学者并不少见,例如,Sebeok(2001:40)认为,语言学家所讲的“零符号”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零能指”(zero signifier),另一种是较为罕见的“零所指”(zero signified)。但他也发现,零符号这一概念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存在矛盾修饰关系(oxy⁃moronic),因为符号,或者更准确地说,能指是不可能为“零“的,因此他在该文的其他地方多次使用“零符号载体”(zero sign vehicle)来替代所谓的零能指。赵毅衡(2016:25)认为,大凡符号,都需要有一个符号载体用来被人们所感知。即便是空符号,它也需要一个能被感知的载体,只是这一载体是以物质符号的缺失来体现的。所以,符号载体可以为“空”,这就是空符号,而符号载体以物质形式体现的,则是实符号。符号载体实际上就是皮尔士所说的再现体,但它与心理层面的能指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Sebeok(2001:6)却说,“皮尔士把能指称作再现体”,Sebeok的这一说法实在令人困惑。
与Sebeok类似,Cantor(2016)也在混用索绪尔和皮尔士不同符号学体系中的概念。Cantor(2016:210)引用Melchuk(1999)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零符号的能指……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位置上原本应该出现的某一特定的能指出现缺失”,所以,他在谈到语言零符号时认为,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零符号,一是有特定含义的能指出现缺失,另一种是存在能指,但是其含义不确定(Cantor 2016:212)。然而,当他在阐述视觉零符号(visual zero sign)时,却使用皮尔士的“再现体”来对视觉零符号的特征进行描述(同上:211),认为视觉零符号要么是感知到符号的再现体出现缺失,但同时能够唤起所指对象;要么是能够感知到再现体的存在,但是所应唤起的所指对象出现缺失。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日本学者Tanaka⁃Ishii(2017)的研究中。她一方面明确使用索绪尔的符号两分法观点,认为能指缺失是空符号的一种类型,另一方面,她把空符号界定为“在表现形式上(representation)存在时空方面的空缺”,特别是她还尝试把表现为时空缺失的“空”等同于皮尔士的“第一性”(firstness),即再现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她所说的能指并非索绪尔经典符号学中的能指,而是皮尔士符号学中的再现体,或者说是符号的物质表现形式,只不过在空符号中表现为物质的缺失而已。
由于索绪尔两分的能指与所指无法与皮尔士三分的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对应起来,甚至能指与再现体、所指与对象或解释项也无法一一严格对应起来。如果我们把两人的符号概念放在一起讨论空符号问题,必然会带来令人困惑的解读。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专注于使用同一套符号学框架进行解读。例如,如果坚持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来解释空符号,我们就可以看到能指绝不可以缺失,因为能指一旦缺失,所谓的空符号就不再具有符号的属性了;缺失的只是能指的外在或物质表现形式。而如果坚持皮尔士的符号观,所谓的空符号就是指再现体缺失的状况。再现体缺失并非完全等同于没有再现体,因为在再现体缺失的位置总是存在一个潜在的再现体,这是保证空符号能被感知到的必要条件,也是空符号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
4 语言空符号的识别特征
根据前人对空符号概念的界定(如赵毅衡2016,Cantor 2016)以及我们前面对能指缺失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语言空符号的基本识别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可识别性,二是空符号的物质表现为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讲的空符号的识别特征仅仅局限于符号过程的前端,围绕能指或再现体来说,而非所指或对象与解释项,因为在谈及空符号类型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所指缺失的问题(如Sebeok 2001,Tanaka⁃Ishii 2017),甚至有能指所指同时缺失的现象(如Tanaka⁃Ishii 2017)。为避免问题复杂化,本文暂不讨论空符号过程中后端的特征。同时,为缩小研究范围,下面讨论的空符号仅限语言空符号。
虽然语言空符号的物质表现为空,但它必须能够被识别,只有被识别出来,才能发挥其符号功能。然而,由于空本身具有无法识别或难以识别的自然属性,它必须借助于其他手段显示出它的存在,而这些手段就成为空符号的具体识别特征。这就是说,“空符号要表意,必须有一个背景。空符号是‘应该有物时的无物’”(赵毅衡2016:16),空符号应该是“不在之在”(胡易容 任洪增2019:177)。
4.1 句法手段
语言学,特别是生成语言学研究中,有不少涉及成分缺失的概念,如空语类、零形式、零成分、零形回指、空动词、截省、空位、省略,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概念大都是在句法层面上进行讨论,而且有些“只是为了解释个别不规则的语言现象才‘添加’给语言的”(袁毓林 王明华2013:25),属于理论层面的解释方法,而不是语言自身具有的构成要素,因此不属于空符号现象,如例①中的NP语迹(ti)和例②中的wh⁃语迹(ti):
①The floweriwas wateredti.
②Whatiwill you buyti?
在谈到语言中的成分缺失或省略问题时,张力(2018:372)认为,应该将空位和零形式区分开来,其中“空位指占据一定的句法位置但没有任何内容填充的无语音输出的成分。而零形式正好相反,是指占据一定的句法位置由具有一定语义内容填充的无语音输出的成分”。从句子层面来说,只有占据一定的句法位置并且具有一定语义内容的空成分才是空符号,因为无论是空符号还是符号,都必须包含意指过程,意义是符号的核心。例①和例②中的语迹ti属于空位,而属于空符号的零形式如下所示:
③Someone stole the book,guess who∅.(截省)
④John likes oranges,and Tom∅apples.(动词空缺)(以上两例转自张力2018:373,有改动)
⑤∅Get up early.(零主语)
由于英语具有较为完备的句法体系,形态缺失但表意的零形式很容易被识别出来,或者说对空符号的识别是以完整的句法结构为参照所实现的。然而,在类似于汉语这种不强调句法完整性而注重词序(word order)及语义的语言中,对空符号的识别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对于英语中常见的动词空缺或省略的现象,有学者(如贺川生2007,傅玉2012)就认为汉语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显然与汉语缺乏英语那样的严格句法参照系有关。因此,句子层面的空符号必须以完整的句法结构作为参照,只有当句法结构不完整时,表现为空的成分才能成为被识别的空符号,体现出符号具有的意指特征。
4.2 标记手段
基于完整句法结构的空符号的符号载体可以完全以“空”的形式来体现能指的存在,然而在需要强调空符号存在,或者在无法确定完整句法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使用某种形式化的标记手段来提示该空符号的存在。最典型的空符号标记手段就是省略号的使用。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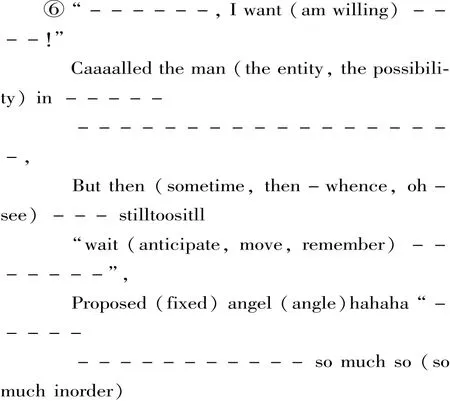
(Ephratt 2008:1925)
上例是一首希伯来诗歌的节选部分,作者通过使用“-----”的长短来表示未显性表达出来的词语的多少,但究竟是哪些词语缺失了,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无法确定。句法的不完整性,尤其是各种标点符号的使用,提示某些词语或语义的缺失,同时限定空符号出现的位置以及信息量的大小。类似的情形在汉语文本中也有,最为典型的就是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中所使用的“□□□□”,用来表示无法直接言说的有关性行为的描写。这种连续使用的符号标记越多,提示所描写的性行为越详细,反之则越简略。与这里所提到的“-----”和“□□□□”不但提示词语及语义内容的缺失还提示缺失信息量的多少不同,最为普通的空符号标记是“……”(汉语状态下)或“...”(英语状态下),以及“——”的这种形式特征固定的省略号,这类符号标记仅仅表示成分的省略,但不提示省略内容的多少。
空符号可以拥有一定的形式标记和空符号应该具有符号载体为“空”的特点并不矛盾。最典型的空符号是那种符号载体完全为“空”的类型(如句法结构中的零成分),对这类空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判断必须依靠一个特定的“背景”或“语境”,需要有某些条件或要素的限定。但是为了句法分析的便利,研究者也会对句法零成分进行标记,使用“∅”这种空符号标记。“∅”本身是一个实符号,其能指与所指都极其空泛;但我们所说的空符号却具有相对具体明确的能指与所指,“∅”只是引导受话人找到该能指所指的一个标记手段,它既不是能指(一个心理层面的存在),也不是能指的符号载体或再现体。因此,有标记手段的空符号包含两套符号系统,即实符号系统和空符号系统,两套符号系统的能指/所指完全不同。
4.3 语义关系之空
无论是句法层面的空符号,还是有空符号标记的空符号,在对空符号进行识别时,都必须基于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句法层面的完整结构是语法的完整性,具有标记手段的空符号的完整结构既可能是语法的完整性,也可能是语义的完整性。只有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中我们才可以发现某个成分的缺失,才能为空符号定位,并提取出其能指与所指。与句法层面的空符号和具有显性标记手段的空符号不同,单纯基于语义关系的空符号几乎无法在语篇层面上定位,它只能根据完整的语义关系推断出是否出现某种空缺。下面我们以因果关系和故事情节为例来说明这种语义关系之空。
人的大脑天生具有完型(gestalt)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人类认知体验的结晶,也是我们对碎片化的现实进行识别判断的基本工具。因果关系是一个完整的事件链,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任何一个成分的缺失,都会打破这个事件链的完整性,会让受话人对缺失的因或果产生期待,这种缺失的因或果就是一个空符号。例如,在对案件、交通事故等的文本描写中,读者首先读到的往往是“果”,而“因”在较长的时间都处在一种缺失的状态。正是对这缺失一环的不懈追寻,构成故事最为引人入胜的环节。“因”空符号是完全可以感知的,但却难以在语篇中体现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甚至有时在故事完全结束时,“因”也可能未完全展现出来,从而为读者留下巨大的悬念。同样,有“因”无“果”也会让“果”成为一个空符号,这个“果”甚至可以游离于文本之外。例如,在影片《盗梦空间》的末尾,主人公柯布拿出自己的图腾陀螺在桌子上转动,在陀螺尚未停止转动的时候影片结束了。根据故事的情节,陀螺最终停止与否将决定柯布能否回到现实空间,这是观众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陀螺是否停止的“果”最终没有出现,这就导致影片之外的观众要用脑补的方式来完善这一因果关系。
再比如,任何一个故事都有其内在的情节完整性,它必须有始有终有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者不完整,都会在人的完型认知中留下一个“空洞”,成为一个空符号,激发受话人努力去对其进行解读。根据萨特的美学思想,全部文学作品都是面向读者的呼吁(朱立元2004),读者的作用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显性表达出来的思想,还需要对作者有意无意留下的各种空白进行识别和解读。由于这些空白之处不是存在于文本的表达层面,而是在思想层面,不但难以定位,而且需要付出一定的认知努力才能发现它的存在,因此对这类空符号的识别和解读效果会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也是出现人们常说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主要原因。
5 结束语
为解释空符号的能指能否缺失的问题,我们必须对能指做一个准确的界定。基于索绪尔经典二元符号观的能指只能是一个心理实体(事实上,在本研究中我们已经对该心理实体的特征做出重新阐述,将其视作心理表征),这一能指不能够缺失,缺失的是能指的外在表现形式或符号载体;如果采用皮尔士的三元符号观,把能指视作一种物质的存在,等同于再现体,在这种情况下的“能指”就可以缺失。但是,两种符号观下的能指概念截然不同,如果分析过程中不坚持或说明所依据的某一特定的理论框架,就必然会带来令人困惑的分析过程和结论。
空符号与实符号一样,必然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结合体,必然体现某种意指过程。单纯的“空”无法识别,自然也无法发挥其符号的功能;“空”必须借助于“实”的映衬,所以空符号的识别特征必须从实符号中去寻找,需要实符号对“空”的存在进行限定或约束。在句法空符号中,“空”被限定在某一特定的句法位置上,体现特定的句法功能,表达特定的语义;在有标记的空符号中,“空”通过某种标记手段被标示出来,其中的某些标记手段甚至可以提示信息量的大小;然而在语义关系空符号类型中,空符号的“空”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完型语义关系结构中某一成分要素的缺失,是一种概念心理层面的存在。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语言空符号,都离不开一个潜在的完整的形式或语义结构作参照,都需要对空符号之“空”进行识别,继而获得对隐含的能指所指的理解。
既然空符号之“空”指的是空符号载体的缺失,那心理层面的能指又是什么。我们已经反复强调,无论是实符号还是空符号,都必须同时存在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结合体。实符号的能指是显性语言表达结构的心理表征,而空符号的能指是隐性语言表达结构的心理表征,需要通过其他显性语言表达手段来突显其存在,有时为了更好地显示该心理表征的某些特点,我们还可以使用某种标记手段来进行提示。但不管怎样,作为能指的空符号心理表征不可能真正缺失。
本文所谈论的主题是空符号能指是否能够缺失的问题,所以空符号的范围仅限符号载体缺失的这种类型,其他类型的空符号,如符号载体为实符号但所指为空的空符号,或符号载体和所指均为空的空符号(Tanaka⁃Ishii 2017)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此外,即便是韦世林(2012)所谈的某些符号载体为空的所谓空符号,如页边距、行间距等文本的空白之处,由于其既不是语言内部的形式或语义空缺,也缺乏符号所必需的能指与所指,因此也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语言空符号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