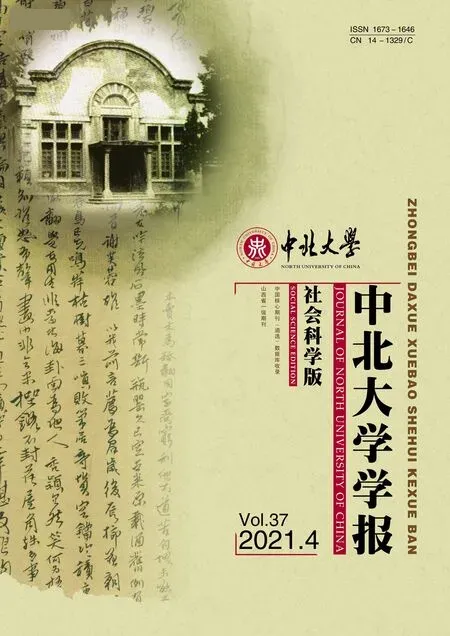“女性奥秘”的祛魅——许鞍华后期作品中的女性话语研究
姜 文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近些年来,“大女主戏”成为荧屏热播题材。从2011年《甄嬛传》到2015年《芈月传》 《武媚娘传奇》 《花千骨》,再到2016年《锦绣未央》 《女医明妃传》,2017年《我的前半生》 《楚乔传》,以及2018年《延禧攻略》,2019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众多“大女主”题材电视剧的涌现,一方面昭示着现实生活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建构着观众的审美趣味和对“女权”的认知。然而,如论者所说,这些剧作大都是古装仙侠题材,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由网络IP改编而来,往往在架空历史的同时也架空了现实,女性的情感和心理体验是缺位的。[1]这里与其说是一种对现实的“架空”、 一种女性情感的“缺位”,不如说是一种对女性经验的“异化”。其“硬伤”在于过度迎合观众娱乐趣味和猎奇心理,古装、 宫斗、 仙侠等偶像化包装不仅“异化”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生命体验,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也并未触及导致这种“异化”的深层社会根源。
“异化”本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论述中的一个核心术语,通常指个体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控制而向其对立面转化的社会现象。“异化”的内涵后来被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借用,发展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2]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往往比较着重于探讨父权制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抑[3],而忽略了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渗透和普及可能给女性带来的影响。后者与前者的合谋导致男权性别话语更为隐蔽。传统的性别等级观念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不再那么明显,而是通过支配传播媒介和大众话语来隐性地影响并强化着性别不平等,就连看似远离意识形态的商业广告,实际上也包含着政治意义上的男性霸权文化。[4]诸多“大女主”题材的影视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合谋的进一步体现。其中的女主人公往往被塑造成红颜英雄,通过各种“玛丽苏”情节最终实现在职场或宫廷的成功。女性的生命体验、 情感经历与现实世界可能遭遇的性别难题一同被创作者规避,不仅弥漫出一种盲目的性别乐观主义,大众文化与传统父权文化的合谋更“异化”了女性受众关于“自我”的理想建构。相比较而言,女性题材在电影行业却一直不温不火,能坚持拍摄女性题材的导演更是屈指可数,许鞍华比较有代表性。《香港电影》杂志创刊号中这样评价许鞍华:“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很多年,电影依旧还是男性为主的世界,香港电影近30年来,男人堆里总是默默站着一个目光坦荡的许鞍华——拍片不快,赚不到什么大钱,但就是愿意拍电影。虽然作品成就有高有低,但在香港,甚至在亚洲,几乎找不出一个女导演可以与之匹敌。” 许鞍华前期作品题材多样,从《女人四十》开始,其创作题材基本定型为女性题材。与“大女主”戏有所不同,许鞍华把视角对准现代生活中的平凡女性,聚焦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情感,却又总是呈现出一种诗化风格,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5],在细腻平实中铺展开一幅现代女性的生活画卷。
1 失常的两性关系
两性关系的失常首先表现为男性在女性世界中的缺席。这种缺席与其说是肉体上的,不如说是心灵上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天水围的日与夜》 《天水围的夜与雾》 《桃姐》 《得闲炒饭》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这四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着共同的特点:她们如野草般顽强,也如野草般孤独。《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叶如棠在和潘知常的相处中付出了真情实感,最后却人财两空。以“知常”为名的潘知常,一番感情轰击取得叶如棠的信任后,却成了叶如棠情感世界里最失常的因素。叶如棠与前夫更是几乎不存在交流,她的生活如同固定镜头一样毫无生气。同样的遭际也发生在叶如棠的女儿身上,郭丰与潘知常一样,都是“行动上的矮子”。在女性视角的审视下,男性的“靠谱”和“知性”水火不容。
《天水围的日与夜》里,贵姐虽然有两个事业有成的弟弟和一个乖儿子,但三人并没有给贵姐的生活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反而都习惯了依赖贵姐,镜头切换之间传达出深深的疏离感。表面上看来贵姐坚强而独立,男性似乎可有可无。但当她看着亡夫遗物痛哭时,她的委屈和脆弱才在荧幕上迸发出来:一个独自供养孩子上学的超市女工有什么理由不需要帮助呢?而男性,随着丈夫的去世,似乎永远地退场了。《天水围的夜与雾》里暴虐多疑的李森、 《得闲炒饭》里的Robert、 《桃姐》里的罗杰以及《黄金时代》中的陆哲舜、 汪恩甲、 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些男性曾经对女性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可一旦进入到女性的情感世界,落到日常生活层面之后,他们的魅力仿佛失效了。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退场之后,生活的齿轮由女性独力推动,男性则成为需要被照顾、 被容忍的客体。
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在封建社会家长制家庭中,料理家务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变成一种私人事务,因此妻子成为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工业才给妇女提供了重新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因此,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6]87-88从恩格斯的考察来看,女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独立的丧失。《得闲炒饭》聚焦女同性恋群体,相比于贵姐、 桃姐、 李晓玲等比较传统的女性,她们不管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都更加独立。Macy一身中性打扮,游走于男女两性之间,享受着恋爱的美好,却并不想受到责任的约束,这正是现代都市很大一部分“单身贵族”的想法。Macy的独立意识来自于经济独立,她靠自己就可以生活的很好。因此,即使她怀孕了也并不需要男人的承诺,她考虑是否流产的出发点始终是自己是否需要,而不是别的什么,Robert就更不在她犹豫的范围内。反观萧红,受制于社会环境,她虽然有着前卫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但受制于经济条件,最后却不得不回到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的“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看法是深刻的。萧红独自在外生活,饱受社会偏见,家庭和社会关系被双双掐断,几乎成为一座孤岛。陆哲舜的陪伴或许给孤岛带来了春天,但当这份爱情也开始变质,孤岛也就成了一座荒岛,再也无人问津。电影对萧红和陆哲舜的这段爱情并没有过多展开,但它不仅表现出了萧红在爱情上的“英武”,而且陆哲舜对萧红的背叛更能反衬出她的勇敢。身为女性的萧红在这里体现出比男性更果断的个性以及与旧社会抗争的决绝,是女性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留下的一笔浓墨。
2 刻画“单身老女人”的生存处境
许鞍华善于关注弱势群体,擅长从真实的女性经验出发刻画她们的生存处境。在一次访谈中,许鞍华曾说过:“我的电影其实从没有特别追求拍得和别人不一样,总是属于比较中间的,也从没有最受大众欢迎的畅销片。我自己和家人都是属于边缘群体,社会的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个群体的。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是我的兴趣,也是天性。”[7]21而许鞍华女性电影的独特之处,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她弥补了对于单身老女人这一书写领域的空缺。[8]与一般的女性相比,“单身老女人”这一群体显然更弱势、 更边缘。有论者认为许鞍华的老年题材电影体现出一种“积极老龄化”的路径,意在让小人物获取现世安稳。[9]许鞍华的老年题材电影确实传达出一种坚韧的生活情绪,但又不止于“积极”和“安稳”,更旨在真实刻画老年女性的生活状况。许鞍华对这类女性投以关注的目光,在一种平凡得近乎刻板的生活中,呈现出她们的坚守,这种坚守赋予她们一种扎根生活并不为其所迫的韧性。
《天水围的日与夜》英文译名为TheWayWeAre,这个译名道出了影片所要表现的生活本象,同时,也传达出导演想要表现的更深刻的女性生活内涵。TheWayWeAre直译为“我们的存在方式”,这里的“我们”显然更偏向于家庭女性群体,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被家务劳动异化的社会现象。恩格斯对妇女地位低下根源的考察是富于启发性的,他认为财产私有制将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分离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劳动因创造出肉眼可见的价值而愈来愈得到重视,家务劳动却越来越私人化、 不被社会认可,从而揭示了女性被异化的深层社会根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依据。达拉·科斯塔认为家务劳动使得妇女被限制在家庭之中,因为家务劳动无法创造出量化的社会价值导致妇女对男性的依附,从而导致了妇女的异化。[10]111时至今日,女性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仍旧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可。在传统性别等级观念宰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几乎终其一生都在为家庭付出,作为个体的自我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异化中渐渐消融。贵姐是这一类型女性的典型代表。贵姐存在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网络中,在家庭网中,她是家里的大姐。年轻时打工供两个弟弟念书,结婚后与丈夫一起贴补家用,丈夫去世后贵姐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在社会网中,贵姐是一名超市女工,负责出售水果。贵姐每天往返于超市和家里,几乎重复着一样的动作:在超市搬水果、 摆水果、 卖水果,在家里她也总是忙于洗衣、 做饭等各种家务琐事——她似乎没有自己的兴趣。在这样一种看似无聊甚至是麻木的生活里,贵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抱怨,在许鞍华平静的镜头里,我们看到贵姐反而有些乐在其中:她对超市新来的女工梁婆婆表达善意,并多次出手相助——买花生油、 搬彩电、 陪她去找孙子; 她在家里也开始教儿子做家务,告诉他哪家的报纸实惠、 衣服怎么叠、 榴莲怎么开; 她也并没有麻烦两个事业有成的弟弟,家庭聚会时她仍然以大姐的身份照顾着两人。如论者所说,在这些看似碎片般的、 零散的生活细节中,作者借此展开的是充盈着诗意的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与真挚情感。[11]贵姐的平静或许跟许鞍华那并不激进的性别立场有关,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可以忽视以贵姐为代表的一类为家庭努力付出却默默无名的女性,也并不说明“贵姐们”的生活是安逸的,这只能再一次证明社会性别价值观念的缺陷和女性的“被迫伟大”。贵姐努力维系着她认为应当维持的世道人情,她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并履行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对贵姐而言,这既是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价值的坚守:她坚守着人与人之间朴素的伦理价值,这种坚守使她忙碌却不显忙乱,也把生活冲泡出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生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也是分析社会阶级和性别剥削的基本术语。工人在社会空间进行生产、 耗费劳动,需要在私人的领域进行补充、 恢复,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式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把男性劳动力的再生产归责给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却没有将之算入社会价值的增殖过程。正如凯瑟琳·麦金农所批评的那样,妇女的家务劳动保证了男性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本身却被排斥在商品生产之外。[12]24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社会中有一部分特殊的女性群体通过特殊的工作形式,一定程度上把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女佣”。其中,有极少一部分从旧时代跨入现代社会的女佣,她们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家庭,几乎完全依存于雇主家庭。少有女性主义创作者和研究者意识到“女佣”这一社会群体的价值,许鞍华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桃姐》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影片截取桃姐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展开叙述。桃姐是一位在罗家做了几十年的女佣,对于桃姐来说,罗家实际上已经成为她的归宿,然而,她对罗家有依恋却没有依附。她不想麻烦别人,而是竭力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并且有一种把平凡过成精致的愿望,这正是桃姐的坚守所在。桃姐的生活以中风为标志,分成前后两个阶段。中风之前,桃姐对自己的工作可谓尽心尽责:她去买蒜,要先穿上一件衣服,再戴上眼镜,一粒一粒地挑; 她帮罗杰面试新的女工,却没有一个符合她的标准。中风以后,桃姐选择辞职,罗杰诧异于桃姐住老人院的想法,其实桃姐只是不想麻烦罗家而已。虽然桃姐对罗家有依恋,但是她不想把依恋变成依附,她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坚持捍卫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面对有些无知的罗杰,桃姐并没有说出自己的不便,她尽量维持自己的独立也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她盛装参加罗杰电影的首映礼,做头发、 抹口红,丝毫看不出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一番精心装扮后的桃姐惊艳了罗杰,也惊艳了荧幕前的观众。面对这样一位女性,她的年龄只会使我们更加尊敬。
许鞍华电影中刻画的“单身老女人”形象,除了贵姐和桃姐外,还有《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叶如棠以及《明月几时有》中的方母。有论者认为“姨妈”和桃姐之间有一种价值观的变奏关系,前者的生活是“后现代”的,后者的生活是“单纯”的。[13]价值观的变奏确实存在,但差距并不是很大。尽管“姨妈”生活在上海,并且赶时髦地谈了一场黄昏恋,但从她的选择来看,她骨子里的生活观念仍是“前现代”的。许鞍华对女性的关注并非是一种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也不是一种启蒙者的姿态,而只是如实地讲述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14]在这种平等的讲述姿态中,“单身老女人”的生存处境被刻画出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性别弱势群体中的年龄弱势群体,她们或许没有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甚至有些安于现状,但这就是她们真实的存在状态。在这些中老年女性题材作品中,许鞍华把一个女人普普通通又起起伏伏的一生压缩成一部电影,给观众带来强烈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跨越了年龄、 时代、 性别和国度,它使镜头前的我们觉得:“是的!就是这样!”。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陌生又熟悉的“她们”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她们的人生,或许就是我们身边许许多多平凡又伟大的女性的人生。
3 表现女性的反抗精神
许鞍华后期作品中的青年女性多扮演着打破成见的角色,她们往往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周围的环境不符合她们的愿望时,她们就化身逆流而上的反叛者。这里说的“流”,是指以男权思想为指导的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规约,如相夫教子、 忍让服从、 遵守妇道等,这些规约限制了女性对生活的想象,是需要被打破的成见。相比于“批判”,“反叛” “反抗”或许是不那么理性的词汇,这样的词汇通常被一些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所使用。如论者所归纳的那样,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是激进的、 革新的,也是反叛的、 张扬的。[15]的确,相比于其他女性主义流派,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往往更加凸显性别差异、 张扬女性价值,对两性状况的改善也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要通过技术革命解放妇女的生理限制,而非仅仅通过制度改良两性观念。这种激进的立场植根于激进者们对“父权制”社会的认知,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的观点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米利特将男权制政府视作由占人口一半的男人向占人口另一半的女人所实施的支配制度,因此,男权制社会有两重原则: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年长者有权支配年少者。[16]39米利特把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 政治关系联系起来,认为权力关系不仅控制着公共空间,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我们这里所使用的“反抗”并非激进式的反抗——“反抗”这个词虽然经常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却并不必然指向暴力,其中有着国情、 民情等方面的差异。以下许鞍华的两部电影就说明了这一点。
《天水围的夜与雾》中,王晓玲自小离家闯荡,她的反抗精神首先体现为改变经济状况的努力。虽然王晓玲的父母恪守着古老的重男轻女观念,但是,王晓玲对家庭的温情盖过了这些。通过一些闪回镜头可知,她竭力改善家庭生活:用头两年的工资给家里买了村里第一台彩电; 借助李森的经济地位给家里安装电话、 翻修房子。她也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命运的安排,李森的加入给王晓玲的反抗加入了些许亮色。然而,一场经济危机带走了一切——那些从李森钱包里吹出的泡沫,随着李森的破产终究显现出来梦幻的本质。王晓玲第一阶段的反抗——作为弱势群体一员对命运的反抗宣告失败。之后,王晓玲随李森入住天水围,靠着李森的救济金维持日常开销,生活拮据。而李森整日好吃懒做,满脑子靠救济金过活。王晓玲出去打工自食其力却被指责,在这之后李森更是对王晓玲拳脚相加,甚至威胁王晓玲。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下,王晓玲开始寻求外界的帮助,进行第二阶段的反抗——对男权的反抗:被李森暴打撵出家后,她找区议员,想要自己申请救济,或者找一份工作,却被安排入住妇女庇护中心; 李森一番花言巧语,加上社工明显对男性的偏向,又把王晓玲从妇女庇护中心转移到深圳,跟两个妹妹生活; 随后,李森到深圳威胁王晓玲,迫使王晓玲又回到天水围。王晓玲如置身逆流中的一叶小舟身不由己,男权思想弥漫在家庭和社会中。王母的忍让逻辑使王晓玲更加孤立无援。可以说,王晓玲的悲剧是由家庭和社会的合力造成的。王晓玲的挣扎轨迹中到处都是男权的影子,她极力想脱离李森,却举步维艰。从家庭到社会,在没有充分了解王晓玲处境的情况下,却都在劝她维持家庭完整。即使如此,王晓玲仍然坚定地迈出了反抗的步伐,对亲情和爱情失望之后,她已不再是那个用“我先生姓李”做自我介绍的沉默女郎。在王晓玲的反抗过程中,只有妇女庇护中心的同伴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些女性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惺惺相惜,共同反抗着男权的迫害。
《得闲炒饭》中,Macy与Anita又“直”又“弯”的性格融合了两性特质,这种中性化的角色设置模糊了男女性别界限。在公共事务方面,Macy是一名职业律师,有着自己的办公室。Anita是一个大银行的职员。两人都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靠自己就生活得很好。两人意外怀孕后,都拒绝了男性的负责,关于孩子的问题决定权完全在自己。Macy和Anita实际上成为电影的主角,而Robert和Mike则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男主角的电影。虽然在这部电影里导演也展现了香港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女同性恋这一文化异类并未受到歧视,但是,我们仍能看到女性为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而进行的反抗:Anita因为未婚先孕而被银行“隔离对待”——把Anita隔离在会议室,让她织毛衣,美其名曰养胎,实际是想迫使她自动辞职。Macy、 Eleanor和惠惠组织静坐抗议来对抗银行的歧视,这次静坐抗议取得了成功,但是当银行决定向Anita支付赔偿金以进行和解时,Anita却只想要银行高层的公开道歉,以挽回自己的尊严。《得闲炒饭》把镜头对准女同性恋群体,折射出来的却是男权社会的问题,“她们在香港这个物质发达、 竞争激烈的男权社会中,构筑了一个女性世界的乌托邦。反映了女性在当今社会中,争取自由平等的努力和女性主义运动不可阻挡的潮流,同时也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反抗,对社会问题的公开质询”[17]。电影最终以“大团圆”结局收尾,其中塑造的四个女性——Macy、 Anita、 Elernor和惠惠都有着坚强的独立精神,无论是她们女同性恋身份本身对于男权的讽刺,还是她们为争取妇女权利所做的反抗,都蕴含着一股“逆流”的力量。
4 结 语
当下,“女性奥秘”论似乎有所“返魅”。“女性奥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众媒介对女性的要求和型塑,植根于美国战后的社会生态:二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大量士兵复员回到美国,从战场上回来的男性需要工作,于是,美国社会以做“贤妻良母”为由,要求女性让出她们已经在社会上占有的工作岗位。这种论调后来愈演愈烈,美国各个媒体纷纷宣传,最终形成一种“女性奥秘”论。它告诉人们:女性跟男性不一样,女性不应妒忌男性、 力图要跟男性一样。女人最高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这种女性特征非常神秘,只有通过做贤妻、 良母和性被动才能实现。“女性奥秘”论认为,广大女性最能够实现自身女性特征的方式就是做郊区的家庭主妇。1963年,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驳斥了这种论调,引起广大中产阶级妇女的共鸣,并引领了西方第二阶段的女权主义运动。
“女性奥秘”论不但没有消失,时至今日或许还有所增强:传统男权体制对女性的压制和歧视往往以“仇女症” “厌女症”的方式表征出来,消费时代和商品社会的到来却使得这种压制和歧视变得合理化和更加难以察觉。商品社会,一切皆可被包装、 被消费,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被异化为人与物、 甚至物与物的关系。虽然男性在消费、 “凝视”着女性的同时,女性往往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女性的性别劣势却比男性有着更深久的历史渊源和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女性奥秘”的“返魅”和增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大众传媒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并强化着人们对女性的刻板认知。众多“大女主”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就是典型代表,千篇一律的“玛丽苏”情节设定和“上位”模式不仅遮蔽了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生命体验,造成女性荧幕形象的异化,从拉康镜像分析影响所及的精神分析学影视理论的角度来看(1)拉康认为,人的自我构建必须经由“他人”的认同,这种认同根据年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最初是婴儿通过认定镜子中的影像而产生自我的归属感,逐渐长大后则是通过他人和语言。见 [法]拉康. 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 《拉康选集》. 储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0。拉康突出了影像作为主体认同、 构建自我的工具性,使电影理论研究者的焦点从“电影怎样模仿现实”转向主体如何通过电影实现自我认同和主体间的文化关系。,也歪曲了女性受众在观看时的自我认同,并进一步影响其关于理想自我、 理想个体的建构。另一方面,虽然女性被伤害的事件一直都有,但近些年爆出来的一些犯罪事实却愈发令人震惊,震惊之余也让人后怕不已。(2)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2020年3月份左右爆出来的韩国“N号房”事件,包括前段时间韩国发生的女星自杀事件、 胜利事件等,北大包丽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一些虽然未产生广泛影响,但程度却相当严重恶劣的事件。读者如想进一步了解,可自行百度。这些恶劣事件彰显出“女性奥秘”信奉者观念之扭曲的同时,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主义斗士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必须明确:女性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独属于女性的话语,女性主义表达的是对权力的拒绝,对歧视的反抗,对偏见的反抗,对于我们把这个社会本质化、 单一化、 片面化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反抗,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文明标志,它也应该成为每一个人文学者或者每一个现代人的内在的思考社会同时反思社会的这样一种力量。[18]许鞍华对女性题材的处理和呈现,对于我们了解真实的女性世界具有启发性。许鞍华把镜头对准平凡女性,通过表现她们的日常生活,在平淡无奇中呈现真实的女性话语,从失常的两性关系、 刻画“单身老女人”的生存处境以及表现女性所受的不公平对待及其反抗精神等方面对“女性奥秘”论进行了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