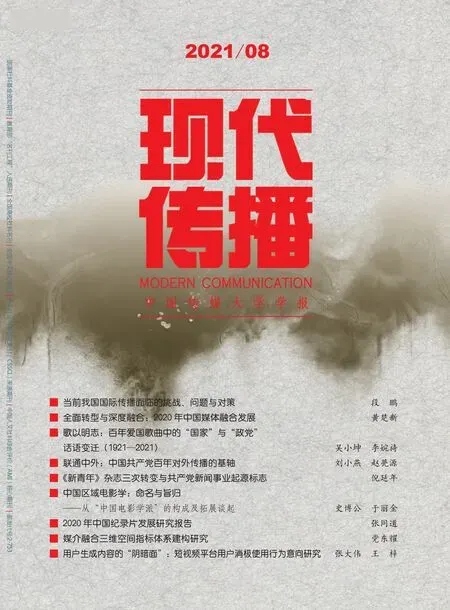脱嵌、再嵌与联结:离散群体的疫情叙事与共同体想象*
■ 陈 薇 柯金妍
一、引言
自诞生之日起,“共同体”就被视为安置个体身份、提供权利保障的理想形态。①这一概念具有的总体性、秩序性与边界感,使其为个体安全性与自我连贯性保驾护航,也为生活在其中的成员划定了生活交往的阈限范围。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技术革命带来的价值多元与离散,人类认知世界的边界与交往方式被颠覆,原本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的个体,在现代性的进程中经历了生存安全与身份认同的双重“脱嵌”。②鲍曼也由此表达了对现代社会“安全”与“温暖”的不可得之憾。③回望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的短短20年,无论是气候变暖与环境污染、经济危机与金融风险,还是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地区冲突与难民潮等等,全球性危机轮番上演。即便是肇始于一国的矛盾,在经济一体化的裹挟下也迅速上升为全球性的生存灾难。2020年以来暴发的全球疫情以及与此相伴的信息疫情,更是加剧了人类共同命运的不确定性,隐喻与偏见撕裂了“世界主义”的乌托邦④,灾难的创伤不断冲击着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自我认知,动摇着对共同体的信任与边界想象。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贝克便站在“文明的火山”上勾勒出了风险社会的轮廓。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相互形塑一再压缩着时空的边界,当流动日益成为遍在化的生命经验,“离散群体”作为穿梭于不同地域与文化的跨国迁徙群体的代表,无疑拥有更为丰富的身份意涵。不同于传统研究中将流动族群的身份构建化约为迁移、定居、适应、同化的线性过程,现代意义上的“离散”(diaspora)群体多用于描述散居于异文化中的少数族群。他们分散居住于最初的“中心”和至少两个“外围”地方,虽然脱离了母国的生活空间,但依然葆有对母国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依恋,因此在身份认同上摇摆不定、暧昧不明。⑤留学生便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辗转于世界各地,一方面享有着流动带来的选择自由和丰富的跨文化体验,另一方面,他们与寄居地国“物理上的亲近性与精神上的疏远性”也加剧了在地方与全球关系夹缝里,作为空间与文化“边缘人”的不确定性与认同困境。⑥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涉及在一个更主动意义上的社群的创造与延伸。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与制度性反思固然加速了个体从原有地方共同体中的脱嵌,但“脱嵌”与“再嵌”是前后连续的系列动作,全球与地方之间依然充满弹性和张力。⑦在这种本体性的不安全感与存在性焦虑中,社交媒体的使用为跨国流动群体维系与母国远距离关系提供了虚拟在场的可能,也为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提供了机遇。⑧全球疫情期间,由于与母国时空上的距离,以及在寄居地国空间上和心理上的隔离,留学生群体对于母国和居住国的想象、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都有着与常态下不一样的体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讲述疫区生活、分享隔离经历、寻求相互支援,以个体书写拼凑了这场全球疫情的亲历性记忆。基于此,本研究以留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体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便是关注在这场全球疫情中,这一特殊群体对于自我身份有着怎样的认知与标识,对于母国与居住国、全球与地方之间有着怎样的界定与想象,“流动”在其中究竟意味着不受保障、不被理解的不安全与不确定,还是会为联结与重聚提供新的契机与可能。这些都是本研究关注并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离散“共同体”的现代性想象
个体与共同体的边界厘定、自由与安全的权衡取舍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议题。无论是传统社会的氏族集体、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还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总是或者总被想象为“有限的”。⑨当流动、多元、断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面,生存的焦虑、自由的高涨与确定性的瓦解,都在不断冲击着共同体的传统边界。本文尝试从共同体的初始概念出发,考察在“流动的现代性”与风险社会下这一概念的发展与流变。
(一)共同体的现代性阈限
共同体(community)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善而建立的”⑩。19世纪中后期,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探讨正式掀开了共同体研究的序幕。有别于以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以价值为导向、极富目的性和计划性的“社会”,滕尼斯将“共同体”视为一种生活共同体——淳朴亲密的自然情感是其天然纽带,生活于其中的成员共享共同的习俗传统与价值观,守望相助、休戚与共。滕尼斯对传统血缘地缘共同体无疑是满怀深情的,涂尔干却对这种旧式连结葆有怀疑。在涂尔干看来,当社会发展到较高级阶段,异质性增强、同质性减弱的个体终将会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借助劳务分工而非血缘地缘的“有机团结”是最为理想的共同体形态。这种预判后来也被证实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17世纪的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高高扛起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旗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轰鸣动员人们从家庭迈向工厂,从乡村涌入城市,无论是从政治经济体系,还是从思想文化和心理归属上,这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见证了氏族邻里、血缘地域式共同体的崩塌与瓦解。正是在传统共同体崩塌消逝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共同体的存在对于本体性安全和自我的和谐连贯具有深远影响。启蒙思想家们随即在革命的烽火中勾勒出民族国家的基本轮廓,并将其视为安置个体身份、提供权利保障的理想的形态。按照知识精英的构想,个人需要“同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至此,脱离血缘集体、地域社区的人们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中,共同体也被赋予了更多给予个体安全保障的政治意涵。
遗憾的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被想象为有限”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解决个人身份认同和安全归属问题的方案陷入了新的困境。一方面,不断压缩的全球时空淘汰了封闭的领土认知,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与他人以及远方相连,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当流动成为生活的新常态,跨越传统疆界、获得空前自由的个体不仅面临着新的身份危机,也需要承接起更大的责任风险。自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个体生存的“存在性焦虑”、民族国家的认同困境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三部曲系统分析了全球化风险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认为置身于断裂、破碎、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着生存性焦虑和本体性不安全感,并提出关切微观个体精神状态与生存意义的“生活的政治”作为应对范式。鲍曼在上世纪末也将研究焦点挪移到相似的议题上,关注生活在日益个体化社会中的人们如何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寻求安全、划分边界、重建自我。
(二)风险社会下的“个体信任”与全球化再嵌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过去与现在的重构、固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价值体系的瓦解,让风险社会下的个体和共同体都变得更加摇摆难定。吉登斯从国家、地方和世界这个“三维空间模型”出发探讨了现代性语境下共同体的想象空间,并使用“信任”一词为我们勾勒了现代性语境下个体寻觅安全生活的基本路径。
吉登斯将信任划分为基于制度体系的信任和基于人际交往亲密性的信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涂尔干所提出的“集体意识或良心”与“功能性相互依赖”的社会团结机制不乏共通之处。在他看来,由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组成的抽象体系是当代社会为流动个体提供安全保障的重要源泉。尽管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机制在维持现代社会的高效运转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需的“相互性和亲密性”。在由知识理性所塑造的高度现代性社会中,启蒙学者们所设想的“理性国家”正面临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人们更有能力与意愿对所生活的世界进行反思与批判。而诸如气候变化、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应对也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范畴。诚如贝克所言,这个在19—20世纪借助领土主权为个体划定身份疆界的“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
不同于抽象体系所提供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庇佑,在吉登斯看来,基于人际交往亲密性的信任才是个体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情感疫苗”和“保护壳”。吉登斯将这种“对个人的信任”称为“基本信任”,指出它是婴儿在早期成长过程中从照料者身上获得的、能够为身处困境中的个体提供坚实牢固的情感盔甲。在风险日益向个体转移的现代社会里,基于信仰和情感的社会连结方式最能为这些承受转型阵痛的“原子人”提供天然的亲密感和可靠的本体安全。因此,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里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亲和力。
然而,吉登斯并不认为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可以解释当代社会团结的全部机制。在他看来,全球化还涉及在一个更主动意义上的“社群”的创造,这一社群既是在地的,也在无限的时空距离中延伸,因此规模上实实在在是全球性的。基于地方共同体的熟悉感的确立与地方的特殊性无关,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之上。因此,现代社会下的“脱嵌”只是暂时的前因,人们“再嵌”的不仅仅局限于“本地的地方”,也包括与“远处的地方”共情,数字科技与通信革命的蓬勃开展也为这种地方与全球想象提供了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既形构人们的行为,人们也通过社会交往形构了全球化的世界,由此达成了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三)个体叙事的想象性疗愈
依循吉登斯的视角,面对本体性不安全与存在性焦虑,叙事与书写是现代社会个体用于形塑自我认同、找寻身份归属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个体对生活经验的诠释和定义是个体价值框架、意义体系的缩影,“定义‘外部世界’一定程度上也是‘定义自我’”。心理学家卡伦·霍妮指出,只有当个体的内心冲突得以解决,人们才有可能走向一个更成熟、更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健全的自我。以自传式日记的方式对日常生活的定格记录,能够帮助个体拼接琐碎的经验性片段,将问题剥离出来进行自我对话,由此成为现代性冲击下个体维持自我持续性与连贯性的有效方式。通过个体生活历程与宏观社会背景的勾连,以整合的经验抵御现代性的自我困顿和意义失焦,个体成为自身的“治疗师”并扩展了自我身份的认知。
另一方面,书写与阅读作为一对并发式行为,不仅是行为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也伴随着他人的观看。上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戈夫曼推动了叙事研究的“互动化”转向。在他看来,叙事研究的重点不是叙事内容文本自身,更应该关注参与者在叙事对话中的角色转变,讲述者与倾听者的互动关系是研究的核心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叙述者向倾听者讲述个人遭遇、回溯既往创伤,倾听者参与意义的诠释与二次传播、协助意义空间的延展。因此,书写实践可被视为一场协同生产仪式,而诉诸于社交平台的在线书写无疑拓宽了这场仪式的范围,丰富了私人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的想象力。在虚拟的赛博空间,传统的书写与观看都呈现出一种“半公开”的互动状态,这既意味着文本的开放性,也体现了内容的公共性。
疫情下相互隔绝的线下生活反而为线上生活腾留了时间,社交网络为个体的即时互动创造了条件,为故事的集体协作开辟了可能。除了作为疫情日记的见证者、共情者,屏幕另一端的读者也成为了“第二作者”,通过对疫情日记的点赞、转发与评论,参与到故事的生产与再生产实践中来,使得个体书写上升为一场集体的叙事实践。在多方的协同互动中,一种群体性的身份认同正在生成,这为我们考察全球风险下流散在外的个体对于自我身份认定和共同体的认知提供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向度。
因此,本研究选择疫情期间留学生群体在“豆瓣”上的个人日记作为研究对象。在互联网产品纷纷尝试视频化转型的今天,作为国内知名的社区网站,豆瓣依然将图文作为内容的主要承载方式,为用户提供相对缓慢的书写时空、半公开的叙事空间和足够连贯的表达场所。疫情期间,豆瓣用户“Yinanaa”发起的“留学生疫情观察”话题引发热烈反响,以此为契机,漂泊在外的留学生们在豆瓣上开展了隔离日记的个人书写并迅速形成集群现象。本研究以“疫情日记”“疫区日记”“隔离日记”为关键词,选取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作为观察周期,爬取了豆瓣平台前100页的检索结果。通过限制写作主体、剔除重复,选取了18位海外留学生、合计约261篇日记作为本次的研究素材。鉴于叙事的表征性、情感性、动态性和社交平台的互动性,本文主要采用话语分析法对豆瓣平台留学生隔离日记进行研究。话语分析以语言学、符号学为学科背景,主要通过对传播过程的观察,研究语言在传播中的组织结构和使用方式,并尝试从语言的交际作用和语言的使用者的认知维度出发,解释影响意义传递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本文虽然不涉及意识形态和权力批判,但对留学生个体叙事的考察,依然需要将文本内容及形式分析与文化使用环境、社交媒体平台对文本意义生产的影响等综合起来予以考察。
三、摇摆的身份边界:“脱嵌”的个体与母国依恋
以“国”为政治保障、以“族”为文化依托的民族国家在19—20世纪里一直是共同体最典型牢固的可靠代表。这里通过分析留学生在日记里所记录的污名经历、所使用的家国隐喻和人称指示,考察风险社会下离散群体对于民族国家在政治法律和文化心理维度上的特定认知,探讨现代性语境下传统共同体所面临的困境与存续的价值。
(一)在地流放的边缘体验
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全球性疫情,留学生作为“离散群体”的多元身份为其身处遥远的异国空间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帕克在有关边缘人的研究中,将拥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特殊群体界定为“文化混血儿”,他们于生活的任何一种文化而言,始终是异质的、有距离的,无法完全被接受,也无法完全融入。在帕克看来,“边缘人”的概念不是原初的而是被建构的,通过界定“非我”而区隔“我群”与“他群”并被他群所排斥。透过豆瓣平台上的隔离日记,不难发现,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这场全球疫病正在为建构“边缘”提供契机。污名、歧视、偏见、排斥在全球范围内的轮番上演、迅速蔓延,让夹在所在国与祖籍国之间的留学生们再一次地被“边缘化”了。一方面,疫情期间,一部分国际政客们用“Chinese Virus”人为地挑起灾难下的种族争议、制造疫病下的对抗分立,驱逐和疏离成为留学生群体在特殊时期所面临的特殊瘟疫。有关疫情的隐喻污名催生的不只是物理隔离,还有社会排斥,被赋予政治色彩和道德意涵的新冠病毒,顺利参与到“他者”的建构和想象中去,并成为对付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修辞手法或隐喻”。恰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疾病是邪恶的、不洁的,因而疾病隐喻代表了混乱、失序,也总是“非我”的,人们对于疾病的想象常常与异乡、他族密切相关。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操控与支配下,涉及疫情的议题由科学防控的疾病母题,被置换成一场指责与归罪的游戏。不少留学生在日记中都记录了在这段特殊时期被排斥与被污名化的亲身经历与情绪反应:
“在那时,意大利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歧视华人的现象。种族主义者把新冠肺炎当成了一种歧视华人的绝佳借口”“我学会了一坐上公交车,就开始忍着不咳嗽、不吸鼻涕、不打喷嚏的技能。像一个犯了错的罪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意大利留学生、豆瓣用户“喜儿喂鸭正经地”,2020年4月2日)
“回顾这一年,‘羞耻感’似乎从2020年初贯穿到现在,从2020年初西班牙疫情刚开始时,面对路人的眼光和一些恶作剧时,这种羞耻感就开始了,后来西班牙开始强制居家令时,我的羞耻感又在我每一次出门购买食物或者散步时肆掠。”(西班牙留学生、豆瓣用户“丁乙”,2021年1月17日)
“一种关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流行病的特征被展现了出来。”(西班牙留学生、豆瓣用户“叉”,2020年3月29日)
另一方面,“疫病污名”并非只是异族人建构区隔的特权专利,在斗室隔离的状态下,这场集体性的身份贬抑也在同族人中制造隔膜和裂隙。在异乡,他们是来自“病源地”的华人亚裔,不洁与落后是他们历史性的族群印记;回到母国,他们又被想象为“崇洋媚外”的精致利己主义分子,故意隐瞒病情的境外威胁者。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这种负面的身份标签会让被污名群体产生强烈的羞耻感。他们被“标记”为“不洁”之人,在边界与边界之间不断地彷徨。如果说此前离散群体关于共同体想象的不确定性是因为适应融入异族文化的过程带来了原初身份的混淆,疫情的特殊语境则使得他们同时承受来自双边的排斥和边缘化。正如一名澳大利亚留学生在接受采访时所感叹的:“疫情作为一条导火索,把一切矛盾都激化了。”
(二)现代性脱嵌下的个体意识
突发性全球疫情俨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寄居国与祖籍国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防控手段、媒体报道,乃至文化差异、体制优劣等,都成为留学生们个人书写的内容之一。他们中有的无法理解“群体免疫”论,认为在“例外状态”下崇尚“正常”是政府对生命的漠视;有的则对“强制隔离”模式保持距离。如前所述,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和安全的双重期待构成了共同体想象的某种悖论:“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留学生群体享有着跨国迁徙带来的高度的个体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当全球风险成为真切可感的生活实景时,他们再一次面临安全与自由的选择,对于体制与个体身份的认知有了新的变化。
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语境里,风险正在发生着不可逆的个体化转向。置身于开放、流动、液态的社会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前现代性语境下作为解决方案的集体化社会正在陷入存在危机。诚如鲍曼所言,个人身份正在经历从“承受者(given)向责任者(task)的转型”。他们看似是拥有自由选择的自主个体,在全球性的瘟疫大流行面前,也需要为这种自由选择行为背后的代价与风险买单。疫情下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们发现,安全成为了一项需要由自己完成的任务,“自救”于是成为疫情下留学生群体在线书写中新的话语模式。
豆瓣用户“堂本栞”对疫情期间公司依然坚持线下办公的模式提出了质疑,选择联合工友和上级进行谈判:“作为劳工,只能自己保护自己,自己的权益自己争取。”德国留学生、豆瓣用户“申屠余夏”建议国内将生存课程纳入基础教育必修课:“不是所有的紧急事件都恰好有父母挡风遮雨。”日本留学生、豆瓣用户“映心堂于铃娜”写道:“最终,新冠疫病的风险还是具体地、扎实地都落到了每个个体的身上。”疫情下留学生公民权利的局部失效是否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划分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全球风险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个体被推向了前台,留学生群体个体意识的觉醒让个体社会的命题得到了再一次确认。
(三)“家国一体”的情感依托
尽管生命安全可以暂时交由自我捍卫,但身份认知依然是研究这群跨国流动的“边缘人”绕不开的议题。鲍曼指出,不管个体对自由主义有着怎样深切的向往,对自主性怀有何等的热忱,也不管他们对有效发挥个人能动性以捍卫这种自由和自主葆有怎样的信心,即便是最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全球精英,也总会陷入对身份和归属感的追问和探寻之中。
自滕尼斯提出“礼俗社区”和“法理社会”的划分以来,共同体有了最为基本的两个维度——文化伦理和政治法律。就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共同体的认同也指向了政治法理和文化心理的双元结构。前者指公民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持肯定,后者则将共同体视为文化血脉的承继和值得奔赴的精神寄托。某种程度上,这与吉登斯所提出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存在共通之处。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基于国家机器、制度体系的信任固然为现代社会日常安全感的诞生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基于幼年情感的人际信任才更为天然、亲密和持久。
这种情感依恋体现在日记中“家国一体”的讲述方式上。“家国同构”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性逻辑,不是冰冷的权利—义务结合体,而被共同的血缘、文化、信仰赋予了温情色彩和伦理意涵。疫情期间,身在海外收到健康包、几经周折回国返乡等都是留学生群体与祖籍国接触的标志性经历。在这些个体叙事中,遥远的“国”既是提供庇护的“身份盔甲”,也是与“家”相连的精神居所和情感寄托。无论是收到来自祖国的“健康包”的温暖,还是听到国航乘务员说“欢迎回家”时的潸然泪下,留学生群体眼中的祖国成为了他们在异乡漂泊的坚实后盾。同时,家国一体的讲述方式也体现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人称代词在语用学中也被称为“人称指示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指代方式,它将对话书写所涉及的说话者、听话者以及第三方联系起来,体现了叙述者对指涉方的关系界定和情感倾向。带有文化规约烙印的“祖国母亲”“自家”“我”等第一人称的指示语前缀在日记里频繁出现,这种同构的归属感成为留学生群体对抗风险和焦虑的“情感疫苗”与“身份盔甲”。
四、灾时的“异质同构”:“再嵌”的地方与全球联结
在由新冠疫情主导的全球性风险中,区隔、边缘被不断建构,断裂、对立在不断生成。除了回到“保护壳”,疫情下的留学生群体也开始更为迫切地找寻着自我与他人、地方与世界的连结。这里通过分析疫情日记里记录的当地故事、民间仪式与共情话语等,考察在全球疫情这一特殊情境下,离散群体对地方和全球的想象。
(一)地方的关系再嵌
吉登斯并不只关注现代社会时空分离与脱域机制对地方的消解,相反,他辩证地将破碎的地方与全球整合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看来,前现代社会中熟悉感和舒适性的生成,建立在人们所遵循的每日生活的常规之上,而非派生于地域化地点的特殊性中。疫情的全球性蔓延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留学生群体“再嵌入”地方的进程。处于同一时空的异质群体虽然因为防疫所需被打散为个体,但在隔离中关于“附近”的感知反而变得清晰起来。那些在忙碌生活中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地方元素,无不在标识着个体与当地的隐秘连结。
在武汉、伦巴第、哥廷根、洛杉矶等有留学生的疫区城市,一种民间仪式悄然产生,将人们以“虚拟共同体”的形式聚集起来。留学生和邻里一起走上阳台,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加入各地的阳台音乐会中,通过歌声呼应情绪、相互鼓舞。他们对于所在地的情感与想象也变得更加浓烈具象:“每晚8点钟的约会,在提醒每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度过难关。”留学以来还没有交到当地朋友的“容安”隔着广场对望平时见不着面的邻居;原本不懂方言、自称“没有地方身份”的“晓宇”第一次和武汉有了相同的情绪共振。社会学家柯林斯将互动仪式的发生要素归纳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参与、共同集聚在同一时空并相互影响、有明确的“他者”判定标准、有共同的情绪聚焦与情感体验,其核心在于通过参与者的行为情感相互感染、共同作用,从而推动仪式内共享情感的生成。这种集体在场所迸发出的情感能量将当地异质的个体集结在一起,无论是本地人与外地人,还是本族人与异族人、本国人与外国人,一切原生的、建构的界限在仪式中渐渐消融,成为与地方关系再造的新资源,从而在各自所处的地方完成了和解与“再嵌”。
再如,日记里多处出现的“浮船”隐喻也描述了灾时状态下留学生群体离散在外、又与当地人共处同一时空的患难经历。疫情风暴眼中这条“漂浮的船”“沉没中的船”作为一种隐喻,传达着离散群体漂泊不定的边缘感、全球风险下的不安全感;而“同一艘船”的隐喻也生动描述了留学生与当地居民之间深度绑定的利害关系。疫病推动着他们与寄居国公民在共同的命运中生命与生命相互依偎、安全与安全互为凭仗。通过强调彼此之间的共性,他们试图探索保障自身生存权利的合理路径,通过倡导合作而非分裂,他们尝试思考特殊时期应对灾难与疏导情绪的方案。
(二)共情话语与全球的联结想象
在贝克看来,全球灾难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高度个体化社会重新实现整合的契机,危难下如果人们“能够被成功动员和激发”,那么“在旧有的社会性正在‘蒸发’的地方”,新的纽带依然可以被创造出来。这场肆掠全球的疫病也再一次印证了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预判。透过这些日记里的患难叙事与共情话语,我们发现,似乎在留学生群体中找到了贝克所说的联合的可能。在场与缺场的纠缠,附近与远方的勾连,似乎再也没有那个真正意义上的“他者”存在,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置身事外,命运共同体下唯有同心协力才能对抗灾难。
跨文化生活的经历让留学生群体对不同社会的“人情味”建立起具象的感知。在德国留学生“申屠余夏”看来:“如果不是一份人情味,陌生的城市与国家不能触动情绪。”正是因为这份“人情味”,他们会为疫情初期的武汉人祈祷,在海外组织筹集防护物资捐赠给国内医院。他们选择在疫情蔓延时留在当地与室友共度难关,希望所在的国家、紧密相连的邻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健康平安。十年前随父母来到加拿大学习生活的“夏打盹儿啊”在日记中谈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疫情初期有别于白人朋友隔岸观火的第三人心态,她对国内新闻保持着高度关注,为武汉难过悲哀、气愤不满。她发现:“自己心里永远不可能真的割舍掉作为中国人的那部分身份,它已经深刻地融进我的血液,我看到同胞经受苦难,会由衷地感到心痛。”尽管因为疫病污名,漂泊在外的留学生群体遭受了来自所在国和祖籍国的双重排斥,但当疫病的天灾与人祸在全球各地接连上演,当每天清晨的关注焦点从中国延伸向世界时,这群拥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离散群体生成了一种近似世界主义的共情。
身处在全球性的关联网络中,留学生群体比任何人都更懂得不被理解的苦楚,也更能清晰地感知到疫病下个体与全球命运的紧密纠缠。自亚里士多德指出“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善而成立”以来,价值伦理便成为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衡量维度。这场全球性的灾难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争取“善”的话语、提倡“利他个体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应对全球性灾难的大势所趋。当个体意识到自身安全与他人和远方密切相关,“为自己而活”和“为他人而活”就不再是一对互斥的价值命题,个人主义的道德内涵有了更多的阐发空间,个体化时代的共同体也生发了新的团结机制。无论是为异国邻居赠送防疫物资,还是选择成立线上心理援助组织贡献力量,透过留学生群体的隔离日记,我们能看到一种有关命运道德、超越地域边界的联结正在生成。正如英国留学生、豆瓣用户“晓宇”在日记的终篇这样写道:
“生存不是问题的时候,来自哪里是急迫的;当死亡逼近的时候,回到哪里才变得紧要。如果我们回答时的一丝温存,保留到后危机的时代,那便是足够的起点。”(2020年3月30日)
五、结语
时空分离、抽离机制与知识的反思性作为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加速了个体从传统共同体的脱嵌历程。诚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既消解了国家权力,又凸显了本土的身份意识,同时通过边缘挤压创造出新的领域。置身于流动多元同时又断裂分立的现代社会,留学生群体作为夹杂在文化间隙里摇摆不定的“边缘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本体性不安和存在性焦虑。风险社会冲击着传统共同体的社会图式与价值体系,但也“掌握了新的冲突和共识之源”。因此,他们对于共同体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不再以有明确边界划定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为原型,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抵御焦虑的情感盔甲,而不仅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权利保障体系提供安全庇佑。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某种“共享情感”和“集体意识”也在生成,同时区、同地域、共患难的经验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存在,为留学生群体提供了与当地人连结的纽带。与其将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现代性生活形态视为对地方的消解,不如说它是在具有共享经验的全球化的“社区”中的一种整合,进一步推动了他们“再嵌入”地方的进程,也赋予了他们最大限度的共情能力。
循着这些琐碎私人的隔离日记,我们勾勒出留学生眼中“共同体”的基本轮廓——一张漏洞扩大的传统安全网,一个极富文化情感色彩的母国家园,以及在地方和全球纠葛互嵌的风险世界中正在生成的一种有关命运道德的新联结。面对风险日益全球化、社会日益个体化的现代情境,许纪霖曾指出,通过补充社群主义来建立社会的自我,引入共和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以重新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化世界主义让个人从普世文明中获得真正的自我。这些社交平台上的个人日记为我们描绘了全球疫情下留学生群体重新界定自我与世界、找寻身份归属的方式与路径,也展演了风险社会下共同体“异质同构”的可能。吉登斯将“生活政治”视为个人应对现代性风险的解决范式,并指出这不是一个排除“他者”的政治。在全球化的时代,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机会的无限可能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都同时铺陈在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全球疫情加剧的人类共同命运的不确定性与后现代的总体性危机,只有相互联结才能更有效地应对这种纷争和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传统、历史和他人的和谐共处,而这,或许也是吉登斯强调的“重构现代性的重要动力”。
注释:
⑤ William Safran.DiasporasinModernSocieties:MythsofHomelandandReturn.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vol.1,no.1,1991.pp.83-99.
⑥ Robert E.Park.HumanMigrationandMarginal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3,1928.pp.881-893.
⑧ 董晨宇、丁依然、段采薏:《作为复媒体环境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配与文化适应》,《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7期,第90页。
⑨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⑩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