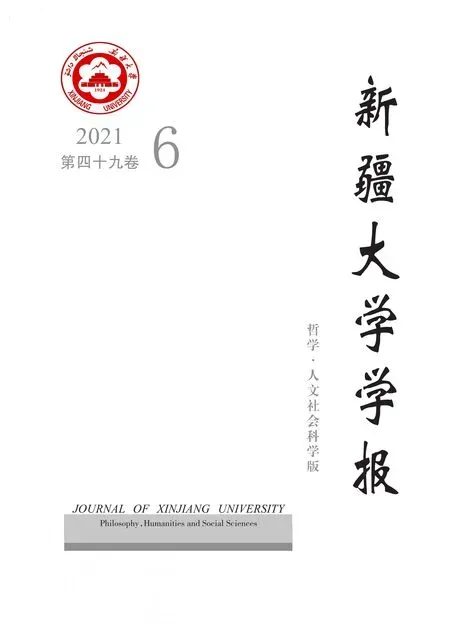迁徙皇族的兼容与管理:清代宗室营发覆*
方玉权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清代政典载“盛京宗室有不同于京旗者,旧居、移居之分”[1]凡例,3,若从养赡待遇与管理等制度分异而言,此“旧居”与“移居”时间临界点乃系嘉庆十八年(1813),即在此之前定居盛京的宗室为旧居,其后定居者属移居。其标志性事件是清廷于是年开始将京城部分宗室陆续移居盛京,主要“因八旗闲散宗室支派繁衍,生计维艰”,为“优待宗室,裕其生业”[2]卷260,527,但兼有“将不安本分之闲散宗室酌量挑出送往,妥为安插”[3]23之意。为安置以上宗室,清廷在盛京城小东门外新建宗室营,其内有住房70所,另有公所、堆房、关帝庙和望楼等,计622间①参见杨同桂辑《盛京通鉴》卷1《宗室事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2-34页。,占地207亩。目前学界对宗室营已有一定关注,成果多围绕嘉庆朝宗室移居的原因、过程及其到宗室营的待遇等内容②如李凤民《嘉庆皇帝设宗室营》,《紫禁城》,1988年第4期,第37、46页;高换婷《嘉庆朝宗室人口迁移述评》,《历史档案》,2003年第3期,第91-95、101页;刘灿《嘉道时期宗室移居盛京考述》,《历史档案》,2020年第3期,第96-104页等。另有清代其他相关研究中提及宗室营或移居宗室的成果,如杜家骥《清代宗室分封制述论》,《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4期,第91页;戴克良《清前期盛京八旗王公贵族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11、13-14页;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28页;等。,却很少有成果将宗室营置于盛京地域权力结构的语境中对其人口迁入迁出的复杂性、职官建置和历史影响等进行深入研究,对嘉道以降宗室营之演变及其内皇族司法等问题的研究更显不足。对以上论域薄弱诸处进行深入研究,能进一步厘清宗室营之发展脉络,明确其在清中后期皇族管理制度中的地位,亦能加深对清代盛京闲散皇族及其管理体制之了解。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为主要史料,撰此专文,尝试对清代宗室营的相关问题再进行深入探讨。
一、人口及其分布范围
(一)人口迁入
清代宗室营大规模人口迁入集中在嘉庆十八年(1813)至二十四年(1819)间,该时期朝廷组织自京城移居盛京的宗室共四起(见表1),这是宗室营最初人口的主要来源。清廷四起共移居宗室74户,连同仆役共407人。而嘉庆二十四年,盛京旧居宗室共167户(其中盛京城129户,散居盛京之牛庄、辽阳和抚顺等处38户)③参见赵增越《嘉庆朝宗室移住盛京档案》(下),《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第27页。,移居宗室占盛京旧居宗室总户数的44.3%,可见前者大大充实了盛京宗室户口数量。这些移居者主要是无爵无职的闲散宗室,并“只将宗室之无业者移居,其家有恒产 者,即不必挑派”[2]卷273,712。
嘉庆朝以后,清廷再未进行皇族集体移居,但宗室营人口流入现象依然存在,以因罪移居和被发遣者及其眷属为主,特点是单次输入人数不多、频度相对较高。嘉庆十九年(1814),清廷定例“宗室缘事发遣,遇赦减释,如系由盛京释回者,即令回京;若由吉林、黑龙江释回者,即令其在盛京移居宗室公所酌给房屋居住”[5]卷725,23。自此,宗室营在安置京城无罪移居宗室的同时,又开始与清代皇族发遣制度接榫,成为部分发遣释回皇族及其家属的安置地。道光十年(1830)清廷议定“嗣后宗室犯案,除遣罪以上者仍照定例办理,如素不安分,或曾经圈禁后复滋生事端,均于结案后连其眷属由兵部押往盛京,交该将军等令在营房居住,作为移驻宗室”[6]卷169,628。即将京城中不安分、屡次犯罪之宗室及其家属强制移居宗室营,以示惩儆。道光十七年(1837)清廷改定“嗣后如遇发往盛京宗室,交该将军酌量给与房间居住,抑或归入宗室营居住,另行登记册档,交该营主事等严加管束”①参见宗人府宗令绵恺《奏为酌议发遣宗室章程事》,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下简称“录副奏折”),档号03-2665-021。。即宗室营又成为安置部分京城发遣宗室的固定之所,被发遣者之家眷亦有安置在营者。不过,获罪发遣盛京之皇族因可“遇赦减释”回京,故此类人在宗室营多属流动人口。从现存档案史料来看,以上诸项政策具有较强延续性,直至清末,宗室营依然承担着安置、管理京城犯罪和移居皇族的职能。
除以上人口来源外,道光朝以后,还有少数皇族由于照看盛京土地、坟茔或生计无着等原因,主动申请由京城移居宗室营,清廷亦酌情允准。如“道光十九年间,镶红旗宗室纯诚告假前往盛京祭扫坟茔后,情愿只身移居盛京居住照料土地”,获准后即定居宗室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城“宗室伊勒图呈请移居盛京居住看守坟茔”,宗人府奏准后“咨行该将军遵照,将宗室伊勒图等饬交宗室营主事等管理安置,作为移居宗室”②参见宗人府左司《为正白旗二族宗室伊勒图呈请移居盛京看守坟茔饬交宗室营主事等作为移居宗室管理安置事致黄档房》,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来文(下简称“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759-0028。。可见,嘉道之后,宗室营所接收的皇族亦不全是罪宗及其家属。
宗室营皇族人口主体是宗室,但亦有少数觉罗。在档案中,获咎觉罗安置于宗室营者并不鲜见,如“已革司狱觉罗吉椿,系正白旗满洲人,因狱犯兆昌屡次诬告滋事案内革职,于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发往盛京,归于移驻营房”③参见宗人府《为回复查出觉罗由发遣改为移居成案致军机处咨文》,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2697-010。。可见,宗室营建立后几年内即有发遣觉罗被安置其中。其后亦有发遣之觉罗改为永久移居者,如“觉罗庆敏素不安分,先因三犯徒罪拟发盛京,三年期满改为移驻觉罗,在宗室营居住”④参见宗人府右司《为移驻盛京镶红旗觉罗庆敏捏控讹诈一案刑部办理完结行该将军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说堂稿(下简称“宗人府说堂稿”),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档号06-01-002-000163-0037。。但由于该营本为宗室所建,营内觉罗多系发遣之人,移居者较少,故其人口比例也相对较小。
由上可知,宗室营人口来源复杂,多元兼容。其中既有宗室,又有觉罗,还有满汉仆役等;既有寻常安分之人,又有因罪移居和发遣之人;既有常住人口,又有流动人口。
(二)人口迁出
嘉庆十九年,清廷规定宗室营男性移居宗室本人身故后,其遗孀等家眷可回迁京城,这种政策使得至道光十年宗室营“陆续回京度日者三十余户”,“空闲住房三十三所”①参见理藩院尚书富俊《奏为移驻宗室眷属回京分别酌拟章程事》,道光十年五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下简称“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14-028。。可见,在十余年里约一半移居宗室家属回迁京城,宗室营人口流失严重。为此清廷规定“至移驻宗室本身物故,其子年已十八岁以上,果能在彼学习清汉文艺、清语骑射,已有成就,或在彼置有产业可以度日者,其眷属扶柩来京安葬毕,应令其仍回该营居住。若其子年虽已在十八岁以上,不能自立,彼处又无近支尊长可以管教照应,亦未置有产业,而京中亲族有可倚靠收管者,孤孀可悯,未便令其在彼失所,应准其眷属扶柩回京,安葬毕照旧归于在京本族”②参见宗人府宗令奕绍《奏为盛京空闲营房现骤难移驻宗室事》,道光十年六月二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2850-047。。此项规定虽有弹性,但对限制宗室营人口的继续流失不无意义。道光二十年(1840)清廷进一步严格规定“凡移居宗室(原注又有获咎之后改为移居者)应在营世居,不准回京复归京族”[7]卷29,311,即所有移居宗室及其眷属(过继子嗣和外嫁宗女除外)皆须世代在宗室营居住,这种硬性要求对抑制人口流失作用显著。
发遣皇族释回京城和皇族犯罪发往吉林、黑龙江也是宗室营人口迁出的重要形式。至道光朝,发遣盛京之皇族由将军定期(一般为三年)呈报原犯案情及在戍表现,由皇帝决定是否释回之制已基本定型。这虽不见于清代政典,但从道光十七年(1837)五月盛京将军的奏折中可窥端倪,宗室春林、觉罗玉盛等即是在此次奏报中获准释回京城③参见署盛京将军奕颢《奏为发遣盛京宗室觉罗春林等已逾三年开单请旨事》,道光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4000-048。。另外,每遇清帝东巡,盛京将军亦会照例将宗室营等处发遣皇族的相关情况呈奏,俟皇帝批准释回④参见《清宣宗实录》卷160,道光九年九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476页。。而宗室营内皇族因犯罪较重发遣至吉林或黑龙江者亦为数不少,如“移居宗室明庄因开场聚赌窝贼分赃”,“革去四品顶戴,发往黑龙江交该将军严加管束”⑤参见盛京将军耆英《奏报移居宗室明庄携带子女前往配所教养事》,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2810-043。。
清廷对宗室营皇族与京城旗族之往来实行比较人性化的管理,不但允许移居皇族遇嫁娶、扶柩安葬、至亲亡故和修理坟茔等事可请假回京⑥参见赵增越《嘉庆朝宗室移住盛京档案》(下),《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第11页。,而且允许移居皇族与京城皇族之间过继子嗣⑦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咨复盛京宗室安林情愿将第三子宗室国廉过继与胞兄族长安松为嗣等事致宗人府》,道光十年九月初八日,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440-0015。、与京城旗人结亲⑧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盛京宗室营正黄旗宗室庄兴告假进京择婿聘女事致宗人府》,道光七年八月初三日,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402-0089。等。如此,通过以上途径,既有宗室营皇族流入京城,又有京城皇族及非皇族女性旗人流入宗室营。此外,宗室营皇族亦可通过仕途晋升迁入京城⑨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盛京宗室营主事文恪留京补用派家人郑顺来营接取眷属等事致宗人府》,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363-0087。,清廷还允许宗室营皇族与盛京旗人自由结亲⑩参见赵增越《嘉庆朝宗室移住盛京档案》(上),《历史档案》,2019年第2期,第27页。。可见,宗室营自建立即与京城、盛京本地、吉林和黑龙江等处在人口上保持着多线交互流动。
(三)人口分布之演变
宗室营人口变动也对该营建筑的保存和人口分布等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光十年以前,宗室营的人口外流严重,其后清廷对营内皇族人口迁出进行管控,同时以因罪发遣和移居皇族对之进行零散持续性补充,这样的政策导向一方面造成该营其后人口迁入总体上大于迁出,人口数量长期处于平稳缓慢回升的状态;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营内部分房屋的较长时间空置、失于维护,进而颓坏。道光十九年(1839),宗室营“原建房屋七十所内,除移居宗室及发遣释回宗室觉罗并陆佳氏居住占用房三十八所,倒坏不堪使用房二十三所,实剩空闲房九所,内有五所整齐堪以拨给发遣宗室占用,其余四所瓦片间有脱落,门窗不全,尚堪粘补住用。至倒坏房间仅有大梁十一根,檩木三十二根”①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安置发遣盛京宗室珠隆阿等房间住所事致宗人府》,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559-0183。。可见,此时宗室营已有近三分之一住房不堪使用,该营的人口承载量亦随之下降。本年安置发遣皇族甚至出现了“或令二人占用一所,或令四人同居一处”的拥挤情况。而嘉庆十八年《安置移住宗室章程》又明确规定宗室营之“庙宇、衙署、官学、办事处等工遇有岁修咨行盛京工部修理,其住房各工由该宗室自行修补”②参见盛京将军《奏为盛京移居宗室营房内原建庙宇衙署住房各工被水冲倒请择要修理事》,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7-0131-021。,即营内的皇族住房不在官方维护修补范围之内,此原则一直贯彻之清末。这也使得很多营内无人居住、已倒坏不堪的住房并未得以重建。
光绪十九年(1893),宗室营所管“移居宗室共七十五户,食饷银宗室男妇子女共一百五十七名,子女二百七十一名,通共四百二十八名”[1]卷2,187,如再加之因罪移居之觉罗、发遣之皇族和仆役等,其人口总数较嘉庆二十四年稍多。就此,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即此时宗室营在住房大幅颓坏缩减的情况下,何以能安置比嘉庆朝还多的皇族人口?这主要因为自道光后期起,有些发遣和移居皇族在谕旨或制度上虽明令于宗室营居住,但限于该营住房有限等原因,其并未被安置在宗室营建筑范围之内,而是安置在营城之外而归该营官僚系统监管。正如光绪朝宗室营官员在呈报文书中所言“查本营城之内外散居宗室等按每月朔望传至公所,查点有无私出之宗室等情历经如斯办理”③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镶红旗移居宗室斌强私离配所等事致宗人府》,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559-0183。。显然,此时将一些移居皇族安置在宗室营城以外居住已是旧例。故自道光后期起,宗室营的人口分布实则突破了旧有营城范围,并分为营内居住和营外居住两部分,且后者随迁入人口的持续补充而逐渐增多,这意味着宗室营官僚系统管理所涉区域得以扩展,其职责亦随之有所扩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宗室营在庚子之乱中“城垣屋舍均被俄兵拆毁,本拟再请款重建,奈款项支绌,是以暂缓”[8],嗣后未再重建,其中之皇族一部分被安置在本地盛字南营,其余则于盛京四散流落。④参见宗人府右司《为盛京将军咨请兵部员外郎宗室富明留办宗室营主事一切事宜碍难照准等行该将军事》,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宗人府说堂稿,档号06-01-002-000808-0077。至此,嘉庆朝所建的宗室营建筑实体走向历史终结,伴随着该营皇族散落各处,其人口分布在盛京之内实则已毫无范围可言。但此后直到清亡,宗室营之名目在官方档案中仍频繁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在该时段宗室营之职官建置和组织架构依然保存完整,其官僚系统照旧负责着所属皇族养赡钱粮等申请发放、回京请假呈报和人口统计等各项事务。民国初年,宗室营之管理职官及其职权等因获当局承认而得以延续,该营主事等还通过奉天省长公署等民国政府机构与逊清小朝廷保持联系。据笔者所掌握史料,相关记载最晚至民国九年(1920)以后⑤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合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卷)》第8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8-340。。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应是民国初年东北政局和《清室优待条件》之规定等共同使然。
二、职官建置与管理
宗室营的主要职官建置实系是对京城闲散宗室基层管理体制的移植和改造。自乾隆中期起,学长、族长和总族长等负责京城闲散宗室基层管理的主要职官皆已出现,其成为宗人府和闲散宗室之间的管理媒介,于前者有指臂之用。宗室营建立伊始,清帝简派宗室“文弼、杰信二员以四品顶带作为郎中前往”[2]卷270,657盛京临时弹压,其后此二人因失职皆降为主事衔,继任者遂皆以主事委署,道光元年(1821)定制额设二员。⑥参见官修《钦定宗人府则例(光绪朝)》卷14《授官》,载《故宫珍本丛刊》第279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6页。宗室营主事秩正六品,系营内部最高主管官员,其实则相当于京城闲散宗室管理中的总族长一职。主事之下,嘉庆二十年(1815),设正副族长各一员、正副学长各一员⑦参见赵增越《嘉庆朝宗室移住盛京档案》(下),《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第16-17页。。在级别上,宗室营族长高于学长,族长之责系稽查督导和上传下达等日常管理,学长协理之。除以上职官,宗室营又于“道光十四年添设委学长二三员,此缺系由宗室营主事等因办事乏员,详请添设,随同族学长学习办事”[1]卷2,185。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京城宗室族长主要以宗支族属为单位来设置,多由族内高官大员兼任,赖惠敏就此提出“清皇族所设族长等严格说来并非正式官职,因而无固定俸响”[9]的观点。但就宗室营而言,其内宗室主要是自京城移居或发遣释回者,后又掺杂少数觉罗,人员构成打破了旧有族属界别,该营族长最初由盛京将军等自移居宗室中挑补,其后规定了明确的选任路径和进阶之途,且正副族长每年各有俸银四十两。故宗室营之族长等应属正式职官。
宗室营内部还设有协助管理、属借调性质的官员兵役等。宗室营建立初期,清廷为加强管理,令盛京将军“摊派佐领、防御各一员,轮住公所,协同约束,帮办事务。其公所三处共派马兵六名,听候差遣;帖写兵各六名,书写事件,俱轮流更换”[3]39。这种临时安排此后成为定制。上述佐领由盛京八旗中派任,秩正四品,防御实系盛京三陵守卫武官,秩正五品,二者品级皆高于宗室营主事。但因前二者的作用是协助,在宗室营内部管理架构中位处边缘,故不影响主事在营内最高主管官员的地位。
盛京皇族“原设有总族长一员,左右翼族长各一员,佐领各一员”[3]33,共同管理旧居宗室觉罗事务。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廷准奏为以上总族长等建专门办事公所①参见盛京将军松筠《奏为盛京宗室族长等办事公所年久坍塌请勘修事》,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16-0114-013。,供办公和存贮档册之用,时人多称“总族长衙门”,其系专门管理盛京旧居皇族之官署。但该总族长等遇两翼旧居皇族申请养赡钱粮和红白事恩赏银以及犯罪等事无权直接呈报宗人府或奏报皇帝,而是先要上报盛京将军,由其酌情处理或转奏。
清廷在筹建宗室营时“拟令移居宗室到沈,即可按旗分翼归入原设族长、佐领下,管理其婚丧事故、子女增减钱粮、恩赏、考试等项一切事件,俱由在沈驻扎章京会同原设族长详细查明,行文注册,加结具保,呈明总族长,照依原住宗室呈报该将军一体办理”[3]33。高换婷就此认为宗室营之人口被纳入到盛京旧居皇族管理组织之下“按旗被接管”[10]94,但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宗室营移居宗室并未编入盛京八旗及其宗室佐领之下,而是与八旗驻防相类,其旗籍族属仍隶在京原编制。如宗室营宗室明海病故后,主事等官在呈报文书中称“据本营左翼正白旗二族咸春佐领下宗室怀喜报称,伊父宗室明海于本年八月初十日未时病故”②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查明盛京宗室营左翼正白旗二族病故宗室明海因犯圈禁照例不准给予恩赏银两事致宗人府》,光绪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432-0155。,而“正白旗二族咸春佐领”实系京城之宗室旗佐族属。其次,宗室营内事务并非由盛京旧居宗室总族长等进行管理,而是由该营主事和族长等自行执掌。如宗室如山于光绪二十年二月“由兵部解交来奉,严加管束作为移居,当经札交宗室营主事等拨房安置,办给钱粮”③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盛京宗室营主事春熙等看管松懈疏脱人犯奉旨分别议处事致宗人府等》,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宗人府来文,档号06-01-001-000395-0136。,可见如山之钱粮等是由主事等宗室营内官员直接办理,其它如恩赏、考试和婚丧等此类例证亦不鲜见。再者,宗室营官员在营内有独立官署——“宗室营办理事务处”,系管理该营皇族的专门机构,在级别上与管理旧居皇族之“总族长衙门”比肩分立,并无隶属关系。故于管理结构而言,盛京宗室营皇族与旧居皇族实系该将军辖区内两个互为独立的皇族系统。
因宗室营官员品级较低,无具折奏事之权,故嘉庆十八年清廷“著派盛京将军和宁、户部侍郎润祥、礼部侍郎诚安专管移居宗室事务,统辖弹压。遇有应奏事件,文弼等二人具报,该将军侍郎等奏闻,以专责成”[2]卷270,657。自此,盛京将军和该地五部中的两部侍郎共同管理宗室营之制形成,但于职分和权力分配而言,盛京将军无疑在宗室营管理中居主导地位。故在地域权力结构中,盛京将军成为管理旧居皇族和宗室营皇族的最高官员,将军衙门成为最高管理机构。从清代皇族管理的权力谱系上看,盛京将军衙门实际上分割了部分原属于主管皇族事务之宗人府的权力,二者呈现出中央与地方非垂直之机构间职能交叉、平行往来密切的特点。这主要因为两京之间相隔千里,宗人府对盛京皇族不便直接管理,而随着该地皇族人口不断增多,相关事务愈益繁剧,为提高管理效能,迫使清廷将部分原属于宗人府的权力转交盛京将军衙门代行,而皇族身份的特殊性和宗人府在皇族管理中的地位又使得盛京将军衙门的相关职权较为有限,且要受到宗人府的制约。
在司法方面,盛京将军与该地刑部等对宗室营皇族所犯流刑以下罪名具有审判处置权。乾隆朝以降,盛京将军对其辖区内皇族的管理之权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在司法定拟权上表现尤为明显。乾隆三十一年(1766),盛京将军衙门获得辖区内犯罪觉罗的司法定拟权①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75,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505-506页。,在此之前遇有辖区皇族犯罪,其仅有受理权,但无定拟权②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15,乾隆五年四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690-691页。。嘉庆十七年(1812),清廷明定盛京“宗室觉罗有犯罪者,即由盛京刑部侍郎会同将军援例定拟,奏到时,再交在京衙门核议”[2]卷259,514,至此盛京将军等对辖区内犯罪的普通皇族皆有司法定拟之权。宗室营建立后,盛京行政系统尤其是该将军衙门的皇族管理权限进一步扩大。嘉庆二十年,清廷又定例“嗣后移居宗室等如有肆意妄为所犯罪名在军、流以上者,照例奏明办理外,若只系寻常过犯,即交该营宗室章京等分别圈禁责处”[4]17。即宗室营之皇族如犯流刑以下之罪,盛京将军可与该地刑部随时审办,并可施之以圈禁等刑罚,不必上奏皇帝,但仍须咨文宗人府备案。流刑以上之罪本地定拟后,仍要据实奏明,并咨行宗人府等在京衙门复核。这显然系嘉庆十三年(1808)京城“嗣后凡遇宗室犯科之案,讯取大概情形,显系罪在军流以上者,随时具奏,其余俱咨送宗人府会同刑部审明,照例定拟”[7]卷20,319-320之规定范式在盛京的翻版扩展,亦可看作上文宗人府与盛京将军衙门之皇族管理权力分配关系的另一旁证。
宗室营的日常管理汲取了清代驻防满城的传统制度资源,但其制度设计与实际情况多有扞格。嘉庆帝在筹建宗室营时曾明确指出“至现拟移往盛京之宗室各户,事同移徙驻防”[3]24,而宗室营实系在盛京城外另建小型“新城”,其形制仿照京城健锐营,皇族于内聚集而居,这些特点与雍正朝以后所建的驻防满城甚为相似③关于清代满城和满营的研究可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04-212页。。清廷如此为之,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便于皇族的集中约束管理,另一方面则是为减少皇族与外界旗民接触,避免不必要纷争。在管理上,宗室营最初与驻防满城也有颇多共性,如宗室营建立之初就定立了门禁制度,营门早开晚闭,“营房楼门内外各安设堆房二间,门内派委官一员,带兵五名;门外派领催一名,带兵四名,值宿巡更,稽查出入,按旬更替”。营内所属皇族不能随意出入营门,如有事外出须“报明弹压司员,俾资稽核”[3]39-40。为防止营内发遣皇族在外滋事或逃跑,清廷定制由宗室营主事等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将之召集,按单点名并报备将军衙门等④参见盛京将军奕兴《奏为发遣宗室丰寅在配私自外出请从重改发吉林事》,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14-0064-047。。因此,宗室营皇族的活动自由在制度层面受到严格约束,远远小于京城皇族和盛京旧居皇族。但因宗室营内的空间有限,且生活设施并不完善,如其内并无市肆,皇族买卖生活物品皆须出营,这就使营内皇族与周边的旗民社会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可能如很多驻防满城一样以独立的小社会而存在。故清廷试图限制宗室营皇族之活动及其与外界交往的制度设计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很难得到切实执行。道光朝后期,归宗室营管理但散居该营之外的皇族人数增多,这类人除每月两次回营点卯之外,所受约束管理实则与盛京旧居皇族的差别不大,这种异化情形的出现,一方面使该营作为盛京独立皇族系统的管理地域界限得以延展,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上述日常管理制度的作用,增加了营官对其所属皇族的约束难度。
三、消极影响与积极意义
宗室营之皇族很多本系不安分之人,道光朝以后因罪移居和发遣之皇族又成为该营的主要人口来源,此类人更属为恶成习之辈,再生事端势所难免。加之宗室营管理制度的缺陷和异化等诸多因素,该营的日常管理之效并不尽如人意,所属皇族不服从管束和在外犯罪等问题严重,对盛京地方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部分宗室营皇族扰乱了盛京地方治安。营内皇族在盛京,有的放恣狂妄,强奸民女⑤参见赵增越《嘉庆朝宗室移住盛京档案》(下),《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第16页。;有的强横蛮霸,讹诈民人钱财⑥参见宗人府宗令永锡《题为会审盛京宗室恒玉呈控民人陈大指房租借钱打闹不还等情一案依律分别定拟请旨事》,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下简称“内阁题本”),档号02-01-07-10141-012。;有的结交收容贼匪,谋利分赃①参见盛京将军禧恩《奏为审拟宗室春林窝留贼犯刘宽接受赃物一案事》,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3956-009。。诸如此类违法事件较多,对盛京当地旗民的正常生活滋扰尤重。
第二,部分宗室营皇族干扰了盛京地方司法。在清末新政前,除宗人府、两京刑部、两京户部和盛京将军衙门之外,其他官府对满洲犯罪皇族一般无权定拟,而地方官员囿于皇族特殊身份也往往投鼠忌器,这些为皇族干预地方司法提供了制度凭恃和现实可能。宗室营建立后,其所属皇族为渔利或博取人情等在盛京插讼民事纠纷的现象较为常见。如该营宗室硕海“图酬谢,为负欠被控押追之雷家瑞讨保不遂,直入承德县署击鼓闹堂,辱骂职官”②参见盛京将军衙门《呈宗室硕海因入承德县署闹堂辱官发黑龙江到配三年案由单》,无朝年,朱批奏折,档号04-01-11-0017-020。;该营宗室妇富佳氏“以民人梁汝让控高玉赊买烟片,业经讯断完结,与该氏毫无干涉之案,包揽插讼,不待验讯,用砖砸坏大堂”③参见盛京将军玉明《奏为发遣宗室孀妇富佳氏私自外出插讼请改发吉林事》,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4576-012。。此类行为干扰了部分司法案件的正常程序,在盛京影响恶劣。
宗室营的建立虽然增加了盛京行政管理的压力,对当地社会秩序等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但从清中后期政治和文化语境中检视宗室营的历时性价值,其积极意义仍不容低估,现笔者究其荦荦之大者兹述于下:
首先,改善了部分闲散皇族的生计。高换婷认为嘉庆朝迁移宗室“是清代解决宗室生计的一次创举,是一次改革宗室人口政策的尝试”[10]95。的确,宗室营建立以后,清廷对无罪移居宗室在给予正常养赡银之外又增发“地租银”,养赡待遇实则优于京城宗室,并提供官建住房,使得很多无产业皇族免受冻馁之苦,生计得到改善。这也是有些皇族争取移居和营内发遣皇族获释后选择留居的重要原因。刘灿认为“移居宗室依赖养赡、游手好闲的积习难改,屡生事端,无法真正在故土立业”,“极渥待遇亦是极大束缚,家无恒产的宗室来到盛京依旧‘无产’”[11]103-104。笔者认为刘氏所论略带悲观,且可能与真实历史情境稍有偏差。原因在于,盛京远离统治中心,清廷对宗室营皇族谋生路径的限制远弱于京城皇族,这就为营内贫寒皇族种田务农或小本经商等提供了现实可能。如移居宗室恒吉在盛京本无祖产,其到营后“每年在团山子自力代(带)领家丁垦种零星闲荒,不成坵段,并房基些须地亩”④参见盛京户部《为请查明吞霸祖产案内正红旗宗室恒吉与宗室孀妇海富氏家有无祖遗关东家人祭田地亩等事致宗人府》,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宗人府说堂稿,档号06-01-002-000415-0043。维持家计;移居宗室恒玉在宗室营附近租赁房屋开设饭铺补贴家用⑤参见宗人府宗令永锡《题为会审盛京宗室恒玉呈控民人陈大指房租借钱打闹不还等情一案依律分别定拟请旨事》,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内阁题本,档号02-01-07-10141-012。;甚至发遣皇族亦在盛京从事商业活动,如营内发遣宗室图克坦在沈阳城内自置铺面房九十二间以出租获利⑥参见盛京将军衙门《为转饬传讯正红旗宗室孀妇佟佳氏有无接使盛京宗室营主事万顺买沈阳房屋定金等事致宗人府》,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宗人府说堂稿,档号06-01-002-000165-0002。。另外,有些京城皇族祖遗田土本在盛京由庄头等代为管理,但因两京距离阻隔,庄头等故意不按时交租或将地亩私典等情况时有发生,间接影响了京城皇族的日常生计。皇族居于宗室营,实则便于对此类土地直接经营管理。如宗室“恩福系都京宗室,自幼随其父母来至沈城宗室营居住,恩福有册地五十八日,招佃耕种”,并直接赴佃户处讨取地租。⑦参见宗人府左司《为盛京民人张保城与宗室恩福共殴赌犯胡仁身死按律定拟刑部同宗人府议奏已经奉旨行该将军正蓝旗事》,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宗人府说堂稿,档号06-01-002-000340-0110。因此,宗室营的建立客观上对其内居住之很多皇族的生计立业有积极作用。
其次,缓解了京城皇族的管理压力。清中期尤其是嘉庆朝以降,京城皇族人数猛增,很多闲散皇族生计日艰,“作奸犯科,行止污下者层见叠出”[2]卷222,992。嘉庆帝曾“叠经降旨,饬谕管理宗人府王、贝勒及族长、学长等加意教诫,并御制宗室训剀切宣示”,还“著管理宗人府王、贝勒及各族长、大员等悉心酌核,务筹一经久可行之法”[2]卷198,633-634。但以上诸多尝试皆收效甚微,京城皇族之管理成其为政困扰之一。在筹建宗室营时,嘉庆帝直言欲“将不安本分之闲散宗室酌量挑出送往”,如将此与上述历史语境相勾连,不难发现宗室营自建立起就带有缓解京城皇族管理压力的政治属性。其后,清廷定例由黑龙江、吉林释回的发遣皇族和京城屡次犯案之宗室及眷属皆永久移居宗室营。这是利用制度规定将部分屡犯罪愆之皇族永久剥离出京城,以避免此类人释回后对京城社会再生滋扰,同时也降低了京城官府对之的管理成本。在此情况下,虽偶有移居或发遣皇族因各种缘由自宗室营逃回京城,但清廷将其抓获后,仍然送回盛京,故皇族偷逃回京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小于以上制度运作对京城社会所产生的正向作用。
再次,促进了族群融合。宗室营皇族虽为移民,但其因生产生活之需,到营后多数能够较快融入当地社会之中,与该地民人的联系亦甚为密切。有的与民人成为素识好友,有的雇民人为帮工,有的租用民人铺面做生意等等。基层社会人际关系中,皇族与民人在制度规定上的身份等级差距并未成为双方日常交往的障碍。在众多关系中,皇族与民人的通婚关系颇值得注意。清制规定“凡宗室(觉罗同)不得与民人结亲,违者照违制律治罪”[7]卷31,348,但宗室营男性皇族与女性民人私下结亲的现象依然不少。如宗室玉林私娶离异民妇杨氏为妻①参见盛京将军奕兴《奏为审明移居宗室玉林外出滋事请旨惩办事》,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31-005。和宗室溥喜纳民女蔡氏为妾②参见盛京将军禧恩《奏为审拟发遣宗室溥喜在盛京配所置妾一案事》,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4003-060。等。清廷虽对结亲当事人处理严厉,但对其私生子女仍“给以红带为记,交该旗入佐领安置,一切食饷当差均照红带子之例办理,所生子女由该都统每年按季汇报”③参见宗人府宗令载铨《奏为宗室白佳氏呈请移居盛京事》,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2854-013。至宗人府,“另记清册”[12]以备稽查。即承认其皇族血脉,又有所区别,给予觉罗待遇,并入八旗管理。宗室营皇族与民人通婚之多发,实际上迫使清廷对部分制度禁止的既定族群融合事实予以承认,这客观上促进了满洲皇族与其它族群间的融合,同时也是清中后期东北不同族群间通婚历史的真实写照。
最后,推动了盛京文化发展。子弟书是一种清代说唱艺术,始创于京城八旗,其词文雅,曲声和缓。子弟书是由移居宗室自京城带至盛京,继而在东北地区传播④参见邓伟《满族文学史》第4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这在学界基本已成共识。宗室营还曾出现过文化名人,宗室裕瑞便是其中之一,其系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⑤参见张佳生《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8-183页。,因罪移居,终老于此。裕瑞在营内创作了《东行吟稿》《沈居集咏》等文集,盛京“芝兰诗社”亦是在其支持下成立⑥参见盛志梅《清代子弟书的传播特色及其俗化过程》,《满族研究》,2012年第4期,第81页。。该诗社系当地著名文学组织,对彼时盛京地方文化发展的贡献可圈可点。据口述史料,宗室营“藏书量是较大的,不仅有各种满汉文的典籍、经史,也有不少的文学书籍”[13],这些自京城运至盛京的大量图书,在文化上应对宗室营以外的盛京局域亦有濡养之效。可见,不但宗室营的建立有益于清代京旗文化在盛京乃至东北地区传播,营内学识渊博的皇族亦对盛京地方文化等发展有推动之功。
四、结语
清中期尤其是嘉庆朝以降,京城闲散皇族生计维艰和犯罪频发日益成为困扰统治者的两大难题,宗室营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刘灿认为嘉庆朝宗室移居“以筹备生计为主要目的”,同时兼有“为维护京师稳定排除‘不安定’因素的意图”[11]100,此说颇为可信。而宗室营作为安置移居宗室之所,宗室移居最初的“主要目的”也决定了该营当时的政治功能重心——解决部分京城宗室的生计问题。但道光朝以后,清廷对宗室营人口管理政策进行调整,这造成其后该营政治功能重心转向安置收容犯罪皇族及其家属。宗室营人口构成复杂多元,并始终与京城、盛京本地和吉林等处保持着多线交互流动,而多线中的主线无疑在宗室营与京城之间,且从总体上看,前者人口迁入大于迁出。如我们将视角转换,并将视域进一步扩展,结合清中后期京城皇族发遣以及圈禁制度调整等诸多因素⑦关于清中后期皇族发遣和圈禁制度调整所导致的皇族人口流动可分别参见孟繁勇《清代宗室觉罗发遣东北述略》,《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第123页;黄培《清代的高墙制度》,《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编委会:《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8-109页等。所导致的皇族人口外流,则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不至于大谬的推论:清中后期京城皇族人口迁出大于迁入是该时段皇族人口流动长期持续存在的基本样态,且其总体规模远大于清前期。宗室营所属人口分布范围在清中后期是变动的,具体表现为道光朝晚期以前仅限于营城之内,其后在该营城外居住人口逐渐增多,至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嘉庆时期旧有营城颓毁殆尽,该营人口在盛京之内流落,分布已毫无范围可言。此变动轨迹一方面展现了嘉庆朝修建的宗室营建筑实体兴衰变迁的大体脉络,另一方面更反映出宗室营作为盛京独立的皇族系统,其组织管理作用凸显和权力舒张之过程。宗室营的管理运作模式汲取了京城闲散宗室和驻防满城等管理制度的传统资源,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较为健全的职官建置,并被嵌入到盛京地域权力结构之中,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京将军及其衙门的皇族管理权力也因之进一步扩大。
宗室营是清嘉庆朝以后整个皇族管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其本质是清廷运用政权力量将京城皇族管理压力向外纾解的实现形式。该营的建立对解决部分皇族生计、缓解京城皇族管理压力、促进族群融合和推动盛京文化发展等皆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亦是以增加盛京地方行政管理成本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