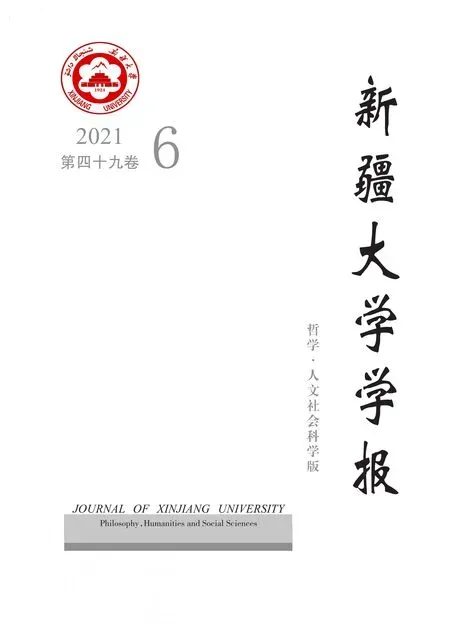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
——甘肃在清朝经营新疆中的独特地位*
邓 涛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直省与藩部的关系是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而清代甘肃地区同西北藩部地带发生了广泛且深刻的联系,其中甘肃与新疆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析。关于甘肃地区在清朝经略新疆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往有部分研究涉及①相关研究参见:汤代佳《试论甘肃在平准之战中的地位》,《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75页;刘文鹏《论清代新疆台站体系的兴衰》,《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第29页;聂红萍《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乾隆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第49页;邓涛《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宁夏地区在清朝边疆经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180页。,或涉及甘肃与新疆的行政关系,或涉及甘肃与新疆的交通联络,或涉及甘肃在清朝统一新疆中的地位,或涉及甘肃移民与新疆开发的关系。综观以往研究,尚无专文立足“直省—藩部”二元疆域结构下直省与藩部的关系,就直省甘肃在清朝经略新疆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故本文专题研究之。
一、清代二元并存疆域结构下的新疆与甘肃
乾隆朝时,清朝实现了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清朝统治区域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甘肃等行省地区,彼时“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以领诸县”[1]243。二是新疆等藩部地区,“至各边外之地,隶在舆图者,复以千万里计,四履之盛,固已超轶汉唐”[1]243。全盛时的清朝,地域广阔,涵盖了原明统治范围、蒙古、西域等地。这一广阔的统治区域,既涵盖了直省地区,也涵盖了藩部区域,体现了长城内外皆属清朝版图这一事实。清朝在直省地区主要实行督抚—布政司—府州县制,体现了中央集权前提下的权力分寄,自治权相对有限;而新疆等藩部地区,主要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等非直省体制,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关于“藩部”内涵,本文使用《清代藩部研究》一书的定义,即藩部与属国不同,广义的藩部是指同清朝建立了封藩关系的部落,含察哈尔蒙古等内属部落,狭义的藩部是专指享有自治权的外藩部落。②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页。藩部与属国存在本质性的区别,“藩部是以统一国家版图内的部落为单位,其首领同皇帝建立宗藩关系;属国则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以国王的身份与皇帝建立国家之间的宗藩关系……”[2]30-31,本文所提及的藩部为广义上的藩部,主要指蒙古、新疆、西藏等非直省区域。
(一)清代新疆是甘肃的屏藩
清人对清代新疆在保卫内地直省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十分清晰。嘉庆、道光时人沈垚曾评论新疆与直省的关系,“夫回部者,安西、关内之籓篱也”[3],在其看来,新疆是甘肃等直省地区的屏藩。从清末的西北局势看,同治十一年,清廷下谕提到:“西陲与甘省,亦属唇齿相依,关外地方绥靖,关内始能安枕。”[4]331认为只有收复嘉峪关以西包括新疆、安西在内的区域,甘肃安全才有保障。同治十三年,丁日昌上奏提到:“俄国染指新疆,联络回部,已与我甘肃、陕西之边境毗连。”[5]由于俄国侵占北疆伊犁一带,导致新疆作为甘肃屏藩地位的弱化和丧失,直省甘肃和陕西面临俄国的潜在威胁。此外,同治朝时,浩罕国侵略者阿古柏入侵新疆,亦直接威胁到了清朝的直省地带,如《西陲事略》提到如果不驱逐阿古柏势力,阿古柏“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6]3。清末维新派人士陈炽亦言:“综观大势,旷览将来,恐中国之大患仍不在水而在陆,不在东南而在西北也。”[7]他认为,东南边患主要涉及不同中国直接接壤的欧洲列强,而西北陆地,因同俄国等直接接壤,故边患更为深切,“惟陆路壤土相连,转输既便,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渐翦我羽翼,渐窥我腹心,蚕食鲸吞,胁以兵力”[7],此虽为一家之言,但亦反映了在部分时人看来,西北边疆安全更为急切,新疆地区被视为护卫甘肃等直省的羽翼。《(光绪)肃州新志》亦评价新疆哈密同甘肃的关系,“于哈密设兵驻防,以固肃、甘藩篱……”[8]。
(二)甘肃是清朝经略新疆的支点
《(乾隆)甘肃通志》评价:“甘肃疆域最广,东接关中,西控边徼,”[9]强调甘肃在清朝经略西北边疆中的地位。乾隆十九年,清朝裁甘肃巡抚,陕甘总督从西安移驻兰州,兼管巡抚之事。结合彼时的时局可知,清朝在大军云集、筹备出兵新疆时,将陕甘总督移驻更靠西北的兰州,主要是为了筹备军需和准备出兵事宜,体现了陕甘总督同新疆局势的密切联系。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后,在讨论甘肃总督驻地时,乾隆帝提到:“总督驻扎地方,关系控制西陲,事体崇重……殊不知就甘肃内地而论,则凉州固为适中。若就统驭新附各部落而言,则肃州犹为近地,而凉州则相距转遥。”[10]655在乾隆帝看来,影响甘肃总督驻地的主要因素是新疆局势,反映了甘肃一地的独特战略地位。尽管此后甘肃总督并未延续下去,但清朝依然设陕甘总督节制陕西、甘肃,并深度参与清朝在新疆的经略。此后,陕甘总督驻扎离新疆更近的肃州,直到乾隆二十九年新疆局势日趋稳定时,总督驻地才改至兰州。
清朝中后期,道光六年张格尔等叛乱势力入侵新疆南部,道光帝下谕提到:“前因甘省控制新疆,地方紧要,不可无大员镇守。”[11]72可见,甘肃地区的官员设置,同新疆局势密切相关。同治七年,丁宝桢上奏提到:“盖回部切近甘省,其归宿之地在甘。”[12]认为清朝经略新疆的根本和依托是甘肃地区。实际上,不仅仅是新疆,清朝经略甘肃周边的藩部,都离不开甘肃地区的支撑。有研究认为,甘肃是西北的中枢,在清朝经略西部边疆上地位重要①参见杨军民《边地与腹里之间乾隆朝君臣的陕甘印象》,《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7期,第59页。。
二、清代甘肃为新疆移民的主要来源
甘肃靠近新疆,具有移民新疆的地理优势。清朝统一新疆之后,鼓励甘肃民人向新疆迁移,一是为了开发新疆,解决新疆驻军的军粮供应问题;二是为了解决边内民人的谋生问题,即甘肃“缘边瘠土之民,生计未免拮据”[13]1796;三是源于新疆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利于农耕,如乌鲁木齐“其地泉甘土沃,并无旱潦之虞”[10]986。自甘肃迁移至新疆的民人,除了汉民也有回民、番民等族群,《清朝续文献通考》曾提到清末新疆的民族分布:“北路汉装回,乾隆中准部既灭,始由陕甘迁来。番,甘凉南山、青海、卫藏诸族流寓……。”[14]可见,回民和番民亦成为新疆移民的来源。结合清代甘肃及其周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而言,“番民”主要指藏民,即“西番、南番,皆吐番之遗种也”[15],但清代西北地区“番”有时也指撒拉尔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的祖先,如《(乾隆)西宁府志》记载,西宁边外“有一种番回,本系缠头,久随番俗……”[16]481,“番回”即是指撒拉尔“回众”。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相比在蒙古地区总体实行封禁政策,清廷对民人出边至新疆,总体是鼓励的。
一是在关禁上提供便利。乾隆中叶,陕甘总督文绶曾提到嘉峪关的关禁政策,“每日晨开酉闭,以便农民商贾前往关外,广辟田畴也”[17]433,鼓励民人赴关外和新疆开垦田地,以解决关外驻军和行政官员的粮食来源。同时,出关的手续也开始简化,文绶提到此前“关吏循照旧例,仍行常闭,凡有经过者,俱查验年貌,询明姓名,注册方得开关放行,不免守候稽延之累……”[17]433,因此建议,“进关者仍行盘诘,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农民”[17]434,在出关手续上予以便利。
二是官方招募民人赴新疆。如乾隆二十六年,清廷在“在甘州、肃州、安西等处招贫民四百余户,男妇大小一千五百余名口”[10]986,前往新疆屯种。清廷通过给予车辆、口食等方式,协助甘肃民人前往新疆。乾隆三十年,陕甘总督杨应琚上奏提到:“巴里坤地气日渐和燠……连前拨给安西户民承垦地,共二万五六千亩。”[13]1846新疆巴里坤地区大量土地得到了开垦。当时,“至巴里坤迤西穆垒地方,直接乌噜木齐之特讷格尔,可垦地数十万亩”[13]1866,土地开垦的空间还很大,也因此,清朝此后一直招募甘肃民人前往新疆屯田。清末同治朝时,甘肃、新疆经历了回民民变和阿古柏入侵,新疆北疆民人或死于战乱,或兴办民团以自卫,或流离失所、赴甘肃等地谋生。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景廉“请仿照成案,由甘肃各州县迁移民人一千户,分居奇、古等处,以实边地”[4]933,并官给牛具和籽种,便是希望通过移民来巩固清朝对新疆的统治。《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一书,对清朝官方组织移民赴新疆的政策十分清晰,提到清政府给予移民优待和补助,以吸引他们前往新疆。①参见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页。
男子喊道:“服务员,过来一下!”服务员:"您好,什么事?"男子怒问:"我20块钱一碗的牛肉面,怎么才一块牛肉?"服务员:"先生,那您希望有几块?"男子想了想说:"怎么也得五六块牛肉吧。"服务员冲厨房喊道:"出来个师傅,帮这位顾客把这块牛肉切一下!"
三是通过政策引导民人去新疆。相比早期官方组织移民,乾隆后期,清廷开始倾向于通过政策引导甘肃民人前往新疆。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帝下谕提到:“即如热河及张家口外各处,凡有可耕之地,山东等省民人俱不远数千里,襁负相属,以为自求口食之计,何尝官为招集耶。甘省密迩新疆,较之山东出口路程更为近便,若能详为劝谕,俾知沃壤可耕,资生甚易,足以自图宁宇,谅皆趋之如骛。俟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13]1957从此段话可知,一是乾隆帝认为移民政策应当调整,不应当由官方招募民人赴新疆,而是通过政策宣传诱导的方式,让甘肃民人知晓新疆地区实情,进而让他们自愿前往;二是乾隆帝鼓励移民新疆的目的之一便是便于以后在新疆设立郡县,将移民视为深化对新疆统治的重要措施;三是移民边外有利于解决甘肃地区的人地矛盾,改善甘肃地区的生存条件。《甘肃通史(明清卷)》一书认为,乾隆后期,清朝逐步减少了对甘肃民众前往新疆的各类补贴,“大约在乾隆五十年前后,清廷即已停止官费资送民户前往天山北路”[18]407。
随着甘肃民人的陆续前往新疆,改变了新疆特别是北疆地区的民族构成,促进了民族融合。到同治朝时,他们成为了反抗沙俄和阿古柏政权的重要力量,兴起了徐学功、孔才等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民团领袖。
三、清朝经略新疆中的甘肃行政支撑
乾隆朝统一新疆、实现大一统之后,清朝逐步在新疆地区设立流官行政体制,新疆开始在体制上同甘肃相联系。《甘肃通史(明清卷)》认为,新疆建省前,甘肃省包括乌鲁木齐的天山以北地区。②参见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一)清人对甘肃与新疆行政关系的认知
乾隆二十九年,清廷讨论增修《大清一统志》时建议新疆东部的文武官制“应即附入甘肃省内……应将西域新疆,另纂在甘肃之后”[10]1046。将新疆视为同甘肃联系紧密的行政区域和地理单元。清后期,琦善曾提到:“国朝于今西域地之东境,已设州一、厅二、县四矣,迪化州一州也,镇西厅、化平川厅二厅也,奇台县、昌吉县、阜康县、绥来县四县也……夫既设州县,不可设行省乎,即此州县不可由甘肃而改隶乎。”③参见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25卷,上海:上海书局,光绪二十八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线装书。主张将甘肃管辖的新疆府州县作为新疆建省的基础。私修史书《甘肃考略》亦将新疆建省前的迪化州、镇西厅纳入甘肃辖区之内④参见龚柴《甘肃考略》,《西北稀见丛书文献》第3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99页。。有研究认为新疆建省之前,乌鲁木齐及其东部地区在行政上隶属于甘肃省,受陕甘总督和乌鲁木齐都统的双重管辖。⑤参见杨军民《舆地与官制之合宜:雍乾时期西北边疆经略与河西走廊军政建制演变(1724一1773)》,《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68页。
刘锦棠上奏建议在新疆设省时认为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若画为两省,势难孤立”[19],即从历史的角度看,甘肃在行政体制上对新疆部分区域有管辖权;从现实的角度看,新疆独立建省缺少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主张甘肃和新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清末清朝在讨论台湾设省时,对新疆建省的情况作了比附,“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20],在时人看来,在台湾新设行省和新疆面临的问题一样,即台湾需要福建,新疆需要甘肃予以扶持和支撑。
(二)新疆在行政建制上与甘肃的一体化
乾隆二十四年,清廷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实现了大一统,当年,甘肃“安西道移驻哈密,安西同知移驻巴里坤,靖逆通判移驻哈密,俱令管理粮饷,兼办地方事务,归安西道统属”,安西道移至哈密,且归甘肃布政司管辖,标志着“道”的体制开始在新疆扎根。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在新疆设迪化厅,隶属于甘肃布政司。乾隆三十八年时,改迪化厅为迪化直隶州,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四年,清廷在新疆新设昌吉县、阜康县、绥来县,隶属于迪化州。乾隆四十二年,清朝在巴里坤设镇西府。新疆直省流官体制进一步深化,且同甘肃地区联系密切。
宣统三年,甘肃新疆巡抚袁大化上奏论及新疆改设总督事宜时提到:“然改设之后,必将离甘肃独立,又恐征兵筹饷,呼应不灵……改设新疆总督,兼管巡抚事……其甘、新两省提、镇、司、道以下各员,仍照旧兼隶甘督辖属,以示联络。既收统一之功,仍不失声援之助。”[13]4417通过此奏可知,一是新疆虽然建省已二十多年,但甘肃对新疆的后勤支撑依然十分重要,且该因素成为清朝讨论新疆如设总督、总督权责如何界定时的重要参考;二是提到“其甘、新两省提、镇、司、道以下各员,仍照旧兼隶甘督辖属”,可见虽然新疆已经建省,但是陕甘总督在名义上依然有兼辖新疆巡抚所辖府州县及绿营的权力,可见甘肃地区在行政体制上对新疆的重大影响。《甘青宁史略》亦评价甘新分省之后,“甘新地界划分而总督仍节制新疆巡抚”[21],即陕甘总督在名义上有节制新疆巡抚的权力。但总体来说,新疆巡抚并非是受到陕甘总督严格节制的地方大员。《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一书认为,新疆巡抚只是名义上受陕甘总督节制,实际上不从属于陕甘总督,只是偶尔一起上奏。①参见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7页。
(三)新疆在流官配置上依赖甘肃
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认为新疆已经统一,故“文武员弁,均应依次移补,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其哈密巴里坤以西,应需用道、府同知若干员,一半于内地事简处”[13]1519-1520。清廷从内地简任官员赴哈密,而唯一同新疆接壤的直省甘肃是首要来源地。彼时,新疆官员从甘肃调派,具有广泛性。《西域图志》记载,清朝在新疆哈喇沙尔设办理粮饷官一员,“乾隆二十四年设,用同知、通判以下,由陕西、甘肃省除派”[22]420。此外,新疆库车等地办理粮饷官员具从陕甘地区调派。即如乾隆三十四年甘肃布政使蔡鸿业所言:“新疆丞倅各缺,向例于甘肃拣员调补。”[13]1941乾隆三十八年,清廷议定:“镇西为冲、繁、难三要缺,遇有缺出,在于陕甘两省满员内拣选、调补,”[23]镇西府员缺从甘肃、陕西地区调任,但主要来自甘肃。
乾隆时,伊犁将军明瑞等人曾上奏提到:“现在伊犁挈眷官兵、跟役与商民杂处,必有词讼交渉事件,请于兵丁全到之后,设立理事同知一员,或从甘肃等处简缺裁调。”[13]1793明瑞建议从甘肃调派行政官员赴新疆,显然对甘肃地区大量行政官员被调派至新疆这一情形十分了解。此后,清朝以甘肃地方行政官员不熟悉满洲语和蒙古语为由,决定从各部院调派官员,即“各部院满洲、蒙古主事及保送头等笔帖式内,拣选发往”[13]1793。
四、甘肃是沟通内地和新疆的支点与纽带
《西域图志》记载:“按嘉峪关,本隶肃州,因为西域新疆门户,故首纪关外驻员……”[22]408认为甘肃嘉峪关是内地通往新疆的门户。有研究认为,清朝通往新疆的台站体系,包括通讯和交通两个方面。②参见刘文鹏《论清代新疆台站体系的兴衰》,《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第29页。
(一)新疆通过甘肃与内地驿站体系连为一体
甘肃是清朝内地连接新疆的交通要道,也是人员、物资的中转地,亦是清朝驿站的重要节点。乾隆朝时,甘肃交通线通过陕西与内地连为一体,“一由陕西沿边一带,自安边、靖边,入宁夏之花马池,由宁夏至凉、甘、肃;一由陕西之邠州、长武,至甘肃之泾州,由泾州至兰州,前往甘、凉、肃”[10]1055,而肃州以西,便是甘肃连接安西和新疆东部的台塘系统。清朝也因战事需要,在甘肃临时新增军塘,如乾隆十九年清朝出兵漠西蒙古之时,“因西域军务,甘省口内自肃州至宁夏之花马池,安设正、腰站七十六塘,每塘额马二十匹”[10]884。道光四年,清廷同新疆的奏折往来,皆通过军站,分南北两路,其中“西路自昌平州回龙观军站起,经由山西天镇县枳儿岭军站,陕西榆林县榆林军站,甘肃灵州花马池军站,至肃州直隶州酒泉军站,出嘉峪关”[25]。有研究认为,清代时,原明九边地区成为北部长城沿线最基础的东西交通线。①参见张萍《官方贸易主导下清代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78-89页。清末时,清朝常设的军报站主要分为两路,一路经张家口出边接阿尔泰军台,为北路,“一沿边城踰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接军塘,以达西路文报”[26]606,即内地驿站和边陲军塘在甘肃过渡和切换。彼时,亦有大臣主张清朝在“安西、哈密、镇西三属,特设军塘,以达出入嘉峪关军站文报;又别设营塘,以达寻常文报”[26]606,军塘由清廷派出绿营兵负责管理。《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清末时,清朝直省地区,“甘肃有驿、有站、有塘、有所,共三百三十一”[26]606。甘肃地区驿站最多,且类型最为丰富,显然是源于该地为内地通往新疆的交通要道。
(二)甘肃是清朝经略新疆的物资集散地和运输承载地
有研究认为甘肃是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基地,作为新疆门户,甘肃又是经略新疆的战略通道。②参见杨军民《边地与腹里之间乾隆朝君臣的陕甘印象》,《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7期,第59页。
一是大一统之前甘肃地区是清朝出兵新疆的粮草聚集地和转输地。康熙五十四年,哈密遭受漠西蒙古侵扰,甘肃地方派兵增援哈密,甘肃巡抚绰奇特地抵达肃州地方筹备前方军粮供应事宜,“查看军粮后,毫不耽延运抵”[27]1005,保证了哈密前线军需。雍正十年,雍正帝下谕提到:“甘肃地方年来预备军需……甘肃为军需总汇之区。”[16]454彼时正值清朝同漠西蒙古对峙胶着之时,可见甘肃地区是清朝西北边疆经略的后勤基地。乾隆十九年,清廷已决定征讨漠西蒙古,因此命在甘肃筹备和运输粮草,将“甘、凉、宁三府属粟米、粟谷、小麦、青稞、豌豆等项共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余石”[28]运至前线。
二是大一统之后甘肃是经略新疆的后方。乾隆五十四年,为解决新疆地区的绸缎需求,清廷命“山东、山西巡抚,江宁、苏州、杭州各织造,照数织办,接送来甘,以便分运各处备用”[29],甘肃是清朝经略新疆的物资集散地。道光六年,清廷出兵平定南疆张格尔之乱时,“征调各路官兵,并粮饷军火器械,皆由甘肃运送回疆”[11]767,体现了甘肃在清朝经略西北中的交通保障作用。清后期时,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评价到:“每年西北各省协济新疆饷银数百万,皆由甘肃转输,故藩库规制之崇宏,甲于各直省。”[30]因为甘肃在经略新疆上的重要后勤地位,故甘肃藩库规模大于它省。
同治时,骆秉章上疏提到:“查道光六年新疆南路四城之役……自兰州以至阿克苏,沿途节节设立粮台,由甘省各州县动碾仓麦,并采买民间粮糈,购备驼只转运出关,源源接济,用饷至二千余万两之多”[31],可见,清朝在平定张格尔之乱时,甘肃在后勤交通保障方面地位重要。道光时,清廷尚有足够财力和物力支撑平定新疆乱局,而同治朝时,清军“尚未出关而军饷又已告匮矣”[31]。同治朝阿古柏入侵新疆、清朝在新疆统治濒于崩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甘肃通往新疆的通道阻塞、粮道中断,援军亦无法抵达,为外敌入侵创造了条件。《西陲事略》认为,清末清朝收复新疆迟迟没有进展,主要原因是“关内未靖,饷道阻隔,累次调兵遣将,卒无成功”[6]4。
同治十一年,清廷在筹备出关进军嘉峪关以西时提到:“将来出关,数千里长途,军装器械如何运载,各州县车马如何雇觅,戈壁数十站,兵丁数千人,裹带糇粮,如何备豫,出关后军食如何设措,饷运如何疏通。”[4]331从清朝收复新疆的角度看,清朝除了在甘肃地区储备粮草,还需考虑如何保障甘肃赴新疆的交通线和后勤补给线。光绪元年,清朝着手出兵新疆之时,左宗棠提到:“哈密现有张曜全军驻扎,安西、肃州、甘州、凉州、兰州、平凉以至陕西,节节驻有防营,原因巡缉游匪兼护运而设。”[32]即左宗棠通过军队打通了从陕西经甘肃直达新疆哈密的交通路线。光绪朝清廷出兵收复新疆时,“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均用车驼,由安西运哈密、运巴里坤,均用驼只,节设厂局,浚水泉、刈草薪,以利运道”[33],可见甘肃在清朝经略新疆上的交通地位。
(三)洋务运动和新政中的甘肃至新疆通讯与交通
一是甘肃通往新疆电报线路的架设。光绪十五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上奏建议铺设西安至嘉峪关的电线,以速边报,并得到清廷批准。清廷修建经由甘肃的电线,是出于经略边疆的目的,即如李鸿章所言:“将来接至新疆,则东西万里,一律灵通。”[13]4251光绪朝时,内地经由甘肃通往新疆的电报线路成功架设,使得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经略能力增强,至迪化的电报线路成功架设①参见王希隆《论明清时期嘉峪关职能的演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0页。,形成了纵贯西北的电报干线。《甘肃通史明清卷》一书认为随着甘肃至西安、甘肃至新疆等电报线路的开通,“甘肃遂成为西北的通讯枢纽”[18]337。
二是甘肃通往新疆铁路的谋划。薛福成在“请试办开铁路疏”中提到:“顾论甘省之力,固万不能有铁路,而论甘省之势,则又万不可无铁路……然使新疆以西俄人永无铁路,则势相均、力相敌,尚可以高枕无忧,如其一无一有,则有铁路者胜乎,无铁路者胜乎。”②参见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第90卷,上海:上海宝善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七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线装书。在薛福成看来,甘肃地区确实无修筑铁路的实力,但从清朝经略西北、保卫新疆的角度看,甘肃地区必须有铁路,做此论断,是基于甘肃为内地通往新疆通衢这一交通地位。清末时人李经邦在“防海防陆难易缓急论”中提到了甘肃在清朝经略新疆上的重要交通地位,他认为俄国铁路逐渐向东延伸,出兵南疆相比清朝从嘉峪关调兵更快,“一旦新疆有事,华兵虽强,迟不敌速,胜负利钝之机,不待交馁而已见,当由嘉峪关造一铁路,至吐鲁番,以吐鲁番为总汇,分为两支……”[34],其建议修由甘肃通往新疆的铁路,源于经略新疆的需要。
宣统朝时,陕甘总督长庚在建议修建通往新疆的铁路时提到:“臣与新疆抚臣陶模会奏边防事宜,曾有展筑铁路之议,迄今二十年,”[13]4408即是将修建铁路作为经略新疆的措施。就清朝修建铁路的动机而言,“铁路性质,约分为二,内地则计懋迁,边地则重征调”[13]4408,即在腹地修建铁路主要是为了贸易这一经济因素,而在新疆等边地修建铁路主要是为了便于运输人和物,巩固边疆。尽管甘肃通往新疆的铁路在清代时并未实现,但反映了时人对甘肃交通地位的认知和关注。
五、甘肃军事力量是统一和稳定新疆的重要依托
总体来说,清朝在统一和稳定新疆的过程中,满洲兵、蒙古兵、索伦兵、绿营兵等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绿营兵主要来自甘肃,这源于甘肃同新疆地理相连。甘肃绿营在清朝应对漠西蒙古的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廷统一新疆之后,甘肃绿营也是清朝稳定新疆的依靠。
(一)甘肃绿营是清朝统一和保卫新疆的重要力量
甘肃绿营参与了清朝西北边疆的诸多战事,在某些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康熙三十五年,清军分北路和西路两路进剿噶尔丹,其中“绿旗率则振武将军孙思克,总兵官宁夏王化行、凉州董大成、肃州潘玉龙各选所属副、参等将校以从”[35],甘肃绿营在出兵漠西蒙古的军队中占有相当比例。当年,甘肃绿营占重要比例的清军西路军,在昭莫多截击西逃的噶尔丹军并大获全胜。康熙五十四年,漠西蒙古侵扰哈密,为应对漠西蒙古对哈密的威胁,甘肃巡抚“立即咨文命肃州总兵官率官兵急速出边前往”[27]1001,保卫哈密。康熙五十四年的哈密之役,甘肃绿营游击潘之善,“以兵二百败厄鲁特数千于哈密”[36],被誉为清前期绿营的重要战功。潘之善率领甘肃绿营兵以少胜多,击败漠西蒙古军,极大地提振了清军士气。雍正八年十二月,清朝筹备出兵漠西蒙古时,雍正帝提到:“再拨凉州绿旗兵一千名,令山西太原总兵王绪级驰驿前往带领赴肃……固原提标兵丁或拨一千名或二千名。”[37]甘肃绿营是雍正朝西征西路军的重要兵力来源。
乾隆十六年九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在奏折中提到:“查甘、凉、肃原定战兵共一万三千名,除派防哈密兵一千五百名外,仍该战兵一万一千五百名,此内尽马。摘拨开警,先行出口派定之兵,计甘提标二千一百名,肃州镇二千名,凉州镇一千九百名,共六千名。系首先应师,不容刻缓。”[38]由此可见,甘肃绿营随时警备,一旦口外哈密等遭到漠西蒙古威胁,甘肃绿营随时出边迎敌。乾隆十九年五月,清廷计划调拨兵力分北路和西路统一新疆,其中北路军三万、西路军两万。北路军和西路军中,有“甘肃各营、安西绿旗兵一万”[10]1027,体现了甘肃绿营在清朝统一新疆之战中的地位。
道光六年,南疆张格尔之乱时,甘肃提督齐慎所领甘肃绿营,“赶赴阿克苏,合之前有官兵,尽可藉资防守”[13]2787,甘肃绿营是清朝稳定南疆局势的依托。同治三年,新疆陷入动乱“情形极为吃紧,边疆重地,亟应及早廓清,惟该处向来用兵,必须内地筹调大支劲旅”[39]。清朝应对新疆局势,离不开直省内地特别是甘肃绿营的帮助。
(二)甘肃绿营有轮戍新疆之责
《绿营兵志》提到清廷在部分边疆地区实行轮流驻防制度,“如新疆南北各城以陕、甘兵去屯戍……”[40],在新疆屯戍的绿营大多来自甘肃地区。
一是戍守新疆北部。乾隆二十九年三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在奏折中提到:“伊犁应驻绿营屯差兵一千二百名,前经工部尚书阿桂等奏明,分作两次换班。除上年已换兵六百名并情愿再驻一班之二名外,计本年应换兵五百九十八名。”[41]可见甘肃绿营有轮流赴新疆驻防之责。乾隆三十七年,清廷计划从陕甘调拨绿营前往新疆参与筑城,清廷提到“若于陕、甘各营匀派未免稽迟,酌于就近甘州、肃州、宁夏三提标营,每处派精壮兵五百兵……统率前往”[10]30。甘肃绿旗兵参与了新疆的城池建设。清末时,甘肃绿营依然有轮戍新疆北部的职责,如光绪三年,清廷下谕提到:“塔尔巴哈台驻防官兵,向由甘肃调拨。”[42]725
二是戍守南疆。乾隆四十七年,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等人上奏,“本年十月,甘肃凉州兵丁五年期满,应行更换,宁夏、固原兵丁亦于明年正月期满……”[10]439,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初,甘肃绿营即有赴南疆轮戍的职责。道光八年,清廷平定张格尔之乱后,“喀什噶尔新设总兵,着将甘肃凉州镇总兵一缺,改为该处换防总兵”[13]2953-2954,体现了甘肃绿营在清朝经略南疆上的重要地位。随着清朝绿营体制在北疆的扎根,北疆绿营兵开始转变为永驻携眷兵,而南疆依然保持了轮戍的体制。咸丰朝之前,南疆的绿营兵依然从甘肃绿营抽调轮换;咸丰朝之后,南疆绿营开始从北疆绿营抽调,“将陕甘两省调往口外换防官兵,自本年为始,概行停止。其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八城应设防兵,即由伊犁、乌噜木齐绿营内如数酌拨……一律定为五年更换”[43]。光绪朝清军收复新疆之后,南疆地区的驻军依然来自甘肃,“由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派兵驻守,保固门户”[44],董福祥所率领的甘军是清朝稳定南疆的依托,体现了甘肃军事力量与新疆的密切联系。
六、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知,基于清朝“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清朝在经略新疆时,直省甘肃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甘肃地区向新疆持续移民,开发了新疆,促进了府州县流官体制在新疆的落地,亦促进了新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和交流。随着府州县体制在新疆逐步生根,甘肃一地在行政管理、官员配备上同新疆联系密切,以至于清代诸多时人将新疆东部视为甘肃所属。甘肃地区亦是内地连接新疆的支点和纽带,清朝在甘肃至新疆一线建立了通畅的交通线,为清朝统一和稳定新疆提供了保障。清末时清朝谋划甘肃至新疆的电线和铁路,亦是出于经略新疆的需要。此外,清朝在统一和稳定新疆的过程中有满洲、蒙古、绿营等不同军事力量的参与,其中甘肃绿营是重要组成部分。从康熙朝时参与对漠西蒙古的反击,到乾隆朝对漠西蒙古的大一统,再到清朝在新疆驻军,甘肃绿营皆发挥了较大作用。通过分析直省甘肃在清朝经略新疆中的作用和地位可知,清朝实现大一统以及对藩部地区的稳固统治,离不开直省地区的全面支撑,反映了大一统政权下直省和藩部之间密不可分,即如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所言:“新疆之与甘肃,形同唇齿。”[2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