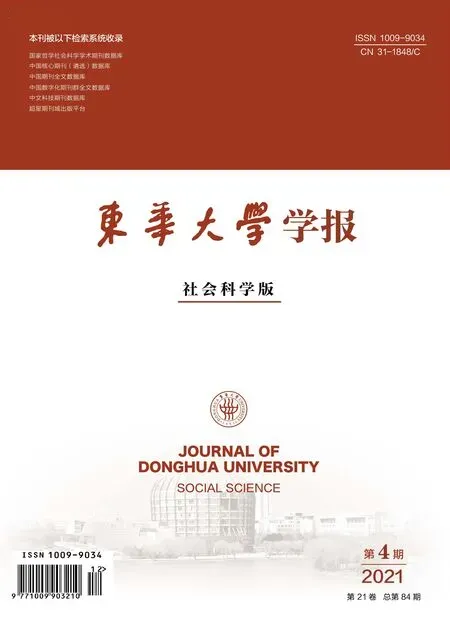交流互鉴: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李国娟 周 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418
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识,更是文明发展的尺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468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只有善于通过文化交流互鉴促进自身文化发展并实现文化发扬光大者,才能不断铸就高度的文化自信。这是因为,文化自信必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它必须经历文化的自我塑形、自我发现、自我确信等环节,这些环节的形成都离不开与其它文化的比较、对照、交流、融合与借鉴。换句话说,交流互鉴是贯穿在文化自信形成过程始终的。没有交流互鉴,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
一、在交流互鉴中实现文化塑形
众所周知,任何文化体都有其区别于他者的特质,文化体在自身演进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体质的过程,也可称之为文化塑形的过程。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化塑形是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借鉴的过程,并且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就拿中华文化来讲,她就是众多的微小文化体在不断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整体。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模式,严文明花心与花瓣之喻,张光直的“中国互相作用圈”等理论都能说明这个问题。[2]最耳熟能详的理论,莫过于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说。
中华文化在融合形成前,文化体众多,差异也相当之巨大,但是中华民族自古信奉“和而不同”原则,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始终推动文化融合发展。新石器时代黄河沿岸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长江沿岸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后来融合成了早期华夏文化;老子、屈原本是楚人,后来融入了汉文化;南北朝时,北方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主的少数民族国家,易儒服,改汉姓,最后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大唐盛世,儒、道、释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可以说,没有文化体间的彼此交流融合,赓续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不可能形成的。
不仅中华文化整体形成是交流互鉴的结果,若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即使区域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交流互鉴。比如广东地方文化的形成,按照《广东通志·风俗篇》记载,粤人受中原移民“风流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气渐变,而俗庶几中州”。1906年,清廷为激发爱乡爱土之情,鼓励地方修“乡土教科书”,其中《广东乡土史教科书》说:“南宋时,中原人避乱,多迁居南雄珠玑巷,故粤人多中国种。”广东是古来百越之地,原住民族为“瑶、僮、平鬃、狼、黎、歧、蛋诸族是也”。[3]至今,广东人的种族构成主要以粤人、潮人与客家人为主。可以推知,今日的广东文化如此具有活力,与这些更微小的文化体之间的交融是不可分割的。[4]
放眼世界,中华文化的塑形和形成,不仅是原有内部各区域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与许多外部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结果,“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1]417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一直崇尚开放与包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不仅发明创造并向西方国家传去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而且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其优势物产如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产的姜、黄连、大黄、白铜等甚至取代了其他国家对同类物产的生产与使用。同时,中华文化还始终以宽广的胸襟吸收借鉴各种文化,展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之路。丝绸之路、敦煌石窟以及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都是文化交流、文明借鉴的历史见证。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来自其他文明,比如苜蓿,发源于古波斯国。晋代时,中国用苜蓿作马的饲料。《西京杂记》记载:“乐游苑中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宋代有诗曰“苜蓿枯时霜雪深”“苜蓿堆盘莫笑贫”“未厌堆盘苜蓿餐”,苜蓿在中国早就是普遍而又廉价的东西了。此外,葡萄是出自亚洲西部与埃及的植物,由张骞引入中国;胡桃生产于地中海与波斯北部,汉代上林苑里已有种植;茉莉花原产波斯,《南方草木状》称其为“耶悉茗花”,而其波斯语正读作ysamīn;胡椒、甘蔗、菠菜、蓖麻、无花果、水仙、西瓜等也是外来植物。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不少日用植物都是从西亚传入的,而且扎根中国的历史极为悠久。[5]
当一个文化体的独特物产被另一个文化体吸收时,其对应的语言也会被吸纳,从而丰富另一个文化体的语言。比如苜蓿的古波斯语读作buksuk或buxsux,汉语早期写作“目宿”,藏语读作bug-sug。据阿布·满速儿的名著《波斯药物学》记载,大量的古波斯药物来自印度,于是波斯语中吸收了许多梵语,比如sur(“米酒”),来自梵语sur;turunj(“香橼”),来自梵语mtulunga;pipal(“长胡椒”),来自梵语pippalī;bang(“大麻籽制麻醉剂”),来自梵语bhang;dand/dend/dund(“巴豆”),出自梵语dantī;等等。毫无疑问,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犍陀罗文明影响了欧洲与新疆地区的造像艺术;印度的佛教推动了中国的形而上学;中国的道教推进了日本的神道教。可见,文化体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早期文化塑形的最直接动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417可以说,文明的塑形离不开交流互鉴,所有文明形式概莫能外。
二、在交流互鉴中实现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意即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发展趋势。[6]俞吾金先生进一步指出,“文化自觉”应具备“元批判”(meta-criticism)精神,即“自觉地反思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身的有限性及其适用范围”[7]。这是因为,文化的自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启发,需要对自身有基本的发现。文化是人的文化,或者说文化就是人本身,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必须通过对象化才能认识自己、认同自己,文化亦然。通过文化交流互鉴,借助文化他者的存在,本民族能够更为科学、理性、全面地认识自身文化,正确地对待自身文化。
回顾中华文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反观自身,对自身限度有所自觉的例子俯拾皆是。春秋时代,赵武灵王在与游牧民族的交互过程中意识到中原民族的军事弱点,于是作出胡服骑射的决定;魏晋南北朝,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意识到专有名词亟需本土化,于是大量吸收道家哲学概念;唐宋以降,三教互相激荡,儒家发现自身形而上学理论严重不足,于是自觉援道入儒,终成独尊之势;晚明时代,欧洲科技涌入,开明士大夫如徐光启者积极学习西方历算,改进了东方历法,弥补了传统的不足。然而,以上种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尚不是触及灵魂的。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可谓更宽泛意义上的交流互鉴,引起了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但由于其具有被动性,于是,在中国人自我反思的初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导致对待传统文化两条错误路线的出现:一条是盲目自大,其代表是“西学中源说”;另一条是彻底绝望,其代表是“汉字拉丁化”“全盘否定说”等。
知识分子中较理性者如梁启超,则携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一行七人主动前往欧洲一探究竟。结果遇到一名美国记者赛蒙氏,他告诉梁启超:“西方文明已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8]22虽得此结论,但梁氏心里仍清楚,当时的欧洲深陷一战泥淖,悲观情绪遍地,可欧洲文明并非真的破产了。但此后,中国人开始认真反思本民族文化,在比较中发现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与不足、价值与边界。如经历欧洲之行后,梁启超就发现,欧洲的今世文明不同于古罗马、古希腊,“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一言以蔽之,万事万物,都是‘群众化’”,他们思想解放,尊重个性,“自然会引出第二个时代来”[8]23。经过比较,他认定,“中国不亡”。因为欧洲的艰巨不比中国少,而欧洲的人力却远不及中国,且中国在激发民智上亦有足够的思想资源。
后来学者们又发现,原来《易经》在1658年时就被传教士卫匡国引入欧洲,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夫则特别重视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年)于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德国哲学家康德,因其思想与中国哲学具有内在关联,被尼采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概念主要来自魁奈的“放任自由”(laiiez-faire)一词。“laiiez-faire”一词是当时新造的法语词汇,而这一词汇则是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希卢艾特为了翻译《论语·卫灵公》中“无为而治”一词创造的。魁奈热衷于中国传统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儒家)”等。中国学者由此不断地发现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与价值,以及她对世界的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文化的不足也不断被有良知的学者揭示出来,比如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极其顽固[9]2,儒学讲名教是异化了人的本质[10],这都是经过文化比较以后得出的客观结论。所以,文化的自我发现是需要条件的,意即必须在文化他者之中找到自己,认清自己,交流互鉴是根本方法。
今天,在日益深化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的强大凝聚力、顽强生命力和独特吸引力。正是这些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才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同样在交流互鉴中,我们更好地发现了古老文明的现代价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古人智慧,可以为克服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价值借鉴。“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可以为现代社会解决不同利益争端、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价值启示。这些认识,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增添了强大底气,可以说,在交流互鉴中确立的文化自信是更为坚定的文化自信。
三、在交流互鉴中实现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2纵观人类历史,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任何一种文化,从形成到发展,从自觉到自信,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人的全部特性,“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11]51,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中[11]41,“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这一理论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同样适用于文化的交流互鉴。文化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互鉴,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知、认同和确信,而这些文化意识的确立,则是通往文化自信的必经之路。
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得以不断发展进步。合作共赢是文化交流互鉴的核心价值。人类交往首先以物质交往为重,借助于优势物质的交流互助,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精神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于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成为了实现共同繁荣的关键环节。1998年,伊朗总统哈塔米(Khatami)向联合国建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此后,有意识的文明对话活动逐渐频繁起来。
对话,必有前提与原则,不是自说自话,亦非各行其是。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倡议者斯维德勒教授提出了“对话的—批判性的”深层对话模式[12]。他认为对话的前提应是,所有关于实在的,包括终极实在的断言,都是被意识了有限性的存在。基于此,对话须确证两个基本原则,即向不同思想的人开放,以及追求自我改变。其实,斯维德勒关于深层对话的前提与原则,许多学者在各种角度上亦有过发挥。杜维明先生指出:“文明对话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它承认平等和差别。没有平等,交流就缺乏共同继承;没有差别,那就没有必要交流。”[13]杜维明先生是最早一批呼吁文明对话的学者之一,他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和实共生。实践一再证明,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的前提下,开展平等对话,开展文化交流,必然赋予文化发展以强大动力。任继愈先生说:“文化发展,是不同地区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停滞不动的文化,既不融合也不分化的文化,是考古的对象,不是活着的文化。”[9]51文化要保持鲜活,就必须不断自我更新,文明对话就是吸收养分、共同成长的关键一步。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了四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1]468-470这四点原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仅为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提供了遵循,更为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实现自我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指南。
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得以日益凸显自身价值。一个文化体只有在更大的共同体中发挥出积极影响力之后,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信。这是因为,值得一个人自信的,往往不在于他实力上的相对优势,而在于他在社群中承担的责任与作出的贡献。主体如果只是被给予的存在,脱离对对象世界的责任与贡献,那么所谓的自信,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自娱自乐。文化亦然。在文化的自我塑形、自我发现的基础上,只有进一步承担起维护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责任并作出贡献,其文化之自信才可能真正养成。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丰富的合力共赢的价值观。《国语》提出五行思想,虽主张五种基本元素,但五种元素却是以生克的方式构成一个系统,以整体呈现出来,强调了和而不同;《周易》推举阴阳思想,虽主张阴阳两种元素,但两种元素仍是以消长变化的方式构成一个系统,以整体呈现;北宋的《西铭》,将万物融于一体,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整体;二程提出“理一分殊”,强调“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明代王守仁倡导“致良知”,提出“一体之仁”;晚明虞淳熙作《全孝图》,提出“一体之孝”;孙中山先生呼告“天下为公”;毛泽东主席倡议“环球同此凉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古至今,中华文化对于推动天下一体、多元共存、合力共赢的努力从未止息。这一传承千年的思想文化,正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所以,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应该自信,因为我们创造了价值。
更值得强调的是,伴随着文化自信的确立,文明的交流互鉴必将被赋予更为坚实的底气。杜维明先生带着中华文化之自信,代表儒家文化投身“对话的文明”之构建;池田大作先生秉持佛教文化之自信,创立国际创价学会倡导“和平文化”等。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重塑了文化自信,在人类文明对话的舞台上,在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潮流中,倡导者和引领者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9年5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其中一个典范。其目的就是倡导文化交流,促进深度对话,避免文明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起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地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愿同各国加强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愿同各国一起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1]469-470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亚洲文明大会只是一个契机,但它所引领的今后的对话必将是深入的、全方位的、造福全人类的。“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1]471
质言之,交流互鉴在文化的塑形、文化的自觉、与文明间的合力共赢中一以贯之,最终促成文化自信的实现与增强。文化自信的增强,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文明间的深度交流、广泛和解,直至促成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