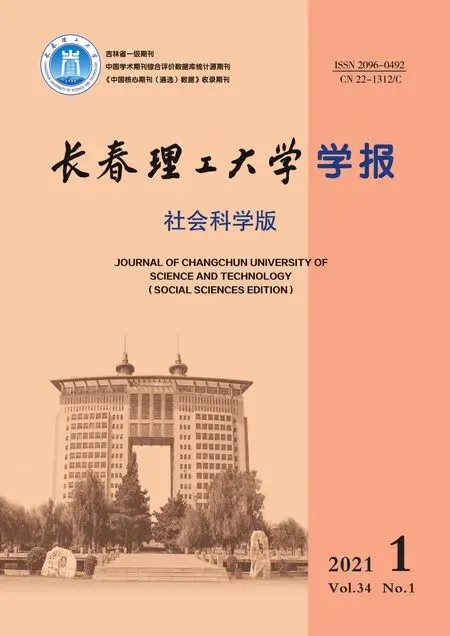朱熹《春秋》学价值发微
庄 丹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漳州,363000)
周予同先生在论述朱熹《春秋》学时,认为“朱熹之于《春秋》,固尝有志而末逮焉。故以经学论,朱熹之在《春秋》学史上,实无地位之可言。然朱熹怀疑之见,为治《春秋》者去一障蔽,亦自有其相当之价值。”[1]周予同先生指出朱熹没有直接的《春秋》注疏著作的历史事实,当代的春秋学史如赵伯雄《春秋学史》、戴维《春秋学史》等也都未提及朱熹《春秋》学价值,似乎仅认同了其“实无地位”之说。在朱熹经学研究中,相对于朱熹《诗经》学、《礼》学、《易》学、《四书》学等经学的研究而言,朱熹的《春秋》学研究极为薄弱,现已发表的论文多从史学角度兼及研究朱熹的《春秋》学。
然朱熹《春秋》学在其经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开创的义理史学、纲目学在后世也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对中国整个经学体系思想创新及中国文化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要全面研究朱熹的经学价值及其学术成就,就必须深入研究其《春秋》学思想。
一、朱熹《春秋》学与经学思想变革
朱熹自幼即学习《春秋》一经,其父亲朱松特别重视《春秋》,认为《春秋》经是君臣父子与大伦大法的代表,可以通过采《春秋》之义例以阐发春秋大义。朱熹《书临漳所刊四经后》载:“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以故未尝敢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2]朱熹年幼即听从父亲研习《春秋》经,并能“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虽然“终不能自信于心”,但这从小培养的对《春秋》经的怀疑精神铸就了其在中国经学体系中的伟大成就,故认识朱熹《春秋》学在其经学思想变革渊源上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春秋》学思想在淳熙十三年还经历了转变①淳熙十三年为朱熹经学、理学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陈来先生即指出:“总起来看,淳熙最后十年是朱熹理气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参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从原来以《春秋》笔法为撰述义例,而最终则又改变为重天理而据史实的编纂思想”[3],这也为其后坚定“于事见义”之《春秋》学打下了基础,奠定了后世《春秋》学“属辞比事”研究的本旨大道。
朱熹《春秋》学在其经学思想乃至中国经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其与《春秋》的渊源上,更体现在终其一生的对《春秋》学的探索上。因现代学科分科研究所限等原因,朱熹的《春秋》学研究一直多处于史学接受的视域;也因为朱熹有将《春秋》作为史书来读的观点,当代研究者多仅关注朱熹《春秋》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甚至将朱熹《春秋》学单纯视为史学。据朱熹《朱子语类》载:“春秋一经,从前不敢容易令学者看,今恐亦可渐读正经及三传。且当看史功夫,未要便穿凿说褒贬道理。”[4]“曰:‘《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5]2836需要注意的是,朱熹在这里是强调孔子据史实而笔削《春秋》,明其大义于史事当中。读《春秋》经可当史书看,明其大义而不穿凿附会。但并不是将《春秋》经视为史,其对《春秋》经的地位并无怀疑与动摇。综合朱熹一生总体对《春秋》的认识,事实上,直到晚年朱熹的临漳四经本中,《春秋》还是作为经的地位显示的②朱熹思想成熟在漳州,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其于绍熙元年十月正式刻印“四经”与十二月刻印“四子”。临漳“四经”“四子”是在经学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四书五经本子。其中“四经”本具体包括《易》《尚书》《诗经》《春秋》;“四子”本则具体包括《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是一个经传相分的名副其实的经学本子,正体现了朱熹经传相分、就经解经的新的经学原则。”(参束景南著《朱熹研究》)临漳“四经”“四子”本是朱熹理学新思想的象征,与汉唐古典经学相对立,体现了其经传相分、就经解经的诠释原则。可以说在漳州,朱熹就是以刊印“四经”“四子”本为载体,使朱子学作为一种新的理学文化而广泛传播。。故在朱熹思想体系中,虽然其赞同将《春秋》当做史看,且不认同《春秋》一字都寓褒贬,但关键是其仍将《春秋》视为经而非史的。因此,我们在认识朱熹《春秋》学之价值时,不仅要从史学的角度出发,也更要结合经学的视域综合研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认识朱熹《春秋》学在其经学思想变革之伟大意义,并客观评价其《春秋》学价值。
二、理学视域下的《春秋》学
以义理解《春秋》经,是朱熹《春秋》学的基本特征。《朱子语类》云:“今理会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亦有唤做是而未尽善者,亦有谓之不是而彼善于此者。……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5]2841,2842朱熹认为义理是评判《春秋》史事之是非的前提标准,凡符合义理的才为是,不符合义理的即为非,鲜明体现了其理学《春秋》学的时代特征。
“经、史、理三者在朱熹的《春秋》学思想里,是相互贯通的,这也是他《春秋》学的一个特点。”[6]470朱熹一再强调将理、经、史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探求《春秋》大义,破解疑难。《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云:“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5]2836这里同样强调必须先研穷义理,义理明后,方可遍通《春秋》等经③蔡方鹿先生曾总结朱熹的义理解经之特征曰:“朱熹以义理解经,阐发义理是其治经学的最高目标,这不仅体现在他以‘四书’学作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而且表现在他把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相结合,朱熹以义理思想为指导,从事解经治经,既超越传注,直探经文之本义,又在通经典基础上,重在阐发义理,而当本义与义理发生矛盾时,则以阐发义理为主,这表现在他不仅增传文以说理,而且删减经传文字,以义理释之;甚至引用伪托之书,以阐发圣人相传之心法。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朱熹以阐发义理为其治经之最高目标的思想。”参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朱熹《春秋》学也从义理出发,对《春秋》三传做了比较与评判。《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载:“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5]2840“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於道理上便差;经学者於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如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5]2841朱熹认为《左传》考事颇精,只是不明《春秋》大义;《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并从义理标准出发,具体分析了《公》《谷》二传的优劣处:其认为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左传》记事为优,义理却差;《公》《谷》考事较疏,义理却精。这些《春秋》学基本思想客观上都促进了《春秋》学的健康发展。
朱熹不仅坚持以理学标准评判了《春秋》三传,还对同时代的《春秋》学代表学者如胡安国、吕祖谦等都做了相应的评价。如对胡安国《春秋》学中符合义理之处给予充分肯定:“《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5]2840;“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5]2845而对吕祖谦重视《左传》学的《春秋》学思想则给予了批评:“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5]2838,2839朱熹在这里即从理学高度出发,以《春秋》大义批评趋利避害的《左传》功利主义价值观。其推崇《论语》《孟子》,认为《论语》《孟子》合于圣人本义,而若以《左传》价值观为导向,则那些为国家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士则得不到应有之肯定。总之,朱熹不仅总结了《春秋》三传研究之基本门径,而且对于同时代代表的胡安国、吕祖谦之《春秋》学都予以批判性总结,这都是其《春秋》学思想不容忽视的价值①后世对理学《春秋》学的弊端批判较多,如认为其从先验的理出发,违背了《春秋》据实而书的基本史学精神;特别是因其被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加以利用而放大了负面因素,且加上历史上对于“理学”违背人性的历史批判等原因,义理《春秋》学更是存在被全盘否定的历史境遇。事实上,理学《春秋》学也是有其优点的,若没有先树立正确的价值评判体系,则实会造成朱熹所言“一代史册被他糊涂,万世何以取信”之后果;而且从学术角度出发来评价,也应吸收其优势之处。也有学者认为:“朱熹要求史著中贯穿义理,实际是从哲学、政治理想高度来统帅编纂史书,这比他的前人与同辈的见解都深刻得多。”参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在朱熹极力倡导以义理解《春秋》、总结义理《春秋》的时代过程中,其不但促使《春秋》经解学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且上承程颐《春秋》学思想,体现了以义理解《春秋》的宋代《春秋》学的典型特征。故对于朱熹理学特征的《春秋》学价值我们也应还其客观的历史地位②相比较于《易》学哲学研究成果,当前极其缺乏《春秋》学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一点不仅反映出哲学视角研究《春秋》学的问题,也说明了对朱熹等代表人物《春秋》学价值研究的不足。在《春秋》哲学的建构上,事实上朱熹的义理《春秋》学就是《春秋》哲学的典范。。
三、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与春秋大义
朱熹虽没有专门的《春秋》学著作,但其不仅在《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中保留了大量论述《春秋》的观点,而且更是创造性地亲撰了得春秋大义的《资治通鉴纲目》。朝鲜柳义孙《纲目训义》即云:“朱文公《纲目》祖《春秋》之笔,其文则史,而义则经也。”朱熹不仅不妄自揣度春秋大义,而且通过《资治通鉴纲目》来阐释其《春秋》学思想,体现出其《春秋》学的践行精神。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实得《春秋》学“于事见义”之精义,也开启了后世学者从“属辞比事”一脉研究及践行《春秋》学的正确道路①后世通鉴学、纲目学之蔚为大观,实离不开朱熹《春秋》学思想的变革与创造。《资治通鉴纲目》在明清时期的影响力事实上超过《资治通鉴》本身,明朝时人将通鉴与纲目合抄在一起,并以“纲鉴”名之;同时还将《资治通鉴纲目》与“四书五经”同列,“颁之学宫,令士子诵习”。清代的康熙帝有《御批通鉴纲目》,乾隆帝也有《御批通鉴辑览》等亲笔评点著作。客观地说,“朱熹的《通鉴纲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通鉴学的发展方向,并对元明清三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左桂秋《明代通鉴学研究》。。朱熹在撰写《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再说明其创作根本旨意:“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7],这里特别阐释了《纲目》的创作是上述《春秋》道统的,是《春秋》学在具体事件中践行的典型表现,体现了《春秋》学“于事见义”之精义。
朱熹强调《春秋》据事直书,反对以一字一义之书法义例理解《春秋》,并且对《春秋》经中的书法义例作出了自己的阐释②宋代以前的《春秋》学学者多认为孔子是以一定的规范笔削史料而成《春秋》的。他们认为孔子所依据的规范就是“例”,后人只有通过“例”才可能探求《春秋》大义。也正基于此,《春秋》三传建构了不同的诠释体系:《左传》的“正例”“变例”;《公羊传》的名物考证、文字训诂及“三科”“九旨”;《谷梁传》的“时、月、日例”。顾颉刚先生对此曾专门批评:“《春秋》原不过记其事而已,而《公》《谷》存如许褒贬于其中,向璧虚造而已。”参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其《朱子语类》云:“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5]2831,2832“《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5]2832“《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5]2835朱熹明确反对《春秋》经书法义例的观点,认为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非“一字上定褒贬”。
“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5]2833“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5]2836“如他经尚是就文义上说,最是《春秋》,不成说话,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说得不成模样。”朱熹坚信后世人们“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也就不可能以一字一义的书法义例来探求春秋的言外之意;如片面机械式地强求,只会造成“诸说之太烦”“前后抵牾”之“说得不成模样”的后果。
而在探求《春秋》大义上,朱熹特别强调通过“于事求义”的方法。《朱子语类》云:“叔器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5]2837“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5]2833在《春秋》三传中,朱子更看重《左传》③明朝状元商辂曾谓:“《纲目》实史中之经也。”笔者以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实与《左传》相通,在“于事求义”上得《春秋》大义。朱熹自谓《纲目》的创作特点是“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故《通鉴》得《春秋》《左传》之正统,而《纲目》也得《春秋》《左传》之正义。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曾指出:“《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从某种角度上说,朱熹《纲目》与司马光《资治通鉴》一样得《左传》精义,并通过“据事直书”之“于事见义”而得春秋大义。,究其内在原因即在于《左传》是以通过记史事来探求《春秋》大义。相比于《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可谓得《春秋》“于事见义”的最典型的代表作,也取得了经的地位。朱熹从读《左传》法之“事理、事情、事势”,认为应该通过对事件的把握,以体悟时势和明了治乱兴衰之事理,强调《春秋》学“于事见义”之本义,可谓得《春秋》大义。
《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8]《春秋》经著作之旨,本是聚连文辞,比次事实。“‘比事’就是要对《春秋》的辞、事、义做细致的分析;‘属辞’就是要在‘比事’的基础上,对《春秋》的辞、事、义前后贯通,进行全面综合的把握。”[9]客观地说,朱熹通过《资治通鉴纲目》“于事见义”的生发,对《春秋》学本旨的理解与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后世《春秋》学学者如家铉翁、吴澄、程端学、赵汸、毛奇龄等沿着朱熹“于事见义”的治学门径上在“属辞比事”的大道不断生发,终得《春秋》学之本义。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于事见义的生发,不仅对《春秋》学本旨的理解与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而且是真正能践行于世的。从朱熹《春秋》学践行效果来看,黄道周之践行即是最典型例子。据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载:“青原公以事至会城,置《通鉴纲目》,躬负以归,手为点定。先生昕夕研阅,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10]黄道周父亲在黄道周七岁时即授之以朱熹所著《资治通鉴纲目》,且是“躬负以归,手为点定”,可谓虔诚之至;而黄道周更是朝夕研读,于事辨义。后黄道周抗清死节,在刑场上以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且历史性地被其以死明志的异朝之清乾隆皇帝誉为“一代完人”,可谓是真正践行了春秋大义并终得以名垂青史的典范。
四、结语
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推崇朱熹云:“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从朱熹经学整体研究看,朱熹《春秋》学研究属于最边缘、最薄弱的环节。但朱熹《春秋》学不仅是其经学思想渊源、经学思想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在义理《春秋》学的创造上,在通过《资治通鉴纲目》“于事见义”的探求上,都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在撰写《春秋》学史的历史进程中,也应还朱熹《春秋》学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
“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科举、文学、史学、宗教、文献学、文字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因而,朱熹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6]565在朱熹经学体系中,其《春秋》学思想受人非议最多,也是其唯一没有集注的经书。事实上,朱熹《春秋》学思想实得春秋大义,元代著名的“儒林四杰”代表揭傒斯即云:“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朱熹自幼即与《春秋》学结缘,且谓“《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朱熹《春秋》学思想的“隔三重四重说”之价值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挖掘与研究。
——有关群文阅读教学法的实践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