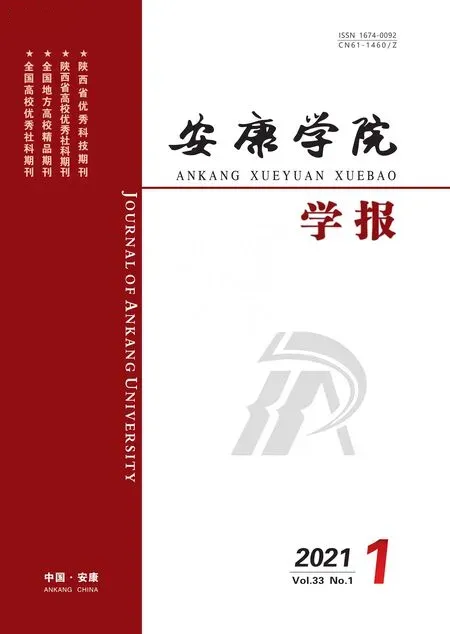从灰姑娘到珂赛特
——论《悲惨世界》的童话属性
龚东风
(温州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一、神奇故事的互文关系
互文性涉及多个历史文本之间的相似性问题,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传统是一个历时的链条,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新文本,文化遗产为后人共享,前文本会对后文本产生扩散性影响,任何作品都会融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复杂系统,后世作品或多或少会带上前代经典的胎记,这就是所谓的文本间性[1]。研究童话故事的目的之一在于回答一个读者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神话传说与童话故事在诗学层面为何呈现异曲同工的面貌?以晚唐段成式辑录的《酉阳杂俎·天咫》为例: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2]9
一种文本总能在世界其他地区找到对应物,它们的叙事策略跨越时间和空间构成“复调”关系,就罪与罚的神话母题而言,吴刚伐桂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是互文关系,形成了文本巧合的奇特现象。在交通不便的远古时代,地域玄远的民族之间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否有交流互鉴?如果有的话,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作品的基因序列希望找到它们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俄罗斯民间文学家弗·雅·普洛普认为神话研究在许多层面可以与自然界有机物的研究相提并论,无论在科学王国还是在文学领域,实体的相似性一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他认为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在文学领域同样适用,其他学者对此则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在相似性不代表拥有共同的族谱,即物种独立产生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相似性是遗传的结果。普洛普的判断是,历史上确实存在两个文本类型,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历史,后来两个传统在遥远的时代相遇并汇合成为一个东西[3]99。
普洛普的真理观和方法论代表了结构主义流派的思想,他认为正确分析一个故事并不容易,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和习惯,其《故事形态学》成书前后正是欧洲结构主义学说的鼎盛时期,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益精确的数理分析,当这一策略应用于人文研究时,出现了结构语言学和数学语言学,它对艺术作品进行解剖,编制出一套缜密的分类法图表,并用复杂的符号系统来表示。普洛普不赞成康德的先验论,认为后者只注重事物的表象,而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得本体认识,它是一个发现规律并用法则加以阐释的过程,民间故事也不例外,他用十九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数理和符号逻辑研究神奇故事的内在逻辑和普遍规律[3]179。
普洛普与语言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给神话传说和童话故事贴上“神奇”的标签,在“问题的历史”中,他肯定了阿尔奈对故事要素的分类方法:(1)神奇的对手;(2)神奇的丈夫或妻子;(3)神奇的难题;(4)神奇的相助者;(5)神奇的物件;(6)神奇的力量或技能;(7)其他神奇的母题,普洛普对比分析后发现诸多神奇故事的内部结构出奇地一致,他据此推导出“普氏万能公式”,用结构主义方法对阿法纳西耶夫的101个俄罗斯神奇故事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要素”“功能项”及其“图式”,他认为“神奇故事就是那种建立在上述各类功能项有序交替之上的叙述,对每个叙述而言会缺失其中几项,也会有其他项的重复”[3]95。
二、灰姑娘的历史研究
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在公元前一世纪讲述了一位远嫁埃及的希腊少女洛多庇斯的故事: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一只老鹰攫走她的鞋子丢在法老脚下,法老随即要求王国内所有女子试穿这只鞋子,由此找到了洛多庇斯并娶她为妻,这个故事后来出现于克劳狄俄斯·艾利安纳斯(Claudius Aelianus)的《史林杂俎》(Various Historia)一书。在搜集和整理“灰姑娘故事”方面,玛丽安·考克斯(Mariam R.Cox)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其母题和诗学展开的研究也最为透彻,她在 《345个不同的灰姑娘》 (Cinderella: 345 Variants,London: David Nutt,1893)中,按照人物和情节把所有口头传说和文献记载的灰姑娘故事从简到繁分成三大类加以研究。吉姆·巴·巴希尔(J.B.Basile)是意大利童话采集者,他编纂的《五日谈》(Pentamerone,1635)收录有 La Gatta Cenerentola,有一些欧洲学者认为此文本是灰姑娘故事的模板,继之而起的是《苏格兰的怨恨》 (The Complaynt of Scotland,1540),它讲的是拉辛·蔻蒂 (RashinCoatie)在小牛帮助下摆脱继母的虐待在教堂邂逅王子并成婚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有相似的故事变体,故事结构符合普氏万能公式,阿法纳西耶夫编选的故事集中有若干继女被逐出家门的叙事,在《冰霜的故事》中,玛尔法苦尽甘来而姐妹却弄巧成拙,这是灰姑娘的俄国版本[4]。法国文学家夏尔·贝洛(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灰姑娘版本据信有两个来源,一是民间传说,二是巴希尔的素材,为了使民间故事更符合法国王室的审美标准,他对原始素材进行去粗存精的艺术加工,《鹅妈妈的故事》于1697年刊印,其中的灰姑娘故事包含了仙女、南瓜车和水晶鞋等全部要素,以至于成为瓦尔特·迪士尼当代动画片的母版。斯蒂思·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 (Motif Index of Folk Literature)中把灰姑娘归纳为阿奈尔-汤普森故事类型,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灰姑娘,按照普氏数学公式来衡量,施事者的名号虽有所不同,功能项却并无太大差别,大致可以归纳为:(1)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女主角;(2)超自然力量的帮助;(3)与男主角相遇;(4)女主角通过某物鉴定自己的身份;(5)大团圆结局[5]。
阿瑟·威利(Arthur Waley)1947年编纂的《民间故事大全》 (Folk-Lore,Vol.58)辑录的《中国版灰姑娘故事》 (Chinese Cinderella Story)来自公元860年左右成书的《酉阳杂俎》,该书由段成式(803—863)所著,续集《支诺皋上》有一则《叶限》的故事,其始末如下: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慧,善淘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
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2]200
在世界范围内这应该算是历史最悠久的灰姑娘叙事了,据撰者附记,此事为“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这则神奇故事先是在岭南民间广为流传,最后由临淄人段成式记录成文,故事发生的地点远离中原地区,时间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先秦时代,《叶限》包含了灰姑娘的全部要素:后母虐待、神鱼相助、聚会出彩、以鞋验身、美好结局、恶人受惩。贝塔海姆认为“小脚与绣花鞋”的古代审美传统即便不是来自大唐帝国,至少来自东方国家,他还把旧中国妇女缠脚的习俗以及欧美国家对高跟鞋的发明与叶限的故事联系在一起[6]239。
345种甚至更多不同版本的“灰姑娘”,历史源流久长,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故事原型,均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高度抽象化的成果。1812年格林兄弟编纂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所收录的灰姑娘(Aschenputtel)建立在贝洛版本的基础之上,它仍没有超出欧洲古典主义美学范畴:模板化叙事结构与17世纪以来欧洲盛行的“三一律”高度契合,与格林兄弟同时代的维克多·雨果在借鉴东西方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突破古典主义的藩篱,把灰姑娘的故事推向艺术新高峰。
三、珂赛特的原型分析
不少学者注意到经典叙事离不开圣诞节,很多神奇的巧合都在这一天发生,《悲惨世界》也不例外。珂赛特作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女主角”在第二部里正式出场,从三岁时离开生母芳汀算起,寄养在德纳第一家已经五年,她的处境是这样的:
珂赛特待在她的老地方,她坐在壁炉旁一张切菜桌子下面的横杆上。她穿的是破衣,赤着脚,套一双木鞋,凑近炉火的微光,在替德纳第家的小姑娘织绒线袜。有一只小小猫儿在椅子下游戏。可以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两个孩子清脆的谈笑声,这是爱潘妮和阿兹玛。
壁炉角上,挂着一根皮鞭。[7]469
壁炉、灰渣、光脚、木鞋、姐妹等元素呈现出灰姑娘的经典意象,主人公被迫前往“鬼魂出没”的森林深处为客栈打水时,雨果是这样描写的:
珂赛特低下了头,走到壁炉角上取了一只空桶。
那桶比她人还大,那孩子如果坐在里面,决不会嫌小。[7]477
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阶级压迫的真实写照,雨果对珂赛特生存状态的描摹是超越旧经典的新发明,为了深入理解作家的文学创造力,我们继续研究珂赛特与上苍派来解救她的“外来人”之间的对话:
她静了一阵,又接着说:
“有时候,我做完了事,人家准许的话我也玩。”
“你怎样玩呢?”
“有什么玩什么。只要别人不来管我。但我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潘妮和兹玛都不许我玩她们的娃娃。我只有一把铅刀,这么长。”
那孩子伸出她的小指头来比。
“那种刀切不动吧?”
“切得动,先生,”孩子说。“切得动生菜和苍蝇脑袋。”[7]493
这就是新版灰姑娘的悲惨生活:无休止的劳作,难得一遇的玩耍机会和卑微的食物(以至于生菜和苍蝇脑袋)。雨果笔下的珂赛特与贝洛的灰姑娘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晰的结构共性:善良的生母亲被凶残的继母代替,姐妹享受爱抚而自己却要到森林里运水,仅有的小刀玩具只有五厘米长。贝塔海姆认为壁炉是家庭的中心,象征母亲的怀抱和失去的天堂,它和木鞋同属灰姑娘叙事的当然工具[6]248。雨果用古希腊的舞台艺术搬演人神共愤的虐童悲剧,在继承贝洛童话元素的同时展示出无与伦比的文学发明能力。
圣诞节这天晚上,珂赛特和她的牧者在恐怖森林里神奇地相遇了,正如《神曲》开头所描绘的那样:“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发现大路不见了,我迷失在黑暗的森林里”。正是在此时,维吉尔带领他通过地狱,走过炼狱,最后进入天堂。主人公在幽暗森林里邂逅魔法师是神奇故事必不可少的情节,魔法师有两种,一种是伤天害理的魔鬼,一种是普度众生的菩萨,前者是邪恶的渊薮,后者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监管人,他仁慈、宽容、无私,以超凡的力量对苦难进行补偿和救济。蒙尘与拯救、反抗与解脱是神话传说和童话故事的永恒主题,用“普洛普功能项”为标尺,用结构主义的显微镜审视《悲惨世界》的主线和母题,雨果对贝洛等前人的继承与超越是显而易见的,这符合作家本人在《〈克伦威尔〉序言》里所阐述的艺术主张,也是他创作实践的指导思想。
荣格认为原型批评是后代文本认祖归宗的过程,学者对原始模型的考证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发现历代作品的互文关系,本质上则是对神话元素的溯源与考古,它从外在相似性着手研究样本的内部结构,进而找到历史文本的关联性和演变规律。原型具有可塑性、转化性和传播性,它不意味着后代文本对前代文本的简单复制,而是艺术创造和价值升华的基础。雨果这样论述艺术天才:“诗人务必当心,不要抄袭任何人……如果真有才华的人竟然不惜放弃自己的本性,把个人的特色丢弃一边,把自己变成别人,他扮演这种纯粹模仿的角色,自己可就一无所有了。天才重发明,不重模仿……这和化学家不同……而是和蜜蜂相同:靠金色翅膀飞舞,在每一朵花上停留,提取蜜汁。”[8]37他认为模仿、平庸和故步自封扼杀天才,限制伟大诗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高乃依和拉辛摘下雄鹰的羽毛之后,变成了平庸的康皮斯特龙”。他不赞成有人以频繁更换布景会让观众糊涂和疲劳并使他们的注意力产生迷惑为借口而固守古典主义艺术法则,指斥三一律的笼子里关着的经常是一具骷髅[8]31。雨果抨击钳制发明创造的教条主义,反对古典主义戏剧在“时间、地点和剧情”方面必须统一的狭隘理念,他批评墨守成规者以逼真性为圭臬,将想象力置于死地,他们的三一律剪去了艺术家的翅膀[8]28。《悲惨世界》突破了三一律的时空限制,打破了室内独幕剧的时空观念,通过多幕剧的复杂艺术,融入十九世纪的现代性元素,强化了文学张力。雨果把跌宕起伏的人间悲剧置于法国大革命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把灰姑娘悲喜交加的故事置换为具有人间烟火气息的“珂赛特历险记”,作品自始至终闪烁着天才作家的奇思妙想。
雨果在描述冉阿让带领珂赛特从沙威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成功逃生的心情时,提到了十七世纪法国诗人和童话作家:“荷马有知,也当来此与贝洛同乐”[7]604。这是雨果和贝洛的作品产生互文关系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则以多条暗线的形式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以白马王子的角色为例:保王派贵族吉诺曼先生的外孙马吕斯是爱潘妮心目中的王孙贵胄,他违背外祖父的意志,执意维护已故父亲的共和思想,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的出身和血统:
马吕斯在这时已是个美少年,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整个面貌有种说不出的高傲、若有所思和天真的神态。他侧面轮廓的线条全是圆的,但并不因此而失其刚强。他有经阿尔萨斯和洛林传到法兰西民族容貌上来的那种日耳曼族的秀气,也具有使西康伯尔族在罗马人中极易被识别出来并使狮族不同于鹰族的那种完全不见棱角的形象。
他发现年轻姑娘们见他走过,常把头转过来望他,她们看他是为了看他的风韵,她们在梦想。在她们中他一个也没有选中。[7]876
与白马王子相比,此时的珂赛特仍然是一副灰姑娘形象,人们称她为“黑姑娘”。马吕斯半年之后再去卢森堡公园的时候,珂赛特已经蜕变成一个美丽动人的公主,刚才还是含苞欲放的蓓蕾,眨眼便成了一朵玫瑰,昨天人们还把她当作丑小鸭,今天再次相见,已变成令人神不守舍的金发公主了。
四、《悲惨世界》的童话叙事
《悲惨世界》共分五部,分别以芳汀—珂赛特—马吕斯—冉阿让为主线展开叙事,四个主角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舞台上演绎奇幻的历险故事,他们的命运在第四部交汇,故事情节符合“生母—失怙的灰姑娘—神仙教母—舞会—白马王子—大团圆”经典童话叙事。冉阿让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他是“提坦”的化身,有着奥德赛的冒险经历,他终生未娶无嗣,青年时期他把全部的父亲之爱倾注在姐姐的子女身上,按照贝塔海姆对童话人物的分类,冉阿让是一个神奇的施救者(a magic helper),扮演无私的圣母角色(all-giving mother)。芳汀二十五岁托孤那年,珂赛特八岁,冉阿让五十岁,无论对密探沙威还是割风老人,他的身份问题、他与珂赛特的辈分问题一直是个谜,珂赛特十四岁时在内心深处探究自己和冉阿让的“父女关系”时,认为母亲的灵魂已经附在白发男人的身体里,一直在身边呵护自己:“他也许就是我的母亲吧,这人”[7]1111。
法国当代批评家阿尔布(Pierre Albouy)认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实际上是一场“神话革命”,他在《雨果作品的神话研究》中认为《悲惨世界》反复提到的“提坦”是人民的救星[9],他发现雨果笔下的各种超人因相貌丑陋而成为被误解被追捕的猎物,施救者与被救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野兽和美女”的奇异搭配,以冉阿让为例,在他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还一直贴着“苦役犯”“拐卖儿童犯”“盗贼犯”以及“杀人犯”的标签,一个被珂赛特和马吕斯曲解和排斥的该隐。阿尔布专门研究雨果如何通过借用、套用、改写、戏仿等手法把斯巴达人抗击波斯入侵的温泉关战役改造成巴黎人民英勇战斗的宏大场面,他认为任何文学艺术都存在历史传承和基因嬗变的特征,互文性一直是“文学考古”的重要课题,雨果继承了古代神话故事的叙事结构及其原则并发扬光大,他的现代诗学气质让作品更接地气,这是因为小说的素材来源于作家的生活年代,他以贫苦农民皮埃尔·莫、迪涅城的主教米奥里斯、革命家圣鞠思特为蓝本创造了冉阿让、卞福汝、马白夫的角色,其中冉阿让的形象最深入人心,他魔法般从“俄里翁号(猎户座)”战船上坠海逃生的一幕,孟费郿森林里藏宝与寻宝的重重魅影,被雨果描绘得像提坦和超人一样神通广大。第二次逃脱沙威的追捕时,他背着八岁的珂赛特飞檐走壁;从战场上背回命悬一线的马吕斯时,他穿越利维坦肚肠般的巴黎下水道,前者上天,后者入地,无不展示出提坦一样的神奇本领。
贝塔海姆认为神话传说和童话故事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民族智慧并为后世所借鉴,具体到诗学层面,最大的共同点在于“超人”的意象构建,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古希腊神话人物的“神性”成分居多,最终以悲剧收场,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称童话为“爱的礼物”,喜剧色彩厚重,主人公大凡富有“人情味”,无论过程多么悲惨,结局总是乐观的。冉阿让和珂赛特的历险记忠实地履行了神奇故事的全部程序:“亡母(感恩的死者)—囚禁的孩子—神秘的树林—神奇的相助者—宝物—劫波—魔法逃遁—心怀敌意的岳父—公主的婚礼”。姐妹相妒是故事情节的经典配置,雨果也不例外:爱潘妮和伽弗洛什五姐弟所经历的希腊式悲剧最终促成了马吕斯与珂赛特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两姐妹暗恋马吕斯并为之惨死于巷战的枪弹之下,王子和公主则在巴黎街头的战斗结束后走向了婚姻的神圣殿堂。普洛普认为童话故事的经典开头一定是“在一个很远、很远的王国里呀……”雨果把它改造成《悲惨世界》的大团圆结局:“从前有一个国王和王后。啊!我太高兴了。”小说以“渡尽劫波—羽化成仙—长乐未央”的叙事逻辑为这场亦真亦幻的人间故事画上圆满的句号:
在这圣坛上和在这荣光中,这两个神化了的人,其实已不知怎么合二为一了,对珂赛特来说是处在一层彩云之后,对马吕斯来说,则处在火焰般的荣光中。[7]1705
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既是一场神话又是一场革命,是对刻板模式的激烈反叛,浪漫主义的基本诉求是反对机械的科学主义,在雨果看来,三一律荒谬至极,世界上不存在事物的绝对结构,过分强调规则会束缚作者的创造力。古典主义把世界抽象成一系列模式和公式是错误的,文学尤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革命,所有妨碍创造力的设计、概括和范式都是一种扭曲和反动的力量。华兹华斯认为如果把文艺限定在一系列公式之内,对于作家而言是一种虐杀,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G.Herder)认为希腊神话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试图复制罗马神话是荒谬的,人类必须拥有现代神话,正如希腊人所创造的古代神话一样[10],从这一观点来看,《悲惨世界》是一部肇始于希腊神话,取材于欧洲童话但又明显超越前代所有作品的新经典,是对古代神话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最新发明成果。
五、结语
普洛普认为任何科学的最高成就都是对规律的揭示,他用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的方法,发现了组装神奇故事的零部件和生产线,同为结构主义流派的列维-斯特劳斯批评普氏公式是一个幻影,是形式主义的幽灵,但后者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形式主义者,他强调当把普适性研究和特殊性研究结合起来的时候,数学方法论及其结果才有阐释力,他承认文学天才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无法仅仅用数理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但丁和莎士比亚是这样,雨果也是这样,他认为一个民族的诗性创造是国家进步的推动力量,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测定的。同时代的格林兄弟继承了贝洛的童话遗产,无论是小红帽还是灰姑娘,都没有摆脱单声道独幕剧的窠臼,雨果在古为今用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用立体声把经典童话故事推上前所未有的新高程,一个是笛子独奏,一个则是交响乐,如果把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看,童话性质的《悲惨世界》 (1862)是神话性质的《巴黎圣母院》 (1830)的续篇,后者是脱胎于神话《俄狄浦斯王》的独幕剧,前者是灰姑娘童话的五重奏,它展示出作者更为磅礴的创新能力和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