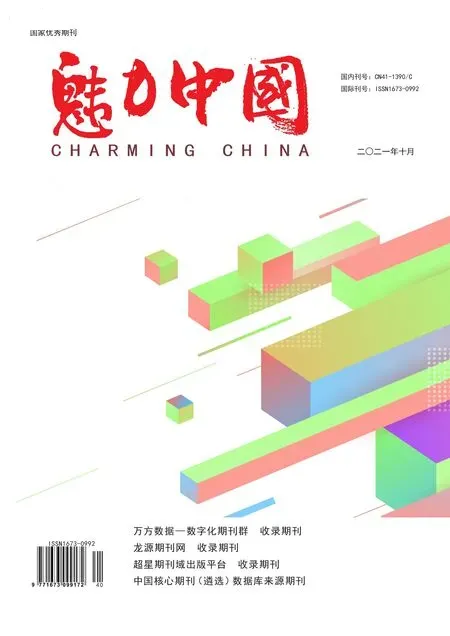汉语古代小说《蒋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译本传播研究
萨日郎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文学传播研究属于文学作品的外围研究。文学传播的传播场域、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受众欣赏、传播影响等环节都是文学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明清汉语小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情况对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相互交融与交流,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关系能够提供重要的研究视角和史料。
一、《蒋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译本文献来源
《蒋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译本以入选《今古奇观》小说集蒙译本和单行蒙译本两种形式流传下来。《蒋興哥重會珍珠衫》入选为《今古奇观》小说集的第23 章小说。《今古奇观》小说集大约成书于明末1632 至1644 年,由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选取了40 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小说主要描写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有非常高的可读性,故事情节丰富,引人入胜。
自19 世纪初以来,《今古奇观》曾数次被译成蒙古文,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据初步统计,目前分藏于国内外图书馆的《今古奇观》清代蒙古文译本至少有200 余册。
《今古奇观》小说集现有两种译本流传于内蒙古和蒙古国地区。即1816 年附有《今古奇观,译者补序》的东部蒙古地区的卓索图盟人哈斯宝译本和蒙古国乌兰巴托译本。乌兰巴托译本是19 世纪末到20 是世纪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库伦翻译,译者不详,从多个章节的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各有差异来看,可以断定多人参与到该小说集的翻译工作中。
在蒙古地区《今古奇观》诗集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灌园叟晚逢仙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单篇小说的蒙古文单行本译本也有传播和流传。其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对蒙古族文学创作与手中审美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古奇观》小说集的哈斯宝蒙译本和乌兰巴托蒙译本两种译本均编入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小说之外,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文工作办公室藏有《蒋兴哥故事》册页式蒙古文抄本。《蒙古文抄本〈蒋兴哥故事〉和哈斯宝译本卷二十〈蒋兴哥重回珍珠衫〉在个别字词的写法上略存差异,其余的大体内容完全一致,而与乌兰巴托译本的对应内容却存在诸多歧异。故可以推断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言文工作办公室所藏蒙古文抄本〈蒋兴哥故事〉实则哈斯宝译本卷二十三章〈蒋兴哥重回珍珠衫〉中以单篇形式誊录出来的独立文本,它是哈斯宝译本的一种特殊传播形式。》[1]
《蒋興哥重會珍珠衫》以蒋興哥和王三巧儿夫妻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他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蒋興哥与妻子三巧儿婚后恩爱有加,但因为生计所迫,他留下妻子独自赴外地做买卖。在此期间三巧儿由于受到陈大郎与薛婆的诱惑和欺骗,做出违背丈夫的不贞之事,后被蒋興哥休弃。但在蒋興哥遭遇之难时,她又出手相助帮他摆脱了冤案。最后蒋興哥不忘旧情,与三巧儿重归于好。作品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一波三折、人物形象丰满有趣、生活细节描写细腻生动。
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丰满生动的普通市民的形象,也不乏汉族市民的生活环境、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习俗礼节、审美标准、饮食服饰等文化符号的体现。当然这些文化符号通过蒙译本传播到蒙古族地区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误读、创造性叛逆等跨文化传播的现象。
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蒙译本的传播场域
文学传播的传播场域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他与文学传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时代背景因素密切相关,并且与文学传播内部系统的的作者、编辑、传播者、受众等多重因素有密切的关联。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段。据统计,清代至民国早期,蒙古族文人曾翻译百余部汉族古代小说,大多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蒙古族地区,且有多种版本。清朝时期,随着蒙汉族地区在整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译本传播的传播者和受众需求两个传播因素的逐渐形成直接推动了对汉族文学的喜爱与认可,随之出现了多部文学作品的蒙译本陆续出现。现在搜集到的最早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译本是1816 年哈斯宝的译本。在清朝嘉庆丙子年间该小说被翻译成蒙古文,供广大蒙古族受众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
清代汉文小说蒙译活动前后延续了两百年,大致分为17 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18 世纪后半叶至19 世纪初、19 世纪初至20 世纪初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翻译活动的内容与地点略有不同。第一阶段的翻译中心为北京,第三阶段是翻译中心转移至东部蒙古地区的卓索图盟和喀尔喀蒙古族地区的库伦。《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两种蒙译本翻译地点正在这个时期的翻译中心卓索图盟和喀尔喀蒙古族地区。
文学传播场域里文学传播者和受众是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19 世纪初期在蒙古族地区有不仅蒙汉兼通,并且认同汉族文化的蒙古族文化人的出现,直接推动了汉族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和传播。与之前只有官方组织翻译活动的情况相比,没有官方背景的文化人员的参与,文学作品的蒙译活动在翻译作品的内容选择与审美趣味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蒙译本译者《哈斯宝饱读中国古籍,精通文史。哈斯宝的文学思想和文化理想中就具有深刻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2]蒙古文学的发展历史与汉族文学发展历史有较大不同。
19 世纪开始,清朝时期汉族小说里描写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的现实关怀都都是蒙古族受众更加接近生活,接近现实的一种文学审美的需求。读者的需求是推动文学创作的有力影响因素。小说里出现的情感恩怨、日常起居、饮食服饰等细节更加拉近了文学作品与受众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市民生活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蒙译本深受受众的欢迎的原因所在了。
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蒙译本的翻译特色
清代蒙古族翻译者因为对汉语文化的理解与认同的差异、个人审美取向的不同对古代汉语小说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有对原文逐字逐句的对等翻译,也有创造性的叛逆,更有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对原文进行大量的删节等情况。原文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文本变异。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哈斯宝译本和乌兰巴托译本在翻译地点和翻译翻译策略上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差异明显。
(一)忠于原文的对等翻译
哈斯宝忠实于原文,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原文小说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等信息进行了对等的符号转码、对人物对话、细节描写、情节发展等所有的内容未加修改与删减,也没有夹述评语,在译文里都能够找到相对的语句,进行了严谨贴切地表达。哈斯宝译本对原文的诗词部分也是做到了完整的翻译。原文共有行数不同的24 首诗词,译文中也没有夹述自己的评语。哈斯宝在翻译诗词与谚语时遵守了蒙古族文化的表达思维与诗歌的首尾押韵。
(二)跨语际转码的创造性叛逆
乌兰巴托译本更加考虑到了受众的阅读期待,便于受众理解与通过小说来教化和感染受众,一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删节、节译和改编,进行了跨语际传播的创造性叛逆。在必要之处改编了原文的叙述模式,将原文中的认读对话直接安变成了叙述形式。乌兰巴托译本对删节故事情节不强、或者与故事主干联系不深紧密的部分。对人物对话和细节描写进行了节译与删译。有事简略了故事情节,便于受众更好地理解,译者夹述了自己的理解和对故事情节的评论。《原著中共有24 首诗歌,翻译时改写了13 首诗歌,增加了3 首诗歌。没有严格遵守字句或段落的原有形式进行翻译,译文中的诗句都遵循了蒙古族诗歌的押韵方式和原则》[3]86。
(三)文化误读的误译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两种译本因为对汉语文化的理解不准都存在不同成的文化误译。
例如哈斯宝译本对原文中一些重要信息漏译之外,还由于不谙汉语文化意境、用词习惯、难辨细微等原因而出现误译的现象。对一个完全崭新的文化及美学体系进行诠释,如果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理解有失偏颇,就会导致传情达意受限。蒙古文抄本《蒋兴哥故事》的误译中,对古代礼制、相关习俗的误译现象占据较大比重。
例如原文中的有一句《只推制中、不繁外事》,在汉族文化中“制中”一词也叫“守制”,指父母丧后,子女在居丧期间不能饮酒、听乐、外出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蒙古文抄本《蒋兴哥故事》将其译为“不理会无关的事情”,没有译出“制中”一词的完整意义。又如原文中的蒋兴哥给三巧儿的休书中写道“过门之后本妇多有过失,正合七出之条,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其中“七出之条”为封建社会,妻子有下列情况之一,丈夫就可单方面休妻的七种理由,即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蒙古文抄本《蒋兴哥故事》将“七出之条”译为法律,对其进行了模糊处理,未能准确表达原文意义。
四、《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蒙译本的传播影响
(一)推动蒙古族文学的叙述内容的变革
清代汉语古代小说的蒙译本传播,推动了文学作品开始关注现实生活,满足受众期待。
古代蒙古族文学植根古老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熏陶,口语文学和英雄崇拜一直是蒙古族文学的主要特色。翻译和接收汉族文学史也是热衷于翻译和传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充满英雄传奇色彩的作品。上述作品的故事情节、叙述风格与蒙古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和变现形式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今古奇观》里的家长里短的故事、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普通市民的人生体验等都是之前蒙古族文学作品中特别少见的。《蒋興哥重會珍珠衫》的广泛传播不仅推动了蒙古族受众审美趣味的逐渐改变,也使得文学创造中开始描写普通人生活场景、塑造普通的形象,展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二)直接影响文学创作
《蒋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译本对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和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曾经数次从汉文译为蒙古文,这不仅是蒙古族读者非常喜爱它的证明,也的确充分显示出蒙古语语言词汇之美妙丰富性。这些故事的译文由书面渗透至民间,不仅有蒙古族乌力格尔齐增补讲述,而且自蒙古国建国初期,还在乌力雅苏台、阿拉坦宝力格以及首都大库伦等地搬上戏剧舞台,编成歌舞剧进行演出》[4]290。蒙古文译本《蒙古国现代著名作家达·宝德瓦的〈美丽的故事〉(wujimjitewugulel)也是模仿〈今古奇观〉中〈蒋興哥重會珍珠衫〉而创作的。他以蒙古国社会生活为背景,以〈蒋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故事为框架,讲述了一个蒙古族生意人家庭类似于〈蒋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故事。〈美丽的故事〉于1990 年由蒙古国政府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小说在蒙古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12。
《蒋興哥重會珍珠衫》蒙译本的传播是清代蒙汉文学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对研究蒙汉文学关系,民族文学相互交融与交流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