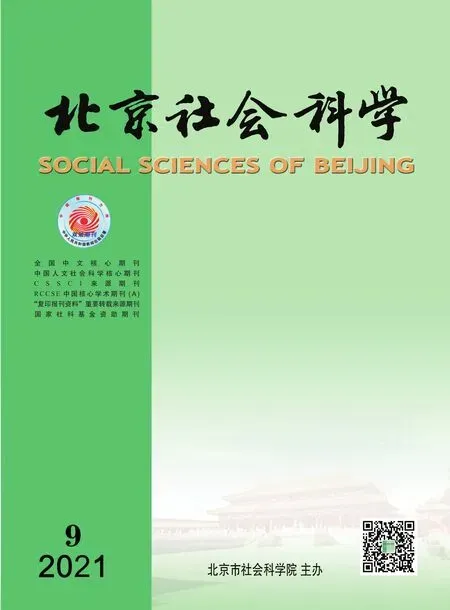从秦穆公的悲剧到秦国的悲剧
——以《秦本纪》载《黄鸟》叙事的矛盾为中心
曹 阳
一、引言
秦穆公①是秦国历史上声誉卓著的君主,《史记》记载其执政期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东服强晋,西霸戎夷”,“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秦穆公开创的霸业在秦国发展史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穆公也是司马迁在《秦本纪》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其事迹占据全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牛运震《史记评注》云:“叙缪公一代事迹……不可谓非太史公用意之文也。”[1]司马迁在记述穆公史事时,叙述重心并不在穆公逐步建立的功业上,而是选取相关史料着意刻画了秦穆公的明君形象。然而,在叙述其逝世时,司马迁却引述了一段《左传》中穆公收“三良”从葬,“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2]的叙事,暴露出了秦穆公的“杀贤”恶行。《史记·秦本纪》载:
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3]
这一文本交代了秦穆公的结局,使关于穆公的叙事文本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但是不论从穆公的人物形象还是《秦本纪》的整体文本来看,这段源于《左传》的叙事均表现出了文本间的前后矛盾。对此明代陈允锡、徐孚远,清代梁玉绳、程馀庆,以及近代童书业等人皆将文本矛盾的根源归结为《左传》叙事视野所限,指出其为《史记》载录《左传》不验之预言。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则指出司马迁如此载录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但并未展开论述。②笔者认为,《史记》这一文本矛盾并非写作过程中的疏漏,也绝非不经意之笔。如何认识这一文本矛盾,对解读《秦本纪》乃至《秦始皇本纪》具有重要意义。
二、秦穆公形象的前后矛盾
在《秦本纪》秦穆公相关文本中,司马迁用多达十分之七的篇幅,通过对“羊皮换贤”“秦晋乞籴”“穆公亡马”“穆公归夷吾”“由余降秦”“穆公悔过”六个故事的重新叙述,凸显出了穆公贤君明主的光辉形象。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刻画秦穆公这一人物时,有意地采纳了《尚书》《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国语》《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文献材料中关于穆公的相关事迹。对所收集的原始材料,司马迁并非简单地随意载录,而是有目的地择选,对相关情节、人物进行了精心安排与加工,重新叙述了秦穆公的故事。这一重述客观上使得文本上下衔接更为合理,叙事更为简明,但其重心旨在凸显秦穆公的形象特征。
经过文本对比可以发现,为刻画秦穆公形象,司马迁采用多种方式对史料进行了改易。其一,人物主体上巧妙改设。如“羊皮换贤”中将《孟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所载以五羖羊皮赎买百里傒的主体从百里傒本人改为秦穆公,凸显出秦穆公的重贤与谋略。又如“秦晋乞籴”中将秦国参与讨论的臣子从《左传》所载子桑、百里傒、子豹,《国语》所载丕豹、公孙枝,变为丕豹、公孙枝、百里傒,刻画了秦穆公重贤且从谏如流的君主形象。再如“穆公归夷吾”中以《左传》《国语》所载史事为框架,却将为晋惠公求情的主体设为周天子、穆公夫人,凸显了秦穆公“尊王”“重情”的形象等。其二,人物言语上用心雕琢。如相对于其他材料粗略的叙述,在“羊皮换贤”中增添“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4]句,“口吻如生”[5],使得穆公“重贤”情态毕现。又如在“秦晋乞籴”中删去了《左传》《国语》所载晋国庆郑主张输籴于秦的言论,显得“晋臣不及秦远矣!”[6]再如在《左传》《国语》所载基础上,为“穆公归夷吾”中秦穆公言论增添“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7]之语,体现了秦穆公的“尊王”“重情”与“宽厚”。其三,情节上经意增删。如“羊皮换贤”中“恐楚人不与”的细节增补,“数语写缪公求贤爱才之意曲至”[5]。又如以《韩非子》与《韩诗外传》叙述为基础,在“由余降秦”中增添“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8]等细节。从对“邻国圣人”由余的礼待与尊崇中,凸显了穆公“爱才”“重贤”。再如出于对秦穆公的尊崇,怕有害穆公之德,在“穆公悔过”中对《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所载秦穆公怒骂蹇叔之事进行了删削。其四,叙述顺序上精心设计。如相对于《吕氏春秋》所载,将“穆公亡马”一事插叙于韩原之战未决胜负之时,叙出秦穆公所赦野人为回报其厚德而拼死力战,使得秦穆公在韩原之战中转败为胜,更为直接地展现了穆公施德在战争胜败间起到的关键作用。
司马迁以上述秦穆公的形象特征为中心来行文属事,与其撰写秦穆公相关文本时所采的原始材料紧密相关。事实上,这些原始材料本身便蕴涵着对秦穆公形象认识的价值导向。除了其所载客观事件表露出来的倾向外,更为明显的直接导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穆公行事的评价。《左传·文公二年》载:“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9]赞美穆公任人以贤。《左传·文公四年》载:“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10]赞美秦穆公有德行,有仁心。《公羊传》曰:“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缪公也。”[11]《荀子·大略篇》曰:“《春秋》贤穆公。”[12]均认为史家以穆公为贤。《吕氏春秋·慎人》载:“缪公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非加贤也。使百里奚虽贤,无得缪公,必无此名矣。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13]将百里傒之贤得以施展归至穆公知贤、重贤、任人唯贤上。在这些文献材料中,有关秦穆公的评价侧重于重贤,兼及爱人,洋溢着对穆公行事的褒美之情。其二,对穆公事迹的归类。《吕氏春秋》中“穆公亡马”的故事收录在《爱士》篇,文中评价此事说:“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14]将故事主题归到穆公“行德爱人”而转败为胜上。这一归类和评价明显影响到了司马迁对这一故事的采用。司马迁依据原始材料对秦穆公相关故事进行重述时,无论是主动寻求还是被动接受,他的叙事思想与历史观念无疑会受到原始材料的价值导向影响。这一影响也使得司马迁在行文属事中有了明确的叙事目的,进而左右了其撰写时对材料的选取、改易和安排,使原本客观的材料再次叙出时增添了一抹明显的主观色彩。
然而,在广采文献材料、用意重述,着力刻画出秦穆公近乎完美的光辉形象后,司马迁突然笔锋一转,载录了秦穆公以“三良”等从葬的“杀贤”之行。这与前文司马迁着意刻画的秦穆公形象显得格格不入。如果司马迁的目的在于塑造秦穆公的完美形象的话,他完全可以像隐去穆公怒骂蹇叔之事一样,出于避讳而选择不载录此事。在撰写“蹇叔哭师”一事时,司马迁主要采用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中的材料。《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蹇叔哭之……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15]《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16]《榖梁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17]而《史记·秦本纪》载蹇叔、百里傒劝谏秦穆公后,穆公说:“子不知也,吾已决矣。”[18]改换了穆公之语,隐去了秦穆公怒骂贤臣的情节。《左传·文公二年》载:“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谓之崇德。”[19]《左传》认为君子出于秦穆公的原因而“尊秦”,所以不载晋、宋、郑伐秦取彭衙之事。司马迁对穆公怒骂蹇叔这一情节的删削很大可能同“卿不书”的原因相同,是出于对秦穆公的尊崇,怕有害穆公之德。但司马迁在《秦本纪》中保留了《左传》中的“杀贤”文本,势必造成秦穆公形象的前后不一。
三、“秦不能复东征”的文本线索矛盾
《秦本纪》借“君子”之口对秦穆公收“三良”从死一事进行了评价,并预言说“秦不能复东征也”,将叙事的核心指向了“东征”。那么,对于秦国而言,“东征”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秦人先祖嬴姓部族曾为殷商镇守西戎,其后人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周孝王“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20]经过数世经营,秦国领土扩至关中东端,成为了较具实力的诸侯国。而晋国在晋献公时期也大事扩张,攻灭骊戎、耿、霍、魏、虞、虢等国,击败狄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21],占据了黄河中游之地,与秦接界。顾栋高评价当时秦晋间的地理形势说:“秦与晋以河为界,河以东为晋,河以西为秦。然秦当春秋时,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关之外,为晋所限阂而不得出也。”[22]自秦襄公起,秦国历代君主基本都沿着渭水向东扩展,秦穆公要继先人之业继续向东就必须“伐晋”,然而其数次伐晋均屡屡受挫。只是到执政的最后几年里,秦穆公才改事西进,“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3]。可见,无论是对秦国发展还是秦穆公个人功业而言,“东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秦穆公时期,“东征”的首要对象即晋国。在秦穆公相关文本中,关于穆公伐晋的叙述占据三分之二。司马迁对秦穆公事迹的叙述即以穆公元年伐晋茅津作为开端,其后史事也多围绕秦伐晋而展开。穆公五年,“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九年,晋献公去世,晋国发生内乱,穆公使百里傒将兵送夷吾归晋。但是夷吾在穆公帮助下被立为君后,并没有兑现“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的诺言。十二年,晋国因旱灾造成饥荒,向秦国求救。秦穆公未听从丕豹伐晋的建议,将粮食运往晋国。十四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君却听取虢射建议,准备乘机发兵攻秦,这直接导致了秦晋韩原之战。在韩原之战中,秦穆公“虏晋君以归”,“将以晋君祠上帝”,周天子、穆公夫人为晋惠公求情,秦穆公“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二十四年,穆公送重耳入晋,是为晋文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卒,秦穆公趁机伐晋,“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但是秦军在殽被晋打败。三十四年,穆公“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三十六年,穆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24]秦穆公执政39年后去世,终其一生都在尽力“伐晋东征”。顾栋高云:“故终穆公之世,未尝一日忘东向。……然终不能越河以东一步。”[25]虽然秦穆公毕生都致力于“伐晋东征”,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心愿。
秦穆公之后的历代秦国君主亦不忘“伐晋东征”。秦康公时,因晋国立君之争,秦晋爆发“令狐之役”,秦师败绩,之后又与晋交战数次。康公去世后,其子共公立。马非百《秦集史》云:“康公、共公二代,在位十六年间,与晋战者凡九次。盖仍是一本穆公之东进政策也。”[26]秦桓公时,“与翟合谋击晋”。秦景公时,“败晋兵于栎”。至秦厉共公时,“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赵、韩、魏”。[27]秦数代“伐晋东征”无果,至此,“东征”的首要目标由“晋”变为了“赵、韩、魏”,“东征”之路终于由难转易。然而,在秦献公之前,“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秦献公时期,与晋“战于石门”,“与魏晋战少梁”。秦孝公继位后,“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称“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28]欲继承先王之志,“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29]孝公时期,“与魏战元里”,“围魏安邑”,“东地渡洛”,“与晋战雁门”。[30]自此后,秦伐“赵、韩、魏”呈破竹之势,三晋多次向秦纳地求和。秦惠文君时期,魏“纳阴晋”,“纳河西地”,“纳上郡十五县”,秦仍不忘东向,数次伐三晋。“渡河,取汾阴、皮氏”,“围焦,降之”,“取赵中都、西阳”,“取韩石章”,“攻魏焦”,“败韩岸门”,“攻赵”。在不可挡的攻势下,秦武王时,“韩、魏、齐、楚、越皆宾从”。武王又“拔宜阳”“涉河,城武遂”。至秦昭襄王时,战争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秦不仅先后战胜了齐、楚,攻取了三晋大部分领土,而且还攻陷东周王都洛邑,结束了周王朝的统治,取得了“天下来宾”的政治地位。[31]经过秦庄襄王时期数次对三晋的攻伐,至秦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32]最终完成了一统。“东征”是秦能够征伐六国统一天下的关键战略,其直接对象是(三)晋,“东征”成败对于秦国的历史命运有着重要意义。
《秦本纪》中“秦不能复东征”的预言录自《左传》。《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33]《左传》载录了一百多条预言,这些预言几乎都精准地预测到了发生的史实,使得《左传》充满了神秘色彩。学者们多认为《左传》中的预言出于记录者事后追述,在这些预言的背后,蕴含着记录者深厚的伦理道德观念。“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属于《左传》中的“君子”预言,与之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存有多处。如“隐公十一年”君子以息国所犯“五不韪”,预言息国将亡。这一预言在庄公十四年时应验,“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34]。又如“文公四年”君子通过鲁国迎娶出姜时礼数不周,预言她将不被敬信。这一预言在文公十八年时应验,鲁文公去世后,在齐惠公的默许下,东门襄仲杀害了出姜的儿子们,拥立敬嬴之子为鲁宣公。在上述预言中,君子通过对个人、国家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礼仪来对其作出评判和预言,显示出了崇德尊礼的观念。与之前不同的是,从秦穆公之后秦的东征进程来看,“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似乎出现了失误,并未应验。程馀庆云:“此以理断之耳,后却不验。”[35]顾炎武《日知录》亦曰:“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36]但是,《左传》中并无完全不验的预言,那些被认为不验的预言多是因时间或程度限制看起来似乎未能应验。针对《左传》“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的预言,明人徐孚远云:“孝公复霸业,在后,左氏不及见也,故有不复东征之语。左氏断语,皆以后事为证验也。”[37]清人陈允锡《史纬》言:“不能东征,以当时言。”[38]童书业提出:“此末一语有预言性质。春秋之世,惟穆公时为强大,其后即渐衰弱……秦势复张,实在入战国百年后惠文王时,约为公元前三三○年左右,亦即《左氏》所记预言之下限。《左传》非一时所成(大体为公元前四世纪物),其大部分撰作时间在秦惠文前,故多保存东方国家原对秦国之传统观念,而出此‘知秦之不复东征’之预言。”[39]就《左传》而言,“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即是因叙事时间限制而未能应验之例。司马迁在《秦本纪》中一方面收录了《左传》中“秦不能复东征”的预言,另一方面却也以详细的叙事展示了秦国最终“东征”成功的史实,这不可避免地使得文本前后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四、从秦穆公的悲剧到秦国的悲剧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40]显示了他遵奉孔子“述而不作”的编纂原则。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秦本纪》所叙史事皆有所本。这就使得司马迁文本编纂者的身份显得尤为明显。程苏东提出司马迁“在钞撮的过程中,难免在其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41]据前文所论,源自《左传》的秦穆公以三良从死相关文本被完整地载录到《秦本纪》中,这不仅使得司马迁在前文中极力刻画的穆公贤明仁德形象出现了极大的反差,也使得叙事线索上与后文秦最终东征成功的事实形成明显的矛盾。《秦本纪》文本中的这两处矛盾是否即是司马迁在编撰过程中因处理材料遭遇困境而造成的“失控的文本”呢?笔者认为文本中的这两处表层矛盾实则深层地寄寓着史公深刻的“过秦”思想和宏阔的历史视野。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所刻画的秦穆公最大的污点即以“三良”从死,以百人从葬,这一过失不仅有害于其贤君明主形象,而且使君子断言“秦不能复东征”。此外,因穆公以“三良”从死之事,还引发了历史上关于秦穆(缪)公谥号之争、《秦风·黄鸟》讥刺对象之争、咏“三良”诗文的创作及其中关于“三良从死”之争等公案。秦穆公杀三良从葬一事对其声名的负面影响极大。然而以人从葬并非始自穆公,而是由来已久。考古学证据表明,史前时期便出现了人殉现象,殷商时期达到了高峰。西周初期统治者进行了文化变革,提倡“敬德保民”,人殉习俗走向衰落。而至春秋战国时期,人殉习俗复兴,流行于秦、楚、吴这些远离周文明中心地带的国家。秦国地处西陲,穆公之前便有以人从死的记载,《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42]献公时期,“止从死”,然而之后仍有关于以人从葬的记载。《战国策·秦策》:“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43]《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44]既然秦俗如此,为何独秦穆公受到如此非议呢?
受西周摈弃以人殉葬野蛮习俗的影响,春秋时期以周文明为中心的国家均对人殉存鄙夷的态度,认为“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想要让嬖妾从葬,其子魏颗以“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45]为由,令嬖妾改嫁。《礼记·檀弓下》载:“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46]《尸子·广泽》曰:“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47]相对人殉而言,以俑代人进行殉葬,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殉俑亦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48]从孔子之言也可见当时贤人君子对殉葬习俗的态度。秦穆公是有名的贤君明主,《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评秦穆公语云:“其志大”,“行中正”,“虽王可也,其霸小矣”。[49]孔子对穆公的评价远超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③《史记评林》载杨循吉语云:“当时称贤君,固未有出缪公之右者。”[50]以穆公之贤,却仍以人殉葬,不禁令人惋惜。《左传·文公六年》载君子评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51]苏轼曰:“独其僻在西陲,礼未同于中国,而用子车氏之三子为殉,《黄鸟》之诗作焉。秦自此不复能东征矣。君子是以惜其盛德之累也。”[52]朱熹云:“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呜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53]方回《续古今考》云:“秦之贤君,莫如缪公,有《秦誓》,入百篇末,而有三良之《黄鸟歌》,太史公‘君子曰’一段深惜之。”[54]足见贤人君子对秦穆公寄予着厚望,希望这样一位贤明仁德的君主可以改变秦国乃至中国,垂范后世,这也正是为何对秦穆公以人殉葬如此苛责的原因。在有关秦穆公的文本中,尽管司马迁也尽力回避穆公的污点,将其形象刻画得近乎完美,但是却仍载录了秦穆公以“三良”从死之事,并在《太史公自序》中云:“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55]重点提明了“以人为殉”,可见史公之哀叹与用意,也说明司马迁对秦穆公以“三良”从死之事的载录绝非不经意之笔或文本编纂中所遇之困境。这一载录反映出以秦穆公之贤德仍然无法左右秦国的人殉制度,或者未能摈弃这一制度,正凸显出了秦文化的鄙陋与残暴。恰如元人刘玉汝所言“观此诗‘三良’固可哀也,而秦亦可哀矣”。[56]秦穆公作为政治强人,他的统治却并未能撼动秦文化的落后根基。从根源上来看,秦文化的残暴与落后不仅造就了秦穆公留有污名的悲剧,而且也为秦国最终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出自《左传》君子曰评价的“秦不能复东征”预言作为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线索,出现在秦穆公相关文本中,不仅涉及穆公形象,是对穆公本人一生“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57]的总结,更是着眼于秦国历史进程的一种宏大政治预言。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叙述了秦国从起于戎狄到被封诸侯再到一统六国的过程,也在最后展现出了秦短命而亡、“东征”落幕的结局。在叙述这一历史的过程时,司马迁在文中点出了秦国短命而亡的根源正是秦文化的残暴。《秦本纪》自献公时期开始载录斩杀数量,献公之后这类记载逐渐增多且更为细致。宋人方回评此云:“细考之,秦献公犹未有一首一级之赏。孝公用商鞅立法,战斩一首赐爵一级,首级之名,自孝公始。秦孝公七年,虏公子卬,与魏战,斩首八万;孝公后七年,条鱼之战,破五国及匈奴,斩首八万二千;十三年丹阳之战,虏楚将屈匄,斩首八万;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十四年白起攻韩、魏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三十三年击芒卯,斩首十五万;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四十余万;五十年,攻晋,斩首六千,流尸于河二万人;五十一年,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首虏九万;秦始皇二年,攻卷,斩首三万;十三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大约计之,秦斩杀山东六国之民一百六十余万人,其得天下不仁甚矣。”[58]清代梁玉绳也指出:“秦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斩首六万,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惠文八年与魏战斩首四万五千……计共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而《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59]《秦本纪》中这样的载录不见于《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晋世家》等春秋战国时期别国的传记。虽然这主要与秦尚军功,史料中对斩杀数量记载较为详细,影响到了司马迁对材料的采录有关,但是与其他传记的记载相比,秦国的崛起显得更为残暴血腥。正如《史记评林》载凌稚隆评所言:“按太史公纪秦斩首之数凡十一处,以秦之尚首功也。不言其暴,而其暴自见。”[60]秦国以“禁暴诛乱而天下服”,“繁法严刑而天下振”。秦始皇以暴力取天下,不思“取与守不同术”,“过而不变”,治政时“以暴虐为天下始”,“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秦二世继位后,“因而不改”,“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61]这一系列的行为最终导致秦朝短命而亡。王世贞云:“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庄襄以前之主。”[62]将秦国取天下之无道归因于“庄襄以前之主”,实际上正言明了秦文化的残暴对秦国政治手段的影响。司马迁借贾谊之文对秦国兴亡进行总结时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63]秦国“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的现实与史公“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的假设两两相形,正从侧面点出了秦国倘不用仁德来改变残暴的文化,功业就不可能长久的道理。
五、余论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对《左传·文公六年》中穆公收“三良”从葬一段叙事的载录,其背后主要有三重原因。一是汉武帝时期儒学独尊,立经学为官学,置《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治经、通经成为当时风尚。史称“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64]司马迁在撰写秦穆公相关文本时广采诸种文献材料,其中以《左传》为最。《左传》中所记载的穆公收“三良”从死一事,又正是《诗经》中收录的《黄鸟》诗之本事。《诗》在汉代的地位自不必言,“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又是对《春秋》记事的具体说明。司马迁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65]因而,在“尊经”思潮的影响下,秉持“述而不作”与“实录”精神进行撰写的司马迁不可能无视《左传》的这段叙事。二是正如在刻画秦穆公的正面形象时受到了之前文献材料中对穆公事迹的褒赞影响一样,司马迁对以“三良”从死所表现出的穆公负面形象叙事的收录亦受到了春秋战国以及汉初文献材料中对秦负面评价的影响。春秋时期,秦国最初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居,文化习俗野蛮鄙陋不同于中原国家,常被视为戎狄。《管子·小匡》云:“西征攘白狄之地……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66]《公羊传·昭公五年》载:“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67]而秦穆公趁晋文公逝世之机,攻打晋国,更被中原国家所鄙夷,认为是夷狄之行。《榖梁传·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68]《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亦有类似记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16]穆公之后,秦国经过数世经营,终于取得天下,然而其取天下与守天下的残暴手段却遭到了诟病。陆贾《新语·辅政》云:“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69]《新语·道基》:“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70]贾谊《过秦论》:“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71]在这些对秦负面评价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史记》部分篇目中所载录的人物言论不仅体现了战国秦汉之际人们对秦国的认识,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司马迁对秦的认识与态度。在《史记》中这种态度也多有表现,《秦本纪》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72]《项羽本纪》记载鸿门宴中樊哙批评秦时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73]《六国年表》曰:“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74]《魏世家》记载魏无忌评价秦国时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75]《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劝谏楚怀王不可赴秦昭王之约时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76]这样的认识与态度除了影响到司马迁对秦的整体认识外,必然也影响到了司马迁对秦穆公“不为诸侯盟主”且“伐晋东征”屡屡失败的归因,即“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未能“遗德垂法”。三是在汉兴之初,以陆贾、贾谊等人受命“著秦所以失天下”为代表,汉初思想界形成一股繁盛的“过秦”思潮。士人以“过秦”为话题,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同时为新兴王朝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治国理念。这一强大的思潮无疑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影响,进而表现在其文本叙述中。司马迁不仅在《秦始皇本纪》论赞部分中引用贾谊《过秦论》一文,并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而且在对秦从崛起到覆灭的整个故事叙述中皆有这种思想。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对秦兴亡的过程进行了总结,表述了自己的“过秦”思想。在司马迁看来,以秦文化之残暴竟然最后能够一统天下,大概是得天之助。而“秦在帝位日浅”,则是由于秦文化根源上的残暴,并非一朝一夕所致。由史公之论也可窥见他撰写《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所秉持的思想与用心,即“著诸所闻兴坏之端”,以“察其终始”。《秦本纪》所载录源于《左传》的以“三良从死”叙事虽然呈现出了文本浅层的前后矛盾,但是在以秦国兴亡为历史背景的宏大叙事中,这段引论并不矛盾,而是蕴含着史公深刻的过秦思想与历史逻辑。
注释:
① 秦穆公,名任好。《公羊传》《榖梁传》《左传》作“秦伯”,《国语》作“秦穆公”,《史记》中《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作“秦缪公”,《孔子世家》作“秦穆公”。
② 参见陈允锡《史纬》卷一《秦》、徐孚远《史记测议·秦本纪》、梁玉绳《史记志疑·秦本纪》、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札记续》(以上内容后文皆有论及)、(日)藤田胜久《〈史记·秦本纪〉的史料特性》(见《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
③ 《论语·宪问》:“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史记·陈杞世家》载孔子赞美楚庄王云:“贤哉楚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