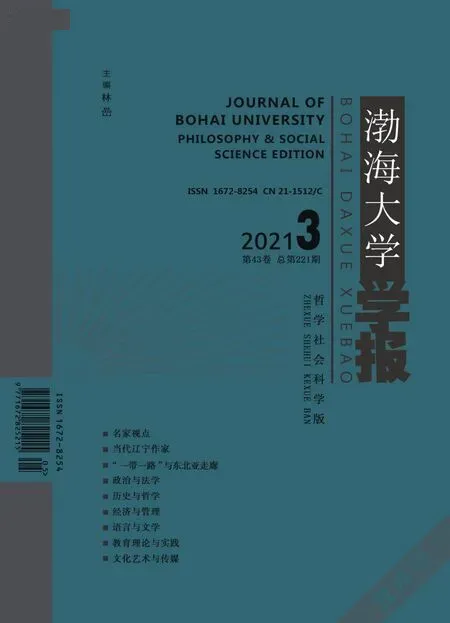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与作家刘国强的对话
林 喦 刘国强(.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锦州 03;.铁岭市西丰县文化局,辽宁西丰 400)
“如果把文学创作的各个文体分别比喻为‘一池水’,我想,这些池子绝非是各自封闭的一潭死水,而是池与池相互连通,相互借鉴和影响。比如在审美理论,在作品中无、生活中有,在继承与创新,在赢得受众喜爱和传播等方面,都有许多相通之处。仅就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而言,结构、语言和叙述乃至人物形象方面,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地方就更多了。”刘国强如是说。
林 喦:您的文学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报告文学,为何选择两种叙事文体写作?在这两个不同文体写作上有何不同感受与体验?
刘国强:小说是以叙述为主的虚构的艺术,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能尝试多种丰富多彩的手段调动无穷尽的想象力,我很喜欢。报告文学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人和事的基础上,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问题甚或直面一些敏感的地方,我也喜欢。创作前者相对自由,可以放开手脚,尽情探索。后者,需要“戴着镣铐跳舞”,表现与时代同步的生活,如同高清镜头近距离拍“特写”,一切都纤毫毕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什么都遮掩不了,更加检验作者的综合实力。
小说创作艺术成熟在探索上却永远上不封顶。小说创作有独特的吸引力,许多理念和技法被借鉴到报告文学创作中,丰厚后者的创作手法,增加艺术魅力。
报告文学有时若“命题作文”“在画定的框子里写作”,正因如此,反而考验作家的应变能力和综合操作技能及表达水准。
林 喦:在很多人看来,“为时代作壮歌”免不了“为尊者讳”,为此不免对英雄人物的言行有所裁剪避讳,这是否有“假大空”的嫌疑?
刘国强:人的一生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短暂而渺小。但大海潮起潮落,永远顺应月球的引力。潮汐汹涌澎湃一往无前的组成元素,却是一滴滴水所建构。渺小与宏大,竟是唇齿相依、互为支撑的“近亲”。从存量上说,“一滴水”的能量很小,许多水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但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一滴水”不仅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站位,还要知道自己的朝向。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朝向问题”至关重要。
现在的小孩子,那么多人想当“网红”、当明星,我认为人生朝向有问题。小孩子的毛病不在自身,而在成人。从根儿上说,这是成人的人生朝向出了大问题。诸如我们貌似一些顶尖科技落后,根子在基础科学薄弱。
我写“时代壮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有所学、受到感染,尽力调动内驱力,为祖国事业、为精彩人生添砖加瓦,向来不把“为尊者讳”当回事。这除了大家都是普通人,即便我写英雄,也写出他们普通人的一面,还因为,这个世界永远不缺挑毛病的人,却永远缺“建设者”。我以前在官场任职,会遇到很多人喜欢“摆毛病”,我说发现毛病、摆毛病没有错,但你要找出怎么解决这些毛病的方法,你能干什么?否则,你提那些毛病有什么用?你们都把问题“摆出来”让别人解决,你们是干什么的?另一层因素便是,提意见谁都会,解决问题的人却少之又少。
报告文学创作也一样,这些先进人物才是建设国家、推动国家发展的主流,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为他们鼓与呼。这也是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朝向。
很多人说现在的报告文学应该写“暴露题材”,我持相反意见。第一,现在的主流网络媒体和新闻媒体、自媒体非常发达,即使在最偏僻的角落也“与时代同步”,文学已经远远滞后,还用你来暴露吗?第二,在纪律和公检法司日益强大的当代,文学的力量微乎其微,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一家独大”的时代。第三,即便暴露得“很成功”,也仅仅是以“题材取胜”,昙花一现。难道只有这样写,才是报告文学的唯一功能?第四,任何人和事都一样,迈上一个台阶很不容易,“坠落”却在一瞬间。作家,应该以一己之力推助他人“上台阶”,做“建设者”。
创作任何一部作品、人物,都有作家主观的裁剪,这一点毋庸避讳。但只要人物的事迹真实、人物感情真实、人格真实、人性真实,回避任何外在附加因素,加上另一个重要参照:作家的内心真实,就会杜绝“假大空”。
林 喦:创新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与提升,这话适用于任何学科。您在《罗布泊新歌》的后记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代文学的同质化问题,您怎么理解文学创作中的创新?
刘国强:对文学而言,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比如武器创新上,你没有独到的领先家伙,就要被动挨打,就要吃大亏。比如科技创新,中国华为是那么优秀的企业,但芯片落后,美国就专从此处入手“制裁”,打你的“七寸”。比如汽车,谁的汽车安全、省钱、省油又结实耐用,一比就知道了。文学不一样。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写什么、怎么写,都没有固定模式。但对经常绷紧创新这根弦、研究创新理论和实践的人,却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当代文学,往往一再出现“一窝蜂”现象,有人提倡短篇小说创作的“形而上”作品好,你看吧,各类评奖都注重“形而上”。我不是说“形而上”不好,而是说群体模仿和“一窝蜂”很成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创作很火,“翻译体”叙述很火,那么多作家、作品“风靡一时”,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有几部作品能留下来?我也不是说现代主义不好,而是说大家都往一条道上挤就很没意思。创新不是跟风,更不是模仿,而是独立的思考和创作。创新不是加高别人的山头,而是另起炉灶、另立山头。我也不是完全反对模仿,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但要永远提醒自己,模仿是学习过程,是为了创新,要很快“跳出来”,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山头”。
比如某位名家的小说叙述好,很快大家就模仿。我觉得,作家、编辑、评论家要共同警惕这种跟风创作、发表及导向,筑高“一窝蜂”防火墙。
文学创作中的创新是个大话题、大范围,宽的没边不好概括。因为,文学创作有那么多要素,一一列举太麻烦。但紧缩点说,凡是写出跟他人作品“不一样”的地方、“这一个”的地方,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都叫创新。为了“省事”,我从反向角度举个“不创新”的事例,比如中国的当代小说创作,那么漫长的时间、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没有一人、一部作品(指影响大的)用幽默和喜剧方式来表达。《堂吉诃德》《钦差大臣》名作怎么就断子绝孙了?我不是说唯有这种创作形式就好,而是说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文学中为什么没有表现?
我认为,电影《你好,李焕英》,最大的长处是用喜剧的元素表达悲剧,导引观众哭中笑、笑中哭,要解决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对冲很难,但贾玲做到了。
林 喦:看来您是看了电影《你好,李焕英》。说实话,如果仅仅从电影创作的角度讲,我不能说这部电影是好作品,但高票房的事实和把一个小时候写的小学生作文《我的妈妈》转换成了一部可以煽情、可以引泪的视频,也着实是一种创新了。当然,文学跟其他学科一样,创新永无止境、探索永无止境。您的报告文学创作强调思想表达的重要性,强调作家主体的激情投入。在当代其他文体的写作中,比如长篇小说,有相当一批作品有意淡化作家主体介入的程度。您能否从主体介入的角度谈一谈对报告文学这一当代文体写作的独特理解?
刘国强:任何文字都是思想的载体。文学作品不表达独有的思想,或者人云亦云,或者拼凑素材拼盘,或者加点调料炒剩饭,无疑背离了“作品”二字。
多数报告文学因为近距离地表现当下生活,能否有“代入感”,能否感染人,营造相对强大的吸力,关键在激情的投入。投入激情也非廉价品,如果没有去除公共话语、去除老生常谈的旧结构、去除粗俗的叙述、去除没有遵循人物情感内心的节奏,便达不到感染人的效果。我一直认为,一篇好的报告文学有多重元素,但如果文字没有温度和吸力,人家看几眼就放下,一切都枉然。
近年来,因为报告文学的约稿多,我很少创作小说。但我一直以每年阅读超千万字的量在读小说。我不反对相当一批作品“有意淡化作家主体介入的程度”,却认为这也是一种误导。文无定法,为什么居然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如此?这与我前边所谈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崇尚“形而上”一样,都是一种“一窝蜂”式的跟风。文学创作不是搞运动,也不应该如此“集体无意识”、一刀切。
即便在小说创作中,我也喜欢那些有激情的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翻译)、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金人翻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么抒情、那么激情扑面,我再次重读;略萨60 多岁创作的《坏女孩的恶作剧》(尹成东翻译)叙述若行云流水,激情澎湃;阅读张贵兴的《猴杯》和《野猪渡河》最大的冲击力便是激情,那种从头至尾阳刚而激情的别样叙述令我激动不已,完全创作出“独有的艺术风格”“独有的艺术辨识度”,鹤立鸡群、超拔地屹立于当代作家之林。我并非非议任何作家,我只在强调张贵兴的作品所带来的冲击力和强悍的创新力。
同样是意识流代表作家,我读不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却对普鲁斯特240 万字的《追忆逝水年华》(徐和瑾翻译)爱不释手,主要是后者激情的叙述吸引我。
林 喦:是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手法上,要吸纳小说的艺术,要有诗的简洁,有散文的收放自如,有戏剧的情节起伏,有绘画的唯美,有音乐的浪漫节奏,有影视作品的跌宕起伏,有儿童文学作品的天真烂漫,要有蝇头小楷的工丽精致又有狂草的无羁野性,要具备多种文体兼容的艺术文本。并实现:要有高屋建瓴的思想站位;要有耳目一新的文字、要有烈火与奔浪兼具的炽热和冲击力。
激越与昂扬的风格、大叙事、重大主题是您创作的突出特征,您是否尝试过其他风格的写作?您最推崇的美学风格是什么?
刘国强:风格的形成和手法的喜爱,与作者生长环境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与东北人所处的气候环境与放达广漠的大自然有关。与江南人喜欢“小”(小桥、小屋、小巷、小径、小巧)和柔媚相反,东北人所处的气候是大热大冷大风大雪,有许多大工厂、大养殖场、大林场、大山、大水、大岭,受客观环境影响,我很喜欢这些“大”,喜欢阳刚和骁勇,喜欢豁达气势,喜欢苍茫辽阔。在报告文学创作上,也喜欢“正面进攻”、大场面作战。但在创作中我特别在意细节和微观。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巨无霸”都是表面的,内在最结实的筋骨却是“微观”。因为,再大的生命都由最小的细胞构建。换言之,所有巨无霸都由微小的细胞来支撑。反过来说,只有那些微小的细胞十分优秀,“巨无霸”才能呼风唤雨、称雄称霸。正如我所理解的“大场面电影”,许多是中国导演在意投资大、场面大、气势大,往往事与愿违。其实这些“大”只是载体,只是外壳,真正的“巨无霸”在于“最大的思想力量和内心力量”。
不久前,我再次研究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姿三四郎》《红胡子》《罗生门》《战国英豪》《影子武士》等,这些影片没一部大制作。由于拍摄年代久远、当时的电影工艺落后,多数黑白影片模糊不清,但部部惊心动魄、震撼心灵。这些七八十年前拍摄的老电影,当今导演(个别除外)仍望尘莫及!这些几乎都是激昂风格、重大主题的作品。
我主张报告文学创作要汲取多元艺术的营养,包括电影、绘画和音乐。我尝试过多种文体和风格的创作,散文“人体笔记系列”,小说“零下生活系列”,都是单一题材或“小切口”创作,风格的选择或文体的选择像量体裁衣一样,取决于题材、体裁或要表达的思想。一部作品就是一场战争,可能有正面进攻、大兵团作战,也可能化整为零、打穿插或打侧翼。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也与当代战争类似,更多的则是“立体战争”。
难度决定高度。在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创作之前不要有任何回避,而是主动设置若干个难题、若干对“大矛盾”,比如宏观与微观的矛盾,纵向与横向的矛盾,扩充与收敛的矛盾,情节与细节的矛盾,局部与整体的矛盾,直行与转弯的矛盾,等等,在创作中捉对解决了这些难题和矛盾,作品一定会登上较高的台阶。
我在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上,着力在追求独特的“视角”上下功夫。比如,全景扫描的视角,悲喜交加的视角,小中见大的视角,侧面的视角,悬念的视角,角色挨骂的视角,人物身份逆袭的视角,等等。在创作上,我推崇以躲过司空见惯的熟悉风景为终生追求,别具审美,迎难而上,向陡峭和奇丽攀爬,以看到别人少见的景观为乐趣。
林 喦: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曾在当代文学和社会生活中产生过引人注目的影响,当下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这一文体写作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压力,您怎么看待当下报告文学写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特别是“非虚构”叙事写作提出之后,您对报告文学写作有无重新认知?
刘国强:新媒体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报告文学,所有纸媒和图书几乎一网打尽。伴随网络的日益发达,形势将更加严峻。但正如图书不会消失一样,报告文学也不会消失。我相信,无论什么文体,只有写出上乘作品,永远会有一席之地。
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处于尴尬境地,或称“文学中的弱势群体”。全国数百种文学期刊,发表报告文学的刊物只有三五家。以省级纯文学刊物为例,除了个别的刊物,都不发表报告文学。这跟当今国际文学图书写实类居多相反,中国小说独大。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在中国,很多理论家和作家瞧不起报告文学一类写实的作品。其实,各种文体皆有自己的位置与作用,也有不同的创作手法与难度,互不可替代,不应该有文体歧视。国际上许多文坛大腕都是由纪实文学“起家”的。迄今获诺奖的作家共112 人,这些大文豪,有记者履历的占10%。海明威、丘吉尔、马尔克斯、怀特、略萨、帕斯、蒲宁、莫言,都写过大量的纪实文学作品。
多数人熟知的茨威格创作了那么多精彩小说,其实他也是纪实文学高手。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亦有轰动效应,产生了全球性影响。菲利普罗斯的《遗产》早就跻身世界名著中。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写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系列作品,非常震撼,不仅写出肉体疼痛,更写出灵魂疼痛和人类未来前景的“疼痛”。
我们在《红楼梦》中不难发现,这部小说有着浓重的“纪实风格”,人称“百科全书”。书中官场风云、君臣争斗、才子佳人、诗词歌赋、商业、建筑等就不用说了,里边的菜谱、中药方子至今能用,健康“补方”也流传后世。从某种角度说,正是扎实的写实基础建立的文学高峰,后人只能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
非虚构文体是个很模糊的概念,除了少数搞创作的人,多数人并不知道“非虚构”可以虚构、至少有部分虚构。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多数读者而言往往是一种误导。除了法律上的回避、怕惹麻烦,当今的许多非虚构作品已经部分丧失了写实功能,或者说,非虚构与虚构“二体合一”了。比如,有的非虚构作品集中写个地名,实际上这个地名根本不存在。比如,将一年的时间“浓缩”成一个季节,把几个人物“合并”成一个人物,把几个人的事“串成”一个人的事,等等。对多数读者来说,“根本不知情”。
这样的非虚构对作家来说“很有利”,会“集中优势兵力”把人物或故事写得更好看,脚力不到也没关系,不影响发挥“合并”或“半虚构”的功能。如果人物、地名、故事都是假的,就可能放开手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阿来的非虚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还曾引发过不小的争议,已经顺利入选十部作品提名奖,终评落选。阿来因此提出抗议,一时间媒体争相报道、炒作。据说争议的焦点便是:非虚构和报告文学不是一回事。有评委甚至质疑:所写的内容为几百年前的人和事,怎么能保证其真实性?
我们在此不讨论争议本身的是与非,就当前非虚构文体现状看,起码有虚与实之间的不确定性,这便造成文本内容的不准确性。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则不同,作品的所有人物和故事地名等都是真实的。这是报告文学的硬件要求,也是报告文学作家所坚守的原则,更是必须秉承的良心所在。
真实的作品,人们会当成“参照物”,也有对比、借鉴、取证和留存的意义。当前流行的非虚构,永远取代不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
林 喦:是的,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好作品是不会被落下的,好文体也是会受到读者青睐的。
语言是作品的灵魂,在报告文学文体中,因新闻性的需要,个人语言的风格表现是否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您怎么看待当下文学写作的语言问题?
刘国强:如果把文学比作建筑,那么语言就是最小的建筑单位。建筑材料的好坏,直接影响甚至左右、决定建筑质地。建筑原料为坯、砖、石头、玻璃、金属,建筑品质将天壤之别。检验建筑作品我们不必面面俱到,“抽样检测”就行。同理,无论是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多么厚的书,只看几页就知道作品品质了,因为,整部书都是用这种材料建筑的,没有必要多看。打个比方,整栋大楼都用同一厂家、同样的材料建筑,“抽样检测”已经足够,还有必要一砖一瓦都看个遍吗?
汉语语言既是记录符号的形式、载体,更是内容。语言本身就具备表达思想的功能。一部书、一篇文章表达不同的内容,一句话、一组词、一个字,也表达着不同的内容。它们之间只有容量之分,没有属性之分。因此,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语言是作品的灵魂”。没有好的语言,不可能有好的作品。就像没优质的建筑原料,就不会有优质建筑物。锤炼语言是文人的“基础武功”,武功基础不行,就别抱取胜的幻想。武功高手从繁杂而琐碎的“一招一式”练起,这一招一式,就相当于文学作品的语言。
许多人赞同“语言要朴素”“语言越朴素越好”,我觉得至少不全对、不准确,甚至有误导之嫌。此朴素不是彼朴素。文学作品中的朴素语言,是锤炼后的朴素,而不是原生态朴素。打个比方,具有相当级别的领导视察或检查叫“下基层”,普通的工人农民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就不能叫“下基层”。因为,你本身就是在基层的基层人。
参军要挑身体好的,移苗要挑健壮的,养殖要挑没毛病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不挑优质语言呢?
在小说创作中“被误导的”也很多,认为“口语创作”就是小说语言。其实非常不准确甚至进了误区。人们公认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叙述语言好,公认毕飞宇小说《玉米》的叙述语言好,公认阿城小说《棋王》的叙述语言好,许多人赞赏迟子建的叙述语言好,我们仔细琢磨琢磨,哪个是原生态口语?都不是。而今,有多少人的小说创作还陷在“口语叙述”的误区中?比比皆是!
我最近读的汪曾祺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深切领悟这位语言大师的真谛,他说:“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我特别欣赏林斤澜先生的作品不合群、不跟风,坚持独树一帜地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人们常把汪曾祺先生和林斤澜先生放在一块说,赞扬他们的小说潮流更迭变幻,认同几乎无人能与他们“比肩”。
林 喦:总之一句话,无论哪种文体的创作,语言既是“第一道关”,也是“最后一关”。没有好的语言,作品入门的“品相”差,过不了“面试关”,“灵魂”差,必然过不了“终审”关。
刘国强:对,报告文学也在上述“语言的管理体制”之内,没有捷径可走。当前是报告文学创作既多又少,作品数量多、优质的极少,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关卡就是多数作品被挡在“优秀语言门外”。
报告文学只是一种文体,创作中没有语言风格的限制。作家尽可以施展语言天赋或才能,不受语言的束缚。因为,同样为“文学建筑”,选择什么建筑材料完全取决于建设者,不在客体文本。
林 喦:在报告文学写作和散文、小说写作之间,由于文体不同,您的创作思维转换是怎么做到的呢?生活中的哪些素材最能激发您的创作欲望?
刘国强:从广义上说都是文学创作,没必要在概念上设置障碍。在结构、语言和塑造人物等方面,这些文体有相通之处。正如我在上边所说,绘画音乐影视戏剧和诗歌都可以参与进来。我没有提到的民间文学、地方戏、曲艺等,也可以参与进来。虽然在体裁上已经各自独立,甚或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专业体系及创作特点,但从“大文艺观”上说,它们都是文学各司其职的家庭成员。
最近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送我一幅书法作品鼓励我,内容为:“无边无涯是小说”。这几个外延意义很强的鼓励语字数虽少,却让人浮想联翩。王蒙先生86 岁高龄,仍在持续创作、宝刀不老,每年都发表质地很高的小说作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特别抢眼,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先生始终在持续探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小说”换成“散文”或换成“报告文学”呢?至少可以相互贴近或交融吧?
在欧美国家,文学大致分为虚构和非虚构。没有中国分得这样细。西方的绘画也一样,不管你用什么材料,也不管你怎么画,是画就行。没有中国的绘画分得出这么多画种。粗分和细分各有利弊,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文学艺术是“一家人”。
我根据题材、素材及规模的不同而分别创作不同体裁的作品。比如现实生活中真实而震撼的人物或事件,故事的曲折程度和震撼程度远远超过虚构,我会首选创作报告文学。因为这是真人真事,有“直面读者”的效果。这样的题材如果写成小说,影响力就小了。因为,即便不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小说再好也是“编的”。换言之,这样的题材只有报告文学能起到“直接介入生活”的作用。另外,报告文学可以“现场指导生活”。比如行业报告文学,单位组织统一采购、集中学习,用以指导工作。此外,报告文学还有史存价值。
我发现人物非常好,或者题材非常独特,写报告文学素材不够丰厚,或者某些方面太单一,我会将其写成小说。独有的角度或人物、故事、思想“单薄些”也没关系,虚构的小说恰好可以弥补。东边的脑袋,西边的胳膊,南方的身子,北方的智慧,完全可以“合并同类项”嘛。当然,还可以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尽情地虚构。
一些“小规模”的素材,我会选择散文创作。但,绝不是“边角废料”。素材规模虽小,却照样有“闪光点”。“小规模”素材不等于作品“当量小”。正如一列车沙子的价值抵不上一小块宝石,体积与价值经常是不对等的。创作短作品“不藏拙”,往往难度更大。
林 喦:由于时间的原因,有时间再向您讨教。谢谢您。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