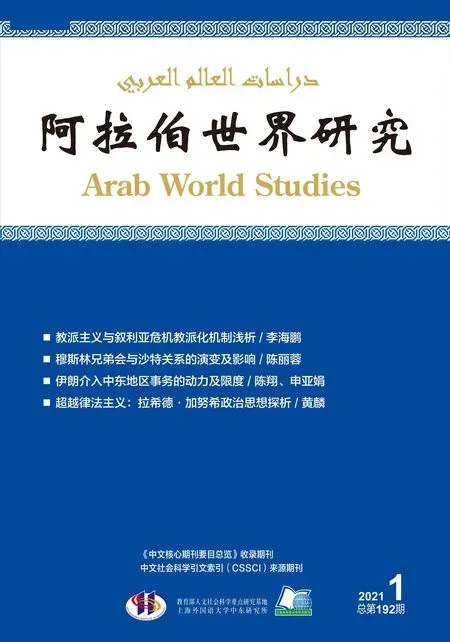从宗教服饰到政治符号:伊朗女性头巾摘戴之争
潘 萌 哈全安
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西化与传统之争、世俗与宗教之辨是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女性头巾的摘戴争议则是其缩影。 伊朗女性头巾的“摘”与“戴”,不仅反映了伊朗政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轨迹,成为管窥伊朗政治变革的窗口,而且这一问题已经超出女性个人生活和宗教文化领域,被赋予了更多政治内涵。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佩戴头巾的女性已然成为伊朗在国际社会中“保守”形象的“代言人”。 回顾学界对伊朗女性头巾问题的相关研究,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宗教信仰、女性个人权利以及性别政治等视角①相关文献参见Abdulla Galadari, “Behind the Veil: Inner Meanings of Women's Islamic Dress Cod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s, Vol. 6, Issue 11, 2012, pp. 115-125; Minoo Derayeh, “The Myths of Creation and Hijab,” Pakist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Alam-e-Niswan, Vol. 18, No. 2, 2011, pp. 1-21; Hamideh Sedghi, Women and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and Reveil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ennifer Heath, ed., The Veil: Women Writers on Its History, Lore, and Poli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eyedeh Razieh Yasini, Mahdi Montazer Ghaem and Abdollah Bicharanlou, “The Discursive Politics of Women's Clothing in Iran at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Era (1979-1981),” Pertani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Vol. 26, 2018, pp. 103-124。上,从政治符号层面分析伊朗女性头巾摘戴现象的论述较为少见。 在伊朗的政治运动中,女性头巾的“摘”或“戴”蕴含何种象征意义、为何头巾的摘戴过程具有反复性,以及缘何官方与社会都对女性头巾的摘戴问题密切关注,均是尚待探讨的问题。 因此,本文拟以政治符号视角,从伊朗关于女性头巾摘戴的百余年争论与政治现代化发展历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女性头巾从宗教服饰演化为政治符号的历史进程及其背后的政治逻辑。
一、 女性头巾: 政治符号与宗教服饰的政治符号化
关于“政治符号”(political symbol)的概念,拉斯韦尔和卡普兰从功能角度出发指出,“政治符号是指那些在某种重要程度上运作于权力实践之中的符号……它们直接运作于权力过程之中,发挥着建构、改变或者维系权力实践的作用”②[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美]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王菲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6 页。。国内学者认为,“携有政治信息、表达政治意义的符号即为政治符号。 因而,政治符号既是携有政治信息、具有政治意义的物质载体,又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①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2 期,第72 页。。 由上可知,在关于政治符号的定义中,其核心在于强调该符号被应用于政治领域,具有政治意义,并与政治权力实践紧密相关。 此外,对西方文献的不同翻译方式使得中文语境中的“政治符号”与“政治象征”常混淆使用。 “在西语中,象征(symbol)一词经常当做‘符号’意义来使用,这是西方符号学自身混乱的原因。”②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4 页。基于此,本文统一使用“政治符号”来表示在政治语境下产生象征意义的某一事物,并将其界定为:将本体赋予政治意义,并广泛存在于政治领域的象征符号,即为政治符号。 首先,政治性与象征性是政治符号的基本特性。 一个符号可以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但只有当它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被给予政治象征含义时才可能称为政治符号。 其次,政治符号具有变化性。 政治符号的产生过程与政治运动进程相伴而行,不仅在不同政治进程阶段的政治符号具有变化性,同一象征物在不同政治进程中的象征意义与使用方式也不同。 最后,政治符号还具有共鸣性。 使用政治符号的最终目标是让更多人通过对政治符号的认同,进而与政治符号下蕴含的政治理念发生共鸣,并对政治权力产生服从。 只有能引起共鸣的政治符号才能称为有价值的政治符号,从而实现“用符号操纵大众达成重大目标”③[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81 页。。
就功能角度而言,政治符号一般具有划分政治归属、代表政治权威、体现政治合法性以及强化政治认同四大功能。 首先,利用政治符号可以划分政治归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会使用不同的政治标志予以区别,对同一政治符号的不同态度也能确定其所属政治立场。 其次,政治符号代表着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和政治秩序的体现。 “权力必须披着象征的外衣才能表现出来。 象征是支持政治统治秩序的必需品。”④[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3 页。一方面,政治符号产生的过程是在政治活动中运用象征物强调和确立政治权威的过程。 另一方面,政治符号展示的过程也是向外界传达和强化政治权威的过程。 再次,政治符号的运用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 政治符号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因而政治符号的运用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宣示。 此外,民众对某一政治符号的认同也标志着这一政治团体所具备的社会基础,是该政治团体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的体现。 最后,利用政治符号可以强化政治认同。 每一个政治符号的出现都与其社会政治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政治符号也正是利用其与社会文化间的关联性,获得了广泛的政治认同感。 “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些象征就是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①[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 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19 页。政治力量通过利用多种政治象征,实现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领域的传递。 民众通过对政治符号的使用,实现政治互动,从而增强政治参与感与认同度。 因此,政治符号被应用的过程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另外,政治运动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和斗争的群众性,所以在政治运动中的政治符号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具备该项政治运动的特质,能够代表政治运动的核心内涵;二是形式简洁,源于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正是因为这些象征符号源于日常生活,其才能在社会群体中引起广泛共鸣,进而迸发出强烈的引领作用与号召力。
服饰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不仅具有大众性特征,而且与所属的社会环境、宗教文化难以割舍。 “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都可能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不同的服装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②[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第182 页。当服饰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政治符号后,与其他政治符号相比,具有以下特性:首先,服饰源于生活,与社会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一些政治派别会通过延续、突出或是变革、剔除某些服饰的传统部分,来表达自身保守传统或是激进变革的政治理念。 其次,服饰作为每日必须穿着的日常用品,可以时时地反映出穿着者的政治立场。 在政治活动中,往往通过身着不同的服饰,直观地展现个体所属的政治派别。 不同的政治派别往往也通过定制不同颜色、款式的服饰直观地划清政治界限。 服饰是大众生活用品,当服饰成为政治符号后,往往会形成“一人穿着、众人穿着”的景象,故能引起广泛的政治认同,并在政治运动中激发民众的政治激情。 在日常服饰中,帽子、头巾等戴在头部的物品,由于更加显眼,其在政治领域中也常常作为政治象征符号被广泛使用。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使用的三色徽,最初起源于1789 年7 月法国革命期间革命军所戴的帽章,后来“三色徽成为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对它的态度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①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9 页。。 此外,在一些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帽子、头巾等服饰的变革还象征着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 例如,在土耳其凯末尔时代,西化与世俗化是土耳其政治道路的发展方向。 凯末尔认为,菲斯帽(Fesi)是土耳其人无知愚昧和抵制社会进步的标志,而西方礼帽则是现代文明的象征。②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8 页。因此在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官方强制民众以西方礼帽取代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盛行的象征穆斯林身份的菲斯帽,时人称之为“帽子革命”。
“广义而言,宗教服饰指公共、家庭和个人祭祀活动中穿着的范围广泛的服装和饰物。”③《不列颠百科全书·宗教服饰》,邓学禹译,载《宗教学研究》1983 年第3 期,第93 页。这类服饰或是在宗教活动中逐渐产生,或是在宗教经典中被规定。从功能上看,宗教服饰具有划分宗教派别、体现教旨教义、激发信仰服从等作用。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宗教服饰,同一宗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服饰也有不同,宗教服饰由此成为区分不同宗教、不同派别的重要标志。 宗教服饰一般具有固定样式和花纹,并常常与该宗教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事件等密切相关,体现了对该宗教教旨教义的传承,具有特定象征性内涵。 一些宗教服饰的应用往往与特定的宗教活动相关联,用以表现宗教仪式的神圣性。 因此,宗教服饰的诞生和应用是实现信仰服从的重要方式。 在宗教服饰与民族服饰、日常服饰的关系上,一些宗教往往与某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在民族服饰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宗教性的印记,体现出宗教在民族文化塑造中的独特作用。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服饰也会具有某些宗教标志,展现了宗教融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此外,宗教服饰本身就是宗教秩序的标志。 在一些宗教中,常以不同的宗教服饰来区别不同的等级,或者一些特定的宗教服饰只允许某些特定的宗教人士穿着,以此形成在宗教群体内部的权威与秩序。
历史上,政教合一在诸多文明中并不鲜见。 无论是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抑或是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宗教都是维系国家统治的重要力量。 但近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使得政教合一在国家政治中走向分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开始了世俗化进程。 政教分离和理性主义成为了西方政治的基本原则,而唯物性、多元性与分权性成为西方政治的突出特点。 然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并非一成不变。 在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在凝聚民族国家认同、整合社会力量和维系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成为部分国家政治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依托宗教建立的国家,其政治系统和运作方式也被赋予了宗教特征,使得国家权力兼具神圣性、唯一性与集权性。 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力量成为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进程中,宗教服饰开始被赋予政治内涵,成为政治符号。 如果说普通服饰的政治符号化是服饰在政治运动中被赋予政治意义的过程,那么宗教服饰的政治符号化,则是将宗教服饰内本身蕴含的权威和秩序向社会政治领域拓展的过程,是以宗教秩序塑造政治秩序。 在宗教服饰向政治领域延伸的进程中,宗教逐渐渗透并塑造社会政治观念、等级秩序与权威归属。 对于神的解释权是宗教等级秩序建立的依据,解释权的唯一性是宗教赖以维系的方式,而由人所主导的对神性诠释的垄断则缔造了物质资料和人身依附关系支配下的权力秩序。 宗教服饰穿着的政治社会化是宗教从对宗教领域中神性的垄断向对社会生活领域中人性垄断的发展过程,进而缔造了宗教政治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伊斯兰教中,头巾是广大穆斯林女性的日常服饰。 《古兰经》中曾言:“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的弟兄的儿子,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 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 信士们啊! 你们应全体向真主悔罪,以便你们成功。 (24:31)”①《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8 页。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宗教学者对女性佩戴头巾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规范。 在伊斯兰世界,各国对女性佩戴头巾的要求存在差异,头巾样式也各不相同。②本文中将穆斯林女性佩戴的可遮蔽头发、面部等部位的服饰,如头巾、面纱、罩袍等统称为头巾,常见样式包括希贾布(Hijab,阿拉伯语意为“遮盖”,通常用来指穆斯林女性佩戴的头巾,多为方形,覆盖女性头部、耳部、颈部)、莎伊拉(Shayla,裹在头上,肩膀处被塞住或有固定,脸和脖子暴露在外,颜色多样,多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流行)、阿米拉(Al-Amira,由紧贴的帽子和围巾组成,露出面部,过肩,覆盖部分前胸,颜色多样)、希玛尔(Khimar,长及腰部,完全遮盖住头发、颈部、肩部,面部裸露,似斗篷状)、查多尔(Chador,波斯语词,原意为“帐篷”,多为黑色,一般无袖,由头部披下来几乎到地面,遮住除脸之外的身体部位,多什叶派穆斯林女性穿着)、尼卡卜(Niqab,几乎覆盖全脸,只留眼睛的面纱)、布卡(Burka,覆盖全身、只在眼睛部位留有网格样的窗口的罩袍)等。在很多国家官方层面对是否佩戴、应戴何种女性头巾作出了明确规定。 自伊朗现代化进程开启至今,其国内社会对女性头巾的佩戴问题一直存有争论。 一方面,无论是巴列维王国还是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官方都将女性头巾的“摘”或“戴”作为划分政治归属的标志,并将女性头巾问题作为宣扬政治权威、强化政治认同与体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伊朗社会也通过对女性佩戴头巾的态度来表达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反对。 历史上,女性头巾问题在伊朗诸多政治运动中被加以利用,成为社会变革的政治信号。 因而,伊朗女性头巾的“摘”与“戴”,逐渐从宗教服饰问题演化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
二、 头巾嬗变: 伊朗女性头巾的政治符号化进程
随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和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伊朗社会开始了对女性头巾摘戴问题的讨论。 在巴列维王国时期,头巾被视为世俗化、现代化的阻碍,佩戴头巾受到官方层面的禁止。 在伊斯兰革命中,女性选择戴上头巾,来表达对巴列维国王威权统治的反抗。 直到伊斯兰共和国时代,女性头巾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性服饰被官方要求强制佩戴,成为坚持走伊斯兰道路的象征。 此外,伊朗社会和民间也一直具有利用女性头巾问题表达政治态度与诉求的传统。 伴随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派别的斗争与政治道路的分化,女性头巾的“摘”与“戴”逐渐被赋予了政治内涵,走向符号化。
(一) 头巾分歧: 伊朗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初探
自萨法维王朝开始,什叶派伊斯兰教就成为伊朗的官方信仰。 国王自称伊玛目家族的后裔和“安拉在大地的影子”。 王权依靠教权树立合法性,教俗权力浑然一体,宗教受国家控制。 到了恺加王朝时期,王权衰微,国王再无圣族后裔的宗教合法性来源,王权与教权分庭抗礼,二元并立。 教权控制宗教、教育、司法领域,并与巴扎商人组成利益联盟。 宗教团体逐渐成为伊朗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影响。 与此同时,伊朗的社会文化习俗严格按照什叶派伊斯兰教规定,女性身着罩袍,佩戴面纱,被牢牢禁锢于家庭范围之内。 正如当时一位作家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男人的国家中,看不见女人。 但奇怪的是,街头有一半的人,从头到脚被黑色袋子包裹着,甚至连呼吸的缝隙都没有。”①Hamideh Sedghi, Women and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and Reveil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
恺加王朝时期,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伊朗主权不断沦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伊朗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开始解体,现代化进程开启。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国家主权遭受侵犯,教俗各界开始探索伊朗的发展之路,民族主义运动兴起。 其中,在19 世纪末爆发的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中,伊朗宗教界发挥了重要作用,运动获得成功。 “烟草叛乱反映了一个由愤怒的教士领导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商人的联盟已经出现。”①[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版,第121-122 页。之后在宪政运动中,伊朗社会各界开始了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行动,而“伊朗女性通过参加1889 年至1891 年的烟草运动和1906 年至1911 年的宪政运动表明了他们对政治事务的浓厚兴趣。 尽管她们的贡献无人承认,她们的要求也从未实现。”②Minoo Derayeh, “The Myths of Creation and Hijab,” Pakist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Alam-e-Niswan, Vol. 18, No. 2, 2011, p. 12.大部分参与宪政运动的女性选择在清真寺集会,激进者甚至将枪藏于罩袍之下。 但在政治运动中,开始出现女性自发的公开摘掉头巾,表达政治诉求的行为。 如在宪政运动中,许多聚集在德黑兰街头的女性摘下头巾,大喊“自由万岁! 我们必须过着自由的生活”。③Hamideh Sedghi, Women and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and Reveiling, p. 25.女性开始通过摘掉头巾,表达寻求自由与解放的政治意义。
宪政运动中的教俗各界形成了广泛的政治联合。 这一时期通过的宪法及其补充条款明确将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伊朗国教,但宪政运动中提出的关于女性的选举、教育等各项权益并未实现。 随着宪政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政治道路出现分野,教俗政治联盟开始分化,教俗是否分离成为新的争论焦点。 伊朗女性是否应该佩戴头巾的问题,也开始被社会更为广泛地探讨。 例如,伊朗当时著名的女性报纸《女性世界》在1912 年至1932 年间发表了大量关于女性是否应该佩戴头巾的文章。 其中有人提出,“毫无疑问,头巾是女性就业的一大障碍”“我们的低下就是因为头巾,它将我们束缚并囚禁于家庭”。④Farzaneh Milani, Veils and Words: The Emerging Voices of Iranian Women Writer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5-96.同时,也有女性对摘下头巾持反对态度,并认为佩戴头巾是对伊斯兰传统道德的遵守和对女性的保护。 女性应该摘掉头巾的呼声,多源于民间世俗主义的支持者,并受到以教界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抵制。 “那些公开批评头巾的人受到了乌里玛的谴责,遭到暴民的骚扰,并受到政府的迫害。”⑤Minoo Derayeh, “The Myths of Creation and Hijab,” p. 14.女性的头巾佩戴问题,表面上是对女性个人权利的争论,背后则是现代化进程中伊朗政治道路选择的分歧。 这一时期,女性头巾已然具有作为政治符号的象征性内涵,开始进入政治视野。
(二) 摘掉头巾: 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道路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伊朗沦为半殖民地,伊朗开启了以民族独立和发展为目标的世俗化进程。 1921 年,出身行伍的礼萨汗发动政变,并希望“通过结束内战、实现社会转型、消除外国占领,进而开创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①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p. 118.。1925 年,伊朗第五届议会拥立礼萨汗继位,开启了伊朗巴列维王国时代。 在礼萨汗时期,世俗主义是其执政的重要原则。 世俗化表现为西化、去宗教化,包括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世俗化的生活方式等。 礼萨汗希望通过世俗化进程排斥教权,实现个人极权和伊朗民族国家建构。 在世俗主义实践过程中,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是一项重要内容。 其中,头巾被当成压迫女性的枷锁,并被视为传统与教权的代名词,摘掉头巾则成为礼萨汗时期解放女性、推行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1926年,礼萨汗为以帽子和围巾代替头巾的女性提供警察保护。 1928 年,礼萨汗颁布了《统一着装法》(Law of Uniformity of Dress),其中规定,除教界外,男子必须身着西式服装,头戴西式帽子——“巴列维帽”。 1934 年夏,礼萨汗访问土耳其后,便开始在官方层面禁止女性佩戴头巾以及穿着传统罩袍。 1936 年1 月7 日,在德黑兰师范学院举行的一次典礼上,礼萨汗正式将禁止佩戴头巾上升为国家官方政策,而这一天也被定为伊朗的“妇女解放日”。 在典礼前,学校的女教师和政府官员的妻子们已经被告知要求身穿西式服装,佩戴帽子,而非身着传统罩袍。礼萨汗还要求自己的妻女身着西式服装参加仪式,以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伊朗通过礼萨汗于1936 年颁布的世俗法令的形式完成了头巾政治化过程。”②Minoo Derayeh, “The Myths of Creation and Hijab,” p. 1.在礼萨汗时期,女性头巾问题正式从民间探讨上升为国家意志,摘掉头巾成为伊朗促进女性解放和排斥教权的重要手段。
对很多伊朗女性而言,官方强制要求摘掉头巾的做法令她们难以接受。 就在这次典礼中,一些年长的女性因被强制要求摘掉头巾“感到极为尴尬,以至于在整个仪式中,她们紧紧拥抱并站在墙边流汗,并在男人们面前遮挡自己的脸庞”③Hamideh Sedghi, Women and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and Reveiling, pp. 86-87.。 之后,伊朗开始利用强制手段禁止女性佩戴头巾或身着罩袍。 公共场合戴头巾的女性将会被强制要求摘掉。 甚至警察会到家中搜查逮捕身着罩袍的女性。 但这些做法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农村的女性则会选择用围巾遮住头发。 政府禁止女性佩戴头巾的做法遭到教权阶层的反对。 在德黑兰、大不里士和马什哈德等地都出现了教士对官方禁止女性佩戴头巾的反抗,但遭到了镇压。 “礼萨汗希望通过禁止佩戴头巾的方式,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但这种强制性的做法适得其反。”①Stephanie Cronin, ed.,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Riza Shah, 1921-194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15.很多伊朗女性因禁止佩戴头巾,拒绝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甚至一些伊朗女性选择移民到伊拉克等其他中东国家。 直到1941 年礼萨汗被迫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最终官方禁止女性佩戴头巾的规定在总理阿里·索赫伊利(Ali Soheili)时期被废除。
1963 年巴列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后,什叶派乌里玛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教俗斗争开始激化,而斗争焦点主要集中于土地改革和女性问题。 伴随巴列维国王的世俗独裁统治达到鼎盛,伊朗现代伊斯兰主义开始兴起,并成为民众反抗独裁统治的思想武器。 其中,著名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家阿里·沙里亚蒂号召以先知的女儿法蒂玛为榜样,认为伊朗女性不仅应该承担传统的家庭责任,还应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 他认为,西方文化使伊朗女性失去了传统美德,而“头巾是伊斯兰谦逊意识的回归,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和欧洲文化的拒绝”②Seyedeh Razieh Yasini, Mahdi Montazer Ghaem and Abdollah Bicharanlou, “The Discursive Politics of Women's Clothing in Iran at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Era (1979-1981),” p. 111.。 沙里亚蒂的思想受到了很多伊朗女性的推崇,曾经摘下头巾的女性也开始纷纷戴上头巾,以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并希望在伊斯兰传统中寻求反抗巴列维威权统治的道路。 “掩盖自己的身体成为一种对现状不满的表达,甚至成为抗议、权力和政治的语言。”③Hamideh Sedghi, Women and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and Reveiling, p. 195.这时女性的头巾已经成为反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武器,女性戴上头巾成为了反抗世俗西化的巴列维独裁统治的表现,而这种象征内涵也在后来的伊斯兰革命中被广泛使用。
(三) 戴上头巾: 伊斯兰共和国的宗教立国
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最终导致伊朗民众的普遍反对,在教俗阶层的广泛政治联合下,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 在革命游行的队伍中,佩戴头巾的女性随处可见,这构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历史记忆中的突出景象。 而在伊斯兰革命中,无论世俗还是宗教的反对派女性都选择戴上头巾,以表达对巴列维国王世俗独裁的反抗。 “在巴列维的反对派中,一群女性身着象征伊斯兰教谦逊精神的服装进行游行,这是一种象征和抗议,与她们的宗教信仰无关。”①Seyedeh Razieh Yasini, Mahdi Montazer Ghaem and Abdollah Bicharanlou, “The Discursive Politics of Women's Clothing in Iran at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Era (1979-1981),” p. 111.革命中的伊朗女性通过佩戴头巾,来标榜自己成为一名“革命者”,这时女性戴上头巾已然成为了反巴列维、反世俗主义和革命的代名词。
随着伊斯兰革命的初步胜利,在革命中由教俗各界组成的广泛政治联盟开始瓦解。 以霍梅尼为首的教法学家逐渐掌握了伊朗的政治方向,并最终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在巴列维时期,女性摘下头巾意味着伊朗世俗主义道路、西化和排斥教权。 但在伊斯兰共和国时代,重新戴上头巾则成为反巴列维和世俗主义、反西化以及本土化、坚守伊斯兰道路的象征。 因而,女性头巾的“摘”或“戴”成为区分不同政治道路的重要标志。 霍梅尼在流亡法国时曾表示,“在伊斯兰共和国,女性将自由选择其活动、前途和着装。”②Karim Sadjadpour, “The Ayatollah under the Bed (Sheets),”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12, p. 4.但随着教法学家掌握国家权力,伊斯兰共和国便迅速开启了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强制女性重新戴上头巾。 伊斯兰共和国的当权者认为,头巾是伊斯兰道德的象征,“是‘保护女性的盾牌’,是用以抵抗破坏女性人性、荣誉与贞操的方式,是保护伊斯兰免受文化帝国主义侵害的手段”③Seyedeh Razieh Yasini, Mahdi Montazer Ghaem and Abdollah Bicharanlou, “The Discursive Politics of Women's Clothing in Iran at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Era (1979-1981),” p. 110.。 1979 年3 月6 日,霍梅尼最终下达了强制伊朗女性佩戴头巾的法令。 伴随强制佩戴头巾法规的出台,伊朗官方于3 月29 日宣布所有海滩和运动场所开始进行性别隔离。 1980 年7 月5 日,伊朗政府发布伊朗女性雇员的着装规范,要求女性身着长裙、佩戴头巾,或穿长袖衣服、裤子,并佩戴头巾。 伊斯兰政府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的规定,不仅受到了来自部分宗教学者和其他政治派别的质疑,还受到了一些伊朗女性的抵制。 “1979 年3 月8 日,成千上万的伊朗女性,其中包括曾在革命中佩戴头巾以表达其反对意见与革命倾向的女性,参加了街头反对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的抗议活动。”④Jennifer Heath, ed., The Veil: Women Writers on Its History, Lore, and Poli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258-259.但是抗议活动遭到来自伊斯兰革命政权的严厉打击。 而在伊斯兰共和国初期,“国家特工对未能按规定佩戴头巾的女性进行骚扰、蔑视、逮捕、罚款甚至鞭打。 另外,被认为佩戴头巾不当的女性还会遭受来自警察、安全部门、革命委员会成员、真主党成员和道德警察的辱骂、审问、恐吓或攻击。”①Hamideh Sedghi, Women and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and Reveiling, p. 211.直到现在,伊朗仍有道德警察对女性佩戴头巾进行监督。
在哈塔米总统时期,伊朗曾对女性佩戴头巾的规范有所变通。 来自伊朗改革派的哈塔米奉行“伊斯兰民主制”,倡导政治宽容和个人自由,承诺给予女性更广泛的权益,因而赢得了女性选民的广泛支持。 在哈塔米时期,伊朗女性着装更为时尚,佩戴的头巾样式、颜色开始更为丰富多彩。 她们“更为自由地表达自己,通过时尚来构建新的形象和身份。 深色、不修身的罩袍变成了短的、色彩鲜艳、更为修身的衣服。 黑色的长裤被能露出脚踝的裤子所取代。 小巧透明且图案丰富的头巾取代了黑色的大头巾。 头巾外飘散着一缕秀发,凸显女性的秀丽面庞”②Jennifer Heath, ed., The Veil: Women Writers on Its History, Lore, and Politics, p. 261.。 虽然这一时期官方对女性衣着和头巾的规范有所放松,但哈塔米政府并未取消国家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的法令,伊朗道德警察仍会对未佩戴头巾的女性采取强制措施。
伊斯兰共和国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的做法让很多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对人权的侵犯。 鉴于伊朗国内经济发展逐步遭遇困境,高失业率造成社会矛盾加剧,以女性头巾为手段的抗议成为表达对现政权不满的重要途径。 例如,2009 年伊朗“绿色革命”中就有女性佩戴绿色头巾,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 2017 年夏,伊朗妇女通过社交网站发起了“星期三白头巾”运动。平时女性佩戴的头巾多为黑色或彩色,而这次活动旨在通过星期三佩戴白头巾的行动表达伊朗女性追求个人权利的呼声。 2017 年末,在伊朗因长期经济困顿而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中,伊朗年轻女子莫瓦赫迪(Vida Movahedi)在德黑兰的街道上披散着头发,用木棍挑起白色的头巾,以反抗政府限制个人自由的行为,进而宣泄对伊朗社会长期困顿的不满。 虽然莫瓦赫迪遭到了政府的逮捕,但更多的女性在抗议中效仿她的行动。 “官方确认,在2017 年12 月的骚乱中有35 名女性因抗议强制佩戴头巾的规定而在伊朗首都被捕。 但激进主义者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③Ava Homa, “Mandatory Hijab Law in Iran Inspires Protests,” Herizons, Summer 2018, p. 21.这次抗议活动也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朗女性希林·艾巴迪认为是“伊朗女性反对强制佩戴头巾运动的高潮”①Catherine Marshall, “The Rise of Iran's Feminist Resistance,” Eureka Street, Vol. 28, No. 2, 2018, p. 19.。 实际上,伊朗女性对政府强制要求佩戴头巾的执着反抗,表面上是对着装自由、个人权利的追求,深层原因则是民众对伊斯兰共和国长期经济发展乏力、政治秩序僵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满情绪的宣泄。
三、 头巾背后:伊朗女性头巾摘戴之争的政治意蕴
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与政治道路的抉择使得女性头巾的摘戴演化成为一种政治符号。 无论是对女性权利的彰显还是背后政治道路的选择,皆可透过头巾作一管窥。 俗权与教权间的张力运动是推动伊朗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而女性头巾摘戴的政治符号化过程则是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体现。 关于女性头巾摘戴问题的争论,展现了伊朗不同阶段俗权与教权政治博弈的斗争态势,并体现出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不同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动趋势。 女性头巾摘戴现象的背后蕴藏了伊朗政治发展的逻辑,体现了当代伊朗政治现代化遭遇的困境,并预示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一) “头巾象征”的政治逻辑
自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伊朗国教开始,教权与俗权的博弈便贯穿伊朗政治至今。 教俗合一的政治传统、教俗权力的斗争历程,给予了伊朗女性头巾摘戴问题由宗教服饰演化成为政治符号的历史契机。 恺加王朝末期,伴随着伊朗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伊朗民间利用女性头巾进行政治斗争的行动开始出现,标志着女性头巾的“摘”与“戴”作为政治符号开始进入政治领域。女性头巾摘戴的问题不仅在社会领域掀起了广泛讨论,亦成为划分政治派别的重要标志。 “对西方人而言,佩戴头巾已成为压迫女性的象征”②Abdulla Galadari, “Behind the Veil: Inner Meanings of Women's Islamic Dress Cod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s, Vol. 6, Issue 11, 2012, p. 115.,因而主张向西方世界学习、具有世俗化倾向的伊朗政治群体对女性佩戴头巾大体也持反对立场。 但以教权阶层为主要代表的政治保守派则坚持主张伊朗女性必须遵从教规佩戴头巾,利用头巾摘戴划分政治归属的现象开始出现。 然而,这一时期伊朗对女性是否应佩戴头巾的讨论多源自民间,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尚无定论,头巾佩戴与否最终也无定数。
从巴列维王国到伊斯兰共和国时代,对女性头巾摘戴的争论经历了从民间探讨到官方强制的历史过程。 作为政治符号的女性头巾,成为塑造政治价值体系、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趋向,亦展现每一阶段教俗双方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 在礼萨汗时期,国家通过强制女性摘掉头巾宣示伊朗国家世俗化、西化与国际化。 通过在伊朗社会推进世俗主义,伊朗将国王的世俗权威凌驾于宗教权威之上,彰显了世俗王权的政治合法性。 在伊斯兰革命时期,女性头巾的佩戴体现了作为革命者反抗巴列维国王个人独裁的政治倾向。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反西化、反世俗化、伊斯兰化组成了伊朗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根基,女性佩戴头巾则成为反对巴列维时代世俗化、西化,以及美伊特殊关系的突出表现。 国家对女性佩戴头巾的强制要求成为新政权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与彰显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女性佩戴头巾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突出体现。 在当下,伊朗女性佩戴头巾的规范程度、颜色、方式等都体现着不同的政治立场。
教权与俗权的政治斗争始终贯穿了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国家与神职人员就女性性别特征展开权力斗争,其中头巾问题则是斗争核心”①Hamideh Sedghi, Women and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and Reveiling, p. 280.,由此形成了伊朗关于女性头巾摘戴问题的百年争论。 不同时期的伊朗官方“一直在努力将伊朗女性的形象限定在与其意识形态相符的范围内”②Jennifer Heath, ed., The Veil: Women Writers on Its History, Lore, and Politics, p. 262.。 女性头巾作为宗教服饰逐渐在政治运动中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并演化成为政治符号。 因而,头巾在伊朗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了一种政治身份的模式化。③John Borneman, “Veiling and Women's Intelligibility,” Cardozo Law Review, Vol. 30, No. 6, 2009, p. 2745.伊朗教俗合一的政治传统是女性头巾由宗教服饰转化成为政治符号的历史土壤。 在女性头巾象征的背后蕴含着政治逻辑,即头巾的“摘”或“戴”代表着“世俗化”或“伊斯兰化”的不同政治倾向,成为表达政治立场、划分政治阵营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 国家利用强制女性摘掉或佩戴头巾的方式,试图以政治服从强化政治认同,从而实现政治权威由上至下的一以贯之。 政治符号的运用是政权统治逻辑的体现,而对政治符号的抛弃则象征着政治秩序的瓦解。因而,无论是巴列维王国还是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社会在头巾佩戴问题上一直都受到来自官方层面的强制压力,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的渗透。 同时,利用女性头巾问题表达政治诉求也一直是民间政治运动的重要手段,表达了社会民众对官方强制力的抗争。
(二) “头巾博弈”与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困局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伴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断变革。 在中东地区,“传统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中东现代化的进程。 伊斯兰传统文明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①哈全安:《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版,第448 页。。 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教俗博弈成为经济变革与阶层变动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女性头巾的“摘”与“戴”作为俗权与教权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关注焦点,以及双方政治理念差异的外在表现,成为体现政治合法性与表达政治立场的政治符号。 教权与俗权的政治斗争是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表现,伊朗女性头巾反复摘戴的过程实际体现出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教权与俗权两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困局。 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兴产业的出现,伊朗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动,由此带来世俗权力诉求的增长,世俗化与西化思潮一时蔚然成风,直至礼萨汗时代世俗立国成为国家根基。 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了乡村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等新兴政治力量的壮大。 但与此同时,传统教权群体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受到严重打击。 加之在威权体制框架下,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失衡,民众合理的政治诉求无法获得满足,由此给予教界人士与巴扎商人、手工业者形成广泛政治联合的契机。 因教权具有完善的基层组织系统、完备的物质支撑体系,以及受到社会成员广泛遵守的律法体系,其在政治运动中可运用宗教的统一信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因而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完成政治运动使命。 在伊斯兰革命中,教权在与俗权的斗争中最终胜出,并形成以什叶派伊斯兰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政权基本框架。 革命期间,女性佩戴头巾也成为革命者反抗巴列维国王的突出象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巴列维王国的全新政治体制,但在巴列维时期或是更早时代的历史遗产,例如经济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却被伊斯兰共和国继承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伊朗是一个“把现代化的组织方法、传统宗教价值观念和广大民众的呼声结合在一起”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9 页。的发展中国家。 它以伊斯兰宗教社会体系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 不仅维护伊朗以什叶派伊斯兰为根基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成为维系利益集团稳定和国家政权存续的重要手段。 女性佩戴头巾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对女性头巾佩戴问题的强制则成为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方式。 然而,伴随现代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伊朗的社会阶层不断变动,新兴产业阶层不断扩大。 新的社会群体在经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影响下,以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目标,并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中包括伊朗庞大的青年群体在内的普通民众,构成了伊朗当下新世俗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权统治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却逐渐呈现出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 教权与俗权的矛盾日益显现,并在伊斯兰共和体制、军队、财税、司法、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皆呈现对抗态势。 女性头巾的摘戴问题作为教俗长期斗争的政治象征以及双方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关注焦点,亦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战场。 “头巾博弈”实为“教俗博弈”,女性头巾摘戴的未来将取决于教俗双方政治力量的斗争结果。
(三) “头巾自抉”与伊朗政治现代化未来
在伊朗未来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教俗博弈将成为影响伊朗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 在教俗斗争中,如果伊朗政治天平完全向教权倾斜,头巾将继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与政治合法性的象征而被要求女性强制佩戴。 然而,教权的巩固将加深以宗教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固化趋势,政治保守化倾向将与伊朗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 新兴阶层的政治诉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最终停滞的政治秩序将被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所打破,变动的经济秩序最终带来的是动荡甚至破碎的政治秩序。 若未来伊朗政治天平的发展完全倾向于俗权,伊斯兰共和制可能将被世俗政治所取代,头巾也将作为教权的遗产而被抛弃。 然而,由于伊朗的宗教与政治长期浑然一体,什叶派伊斯兰已然成为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全盘世俗化不仅会造成伊朗国家意识形态的混乱,更会造成伊朗民族认同危机,进而导致国家秩序的全面混乱。 所以全盘倾向“教权”或“俗权”都无法与伊朗国家政治发展传统以及当代社会阶层变动趋势相匹配,均可能会造成伊朗政治秩序的动荡,并导致伊朗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现代化进程一般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阶层的急剧变动,需要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及时变革以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的持续发展。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有序的政治秩序是现代化推进的坚实基础。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6 页。因而,伊朗以国家力量开启教俗关系调试,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拓展国家政治维度,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在此过程中,宗教既要发挥其组织机能,又要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以宗教上的开明和宽容推动政治体系的革新,从单向度的政治统治走向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利用宗教的整合动员效能统合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元利益诉求,从而拓展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并探索出一条中东地区独有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在此基础上,女性头巾的摘戴问题将会从政治符号转化为社会生活符号。
现代化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历史进程,经济领域的飞速变动将会带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剧烈变革。 期间,宗教的等级制和权威性将受到来自唯物主义、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击,因而在依托宗教建立的国家秩序中,需要及时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使政治系统可以有效容纳新兴阶层的发展与诉求。 “公民权是现代文明的社会基础,自由则是公民权的基本要素,亦是现代文明之区别于传统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服饰自由构成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②哈全安:《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第462 页。伴随着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壮大,公民个人权利将得到有效尊重。 政治改革和发展将使新兴阶层在政治权利中的表达渠道和能力逐渐扩展,公民自我权利的获得将成为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头巾自抉也将作为女性在个人社会生活领域自我权利的体现,标志着伊朗未来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四、 结语
在伊朗教俗合一的政治传统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头巾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宗教服饰,逐渐成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 女性头巾的“摘”与“戴”变成了不同政治派别划分政治归属、宣扬政治权威、强化政治认同与体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回顾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女性头巾作为政治符号,经历了由民间政治理念探讨到国家意识形态抉择的历史过程。 在不同时期,官方通过对女性头巾摘戴的强制要求,进而实现政治权威与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领域的渗透。 在礼萨汗时期,女性摘掉头巾彰显了巴列维王国以世俗立国、排斥教权和西化的政治倾向。 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女性戴上头巾宣示着以宗教立国、排斥俗权和反巴列维、反西化的政治态度。 这两个时期官方在对待女性头巾问题上,均表现为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特点,有悖于女性人权自由,可谓异曲同工。 在伊朗民间政治运动中,逐渐形成女性通过头巾表达与官方不同立场的政治传统,这一现象在伊斯兰革命中的体现尤为突出。 女性头巾的“摘”与“戴”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教俗博弈的鲜明表征,而俗权与教权之间的张力运动则左右着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历史上,宗教在伊朗社会中积蓄了强大的力量。 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则需要借助宗教力量凝聚民族意识、建构央地关系,以及维系有效的国家政治秩序,因此宗教成为伊朗政治秩序建立与维护的重要依托。 但是,发展中的生产力和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冲击着政治秩序的基础。 新兴社会群体和宗教传统势力之争,只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相互博弈的缩影。 经济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前提在于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而维系伊朗政治稳定的根本路径则在于将自下而上的社会诉求融入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从而实现政治体制对新兴社会群体的接纳。 通过政权的自我革新与完善,进而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充分利用传统政治力量的引导优势和发挥新兴政治力量的促进作用,应成为伊朗政治现代化的方向。 因此,女性摘掉头巾不一定象征“进步”,戴上头巾也不一定代表“退步”。 女性头巾的“摘”与“戴”最终将作为公民自由权利的体现,从自上而下的强制走向个体的自由选择,从政治约束变为个人自抉,成为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社会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