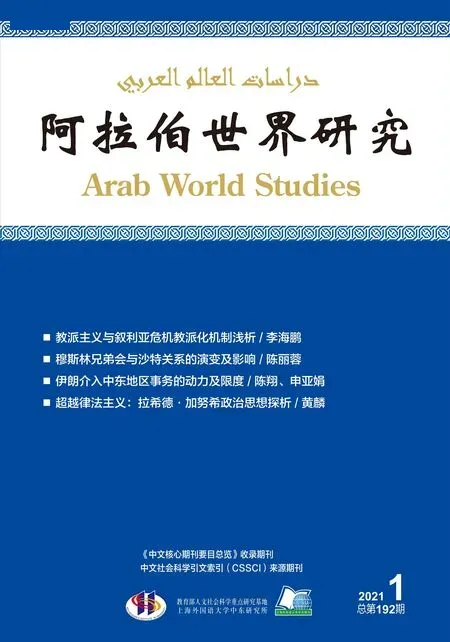伊朗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动力及限度∗
陈 翔 申亚娟
2020 年1 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Quds Force)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uleimani)被美国袭杀,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升级,美伊两国的报复与反报复行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苏莱曼尼被称为“影子指挥官”与“伊朗代理人战争总设计师”,在伊朗国内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声名显赫。 在苏莱曼尼遭暗杀以后,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开启了伊朗直接攻击美国军事目标的先例。 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Popular Mobilation Force/PMF)等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采取报复性行动,代理人战争依然是伊朗地区安全战略的主要抓手。 事实上,自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代理人战争一直是伊朗介入中东事务的战略工具,也是伊朗与地区对手博弈的有力筹码。 目前,国内外对代理人战争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主要涵盖了代理人战争的含义、形式、动因、过程及影响等几个方面①参见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righton and Eastbowrne: Susex Academic Press, 2014;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Eli Berman and David A. Lake, eds., Proxy Wars: Suppressing Violence Through Local Agen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2, No. 3, 2002,pp. 29-47;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1 期,第27-52 页;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 年第4 期,第124-155 页;陈翔:《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代理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1 期,第2-23 页。,但对伊朗在中东代理人战争的研究多为新闻评论类成果,对于这一重要国际政治现象的学理性研究相对有限。 本文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实践出发,着重分析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动力及其限度,并据此展望伊朗代理人战争的前景。
一、 伊朗在中东地区代理人战争的表现
代理人战争在二战以后就逐渐盛行起来,在国际冲突中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认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进行的国际冲突,将使用第三国的人力、资源及领土作为实现本国目标与战略的手段。②Karl W. Deutsch, “External Involvement in Internal Wars,” in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Problem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 102.多伊奇主要从国家中心角度解释代理人战争,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 安德鲁·芒福德(Andrew Mumford)指出,代理人战争是第三方希望影响战略结果而间接介入冲突的战争形式。①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p. 11.综合以上观点,本文将代理人战争定义为间接干预的暴力冲突形式,即行为体不直接参与,而是借助于第三方作为代理人间接参与其中的战争形态。
作为中东地区大国,伊朗将代理人战争作为应对战略压力及拓展战略利益的有力工具。 自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积极资助各种地区武装组织,为它们提供武器、资金以及进行培训与训练,打造地区代理人用于对抗及掣肘地区对手。 21 世纪以来,基于应对不同的地区对手和目标差异,伊朗的中东代理人战争主要分布在三个次级战略板块。
第一,在海湾地区,伊朗的代理人战略主要是将伊拉克的“人民动员部队”及真主党旅(Kata'b Hezbollah)等亲伊朗什叶派民兵武装培养为代理人,借助其发动针对美国的军事袭扰。 自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朗持续向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提供武器、顾问、资金与技术支持。 其中,2014 年组建的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是伊朗在伊拉克的重要代理人,由“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伊玛目阿里旅” (Imam Ali Brigades) 以及“萨义德·舒哈达旅” (Sayed al-Shuhada Brigades)等多支民兵武装分支构成,拥有14 万名成员。②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城略地之际,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号召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担任收复国土的先锋队。 在伊朗的大力支持下,这些什叶派民兵迅速壮大为与正规军比肩的骨干力量——“人民动员部队”。 也有学者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的支持与鼓励实际上早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摩苏尔。 参见Nicholas A. Heras, “A History of Quds Force Proxy-Shaping in Iraq,” Iraq's Fifth Column: Iran's Proxy Network,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1, 2017, p. 7,https:/ /www. mei.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P2_Heras_IraqCT_0.pdf,上网时间:2020 年12 月7 日。据美国军事部门官员估算,伊朗每月向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组织提供价值75 万至300 万美元不等的装备与资金援助。③Kimberly Kagan, “Iran's Proxy Wa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May 2006-August 2007, p. 5, http:/ /www. understandingwar. org/report/irans-proxy-war-against-united-states-and-iraq, 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4 日。在伊朗的大力支持下,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力量使用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发射器、突击步枪、爆炸装置等袭击美国驻军及其他目标,开展代理人战争。 伊朗在伊拉克代理人战争的形式主要包括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袭击巴格达“绿区”的美国目标,频繁向巴格达美军基地发射火箭弹等。 2006 年至2011 年间,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宣称对数百起针对美军的袭击行动负责。①“Iran Proxy Militia Vows to Fight Against Forces in Iraq, ” Iranian American Forum, March 22, 2016, http:/ /iranian-americans. com/iran-proxy-militia-vows-to-fight-against-us-forces-iniraq/,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9 日。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在伊拉克代理人战争的目标对象除了美国之外,还包括沙特,这是伊朗与沙特在中东代理人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海湾地区,伊朗还在巴林扶持代理人。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长期致力于向阿拉伯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 海湾小国巴林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这为伊朗传播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利条件。 伊朗在巴林通过提升软实力影响和支持反对派组织、训练武装组织来培养代理人。 根据巴林方面的报告,包括“阿什塔尔旅”(Saraya al-Ashtar)在内的多个地下组织,均是在伊朗统一安排下运作,且伊朗在军事上日益通过提供武器、情报和训练等来支持激进反对派组织。②Majid Rafizadfh, “Iran's Sophisticated Interventions in Bahrain,” Arab News, April 9, 2018, https:/ /www.arabnews.com/node/1281601, 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22 日。迈克尔·奈特斯(Michael Knights)和马修·莱维特(Matthew Levitt)注意到,伊朗经常通过海上通道利用快艇向巴林进行人员和武器渗透。③Doron Itzchakov, “Iran and Bahrain: Ancient Ambitions, New Tactics,”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7, 2018, https:/ /besacenter. org/perspectives-papers/iran-bahrain/, 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22 日。
第二,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伊朗资助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也门哈迪政府军及为其提供庇护的沙特。 尽管伊朗在国际上一直否认其资助也门胡塞武装,公开宣称其与也门冲突无关,但当地局势明显与其存在战略关联。 也门是伊朗对抗沙特的重要平台。 西方研究报告称,“(伊朗)计划在也门建立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民兵组织,为了对抗沙特……伊朗需要利用它所有的牌”④J. Matthew McInnis, “Proxies: Iran's Global Arm and Frontline Deterrent,” CSIS, April 7, 2017, https:/ /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proxies-irans-global-arm-and-frontline-deterrent/,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1 日。。 伊朗向胡塞武装供给武器、训练、技术、顾问等。 伊朗原本通过德黑兰与萨那之间的空中航线向胡塞武装运输军事物质,沙特等国设立禁飞区以后,伊朗转而通过海运向也门输送各式武器。 伊朗也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等其他方面的援助,用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阿里·贾法里(Ali Jafari)少将的话说,“伊朗为其提供了咨询和精神支持”①Ahmad Majidyar, “IRGC Admits Aiding Houthis Against Saudi-led Coalition in Yemen,”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vember 27, 2017, https:/ /www. mei. edu/publications/irgc-admitsaidinghouthis-against-saudi-led-coalition-yemen,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25 日。。 伊朗同时在外交场合声援胡塞武装。 例如,2015 年4 月伊朗向联合国提交“四点和平计划”,呼吁结束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强调恢复也门和平及稳定的唯一办法是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全国统一政府。 伊朗还通过黎巴嫩真主党支持胡塞武装,由真主党向胡塞武装提供培训以及导弹和无人机等装备物资援助。②Seth G. Jones et al., “Iran's Threat to Saudi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e Implications of U.S-Iranian Escalation,” CSIS, August 5, 2019, https:/ /www. csis. org/analysis/irans-threat-saudicritical-infrastructure-implications-us-iranian-escalation,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5 日。胡塞武装则运用各种军事手段对抗也门政府军与沙特领导的联军,特别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内的港口、炼油设施、军事基地甚至首都利雅得的机场等目标,使沙特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 西方媒体、沙特和也门哈迪政府都把胡塞武装描述为“也门版真主党”③李亚男:《胡塞武装会成为“也门版真主党”吗》,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12 期,第35 页。。
第三,在东地中海地区,伊朗扶持黎巴嫩真主党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简称“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 Movement in Palestine,简称“杰哈德”)等武装抗衡以色列,扶植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助叙利亚政府军对抗美国、土耳其等国扶持的反政府逊尼派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成为伊朗最重要的忠实代理人,通过反抗以色列及打击该地区的美国目标,服务于伊朗的地区战略需求。 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长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及资金支持,借助真主党对抗以色列。 2006 年7 月黎以战争后,伊朗为黎巴嫩真主党继续提供了大量资金与武器援助,重建被以色列破坏的各种设施及重整军队。 2011 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后,真主党积极支援叙利亚政府军。约有2 万名真主党战斗人员被派往叙利亚战场,其主要的武器、训练以及后勤援助均来自伊朗。 2020 年1 月苏莱曼尼遇袭后,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在第一时间痛斥美国的行径,声称要袭击美国的目标加以报复。④“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on Hezbollah: Full Report,” AJC Global Voice, https:/ /www.ajc. org/news/setting-the-record-straight-on-hezbollah-full-report#claim1,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30 日。伊朗还向巴勒斯坦哈马斯与吉哈德提供大量资金援助,促进准军事行动与社会服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为其训练武装人员、提供武器,增强其对抗以色列的能力。
此外,在中亚及北非地区,伊朗试图开辟代理人战争的新舞台。 在中亚方向,阿富汗可能成为伊朗开展代理人战争的潜在舞台,积极谋求与塔利班开展对话,力促阿富汗局势的稳定符合其国家安全利益。 伊朗与塔利班由秘密联系转向公开接触,凸显了伊朗对美国在阿富汗意图的担忧。 一方面,伊朗因自身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之外,亟需寻求其他途径维持其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伊朗认为美国不会真的离开该地区。①Shahram Akbarzadeh and Niamatullah Ibrahimi, “The Taliban: A New Proxy for Iran in Afghanist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1, Issue 5, 2019, p. 765.在阿富汗,伊朗支持塔利班内部的什叶派分支,该分支活跃于阿富汗西部地区。②Shahrbanou Tadjbakhsh, “The Persian Gulf and Afghanistan: Iran and Saudi Arabia's RivalryProjected,”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March 2013, p. 46, https:/ /www. prio. 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x=5850,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4 日。此外,伊朗还在北非地区寻求开展代理人战争,如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组织“波利萨里奥运动”(Polisario Movement)与摩洛哥政府进行对抗。③“Iran's North African Proxy War?,” Inside Arabia, July 2, 2018, https:/ /insidearabia.com/irans-north-african-proxy-war/,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4 日。
总体来看,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实践已遍及中东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抵抗轴心”(resistance axis)。 正如格兰特·休斯(Geraint Hughes)所言,国家资助代理人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很难得知这种援助的真实水平。④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员赛斯·琼斯(Seth G. Jones)指出,伊朗的代理人网络战斗人员已从2011 年的11 万至13 万增加到2018 年的14 万至18 万。⑤Seth G. Jones, “War by Proxy Iran's Growing Footprint in the Middle East,” CSIS, March 2019, https:/ /csis-website-prod. s3. amazonaws. 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90312_IranProxyWar_FINAL.pdf,上网时间:2020 年12 月13 日。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形式是发动方军事人员远离战场,伊朗在地区的代理人战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包括单边代理人战争以及复合代理人战争。⑥单边代理人战争是最为常见的形式,涉及一国利用其他行为体等作为代理人对付目标对象的情形;复合代理人战争的代理关系较为复杂,同时存在两个代理关系,在同一个代理人战争中的A、B、C 三方共同打击D。 其中,A 是施动方,B、C 是代理方;B 既是C 的施动方,又是A 的代理方。单边代理人战争是指一国利用其他行为体等作为代理人对付目标对象的情形。 伊朗在巴勒斯坦扶持哈马斯、杰哈德武装以对付以色列,属于单边代理人战争的形式。 复合代理人战争则是指同时存在两个代理关系的代理人战争。 在伊拉克、叙利亚甚至也门的代理人战争较为复杂,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等次级代理人,属于复合代理人战争。
二、 伊朗在中东地区代理人战争的动力
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争是当前中东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也是影响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的重要因素。 伊朗对于代理人力量的重视可追溯到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当时伊朗寻求通过支持中东什叶派组织来输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 自两伊战争结束以来,伊朗未再与地区对手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或者战争,而是通过当地代理者来实现其战略目标,避免直接卷入流血与耗资不菲的战争。①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2, No. 3, 2002, p. 30.代理人战争是具有显著吸引力的战略手段,伊朗发动代理人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以更有效的方式维护和服务伊朗的国家利益。 英国伊朗问题专家安欧施拉凡·伊赫提沙米(Anoushiravan Ehteshami)指出,革命的伊朗总是一个按照经典现实主义模式行事的理性行为体。②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in Raymond Hinnebusch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2, p. 284.在较为险恶且不确定性较大的地区安全环境中,促进伊朗的国家利益是伊朗外交战略的根本出发点,这促使其选择借助代理人战争实现自身的政治与军事目标。 不可否认,直接或间接支持非国家行为体作为代理人可以产生更为隐蔽和理想的效果。③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5.具体来说,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制衡与掣肘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全球及地区对手。 在较为险恶、安全威胁居高不下的地区战略环境中,安全利益考量及维持政权生存始终是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首要关切。 美伊结构性矛盾背后反映了美国全球霸权与伊朗地区大国追求的战略冲突,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改变伊朗现政权的性质,基本目标是迫使伊朗改变对外行为,尤其是地区反美政策与活动。 有学者指出,美国对伊朗政策的目标包括阻止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改变伊朗人权状况以适应西方模式、阻止伊朗的区域霸权野心以及制约伊朗反对以色列的行为。①Karin A. Esposito and S. Alaeddin Vahid Gharavi,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U. S Tactics for Chang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 Paul Sharp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American Diplomacy,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1, p. 92.伊朗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冲突更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角力。 以色列不断寻求加大遏制伊朗的力度,压缩伊朗的地区活动空间。 当前,美国与以色列联合部分阿拉伯国家遏制伊朗的态势更加明显,尤其是以色列与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隐性战略合作成为伊朗新的安全威胁,突出表现为美国积极主导建构“中东战略联盟”(MESA),欲与中东盟友打造“阿拉伯版北约”。
通过代理人战争方式御敌于国门之外,降低对手对伊朗带来的安全威胁,突破美国和地区对手对其的包围与遏制,这是伊朗主动应对外部威胁刺激的方式。险恶的国际环境塑造了伊朗的安全观,在伊朗看来,其不仅面临美国的直接威胁,也被沙特、以色列等美国的代理人所包围。 “9·11”事件后,美国主导军事占领阿富汗与伊拉克增强了伊朗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担心在地缘政治上被包围。②Enayatollah Yazdani and Rizwan Hussai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Iran Afte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An Irania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2006, p. 287.因此,伊朗积极主动地推行代理人战争,影响中东国家内部政治和地区形势变化。 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的存续,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崛起,背后都有伊朗代理人的影子。③Mahjoob Zweiri, “Iran and Political Dynamism in the Arab World: The Case of Yemen,”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5, No. 1, 2016, p. 5.埃胡德·艾拉姆(Ehud Eilam)指出,如果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会通过真主党这样的阿拉伯代理人还以颜色。④Ehud Eilam, “Arab Factors as a Part of the Iranian-Israeli Conflict: An Israeli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 3, No. 4, 2016, p. 425.伊朗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威胁认知度越高,推行代理人战争的动力就越强。
同时,伊朗采取较为审慎的现实主义地区外交战略,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伊朗利用代理人牵制美国的战略注意力,转移对手的视线,甚至试图借助代理人战争把美国的势力从中东驱除出去。 为突破美国的包围与孤立,伊朗加强了与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关系,如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组织等,借此提高对美国的报复能力。⑤蒋真:《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及其局限性》,载《国际论坛》2020 年第4 期,第20 页。马修·麦金尼斯(J. Matthew McInnis)指出,伊朗通过低烈度的代理人冲突作为震慑美国或其盟友的尝试。⑥J. Mattew McInnis, “Toward a Model of Iran at War,” in Report “Iran at War: Understanding Why and How Tehran Uses Military Forc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ecember 1, 2016, p. 45.例如,也门胡塞武装凭借对也门地形的熟悉及勇猛的作战态势,帮助伊朗制造了一场冲突,导致伊朗的主要地区竞争对手沙特及其领导的联盟付出了高昂的军事干预代价,伊朗则利用较少的资金支持分散了对手在叙利亚的注意力。①Afshon Ostovar, “The Grand Strategy of Militant Clients: Iran's Way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Issue 1, 2019, p. 172.而黎巴嫩真主党异军突起,加大了对美国中东战略的威胁,使得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威胁更趋复杂。 美国一旦还手,可能会刺激阿拉伯世界民间反美和仇以情绪,加大地区亲美和世俗政权的压力而不敢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②董漫远:《黎巴嫩局势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第6 期,第50 页。在一定程度上,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刺激—反应关系模式的结果,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断加大伊朗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压力,伊朗则通过扶持代理人加以回应。
第二,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巩固与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代理人战争不仅是伊朗应对美国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威胁以维持国家生存与安全利益的反应式战略手段,还是其为实现地区权力延展目标的主动性政策工具。 伊朗通过造就“庇护—代理”关系网络及推行代理人战争,增强对于代理人所在国家以及邻近区域的影响力,获取代理人的追随,实现权力控制与扩展的目标。 扶持代理人是伊朗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借此增强了在什叶派群体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建立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及巴勒斯坦的反美反以抵抗运动轴心,成为中东“什叶派新月”政治联盟的核心领导者。③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派别在伊朗代理人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绝非唯一原因,如哈马斯、杰哈德属于逊尼派,虽然和伊朗分属不同教派,但共同的对手(美国和以色列)及战略目标的契合促使双方走到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伊朗外交政策的根源与目标是防御性的,尤其是具有基于国家既定战略议题的实用主义特征。 参见Kayhan Barzegar, “Iran's Foreign Policy in Post-Invasion Iraq,”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5, No. 4, 2008, p. 149。艾迪恩·萨利希安(Idean Salehyan)认为,伊朗没有与以色列进行直接的国家间冲突,而是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强化讨价还价的手段及提升地区影响力。④Idean Salehyan, “The Delegation of War to Rebe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3, 2010, p. 494.伊朗通过代理人投射权力,把什叶派民兵组织网络作为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代言人及力量投射载体,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由此,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及也门等国成为伊朗的战略纵深与地区权力投射的主要范围,推动伊朗在整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
第三,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避免与对手直接开战,降低对抗与竞争成本,试图以最低成本实现收益最大化。 代理人战争是一种“廉价的战争”,扶持代理人是风险转移政策的一部分。 在伊朗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不对称性力量结构中,伊朗难以与美国开展正面对抗,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进行幕后操纵而不必直接介入战争,这是基于成本、收益与风险的考量。 比莱·萨阿布(Bilay Y. Saab)在分析伊朗与沙特地区博弈时指出,双方军事冲突的结果不会有赢家。①Bilay Y. Saab, “Beyond the Proxy Powder Keg: The Specter of War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y 2018, p. 31,https:/ /www. mei. 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P3_Saab_IranSaudi.pdf,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5 日。尤其是对于伊朗的核技术开发而言,以色列可能先发制人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基地设施已多次遭到以色列的精准打击。 在此背景下,伊朗恐难以承受以色列和美国的大规模军事打击。 而伊朗运用代理人的成本较为低廉,代理人可以降低风险且充当力量倍增器的角色。②Anthony H. Cordesman and Martin Kleiber, Iran's Military Forces and Warfighting Capabilities: The Threat in the Northern Gulf,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 203.代理人更熟悉当地环境,打击对手的方式更为灵活多样且更加有效,行动自由度高,可以有效避免幕后双方的直接冲突。有学者指出,针对2003 年以来伊朗核问题的急剧升温以及以色列军事打击的潜在威胁,伊朗可以借助真主党或者哈马斯等代理人组织袭击以色列,包括自杀性爆炸袭击、从南黎巴嫩与叙利亚发射导弹等。③Ibid., p. 232.伊朗的一贯原则是避免落入不得不与更强大敌人进行常规战争的陷阱,这是苏莱曼尼和其他伊朗军事领导人反复强调的战略。④Ahmed S. Hashim, “ Iranian General's Killing: How Will Iran Respond?,” RSIS Commentary, No. 005-7, January 2020, pp. 2-3, https:/ /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idss/138165/#.X8IEiTNirDw,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6 日。即使在2020 年初苏莱曼尼遇袭身亡后,伊朗仍主要借助代理人报复美国,并不寻求升级局势或者挑起战争。
第四,伊朗通过推行代理人战争调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历史角度来看,伊朗一直是一个拥有大国理想的国家,民族主义在伊朗历史上一直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反对外来干涉的民族主义情绪始终十分强烈。 20 世纪70 年代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谴责世俗民族主义,并将民族的分裂归咎于帝国主义分裂穆斯林的企图。 自1979 年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伊朗愈发重视其国家尊严与国际地位。 霍梅尼在讲话中反复使用“这个伟大的国家”的表述,反映了伊朗持续抵制美国制裁与遏制压力的强烈意识,其认为有必要增强伊朗的国家安全能力。⑤Fred Halliday, “Iranian Challenges: Iran's Regional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6, p. 4.但伊朗的综合实力相对有限,在国际上长期遭受美国的遏制与制裁,在地区层面受到沙特、以色列等国的制约,调动国内民族主义有助于激发伊朗人实现国家重新崛起的意愿与期待,进一步促使伊朗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而精心、巧妙地扶持其分布在中东多地的代理人。
伊朗的代理人众多。 由于伊朗在不同的次级战略板块谋求的战略目标具有差异性,代理人在伊朗构建的“抵抗轴心”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伊朗对代理人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代理人战略的重点及具体政策。 为制衡地区首要对手沙特,伊朗将叙利亚、伊拉克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博弈平台,视巴沙尔政权为掣肘对手沙特的“有力武器”,对巴沙尔政权的支持力度极大、影响范围最广。 2011 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伊朗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巴沙尔政权,而且派出大批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进入叙利亚境内帮助叙政府军作战。 此外,伊朗还借助黎巴嫩真主党援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盘踞在叙南部、受到沙特扶持的叙反对派武装。①陈翔、熊燕华:《沙特与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代理人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8 页。同样,为在伊拉克制衡沙特,伊朗支持包括伊拉克达瓦党及伊拉克伊斯兰最高指导委员会在内的什叶派政党联盟,以此打压沙特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并支持组建大批什叶派民兵武装。 为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伊朗实行“阿拉伯街头战略”(Arab Street Strategy),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兵组织,将其视为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抓手,以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直接向阿拉伯国家民众宣传等方式,侵蚀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控制力。②Simon Mabon, Saudi Arabia and Iran: Power and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6, p. 63.为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有效抗衡空军实力高于本国的以色列,伊朗利用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以自杀性爆炸、从南黎巴嫩与叙利亚发射导弹等方式威胁和制衡以色列,间接报复以色列在对叙目标的空中打击行为。③Anthony H. Cordesman and Martin Kleiber, Iran's Military Forces and Warfighting Capabilities: The Threat in the Northern Gulf, p. 232.
可见,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受到多种动机的驱使,既有制衡地区对手的考虑,应对美国、以色列等对手围堵与压制的被动反应,以维系国家政权生存与周边安全,又是主动出击和塑造地区环境的积极行动,以扩大地区影响力,还有以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的务实考量。 伊朗在推行代理人战争的过程中,采取主动出击与被动应对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以攻为守的地区战略行动,这使伊朗在地区内具有更大灵活性与战略主动权。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极限施压”与遏制战略,伊朗通过培植地区代理人及借助代理人来打击对手,这种投入小、收益大、风险低的战略举措更加安全、经济且更易实现伊朗的战略目标。
三、 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限度
代理人战争的要义是以最低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成本,迫使对手屈服或让步,力求不直接借助自身武力实现相应的战略目标。 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争产生了相应效果,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拓展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增强了其左右地区安全局势的能力。 然而,代理人战争的效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也有限度。
第一,伊朗代理人能力与战略意愿的改变影响其借助代理人战争制衡及打击对手的效果。 一方面,伊朗代理人的势力与其地区对手相比,大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代理人战争的效果。 例如,无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多少有力的支持,相对于沙特及其盟友的支持和介入而言依然要少得多,无论是在政府、武装部队、官僚机构、安全部门、非政府组织中,还是瓦哈比宗教机构和部落民兵等实体上都是如此。①Thomas Juneau, “Iran's Policy Towards the Houthis in Yemen: A Limited Return on a Modes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3, 2016, p. 662.另一方面,代理人的意志影响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效果。 代理人的自主性程度影响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效果,这种自主性体现在代理人对于自身利益的关注以及独立形象的维护上。 例如,真主党既是伊朗的代理人又是黎巴嫩合法政党的双重身份,相应地限制了其代理人作用的发挥。 一旦代理人的能力趋强或者其他行为体能为其实现目标提供更大便利,代理人可能会逐渐失去与原庇护方合作的兴趣。②Amox C. Fox, “Conflict and the Needs for a Theory of Warfare,”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12, No. 1, 2019, p. 56.例如,伊拉克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影响了伊拉克国内伊朗代理人发挥效力的能力与意愿。 在2018 年伊拉克大选中获得最多席位的“萨德尔联盟”日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其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ar)刻意与伊朗保持距离,一度对伊朗干涉伊拉克事务持高调批评态度,并寻求与沙特恢复联系。③Beston Husen Arif, “Iran's Struggle for Strategic Dominance in a Post-ISIS IRAQ,” Asian Affairs, Vol. 50, Issue 3, 2019, p. 4.2019 年9 月,伊拉克爆发带有明显反伊朗色彩的大规模示威,一定程度上导致被视为亲伊朗的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Adel Abdul-Mahdi)于当年11 月辞职。
此外,伊朗代理人的自身目标与伊朗的地区战略并不完全一致,影响了伊朗在整个地区的战略布局,有时甚至将伊朗拖入不必要的战略泥潭。 如2006 年爆发的黎以战争并不符合彼时伊朗的地区战略,真主党挑起与以色列冲突的真实意愿使伊朗产生怀疑。 事实上,伊朗不愿意发动一场针对以色列而不符合伊朗利益的战争。①Daniel Sobelman, “New Rules of the Game: Israel and Hizbollah After the Withdrawal from Lebano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January 1, 2004, p. 67, https:/ /www.inss.org.il/publication/new-rules-of-the-game-israel-and-hizbollah-after-the-withdrawal-from-lebanon/,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2 日。由于代理关系没有明确的条约规定,非正式性特征使代理方与庇护方的关系较为松散,因此,双方存在相互抛弃或背叛的可能性。 伊朗及其代理人之间也存在信任问题及相互抛弃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效力。
第二,伊朗国内政局的变化以及民众压力影响到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战略意志和资源汲取能力。 作为代理人战争的发起方,国内局势变化对于伊朗在地区开展代理人战争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国资源汲取能力决定的。 一国拥有的实力及能够运用的实力并非完全一致,伊朗需确定战略目标并评估资源动员手段,使之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实现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平衡。 近年来,美国的极限施压导致伊朗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遇到极大困难,财力等资源较为有限。 自2019 年以来,美国的制裁使伊朗的收入减少了500 亿美元,其原油出口已降至过去30 年来的最低点,导致政府石油收入减少66%。 仅在2020 年的3 月至6 月,新冠肺炎疫情就使伊朗损失了超过108 万亿土曼。②《伊朗政府面临的几大困难》,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 年6 月13 日,http:/ /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6/20200602973710.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25 日。2020 年上半年以来,伊朗国内公众对失业、经济的焦虑和对腐败的愤怒已对政权生存构成威胁。 在政治方面,伊朗政治体制中的派系斗争也影响了该国作为单一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能力,伊朗的决策时常受制于国内各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 与此同时,外部敌人不断寻找机会恶化伊朗的国内局势,如2019 年11 月的伊朗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曾迅速升级为暴力破坏行径。
黯淡的经济前景以及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削弱伊朗升级与美国进行敌对行动的意愿。 鉴于代理人战争会消耗伊朗的有限资源与精力,进一步恶化伊朗的国内状况,因此伊朗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代理人的扶持。 伊朗国内存在反对政府把国家本来就有限的资源投放到国外的声音,一旦伊朗无法为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也门等国的伙伴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这些伙伴还能配合伊朗地区战略的程度值得怀疑。①范鸿达:《伊朗提升区域战略地位的策略及前景》,载《当代世界》2020 年第2 期,第9 页。
第三,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对手的反制,可能带来代理人战争升级为直接战争的战略风险,且伊朗在不同地区推行代理人战争因各次区域战略目标的差异而面临不同的风险临界点。 美国为反制伊朗也在地区积极推行代理人战争,不断向沙特等国提供军事援助、后勤保障与政治外交支持,强化其对抗伊朗的实力与意志。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伊朗视为“一切麻烦的制造者”与“美国在中东的最大敌人”,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以遏制伊朗。 2017 年5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把出访地首选在沙特,并与沙特签订了价值1,100 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合同,旨在遏制伊朗不断增长的影响力。②“U. S President Trump, King Salman of Saudi Arabia Sign $110bn Arms Deal,” Vanguard, May 20, 2017, https:/ /www. vanguardngr. com/2017/05/u-s-president-trump-kingsalman-saudi-arabia-sign-110bn-arms-deal/amp/,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7 日。特朗普政府遏制伊朗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对伊朗的代理人进行打击,包括支持沙特等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力图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阻断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③Kenneth Pollack and Bilal Y. Saab, “Countering Ir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7, pp. 97-108.美国还一直扶持伊朗海外反对派进行渗透,企图通过培植所谓的“健康力量”来实现推翻伊朗现政权的目标。 美国长期向“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等伊朗反政府力量提供资金援助、安全庇护和政治支持,以换取这些力量服务于美国扰乱甚至颠覆伊朗现政权的战略意图。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1 年发布《哪里是通往波斯之路》的报告,建议美国充分武装、训练及支持“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把其作为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盟友及获取情报的有效代理人。④Tony Cartalucci, “U. S. Proxy War Against Iran, Sponsoring the MEK Terrorist Cult,” Signs of The Times, October 18, 2014, https:/ /www. sott. net/article/287548-US-proxy-war-against-Iran-sponsoring-the-MEK-terrorist-cult,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7 日。美国意在通过支持伊朗现政权的国内外敌对力量和分散伊朗注意力,降低其对外扶持代理人的力度。
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力量众多,但由于伊朗在各个地区的战略目标不同,其在不同地区推行代理人战争面临的风险临界点存在差异,这也对伊朗的地区战略带来考验。 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推行的代理人战争旨在抗衡美国的地区霸权,因此,伊朗在这两个国家面临冲突升级的风险最高。 2020 年1 月3 日,美国暗杀苏莱曼尼的背后,是对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扶植代理人进行非常规战争威胁到美国地区利益的反制。 苏莱曼尼事件虽在伊朗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但伊朗已在中东地区建立起完整的防御网络,伊朗依然有能力对美国造成重大威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将摒弃以往传统,报复行动必须由伊朗军队完成。①“Khamenei Wants to Put Iran's Stamp on Reprisal for U.S. Killing of Top Genera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20, https:/ /www. nytimes. com/2020/01/06/world/middleeast/irankhamenei-general-soleimani.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30 日。苏莱曼尼的继任者伊斯梅尔·卡尼(Ismail Qaani)也是强硬的反美派,曾在受访时表示,过去十多年来美国等敌人越是增强攻势,伊朗人民的抵抗就越厉害。②孙微、王逸:《要让“美国人尸横遍野”?! 苏莱曼尼继任者是什么来头?》,载《环球时报》2020 年1 月6 日,第4 版。伊朗总是将袭击活动隐藏于在周边地区扶持的代理人的行动背后,但苏莱曼尼被杀引起的愤怒导致伊朗一改之前传统的回应手段。 事件发生后不久,伊朗没有使用以往惯用的代理人战争手段,而是直接向美国驻伊拉克的两个军事基地发射了15 枚导弹予以报复。 虽然这场袭击并没有造成可能促使美军发动进一步进攻的人员伤亡,但几乎无人相信伊朗对美国的反击会到此为止。③“Trump Downplays US Troops' Concussion Injuries From Iranian Missile Attack,” Press TV, January 23, 2020, https:/ /www. presstv. com/Detail/2020/01/23/616869/US-military-Iraq-Iraqmissile-injuries,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22 日。有评论认为,即使伊朗的代理人采取报复行动,美国也会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甚至是伊朗境内设施。 尽管特朗普可能并不渴望战争,但他身边的鹰派人士渴望战争,伊朗的重大不对称反应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④Ahmed S. Hashim, “Iranian General's Killing: How Will Iran Respond?,” pp. 4-5.
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伊朗面临的冲突升级风险次之。 伊朗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等以摧毁以色列为目标的武装组织,并在叙利亚建立了军事基地,以此为支点威胁以色列本土安全。 伊朗的空军实力不如以色列,但地面作战能力及其灵活性要高于以色列,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例如,2020 年4 月,以色列战机从黎巴嫩南部上空向叙利亚境内发射导弹。 伊朗通过扶持代理人在地面袭击以色列多次得手但并非毫无风险,只是目前以色列在国家安全方面不愿轻易冒险。①Alon Ben-Meir, “Preventing an Israeli-Iran War,” American Diplomacy, May 1, 2019, http:/ /americandiplomacy.web.unc.edu/2019/05/preventing-an-israeil-iran-war/,上网时间:2020 年12 月10 日。此外,也门冲突成为伊朗与其地区对手沙特展开斗争与博弈的舞台,沙特等国的强势反制影响了伊朗目标的实现。 同时,沙特与伊朗在多个地区的冲突中处于对立面,双方的代理人战争也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和趋势。
第四,新冠疫情制约了当前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效果。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伊朗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内经济状况持续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朗对外政策的实施,尤其是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有所下降。 在疫情暴发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来自美国的制裁已经使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了约80%,伊朗货币贬值了一半。②“Iran's Economy and the New Parliament,” Tehran Times, June 14, 2020, https:/ /www.tehrantimes.com/news/448870/Iran-s-economy-and-the-new-parliament,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5 日。即便遭受疫情侵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从未停止。 2018 年美国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后,对伊朗全面制裁的核心是将伊朗的石油收入置于国际监管之下,确保伊朗政府将财政收入用于民生而非对外穷兵黩武。③赵广成:《伊朗鲁哈尼政府的外交评析》,载《国际论坛》2019 年第3 期,第154 页。当前,伊朗国内形势恶化,政府隔离和控制疫情能力备受质疑,也缺少为企业纾困的手段,更无法为失业人群提供有效的经济支持。 如何有效遏制疫情,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④李睿、柳玉鹏:《伊朗在疫情与制裁中迎来新年》,载《环球时报》2020 年3 月20 日,第2 版。在严重的治理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压力下,伊朗应对国内事务已略显自顾不暇,难以继续维持以往的对外战略和资源调动能力,因此未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 在此情况下,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意愿下降,这一战略调整也将影响伊朗在地区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效果。
四、 结语
伊朗精心扶持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国家都成为伊朗与对手对抗的战场,这是伊朗维护自身安全和拓展地区影响力的重要途经。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成本低、获益大,避免了与美国及其中东盟友正面冲突,地区代理人分担了伊朗承受的巨大压力,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实现了伊朗的地区利益。 与此同时,伊朗在推行代理人战争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和代理人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潜在风险。 伊朗代理人的能力与战争意愿的改变、伊朗国内局势的变化与压力,以及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的反制,都会制约或影响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效果。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在中东地区的持续扩散使得伊朗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其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受到制约。因此,伊朗推行代理人战争的限度十分明显。
以2020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和核科学家穆赫辛·法里克扎德(Mukhsin Farikzad)被袭杀为重要标志,中东地区进入了新一轮动荡期。随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和政权交接的展开,美国的中东政策尚不明朗,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将走向何方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伊朗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维持地区影响力的考虑,必然不会放弃代理人战争。 美伊关系仍将是中东地区最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即使在全球疫情的阴霾笼罩下,伊朗依然存在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走向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双方可能会越过既有的缓冲地带,紧张局势升级甚至直接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国际秩序也处于大调整大动荡时期,加强对国际关系中代理人战争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区局势的发展规律与态势。 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当下,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培育和扶持代理人从而间接取得战略利益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较大。 可以说,扶持代理人已成为大国低投入、高收益的重要战略手段,并将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