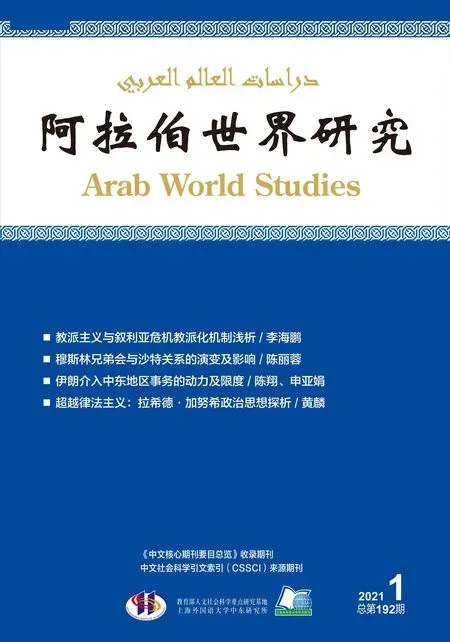穆斯林兄弟会与沙特关系的演变及影响
陈丽蓉
2011 年以来,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走向和国际关系变动的重要因素。 2017 年6 月,沙特以卡塔尔支持和资助“恐怖组织”及穆兄会为由而与卡塔尔断交。 穆兄会之所以被沙特列为“恐怖组织”,并成为海湾地区发生外交危机的因素之一,与穆兄会在海湾地区的扩张及其对海湾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影响有关。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已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卡塔尔等国的穆兄会及其分支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内对于沙特和穆兄会关系的研究,散见于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沙特现代化的相关论著中。①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 年版;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吴彦:《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在国外研究成果中,斯蒂芬·拉克鲁瓦(Stéphane Lacroix)细致梳理了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沙特“觉醒运动(Sahwa Awakening)”的影响,并持续跟踪研究了中东剧变以来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和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状况。②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George Holoch,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Islamists and the Arab Spring,” Research Paper at Kuwait Program on De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Gulf States, Kuwait, May 2014.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分析了20世纪80 年代穆兄会和沙特在阿富汗进行的合作以及海湾战争后二者关系恶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③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以托马斯·黑格海默(Thomas Hegghamm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穆兄会是导致沙特伊斯兰主义运动兴起和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④Thomas Hegghammer, Jihad in Saudi Arabia: Violence and Pan-Islamism Since 197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n B. Alterman,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5; Robert Lacey, Inside the Kingdom: Kings, Clerics, Modernists, Terrorists, and the Struggle for Saudi Arabia, London: Viking Penguin Group, 2009; 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本文通过梳理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及其与沙特关系的演变,试图剖析穆兄会对沙特内政外交的影响,进而分析穆兄会与沙特关系破裂及其被沙特列为恐怖组织的原因。
一、 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历程
穆兄会在埃及成立之初,其创始人哈桑·班纳就对沙特显示出浓厚兴趣,并试图在沙特建立分支机构。 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初步发展、扩张、衰退三个阶段。
(一) 初步发展阶段(1932 年至1953 年)
1932 年至1953 年,在沙特的有限许可下,穆兄会在沙特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哈桑·班纳与时任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穆兄会受到沙特政府的资助。 1932 年,哈桑·班纳在沙特朝觐并为建国不久的沙特国王祈福。 这一姿态在当时尤其具有象征意义。 一般来说,在伊斯兰教中,只有哈里发才是被祈福的对象。 为感谢哈桑·班纳,伊本·沙特国王命令时任财政次大臣穆罕默德·苏鲁尔·法尔罕(Mohammed Srour al-Farham)向穆兄会提供资金支持。 1948 年,沙特国王还向躲避埃及政府追杀、逃亡到沙特的哈桑·班纳提供出行车辆和私人护卫,暂时确保了班纳在沙特的安全。①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1, 2017, p. 130.
第二,穆兄会成员获得沙特政府许可,可在沙特旅行、短暂居留并教沙特人读书识字。 同时,沙特也借助穆兄会制衡国内保守的瓦哈比派势力。 沙特建国之初,社会发展落后,亟需引进现代物质文明,但遭到瓦哈比派保守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该派认为引进现代设施即为“不信道”,穆兄会的支持由此为沙特国王推行现代化政策提供了宗教合法性。②Ibid., p. 131.
然而,即便当时沙特对穆兄会态度友好,也不意味着沙特允许穆兄会在其国境内建立分支机构。 1936 年,伊本·沙特就以禁止建立政党为由,拒绝了哈桑·班纳在沙特建立分支机构的请求。 当穆兄会介入1948 年也门军事政变、参与刺杀也门伊玛目并试图在也门建立哈里发国一事败露后,沙特国王便开始将穆兄会视为威胁,同穆兄会断绝官方联系。③Abdel Latif el-Menawy, “A History of Banning the Brotherhood,” Al Arabiya, September 29, 2013, http:/ /english. alarabiya. net/en/views/news/middle-east/2013/09/29/A-history-ofbanning-the-Brotherhood-.html,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9 日。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1953 年。
(二) 扩张阶段(1953 年至1990 年)
埃及强人纳赛尔上台后,沙特主动接纳大批被埃及政府镇压的穆兄会骨干、成员,以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同样遭受打压的穆兄会成员。 大批逃亡到沙特的穆兄会成员进入沙特教育领域,获得了扩大影响力的机遇。 这一态势一直持续至1990 年海湾战争爆发。
第一,穆兄会许多著名人物进入沙特中小学及高校担任教职。 20 世纪50 年代,沙特国内中小学师资匮乏,文盲率高达85%。 大部分从埃及逃亡的穆兄会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这批人很快在文化水平低、师资匮乏的沙特教育机构占据重要地位。 1961 年,沙特王室将整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当做礼物送给了穆兄会,允许他们进行慈善活动,并向他们提供了活动经费。①廖百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把脉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年版,第218 页。1969 年至1973 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ad al-Mubarak)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 Aziz University)麦加分校②1950 年伊本·沙特国王在麦加建立的沙里亚学院,是沙特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乌姆·古拉大学(Umm Al-Qura University)的核心院系。 1953 年,乌姆·古拉大学设立教师学院(The College of Teachers),负责培训教师。 1960 年,教师学院被撤销。 1962 年后,培训教师的任务被分配给沙里亚学院(沙里亚学院当时被称为沙里亚与教育学院)。 1963 年,沙里亚学院的一部分被拆分出来,组成了教育学院,两个学院独立运行。 1971 年,沙里亚学院和教育学院被并入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这两个学院共同组成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麦加分校。 参见“Overview of the Umm Al-Qura University”,Umm Al-Qura University, https:/ /uqu. edu.sa/en/main/AboutUs, 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20 日。的沙里亚学院担任领导。 穆罕默德·库特布(Muhammad Qutb)③穆罕默德·库特布为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之弟。以及后来成为阿富汗“圣战”组织主要领导者的阿卜杜拉·阿扎姆(Abdallah Azzam)④阿卜杜拉·阿扎姆被称为全球“圣战”之父。也曾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讲学。⑤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p. 43-44.
第二,穆兄会成为沙特国内修订教材和制定课程的一支重要力量。 1964 年,沙特当局授权穆罕默德·穆巴拉克为麦加的沙里亚学院设计教学课程。 由此,穆罕默德·穆巴拉克成为“伊斯兰文化(Islamic Culture)”这门新学科的创始人。他在这门新学科中教授现代伊斯兰史和伊斯兰体系这两门专业课,将穆兄会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植入教材。 学习经济学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在“伊斯兰文化”这门学科中受到穆罕默德·库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扎姆的政治影响。⑥Ibid., pp. 46-47.
1965 年,沙特费萨尔国王成立了一个旨在提升国民教育的专家小组,其中许多穆兄会人士即为该专家小组下属的委员会成员。 委员会主导制定了沙特教学
大纲《沙特王国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该教学大纲对伊斯兰概念的解释掺杂了穆兄会的意识形态。 随着新教育政策的施行,穆兄会推动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伊斯兰化。 一些高校成立了伊斯兰经济学系、伊斯兰心理学系和伊斯兰社会学系,穆兄会成员在其中参与教学或组织活动。①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Arabia, p. 47.
第三,除了在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社会科学领域外,穆兄会还对宗教学领域发挥着显著影响。 当时,有不少穆兄会成员在沙特高校教授经注学②即《古兰经》注释学。和伊斯兰法学。 1977 年至1978 年,埃及穆兄会成员成为沙特伊玛目大学经注学系的领导人,该系其他8 名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教师也赞同穆兄会思想。③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7.仅有教义学这门学科由瓦哈比派乌里玛绝对掌控,没有穆兄会成员参与。 20 世纪70 年代,沙特高校出现两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学中心,一个是瓦哈比教义学中心,另一个是聚焦于伊斯兰文化的穆兄会中心。 但“两强并立”的时间并不长,穆兄会中心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其他系,甚至渗透进瓦哈比教义学中心。 萨法尔·哈瓦利(Safar al-Hawali)就曾对穆罕默德·阿明·马斯里(Muhammad Amin al-Masri)④穆罕默德·阿明·马斯里是来自叙利亚的穆兄会成员。称赞道:“他做出巨大努力,才使得‘现代思想流派(Contemporary Schools of Thought)’被确定为教义学的指定教学内容。 教义学这门课本应由具有现代伊斯兰思想的穆罕默德·库特布教授来授课”。⑤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7.20 世纪80 年代,由穆罕默德·库特布指导毕业的学生也在各自任教的学校教授“现代思想流派”,继续传播穆罕默德·库特布的思想。
总的来说,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尤其是费萨尔国王时期,沙特高校聚集了一批从叙利亚、埃及、约旦等国流亡而来的穆兄会教师。⑥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第156 页。此外,沙特王室还支持穆兄会成员参与创建由沙特资助的伊斯兰慈善组织和机构,其中包括1961 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和1972 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⑦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1.
(三) 衰退阶段(1990 年至今)
自1990 年以来,穆兄会逐渐遭到沙特的削弱和遏制,其在沙特的活动空间因受到限制而步入衰退阶段。 2014 年,随着沙特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沙特穆兄会遭到全面打压。
第一,1990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穆兄会强烈反对美国在沙特驻军。 随着公开质疑沙特王室统治合法性的“觉醒运动”兴起,沙特将矛头之一指向穆兄会,将穆兄会作为重点打击对象,驱逐了许多长期逗留在沙特境内的穆兄会成员。①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3.自阿富汗返回的“圣战”分子在沙特发起多次恐怖袭击后,沙特对穆兄会采取了更加敌视的政策。 20 世纪90 年代晚期,沙特大穆夫提阿卜杜·阿齐兹·本·巴兹(Abdul Aziz bin Baz)斥责穆兄会为叛教者。 2002 年,时任沙特王储纳伊夫(Nayef)谴责穆兄会背叛海湾国家,是“王国的万恶之源”。②John Jenkins, “The Gulf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Foreign Policy Trends in the GCC States, Autumn 2017, p. 31.沙特还支持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镇压穆兄会。
中东剧变后,沙特对穆兄会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遏制和打压政策。 2014 年2月4 日,沙特政府发布一则王室令(Royal Decree),宣布“将对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宗教人士或同情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者处以3 年以上、20 年以下监禁”③Stéphane Lacroix, “Saudi 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 Predicament,”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20, 2014, https:/ /www. washingtonpost. com/news/monkey-cage/wp/2014/03/20/saudi-arabias-muslim-brotherhood-predicament/,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8 日。。 其中,“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即指穆兄会或受穆兄会影响的知识分子。 就职于“使命”电视台(Al-Risala TV)的塔里克·苏维丹(Tareq al-Suwaidan)就因被指责参与“穆兄会恐怖活动”而被电视台辞退。 在沙特政权的警告和威慑下,约有2.5 万名穆兄会成员不得不取消集会,尽量保持低调。④Jon B. Alterman and William McCants, “Saudi Arabia: Islamists Rising and Falling,” in Jon B. Alterman,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pp. 163-164.
第二,2014 年3 月7 日,沙特正式认定穆兄会为“恐怖组织”,并在国内大规模搜捕、镇压穆兄会成员及其支持者,穆兄会在沙特的处境急剧恶化。 与穆兄会有关的人士遭到沙特当局监禁或被判处死刑,与穆兄会相关的书籍被没收和销毁。 萨法尔·哈瓦利、萨勒曼·奥达(Salman al-Ouda)等37 名具有穆兄会思想的宗教学者皆受到监禁和刑罚。 2015 年12 月,沙特要求所有学校、图书馆和研究中心销毁由穆兄会成员或与其有关联学者出版的书籍,其中包括尤素福·格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赛义德·库特布和哈桑·班纳撰写的书籍。①Khalid al-Shayea, “Saudi Arabia Has Pulled a List of Books, Many by Muslim Brotherhood Scholars from Its Schools, Causing Heated Debate Around the Decision,” The New Arab, December 3, 2015, https:/ /english. alaraby. co. uk/english/news/2015/12/3/blacklisting-of-books-in-saudi-arabian-schools-causes-controversy,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11 日。 “80 Books Promoting Brotherhood Banned,” Arab News, December 2, 2015, https:/ /www.arabnews.com/featured/news/844241,上网时间:2020 年12 月5 日。至今,穆兄会仍未能在沙特进行公开活动。
二、 穆兄会与沙特关系的演变
自1932 年穆兄会进入沙特至1953 年,沙特当局一直严格限制穆兄会在沙特建立分支。 1953 年以后,沙特和穆兄会逐渐形成了既合作、又相互利用的盟友关系。 在1990 年至2013 年期间,二者关系日趋恶化。 自2014 年沙特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以来,二者关系彻底破裂。 由于1932 年至1953 年穆兄会在沙特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穆兄会和沙特的交往相对较少,因此笔者着重论述1953 年后二者关系的演变。
(一) 合作与相互利用的盟友关系
1953 年至20 世纪90 年代以前,沙特与穆兄会结成了“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二者通过相互利用来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 对沙特来说,穆兄会是其反制埃及纳赛尔政权的有力武器,可为其引进现代设备和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宗教合法性支持,穆兄会遍布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网络还有助于其提升影响力。对穆兄会来说,沙特政权的庇护可使其保持有生力量,来自沙特的资金支持可以帮助其不断地扩大“全球网络”,促进其思想观念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
第一,二者具有反对纳赛尔及其政权的共同需求。 纳赛尔掌权后,穆兄会在埃及成为碎片化的非法组织,其骨干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少成员逃往海湾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②毕健康:《试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二重性问题》,载《世界历史》2004 年第1 期,第98 页。纳赛尔利用“阿拉伯之音”广泛传播泛阿拉伯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鼓动推翻君主统治,建立共和制。 1962 年也门战争爆发,埃及和沙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由此,被纳赛尔打压的穆兄会和受到纳赛尔攻击的沙特之间的合作增强,二者遂结成盟友来共同应对纳赛尔政权带来的威胁。
一方面,具有丰富抗争经验的穆兄会弥补了沙特传统瓦哈比派乌里玛无法与纳赛尔进行大规模论战的短板。 沙特将在其国内避难的穆兄会成员组织起来,让其负责多种外宣平台,如“伊斯兰之音”(Voice of Islam)广播电台和1962年建立的第一座电视台。 沙特报纸刊文称纳赛尔是“埃及的斯大林”。①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Arabia, pp. 41-42.另一方面,沙特让在其国内避难的穆兄会成员参与创建以沙特为基地的跨国伊斯兰慈善机构,试图“加强伊斯兰团结,维护和帮助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和事业,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并提高穆斯林在各国的地位,从而维护沙特的君主政权统治”。②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4 页。其中,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和约旦人卡米勒·谢里夫(Kamil al-Sharif)是世界穆斯林联盟的重要创始人。③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p. 42.“1961 年,沙特王室将整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当作礼物送给穆兄会,允许他们进行慈善活动,并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④廖百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把脉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向》,第218 页。
与此同时,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在沙特境内得以传播。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沙特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费萨尔允许穆兄会在其国内开展宣传活动。 之后,穆兄会成员被允许参与王国内部事务,通过广播、公开演讲和出版书籍等在城市中心地区开展宣传与大众动员活动。⑤Mike Kelvington, “Import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reation of the ‘Sahwa’ in Saudi Arabia,” The Havok Journal, April 27, 2019, https:/ /havokjournal. com/word/middle-east/improting-muslim-brotherhood-creation-sahwa-saudi-arabia/,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11 日。苏丹哈桑·图拉比(Hasan al-Turabi)等人仇视西方文化以及推崇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在沙特逐步传播开来。⑥Hillel Frisch and Efraim Inbar, Radical Isla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76.
第二,沙特依靠穆兄会来为其现代化政策提供合法支撑。 石油开采及其巨额石油收入,使沙特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 但由于瓦哈比乌里玛对现代事务了解较少,沙特国内掌握现代技术的人才储备有限,人数有限的青年知识分子则需从事行政和管理工作。 这使得大多为大学毕业生的穆兄会成员成为沙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费萨尔国王采纳了穆兄会“伊斯兰现代化”的观点。 对费萨尔国王来说,如同穆斯林改革主义者对其父伊本·沙特国王具有重大意义一样,穆兄会对他推动现代化也同样重要。①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Arabia, p. 43.从某种程度上看,穆兄会是沙特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支持者。②Adli Sadeq, “Saudi Arabia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 Relationship to Be Restored,” MiddleEast Monitor, July 23, 2015, https:/ /www. middleeastmonitor. com/20150723-saudi-arabiaand-the-muslim-brotherhood-a-relationship-to-be-restored/,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13 日。
第三,沙特利用穆兄会的跨国界网络将其国内兴起的激进主义思想导流至国外。 1979 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使沙特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烈冲击,越来越多的舆论开始谴责沙特君主制违反伊斯兰教。③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第227 页。反政府动乱很快在沙特爆发。 1979 年11 月20 日,在激进分子朱海曼·欧泰比(Johaiman al-Qtaybi)的率领下,由沙特人、埃及人等组成的约500 名激进分子④其中很多是来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的穆兄会激进分子。 参见[美]詹姆斯·温布兰特:《沙特阿拉伯史》,韩志斌、王泽壮、尹斌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版,第267 页。,攻占麦加禁寺,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要求回归伊斯兰原初教义,废除腐败的、将西方文明引入伊斯兰圣地并逐步走上亲美道路的沙特王室,还谴责沙特宗教阶层违背职责,成为王室的附庸。⑤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第228 页。与此同时,沙特东部哈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也在伊朗输出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发动了反对沙特王室统治的示威抗议运动。
为缓和国内紧张局势,沙特国王整治了王室的挥霍和腐败现象,也采取了措施来加强国家的伊斯兰特征,⑥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第228-229 页。但这仍不能遏制激进主义思想的蔓延。 沙特政治反对派认为,瓦哈比派是王室政权的同盟者,国王的举措毫无意义。 于是,沙特采取将国内矛盾转移至国外的策略,希望借助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契机实现“祸水东引”,通过满足伊斯兰主义者的诉求来增强王室统治的宗教合法性。 其中,穆兄会的跨国网络及其较为强大的动员能力恰好为沙特所用。 由此,沙特给予穆兄会支持,鼓励其把成批带有激进思想的“圣战者”和武器运往阿富汗。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卜杜拉·阿扎姆。 沙特曾以阿扎姆与麦加禁寺事件有关为由将其驱逐出境,但却大力支持他招募思想激进者并带领他们前往阿富汗发动抗苏“圣战”运动。 阿扎姆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本·拉登的精神导师,并与后者成立“圣战者服务处”,为“基地”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⑦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第154-157 页。通过这种方式,激进主义者被分流至国外,沙特国内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解。
然而,沙特矛盾外引的做法实为“饮鸩止渴”。 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所说,“20 世纪80 年代,沙特和穆兄会结成了一种近似‘联合冒险’的关系。 穆兄会同意不在沙特境内开展活动,仅在沙特与国外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 但穆兄会在决定哪个组织和个人能获得沙特资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7.这意味着,对资金具有一定分配权的穆兄会可以轻易输出其意识形态。 另外,穆兄会及其意识形态在沙特社会的传播,也导致沙特伊斯兰教的政治化。②Stéphane Lacroix, “Saudi 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 Predicament”.二者的脆弱同盟关系随着外部威胁减小、“圣战”分子回流以及极端思想的倒灌而破裂。
(二) 疏远与恶化的对手关系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穆兄会转变发展战略。 它放弃暴力,接受多元民主思想,试图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和合法的议会斗争来夺取权力,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民主观”,并成长为一股强大的政治伊斯兰力量。 穆兄会新形成的参与议会斗争和“伊斯兰民主”的思想观念对沙特君主统治及其官方瓦哈比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威胁。 由于二者对1990 年海湾战争存在意见分歧,穆兄会和沙特的关系渐趋疏远。 中东剧变后,二者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一,沙特国内接受穆兄会思想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发起伊斯兰“觉醒运动”,从思想和政治实践两方面挑战了沙特的政权合法性。 “觉醒运动”中的一个组织甚至以“沙特穆兄会”来命名。③需要指出的是,“沙特穆兄会”独立于埃及穆兄会,既不效忠于开罗,也不遵从开罗的指令。 参加Stéphane Lacroix, “Saudi Arabia's Muslim Brotherhood Predicament”。
从思想上看,沙特的穆兄会成员把穆兄会的现代主义和传统的瓦哈比意识形态相结合,严重冲击了传统上支持王室的瓦哈比派以及沙特的政教联盟体制。④Wojciech Grabowski,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Crisis in the GCC: Root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 Vol. 2, No. 52, 2016, p. 358.萨法尔·哈瓦利和著名宗教反对派人士萨勒曼·奥达等人强烈谴责沙特建制派乌里玛,称其为“西方”和“世俗主义者”的奴仆。 他们认为,1990 年海湾战争是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进攻,应该推翻未能在战争中维护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利益的沙特王室,改由伊斯兰组织执政。⑤Hillel Frisch and Efraim Inbar, Radical Isla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 79.
从政治实践上来看,部分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发起公开请愿活动,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1991 年2 月,不满沙特与美国结盟的知识分子向时任国王法赫德提交“请愿书”,要求沙特实行民主改革。 5 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500 多名宗教界人士通过沙特大穆夫提伊本·巴兹向法赫德国王呈交“劝告备忘录”,质疑沙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要求限制王室权力、实行广泛的政治改革。①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80 页。而在沙特统治集团看来,“觉醒运动”是穆兄会异化的产物,保守的瓦哈比派教士也抨击它是“沙特版本的穆兄会”。②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1.面对政治反对派和宗教界的压力,沙特国王实行了部分改革。③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480 页。但至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沙特已不愿再容忍“觉醒运动”的挑衅,开始压制“觉醒运动”参与者并驱逐穆兄会成员。 穆罕默德·库特布即是被驱逐的人员之一。④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3.
第二,在中东剧变中,穆兄会势力迅速壮大。 穆兄会“伊斯兰革命”的主张引发沙特对其领导地位和政权安全的担忧,二者关系进一步恶化。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穆兄会2000 年以来通过参与选举政治逐渐进入多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在2011 年地区动荡中急剧扩张。 2002 年,与穆兄会政治理念较为接近的正义与发展党成功问鼎土耳其政权;2005 年,穆兄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在埃及大选中获得88 个席位,成为埃及最大的反对党;2006 年,前身为埃及穆兄会巴勒斯坦分支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2011年,突尼斯“复兴运动”在制宪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 不仅如此,与穆兄会有关的组织或政党还在阿联酋、科威特和沙特密谋策划反对各国统治集团。 穆兄会势力的壮大促使这三个国家于2011 年拉响“穆兄会接管政权”的警报。⑤Eugenio Dacrema, “New Emerging Balances in the Post-Arab Spr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Gulf Monarchies,” 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No. 155, January 2013, p. 4.更严峻的是,随着埃及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穆兄会在2012 年掌管埃及政权。 沙特失去了自1979 年以来共同对抗伊朗的政治盟友,其外部安全环境急剧恶化。 此外,埃及穆尔西政权大打“穆兄会外交牌”,不仅和卡塔尔保持密切联系,还与伊朗建立了友好兄弟关系,并实现1979 年以来的首次互访。⑥柳洪杰:《穆尔西抵达伊朗:埃及总统33 年来实现首访》,中国日报网,2012 年8 月30 日,http:/ /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08/30/content_15720677.htm,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15 日。
从政权安全角度来看,穆兄会在沙特国内鼓动宗教政治反对派,严重触犯了沙特禁忌,威胁了统治集团的权威。 曾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转入地下的沙特“觉醒运动”成员把“阿拉伯之春”视为再次进入沙特政治权力中心的绝佳机会。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工人、劳工联盟活动家、女性主义者联合起来,主导着公共舆论并呼吁改革。①Beverley Milton Edward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Arab Spring and Its Future Fa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76.2011 年2 月10 日,与“觉醒运动”关系密切的伊斯兰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建立了沙特历史上第一个政党——“伊斯兰乌玛党”(Hizb al-Umma al-Islami)。 该党要求实现议会选举,任命一位与国王无关且只对议会负责的总理。②Wojciech Grabowski,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Crisis in the GCC: Root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p. 359.包括萨勒曼·奥达在内的“觉醒运动”著名领导人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要求“建立权力和制度完善的国家”,呼吁“改革”。③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33.尽管“伊斯兰乌玛党”的创建者和请愿活动召集者很快被沙特当局逮捕,但这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觉醒运动”反对派已经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对沙特王室和宗教上层人士构成了一定威胁。
1990 年至2013 年,沙特和穆兄会的关系不断疏远和恶化。 沙特当局专注于打击其国内穆兄会以及穆兄会的支持者,未和地区范围内的穆兄会发生公开冲突,二者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沟通和交流。 例如,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邀请穆尔西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穆尔西访问沙特期间,沙特同意向埃及中央银行提供10 亿美元资金、5 亿美元经济援助,还准备拨款2.5亿美元,以便向埃及出口天然气④石页:《穆尔西“处女访”给了“传统密友”沙特》,载《青年参考》2012 年7 月18 日,第7 版。。 穆尔西承诺“不输出革命”,在就任总统12 天后便将沙特作为首次出访的国家,这足以说明穆尔西对沙特的重视及其强化与沙特关系的愿望。
(三) 持续恶化的敌对关系
2014 年3 月7 日,穆兄会被沙特内政部列为“恐怖组织”,沙特和穆兄会的矛盾全面公开化。 在地区层面,沙特支持埃及军方强力压制穆兄会,并向与穆兄会维持友好关系的卡塔尔施压,最大限度地压缩穆兄会的发展空间。 在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政权后,沙特联合阿联酋迅速向埃及过渡政府提供了12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①Guido Steinberg, “Lead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Germ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June 2014, pp. 17-18, https:/ /www. 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4_RP07_sbg,上网时间:2020 年1 月10 日。沙特还打击穆兄会在利比亚和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 在利比亚,沙特支持由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将军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Libya National Army),打击具有穆兄会背景的“民族团结政府”。 在巴勒斯坦,沙特将作为穆兄会分支的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并于2019 年5 月10 日将哈马斯骨干列入40 人恐怖分子“黑名单”,其中包括哈马斯创始人艾赫迈德·亚辛(Ahmad Yassin)、前任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eshaal)和现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②Adnan Abu Amer, “Hamas Is Worried and Silent About Saudi Arabia's Policy Towards It,” Middle East Monitor, May 15, 2019, https:/ /www. middleeastmonitor. com/20190515-hamas-isworried-and-silent-about-saudi-arabias-policy-towards-it/? fbclid = IwAR11bkeK06gILhaYF-Us1YNEUuu79ET00VvEaAq65cY92UtiNqfqVbiYhXg,上网时间:2020 年1 月18 日。在卡塔尔,早在2014 年3 月,沙特就通过召回驻卡大使来向卡塔尔施压,要求其停止援助穆兄会。③Madawi Al-Rasheed, “Saudi-Qatar Tensions Divide GCC,” Al-Monitor, March 6, 2014, https:/ /www. al-monitor. com/pulse/originals/2014/03/saudi-qatar-gcc-tensions-islamist.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1 月18 日。2017 年6 月5 日,沙特增加对卡塔尔的施压力度,不仅宣布与其断绝外交关系,还对其进行一系列封锁。
在国内,沙特政府官员在多个场合指责穆兄会为“恐怖组织”。 一位沙特官员说道:“早该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了。 我们居然为国外的穆兄会成员敞开学校的大门,允许他们向我们的青年灌输其思想观念。 我们这么晚才意识到,实为不幸。”另一位官员表示:“一些穆兄会成员颁布的法特瓦毁坏了伊斯兰的声誉,影响了沙特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沙特决不允许任何破坏国家稳定的企图得逞。”④Mustapha Ajbaili, “Saudi: Muslim Brotherhood a Terrorist Group,” Al Arabiya English, March 7, 2014, http:/ /english. alarabiya. net/en/News/middle-east/2014/03/07/Saudi-Arabia-declares-Muslim-Brotherhood-terrorist-group.html,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23 日。沙特王室的一位成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穆兄会是恐怖分子的培养皿”,该成员还强调,“奥萨马·本·拉登是穆兄会成员,IS 的巴格达迪也是穆兄会成员。 如果认真查询每一个恐怖分子的资料,你会发现他们都是穆兄会成员”。⑤Mohamed Mokhtar Qandil,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audi Arabia: From Then to Now,”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May 18, 2018, https:/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the-muslim-brotherhood-and-saudi-arabia-from-then-to-now,上网时间:2020 年5 月24 日。
沙特教育部则着手清除渗透进教材及各类书籍的穆兄会思想。 支持穆兄会或受到穆兄会思想影响的人员遭到了严厉打击。 例如,任教于沙特国王大学的穆罕默德·阿里菲(Muhammad al-Arifi)被辞退。①Wojciech Grabowski,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Crisis in the GCC: Root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p. 361.沙特的这些举动使穆兄会受到沉重打击。 穆兄会愤怒地指斥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称该王储“不停地撒谎、不断地散布关于穆兄会的虚假消息,并将穆兄会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他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期望通过获得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好感来得利,而这将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他不是通过自己当之无愧的政绩,而是通过屈辱的让步。”②Mohamed Mokhtar Qandil,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audi Arabia: From Then to Now”.
总的来看,自1953 年以来,穆兄会和沙特的关系经历了从盟友向对手和敌人的演变。 二者关系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以下四大因素。
第一,沙特政权利益的维护。 沙特是在瓦哈比派教义基础上创建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 宗教、王权、部落家族是构成沙特国家政治稳定的三大支柱,其中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与沙特家族统治从宗教和传统两方面为沙特君主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提供了坚实基础。③曲洪:《伊斯兰: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70-172 页。作为“两圣地的仆人”,沙特的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利益在于坚持伊斯兰教义,保持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特色,抵御世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和制。 当沙特面临来自奉行世俗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纳赛尔共和政权的威胁时,穆兄会就成为沙特的政治盟友;当穆兄会的意识形态成为沙特宗教政治反对派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并威胁沙特的政权安全时,穆兄会就成为沙特打击的对象。
第二,与官方瓦哈比派的关系。 瓦哈比派教义是沙特的官方教义,瓦哈比派和沙特政权是“二元一体”的宗教—政治联盟关系。 瓦哈比派强调对君主忠诚,而穆兄会反对人治,严格遵守“真主主权”和对超越民族、地域和血缘的乌玛的忠诚。 这意味着二者具有内在张力,很容易产生冲突和对抗。 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瓦哈比派排斥一切现代器物和文明,对现代化具有强烈现实需求的沙特被迫向主张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穆兄会寻求支持,暂时压制了穆兄会与瓦哈比派的冲突,使得双方呈现出一种合作的盟友关系。 随着穆兄会在沙特社会和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逐渐加深,其与官方瓦哈比派的矛盾急剧凸显,并从根本上危及沙特的政教联盟关系,沙特王室便强化了瓦哈比派的地位,沙特与穆兄会的关系出现恶化。
第三,现代化进程中下层民众的不满。 沙特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导致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突出,产生了一批不满现状和要求变革的下层平民。 相较于代表精英和统治集团的官方瓦哈比主义,注重社会下层的穆兄会获得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机会。 长期潜伏于沙特教育领域的穆兄会成员或亲穆兄会者将其激进思想和瓦哈比派的原旨教义有机结合,要求“通过‘圣战’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由此,被称为‘新瓦哈比派’或‘新伊赫万运动’的武装叛乱集团形成”①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41 页。。 穆兄会和沙特国内不满现状者形成联盟,严重挑战了沙特政权的统治基础。 这是导致沙特和穆兄会后来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穆兄会宗教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分化。 如果说沙特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二者关系变化这枚硬币的一面,那么穆兄会宗教政治思想变化则是另一面。 在纳赛尔政权的打压下,穆兄会发生温和化和激进化的分化。 一方面,自哈桑·胡代比(Hassan al-Hudaybi)承认世俗社会合法性以及认可政党和多党制的政治理念②易小明:《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37-38 页。以来,作为主流的温和派逐渐走上参与议会政治的道路,试图通过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其伊斯兰民主政治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力。 但穆兄会组建政党和参与议会政治的战略不仅在沙特国内激起要求政治改革的连锁反应,而且还挑战了沙特伊斯兰君主统治模式和瓦哈比官方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赛义德·库特布提出了以暴力手段推翻世俗政权的反国家、反社会的极端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沙特的传播同样威胁着沙特王室的统治。 因此,无论穆兄会宗教政治思想走向温和化还是激进化,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穆兄会和沙特的关系走向敌对。
三、 穆兄会对沙特内政外交的影响
在沙特王国的政治环境中,穆兄会不可能通过组建政党成为沙特的一支政治力量,但穆兄会在沙特的长期存在仍然对沙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对沙特而言,穆兄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积极影响,也产生消极影响。 20 世纪50年代至80 年代末,穆兄会对沙特的积极影响多于消极影响。 其中的积极影响主要有:穆兄会帮助沙特抵抗来自埃及纳赛尔的攻击,促进实施泛伊斯兰主义战略,扩大了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消极影响主要有:穆兄会库特布极端思想为沙特国内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 海湾战争后,穆兄会对沙特的危害凸显,消极影响急剧上升,积极影响日益减弱。 库特布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沙特本土原始瓦哈比主义①这里的原始瓦哈比主义,指的是沙特建国前在阿拉伯半岛盛行的瓦哈比主义。 沙特建国后,放弃了早年瓦哈比派“圣战”的宗教—政治主张,规定在国内的宣教布道上不得鼓吹“圣战”思想,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禁止以宗教名义干预政治或攻击、诋毁国王和王室。 为更好区分本文多次所述“瓦哈比”的不同含义,笔者将沙特建国后官方信奉的相对温和的瓦哈比主义称为官方瓦哈比主义,它与1979 年后沙特民间出现的主张通过“圣战”、暴力和恐怖活动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的瓦哈比主义不同。 金宜久先生将1979 年后出现的持“圣战”极端思想、坚持原旨教义的瓦哈比派称为“当代瓦哈比派”。 文中提及的“瓦哈比派”皆指沙特官方瓦哈比主义,偶有提及的“原始瓦哈比主义”指的是沙特建国前出现的瓦哈比主义,而将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出现的反对沙特王权,主张干预政治的瓦哈比思想统称为“民间瓦哈比主义”。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第234-245 页。的融合,激活了曾经被瓦哈比派废弃的“圣战”思想,沙特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袭击行动的危害。 中东剧变后,穆兄会还成为卡塔尔用来争夺地区领导权、削弱沙特地区影响力的工具。
(一) 为沙特对抗纳赛尔世俗政权和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战略提供支持
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提供思想指导,还是国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义外衣。
第一,穆兄会是沙特抵制埃及纳赛尔对其君主制进行攻击的有力武器。 20世纪50 年代初,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纳赛尔掌握埃及政权后,一批新的共和制国家陆续建立。 先后于1958 年、1962 年和1967 年成立的伊拉克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及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从东西两面包抄,对沙特几近形成合围之势。 而当时瓦哈比派的影响力主要限于阿拉伯半岛地区,并不能很好地配合沙特政权抵抗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强烈冲击。 于是,穆兄会成为沙特用来与埃及进行竞争的重要工具。 沙特庇护和资助了一批来自埃及的穆兄会成员,使得埃及穆兄会在沙特得以秘密重建。 其中一些人潜回埃及,网罗穆兄会中坚分子,加紧行动,不断对抗纳赛尔政权。②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383-384 页。而在沙特的穆兄会成员,则被鼓励将沙特的财富和权力解释为是对沙特虔诚信仰的神圣嘉奖。③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5.通过扶持对手的对手,沙特守住了对抗纳赛尔的意识形态阵地。
第二,穆兄会是沙特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穆兄会和瓦哈比教派的主张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其中包括信奉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中最严格的罕百里教法学派。 二者激烈反对什叶派和“圣徒”崇拜,主张宗教改革和“净化”宗教,并具有实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共同要求。①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p. 117.但沙特瓦哈比派强调忠诚于君主,这使其难以在国外广泛流行起来。②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p. 64.因此,与瓦哈比派有一定共性、寻求将伊斯兰传统和西方政治经验相结合且具有更灵活教义和广泛跨国网络的穆兄会,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为费萨尔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费萨尔资助建立的众多泛伊斯兰组织中,穆兄会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包括穆斯林世界联盟和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③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Arabia, p. 42.这些组织促进了瓦哈比主义的传播,同时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沙特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④Hicham Moura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audi Arabia,” Ahram Online, May 15, 2013, http:/ /english.ahram.org.eg/News/71498.aspx,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18 日。
(二) 沙特社会宗教氛围趋于保守,宗教政治反对派兴起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逃亡至沙特的许多穆兄会成员信奉库特布的极端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沙特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宗教政策,宗教政治反对派逐渐兴起。尽管不能把库特布宗教极端思想对沙特反对派的影响绝对化,也不能将沙特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完全归因于穆兄会,但不能忽视的是,穆兄会尤其是库特布极端思想的传播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一,穆兄会意识形态在沙特的传播对沙特的社会氛围和宗教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广泛分布于沙特教育领域的穆兄会成员向学生和青年灌输仇恨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教导学生有责任也有义务推翻不严格执行沙里亚法的有罪伊斯兰政权和统治穆斯林的异教徒政权,建立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政权。他们还谴责沙特政权是美国这一异教徒政权的同谋者。⑤Hillel Frisch and Efraim Inbar, Radical Isla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 76.来自叙利亚的许多穆兄会女性成员成功说服了沙特女学生排斥西方文化和佩戴遮盖面部的面纱(Niqab)。⑥Robert Lacey, Inside the Kingdom: Kings, Clerics, Modernists, Terrorists, and the Struggle for Saudi Arabia, London: Viking Penguin Group, 2009, p. 56.
因受1979 年麦加禁寺事件的影响,沙特为维护其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的形象,陷入了一场争夺伊斯兰教正统性和话语权的无声战争。 为回应受到库特布极端思想和原始瓦哈比主义影响而兴起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沙特哈利德国王及其后继者法赫德国王转向较为原始和保守的瓦哈比主义,在教育和社会管理上执行了更加严格的宗教政策。 在教育领域,沙特增加了宗教教育的比重,高中生花在宗教必修课上的时间占比为1/4,高校里学习伊斯兰教的学生也增多。 在社会领域,沙特严格遵守原始瓦哈比教义。 店主不得在店内礼拜,必须停止营业前往清真寺礼拜。 曾经仅在内志地区执行的男女隔离制度也扩散至沙特其他地区。 政府还禁止报纸和电视上出现不遮面的女性。①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pp. 83-85.
第二,穆兄会促成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 在来自埃及、叙利亚等国穆兄会教师的影响下,穆兄会积极参与政治的思想观念被糅合进沙特的民间瓦哈比,使得沙特出现了伊斯兰“觉醒运动”,沙特政权受到政治改革的压力。②Thomas Hegghammer, Jihad in Saudi Arabia: Violence and Pan-Islamism Since 197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受到穆兄会思想影响的沙特青年和宗教学者倡导“公民吉哈德”(Civil Jihad),抨击建制派乌里玛,还试图模仿埃及穆兄会通过议会选举参与政治,希冀通过和平手段改革沙特现有政治体制,将沙特建成尊重公民权利的君主立宪制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民主。③Stéphane Lacroix, “Saudi Islamists and the Arab Spring,” pp. 2-3.
此外,1993 年5 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中的6 名主要成员宣布成立沙特首个人权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gitimate Right)。 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将反政府活动同世界人权运动挂钩,使沙特政府陷入被动。④王铁铮:《浅析九十年代沙特王国的伊斯兰潮》,载《西亚非洲》1996 年第6 期,第16 页。曾为沙特穆兄会成员的瓦利德·阿布·哈伊尔(Walid Abu al-Khayr)在2008 年成立沙特“人权监察”(Monitor of Human Rights)机构。⑤Stéphane Lacroix, “Saudi Islamists and the Arab Spring,” p. 7.中东剧变后,沙特境内主张以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来推动国内政治变革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再次兴起。
(三) 受库特布思想影响的极端分子对沙特发动恐怖袭击
20 世纪80 年代,许多从阿富汗返回的极端分子在沙特成立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并针对美军、西方人以及沙特安全部队和官员发动恐怖袭击。 沙特深受恐怖袭击之害。 1996 年,沙特东部城市胡拜尔(Al Khobar)发生汽车爆炸,19 名美军丧生,近400 人受伤。①Erica Pearson, “Khobar Tower Bombing of 1996,”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June 18, 2019, https:/ /www. britannica. com/event/Khobar-Towers-bombing-of-1996,上网时间:2019 年11月18 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沙特在2003 年至2006 年遭到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 2003年5月和11月,沙特连续遭到多起爆炸袭击事件。②张金平:《沙特去“极端化”反恐策略评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5页。排除已被沙特警方挫败的恐怖袭击,从2003年至2007年,仅“基地”组织就在沙特成功实行20至25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其中包括5次自杀式重型汽车炸弹袭击,5次多人协作枪击和12次单人暗杀袭击。③Thomas Hegghammer, “Jihad, Yes, but Not Revolution: Explaining the Extraversion of IslamistViolence in Saudi Arabia,”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3, 2009, pp. 401-403.2004 年,沙特发生了8 起针对安全部队和外资企业的恐怖袭击。④马晓燕:《沙特阿拉伯自2003 年5 月发生血腥连环汽车爆炸事件后频遭恐怖袭击》,载《北京晨报》2004 年12 月7 日,第12 版。2007 年后,沙特的恐怖袭击数量减少,但仍有发生。 2011 年以来,沙特反恐形势再次恶化。 2016 年,沙特遭遇恐怖袭击数量高达34 起。⑤《2016 年沙特遭遇恐怖袭击34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驻吉达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2017 年1 月11 日,http:/ /jedd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1/20170102499505. 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12 月20 日。
沙特政府将国内发生的恐怖袭击直接归因于穆兄会。 有人认为, “觉醒运动”作为穆兄会的“变种”,是沙特暴力事件发生的幕后黑手。 事实上,“沙特不支持暴力,暴力是由那些20 世纪60 年代进入沙特的人带来的。”还有人表示,“我们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感到十分陌生。 但它却在学校和清真寺广泛传播,很多年轻人就像高级宗教学者一样在学校和清真寺宣教……他们都是穆罕默德·库特布的学生,到处散布赛义德·库特布和毛杜迪的思想。”⑥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7-78.
(四) 中东剧变后穆兄会成为沙特既有外交政策的制约因素
伊斯兰教是沙特在外交政策中用来确保和巩固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软实力”,是维护王室政权的统治及其合法性的工具。 然而,穆兄会在沙特庇护下发展壮大后,反而成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竞争者,制约和阻碍了沙特外交政策的执行。
第一,20 世纪90 年代穆兄会通过自身的温和化与和平参政议政,在中东国家的影响不断扩大,而沙特实行的政教合一君主制模式的影响力则有所下降。2000 年以来,穆兄会或支持穆兄会的政党在一些国家进入政治权力中心。 尤其是中东剧变后,“出现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都在探索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动伊斯兰民主的建设”①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5 期,第79 页。。 尽管沙特支持埃及军方通过“7·15”政变罢黜了穆尔西政权,但穆兄会将其伊斯兰思想付诸政治实践所带来的效应,仍对沙特的政治模式构成潜在威胁。
第二,穆兄会势力的扩大导致沙特与卡塔尔关系持续恶化,沙特的地区领导权和影响力受到严重挑战。 对沙特来说,什叶派伊朗是其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和确保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 维持对逊尼派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是沙特与伊朗在竞争与对抗过程中必须掌握的筹码。 然而,具有全球网络的穆兄会却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中打下了多个“楔子”,它在中东多个国家建立分支,组建具有穆兄会性质的政党,并利用局势变化通过政治选举参政或掌握政权,这严重阻碍了沙特外交战略的实施。 卡塔尔不仅支持在埃及执政的穆兄会政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与由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土耳其关系日益密切。②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5期,第57-58 页。
由于对穆兄会的立场不同,2017 年6 月5 日,沙特联手阿联酋等国与卡塔尔断交,要求卡塔尔停止支持穆兄会和哈马斯等组织。 延续多年的沙特和卡塔尔的断交危机,实际上已导致海合会陷入内部矛盾和分裂,阿拉伯国家整体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同时,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则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弱化对其展开争夺,从而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③同上,第61 页。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而言,穆兄会因素的凸显推动了地缘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地区安全形势趋于恶化。
总的来说,穆兄会对沙特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 1953 年至1990 年,穆兄会与沙特的关系较为积极,穆兄会在沙特反制纳赛尔政权及其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战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不过,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在沙特教育和社会领域的传播潜藏一定风险。 1990 年以后,穆兄会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它带来的风险演化为事实上的危害。 同时,也正由于穆兄会对沙特政权及其官方瓦哈比主义造成了消极影响,沙特开始严格控制穆兄会的发展规模,并限制其影响力的扩大。 因此,相较于海湾等其他国家的穆兄会,沙特的穆兄会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在不允许政党存在和强调王权至上的沙特,穆兄会不可能像在科威特那样以政治反对派的形式参加国会选举,也不可能像在埃及那样通过议会选举参政或上台执政,更不可能像在卡塔尔那样通过放弃组织党派、避免参与其国内事务而“与王室和政府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①刘辰:《卡塔尔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3期,第143 页。成为政府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四、 结语
沙特与穆兄会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建立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与相互利用的盟友关系向疏远与对抗的对手和敌人关系的转变。 沙特建国初期对来自埃及等国穆兄会的接纳和庇护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主义色彩。 穆兄会为沙特抵抗来自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跨国网络为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提供了重要支持,其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实用主义态度为沙特的现代化改革增添了助力。 然而,沙特在利用穆兄会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同时,穆兄会也利用沙特的资金和庇护将其思想观念输入到教育领域这一意识形态竞争的关键阵地。 它还与沙特社会中的不满现状者结盟,形成了对沙特政权构成重大威胁的宗教政治反对派。 此外,一些接受库特布极端主义思想的沙特人自阿富汗返回后将沙特政权作为“圣战”对象,这导致沙特自身也深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害,令沙特政权始料未及。
对沙特来说,维持与瓦哈比派的政教联盟是其立国之根、治国之本,保持对教权的控制,使教权服从王权是题中之义。 沙特对穆兄会的态度和穆兄会在沙特的发展状况取决于穆兄会能否服务于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对外战略及其国家利益。 当穆兄会以及受其影响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对沙特王权构成威胁,阻碍其地区战略的实行时,沙特会果断地对其进行打击。 正是由于中东剧变以来穆兄会在地区范围内推行伊斯兰民主模式,与沙特的战略竞争者和对手保持密切联系,导致2014 年沙特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并于2017 年6 月不惜冒着海合会瘫痪的代价与卡塔尔断交。 从阿拉伯整体视角来看,穆兄会因素给海湾和更大范围的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分化,这不利于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地区安全环境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