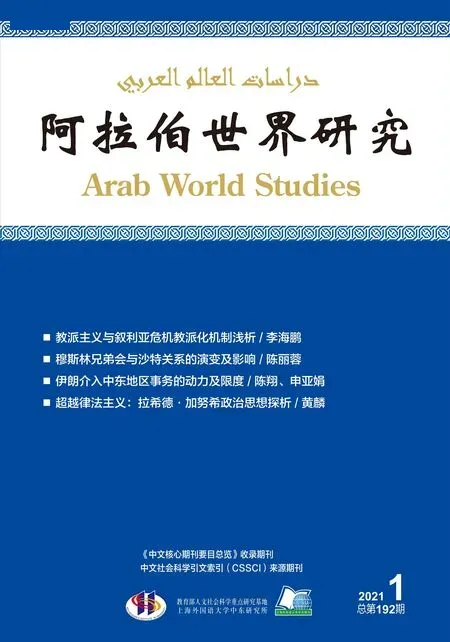利益、信息与偏好:美军与安巴尔部落镇压叛乱的代理人战争∗
文少彪
2006 年9 月,美军支持下的伊拉克安巴尔(Anbar)部落发动“觉醒运动”(Awakening Movement),“一股强大的逊尼派力量将扎卡维的残余势力从大街小巷中清除出去,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地下世界”①[美]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 的崛起》,钟鹰翔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版,第243 页。。 负责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Islamic State in Iraq)②该组织自称“伊拉克伊斯兰国”,美国一般称之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或“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AQI),因此很多研究这一时期伊拉克的英文文献中所称的“基地”组织就是指“伊拉克伊斯兰国”。 本文统一称之为“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对当地部落参与军事行动的意义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伊拉克的部落反抗减少了美国的伤亡,加强了安全,甚至节省了美国纳税人的钱。”③General David H. Petraeus, Commander of Multi-National Force-Iraq,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Iraq,” Testimony on Senat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eptember 10-11, 2007.从代理人战争的角度看,彼得雷乌斯不自觉地表达了“委托方中心”的逻辑:委托方(也称施动方)在干涉目标国事务的过程中可以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代理人,从而避免自身卷入与对手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虽然历史中不乏大量可以印证代理人战争成效的案例,但学界更常用诸如“双刃剑” (double-edged sword)、“回火”(backfire)或“反吹”(blowback)来形容和揭示代理人战争附带的长期或潜在代价。 美军支持安巴尔部落发起的代理人战争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在解除“伊拉克伊斯兰国”威胁的过程中,安巴尔部落成为美军的代理人,但这种联手逐渐偏离双方的共同议程并走向抛弃与背离。 那么,这场代理人战争为何会朝着不受彼此欢迎和控制的方向演化? 为何美军难以完全管控在实力上弱小得多的安巴尔部落?
一、 利益、信息、偏好与代理人战争
结合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利益、信息与偏好三个维度来观察和理解这场代理人战争的复杂过程。
(一) 利益维度
在代理人战争中,当遵循委托方的偏好也恰好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时,即某项特定议程同时对委托方与代理人都很重要,则两者在特定时间段被视为利益匹配。 利益匹配对于代理关系的建立、维系以及对代理人自主性管控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伊莱·贝尔曼(Eli Berman)、大卫·莱克(David A. Lake)等学者指出,在代理人战争中,“委托方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或目标的一致是最重要的”,利益分歧越大,代理人的努力成本越高。 当委托方与代理人的利益完全不匹配时,“委托方提供的资源不会被代理人用来抑制对前者的威胁,而是用来追求后者的优先议程”①Eli Berman, et al., “Principals, Agents, and Indirect Foreign Policies,” in Eli Berman and David A. Lake, eds., Proxy Wars Suppressing Violence Through Local Agen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4, 10.。 利益匹配程度越低,委托方越倾向于直接处理问题,而代理人则越倾向于维持高度的自主性,代理关系也就无从建立或不稳定。②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1 期,第27-52 页。
然而,委托方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匹配通常是一种理想化的巧合或一厢情愿的假想,如果考虑时间因素,利益分化则更符合常理。 一般认为,“代理人战争中的主要风险集中在代理人动机、战斗方式以及委托方与代理人的战争目标不一致等方面”③Candace Rondeaux and David Sterman, “Twenty-First Century Proxy Warfare: Confront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Washington, D.C.: New America, 2019, p. 20.。 基于理性,委托方希望付出最低的成本让代理人不知疲倦地工作,而代理人则希望从前者那里获得最多的援助并从事最轻松和安全的任务。在代理人战争中,委托方的利益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代理人不同,尽管存在权力不对称,但代理人几乎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冲动行事,他们对彼此的期待是理想化和矛盾的。④Stephen Biddle, Julia Macdonald and Ryan Baker, “Small Footprint, Small Payoff: The Military Effectiveness of 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1, No. 1-2, 2017, p. 96; Daniel Byman, “Approximating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8, p. 13.正因如此,丹尼尔·拜曼(Daniel L. Byman)指出,“当美国依靠其盟友打击美国的敌人时,它不仅必须认识到后者的有限能力,而且必须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不同。”⑤Daniel Byman, “Friends Like These: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2006, p. 112.在利益分化的情形下,代理人将优先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付出多少努力。
(二) 信息维度
艾瑞克·雷廷格尔(Eric Rittinger)指出:“代理关系涉及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签订的正式或非正式合约。 委托方将一些权力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则负责代表委托方工作。”⑥Eric Rittinger, “Arming the Other: American Small Wars, Local Proxi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2, 2017, p. 397.信息非对称是指一方拥有其他方不拥有的信息,它使得委托方与代理人之间开展真诚合作变得异常困难。 代理人通常对如何执行代理议程和实际付出的努力程度有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不容易被委托方所衡量或观察。因此,代理人在执行代理任务方面具有私人信息优势。
这种“信息差”为代理人谋求私利提供了掩护,使其拥有了进退自如的主动性。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均指出,信息非对称造成的不确定性是阻碍协议达成并导致合作低效的重要根源之一,一些行为体可能比其他行为体对某种形势所占有的信息更多,即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知识,因此有能力和政治优势操纵一种关系或者成功地实施欺诈行为。①[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96 页;[美]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8-21 页。为降低信息不足的劣势,理性行为体都试图占有相对更多的信息,因为“信息就是力量,信息会有利于那些掌握私人信息的行为体”②[美]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第20 页。。 在代理人战争中,委托方往往要求代理人及时报告其全部所知信息。 但这意味着代理人谋求私利的空间将变小,不会得到代理人的全面配合。 在争夺信息优势的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是持久的和结构性的。 例如,美国在中东地区打击叛乱分子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代理伙伴可以操纵上报给美国的情报。 代理伙伴可以把当地的叛乱分子描绘成“基地”组织的一部分,也可以夸大受援机构的作战效力,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对这场斗争的看法,谋求美方增加整体援助规模。③Daniel Byman, “Friends Like These: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p. 112.委托方(国家)更有可能通过外交和情报接触来获得信息,但代理人(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主要从不同的地下来源获取信息,这种“信息差”在原本契合的偏好之间插上了一个楔子。 信息不对称使得委托方陷入“两难”:尽管缺乏关于代理人的能力和意图的完整、及时、真实的信息,但委托方仍然期待后者来完成自身不便或不愿意执行的任务。 这种信息非对称可能会鼓励代理人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同时偏离委托方的指示,同时仍然获得代理关系带来的好处。
(三) 偏好维度
偏好异质指代理人内部不同的利益团体拥有的偏好不一样,它们对代理议程的认知存在理想目标上的错位,以至于在代理议程上做出不同的反应。 在代理人战争中,代理人是一个集体而不能被简化为一个“黑箱”,其内部的权力、观念和利益等结构具有重大影响。 代理人往往是由不同的利益单元(派别、团体、族群、政党等)组成,每个单元都有对特定利益负有责任的领导人,不同单元所具有的能力、资源、处境、观念不一样。 有些代理人的政策目标是在国家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获得更多的领土自治,其他一些团体只是想获得物质财富和权位。
偏好异质会削弱代理人集体行动的能力和意愿。 在一个松散的代理人集体中,没有最高的权威可以化解内部分歧、统合所有的忠诚并有效塑造对共同威胁和整体利益的感知,这使得为代理议程所采取的集体行动变得异常困难。 例如,“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是由众多大小不一的武装团体组成的松散反对派联盟,其内部并不存在一个最高的、有效的指挥机构和共同议程。 有学者认为,“‘叙利亚自由军’不过是一个‘伞状组织’,一个没有自上而下命令和控制的松散机构”①Rania Abouzeid, “The Jihad Next Door: The Syrian Roots of Iraq's Newest Civil War,” Politico Magazine, June 23, 2014, https:/ /www. politico. com/magazine/story/2014/06/al-qaedairaq-syria-108214_full.html,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0 日。。 当代理人“黑箱”被打开,人们会发现其内部的“碎片化”现象,代理人因偏好异质而削弱了其凝聚力和领导力,这不仅对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构成巨大挑战,也致使对拥有不同资源和意愿的力量单元实行有效控制变得异常困难,一部分不认可、不服从代理议程的力量单元可能出现懈怠和偏离,致使代理人内部呈现出“分裂式”自主性。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维度并非同等重要,利益是首要的观察维度,而信息和偏好两个维度起到辅助作用。 当委托方与代理人的利益出现分化,考察信息不对称和偏好异质对代理人谋求自主性产生的影响会更有意义。 本文将从以上三个维度考察美军利用安巴尔部落力量镇压“伊拉克伊斯兰国”叛乱问题。 从案例研究价值来看,镇压叛乱本属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职责,但游离或被排斥于权力体系之外的地方非政府力量(部落)也加入了这一过程,其反常的“跨界”角色构成了一个特殊案例。 该案例符合代理人战争的特征并呈现出明显的代理困境,折射出伊拉克战后秩序重建的复杂性,也构成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略“包裹”里的一个标本和模式,具有更广泛的理论与现实参考价值。
二、 从反美到联美: 代理关系的形成
位于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聚集了大量的逊尼派部落,当地的反美主义长期盛行,但他们为何从反美转向联美,转而对付此前受其庇护的“基地”组织?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值得深入探究。
(一) 安巴尔成为反美中心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去复兴党化”政策激化了教派冲突。伊拉克战争之前,教派之间的分界线和冲突并不是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而美国在伊强力推行“美式民主”,使什叶派借机上台执政,为激化多年的教派积怨爆发埋下了隐患。①Ghali Hassan, “Iraq's New Constitution,”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ugust 17, 2005, https:/ /www.globalresearch.ca/iraq-s-new-constitution/837,上网时间:2019 年11月20 日;杨洪林:《浅析伊拉克战后的教派之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 年第5 期,第29 页。小布什政府倾向于构建包括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在内的新伊拉克,但这不过是美国政府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为了在伊拉克建立“三位一体”且“自我运转”的联合政府和新社会秩序,美国驻伊拉克“同盟临时权力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负责人布雷默(Paul Bremer III)推行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去复兴党化”法令和伊拉克宪法草案,肃清前“复兴党”在政治体系中的残余精英力量并允许流亡“海归派”(什叶派力量)填补当时占领当局设置的几乎所有临时政府职位,解散50 万之众的伊拉克武装、情报机构并重组伊拉克安全部队,私有化逊尼派主导的庞大国有经济体系并引入外国资本。②“Order Number 1: De-Ba'athification of Iraqi Society,”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 in Iraq, May 16, 2003, https:/ /web. archive. org/web/20040621014307/http:/ /www.iraqcoalition.org/regulations/20030516_CPAORD_1_De-Ba_athification_of_Iraqi_Society. pdf; “Order Number 2: Dissolution of Entities,”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in Iraq, May 23, 2003, https:/ /web. archive. org/web/20040701202042/http:/ /iraqcoalition. org/regulations/20030823 _CPAORD_2_Dissolution_of_Entities_with_Annex_A.pdf; “Order Number 39: Foreign Investment,”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in Iraq, September 19, 2003, http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20031220_CPAORD_39_Foreign_Investment. pdf; Ghali Hassan, “Iraq's New Constitution,” Global Research, August 17, 2005,https:/ /www. globalresearch. ca/iraq-s-new-constitution/837,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3 日。布雷默的私有化政策和解散伊拉克军队的决定被普遍认为助长了伊拉克反抗美国占领的叛乱。③Naomi Klein, “Baghdad Year Zero: Pillaging Iraq in Pursuit of a Neocon Utopia,”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24, 2004, https:/ /harpers. org/archive/2004/09/baghdad-year-zero/; Jeremy R. Hammond, “Documents Indicate Policy Plan That Fueled Iraqi Insurgency Was Compartmentalized in Rumsfeld's Pentagon ”, Foreign Policy Journal, February 17, 2011, https:/ /www.foreignpolicyjournal. com/2011/02/17/documents-indicate-policy-plan-that-fueled-iraqi-insurgencywas-compartmentalized-in-rumsfelds-pentagon/, 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3 日。美国一系列失衡的宗派政策在短期内摧毁了逊尼派的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优势地位,导致国家机构中的十几万精英失业,加剧了伊拉克本土势力、社会民众对美国扶植的临时傀儡政府的不信任和仇视,被边缘化的逊尼派成员纷纷加入宗派民兵组织寻求经济和安全庇护。 最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的政策都导致不断升级的宗派紧张局势,鼓励了以宗派方式表达的报复行动,叛乱活动、教派暴力层出不穷。①Nabil Al-Tikriti, “US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a Sectarian Iraq,”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2, 2008, https:/ /www. mei. edu/publications/us-policy-and-creation-sectarian-iraq, 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7 日。总的来看,美国占领伊拉克初期(2003 年~2005年)的政策导致什叶派主导的权力系统在“复兴党”强人体制的迅速瓦解中被建立起来,但“去复兴党化”政策没能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伊拉克,失业的逊尼派政治、军事精英无法通过票箱获得权力。 他们开始抵制2005 年12 月的选举并诉诸暴力以反抗什叶派的夺权,这种变化使得战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转变为反抗美国统治的武装起义。②[美]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 年至今》,廉超群、李海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647-649 页。伊拉克在政治与社会结构大重组的过程中滑向美国无法控制的教派冲突深渊。
逊尼派群体普遍将美军视为有利于什叶派的入侵者,伊拉克最西部的安巴尔省不仅是逊尼派的一个据点,而且成为窝藏“基地”组织分子和发动叛乱活动的中心。③安巴尔省是伊拉克面积最大的省,人口大约为100 万,90%以上为逊尼派阿拉伯人,长期以来在部落的统治下,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有限。 安巴尔省紧邻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接壤,2005 年已经成为叛乱分子的一个关键活动区,叛乱分子利用沙漠和崎岖的地形进行走私活动。美军以入侵者的姿态进驻安巴尔省,没收当地民兵组织的武器,与当地居民保持隔离、猜疑的状态,且缺乏对部落文化传统的尊重。 当地的部落酋长阿卜杜·萨塔尔(Abdul Sattar)指出:“美国朋友来的时候没有理解我们。 他们是骄傲、固执的人,我们也是。”④Fouad Ajami, “You Have Liberated a Peopl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0, 2007, http:/ /www.opinionjournal.com/editorial/feature.html?id110010610,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7 日。此外,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流向逊尼派地区的石油收入被切断,引发当地人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导致他们通过袭击石油设施等策略阻止石油生产或出口,直到得到他们认为公平的那部分收益。⑤Michael Schwartz, “It's Still About the Oil,” The Nation, June 24, 2014, https:/ /www.thenation.com/article/its-still-about-oil-stupid/,上网时间:2019 年11 月27 日。逊尼派部落群体认为美国重建伊拉克是要以他们的利益为代价。 “美国的占领并赋予什叶派权力,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从国家机器中清除出去以及解散逊尼派主导的军事和安全机构,都助长了激进的抵制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使逊尼派叛乱合法化并纵容了叛乱。”⑥Harith Hasan Al-Qarawee, “Iraq's Sectarian Crisis: A Legacy of Exclus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14, p. 11.美国对伊拉克的战后秩序改造计划本质上是基于教派主义的,帮助什叶派掌握了中央政府权力,致使逊尼派饱受权力被剥夺的痛苦,加之美国在部落区推行戒严令和支持伊拉克民主化进程等,破坏了部落酋长在该地区的传统权力和控制其部落成员的能力,这促使他们倒向“伊拉克伊斯兰国”并支持针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主导的中央政府和美军的全面叛乱。①Carlos Pascual and Kenneth Pollack, “Salvaging the Possible: Policy Options in Iraq,”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September 2007, pp. 3-4; John A. McCary, “The Anbar Awakening: An Alliance of Incentiv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2, No. 1, 2009, p. 44; David Unger, “The Foreign Policy Legacy of Barack Obama,”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1, No. 4, 2016, p. 9.安巴尔省有不少部落成员受到“基地”组织的极端意识形态吸引,他们同情、包庇“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甚至暗中提供情报、物资支持叛乱活动,一些部落成员直接参与袭击和杀害美国士兵。
“基地”组织从碎片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中找到渗透机会,将西部逊尼派部落区变成叛乱中心。 “伊拉克伊斯兰国”抵制战后秩序的重建,努力使伊拉克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国家,乘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该组织打着“圣战”旗号招募大量外籍武装分子和少量当地的极端分子前往反美主义高涨的安巴尔安营扎寨。费卢杰和拉马迪成为叛乱策源地,俨然成为叛乱者的庇护“天堂”。 为谋求更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伊拉克伊斯兰国”故意激化教派冲突,2006 年2 月炸毁了阿斯卡里亚什叶派清真寺(Askariya Shrine),成功点燃了教派仇恨情绪。 “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最高委员会”(Shiite 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组建“敢死队”,进一步升级了教派冲突。 截至当年10 月,教派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每月高达3,000 人左右,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从每天70 起增加到180 起。②[美]罗伯特·盖茨:《责任: 国防部长回忆录》,陈逾前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1 页。在安巴尔省,主要由逊尼派极端分子发起的针对联军、伊拉克安全部队、平民和基础设施的暴力活动极为猖獗,2006 年8 月至11 月,平均每天发生40 多起袭击事件,高居伊拉克各省之首。③“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 Report to Congres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2006, pp. 17-21.
(二) 联美: 应对“伊拉克伊斯兰国”威胁
“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叛乱活动严重威胁到美军在伊拉克的安全与重建进展。 该组织设想通过叛乱活动使美军战后重建计划失败并撤出中东,其战略接近于成功。④Michael E. Silverman, Awakening Victory: How Iraqi Tribes and American Troops Reclaimed Al Anbar and Defeated Al Qaeda in Iraq, Philadelphia: Casemate Publishers, 2011, p. iv.“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发展对美军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文件指出,必须“采取反恐行动阻止‘伊拉克伊斯兰国’通过建立安全庇护来侵蚀迄今取得的安全成果”①“Prospects for Iraq's Stability: Some Security Progress but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Elusive,”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August 2007, p. 4, https:/ /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Press%20Releases/2007%20Press%20Releases/20070823_release.pdf,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 日。。 此外,伊拉克的叛乱和宗派暴力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挑战和安全威胁,如不能有效消除“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威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秩序塑造能力以及在盟友中的威望、信誉都将受到质疑。②Christopher M. Blanchard, Kenneth Katzman, Carol Migdalovitz, Jeremy M. Sharp, “Iraq: Regional Perspectives and U. 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6, 2009, pp. 32-34.然而,利用大规模的、笨重的正规地面部队来对付叛乱活动是无效的。 截至2006 年,美军在伊拉克死亡3,000 多人,其中875 人死在安巴尔省。③Joshua Partlow, “Sheiks Help Curb Violence in Iraq's Wes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07.美军对死亡的敏感性极高。“对美国而言,选择代理人战争通常是基于成本考虑:当地人承担战斗和死亡,而美国人不必如此”④Danniel Byman, “Approximating War,” p. 12.。 而且,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士兵数量和预算与其进行的反叛乱任务之间根本不相称。 如果没有伊拉克本土力量的支持,美军将不堪重负。⑤Steven N. Simon, “After the Surge: The Case for U. S.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Iraq,” CSR No. 23,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2007, pp. 3-4.
与此同时,由于“伊拉克伊斯兰国”对安巴尔部落日益上升的威胁,其不再被认为是“反美事业”的“圣战斗士”。 随着形势的发展,“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始运用经济制裁、暴力施压和极端主义等手段加强对部落的控制,继而严重威胁到部落酋长的统治地位和部落传统利益。 2005 年末至2006 年夏季,大量来自境外的“伊拉克伊斯兰国”成员快速向安巴尔省聚集,他们开始在当地散布极端宗教思想,对当地部落的文化传统、社会秩序、生活习俗进行干预,破坏社区的公共设施,企图控制走私获取高额利润,扼杀部落的非法经济活动,一些不顺从的部落领袖也遭到生命威胁。⑥Kimberly Kagan, “The Anbar Awakening: Displacing al Qaeda from Its Stronghold in Western Iraq,”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ISW), August 21, 2006-March 30, 2007, pp. 5-6; S. Tavernise and D. Filkins, “The Struggle for Iraq: Skirmishes; Local Insurgents Tell of Clashes with Al-Qaeda's Forces in Iraq,”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06, http:/ /query. nytimes. com/gst/fullpage.html?res=9F07EFD7163FF931A25752C0A9609C8B63,上网时间:2020 年12 月27 日。“‘基地’组织的活动从援助到劝说、恐吓,再到以最恐怖的方式杀人,都是为了恐吓安巴尔部落社会和领袖,迫使他们接受伊斯兰极端思想。 该组织越来越多地针对部落领导人,对他们的商业利益产生影响。”①Gary W. Montgomery and Timothy S. McWilliams, eds., Iraqi Perspectives: From Insurgency to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2004-2009), Quantico: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viii.“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逆行”激起了一些当地部落酋长的担忧,后者开始联手组建“安巴尔拯救委员会”(Anbar Salvation Council)以反抗“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侮辱、暴行、权力攫取以及对部落经济活动的侵犯。②Colin H. Kahl, Brian Katulis, Marc Lynch, “Thinking Strategically About Iraq: Report fromaSymposium,”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5, No. 1, 2008, pp. 82-110.
美军从安巴尔部落遭遇中看到了机会并采取了有效的激励策略。 没有安巴尔部落酋长的支持,伊拉克政府和美军就无法控制“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叛乱活动。③John A. McCary, “The Anbar Awakening: An Alliance of Incentives,” p. 46.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当地部落的支持来扭转该省的乱局成为美军的最大诉求。 成本决定了临时联盟的必要性,与当地人合作可以减少美军的战争成本。④Ivan Diyanov Gospodinov, “The Sunni Tribes of Iraq Tribal Consolidation, Through Turbulent Years 2003-2009,” Academic Dissertation of Leiden University, Academic year: 2014-2015, p. 35.为此,美国几乎完全改变了在当地的重建和安全政策,从主要依靠伊拉克政府和军队转变为巩固、增进被扶植的部落酋长的统治与利益。 美军采取了多种激励策略,激励重点也相应地调整为通过部落而不是通过中央政府来输送援助资金,承认部落的地方治理权。⑤John A. McCary, “The Anbar Awakening: An Alliance of Incentives,” p. 45; Hosham Dawod, “The Sunni Tribes in Iraq: Between Local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nd the Islamic State,” The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re, September 2015, pp. 3-5.这种策略调整的深层原因,是承认部落酋长占据安巴尔权力和社会结构的中心这一现实。
第一,人心激励。 面对叛乱这一非常规战争,“只有使平民认同某种相反的方向,在军事占领中对重建秩序和正常生活给予默许,才能赢回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人心而战的含义”。⑥[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案例恶道德论证》,任献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171 页。美国海军陆战队《反叛乱手册2006》指出:平叛是争取人民支持的斗争,对他们提供保护和福利是发展友好力量的重心,“协助重建当地基础设施、基本服务以及地方治理”是反叛乱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指挥官和士兵被要求学习一些当地的社会结构、部落文化以及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技巧,尽量避免冒犯当地人的尊严。①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2006 (FM 3-24 Counterinsurgency), US Army Manual, Created by General David H. Petraeus and James F. Amos, June 16, 2006, Chapter 1, No. 134; Chapter 3, No. 14-52; Chapter 8, No. 37-45.美军逐渐转向“群众路线”来修复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庇护、市场秩序、民用公共设施和生活资源②David Petraeus, “How We Won in Iraq,”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9, 2013, https:/ /foreignpolicy.com/2013/10/29/how-we-won-in-iraq/,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19 日。,这实际上是与“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安巴尔部落争夺人心的行动。
第二,政治和解激励。 时任伊拉克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彼得雷乌斯极力倡导与伊拉克前叛乱分子和解,并安排专人了解当地情况,与各种力量进行协调和接触。 他指出,“必须以尽可能细致入微的方式来理解反叛乱,无法通过杀戮或俘虏的方式来摆脱大规模叛乱,能够和解的前叛乱分子越多,被杀或被俘的人数就越少。”③Carlotta Gall, “Insurgents in Afghanistan Are Gaining,”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08,https:/ /www.nytimes.com/2008/10/01/world/asia/01petraeus.html,上网时间:2020年3月10日。而美军从当地部落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裂痕中看到了政治和解机会。美军和驻伊拉克大使馆负责人频繁拜访部落领导人,向后者提供各种安全、政治保证,甚至和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一同前往逊尼派部落推动政治和解进程。和解倡议在安巴尔部落逐步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三,容错激励。美军给予部落领导人大量现金资助,任由后者分配,对资金滥用和腐败行为以及走私、抢劫等违法活动也“视而不见”,对部落的不当行为不作过多干涉和纠正,部落领导人因而从中获利颇丰。
第四,项目激励。 美军还将大量战后基础设施重建、废墟清理等项目合同发包给当地部落领导人,并由后者根据自身偏好来分配相关工作机会。④Gary W. Montgomery and Timothy S. McWilliams, eds., Iraqi Perspectives: From Insurgency to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2004-2009), p. 209.在能源项目上,美军允许当地部落酋长从拜伊吉和哈迪塞炼油厂抽取多达20%的份额,部落酋长在这些激励下逐步将叛乱分子逼到了绝境。⑤Michael Schwartz, “It's Still About the Oil”.
第五,权力激励。 美军积极援助并影响被选定的关键部落领导人,帮助后者在部落体系中提升权力地位,使他们更有能力和动力来推进美国的议程。 例如,萨塔尔在安巴尔的部落体系中原先只是一名普通的部落酋长,后来在美军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下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和更高的地位。 相对于当地其他部落领导人,萨塔尔更受美国军方官员的支持与偏爱。⑥Ivan Diyanov Gospodinov, “The Sunni Tribes of Iraq Tribal Consolidation, Through Turbulent Years 2003-2009,” p. 47.
美军因地制宜的激励方法与思路构建了一种契合当地部落权力运作模式和社会文化的激励结构,影响了安巴尔部落酋长的行为,使“关键少数”酋长获得更多的好处,包括经济、能力、凝聚力和个人威望,赋予他们在部落体系内扮演资源再分配的“漏斗”角色,利用后者的权威和资源去引导、诱惑、命令部落成员遵从反叛乱议程或者至少不要站在美国对立面。 一些部落酋长从代理关系中获得经济、安全、威望等诸多好处之后,在安巴尔的部落体系中产生了示范效应,推动了安巴尔部落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决裂进程。
在共同威胁和激励下,安巴尔部落成为美军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代理人。 安巴尔省乃至整个伊拉克越来越多的逊尼派部落受到鼓动,纷纷加入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形成彼得雷乌斯所期待并极力触发的连锁反应——“觉醒运动”。①David Petraeus, “How We Won in Iraq”.驻伊美军上将约翰·克里(John F. Kelly)指出:“安巴尔部落与‘基地’组织联姻,是因为后者带来了忠诚、组织、资金和死亡的意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把极端伊斯兰议程强加于一种普遍世俗的、高度部落化的文化之上,过分夸大了自身影响力,逐渐不再受欢迎。”②Gary W. Montgomery and Timothy S. McWilliams, eds., Iraqi Perspectives: From Insurgency to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2004-2009), p. viii.在拉马迪推动部落“觉醒运动”的美军负责人肖恩·麦克法兰(Sean MacFarland)也指出:“‘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暴行给了我们与拉马迪人民接触的机会……我们已经和城市里的人们建立了真正的关系,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③“DOD News Briefing with Colonel Sean MacFarland from Iraq,” Global Security, July 14, 2006, https:/ /www. globalsecurity. org/military/library/news/2006/07/mil-060714-dod01. htm,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13 日。为赋能和诱导当地部落与“基地”组织作战,美国向部落民兵提供了大量小型武器、薪水、培训等资源,推动反叛乱运动迅速从逊尼派三角区向外传播,约10 万民兵参与其中。④Greg Bruno, “Finding a Place for the ‘Sons of Iraq’,”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3, 2008, https:/ /www.cfr.org/backgrounder/finding-place-sons-iraq,上网时间:2020 年4 月1 日。可以说,安巴尔“觉醒运动”起到了示范效应,成为伊拉克反叛乱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三、 利益分化: 脆弱的代理关系
代理关系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协议上,也不太可能发展出一套管理和运作代理关系的机制,因此它更容易基于利益行事。 一旦发生利益分化或动机错位,代理关系就可能生变。 在反对“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过程中,美军与安巴尔部落就面临这种挑战。
(一) 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动机错位
就当地部落而言,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动机主要源于部落和个人两个层面,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挽回部落传统统治秩序。 安巴尔部落既不是为伊拉克国家前途而战,更非甘愿为美军镇压叛乱而冒险,其动机更多是出于维护传统的部落统治秩序,特别是部落酋长的权威。 在安巴尔部落秩序中,普通成员如果无法从部落获得安全庇护、社会秩序、经济福利等,部落酋长就可能会失去对部落的控制。 而“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行为和策略破坏了以酋长为中心的部落传统,这迫使后者寻求美军的安全援助以消除威胁。
第二,平衡或对抗什叶派势力的压制。 在当地部落看来,相对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短暂威胁,来自什叶派势力的打压和敌意则是持久威胁。 尼尔·罗森(Nir Rosen)教授出席美国国会听证时指出:“美国人认为他们购买了逊尼派的忠诚,但事实上是逊尼派通过收买美国人来争取时间挑战什叶派政府。”①Greg Bruno, “Finding a Place for the ‘Sons of Iraq’”.与美军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其态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它代表逊尼派团体试图借助美军的援助与支持来努力扭转他们的政治边缘化地位,以便美军撤离后可以有效应对什叶派。②John F. Burns and Alissa J. Rubin, “U. S. Arming Sunnis in Iraq to Battle Old Qaeda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1, 2007.
第三,获得个人权威和金钱。 美国通过经济激励对部落酋长施加了巨大影响,酋长们被允许在其部落成员之间自由地分配美国提供的资金,以提高他们在部落内部的地位。③John A. McCary, “The Anbar Awakening: An Alliance of Incentives,” p. 50.“觉醒运动”的创始领导人萨塔尔也被认为“对任何人或任何意识形态都缺乏忠诚,只是为了得到金钱和权力”④Mark Kukis, “Turning Iraq's Tribes Against Al-Qaeda,” Time, December 26, 2006, http:/ /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572796,00.html,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10 日。。 部落民兵也都是受到金钱和个人利益的驱动。⑤“The Awakening: Protectors or Predator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8, https:/ /atwar. blogs. nytimes. com/2008/08/22/the-awakening-protectors-or-predators/,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11 日。此外,部落酋长力图保住非法财源。 几十年来,安巴尔部落酋长一直从走私、抢劫、勒索等犯罪活动中获得可观收益,“伊拉克伊斯兰国”进入当地后强行“分享”脏钱并抢占部落地下“财路”,这无疑减少了酋长的收入,且削弱了后者通过提供经济福利来维系自身统治的能力。
第四,向国家权力体系渗透。 逊尼派部落酋长帮助美军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一个潜在目标是获得更多的安全和政治代表性,希望美国助其融入伊拉克国家治理进程,并将部落力量嵌入并固化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
相对于安巴尔部落,美军则将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议程视为“反恐”和“反叛乱”战略以及维护伊拉克战后和地区秩序的一部分。 在此过程中,美军希望将反叛乱负担转嫁给安巴尔部落。 而后者参与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像是一种短期的应急和谋私利之举,主要受到狭隘的个人利益驱动。 酋长们站在哪一边取决于是否更有利于为部落成员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安全,以及为酋长提供更牢固的地位。①Ivan Diyanov Gospodinov, “The Sunni Tribes of Iraq Tribal Consolidation, Through Turbulent Years 2003-2009,” p. 54可以说,在反叛乱问题上,美军侧重于战略与秩序层面考量,而后者更多是为了保住和扩大部落及个人利益。
(二) 马利基当局的干扰
马利基政府对“觉醒运动”一直十分警惕。 当该运动蔓延到巴格达以及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社区或混合社区附近时,马利基当局担心逊尼派在此过程中乘机壮大政治与安全力量,进而分享更多的国家权力、石油资源并挑战什叶派执政地位。②David Petraeus, “How We Won in Iraq”.马利基一方面担心纵容逊尼派部落将削弱自己在什叶派权力体系中的威望,另一方面还需要顾忌甚至迎合伊朗在伊拉克扶植的政治与安全力量。 这些力量主要包括“巴德尔组织”(Badr Organization)、“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以及一些附属的逊尼派民兵组织,它们都与伊朗保持密切联系并受到后者的影响。③Jack Watling, “Iran's Objectives and Capabilities: Deterrence and Subversio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ebruary 19, 2019, pp. 27-30.可以说,马利基对“觉醒运动”的政策受到伊拉克内部政治安全格局的掣肘,很难做出实质性让步。
第一,马利基政府极力抵消美国的压力。 在伊拉克战后安排方面,美国试图推动地方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和解进程,将实现石油收入共享、对前“复兴党”成员和叛乱分子的宽大处理以及赋予地方政府权力视为伊拉克政治进步的关键指标。④Alissa J. Rubin, “Ending Impasse, Iraq Parliament Backs Measur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08.对于美国来说,有效推动政治和解进程并兑现对逊尼派部落的承诺,意味着需要向马利基政府进行施压。 为巩固“觉醒运动”取得的反叛乱成果,美国一直要求马利基政府通过赦免前复兴党成员和石油收入分配的法案,但后者无意快速落实这两个法案。 随着2008 年“伊拉克伊斯兰国”被基本打垮以及2011 年美军的撤离,马利基的和解意愿进一步减弱。 相反,他着手在政府、议会、安全和情报等关键部门削弱、清洗逊尼派势力和政治对手,全面加强对权力的掌控。①Ali khedery, “Why We Stuck with Maliki and Lost Iraq?,”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4, https:/ /www. washingtonpost. com/opinions/why-we-stuck-with-maliki--and-lost-iraq/2014/07/03/0dd6a8a4-f7ec-11e3-a606-946fd632f9f1_story.html,上网时间:2020 年4 月13 日。马利基政府甚至撕毁了和安巴尔部落首领达成的一项互不侵扰的临时协议。 当美军离开后,马利基便以“支恐”为名指控和逮捕逊尼派高级领导人及骨干成员,解除部落民兵的武装。 2011 年,他指控财政部长兼世俗的、非教派政党联盟(al-Iraqiya List)领导人拉菲·伊萨维(Rafi al-Issawi)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这在伊萨维的家乡安巴尔省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②Harith Hasan Al-Qarawee, “Iraq's Sectarian Crisis: A Legacy of Exclusion,” p. 10.此外,马利基在经济上长期实行排斥政策,拒绝与逊尼派地区分享石油收入。
第二,马利基政府在吸纳部落民兵问题上违背承诺。 如果不能将参与“觉醒运动”的部落民兵永久性地整合到伊拉克安全部队和政府部门任职,他们就有可能重回暴力。③Greg Bruno, “Finding a Place for the ‘Sons of Iraq’”.经过与美方、逊尼派部落的一番讨价还价,马利基政府同意将20%的“觉醒运动”成员纳入伊拉克安全部队,并为其余成员提供非安全工作岗位。 此举又引发了什叶派的疑虑,什叶派人士认为许多逊尼派部落成员的忠诚值得怀疑。 “基地”组织的支持者渗透到伊拉克安全部队,将比“基地”组织本身更加危险。④Solomon Moore, “Attacker Bombs Pro-U. S. Sunnis in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3, 2008, https:/ /www.nytimes.com/2008/01/03/world/middleeast/03iraq.html,上网时间:2020 年4 月29 日。因此,马利基政府在此问题上十分消极,到2009 年只有约9,000 人被编入伊拉克安全部队,30,000 人受雇于其他非安全部门,而大部分参加“觉醒运动”的民兵被抛弃。⑤“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Quarterly Report to the US Congress, April30, 2010, p. 11.马利基政府违反承诺的做法遭到广泛质疑,一位“伊拉克之子”领导人警告:“如果政府不把他们加到工资单上,人们将会非常愤怒……如果有人出钱让他们埋炸弹或袭击美国人,他们可能会回到叛乱”。⑥Brian Glyn William, “Fighting with a Double-Edged Sword?,” in Michael A. Innes, ed., Making Sense of Proxy Wars,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 2012, p. 71; Erica Goode, “Friction Infiltrates Sunni Patrols on Safer Iraqi Street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08; “Securing Baghdad with Militiamen,” BBC News, August 27, 2008; David Unger, “The Foreign Policy Legacy of Barack Obama,” p. 10。 2008 年夏季,美国将“觉醒民兵”改名为“伊拉克之子”,这些部队不是政府安全部队的正式成员,全国10 万名左右“伊拉克之子”中80%左右成员属于逊尼派部落。
第三,由于美国更依赖什叶派主导的权力系统,其不得不容忍和偏袒马利基政府的保守政策。 美国很清楚失衡的教派政策会加剧叛乱和教派暴力,希望伊拉克达成政治和解并过渡到超越教派主义的民主体制,而马利基则进一步强化什叶派中央政府权威,日益倾向于保守的教派政策,致使逊尼派部落成员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机构遭到系统性排斥。 美国选择容忍马利基政府的政策,其希望马利基政府在《驻伊美军地位协议》(U.S.-Iraq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谈判上让步,并担心过度施压后者将更有利于伊朗在伊拉克的渗透。 特别是2011 年美军大规模撤离后,美国需要依赖伊拉克安全部队发挥更大作用。 在此背景下,美国迫使马利基政府为超越教派主义的民主化进程而作出更多改革努力,必然徒劳无功。 而放弃或削弱对安巴尔部落的承诺则可以将美国从教派主义政策的陷阱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调控伊拉克利益格局的灵活空间。
(三) 减少援助: 应对部落的不确定风险
在“伊拉克伊斯兰国”被削弱的过程中,逊尼派部落试图在安全、政治和经济上争取更多的利益。 到2008 年2 月,“伊拉克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数量从12,000 名减少至3,500 名①Greg Bruno, “Finding a Place for the ‘Sons of Iraq’”.,力量被大大削弱,绝大部分势力被驱逐出去,残余势力最终逃窜到西北部的摩苏尔地区。 两年来,伊拉克约有8 万人(其中约80%是逊尼派部落成员)加入到“关注本地居民”(Concerned Local Citizens)等民兵团体。②“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 Report to Congress,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2007, p. 17.此外,“觉醒委员会”遍布安巴尔部落,成为美国军方和部落领导人讨论安全问题和协调行动的平台。 该组织积极鼓励“觉醒”民兵加入到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地方警察队伍,试图通过嵌入到国家安全机构的方式来获得更持久的安全。例如,在2007 年初,部落领袖阿布·阿扎姆(Abu Azzam)希望其部落民兵组织也被承认为当地官方安全部队,并被编入伊拉克政府的工资名录。③Colonel Joel D. Rayburn and Colonel Frank K. Sobchak, The U.S. Army in the Iraq War: Surgeand Withdrawal (2007-2011),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9, p. 174.除了安全力量的积累,逊尼派部落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显著提高,成立了代表部落利益的政党并在安巴尔省议会占据了一席之地。 美国援助的资金使“觉醒委员会”能够吸引更多成员,他们希望重新整合政治秩序,实际上是为了自我保护,也可能为了恢复逊尼派权力。④“Iraq's Provincial Elections: The Stakes,” Middle East Report of Crisis Group, No. 82, January 27, 2009, p. 21.许多“觉醒运动”领导人参加了2009 年1 月的省级选举。 其中,安巴尔省的部落酋长领导的“伊拉克觉醒委员会”(Iraq Awakening Council)在省议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①“The Status and Future of the Awakening Movements,” Arab Reform Bulletin, June, 2009, https:/ /www. washingtoninstitute. org/policy-analysis/view/the-status-and-future-of-the-awakening-movements,上网时间:2020 年4 月13 日。此时,逊尼派部落在安全和政治上获得了更高地位,成为伊拉克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断壮大且具组织化、武装化特点的逊尼派部落抑制了美国的援助意愿。对美军而言,部落代理人力量增强的潜在影响十分微妙。 部落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强化自身偏好,包括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收益,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伊拉克,并把撤军作为实现政治和解的先决条件,激进势力更加坚持武装对抗等。②杨洪林:《浅析伊拉克战后的教派之争》,第30 页。实际上,很难确定壮大且被组织起来的逊尼派部落会不会产生“反冲”作用,特别是当部落的诉求无法实现时,它们可能与美军、中央政府发生冲突,甚至重新转向“基地”组织。 为防范类似的风险,美国的战略是在允许部落民兵保护社区安全的同时限制其进攻能力,阻止其获得重型武器,避免其军事实力超过伊拉克安全部队。③Colin H. Kahl, Brian Katulis and Marc Lynch, “Thinking Strategically About Iraq: Report from a Symposium,” pp. 82-110.2008 年之后,美国以加强伊拉克中央政府权威的名义,逐渐更多地将援助物资转交给伊拉克中央政府,并授权后者进行资源再分配。 实际上,这是美国变相地削减对逊尼派部落的直接援助。
2008 年之前,美国通过发放工资的形式来收买部落成员,“他们觉得这是保护美国士兵安全的最简单方法”,美军每月付给每个“觉醒运动”民兵300 美元。④“The Awakening: Protectors or Predators?”.到2009 年初,美国政府在“觉醒运动”上的总支出接近4 亿美元,平均每个月为部落酋长发包2,100 多万美元的各种项目(包括基建、工资和武器)。⑤“Information on Government of Iraq Contributions to Reconstruction Costs,” SIGIR09-018, Office of the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April 29, 2009, p. 6; Mark Wilbanks and Efraim Karsh, “How the ‘Sons of Iraq’ Stabilized Iraq,”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7, No. 4, 2010, p. 67.这使美军面临着持续增大的激励成本压力。 为减轻负担,美军在目标基本实现后抛弃了这些部落民兵,这导致许多部落民兵被恐怖组织打死,他们没有得到保护,甚至没有工资。⑥Wathek AL-Hashmi, “Tribal Mobilization Forces in Iraq: Reality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Center of Making Policies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 July 12, 2018, https:/ /www.makingpolicies.org/en/posts/tmfi.english.php,上网时间:2020 年5 月14 日。伊拉克最重要的逊尼派政治家之一、议长乌萨马·努贾伊菲(Osama al-Nujaifi)指出:“从2006 年到2008 年,部落成员在美军和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下打败了‘基地’组织。 但之后,这些部落成员有的薪水被削减,有的被暗杀,还有的被迫流离失所,独自面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政府的忽视。”①Tim Arango, Kareem Fahim, “Iraq Again Uses Sunni Tribesmen in Militant War,”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 2014, https:/ /www. nytimes. com/2014/01/20/world/middleeast/iraqagain-uses-sunni-tribesmen-in-militant-war.html,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3 日。很难想象在没有金钱激励和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安巴尔部落会长期留在与美国合作的轨道内。 美军提供必要的资源来保持与安巴尔部落合作的弹性,但如果“派人去打击恐怖分子,却没有慷慨的资金,结果将是可悲的”②Carter Malkasian, “Anbar's Illusions: The Failure of Iraq's Success Story,” Foreign Affairs, June 24, 2017, https:/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q/2017-06-24/anbars-illusions, 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10 日。。
在“伊拉克伊斯兰国”被削弱后,美军不愿意向代理人价值下降的安巴尔部落支付长期激励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后者就像需要被甩掉的“负资产”。 一旦当地部落无法获得来自美军持续的、可信的正面激励,美军试图继续依赖当地部落来解决麻烦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部落只有在符合他们自身最大利益的情况下,才会继续合作。③John A. McCary, “The Anbar Awakening: An Alliance of Incentives,” p. 51.
四、 信息不对称: 无效的监督
代理人天然拥有私人信息优势,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委托方无法知晓的事情,这对代理人战争的运作构成持久挑战。 因此,委托方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压缩“信息差”。 在镇压“伊拉克伊斯兰国”叛乱过程中,美军非常依赖安巴尔部落提供当地情报,这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第一,从当地部落获得情报信息成为美军反叛乱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准确和及时的情报对于反叛乱至关重要,从街头巷尾发现、识别出叛乱分子是美军开展行动的基础。 但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叛乱分子一直在争取当地人的支持和庇护,拥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他们藏匿在人群中很难被美军识别,这是情报工作中的难点。
美军自身无法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美军的情报资源投入和整合存在问题。 国会对情报相关预算的阻碍导致无人机和侦察机等设备严重不足,分析和翻译人员缺乏,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军队官僚主义等因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军获取情报的能力。①[美]罗伯特·盖茨:《责任:国防部长回忆录》,第125-132 页。二是缺乏当地专业知识的支撑,美军无法了解叛乱分子的身份信息、社会网络、组织运作方式等关键情报。 三是收集情报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建立新的地面情报网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金成本,效率和准确性也难以保证。 同时,美军也不具备从当地收集情报的合法性身份。 因此,美军不得不转而寻求当地部落的配合以更为有效地获取情报信息。 “如果设法与逊尼派部落合作和协调,美国将能够获得更多有针对性的战斗行动所需的实地信息,特别是在它不愿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下。”②Raed El-Hamed, “The Challenges of Mobilizing Sunni Tribes in Iraq,”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17, 2015, https:/ /carnegieendowment. org/sada/59401,上网时间:2020 年4 月16 日。彼得雷乌斯认为,反叛乱行动受到情报驱动,它依赖于美军对当地形势的深刻理解和动态掌握,还需要从当地人的支持中获得识别和击败叛乱分子所需的情报,这为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来识别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起到重要作用。③David Petraeus, “How We Won in Iraq,”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2006, Chapter 1, No. 134-136.实际上,在安巴尔“觉醒运动”之前,美军就着手在部落中安插眼线,收买当地社区的负责人,希望后者为其提供情报。④William Knarr, “Al-Sahawa: An Awakening in Al Qaim,” Combating Terrorism Exchange, No. 2, 2013, p. 20.
第二,部落代理人具备私人信息优势。 一般来说,当地人具有身份合法性和当地知识优势,能更好地借助社区联系来收集情报,而不用担心刺激民族主义情绪。⑤Danniel Byman, “Approximating War,” pp. 14-19.当地部落代理人熟悉语言、文化、地形、社会网络,能够及时、全面、真实地掌握安巴尔省情况和动向,为美军识别、清理安巴尔省的叛乱分子提供珍贵的情报信息。 拉马迪的一位部落酋长指出,“联军具有很强的军事能力,而平民和部落拥有联军所没有的优势:他们是当地人,他们发现并知道谁来自外面,他们知道谁是叛乱分子,谁是‘基地’组织。 毫不夸张地说,在两个月内一切(识别任务)都完成了。”⑥Max Boot, “More News from Ramadi,” Commentary, July 17, 2007, http:/ /www.commentarymagazine.com/contentions/index.php/boot/657,上网时间:2020 年4 月23 日。
第三,授权链的复杂化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美军与安巴尔部落成员之间存在间接、非正式的授权链,从美军的偏好到当地部落的执行之间存在复杂的传导过程。 总体上看,其主要由两条“主链”(美军内部的“授权—控制”链和部落内部的“授权—控制”链)来衔接。 与此同时,两条“主链”各自内部又存在不同运作方式的 “次链”。 “主链”与“次链”交错发挥作用,共同将代理关系变成十分复杂的网络状结构,授权、控制环节的复杂化以及决策、执行末端的距离被拉开。 这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存在损耗、延时、扭曲等问题,最终身处其中的每个“节点”所掌握的信息并不一样。
部落酋长在“授权—控制”链中占据关键位置。 他们不但垄断了物质利益的接收和分配权力,还把控了信息收集、传递的过程,这使得美军对其监督异常困难。 首先,部落酋长不希望其从事的走私等非法活动遭到美军的严格监督。 与此同时,部落酋长在援助资金分配和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腐败和造假行为,他们也不希望此类信息被美军掌握。 其次,为避免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受损,一些部落酋长需要顾及其内部成员的反美情绪而拉开与美军的距离并努力抵制后者的监督,这是保持“政治正确”的一种策略。 例如,阿尔·高德(Al-Gaoud)酋长所在的部落大多数成员与叛乱组织、“基地”组织存在交易,而与美国的关系削弱了其在部落中的地位。 2005 年他在伊拉克议会选举中失利,2007 年6 月被暗杀。2007 年9 月,安巴尔“觉醒运动”领导人萨塔尔因高调地与小布什总统会面而被炸死在家中。 再次,在一些极端情形下,美军甚至与当地部落酋长共谋,呈现给上级监督部门一个经过编辑的事实,达到联手削弱监督的目的。 例如,有美方官员与部落酋长勾结,损毁或者伪造经费收支文件,滥用、贪污来自美国的援助资金、项目建设经费。①A. Madhani, “U.S. Troops, Contracto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Suspected of Corruption,” ABC News, June 20, 2010, http:/ /www.abcnews.go.com/Politics/us-troops-charged-corruption-iraqafghanistan/story?id=10952163,上网时间:2020 年5 月18 日。最后,“道德陷阱”削弱了美军对当地部落的监督。 美军必须依赖安巴尔部落代理人来获取信息,并需要支付某种“信息租金”,这是反叛乱战争成功的基础。 但代理人为了获得可持续的信息租金(未来收益),更有动力懈怠而不是努力表现。 这意味着,信息租金可能会削弱委托方试图使代理人发挥高水平的努力。②Robert Powell, “Why Some Persistent Problems Persi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3, No. 4, 2019, p. 982.为尽可能延长这种潜在收益,部落酋长在反叛乱议程上就有了卸责和偏离动机,部落可以操纵信息,只有当他们获得更大的收益时,才向美军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第四,部落还可以将信息不对称优势转化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杠杆。 部落酋长在一定程度上遵从美国反击“伊拉克伊斯兰国”与推动和解进程的偏好,以此换取美国的援助和庇护。 与此同时,他们又利用美国投入的资源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来谋求其他利益,如追求更高的政治与安全地位来对抗什叶派势力,防止在伊拉克的权力和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 显然,安巴尔部落所承载的基于教派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反抗并不契合美国对伊拉克战后秩序的设想。
从理论上讲,要确保部落酋长严格服从美国的偏好,美军就需要严格限制前者的行动范围并密切监督他们的遵守情况。 但是,美军与安巴尔部落民兵组织之间存在比较复杂的、间接的、非正式的“授权—指挥—控制”链,这使得信息的传递存在诸多损耗。 加之信息依赖、道德陷阱等原因使得美军压缩“信息差”的监督努力更加困难,不完整、不及时、不真实的信息就成为当地部落酋长谋求自主权空间的杠杆。
五、 偏好异质: 不受控制的裂变
在代理人战争研究领域,代理人内部的结构往往容易遭到忽视,但这却是影响代理人战争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代理人内部是一种“碎片化”的结构,期待它们为同一个议程而采取集体行动将变得不切实际。 相反,一些不受控制的力量单元将挑战委托方的管理能力,扰乱代理关系的稳定。 安巴尔部落是一个偏好异质的代理人集体,如何约束它们的全部行为成为美军的棘手挑战。
安巴尔部落内部存在多重分裂,是一个偏好异质的团体。 2006 年夏季开始的安巴尔“觉醒运动”暂时将当地部落成员和一些前叛乱分子拉回到反抗“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阵营,在外部威胁和援助的刺激下部落间可以形成短暂的、策略性的松散联合,但这不意味着这一联盟就是铁板一块。 参与“觉醒运动”的部落团体十分庞杂,它们的表现和偏好并不完全受到一个更高的权威和统一的议程影响、约束,实际上,安巴尔部落内部呈现出“沿着势力范围、意识形态、部族为基础的分裂”①Steven N. Simon, “After the Surge: The Case for U. S.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Iraq,” p. 5; “Iraq's Provincial Elections: The Stakes,” p. 21; “Prospects for Iraq's Stability: Some Security Progress but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Elusive,”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August 2007, p. 2, https:/ /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Press%20Releases/2007%20Press%20Releases/20070823_release.pdf,上网时间:2020 年5 月12 日。。 到2008 年夏季,随着反叛乱议程进入尾声,不同部落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 事实上没有一个权威可以代表逊尼派社区的整体利益或偏好,其凝聚力越来越多地被内部权力斗争所消耗。②Colin H.Kahl, Brian Katulis and Marc Lynch, “Thinking Strategically About Iraq: Report From a Symposium,” pp. 82-110.部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助长了制度的脆弱,使其软弱无力、无法控制部落领导人的势力和权力范围之外的活动,这在逊尼派的安巴尔省、萨拉丁省和尼尼微省都很明显。①Wathek AL-Hashmi, “Tribal Mobilization Forces in Iraq: Reality and Future Challenges”.在安巴尔,不同部落酋长之间因为有些部落与“伊拉克伊斯兰党”(Iraq Islamic Part/ IIP)结成联盟而产生分歧与对抗。②“Iraq's Provincial Elections: The Stakes,” pp. 30-31.当地部落领导人为了追求私利,其行为并不一定受到美国的偏好约束。
在遭到美国抛弃后,部落领导人对威胁来源的认知存在分歧,更难执行目标一致的代理议程。 安巴尔部落中有很多人认为马利基政府是伊朗的代理人,比“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危险。 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 )部落领导人阿布·阿扎姆表示,“比美国的占领更危险的是来自邻国伊朗的占领……不是媒体所描述的‘基地’组织,而是伊朗及其代理人。”③“Abu Azzam Interviewed on al-Arabiya,”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No. 1675, January 18, 2008, https:/ /www. memri. org/tv/former-terrorist-islamic-army-iraq-abu-azzamal-tamimi-american-withdrawal-will-spell-disaster/transcript,上网时间:2020 年5 月1 日。“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一些不满现状的逊尼派部落受到叙利亚叛乱运动的鼓舞,承揽了从海湾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极端伊斯兰组织走私武器的生意,进一步加大了对伊拉克什叶派中央政府的反抗,而这被正当化为更广泛地对抗伊朗地区影响力一部分。
此后,部落内部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方面的分歧更大。 即使美国后来仍试图诱导逊尼派部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但后者内部的偏好异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方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另一方是与“伊斯兰国”作战的人,还有一方是中立派。④Raed El-Hamed, “The Challenges of Mobilizing Sunni Tribes in Iraq”.安巴尔省的安全形势很复杂,不同的逊尼派部落之间乃至单个部落内部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和政策存在冲突。 与2006 年发生的情况相反,当时安巴尔的所有部落团结起来与“基地”组织作斗争,部分原因是因为后者的许多战士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或更远的地方,而此次很多“伊斯兰国”战士就来源于伊拉克部落内部。 在一段时间内,“选边站”的分歧变成了部落间的冲突,有些部落愿意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有些部落酋长站在政府一边,但其成员却暗中加入“伊斯兰国”;有些部落采取中立策略,但其内部存在分裂。⑤Mustafa Habib, “Iraq's Tribes Not United on Extremists - and Bloody Tribal Justice Will Likely Prevail,” Niqash, November 2014, https:/ /www.niqash.org/en/articles/security/3573/,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12 日。例如,2013 年当马利基政府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为名派兵进入安巴尔省时,遭到许多部落领袖的抵制,这实际上为“伊斯兰国”提供了庇护。 2014 年1 月,经过多年的准备和发展,“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继任者“伊斯兰国”占领了安巴尔省的大部分地区。而那些曾经发起、组织“觉醒运动”的当地部落由于分裂和孤立而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①Carter Malkasian, “Anbar's Illusions: The Failure of Iraq's Success Story”.
偏好异质的部落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渗透提供了便利。 美国和马利基政府在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后期不仅没有兑现和解承诺,还利用教派安全化和民主化改造等一系列措施防范部落势力渗透到国家政治、安全和油气部门,这进一步加深了部落内部在威胁认知上的分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感到越来越被边缘化、被抛弃而变得更激进。 2011 年美军不负责任地撤离后,“‘伊拉克伊斯兰国’很快就从军事真空中获益,其中一个原因是该组织受到的军事压力减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马利基在美军撤离后朝着独裁方向大步前进,加紧疏远和削弱逊尼派,温和逊尼派开始转而支持‘伊拉克伊斯兰国’。”②[美]迈克尔·莫雷尔、比尔·哈洛:《不完美的风暴: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30 年》,朱邦芹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版,第340 页。可以说,美国和马利基政府对安巴尔部落的背叛和打压进一步助长了部落中偏好异质问题,加深了极端主义的吸引力,这为极端组织提供了渗透的理想环境。 “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又开始回流到安巴尔省,它们从被抛弃的愤怒部落成员那里再次获得了庇护和资源。 “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新领导人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利用部落的不满情绪,组织、号召激进部落分子走上街头并重获影响力。 正是由于部落存在广泛的分歧,熟悉部落文化且具有丰富当地经验的“伊斯兰国”组织利用这一点在部落间和部落内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拉拢、分化不同的部落和关键部落领导人,并取得了成功。③Hassan Hassan, “ISIS Exploits Tribal Fault Lines to Control Its Territory,” The Guardian, October 26, 2014, https:/ /www. theguardian. com/world/2014/oct/26/isis-exploits-tribal-fault-linesto-control-its-territory-jihadi,上网时间:2020 年6 月11 日。可以说,美国短视的代理人策略对此后的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造成灾难性影响,“基地”组织在伊拉克部落区重新复燃、壮大,为“伊斯兰国”的坐大埋下了隐患。
总之,逊尼派部落参与“觉醒运动”的团体十分庞杂,它们的表现和偏好并不完全受到一个更高权威和统一议程的约束,其内部的分歧难以弥合,无法为特定的议程采取集体行动。 特别是当“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威胁被解除后,它们原本就存在的偏好异质问题就更加难以抑制,部分力量单元更是倾向于对抗美国扶植什叶派当局的努力。 偏好异质的部落不但难以受到美国管控,还成为极端力量发展壮大的温床。
六、 结语
总体来看,美军与安巴尔部落代理人的动机、利益存在错位,双方的合作带有阶段性的、策略性的色彩,并没有形成以高度稳固的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代理关系。 虽然来自“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威胁为美军与安巴尔逊尼派部落达成临时性的代理关系提供了契机,但它是建立在物质激励基础上的,这种仅仅靠一个共同的敌人和短期利益来维系的合作过于脆弱。 随着反叛乱行动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利益分化加剧并导致它们的交易面临多种挑战。 美军对部落代理人采取了削减援助和更加偏袒马利基政府的负向激励,导致后者遭到抛弃和边缘化。 安巴尔部落无法从美军那里获得持续的好处,这种预期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和安巴尔部落的偏好异质问题,致使逊尼派部落无法共同努力推进美国的议程。美国与安巴尔部落联手取得的反叛乱成绩只是表面的、临时的。 其代理关系背后的暗流涌动一直在侵蚀双方的信任基础,最终导致安巴尔部落反美浪潮回流和“伊斯兰国”崛起。 美国之前的投入和双方取得的成果随之化为乌有。
2014 年当美国试图重启“安巴尔觉醒”模式来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时,“逊尼派部落仍然记得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对‘觉醒运动’的影响”,这使得当地部落担心在完成任务后“被抛弃”的一幕会重演。①Raed El-Hamed, “The Challenges of Mobilizing Sunni Tribes in Iraq”.对此,安巴尔部落首领阿布·里沙(Ahmed Bezaa Abu Risha)批评美国与伊拉克政府忽视了“觉醒”民兵组织,既没有给民兵发工资,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武器,因此“我们有义务保卫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省,而不是为美国或伊拉克政府而战,我们不想被指责为政府工作。”②Tim Arango and Kareem Fahim, “Iraq Again Uses Sunni Tribesmen in Militant War”; Ali AbelSadah, “Sunni Iraqi Leaders Accused Of Supporting Terrorism,” Al-Monitor, August 31, 2013, https:/ /www. al-monitor. com/pulse/originals/2013/03/tensions-rise-iraq-sunnis.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0 日。很显然,当地部落试图与美国拉开距离,以便更好地保全自己。
美军的安巴尔代理人战争表明,“如果干预要起作用,它将永远是一项代价高昂的长期项目,而且可能只有通过长期的投入才能维持下去”③Carter Malkasian, “Anbar's Illusions: The Failure of Iraq's Success Story”.。 同时,安巴尔的案例也反映出代理人战争的长期性和不确定后果,以及美军与安巴尔当地部落之间复杂的双向博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