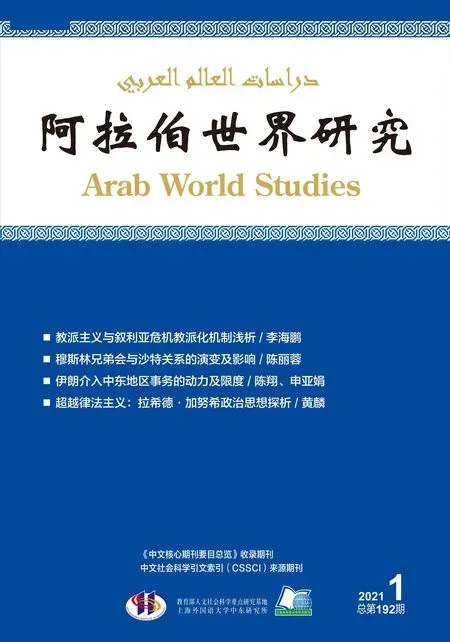多维视角下的阿塞拜疆什叶派问题∗
李福泉 张雅梅
阿塞拜疆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地区,民族和宗教构成比较单一①阿塞拜疆总人口为1,010 万,阿塞拜疆族的人口占比达91.6%。 参见《阿塞拜疆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20 年10 月)》,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 /www. fmprc. gov. 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84/1206x0_676286/,上网时间:2020 年12 月1 日。,是当今世界什叶派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的四个国家之一。②除阿塞拜疆以外,什叶派在伊朗(90%)、巴林(75%)、伊拉克(65%)也占人口多数,在黎巴嫩(45%)、科威特(30%)、巴基斯坦(20%)、阿富汗(19%)、沙特(10%)等国家也有一定分布。参见Vali Nasr, “When the Shiites Rise,”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4, 2006, p. 58。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穆斯林占阿塞拜疆总人口的99.2%,其中65%~75%属于什叶派,其余为逊尼派。③Pew Research Center,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Washington, D. C.: Pew Research Center, 2019, p. 10.近十几年来,伊斯兰教派矛盾激化是中东地区的突出现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塞拜疆两大教派关系比较融洽,彼此从未发生过严重冲突。 不仅如此,阿塞拜疆什叶派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教派政治动员,政治化水平远远低于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什叶派。 在教派政治备受关注的背景下,阿塞拜疆的什叶派问题呈现出不同于中东国家的显著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时至今日,国内虽然有不少论著探讨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的什叶派④主要著作包括王宇洁:《伊朗伊斯兰教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程彤:《“正统”观念与伊朗什叶派:从旭烈兀到阿巴斯一世之间的伊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版;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但对阿塞拜疆什叶派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鉴于此,本文将以阿塞拜疆什叶派的历史演进、独立以来阿塞拜疆的宗教政策、什叶派政治化历程以及阿什叶派与伊朗关系等多个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以深化对什叶派问题多样性的认识。
一、 阿塞拜疆什叶派的历史演进
阿塞拜疆什叶派的现实处境和政治特征是其独特的历史传统作用的结果。什叶派在阿塞拜疆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16 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宣布什叶派为国教加速了什叶派在阿塞拜疆的传播,最终基本上完成了阿塞拜疆人的什叶派化。
(一) 阿塞拜疆的什叶派化
公元639 年阿拉伯军队占领阿塞拜疆南部地区后,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当地。①目前,阿塞拜疆人主要分布在伊朗和阿塞拜疆,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人约为2,041 万,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5%;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阿塞拜疆人约为1,010 万。 参见《伊朗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20 年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72/1206x0_677174/,上网时间:2020 年12 月1 日。至8 世纪后期,伊斯兰教开始取代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等宗教,成为整个阿塞拜疆地区的主体宗教。 9 世纪前半期,阿塞拜疆人巴贝克(Babik)发动起义,反对逊尼派阿拔斯王朝。 他将什叶派与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进行融合,无意中推动了什叶派在当地的发展。 在塞尔柱王朝时期(1037 年~1194 年),什叶派由于遭受打压,采用了塔基亚原则②依据“塔基亚”原则,什叶派在遭遇危险时,可以隐藏或否认自身的信仰。,使其在阿塞拜疆地区得以延续。 与此同时,多个突厥部落进入阿塞拜疆,开启了阿塞拜疆地区的突厥化过程。 1309 年,伊尔汗国国王完者都(Oljaytu,1304 年~1316 年在位)公开皈依什叶派,成为推动该教派在阿塞拜疆发展的有力因素。 14 世纪后期,统治阿塞拜疆地区的黑羊王朝(1375年~1468 年)尊奉什叶派为国教,促使不少阿塞拜疆人改信什叶派。 但直到15世纪末,逊尼派依然是阿塞拜疆地区的主导性教派。
1501 年,伊朗萨法维王朝(1501 年~1722 年)创建者伊斯玛仪一世宣布什叶派中的主流支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这成为阿塞拜疆人什叶派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事件。 什叶派的国教化赋予伊朗境内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共同的教派认同。 作为王朝合法性的关键来源,什叶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伊斯玛仪一世等国王依靠国家机器,大力推行什叶派伊斯兰教。 他们从伊拉克、黎巴嫩和巴林等地大批引进什叶派乌里玛,进行了一场什叶派信仰的普及运动。 乌里玛撰写宣教著作,充任法官或者清真寺领拜人,成为推行什叶派的中坚力量。 在1722 年萨法维王朝灭亡之时,什叶派教义已经成为大多数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的宗教信仰。③Said Amir Arjomand, The Shadow of God and the Hidden Imam: Religion, Political Order, and Societal Change in Shi'ite Ir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189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191.阿塞拜疆人由此成为诸突厥语族民族中唯一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占据多数的民族,而这一什叶派化的过程也促进了阿塞拜疆人认同的形成。④Brenda Shaffer, Borders and Brethren: Iran and the Challenge of Azerbaijani Identit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pp. 19-20.阿夫沙尔王朝(1736 年~1796 年)建立后,国王纳迪尔汗打压什叶派伊斯兰教,但这并没有改变什叶派在包括阿塞拜疆地区在内的整个伊朗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事实。 18 世纪末期恺加王朝(1796 年~1925 年)建立后,依然以什叶派为国教,保证了这一教派在伊朗的稳定发展。
(二) 沙俄的征服和阿塞拜疆什叶派世俗化的开启
从历史角度来看,沙俄的征服对一个半世纪以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政教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地缘位置而言,阿塞拜疆处于伊朗伊斯兰文明和沙俄东正教文明的交界地带,沙俄征服的直接结果是阿塞拜疆北部地区长期脱离了伊朗的政治控制,并被纳入东正教文明的影响范围。 自此以后,虽然穆斯林在俄属阿塞拜疆一直是绝对多数,但东正教文明的政治原则和世俗观念逐渐在当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19 世纪初期,在经历沙俄和伊朗的两次战争①两次战争分别发生在1804 年至1813 年和1826 年至1828 年。后,历史上的阿塞拜疆地区以阿拉克斯河(Araxes river)为界分为两个部分:南部继续处于伊朗的统治之下,北部则被沙俄侵占,后来成为阿塞拜疆共和国。 在俄属阿塞拜疆,什叶派起初并不享有明显优势。 19 世纪30 年代,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比例大致相当。 后来由于逊尼派大量向奥斯曼帝国迁移,至1860 年这一比例转变为二比一。②Tadeusz Swietochowski, Russian Azerbaijan, 1905 - 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就地域分布而言,逊尼派主要在俄属阿塞拜疆的北部地区,什叶派则大多分布于巴库和邻近伊朗的南部地区。
沙俄对阿塞拜疆穆斯林采取了以控制为主的政策。 为隔绝伊朗对阿塞拜疆什叶派的影响,沙俄当局禁止阿塞拜疆年轻人前往伊朗求学,也禁止在伊朗受过教育的人在阿塞拜疆任宗教职位。 对阿塞拜疆穆斯林进行统一管理是沙俄的基本目标。 1823 年,沙俄设立了“伊斯兰谢赫”(Sheikh al-Islam)的职位,以代表该地全体穆斯林。 1872 年,两个独立的“外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Transcaucasian Muslim Board)成立,分别管理阿塞拜疆的什叶派和逊尼派。 此外,什叶派的阿舒拉节等宗教活动也遭到禁止。 沙俄的政策使阿塞拜疆的宗教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20 世纪初期,阿塞拜疆只有23 名什叶派法官和16 名逊尼派法官,③Anar Valiyev, “Azerbaijan: Islam in a Post-Soviet Republic,”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 No. 4, 2005, p. 3.宗教人才非常匮乏。
沙俄的统治客观上给阿塞拜疆带来了现代教育和世俗思想,使当地穆斯林走上了不同于伊朗穆斯林的发展道路。 阿塞拜疆人更多地与沙俄国内的穆斯林联系在一起,深受欧洲世俗文化的影响。①祖力甫哈尔·哈力克、黄民兴:《当代伊朗阿塞拜疆人国家认同探讨》,载《世界民族》2015 年第3 期,第26 页。当地现代民族主义者引入世俗学校和出版社等现代事物,改变了阿塞拜疆的面貌。 鉴于阿塞拜疆人由逊尼派和什叶派构成的现实,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将泛伊斯兰主义作为认同的基石,而是以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跨越分歧的桥梁和民族构建的工具。②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Washington, D. 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2006, pp. 19-20.在反对沙俄统治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传统宗教学者则被边缘化。 1918年,民族主义者宣布阿塞拜疆独立,使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世俗共和国。 开国元勋们决定在这个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制,规定妇女拥有选举权,试图建立一个面向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 阿塞拜疆共和国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却为1991 年阿塞拜疆再次独立后政教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三) 苏联时期阿塞拜疆什叶派世俗化的深化
1920 年苏联红军占领阿塞拜疆使得当地什叶派进入了深度世俗化的新阶段。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世俗主义在阿塞拜疆的发展从内部和外部都获得了推动力。 在外部,新生国家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为同样是突厥语族民族的阿塞拜疆人树立了榜样;在内部,苏联在阿塞拜疆实行强制性的政教分离政策,禁止宗教人士以任何形式参与政治活动。
苏联推行世俗化和俄罗斯化并行的措施,限制了宗教的影响力。 1929 年,阿塞拜疆语由原本的阿拉伯字母变为拉丁字母,1939 年又被改为西里尔字母。③Lala Aliyeva, “Mutual Influence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Processes: In the Case of Azerbaijan,”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view, Vol. 2, No. 4, 2013, p. 339.这一变化使阿塞拜疆青年一代难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新的宗教著作更容易受到政府的监管。 政府在全社会推行大规模的无神论教育,关闭处理家庭和宗教事务的传统法庭。 赴麦加的朝觐活动几乎停止,礼拜和斋戒等其他宗教功课极少有人遵行。 清真寺丧失了宗教教育的功能,阿塞拜疆人对伊斯兰教普遍缺乏了解,有的甚至一无所知。 宗教学者数量锐减,且处于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 1991 年阿塞拜疆独立之际,全国只有16 个人接受过宗教教育,他们全部在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任职。④Nijat Mammadli, “Islam and Youth in Azerbaijan,” Baku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https:/ /bakuresearchinstitute.org/islam-and-youth-in-azerbaijan/,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3 日。
苏维埃政府还禁止什叶派阿舒拉节宗教游行活动,关闭了大量清真寺。 在并入苏联之前,阿塞拜疆有2,000 座清真寺。 1929 年,阿塞拜疆共有960 座什叶派清真寺和400 座逊尼派清真寺。 到1933 年,只剩17 座清真寺,其中逊尼派清真寺2 座,什叶派清真寺11 座,混合清真寺4 座。 首都巴库只有两座大清真寺和5 座小清真寺在开放。 二战期间,宗教政策趋于宽松,部分清真寺重新开放,曾停止活动的外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在1944 年恢复活动。 到苏联末期,阿塞拜疆共有清真寺200 座,其中包括未经登记的礼拜场所。①数据参见Anar Valiyev, “Azerbaijan: Islam in a Post-Soviet Republic,”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 No. 4, 2005, p. 4。
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世俗化政策下,伊斯兰教在政治、法律和教育等领域处于边缘地位,宗教生活的主要形式为什叶派游访圣墓。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阿塞拜疆什叶派的复兴。 什叶派葬礼变得普遍,什叶派穆斯林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频率也明显增加。 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宗教在阿塞拜疆人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地位,伊斯兰教只是阿塞拜疆穆斯林身份认同的次要来源,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从长期来看,自1828 年沙俄完全占领阿塞拜疆开始,俄罗斯人长达160 年的统治不仅给当地留下了世俗主义的遗产,也使什叶派和逊尼派因强大的外部压力增强了民族认同,淡化了教派意识。 这成为后冷战时代阿塞拜疆教派关系和睦的历史远因。
二、 1991 年独立以来阿塞拜疆宗教政策的演变
对于穆斯林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阿塞拜疆而言,宗教政策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1991 年独立以来,在保持世俗化基调的前提下,阿塞拜疆的宗教政策大致经历了温和规范、严格管控和局部调整三个时期。 这种政策对于什叶派在阿塞拜疆的处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 温和规范时期(1991 年~2000 年)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在阿塞拜疆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虽然宗教人士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民族主义者处于支配地位。 1991 年10 月阿塞拜疆宣布独立后,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是社会的普遍共识。 伊斯兰问题在阿塞拜疆政府的议程上处于次要地位,世俗民族主义是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的首要凝聚力量。 作为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阿塞拜疆继承了苏联时期关于政教分离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遗产。 但与此同时,在脱离苏联后,阿塞拜疆穆斯林陷入了一定的认同危机,许多人被压制的宗教意识开始复苏,伊斯兰教在民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复兴。 部分妇女开始穿戴宗教服饰,少数人对于执行伊斯兰教法持积极态度。①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 13.在此情况下,阿塞拜疆由苏联时期的强制型世俗化向温和型世俗化转变,政府不再大力推行无神论教育。
1992 年6 月,埃尔奇贝(Abulfaz Elchibey)成为阿塞拜疆第一位民选总统。作为“阿塞拜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of Azerbaijan)的领袖,他实行亲西方外交,奉行土耳其版本的世俗民族主义,反对宗教干预政治。 同年8 月,埃尔奇贝总统签署了阿塞拜疆历史上唯一一部《宗教自由法》。 该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赋予信徒选择、实践、改信和传播宗教的自由以及加入宗教团体和建立宗教教育机构的权利。②Law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On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December 4, 2015, https:/ /adsdatabase. ohchr. org/IssueLibrary/AZERBAIJAN_Law%20On%20Freedom%20of%20Religious%20Belief.pdf,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29 日。这些条文反映了后苏联时期阿塞拜疆民众对信教自由的诉求,但其缺乏必要规范的弊端日益显露。
1993 年10 月,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当选总统,阿塞拜疆由此进入了延续至今的阿利耶夫家族世代。 盖达尔·阿利耶夫在2003 年10 月卸任总统后,其子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当选,并连任至今。 阿利耶夫父子都曾受苏联时期的无神论教育,都是坚定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也都反对宗教干预政治。 他们不否认自身的穆斯林身份,但并不严格履行礼拜和斋戒等宗教功课。 他们的教育经历和政治理念给阿塞拜疆的政教关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规范和利用并举是盖达尔·阿利耶夫总统早期宗教政策的基本特点。 1995年11 月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正式确立了阿塞拜疆政教关系的基本框架。 宪法序言和第7 条明确了世俗主义的原则;第18 条规定宗教与国家分离,教育制度具有世俗性,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传播和宣传侮辱人的尊严和违背人性原则的宗教;第48 条规定任何宗教仪式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宗教信仰不能作为违反法律的借口;第89 条规定在宗教组织任职的人不能担任国会议员。③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March 18, 2009, https:/ /www. wipo. int/edocs/lexdocs/laws/en/az/az057en.pdf,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8 日。和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同,阿塞拜疆宪法没有规定任何宗教或教派为国教,这就从制度层面消除了宗教或教派歧视的隐患。 政府保留苏联时期的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对全国宗教进行管理。 高加索穆斯林委员由什叶派宗教学者帕沙扎戴(Allahshukur Pashazade)①据称,帕沙扎戴是全球唯一可以同时发布逊尼派法特瓦和什叶派法特瓦的宗教学者。 参见Milikh Yevdayev, “Azerbaijan: A Country of Unusual Shia-Sunni Harmony,” Jewish Journal, May 19, 2016, https:/ /jewishjournal.com/israel/185602/, 上网时间:2020 年11 月8 日。任主席,一位逊尼派宗教学者任副主席,其职责为任命教职人员,监管清真寺的宣讲词,组织穆斯林到麦加朝觐。
与此同时,面对国内严峻的挑战,盖达尔·阿利耶夫总统力图借助宗教界的支持稳固政权。 他鼓励举办伊斯兰教会议,在宗教节日时拜访清真寺。 1994 年,他成为现代阿塞拜疆第一位到麦加朝觐的政治领袖。 作为回报,宗教界积极配合总统,公开支持他的各项政策。 阿塞拜疆总体上呈现出政府与宗教界和谐共处的局面,但是宗教领域也出现一些混乱现象。 1991 年之后,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国宣教者的活动在阿塞拜疆几乎不受监督,严重影响了阿国内的宗教生态,进而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面对这种局面,1996 年阿塞拜疆政府对《宗教自由法》进行了修订,以限制外国人的宣教活动,加强对宗教团体的管理。20 世纪90 年代后期成为阿塞拜疆政教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
(二) 严格管控时期(2000 年~2012 年)
在国内外形势的作用下,2001 年成为阿塞拜疆政教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伴随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权力的巩固,严格管控成为政府宗教政策的显著特点。“9·11”事件发生后,阿塞拜疆政府将防止宗教渗透和打击极端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并以反恐的名义强化对宗教的控制。 同年,总统下令在内阁之下组建国家宗教组织工作委员会(The State Committee for Work with Religious Organizations),专门负责全国宗教社团的登记工作。 按规定,凡没有登记的宗教社团,都不得在阿塞拜疆活动。 这使政府掌握了判定全国宗教团体和活动是否合法的权力,拒绝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社团面临解散的压力,未获登记成为政府关闭清真寺的理由。 2004 年3 月,阿塞拜疆警方以没有登记为由,关闭了巴库最重要的聚礼清真寺。②Jean Christophe Peuch, “Azerbaijan: Authorities in Baku Target Shi'a Mosque, Say It Is Being Illegally Occupied,” Payvand, April 3, 2004, http:/ / www. payvand. com/news/04/mar/1019.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8 日。此外,该委员会在监管宗教文献的出版、发行、进口和传播方面也拥有广泛权力。 2005 年,它禁止了92 本被视为宣扬“政治伊斯兰”的宗教书籍。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zerbaijan: Independent Islam and the State,” Europe Report, No. 191, March 25, 2008, p. 17.限制外国宗教影响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2001 年,据称与黎巴嫩真主党有联系的6 名公民在阿塞拜疆南部和伊朗边界附近被逮捕。①Anar Valiyev, “Azerbaijan: Islam in a Post-Soviet Republic,”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 No. 4, 2005, p. 8.2002 年,政府关闭了国内22 所由伊朗资助建立的宗教学校,②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 44.召回了在伊朗留学的本国学生。 2007 年5月,政府禁止全国清真寺通过扩音喇叭传送唤礼词。 由于宗教界反应强烈,几天之后政府废除了该禁令,但其在一些清真寺仍然有效。 由于新成立的国家宗教组织工作委员会与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在权责方面出现矛盾,阿塞拜疆国家安全部开始介入宗教管理,监控清真寺和宗教组织,逮捕被认定的宗教危险分子,成为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发展的主要机构。
阿塞拜疆政府还把修订法律作为推进世俗化的有效手段。 2009 年,《宪法》和《宗教自由法》的修订版以及其他法律大幅度增加了对宗教活动和社团的限制。 在国外接受宗教教育的人被禁止在国内担任宗教职务,所有宗教社团被要求在2010 年1 月之前按新的条件重新登记。 国家宗教组织工作委员会有权将非法生产、分发和进口宗教文献定为刑事犯罪,对有关罪行的处罚包括对初犯处以6,329 美元至8,860 美元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监禁,多次违法者将被处以8,860 美元至11,392 美元的罚款或2 年至5 年监禁。③“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http:/ /www.state.gov/j/drl/rls/irf/2010/148912.htm,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8 日。此外,政府下令从国家建筑中剔除所有宗教标志,从互联网网站、电视节目中删除宗教歌曲。④Audrey L. Altstadt, Frustrated Democracy in Post-Soviet Azerbaija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re Press, 2017, p. 205.前往麦加朝觐名额从6,000 人削减至2,000 人,朝觐只能由“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统一组织,私人公司不得参与。 依据新法律,政府拆毁了部分未登记的清真寺。 2010 年12月,教育部禁止所有女学生在公立学校戴头巾,这使世俗化政策的推行达到了高潮。 此后,头巾成为伊斯兰组织和政府矛盾的焦点。
(三) 局部调整时期(2013 年至今)
进入21 世纪以来,日益严厉的限制性措施导致阿塞拜疆政府与穆斯林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阿塞拜疆伊斯兰教界逐渐形成官方和民间两个界限日益清晰的部分。 阿塞拜疆政府试图通过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和国家宗教工作委员会实现对全国穆斯林的有效管控,使伊斯兰教服务于社会稳定,而不是成为反对政府的力量。 但是,政府的多项举措被穆斯林认为破坏了伊斯兰教传统,伤害了部分阿塞拜疆人的宗教情感,官方伊斯兰教界由此日益丧失了表达穆斯林民意的能力。 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被认为是腐败的机构,根本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在调查中只有4%的人信任该组织主席。①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 64.民间伊斯兰教界得到广泛支持,对官方伊斯兰教界形成了挑战。 对于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而言,民间伊斯兰教和官方伊斯兰教的疏离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影响到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问题。 因此,修正宗教政策,强化与民间伊斯兰教的沟通,就成为总统审时度势之后的必然选择。
2013 年,阿塞拜疆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改善与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的关系。为此,国家宗教组织工作委员会在首都巴库和其他地区组织了圆桌会议和公开讲座,其中包括为期两天的“国家宗教关系与启蒙工作”(State-Religion Relations and Enlightenment Work)会议。②Ansgar Jödicke, “Shia Groups and Iranian Religious Influence in Azerbaijan: The Impact of Trans-boundary Religious Ties on National Religious Polic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8, No. 5, 2017, p. 544.2014 年,总统签署了三项向阿塞拜疆宗教组织提供财政援助的命令,此后国内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各宗教社团多次获得来自总统的财政援助。 总统还为促进宗教文化宽容以及宗教和文化间对话拨款。 同年,政府出资建成了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它以前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的名字命名。 每周五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在此一起进行聚礼,以此作为和平、包容和团结的象征。③Ilia Brondz1 and Tahmina Aslanova, “Sunni-Shia Issue in Azerbaijan,” Voice of the Publisher, Vol. 5, No. 1, 2019, pp. 8-9.
2015 年4 月,总统与全家人前往麦加朝觐,以公开的方式显示自身的穆斯林身份。 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意在拉近与国内穆斯林大众的心理距离。 同年,政府向宗教文化发展基金拨款,还提供资金用于修复国内的宗教历史文化古迹。2016 年,阿塞拜疆将该年确定为本国的“多元文化年”,④Aynur Karimova, “Azerbaijan Declares 2016 Year of Multiculturalism,” Azernews, January 11, 2016, https:/ /www.azernews.az/nation/91533.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8 日。以推进阿塞拜疆的多元文化建设。 2017 年,总统宣布当年为“伊斯兰团结年”,并为相关活动拨款。 当年4 月,议会修改了《宗教自由法》,放松了对国民接受国外宗教教育的限制。 按规定,如果获得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和国家宗教组织工作委员会的许可,在国外接受宗教教育的阿塞拜疆公民可以在国内主持宗教仪式和活动。⑤Altay Goyushov and Kanan Rovshanoglu, “A History of Political Shiism in Post-Soviet Azerbaijan,” Baku Research Institute, 2019, https:/ /bakuresearchinstitute.org/, 上网时间:2020 年3月8 日。但在政府向宗教团体示好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宗教活动的监管。 在此期间,多名宗教领导人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被逮捕和判处监禁。 与此同时,除学校之外,政府也开始禁止戴头巾的嘉宾在电视节目中出现。 宗教力量不得影响公共生活和政治稳定是阿塞拜疆政府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 阿塞拜疆什叶派的政治化
从历史上看,阿塞拜疆政府总体上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核心的宗教政策。阿塞拜疆独立后的历任总统都是穆斯林,但都没有明确的教派归属。 作为深受世俗思想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们都主张阿塞拜疆必须实行政教分离。①Sofie Bedford, “Oppositional Islam in Azerbaijan,” Caucasus Analytical Digest, No. 44, November 20, 2012, p.10.在政府推行世俗主义的背景下,国家和民族认同在阿塞拜疆穆斯林中占据主导地位,宗教或教派并不是阿塞拜疆政治划界的优先标准。 依据2011 年巴库研究所的调查,阿塞拜疆人优先认同的对象依次是国家、民族、宗教和地区(出生地)。②Nijat Mammadli, “Islam and Youth in Azerbaijan”.主导阿塞拜疆政坛的是新阿塞拜疆党和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等世俗民族主义政党,它们都具有跨教派的特征,不单独代表某个教派的利益。 对于阿塞拜疆什叶派而言,宗教成为实现教派政治化的唯一手段。 虽然什叶派融入了阿塞拜疆社会,但政府并没有在什叶派中完全实现宗教的去政治化。 1991 年以来,部分什叶派以宗教为旗帜进行自我组织和动员,在阿塞拜疆发出自己的声音。 总体而言,阿塞拜疆什叶派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典型形式,一是巴库聚礼清真寺社团的温和政治参与,二是纳达兰村的激进政治抗争。
(一) 聚礼清真寺社团的政治参与
聚礼清真寺社团的形成和发展是阿塞拜疆什叶派知识分子表达自身诉求的结果。 位于首都巴库的聚礼清真寺始建于公元8 世纪,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1992 年,在宗教复兴的背景下,易卜拉希莫格鲁(Ilgar Ibrahimoglu)等人以聚礼清真寺为中心,组建了穆斯林社团,并在司法部获得了登记。 它成为20 世纪90 年代阿塞拜疆最具影响力的什叶派社团,在该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的穆斯林曾多达3,000 人。③Audrey L. Altstadt, Frustrated Democracy in Post-Soviet Azerbaijan, p. 197.该社团建立了两个非政府组织,一个是旨在捍卫信仰权利的“保护良知和宗教自由中心”(Centr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n),另一个是呼吁宗教宽容和跨宗教对话的“伊斯兰伊提哈德协会”(Islam Ittihad Society)。
聚礼清真寺领拜人易卜拉希莫格鲁曾在1992 年至1996 年就读于伊朗加兹温大学,受到伊朗宗教思想的影响,后来又在波兰接受了人权方面的培训。 他的思想呈现出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特征,反对暴力斗争,也不愿对抗政府,主张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实现目标;他大量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擅于用西方的人权观念反对阿塞拜疆政府对什叶派的控制;他主张推进公民社会建设,要求保护包括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 他的追随者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会好几门外语。 他通过聚礼清真寺社团,传播经过现代阐释的什叶派伊斯兰教。 这迎合了城市穆斯林的需求,提高了他们的宗教知识水平。 该社团拒绝接受官方伊斯兰组织的控制,不愿意按照1996 年的《宗教自由法》重新登记,也不承认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主席帕沙扎戴的宗教权威。
聚礼清真寺最初主要从事宣传活动,在2001 年政府加强对宗教的控制后,它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2003 年以来,聚礼清真寺社团在大多数选举中一直支持反对派政党,并参加了反对政府操纵选票的抗议活动。 阿塞拜疆政府认为,聚礼清真寺的活动创造了宗教政治化的危险先例,对世俗政治体系构成了威胁。①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 58.同年12 月,政府逮捕了易卜拉希莫格鲁,指控他利用宗教参与政治。 被关押4 个月后,他被判处5 年的缓期徒刑。 易卜拉希莫格鲁继续批评阿塞拜疆的人权状况,指责政府参与伊拉克战争。 2004 年3 月,政府关闭了聚礼清真寺。 约3,000 名穆斯林上街示威,反对政府将社团人员逐出清真寺,阿塞拜疆政治反对派和国际社会也严厉批评阿塞拜疆政府的驱逐行动。②Ansgar Jödicke, “Shia Groups and Iranian Religious Influence in Azerbaijan: The Impact of Trans-boundary Religious Ties on National Religious Policy,” p. 547.在2005 年12 月的议会选举中,易卜拉希莫格鲁公开与反对派阿扎德利克集团(Azadliq bloc)联合③Sofie Bedford, “Oppositional Islam in Azerbaijan,” Caucasus Analytical Digest, Vol. 44, 2012,p. 9.,作为反对党候选人参加竞选。 2006 年以来,易卜拉希莫格鲁多次要求阿塞拜疆政府从伊拉克撤回军队。 2010 年12 月9 日,当教育部长宣布在公立学校禁止女生戴头巾后,聚礼清真寺社团参与了什叶派的抗议活动。④这一天是什叶派重要宗教节日阿舒拉节的前一天,政府的举措被认为是对什叶派的故意挑衅。总体而言,在2004 年之后,聚礼清真寺社团由于无法在清真寺集体活动,其影响已无法与以前相比。 近年来,网络成为其开展宣传的重要平台,易卜拉希莫格鲁的“脸书”账号受到大量穆斯林的关注。
(二) 纳达兰村的激进政治抗争
纳达兰(Nardaran)村是位于首都巴库北部25 公里处的一个什叶派村庄。1991 年以来,该村是全国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地方,与高度世俗化的首都巴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村内有13 个什叶派圣墓,街道两边常年悬挂宗教旗帜,大部分妇女在公共场所穿伊朗式黑袍,猪肉和酒精在村内遭到禁止,伊朗领袖哈梅内伊是最受欢迎的宗教学者。①Altay Goyushov and Kanan Rovshanoglu, “A History of Political Shiism in Post-Soviet Azerbaijan,” Baku Research Institute, 2019, https:/ /bakuresearchinstitute.org/, 上网时间:2020 年3月8 日。苏联时期,该村曾是花卉和蔬菜市场。 苏联解体后,由于基础设施崩溃和天然气供应停顿等原因,90%的居民一度处于失业状态②N. Antelava, “Azeri Poverty Fuels Rise of Islam,” BBC News, November 6, 2005, https:/ /islamawareness.net/Asia/Azerbaijan/, 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1 日。,村子里由此积聚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正是在纳达兰村经济和宗教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阿塞拜疆伊斯兰党在此诞生。 该党是阿塞拜疆最重要的宗教政党,1991年11 月由阿里·阿克拉姆(Ali Akram)在纳达兰村建立,次年在政府获得登记,被认为“在阿塞拜疆宗教政治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③Vahram Ter-Matevosyan and Nelli Minasyan, “Praying Under Restrictions: Islam,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Azerbaija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9, Issue 5, 2017, p. 12.。 纳达兰村是伊斯兰党活动的主要基地。 与聚礼清真寺社团不同,伊斯兰党领导层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只有中学学历。 阿里·阿克拉姆曾长期从事卡车装载和食品店店员的工作,缺乏宗教方面的专业知识。 也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党缺乏吸引高学历精英人士的能力。
伊斯兰党是阿塞拜疆最主要的亲伊朗组织,其思想主张深受伊朗影响。 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主张与伊朗建立紧密的联系。 它认为伊斯兰教是阿塞拜疆的唯一基础,只有国家领导人接受伊斯兰教价值观,阿塞拜疆才能摆脱危机。 它抵制西方价值观,反对美国、以色列和土耳其,拒绝泛突厥主义。 该党宣称,伊斯兰世界真正的敌人是以色列主导的共济会。 伊斯兰党建立后,很快便拥有6 万党员,在全国65 个城镇开设了办公室。④Murad Ismayilov, “Islamic Radicalism that Never Was: Islamic Discours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Elite's Quest for Legitimation. Azerbaijan in Focu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 10, No. 2, 2019, p. 185.该党还出版《伊斯兰之声》(Voice of Islam)和《伊斯兰世界》(Islam World)两份报纸,在全国宣扬自己的思想。
伊斯兰党激进的意识形态使其成为政府打击的重点对象。 1995 年,阿塞拜疆政府以伊斯兰党企图发动政变为由,注销了该党。 1996 年,政府逮捕了阿里·阿克拉姆等三位该党领导人。 2001 年,在宗教政策收紧后,伊斯兰党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张。 2002 年6 月,伊斯兰党组织纳达兰村村民走上街头,高喊宗教口号,抗议社会经济状况。 在和警察的冲突中,阿里·阿克拉姆等40 人被逮捕,1名村民死亡。 政府指责伊朗代理人煽动抗议,谴责村民非法获得武器对付安全力量,但这遭到了坚决否认。 在2003 年的总统选举中,纳达兰村99%的人投票支持反对派候选人。①Julie Wilhelmsen, “Islamism in Azerbaijan: How Pot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2, No. 8, 2009, p. 730.2006 年1 月,伊斯兰党发起的抗议活动又造成3 人死亡。政府的行为加剧了纳达兰村的不满。
2007 年7 月,莫萨姆·萨梅多夫(Movsum Samedov)当选为伊斯兰党新任主席②2002 年,阿里·阿克拉姆辞去党主席职务后,由阿加·努里(Agha Nouri)接任。 莫萨姆·萨梅多夫是一名医生,1993 年加入伊斯兰党,1996 年至1997 年曾在库姆学习。,他起初回避对现政权的直接批评,仅限于发表反西方言论和谴责阿塞拜疆与以色列的联系。 但2009 年以来他逐渐激进化,频频利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发起抗议活动。 2010 年12 月,伊斯兰党与其他反对党联合抗议女学生不得戴头巾的禁令。③Sayed Abbasov, “Azerbaijan: Hijab Ban in Schools Fuels Debate in Baku on Role of Islam,” Eurasianet, January 6, 2011, https:/ /eurasianet.org/, 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1 日。2011 年1 月2 日,萨梅多夫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禁止女孩戴头巾上学,谴责官员腐败和政府限制言论自由。 他把总统阿利耶夫和下令杀死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的叶齐德(Yazid)④叶齐德是伍麦叶(倭马亚)王朝第二任哈里发。相提并论,呼吁人民推翻“这一专制政权”。⑤萨梅多夫宣称:“伊力哈姆·阿利耶夫把父亲当作偶像,强迫人们崇拜他。 但阿塞拜疆的大多数人是穆斯林,他们必须站起来反对这个无情的政权,结束这个酷似叶齐德的人的统治”。 参见“Islamic Party Activists' Trial Starts in Azerbaijan,” Radio Liberty, August 4, 2011, http:/ /www.rferl.org/content/azerbaijan_islamic_party_activists_trial/24287231.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1 日。这是阿塞拜疆历史上什叶派领导人第一次发出推翻现政权的号召。 萨梅多夫随即被捕,在2011 年10 月被冠以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罪名,判处12 年监禁。⑥Murad Ismayilov, “Islamic Radicalism That Never Was: Islamic Discours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Elite's Quest for Legitimation. Azerbaijan in Focus,” p. 188.
同年,塔勒·巴吉扎德(Taleh Bagirzade)⑦2005 年至2010 年和2010 年至2011 年,巴吉扎德先后在伊朗库姆和伊拉克纳杰夫学习宗教。成为阿塞拜疆什叶派新兴领导人。 2011 年5 月,他因参加反对头巾禁令的抗议活动而在纳达兰村被捕。 此后,他多次被捕,其政治态度也从批评政府限制宗教自由升级为反对现政权。 2015年1 月,他创建了旨在促进伊斯兰团结的穆斯林统一运动(Muslim Unity Movement),成员大部分为纳达兰村居民。①Galib Bashirov, “Islamic Discourses in Azerbaijan: The Securitization of ‘Non-traditional Religious Movement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7, No. 1, 2018, p. 36.2015 年11 月,警方以支持恐怖主义、策划政变、非法持有枪支和杀人等罪名在纳达兰村逮捕了塔勒·巴吉扎德等17 人,并造成包括2 名警察在内的6 人死亡。②Mike Runey, “Azerbaijan: Show Trial Ends with Harsh Sentences for Islamic Activists,” EurasiaNet, January 26, 2017, https:/ /www.ecoi.net/de/dokument/1394784.html, 上网时间:2020年3 月1 日。这成为1991 年以来什叶派与政府最严重的冲突事件。 2017 年1 月,塔勒·巴吉扎德被判处20 年监禁,其他16人也被判处10 年至20 年的监禁。③“Taleh Bagirzade Receives 20 Years and Fuad Gahramanli 10 Years in Jail,” The Institute for Reporters' Freedom and Safety, January 25, 2017, https:/ /www.irfs.org/news-feed/, 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1 日。绝大多数什叶派反政府骨干力量丧失了自由,纳达兰村自此进入了平静期。
2.2.2 饮食指导,指导患者多饮水,禁烟酒,少吃含亚硝酸盐的食物,例如:香肠、腊肉多摄入高纤维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营养均衡。
总之,独立近30 年以来,阿塞拜疆什叶派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经历了逐步政治化的过程。 巴库聚礼清真寺社团代表了大都市新式知识阶层的意愿,而纳达兰村则是来自农村的社会中下层激进抗议的典型。 二者的多名领导人都有在伊朗留学的经历,且都对政府提出了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诉求,其中纳达兰村出现了与政府的小规模暴力对抗。 但时至今日,阿塞拜疆什叶派参与反政府活动的人数比较有限,他们也缺乏有广泛群众性基础的政治组织。 政治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教派政治的动员效力也比较有限。
四、 伊朗对阿塞拜疆什叶派的影响
1991 年以来,外部伊斯兰教的输入和传播是阿塞拜疆宗教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主要来自土耳其、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三大源头。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在语言和种族方面比较接近,它通过政府和非政府两个渠道在阿塞拜疆开展宗教活动,主要针对的是受过较多教育的逊尼派穆斯林,宣传的内容局限于文化伊斯兰教,阿塞拜疆政府对其的管理相对宽松。 沙特和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则积极支持萨拉菲主义(Salafism)在阿塞拜疆北部逊尼派地区和首都巴库传播,被阿塞拜疆政府视为首要的宗教威胁。④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p. 47-49.伊朗既是阿塞拜疆的邻国和最大的什叶派国家,又拥有数量最多的阿塞拜疆人,具有影响阿塞拜疆什叶派的地理、教派和民族优势。 但与此同时,伊朗对阿塞拜疆什叶派的影响远远无法与其对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什叶派的影响相提并论。
(一) 伊朗影响阿塞拜疆什叶派的方式
1979 年以来,伊朗把西亚地区的什叶派作为输出革命的主要对象。 在20 世纪80 年代,由于苏联的强力控制,伊朗难以在阿塞拜疆开展活动。 阿塞拜疆独立初期国家能力的孱弱为伊朗提供了机遇,而伴随民众宗教意识的复苏,阿塞拜疆国内也产生了对宗教知识的较大需求。 在此情况下,伊朗试图在阿塞拜疆施加影响,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 与此同时,在20 世纪90 年代,伊朗将阿塞拜疆独立后明确把世俗民族主义作为立国基础的做法视为对其领土完整的潜在威胁,伊朗政府担心本国的阿塞拜疆人会在阿塞拜疆国家的刺激下产生民族独立的情绪。 因此,向阿塞拜疆传播什叶派伊斯兰教,也是伊朗以宗教对抗阿塞拜疆世俗民族主义的重要措施。 总体而言,伊朗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影响阿塞拜疆什叶派。
第一,借助各类官方背景的伊斯兰组织机构在阿塞拜疆开展活动。 政府与具有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紧密配合是伊朗对外宣传的重要特点。 在伊朗驻阿塞拜疆大使馆的支持下,伊朗伊斯兰文化指导部下属机构文化和伊斯兰联络组织(Organization of Culture and Islamic Relations)在该国积极推进波斯语教学,宣传什叶派伊斯兰教。 伊玛目霍梅尼援助委员会(Imam Khomeini Relief Committee)自1993 年以来就在阿塞拜疆活动,截至2001 年阿政府强化管控之前,在该国设有415 个分支机构。 它除了为难民①难民是由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而产生,最多时达150万。 参见Svante E. Cornell,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London and New York: Curzon Press, 2005, p. 47。提供服务外,还大量分发宗教书籍和霍梅尼的图片。②Ansgar Jödicke, “Shia Groups and Iranian Religious Influence in Azerbaijan: The Impact of Trans-boundary Religious Ties on National Religious Policy,” p. 539.此外,伊斯兰宣教组织(The Islamic Propaganda Organization)、朝觐与福利组织(The Hajj and Welfare Organization)和伊斯兰教派和解协会(The Society for Reconciliation among Islamic Sects)也是伊朗在阿塞拜疆传播伊斯兰教和展现伊朗软实力的重要力量,这三个组织都听命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其国外宗教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③Eva Rakel, “Paradigms of Iranian Policy in Central Eurasia and Beyond,”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Vol. 2, Issue 3-4, 2003, p. 556.
第二,大力传播伊朗版本的什叶派伊斯兰教。 伊朗政府对阿塞拜疆境内亲伊朗乌里玛的宣教活动进行资金和意识形态支持,经常派遣乌里玛参加阿塞拜疆南部什叶派聚居区的宗教活动。 伊朗电视台向阿塞拜疆南部发射电视信号,宣传什叶派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革命思想和反西方思想。①Huseynov Rashad, “Combatting Global Threat of Religious Radicalization: Hard-line and Soft-line Measures,” Chorzowskie Studia Polityczne, No. 8, 2014, p. 77.伊朗政府还派出人员在阿塞拜疆建立宗教学校,直接在当地培养宗教人才,最多时其数量达30 所。学校里不仅教授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还散发赞扬伊朗及其政权的资料。②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 44.伊朗政府相关机构把霍梅尼等人的著作翻译成阿塞拜疆语和俄语,在阿塞拜疆的宗教用品商店出售。 它们还将什叶派文章、视频和音频传到网络上,供阿塞拜疆年轻一代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 在宗教节日期间,伊朗以资金支持亲伊阿塞拜疆民间宗教人士为穷人提供免费食物,以此彰显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人道精神。此外,伊朗政府还利用每年阿塞拜疆穆斯林前往马什哈德和库姆等什叶派圣城朝拜的机会进行宗教宣传。
第三,吸引和支持阿塞拜疆穆斯林到伊朗接受宗教教育。 1979 年以来,伊朗把宗教教育作为传播伊斯兰革命思想的主要方式。 阿塞拜疆独立之初宗教人才十分匮乏,全国只有七八十位领拜人。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zerbaijan: Independent Islam and the State, Europe Report, No. 191, March 25, 2008, p. 7.而且,阿塞拜疆国内也无法为什叶派穆斯林提供高级宗教教育,伊拉克和伊朗成为阿塞拜疆什叶派年轻人学习宗教的主要选择。 伊朗的圣裔协会和多位大阿亚图拉向阿塞拜疆年轻人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到库姆等城市学习宗教。 2009 年成立的穆斯塔法国际伊斯兰大学向全球穆斯林提供免费的宗教教育④See Mehdi Khalaji, “Balancing Authority and Autonomy: The Shiite Clergy Post-Khamenei,”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37, October 2016, p. 5.,对部分阿塞拜疆什叶派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易卜拉希莫格鲁、莫萨姆·萨梅多夫和塔勒·巴吉扎德等多位阿塞拜疆什叶派领导人都有在伊朗学习的经历,他们成为伊朗在阿塞拜疆扩展影响的重要载体。⑤在伊朗学习的阿塞拜疆学生缺乏准确统计数字。 2003 年,仅在库姆就有200 名阿塞拜疆学生。 参见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44。
第四,公开声援阿塞拜疆什叶派。 关心国外穆斯林的处境是1979 年以来伊朗外交的重要内容。 当阿塞拜疆出现抗议活动时,伊朗多次公开支持什叶派,批评阿政府的行为。 2010 年12 月,阿塞拜疆政府颁布头巾禁令的举动受到伊朗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阿亚图拉马卡雷姆·设拉兹(Makarem Shirazi)公开谴责巴库禁止头巾的做法是“反伊斯兰的”,认为它是对“伊斯兰神圣价值观的挑战”,呼吁阿塞拜疆人民“和平抵制这一决定”,而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的一些居民则在阿塞拜疆领事馆门前抗议,宣称“阿利耶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①Shahin Abbasov, “Azerbaijan: Hijab Ban in Schools Fuels Debate in Baku on Role of Islam,” Eurasianet, January 6, 2011, https:/ /eurasianet.org/, 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4 日。伊朗的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自身与阿塞拜疆什叶派的联系,但也引发了阿塞拜疆政府的不满。
(二) 伊朗影响阿塞拜疆什叶派的限度
伊朗通过以上多种方式对阿塞拜疆什叶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伊朗的宣传下,部分阿塞拜疆什叶派穆斯林开始积极履行宗教功课,把伊朗作为宗教实践的标准②2005 年,阿塞拜疆官方宣布,当年的开斋节在12 月3 日,这一时间和世界上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一样,然而伊朗却宣布开斋节时间应在12 月4 日,于是阿塞拜疆南部什叶派比国内其他穆斯林多斋戒一天,在12 月4 日庆祝节日。 参见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 45。,伊斯兰党甚至接受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的思想,主张在阿塞拜疆建立伊斯兰国家。 但总体而言,伊朗行动的效果差强人意。
20 世纪90 年代,在世俗民族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双重作用下,阿塞拜疆政府确定了亲土耳其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 阿塞拜疆是在伊斯兰世界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①阿塞拜疆曾在“9·11”事件后主动提供本国领空和机场供美军使用,还在2003 年后向伊拉克派驻150 人的军队以示对美国的支持。 虽然许多阿塞拜疆人不满美国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偏袒”亚美尼亚和2003 年美国“侵略”伊拉克,但阿塞拜疆政府一如既往地奉行亲美政策。 参见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p. 26-34。阿领导人力图投入西方阵营,以获得经济和外交支持。 美国盟友以色列甚至是和阿塞拜疆关系最好的国家之一。 在穆斯林国家中,阿塞拜疆政府青睐同为突厥语民族的土耳其,视其为发展的榜样,阿塞拜疆的许多教室甚至悬挂着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画像。②Jennifer Solveig Wistrand, “Azerbaijan and ‘Tolerant Muslims’,” Caucasus Analytical Digest, No. 44, November 20, 2012, p. 6.与此相反,阿塞拜疆领导人普遍对伊朗缺乏好感。 相邻的地理位置以及共同的民族和教派纽带不仅没有拉近两国的关系,反而使得阿塞拜疆对伊朗充满了警惕。 阿塞拜疆领导人不认同伊朗的政治模式,把其在国内的宣教活动视为渗透和威胁。 两国在里海划分等问题上的矛盾加剧了阿塞拜疆对伊朗的不信任。 因此,在保持两国正常关系的前提下,限制伊朗在国内的影响是阿塞拜疆政府的基本政策。③Rufat Ahmadzada, “Growing Iranian Influence in Azerbaijan: What Should be Done,”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11, 2019, https:/ /blogs.timesofisrael.com/, 上网时间:2020 年3 月11 日。
早在1993 年~1994 年,阿塞拜疆政府就驱逐了境内的大部分伊朗宗教人士。④Julie Wilhelmsen, “Islamism in Azerbaijan: How Potent?,” p. 731.1997 年,盖达尔·阿利耶夫总统发布命令,禁止外国人在阿塞拜疆进行宣教活动。 随后,《宗教自由法》的附加条款规定,只有在国内接受过教育的阿塞拜疆人才能主持宗教仪式和活动。 2000 年,阿政府进一步驱逐了所有的伊朗宣教者。2001 年,阿政府关闭了伊朗支持建立的22 座宗教学校,认为它们在削弱学生们的国家认同。 国家宗教组织工作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宣称:“我们之所以关闭它们,是因为它们在传播伊朗政权的思想。 学校里的教师在设法让孩子们忘记对阿塞拜疆祖国的热爱。”⑤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zerbaijan: Independent Islam and the State, p. 8.此后,伊朗向阿塞拜疆输入资金和意识形态的难度大大增加。
一方面,阿塞拜疆政府严厉打击在伊朗接受过宗教教育的人在国内活动,多名有此经历的什叶派领导人被逮捕和判处多年监禁。 政府官员还多次公开批评伊朗对阿塞拜疆的“干涉行为”。 2011 年5 月,当人们抗议头巾禁令时,阿塞拜疆前外交部长声称,“伊朗正试图利用伊斯兰教增加其在阿塞拜疆的影响力,它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这样做的机会。 我完全相信伊朗正在挑起这一问题,并激起人们对头巾禁令的抗议”⑥Murad Ismayilov, “Islamic Radicalism that Never Was: Islamic Discours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Elite's Quest for Legitimation. Azerbaijan in Focus,” p. 188.。 由于阿塞拜疆政府的压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思想很大程度上被隔离,在伊朗接受过宗教教育的人难以产生强大的宗教影响。 阿塞拜疆什叶派与伊朗的宗教交往依然存在,但被置于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①2015 年8 月,伊朗重要宗教学者努里·哈马达尼(Nuri Hamadani)应高加索穆斯林委员会主席邀请访问阿塞拜疆。 2016 年12 月,高加索穆斯林索委员会主席帕沙扎戴访问伊朗,会见多位阿亚图拉。
另一方面,阿塞拜疆什叶派普遍缺乏对伊朗的亲近感。 对大多数阿塞拜疆人来说,伊斯兰教首先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的传统,他们认同的对象主要是文化和民族,而不是宗教或教派。 2012 年在阿塞拜疆的一项调查显示,针对“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宗教或教派”的问题,85%的人选择伊斯兰教,10%的人选择什叶派,4%的人选择逊尼派,剩余的1%选择其他宗教。②“Opinion Poll: Religiosi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Religion,” Caucasus Analytical Digest, No. 44, November 20, 2012, p. 6.大部分阿塞拜疆人只是名义上的穆斯林,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在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③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p. 21-22.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宗教在阿塞拜疆虽有复兴,但其缺乏深度和广度,远未动摇世俗主义的根基。 “阿塞拜疆人是伊斯兰国家中最不重视宗教仪式和斋戒的人,巴库仍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世俗的地方。”④Arzu Geybulla, “Azerbaijan: Ruling in Bad Faith,” Open Democracy, October 20, 2015, https:/ /www.opendemocracy.net/en/odr/azerbaijan-ruling-in-bad-faith/, 上网时间:2020 年8 月23 日。据200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3.6%的阿塞拜疆人从来不礼拜,13.2%的人偶尔礼拜。⑤H. Hajizade, “Religion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in Azerbaijan After September 11,” III Era,No. 6, 2005, p. 38.而到2013 年,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仪式的人只有5.6%。⑥Nijat Mammadli, “Islam and Youth in Azerbaijan”.阿塞拜疆什叶派自视为“宽容的穆斯林”,绝大多数人拒绝将宗教与政治相结合,他们不欢迎伊朗的政治模式,反感伊朗以宗教约束人行为的做法。⑦1992 年6 月,霍梅尼之女莫斯塔法维(Zahra Mostafavi)访问阿塞拜疆时,虽然天气酷热,但依然身穿黑袍,当地妇女对此极为惊讶并表示无法理解。 参见Nairi Tohidi, “The Global-Local Intersection of Feminism in Muslim Societies: The Cases of Iran and Azerbaijan,” Social Research, Vol. 69, No. 3, 2002, pp. 853-854。即便是什叶派中宗教情感比较强烈的穆斯林也试图保持对伊朗的独立性。 20 世纪90 年代,阿塞拜疆南部的什叶派乌里玛曾坚决抵制伊朗在当地传播激进思想。⑧Farideh Heyat, “New Veiling in Azerbaijan: Gender and Globalized Islam,”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 15, No. 4, 2008, pp. 364-365.总之,虽然什叶派在阿塞拜疆的比例很高,但与黎巴嫩什叶派不同,他们的这种身份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宗教观点和交往意愿,什叶派大国伊朗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五、 结语
自19 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悠久的世俗化传统使得阿塞拜疆在独立之后也一直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治精英借助世俗民族主义塑造了阿塞拜疆人独立的身份认同。 阿塞拜疆政府一方面强化对宗教的管理,坚决反对宗教干预政治;另一方面实践宗教平等的原则,倡导伊斯兰教的团结和统一,不支持或打压某个宗教或教派。 阿塞拜疆大体上实现了对什叶派的有效整合,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总之,什叶派问题并非阿塞拜疆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阿塞拜疆什叶派与政府的矛盾主要在世俗领域,什叶派不满政府腐败和发展经济不力。 总体而言,双方的矛盾是可控的,远未达到对抗的程度。 虽然什叶派中出现了以宗教进行政治动员的反政府现象,但政治伊斯兰的大规模发展仍缺乏必要的动力和土壤。 伊斯兰党作为唯一的什叶派宗教政党,无法聚合全国什叶派力量,不能对政府形成足够的威胁。①有学者认为,阿塞拜疆政府在有意夸大国内伊斯兰力量的威胁,以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参见Murad Ismayilov, “Islamic Radicalism that Never Was: Islamic Discours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Elite's Quest for Legitimation. Azerbaijan in Focus,” pp. 183-196。以伊朗模式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方案在阿塞拜疆什叶派中严重缺乏共鸣,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②Svante E. Cornell,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 in Azerbaijan, p. 26.渗透世俗精神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以及宗教人员对国家的从属关系共同阻止了阿塞拜疆什叶派的普遍激进化,和平发展始终是其主流趋势。 就教派关系而言,和谐共处依然是阿塞拜疆的基本特征,什叶派和逊尼派在现代阿塞拜疆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冲突事件。 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2012 年的调查显示,阿塞拜疆只有2%的人认为教派矛盾是个问题,这与其他许多穆斯林国家形成了强烈反差。③作为对比,持相同观点的被访者比例在伊朗是23%,在阿富汗是44%,在伊拉克是52%,黎巴嫩是67%。 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 “Many Sunnis and Shias Worry About Religious Conflict,”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7, 2013, http:/ /www. pewforum. org/2013/11/07/many-sunnis-and-shias-worry-about-religious-conflict/, 上网时间:2020 年2 月23 日。由此可见,弱政治化和弱教派认同将是阿塞拜疆什叶派的长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