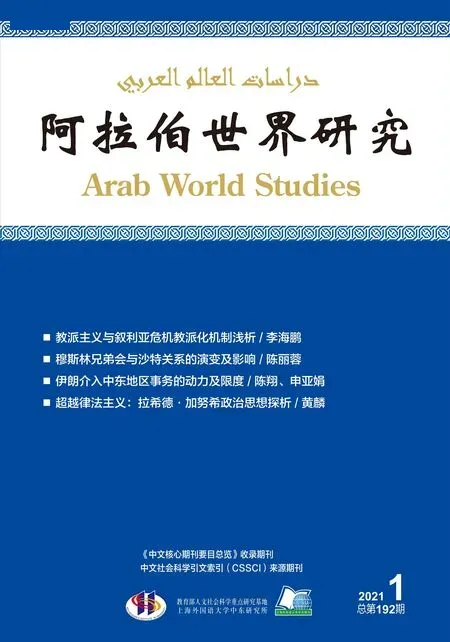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基于世界主义光谱的分析∗
曹亚斌
近年来,关于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的研究逐渐兴起。①Colin Chapman, Islam and the West: Conflict, Coexistence or Conversion?, London:Paternoster Press, 1998; Shireen Hunter, The Future of Islam and the Wes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Praeger Press, 1998; YohananFriedmann, Tolerance and Coercion in Islam: Interfaith Relations in the Muslim Tradi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aron Tyler, Islam, the West, and Tolerance: Conceiving Coexistence,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08; Johannes Bork, “Models of Coexistence,” Journal of Beliefs & Values, Vol. 38, No. 3, 2017, pp. 247-256.这既是对当前伊斯兰世界中诸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反击,又是对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论”的回应。 一般来说,“共处”思想的挖掘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文明的误解和疑虑,进而为寻找伊斯兰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间的合作之道提供思想源泉。 然而,在对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的具体发掘过程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关于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的论述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探讨,甚至一些思想家出现前后矛盾的观点。 而“共处”思想在伊斯兰文明发展过程的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其所具有的现实影响力比较有限。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的时代价值其实并不高,且无法承担起消除误解和疑虑,实现跨文化沟通与合作这一时代重任?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世界主义光谱的视角出发,将伊斯兰文明中的诸种“共处”思想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指的“共处”思想是不同时期伊斯兰思想家关于“共处”问题的相关论述,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经典的阐释或解读。置于世界主义的光谱之中进行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予以再评估。
一、 世界主义光谱与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
所谓世界主义光谱,是指从程度的视角出发对诸种世界主义思想所进行的排列。③蔡拓:《世界主义的类型分析》,载《国际观察》2018 年第1 期,第29 页。能够进行这种排列,主要是因为世界主义思想所关注的核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各种世界主义思想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不同处理导致其在世界主义光谱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也就是说,尽管各种世界主义所主张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涉及道德、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文化、正义等诸多领域,但如果从程度的视角出发,我们却可以将诸种世界主义思想纳入一个光谱之中进行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通常将世界主义光谱中强调普遍性的一端称作“极端世界主义”(radical cosmopolitanism),而将容纳特殊性的一端称作“温和世界主义”(moderate cosmopolitanism)。 “‘极端世界主义’的立场偏向单一的、简单的、彻底的世界主义;而‘温和世界主义’一般会在认同普遍性的前提下,为特殊性保留一定的空间,持平衡的、中庸的、务实的立场。”①蔡拓:《世界主义的类型分析》,第30 页。
“极端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斯多葛派所提出的世界主义思想。 在斯多葛派看来,世界理性是永恒至高的存在,宇宙万物都是由世界理性所创造的,同时宇宙万物的运行和变化也完全受世界理性的决定。 尽管人具有理性和自由,人同样也是被决定的存在。 世界理性为人的生存设定了目的,即人运用自己的理性遵守世界理性所设定的普遍法则,从而实现人的幸福。 斯多葛派认为,“这个完整的宇宙循环受到神性实在的完全决定,它严格地按周期重复自身。 ‘神’在机械性的必然法则之下像一个物体那样起作用,它作为一切个体运动的绝对规定者而言就是‘命运’”②[德]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295 页。。
“温和世界主义”的代表则是当代基于关系、自我与他性、对话伦理、沟通共同体、天下体系等概念而提出的诸种世界主义主张。 例如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世界主义应该是将全球看成一个整体的同时,承认诸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 他主张用五个纬度来实现对他者或差异的承认:承认文化不同的他人的异样性(异样的文明和现代化);承认未来的异样性;承认自然的异样性;承认客观的异样性;承认其他合理的异样性。③[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蒋仁祥、胡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96、292、291 页。哈贝马斯同样认为,世界主义的核心在于对普遍性的追求首先应建立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之上。 “整体和同一性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抹杀差异与个性,也不是要取消对话的多元性。 相反,它是建立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④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1 期,第29 页。
与其他文明相比,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宗教普遍主义与宗教社群主义的并存。 “伊斯兰用一种黑格尔式的机智将普遍和特殊结合在了一起。 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去朝拜黑圣石:一个曾经属于当地部落的圣物。 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人类一家’宗教观念的存在而得以根本缓和。 民众之间的界限即是普遍伦理之间的界限……伊斯兰社会在原则上是普遍性的,在实践中是商业的和都市化的,但个人却依然是社群性的。”①Antony Black, The 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一神教特质以及在伊斯兰社会中宗教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从而使得伊斯兰文明的宗教普遍主义特质十分明显②Bern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2, p. 61.;另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文明的独特发展历程及其所处的特殊地缘环境,使得伊斯兰文明中还蕴含了很强的宗教社群主义色彩。③Ayesha Jalal, “Secularists, Subalterns and the Stigma of ‘Communalism’: Partition Historiography Revisited,”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Issue 3, 1996, pp. 681-689; Ram Puniyani, Muslims and Politics of Exclusion, in Abdul Shaban, ed.,Lives of Muslims in India: Politics, Exclusion and Violence, London:Routledge Press, 2012, p. 19.
宗教普遍主义与宗教社群主义的并存为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基础,然而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也导致伊斯兰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许多困境。 例如,伊斯兰社会对于“乌玛”(ummah)一词内涵的多种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导致的诸种政治观念的冲突便是最好的证据。 “穆斯林对‘乌玛’符号的信仰本身是简单明确的,但这个符号的内涵却复杂不一;穆斯林对‘乌玛’符号的信仰体现了伊斯兰教的统一性,可是他们对‘乌玛’内涵的理解却呈现出多元性。”④钱雪梅:《乌玛:观念与实践》,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4 期,第109 页。“乌玛”有时用来指代整个人类,有时又用于指代各个民族,有时则专指与其他宗教共同体相对的穆斯林共同体。 不同的政治主张便利用这种多样性各取所需,进而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同时又抨击与自身相竞争的主张。 在此背景下,如何纾解这种张力,实现宗教普遍主义与宗教社群主义之间的协调便成为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总体来看,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主要包括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共处”,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间的“共处”,以及社会内部宗教群体间的“共处”三个方面的内容。 尽管这些“共处”思想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千差万别,然而所有“共处”思想关注的核心问题都在于:如何解决承认伊斯兰教普遍性/唯一性与各种以伊斯兰教为标尺而划定的“他性”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显然,如果从这种角度进行分析,那么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实质上都可以被纳入世界主义的范畴之中,作为伊斯兰文明中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宗教以及教派之间的“共处”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不同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共处”;二是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信仰之间的“共处”。 就不同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共处”问题而言,世界主义思想主要通过实现伊斯兰教义的同一性与不同教派对教义的差异化解读之间的协调得以体现;就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信仰之间的“共处”问题而言,世界主义思想通过协调伊斯兰教的普世性与承认其他宗教信仰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得以体现。
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间的“共处”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伊斯兰话语体系中化解宗教教义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是面向全人类的,其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拯救。 《古兰经》中明确指出:“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21:107)。”①《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7 页。与此同时,在伊斯兰文明发展过程中,其始终都在与非伊斯兰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和交流。 因此,如何在伊斯兰话语体系中化解这一结构性矛盾,使其在保证伊斯兰教普遍主义特质的前提下实现具有不同宗教属性的国家之间的“共处”便不仅是一个现实利益的协调问题,同时还具有理念层面的深远意涵。
社会内部宗教群体间的“共处”则主要围绕伊斯兰国家与非穆斯林居民之间的“共处”,以及非伊斯兰国家与穆斯林居民之间的“共处”两个问题展开。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保持伊斯兰教中心地位的基础上保障非穆斯林群体的权益和地位;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在遵守“他者”所设定的制度规范的同时保持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完整性。 显而易见,在伊斯兰话语体系中社会内部不同宗教群体间的“共处”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社会整合的范畴,而变成一个如何实现宗教普遍主义与宗教社群主义之间协调的世界主义问题。
当然,《古兰经》和“圣训”对不同“共处”问题的论述存在宽容度、应对手段、重要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这导致伊斯兰思想家在进行阐释和解读的过程中所凭借的教义论据并不相同。 与此同时,由于伊斯兰文明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不同,伊斯兰文明中不同领域的“共处”思想在协调宗教普遍主义与宗教社群主义之间关系的方式上也不尽相同:一些领域“共处”思想的宗教普遍主义色彩比较明显,而另一些领域则更具有宗教特殊主义的色彩。 此外,在某些领域,处于不同阶段的“共处”思想也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需要使用世界主义光谱来对伊斯兰文明中的不同“共处”思想进行排列,进而将不同思想置于不同的区间进行分析。 当然,在使用世界主义光谱对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进行分析之前,我们还需要对世界主义光谱本身进行若干调适。 这是因为,与西方世界主义思想不同,伊斯兰文明中的诸种“共处”思想都可以纳入世界主义范畴之中,但“共处”思想主要致力于实现宗教普遍主义与宗教社群主义之间协调,因而在“共处”思想中不存在类似于极端世界主义的主张,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对他性的承认。 因此,我们需要从“共处”思想中宗教普遍主义和宗教社群主义的混合程度来进行光谱的设定:一侧偏向宗教普遍主义,另一侧则偏向宗教社群主义。 与此同时,无论是偏向哪一端,其中都存在两种主义,区别只在于宗教普遍主义和宗教社群主义在某种“共处”思想中所含的比重不同。
二、 偏向宗教普遍主义一端的“共处”思想
偏向宗教普遍主义一端的“共处”思想是指那些对于宗教普遍主义的强调程度高于宗教社群主义的思想,其间的主要区别是对他性的不同承认程度。 一般来说,最偏向宗教普遍主义的“共处”思想对于他性的承认程度较低,往往将其看作是暂时性的存在,甚至认为他性是错误的,只是由于当下的某种因素而不得不暂时忍受。 而靠近整个光谱中间但又略偏向宗教普遍主义一边的“共处”思想,则往往承认他性存在的长期性,认为宗教普遍主义终将克服他性,但这一过程必定是极其漫长,因此“共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唯一的选择。 根据偏向宗教普遍主义一端的程度高低,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不同伊斯兰教派间的“共处”思想、伊斯兰国家与非穆斯林居民之间的“共处”思想、古代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共处”思想。
(一) 不同伊斯兰教派间的“共处”思想
在伊斯兰社会中,《古兰经》和“圣训”共同构成了伊斯兰宗教信仰体系的核心,并贯穿于整个伊斯兰社会结构之中。 特别是《古兰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伊斯兰文明的基石。 然而在对《古兰经》和“圣训”解读的过程中,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加之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众多的宗教派别。这些教派之间的主张往往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 与此同时,这些教派内部又进一步分化出更多的支派,它们之间同样差异巨大。 这种状况使得不同伊斯兰教派之间围绕信仰的正统性、政治制度的设计等问题展开了长期斗争。
在伊斯兰文明中,实现不同教派间的“共处”主要是通过在坚持伊斯兰教义唯一性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承认不同教派对教义的差异化解读的必然性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也就是说,不同伊斯兰教派间“共处”的前提是各方都承认伊斯兰教义中真理的唯一性,出现差异化解读的主要原因在于信徒自身的某种缺陷(如片面理解、误读等)。 “共处”的实质即是对信徒缺陷的容忍,而最终的归宿则是信徒克服自身缺陷达到对唯一真理的统一认知。 例如穆尔吉埃派(Murji'ah)便认为,应该将伊斯兰教内各派所争执的问题推延到来世,听候安拉的裁判,而不是以自己的理解将不同意见者指为异端并进行宗教迫害。 他们提出,信仰是信安拉、信先知,凡说过信仰证言“除安拉外,别无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便是信士。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298 页。
(二) 伊斯兰国家与非穆斯林居民之间的“共处”思想
自伊斯兰教创立以来,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与伊斯兰国家的地域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状况使得诸多非穆斯林被纳入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内。 总体来看,伊斯兰国家对非穆斯林的政策相对比较宽容。 例如基督徒、犹太教徒等“有经人” 在伊斯兰国家中被称为“迪米”(dhimmis)②也译作“顺民”。,容许他们在缴纳丁税(jizya)之后继续保持其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 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律和宗教体系、领导机构以及教堂、修道院等宗教设施。 除宗教差异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被容许与穆斯林邻居的正常交往,有时这种关系非常密切。
然而,伊斯兰国家对非穆斯林居民的这种宽容态度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在伊斯兰国家中,迪米的地位随时处于变化之中。 早期的宽容政策在之后经常会被统治者破坏或刻意遗忘……伍麦叶王朝③即“倭马亚王朝”。时期对于迪米的态度较为灵活,然而自阿拔斯王朝之后这方面的政策则变得越来越严格。 自中世纪以来,对于迪米的限制政策进一步趋向严厉,这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宗教上的原因,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变得更加明显。”④John Esposit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08-309.面对这种状况,如何在理论上为伊斯兰国家与非穆斯林居民之间的“共处”寻找合法性便显得非常重要,从而使其不至于仅仅是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一旦形势不利就可以被轻易取消。
总体来看,穆斯林学者论证伊斯兰国家与非穆斯林居民之间“共处”的正当性主要是通过坚持穆斯林生活方式完满性的基础上,承认非穆斯林与穆斯林在生活方式上具有相似性而得以实现的。 当然,在对相似性承认的同时,依然坚持认为较之于穆斯林,非穆斯林生活方式存在某种缺陷。 也就是说,伊斯兰国家内部尊重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容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这主要是因为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样是来自于真主的启示和法令,尽管这种启示和法令较之于伊斯兰教义存在诸多不完满之处。①Antony Black, The 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p. 13
例如,纳哈义(al-Nakha'i)和埃米尔·沙比(Amir al-Sha'bi)认为,拜火教徒和穆斯林在赔偿金(diya)这一法律条款上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因为拜火教徒和穆斯林相似,也是一个自由且有尊严的群体。②Yohanan Friedmann, Tolerance and Coercion in Islam: Interfaith Relations in the Muslim Tradition, p. 50.在此基础上,哈乃斐派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保障伊斯兰国家内部非穆斯林群体权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而主要是源自“守约”对穆斯林所具有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古兰经》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 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 (8:61)”③《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90 页。非穆斯林向伊斯兰国家缴纳丁税实质上就是缔约,而伊斯兰国家保障非穆斯林群体的权利则是守约。④Yohanan Friedmann, Tolerance and Coercion in Islam: Interfaith Relations in the Muslim Tradition, p. 51.
(三) 古代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共处”思想
与目前国际社会惯用的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进行划分的方式不同,在古代伊斯兰话语体系中主要采用伊斯兰教为标准来划分世界。 在这种思维理路下,世界被划分为由穆斯林占统治地位且伊斯兰教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区”(dar al-Islam)和由非穆斯林所统治的“战争区”(dar al-harb)。 这种二元划分对古代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曾造成过不小的阻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张力。 许多极端组织都以“战争区”的存在为理由来论证“圣战”的必要性。 在他们看来,穆斯林的任务就是运用“圣战”将伊斯兰教传播到“战争区”,并最终使其纳入“伊斯兰区”。⑤田文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根源和困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4 期,第5-8 页。
在古代伊斯兰文明中,实现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共处”主要通过坚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伊斯兰社会必将覆盖整个世界的基础上,承认当下非伊斯兰国家存在的合理性而得以实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共处”思想特别强调这一覆盖过程的客观性与非政治性。 也就是说,一方面,这一过程并不随信徒的主观能动性而加速或减缓;另一方面,这一过程是通过伊斯兰信仰而非哈里发制度或沙里亚法的推行来体现的。 例如,哈乃斐学派的一些思想家认为,世界被划分为“伊斯兰区”和“非伊斯兰区”并不与“圣战”相关,而只具有法律体系上的意义,即“伊斯兰区”仅仅意味着沙里亚法在该地能够有效实施,而一个地方被称为“非伊斯兰区”也只是表示沙里亚法不能在该地区实施而已。①Samy Ayoub, “Territorial Jurisprudence, Ikhtilaf al-Darayn: Political Boundaries & Legal Jurisdiction,” Contemporary Islamic Studies, No.2, 2012, pp. 1-14.马立克教派的创始人马利克·本·艾奈斯(Malik ibnAnas)则援引穆圣和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帝国(Abyssinian state)共处的例子,提出伊斯兰国家完全可以和非伊斯兰国家和平相处,且进一步认为,只要这种相处对于伊斯兰国家有利,那么和约就可以超越“十年之期”,甚至可以无限期延长。②Rashied Omur, “Islam and Violence,” Ecumenical Review, No.1, 2003, pp. 158-163.而沙斐仪派则通过提出“和平区”(dar al-sulh)③阿拉伯语单词“sulh”有“和解”“和约”“和平”等含义。这一概念,来论证伊斯兰社会与非伊斯兰社会“共处”的长期性。④Rashied Omur, “Islam and Violence,” pp. 158-163.
三、 偏向宗教社群主义一端的“共处”思想
偏向宗教社群主义一端的“共处”思想是指那些承认“他性”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试图在多样性中寻求普遍性的思想,其间的主要区别是对他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不同认可程度。 一般来说,最偏向宗教社群主义一端的“共处”思想对于他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认可程度最高,并具有很强的宽容性。 而靠近整个光谱中间但又略偏向宗教社群主义一边的“共处”思想则对于他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保留度较高,同时更倾向于用协调而非宽容的方式看待他性。 根据偏向宗教社群主义一端的程度大小,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处”思想、非伊斯兰国家与穆斯林居民之间的“共处”思想、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共处”思想。
(一) 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处”思想
伊斯兰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 《古兰经》中指出:“世人原是一个民族,嗣后,他们信仰分歧,故真主派众先知作报喜者和警告者,且降示他们包含真理的经典,以便他为世人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2:213)。”①《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 页。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尊奉“认主独一”的信仰理念,反对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 “除真主外,假若天地间还有许多神明,那么,天地必定破坏了(21:22)。”②同上,第164 页。“你们所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2:163)。”③同上,第12 页。上述因素的结合使得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信仰之间存在不小的张力。 而如何纾解这种张力,使普世性和独一性得以协调,便成为伊斯兰“共处”思想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伊斯兰文明中,实现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处”主要是通过强调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在核心理念、人的拯救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性得以实现。 一些苏菲派学者认为,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之间虽有各种分歧,宗教教义也彼此不同,然而在“爱主”这一点上却都一样,并无本质区别。 对信徒而言,“爱主”是追求至善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目标。 “爱主”所包含的意义要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所包含的东西都要宽丰富得多。 因此,人们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宗教内而否定其他宗教存在的合理性。 苏菲派“在天房、清真寺、修道院和庙宇都能看见真主”④[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六册)》,赵君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74-75 页。。 “我原本否定其他信仰,而今心胸开放,面向修道院和牧场;旧约的法版、古兰的圣卷,偶像之地,绕行的天房。 我信奉爱的宗教,那是我的向往;爱,是我的宗教,我的伊玛尼信仰。”⑤周燮藩等:《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99 页。
(二) 非伊斯兰国家与穆斯林居民之间的“共处”思想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学者都认为,除经商、外交等短期事务外,穆斯林在非伊斯兰国家长期生活是不被容许的。 伊本·泰米叶曾提出,穆斯林只能生活在由沙里亚法所统治的地区,一个穆斯林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处在了非伊斯兰社会之中,对他来说唯一正确的选择便是尽快从此地迁徙(hijra)。⑥Mohamed Badar and Masaki Nagata, “Modern Extremist Group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A Critique from an Islamic Perspective,” Arab Law Quarterly, Vol. 31, No. 1, 2017, pp. 305-335.艾哈迈德·瓦沙里希(Ahmad al-Wansharishi)则认为,生活在非伊斯兰社会中的穆斯林将面临巨大的宗教风险,因为与异教徒的接触会不可避免地贬损穆斯林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因此穆斯林生活在非伊斯兰社会是不被允许的。①Mohamed Badar and Masaki Nagata, “Modern Extremist Group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A Critique from an Islamic Perspective,” Arab Law Quarterly, Vol. 31, No. 1, 2017, pp. 317-318.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也认为,世界上只要有一处沙里亚法有效运行的地方,那么对于非伊斯兰社会中的穆斯林来说就必须离开自己所生活的地方,进而移民到伊斯兰社会。②Ibid., p. 323.然而,与此相对的社会现实状况是,由于历史、战争、经济等原因,有大量穆斯林在非伊斯兰国家中定居。 因此,如何为这种状况寻求正当性,从而实现非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群体间的和平相处便显得十分重要。
伊斯兰世界的学者论证非伊斯兰国家与穆斯林居民间“共处”的正当性,主要是通过探究非伊斯兰国家与伊斯兰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性来实现的。 同时,这一过程又特别强调这种共同性与伊斯兰教义的相通性。 例如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援引“圣训”中的文本,“难道真主的大地不是宽阔的、能容你们迁移的吗?”③《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4 卷)》,祁学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版,第240 页。,并指出穆斯林可以生活在非伊斯兰国家,即使没有外力阻碍而可以进行迁徙时同样如此。④Khaled Abou El Fadl, “Islamic Law and Muslim Minority,” Islamic Law and Society, Vol. 1, No. 2, 1994, pp. 141-187.沙斐仪(Al-Shafi'i) 则分别援引“阿卜杜拉·阿巴斯(Abdallah Abbas)事件”和游牧部落皈依伊斯兰事件提出共处思想。 在“阿巴斯事件”中,当穆圣在麦地那建立穆斯林社团后,穆圣依然容许阿卜杜拉·阿巴斯等人居住于当时尚处于多神教徒统治的麦加。 而在后一事件中,当游牧部落皈依伊斯兰教后,穆圣鉴于这些部落的游牧属性,要求他们依然在当地生活而不是迁徙到穆圣所在的麦地那。 沙斐仪认为,这两个事件说明只要能够保证自身宗教信仰的完整性,穆斯林可以被容许居住于非伊斯兰国家。⑤Ibid.
当代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威(Yusuf al-Qaradawi)则从伊斯兰教的普适性角度出发,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全球性宗教,且《古兰经》中也有“天下一家”的表述,因此穆斯林可以生活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穆斯林不仅可以生活在非伊斯兰国家,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和非穆斯林通婚。他认为,当一对非穆斯林夫妇中的任何一方在婚后皈依伊斯兰教后,无论从伊斯兰教的普世特征还是契约对于穆斯林所具有的崇高价值来说,这段婚姻关系依然有效。①Johannes Bork, “Models of Coexistence,” Journal of Beliefs & Values, Vol. 38, No. 3, 2017, p. 254.
(三) 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共处”思想
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曾经专属于非伊斯兰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的许多国际规则逐渐演变为整个世界所通行的规则,伊斯兰国家也开始接受其中的一些规则。②Antony Black, The 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pp. 284-285.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家在诸多国际事务的竞争过程中通常处于劣势,甚至一度完全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在这种状况下,如何既论证接受源自非伊斯兰世界的国际规则的合理性,又保持某些源自伊斯兰文明的国际规则的正当性,便成为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间共处思想的核心。
近代以来的伊斯兰思想家论证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间的“共处”主要通过对“伊斯兰区”和“战争区”内涵的重新解释而实现的。 其中特别强调二者之间存在的相同性或重叠性。 例如,瓦赫巴·祖海利(Sheikh Wahbah al-Zuhaili)认为,“战争区”这一概念的出现与早期伊斯兰社会所面临的特殊安全环境紧密相关。 由于早期伊斯兰社会与周边地区频繁发生战争,穆斯林基于安全和防御等方面的考虑将所有由非穆斯林统治的区域都称为“战争区”。 既然“战争区”并无特殊宗教意涵,这一概念便是可以改变的。 当今世界,所有的主权国家均已加入联合国且普遍受《联合国宪章》的约束,这意味着早期伊斯兰社会所遭遇的那种持续威胁已经消除,在这种情况下仍将非伊斯兰社会称作“战争区”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联合国宪章》所具有的契约本质,使得如今所有的非伊斯兰社会都可被称为“契约之地”,其与伊斯兰社会之间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契约关系。③朱文奇主编:《国际人道法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289-309 页。
塔里克·拉玛丹(Tariq Ramadan)则认为,“战争区”和“伊斯兰区”本质上不是一对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具有宗教意涵的空间/领域概念。 因此,“伊斯兰区”是那些体现了中正、和谐、仁爱等伊斯兰教核心原则的空间/领域,而“战争区”则是违背了这些原则的空间/领域。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对于伊斯兰社会来说,其在经济空间/领域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因而是“伊斯兰区”。 然而,这些地方往往战争频仍,民众安全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从安全空间/领域来说又属于“战争区”。 同样,对非伊斯兰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来说,该地区民众在安全、信仰自由等方面拥有切实保障,因而可以称为“伊斯兰区”;但从经济方面来看,其又是全世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始作俑者和受益者,因此这些区域又属于经济空间/领域的“战争区”。 拉玛丹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今时代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之间已处于“相互嵌入”的共处关系之中,并不存在严格的敌我之分。①Mariella Ourghi, “Tariq Ramadan: From a Mere Co-Existence to an Authentic Contribution of Europe's Muslims,” Journal of Religion in Europe, No. 3, 2010, pp. 285-309.
四、 “共处”思想与当今伊斯兰世界所面临核心挑战的纾解
通过对伊斯兰文明中诸种“共处”思想的分类和排序,我们发现这些“共处”思想的核心差别在于对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 偏向于宗教普遍主义一侧的“共处”思想倾向于用普遍性来统摄特殊性,是一种“同中存异”的思维方式;而偏向于宗教社群主义一侧的“共处”思想则倾向于用特殊性来制衡普遍性,是一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
当今时代,在挖掘伊斯兰文明“共处”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视不同“共处”思想在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时的具体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的处理方式与不同领域当下所面临的核心挑战结合起来,分析和评价各种“共处”思想。也就是说,各种“共处”思想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思想延续性和逻辑完整性,更在于其和当今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之间所具有的契合性。 只有通过有针对性的思想挖掘,用最能够从根本上应对某一领域核心挑战的“共处”思想来处理问题,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有效纾解当今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真正体现伊斯兰文明“共处”思想研究的时代特性。
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看,当今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表现为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在伊斯兰世界的蔓延,以及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文明的贬斥和对抗两个方面。 就极端主义思潮而言,一方面,其所鼓吹的复古、排外等主张对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的阻碍,这些思潮的蔓延事实上已成为当今一些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以及社会动乱频仍的重要诱因之一;另一方面,极端主义思潮对战争、暴力的崇奉,则对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部世界对伊斯兰文明的误读。①田文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根源和困境》,第5 页。就“文明冲突论”而言,其对于伊斯兰文明的贬斥和对抗为某些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口实,并进一步激发了伊斯兰世界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增长。 “文明冲突论”还使得试图发扬伊斯兰文明独特性的诸种改革变得举步维艰,进而造成一些伊斯兰国家只能在“完全西方化”和“复古主义”这样两个不切实际的极端不断徘徊。②Wallace Daniel, “Islam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49, No. 3, 2006, pp. 509-523.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扬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来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和“文明冲突论”进行批判和反击便显得尤为必要。 当然,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和“文明冲突论”在核心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在应对上述两种挑战时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共处”思想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回应。
(一) 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反击
尽管在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上存在差异,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核心思维方式上却拥有一以贯之的特性,即通过将某些主张绝对化和普遍化,进而以这种绝对普遍性来排斥和消除“他性”。 也就是说,在极端分子看来凡是自己所坚持的东西都是唯一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一定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凡是与其相左的主张都是绝对错误的,不存在某一时间、某一地区会变成正确的可能性。 例如,法拉吉(Muhammad Faraj)在反对通过和平方式(政党选举)结束“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时,其核心理由就在于和平方式实质上意味着对于“错误”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并不能逐渐消解“错误”,反而会使“错误”的破坏力变得更大。 “有人提出,如果所有的机构都充满穆斯林医生和穆斯林工程师,那么,异教徒的政治魅力自然会丧失,有朝一日穆斯林的法度自然会建立……这种说法毫无道理……无论我们有多少穆斯林医生和工程师,他们都只是在帮助建立异教徒国家。”③王晋:《对立与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刍议》,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4 期,第39 页。库特布认为,人类在任何时空中都要面临选择:要么全然遵守真主之律法,要么实施人为的法律,除此之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因此,穆斯林一定要对“非伊斯兰社会”(他所谓的“蒙昧社会”)发动“圣战”。④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3期,第9 页。而“伊斯兰国”选择黑色作为旗帜颜色,则是要表达“在正确与错误、信教与不信教者之间,没有灰色地带”的信念。①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3 期,第57 页。
很显然,这种将某些主张绝对化和普遍化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而在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回击的过程中,通过“同中存异”的策略似乎更为有效,即在坚持普遍性的前提下,通过对特性的宣扬达到对“他者”的承认。 这种策略与我们所熟悉的“证伪逻辑”有些相似:证伪“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只需要找到一只黑天鹅就足够了。 但黑天鹅的出现并不妨碍“有些天鹅是白的”这一结论的成立。 具体到本文,我们认为只有积极宣扬“同中存异”的“共处”思想,特别是那些能够对“他者”实现最大程度承认的“共处”思想,才能够达到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有效反击。②需要说明的是,对“异中求同”的“共处”思想的宣扬也同样必要,这里只是从“更为有效”的层面提出上述观点。 另外,在“同中存异”的共处思想中,那些对“他性”的承认程度非常有限的思想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反击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例如,以穆尔吉埃派为代表的、强调不同教派对教义差异化解读必然性的“共处”思想,便不能有效应对挑战,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提供便利。也就是说,在坚持普遍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诸种特殊性进行最大程度的认可,从而实现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所秉持的绝对化思维方式的有力批判。
关于武力的运用问题,“同中存异”的思想承认穆斯林拥有使用武力推翻暴政、反抗恶行的权利,但同时又特别强调对于武力的使用必须十分谨慎。 “惩恶、扬善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但通过暴力方式来改变(恶行),必须得到全体穆斯林学者的共同认可。 否则,随意宣布惩恶扬善,就会带来邪恶和混乱。如此一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运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人遵从自己的意志。”③Yusuf Al-Qaradawi, State in Islam, 3rd edition, Al-Falah Foundation, trans., Cairo: Al-Falah Foundation, 2004, p. 178.再如,关于伊斯兰社会中非穆斯林的地位问题,“同中存异”的思想承认古代伊斯兰时期所实施的那种丁税和“迪米”制度在当时所具有的合理性,但同时又强调当今时代所发生的一大重要变化,即现代国家制度在伊斯兰世界的设立。 因此,在当今时代任何向伊斯兰国家缴纳税收、承担兵役等义务的本国居民都应被视为“迪米”;与此同时,“迪米”和穆斯林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他们都是本国的公民。④Yohanan Friedmann, Tolerance and Coercion in Islam: Interfaith Relations in the Muslim Tradition, pp. 51-53.关于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同中存异”的思想承认西方国家的霸权政治和经济剥削对伊斯兰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复古、排外才是摆脱西方控制的唯一方式。①Sami Baroudi, “Sheikh Yusuf Qaradawi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0, No. 1, 2014, pp. 2-26.
(二) 对于“文明冲突论”的反击
“文明冲突论”认为,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发展而来的并不是普世文明的胜利,而是存在着本质性区别的各种文明之间相互对立和冲突的时代的到来。“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事情。”②[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第31 页。其中,由于当代伊斯兰世界所存在的一些状况(如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和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互动不断扩大等),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尤为严重。 需要指出的是,“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文明——伊斯兰……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③同上,第194 页。。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貌似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其将冲突的根源归之于基于文明的“认同政治”的兴起,才使得“文明冲突论”能够在西方世界拥有诸多拥趸,而其所具有的煽动力才能够一直持续。
从思维方式上来看,“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一种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无限夸大的思维逻辑。 在这种思维逻辑之下,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被视为一组截然对立的存在,而这种截然对立性则导致冲突不可避免。④Wallace Daniel, “Islam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p. 509-523.在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回击的过程中,通过“异中求同”的策略似乎比较有效,即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共同性、互补性的不断寻求来达到与“他者”的和平共处,一方面承认世界文明和各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不同文明所具有的共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互补性,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关于民主问题,“异中求同”的思想承认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民主的具体实施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二者在核心理念上则殊途同归。 “民主与伊斯兰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和谐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被民众所拥戴,那么这个人就无法组建自己的团体。”①Yusuf Al-Qaradawi, State in Islam, p. 194.关于“伊斯兰区”与“非伊斯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异中求同”的思想承认二者在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上的不同,但又特别强调应对各自挑战的手段的互补性以及相互合作的必要性。②Mariella Ourghi, “Tariq Ramadan: From a Mere Co-Existence to an Authentic Contribution of Europe's Muslims,” pp. 285-309.关于西方穆斯林的地位问题,“异中求同”的思想强调穆斯林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但同时又指出其对于所在国法律的遵从、社会责任的承担等方面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同等性和一致性。③Andrew March, Islam and Liberal Citizenship: The Search for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关于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特征问题,“异中求同”的思想认为,尽管各个宗教之间在宗教教义上彼此不同,但其在仁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以及自由等方面却存在根本上的一致。④李艳枝:《试析法图拉·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及其影响》,载《世界民族》2012 年第6 期,第166-167 页。
五、 结语
总体而言,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思想群”,通过世界主义光谱这样一个概念工具,我们可以对诸种“共处”思想进行结构性归类,并将不同的“共处”思想置于该光谱的不同区间。 通过此种归类研究,我们可以对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挖掘,进而用最能够从根本上应对当今伊斯兰世界在不同领域所面临的核心挑战的“共处”思想来处理问题,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并最终为纾解当今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诸种困境、消除外部世界对伊斯兰文明的误解、实现真正的全球之治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