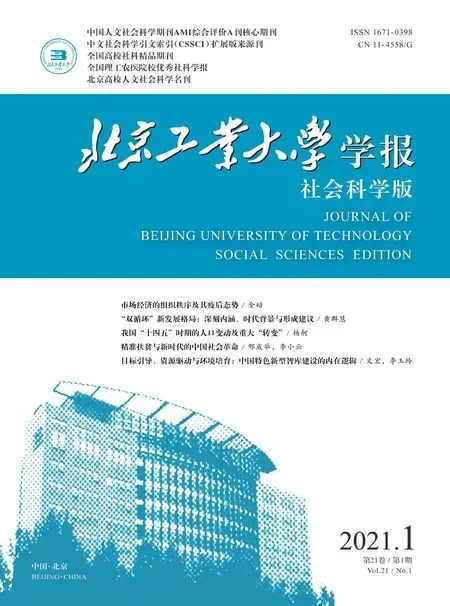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思考
刘彩娥,李永芳
(北京工业大学 图书馆,北京 100124)
21世纪以来,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日渐深度融合,尤其是以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为代表的,基于移动通讯网络与web2.0技术的新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不仅让人们面对海量的信息应接不暇,而且使每个人都可以广泛参与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形成了复杂的信息环境。信息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观点与态度、价值观与信仰,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公众信息素养的提高不仅有助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也有助于社会群体远离偏见、消除分歧、和谐发展。信息素养是人类应对信息社会的必备素养,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信息社会,公众信息素养已经成为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
这里的公众是指参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活动的成年人口。国外有专家将其界定为25—62岁的人口,并用“经济活跃的成年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adult population)来表述。认为信息对于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日常与生计资源,关系他们的工作、家庭、兴趣、终身学习、参与社会等所有方面[1]。
一、研究与实践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信息素养概念提出之后,国际国内都普遍重视高等学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有关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也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了充分持久的讨论与深入的研究。相关国际组织如国际图联(IFLA)、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等也制定过一系列的有关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标准或内容框架。相应的教育实践也在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高等学校以多种形式普遍开展。但是,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主体部分的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相关研究与教育实践都比较薄弱。
进入21世纪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带动信息社会全方位、多角度发展。一些国际组织也认识到了公众信息素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先后研究制定相关计划,致力于提高全人类应对信息社会的能力。早在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便启动了“全民信息计划”(Information For All Programme,IFAP),以此推动信息素养教育走向社会公众[2]。2013年,UNESCO又发布了《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从国家、区域和个人3个层面评估媒体与信息素养水平,旨在为各成员国开展针对媒体与信息环境的综合性评估提供方法指导[3]。2014年3月UNESCO又发布了《媒体与信息素养政策与战略指南》(Media and Informational Literacy Policy and Strategy Guidelines) 将信息素养定位为“确保公民参与知识型社会建构的必备能力”,围绕8个主题对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发展战略提出指导性意见[4-5]。这3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人类应对信息社会、消除信息鸿沟、提升公众信息素养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对于推进各国公众信息素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从2003年开始,UNESCO与IFLA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的有关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宣言[6],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公众信息素养。但是,对这些纲领性文件最积极的响应仍然是高等学校,而不是政府或社会组织。
1984年,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此后,我国有关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在高等学校广泛开展,并不断跟进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的进展。但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指向学术信息,目的是提高学生对学习资源与科研文献的获取与利用能力。直到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对 “国民信息素养”作了相关表述:“支持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行业协会、培训机构等开展信息素养培养,加强职业信息技能培训,开展农村信息素养知识宣讲和信息化人才下乡活动,提升国民信息素养。”[7]相对于《规划》全文,这一表述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图书情报学专业刊物发表了少量有关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文章,但没有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尤其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公众信息素养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相关组织与业界专家认识到公众信息素养问题在信息社会的重要性,2019年8月在鄂尔多斯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信息素养与可持续发展主题论坛”中,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提升行动倡议》,旨在推动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的普及与发展[8]。2019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又在海口举办了首届“图书馆对公众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研讨班”。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围绕这一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虚假新闻、不实信息频出,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公众信息素养受到严峻考验。由此,公众信息素养问题再一次引起业界聚焦。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2期发布了一组专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科学应对与思考:图情专家谈新冠疫情》,图书情报界的专家撰文探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众信息素养问题[9]。聂云霞等也在其他刊物发表文章,探讨公众信息素养培养的路径[10],部分报纸也撰文呼吁加强公众信息素养教育[11-12]。 总的来说,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才刚刚起步,许多问题都有待于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同时也提示信息素养教育的重心将由高等学校向社会公众转移。
二、信息素养概念的发展与公众信息素养内涵
信息素养不是一个完备的概念,而是一个多元化、情境化、动态发展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以来,它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IFLA、ALA等组织不断对信息素养概念进行完善与补充,2015年,ACRL针对21世纪信息环境发展的特点,给信息素养以最新的、相对权威的定义:“信息素养是指包括对信息的反思性发现,对信息如何产生和评价的理解,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并合理参与学习团体的一组综合能力。”[13]然而,这一概念更多地指向学术信息环境,适用于高校学生开展创新性学习与科学研究活动,而非社会公众。尽管如此,这一概念强调以批判性的思维去审视、理解信息,并参与信息社会,在新媒体信息环境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以来,受到信息、媒体、通讯、数字技术持续的影响和冲击,产生了一系列与信息素养相关的概念,诸如:媒介素养,数字素养、视觉素养、数据素养等,且不同概念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与信息素养最为密切的概念是媒介素养,但媒介素养基于信息传播的途径,而信息素养指向信息内容的利用,二者不能等同。2014年,UNESCO发布的《媒体与信息素养策略与战略指南》(Media and Informational Literacy Policy and Strategy Guidelines),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概念合二为一,称为“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并正式给出了定义:媒介与信息素养是一整套的能力,它赋权于公民,使其能够以批判、道德与有效的方式,运用多样化工具去存取、检索、理解、评价、使用乃至创造、分享各种形式的信息与媒介内容,以便于参与和从事个人的、职业的、社会的活动。《媒体与信息素养策略与战略指南》还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具备信息素养,不仅有助于公民分辨信息的真假虚实,而且信息素养赋予各行各业的人有效地查找、评价、使用和创造信息,以实现其个人、社会、职业与教育目标的能力[14]。
虽然有关公众信息素养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权威的概念,但媒介与信息素养概念非常贴近公众信息素养的实质内涵,可以被理解为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素养。本文认为,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信息素养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4种要素:(1)信息意识。能够认识到信息的价值,并知道自己什么情景下需要怎样的信息;(2)信息获取与利用能力。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与自己的信息需求最相关的信息,并利用信息解决问题,优化决策,以促进自己的生存、职业、文化、终生教育等的发展;(3)批判性思维。有意识审视信息发布者的资质、性质,与发布信息的目的,能够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质量与效用的评价;(4)信息道德。在参与信息社会活动中,不发布、传播虚假的、片面的信息,以及危害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信息,不侵害他人的个人信息与信息隐私,具备信息社会的社会责任感。
三、新媒体信息环境分析
新媒体是相对概念,相对于以往的媒体,新出现的媒体形式便被称为新媒体。例如,电视对于报纸,网络对于电视。21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以微信、微博、twitter为代表的新兴新媒体形式,各种应用APP不断推陈出新,机构、团体、个人信息内容铺天盖地,形成了独特的新媒体信息环境。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信息环境。新媒体在促进信息民主化等方面有着非常积极与进步的意义,但是,由于信息的生产、获知、传播具有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即时性等特点,使新媒体信息环境又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信息超载与“信息茧房”并存
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信息生产、传播不受更多的限制,个人、 机构、组织等都可以随意发布信息,而不受更多的、严格的审查,且传播迅速,因而信息超载现象严重。人们每天都接受大量的信息,无暇对信息的真实性、目的性深入思考,也来不及对信息进行有效的选择与取舍。信息超载不仅使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淹没在信息海洋之中,更重要的是,信息洪流时时冲击人们的生活,其中错误的、虚假的、片面的信息影响着人们正确的判断与决策。新媒体信息环境下,信息主宰人,而不是人主宰信息,人与信息的关系表现出倒置现象。
另一方面,新媒体信息与大数据的并存,导致信息超载与“信息茧房”并存现象。各网络信息主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利用算法推送技术,实现用户与内容的精准对接,为用户推送个性化的信息,带来用户受困“信息茧房”与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例如:用户的网络浏览内容、注册信息等数据会被许多互联网运营商挖掘,进而持续推送相似或系列内容,使得用户深陷“信息茧房”困境而难以突破[15]。另外,新媒体信息以“圈子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也加重了“信息茧房”现象。
(二)虚假信息、片面信息泛滥
新媒体时代,移动通讯网络技术与数字社交网络使信息民主化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最大限度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虚假信息与夸大的片面信息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干扰人们正确判断,并以更广泛的方式影响社会。
新媒体环境下,至少有2个方面的动机促使虚假信息的产生。首先是信息的广泛传播可能会为信息发布者带来可观的广告收入,这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因此,信息发布者宁愿关注敏感话题,放大片面信息,甚至制造虚假信息,冠以吸引眼球的标题进行推送传播,获得流量或广告的点击率。第二个动机是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体的广泛传播,有目的地推广自己的观点、观念,或诋毁、反对与自己对立的、或不同的派别与观点[16]。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虚假新闻、不实信息不仅难以消除,而且经常快速传播,进而形成舆情中心。由于民众信息素养的缺失,或将造成信息风暴或信息灾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1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方方日记事件”,其中片面信息与未经核实的信息被迅速传播,形成极大的社会负面情绪,并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
虚假信息的另一种极端表现是信息诈骗与网络诈骗。由于网民不能有效分辨信息的真假,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
虚假信息已经成为国际信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欧洲信息素养大会(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ECIL)将2020年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in a post-truth era),其中有6个分主题与虚假信息有关,分别为:虚假新闻,另类事实(fake news, alternative facts);后真理政治(post-truth politics);后真理社会(post-truth society);信息素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IL,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可信度和来源评估(credibility and source evaluation);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FSCO)也将2020年“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的主题确定为“抵制假信息:每个人的媒体与信息素养”(resisting disinfodemic: media &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everyone & by everyone)[18]。
(三)信息低俗化倾向比较严重
新媒体的宽松与个性化使得网络信息从传统媒体的严谨与权威走向宽松与随意,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信息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信息载体从纸质与PC机为主流,转变为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载体为主流,人们使用手机阅读时呈现碎片化与轻浅化的特征,拒绝经典与严肃,倾向于阅读并传播娱乐化、低俗化的信息,助推了网络信息的低俗化倾向。
四、公众信息素养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鸿沟始终存在,公众信息素养差距加大
有研究者认为信息鸿沟表现为3个层次:接入沟、 使用沟,知识沟[19]。
尽管新媒体时代网络覆盖率很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的信息鸿沟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网络信息的获取与利用层面的差距。即“接入沟”基本弥合,“使用沟”与“知识沟”,尤其是“知识沟”却有逐步加大的趋势。
在相同的网络接入条件下,不同的网民个体对网络有不同的使用需求和利用程度,即信息素养的差异。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网民,更倾向于把互联网当作获取新知、寻求机遇、发展自我的工具,并尽可能在网络空间中趋利避害;而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信息素养较低的网民,则对海量的网络信息不能够有效取舍,更容易被网络世界异化。例如:MOOC被誉为一场具有超越国界、种族、性别、阶级和收入潜力的教育革命,但是,一项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MOOC活跃用户的调查显示:80%的MOOC用户来自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6%的人群,低学历群体使用率非常低[20]。MOOC非但没有实现其倡导者的初衷,反而似乎在强化“富人”的优势,而不是给与“穷人”的教育福利。信息本来是重要的生存与发展资源,但信息素养较低的群体却找不到“信息富矿”,不能从信息海洋中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而是被垃圾信息、低俗信息淹没。
(二)普遍缺少批判性思维
自由开放的新媒体信息环境下,大量的虚假信息与低质量、无价值信息普遍存在,批判性思维成为公众信息素养的核心要素,也成为公众信息素养最缺失的内容。
首先,新媒体环境下,网民在网络世界里得到了自由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使信息环境日趋复杂。网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忽略信息发布者的资质、性质与目的,缺乏对信息的选择、甄别、评估和思辨能力,大量虚假、不实信息、片面信息不可阻挡地进入公众视野并被广泛传播,导致民众的非理性判断与行为。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始,各种有关疫情的信息或者有关抗“新冠”病毒的医疗信息让民众真假难辨,出现连夜排队抢购“双黄连”药品而感染病毒的案例。期间也有不少媒体为了拉动流量,发布一些危言耸听的虚假或片面信息,对民众产生误导。
批判性思维有助于人们对信息进行有效取舍,选择正确的、有价值的正向信息,放弃错误的、低质量的负向信息。正向的信息可以赋能社会和个人,错误信息、片面信息、低俗的垃圾信息等不仅会浪费个人的时间,而且会误导个人的判断与行为决策,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对个人和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五、发达国家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举措
综上所述,在信息时代,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有效开展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提升国民信息素养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出台一些具体的举措,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素养概念本是不分群体的,没有学生与公众之分。美国是信息素养教育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的引领者,历来重视信息素养教育,首先在高等教育领域制定了一系列的信息素养评估标准与框架,并根据信息环境的发展不断调整修订。在公众信息素养教育领域,美国也做了许多典范性的工作。2009年,奥巴马政府将每年10月确定为“国家信息素养意识月”(national information literacy awareness month),强调所有美国人都要认识到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并熟练掌握有效应对信息时代所需的技能,具有寻找、发现和破译信息的能力,并应用于人们的人生决策,无论是财务、医疗、教育还是技术[21]。
2018年,英国“图书馆与情报专家协会”(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CILIP )信息素养工作组对信息素养定义进行更新,强调信息素养教育要面向所有公民,并界定了信息素养的5种场景:日常生活、公民身份、教育、工作、健康。CILIP建立了专门的信息素养教育网站,汇集该领域研究、实践与教学资源,并创办专业刊物《信息素养期刊》(Journal of Information Literacy)讨论人们生活、研究、工作等场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实践与方法[6]。
新加坡为使不同群体、具有不同需求的人受到良好的信息素养教育,2013年开始推广公众信息素养教育运动项目——“来源、理解、研究与评估”(source、understand、research、evaluates,SURE),该项目有3个子项目:source for school、 source for work、source for life,其中2个与公众信息素养有关。 2019年,又发布《数字媒介与信息素养框架》(Digit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媒介与信息素养项目的指导。
六、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手机网民达8.9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农村网民为2.55亿[22]。这一组数据表明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互联网接入鸿沟基本弥合,使用互联网的公民,尤其是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很高。我国有数量庞大的网民,但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开展过官方国民信息素养状况调查,缺乏权威的数据,而且国内公众信息素养平均水平偏低,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也相对落后,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区间与群体间的信息素养差异较大
与经济发展的地区间不均衡相对应的是信息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平衡,占有的文化、教育资源悬殊较大,信息素养水平也出现相应差距。同一地区,不同的群体(例如: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也存在信息素养水平的差异。发达地区与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善于利用信息资源发展成就自己,而欠发达地区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则不能享受信息社会的红利。具体地讲,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人口信息素养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居民信息素养高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信息素养也高于低学历群体。随着信息环境复杂化,地区与群体间信息素养差距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农村网民2.55亿,占网民总数量的28.2%;在4.96亿非网民中,农村人口占59.8%。调查显示,非网民不能上网的原因有三点:使用技能欠缺、文化程度限制、年龄因素[22]。这些原因说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程度低的群体信息素养十分低下。
(二)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比较薄弱
在消除信息鸿沟方面,国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主要集中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几十年来,我国的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在高校展开,进入21世纪后,中小学的信息技术课也增加了信息素养的内容,但公众信息素养问题没有被引起高度重视,缺少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与发展规划,也没有具体有效地面向社会与公众的信息素养教育方案与举措。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提到“加强职业信息技能培训,开展农村信息素养知识宣讲和信息化人才下乡活动,提升国民信息素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没有大规模、具体有效的举措,将公众信息素养,尤其是落后地区与农村人口的信息素养教育落到实处。
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移动网络的发展带来的新媒体信息环境给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在不断消解人们已有的信息素养。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论述,新媒体信息环境的复杂性对人类的信息素养带来了种种挑战,使人们深陷信息海洋,而不能有效利用信息。据统计,国内互联网市场检测到的各类APP共有367万种[22],其中包含大量的游戏软件、娱乐性短视频等,这些内容都在和人们有效利用信息争夺有限的时间。
七、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对策思考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对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作如下思考。
(一)从国家层面制定公众信息素养培养计划
阅读是与信息素养相关的话题。我们国家对全民阅读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2012年,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4 年、2015 年又两次将全民阅读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作为一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被提升到提高全民族文化与文明素质,提高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23]。在实践层面,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以公共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机构为主,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提倡公民放下手机、回归经典阅读,并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网络信息势不可挡,回归经典是必要的,放下手机是不可能的。以移动网络与手机阅读为主的新媒体时代,提升全民信息素养似乎是一件比倡导全民阅读更重要的事情。我国对于提高全民信息素养还没有明朗的思路。鉴于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调查与分析我国公众信息素养现状与需求,评估公众信息素养水平,结合我国信息化战略发展规划,制定有关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指导性意见或相关政策,明确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目标、任务、相关主体及其责任、具体措施与步骤等,倡导整合各种资源,利用各种途径,培育并提高全民信息素养,以构建我国公众信息素养培养体系,引导信息洪流向利于民生、利于社会健康和谐方向发展。
(二)分层次、分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以后,获得很高的收视率,有效地普及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公众文化素养,为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已有的“学习强国” “慕课中国” “学堂在线”等平台有很多有关信息素养教育的MOOC内容,但总体上以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为主,公众信息素养内容十分微弱,受众也主要是高校学生,在社会公众中没有足够的显示与影响。高校学生信息素养内容以学术资源的利用为主,而公众所缺少所需要的信息素养与高校学生有明显的区别,而且他们的信息素养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与群体性。因此,需要调动各级各类政府部门、文化机构,根据职业、年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等不同,采用多种教育方式,线上与线下、电视等传统媒体,开展内容各异、层次不同的信息素质教育。
(三)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图书馆的作用
“信息素养不仅应成为大学的公共课程,而且应成为社会的公共课程,甚至行政管理人员的必修课。”[24]“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重心,应逐渐从阅读向包括阅读在内的更广泛的素养转移,更加突出信息素养、技术素养、环境素养等多元素养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25]图书馆是信息素养教育的主力军,各级各类图书馆,尤其是公众图书馆有义务、也有必要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向公众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我国高校图书馆积累了30余年的信息素养教育经验,除课堂教学外,很多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信息素养MOOC等网络教学方式,有的还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项目资助。在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中,高校图书馆也应该发挥优势,探索适用于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素养教育,服务社会。《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2016)规定高校图书馆的任务包括“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服务”;“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26]
除了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鼓励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培训机构、其他行业协会等参与全民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国家信息化战略,构建中国公民信息素养培养体系。
八、结束语
公众信息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赋权公民并保障其知情权和参与权,而且具备高信息素养的人,善于利用多元信息丰富认知、促进对话、远离谣言与仇恨。因此,公民信息素养的提高,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升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公众信息素养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FSCO)2019年“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week)的主题定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公民:知情、参与、赋权”(MIL citizens: informed, engaged, empowered)[27]。然而,在国际范围内公众信息素养的研究与实践尚没有广泛而深入地展开,新媒体信息环境又增加了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复杂性,因此,公众信息素养的论题方兴未艾,也面对诸多挑战。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也将是一项比较浩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并分地区、分群体、分层次去实施,并不断探索、完善相应的评估标准,促使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