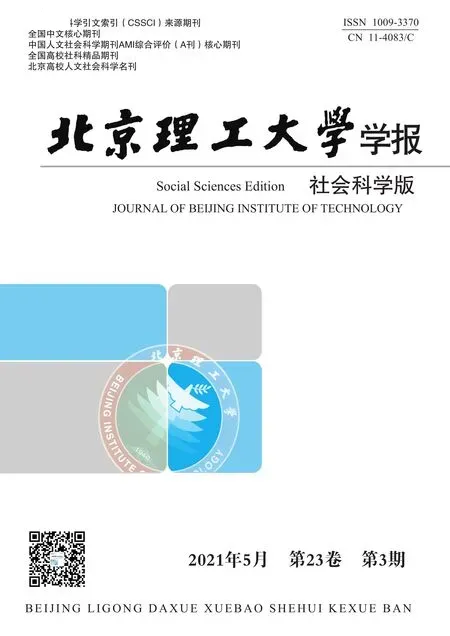儒家人本理念的伦理性与超越性论析
蔡 杰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儒家重视以人为本位的伦理观念,人本理念是传统儒家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尚书》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礼运》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说明人是天地之间最为灵秀者。同时,古人对这种灵秀的重视,突显出在人身上所特有的伦理特征。《汉书·刑法志》载“夫人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也”,《白虎通》云“人生而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所谓仁义礼智信等诸多美德正是基于对人伦之理的提炼与概括,所以儒家的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伦理性特征。
人本理念的伦理性特征,似乎与西方强调个人自由的人本思潮有某种程度上的相违。在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包括以情感主义为特征的极端个体化的自我倾向的问题,我们或许正好能够反过来认识到,儒家人本理念中的伦理性将会不仅仅是全球视域中的人本思想的重要补充,更是救治现代性笼罩下的人本思潮弊病的良方。要而言之,儒家的人本理念强调,人的灵秀在于能够感知与践行人伦之理,而人伦正是使人区别于草木禽兽的特质。
一、儒家人本理念的伦理性特征
在儒家经典中,《孝经》是基于人伦之理而展开论述的一部圣人经典,其中有“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儒门典籍中类似的文句还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说苑·建本》)。对“人为贵”最通俗的理解,是将人与其他物种相对而言,即人贵于物,如唐明皇御注“贵于异于万物也”[1]33。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董仲舒对这句话有极为到位的解释: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榖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圏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天人三策》)
这段话主要是回答人如何灵贵于万物的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人之所以灵贵于万物,首先在于人拥有并按照伦理秩序进行生活,其次是人能够生养、管理、驯化其他物种,再次是人有自明自知的能力,即明于伦理的德性自觉。可见,人伦是人之所以区别于万物的首要特征。而人能够生养、管理与驯化其他物种,也是人将亲亲、仁民之理向万物的推扩,即试图以人伦之理的方式去治理与教化万物①儒家的这种伦理推扩,相对于庄子的“物化”而言,可以称为“人化”,即儒家讲万物一体是将万物进行人化的特点,而庄子讲万物一齐则更倾向于将人进行物化。相较而言,儒家虽然承认人性与物性同源,但更主张人要贵于万物。。虽然其中不可否认包含使草木禽兽为人自身所用的成分,但是从人伦出发的“爱物”势必蕴含着将万物伦理化的潜在因素,由此能够将万物容纳进文明圈层②至于第三层涵义人所独有的自明自知于伦理的德性自觉,更与儒家人本理念的伦理性特征息息相关,其实质是对人本理念的伦理性的本源追溯。这一层意涵在宋明的心学家那里获得极大的发明,下文会详细论述。。
《孝经》在“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之后,便与“人之行莫大于孝”紧紧连在一起,说明圣人之意正是以伦理性突显人贵于万物的特征。董鼎提出:“人惟不知孝之大也,是以失于自小;惟不知人之贵也,所以失于自贱。自贱则虽有人之形,无以远于禽兽矣;自小则虽有圣贤之资,无以拔于凡庶矣。此夫子答曾子之问,必先之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所以使人知所自贵而先务其大者。董仲舒谓必知自贵于物,而后可与为善,亦夫子之意也。”[2]董鼎突出人之所以能贵于万物的前提条件,在于人能孝亲;也就是说,人能自大自贵的原因并不在于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低,不在于囊中金钱之多寡,即以富为贵,而是以伦理美德作为人为大、为贵的决定因素。应该说,这与《孝经》中所体现的圣人之意是深为契合的。
在儒家的理解当中,人与万物一样均禀受天地之性,即人性与物性是同源的,那么为何人在伦理层面能够胜于万物,甚至可以极端笼统地说,人性贵于物性?关联于孟子所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孟子主要是从本源之性的意义上讲人性与物性相去无几,早在明代即有人提出疑问:“孟子道性善是矣,而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无乃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也?”[3]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的孟子所谓性善论,就人性而言应该问题不大,而物性是否为善?这在宋代理学家那里,主要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作为区分,那么可以说由于气禀不同而产生人性与物性的差异。物性中的不善者要甚于人性,由此认定人性贵于物性。
在基本否定“天命之性”与抛弃“气质之性”概念的清儒叙述中,以善恶价值作为人性与物性的区分,即人性为善,物性为不善,以此解释人性虽与物性同源但又贵于物性的原因。孟子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非人者即禽兽,如赵岐所注“无此四者,当若禽兽”[4]。“四心”作为人与物的区别,其本身具有善恶的价值,这也是厘定孟子性善论的重要根据。“四心”为善,故而清儒如焦循、刘宝楠等提出人性有此“四心”则为善,物性无此“四心”则为不善。
人之有男女,犹禽兽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无别,有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人伦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兽,禽兽不知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人纵淫昏无耻,而己之妻不可为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纵贪饕残暴,而人之食不可为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5]212
饮食男女人有此性,禽兽亦有此性,未尝异也,乃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者,人能知义,禽兽不能知义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则异于禽兽,心虽能知之而舍而去之,则同于禽兽矣。[5]378
这段话的义理思想可以追溯到董仲舒,所谓嫁娶之礼与耕耨之法,就是人能够按照伦理秩序进行生活,以及能够生养、管理与驯化其他物种。焦循对“性”的认识实际上已与孟子有所偏离,似乎更接近于告子或荀子。这应是清代对情欲的肯定所带来的结果,同时也是清代荀学复兴的一种体现。尽管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焦循仍然将“人禽之辨”的着力点放在人知伦理,而禽兽不知伦理,即以“知”作为判定人性与物性之善与不善的标准。“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之贵也。”(《荀子·王制》)焦循所谓“知”不仅仅是肌体发肤的知觉,更主要是一种对于仁义的认知,即德性自觉。人拥有德性自觉,故而人性善;禽兽没有德性自觉,故而兽性不善①清儒刘宝楠对人之性与禽兽之性的判别:“先儒谓孔子所言者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极本穷源之性。愚谓惟其相近是以谓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盖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则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禽兽草木无非是者。然禽兽之性则不可言与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孔子之说无异于孟子也。禽兽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谓善者以其同类而相近也。”当然,清儒反对者如俞樾,则主张人性与物性同源而皆有善有不善,人与物的区别在于才,人之才要胜于物之才,所以人之为善或为恶都会远远大于禽兽:“禽兽无人之才,故不能为善,而亦不能大为恶;人则不然,其耳之聪,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变,可以无所不为,故能役万物而为之君,配天地而参焉。若是者皆其才为之也,故方其未有圣人也,天下之人率其性之不善,而又佐之以才,盖其为恶有什伯于禽兽者矣。”俞樾基本上放弃了宋明儒者所关切的心性维度。[6-7]。
二、传统儒家的“自我”与人心之爱
清儒将人性理解为生物的自然属性,从而失去了儒家“天命之性”这一重要且具有超越意义的维度,但清儒仍然保留对“知”(德性自觉)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继承了阳明心学的精髓。从历史儒学的角度看,对本心之知的发明,无疑是由宋明儒者(特别是陆王心学)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时常与阳明心学联系起来,也有人考证阳明心学在历史上曾传入欧洲而推动了“启蒙运动”,但是陆王心学对本心之知所极力发明的功劳,是不应该被磨灭的,而且陆王心学所发明的本心之知其实深刻地蕴含着儒家人本理念的伦理性,这与传统儒家的人本精神并不相违。
孟子云“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现代的诠释者在理解这句话时往往侧重于“由仁义行”的哲学内涵,而忽略了“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这一重要前提。并且需要指出,仁义之美德虽然是基于对人伦之理的概括与总结,但是孟子这句话的“明”与“察”才是人能遵照伦理秩序进行生活的根本原因。“明”与“察”是人的一种自明自知于人伦的德性自觉,而人的身上拥有德性自觉之功能者,确切而言并不是性,而是心,譬如孟子讲的“四端之心”虽源自于性,但其实质仍是心。所以我们会发现,历史上重视心性的宋明儒者对“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德性自觉有很深刻的体认,展现了儒家人本思想中重要的心性维度。宋代心学宗师陆九渊专门作《天地之性人为贵论》云:
人生天地之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其为贵孰得而加焉?使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则谓贵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圣人之言为?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自拔,则其贵者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寖。……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举以事天地者,而必之于事父母之间,盖至此益切而益明。[8]
陆氏的论述确实体现了突显自我的特征,但是这种“自我”并不是基于对个体情欲的肯定的自我,而是指向孝事父母的伦理性与孝事天地的超越性的自我。因为人的情欲往往不是光秃秃的存在,而必然要附着于物,所以陆九渊作此文实际上正是为了批评逐于物质、逐于利益的自我情欲。当人出于情欲而逐于物质与利益时,人便沦为物的奴隶,于是所贵者是物而不是人,人身上的“良贵”也自此丧失。对此,明代心学家罗汝芳将人与动物作对比:“世言物莫贱于蛇,然蛇知潜修,多成蛟龙,其变化飞腾又万夫莫及矣。此无他,其性天本灵,而与人同贵也。故知悟觉在人,极为至要,能觉则蛇而可龙,不觉则人将化物。”②需要指出,心学家这种强调自我觉心的自愿自力倾向,应是受到佛教的较大影响,这也是对宋明心学需要反思的地方。[9]20蛇修炼成仙或成龙,自然是停留在神话传说,所以很难讲作为动物的蛇具有修炼的觉悟,然而人若丧失自知自觉的能力,即与动物无别。罗汝芳的弟子杨起元则从世俗的角度,提出:“人道至贵,以其不爵而尊。……民之所共贵者,有官之人也,然有官之人苟不兢业自慎、一罹于法,与罪人无别。是故贵不在位,而在乎兢业之心,是心不失,虽匹夫未尝不贵。”[10]235-236可见,对逐于物质、利益和名位的自我情欲的肯定,实则违背了传统儒家的人本理念,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需要着力反思与坚决批判的。
陆九渊所谓“良贵”可理解为良知良能,当剥除物欲与利欲之后,人的本心自然呈现。所以陆九渊生前讲过多次,“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所灵贵者,正是在于人的本心。对于这一点,不光是心学如此主张,朱熹其实也相对肯定陆九渊的观点,认为“信如斯言”③这是朱熹回答一位从陆九渊处而来的门人的话,其人有云:“他(陆九渊)只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人所以贵与灵者,只是这心。”[11]。朱熹弟子辅广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乃人之心也。……致吾心之爱与敬而已,故曰致爱则存,致悫则著。爱则心也,故曰存;悫则诚也,故曰著。存虽若存于内,著虽若著于外,然诚不可以内外言,故终之以著存不忘于心。著存不忘乎心,则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12]这是说,孝之爱敬均发于人的内心,存爱之心体现的是人本理念的伦理性,也正是这一方面获得心学家的格外重视,对心之“爱”的内涵具有极大的阐发与拓展。而著敬之诚则体现了人本理念的超越性,敬虽发于人的内心,但是此敬所著之诚却“不可以内外言”,意思是说人通过持敬的工夫,将人心接通于超越的天地之心,即《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孟子·离娄上》也有类似说法:“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概念,本无所谓纯粹外在,也无所谓纯粹内在,譬如传统儒家观念中超越的“天”匀布四处,我们凭借眼睛和耳朵在经验世界中是无所见闻的,但是“天”既在人之外的自然之中,又在人的内心里面,所以其超越性“不可以内外言”。
不过历史上整个儒学的发展,从先秦汉唐至宋明有一个明显的内在化倾向,即越来越注重人的心性维度,尤其是随着明代心学的全面兴盛。宋明儒者虽然没有否定天地的超越性,但实际上已然逐渐弱化超越的维度,直至一些心学家将天地完全收纳进入人心之中,从而导致阳明后学的流弊,原因就在于人心之爱的开启需要有对超越之天地的敬来激发②宋代心学家钱时:“《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即性也,天地万物皆于此乎出也。有天地而后万物形于其间,因指万物,曰天地之性,岂天地有此性而分以授万物哉?万物即天地也,无二性也,无先后之间、彼此之殊也,故曰明目视之不可见,倾耳听之不可闻,明此不可见闻之旨,可与言性矣。”钱时将天地与万物等同起来,消解了天地的超越性,而天地与万物的来源却是太极,如果我们将心学家所主张的本体视为本心的话,那么太极在心学家看来就是本心,所以天地与万物都能收摄于人的本心。这一点我在下文论及人文理念的超越性时会再展开。[13]。不过尽管心学家不是很重视人本理念的超越维度,他们为人心之爱的阐发所作的贡献,却是不应该被抹煞的。而将心之爱的意涵发挥到极致的,可以明代罗汝芳等人为代表。罗氏提出:“仁,人心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处安此心字?非心何处安此道字?故道虚而心实,心虚而人实也。”[14]罗汝芳的人本思想突出人的本心地位;而且我们还需注意到,他将本来具有外在特征的道收纳进入人心,再进一步将对抽象化的人心的认识转向具体化的人身,也就是其所谓“道→心→人”的步步落实。罗汝芳对人身的重视,应是继承自王艮而来的泰州学派重视身体的传统。而泰州学派重视人身的观念,应该说并非凭空捏造,“仁”字在先秦时期郭店楚简的文字书写中常作“”或“”,前者为从人从心,后者为从身从心,至少说明了早期儒家的“仁”含有“心”“人”“身”的义素。这种观念在罗汝芳的弟子杨起元的叙述中,则更为明显:
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全付于人,故真爱凝焉。人之初生也,一无所知,而爱由身始,肤发之间少有不遂,则哑然而啼,是真爱之所形也。由是而渐知此身之所根连者,而爱亲爱兄;渐知此身之所覆冒者,而爱君爱长;渐知此身之所贻衍成就者,而爱妻子爱师友。由是而凡所附丽此身、感触此身者,无所不用爱焉。爱若此其周也,皆所以自爱其身也,始于爱身,终于爱尽万物。此人之生德所以为全,而与天地一,故命之曰“人”,而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也。此见爱之为至重,而身之为至贵矣。[10]190
杨起元这段话很重要,应该受到重视。仁即天地生生之德,亦即天地生物之心,其由人所秉承,故曰天地之心在人心之中,体现为杨起元讲的“真爱”。这种源自天地之心的真爱使人在初生时已然形体俱全,并由婴儿的一声啼哭所体现。如此叙述自然是泰州学派很典型的特点,但是通过对人身形态的洞察,其实仍然隐含着较为微弱的超越维度,毕竟仍然能够注意到人心之爱是源自天地之心。只是泰州学派大多注重人心之爱的伦理维度,而忽略了与天对越的敬,从而认为人心之爱的开启是自发的,由婴儿的一声啼哭所自动呈现。由于人心之爱直接呈现出天地的生生之德,故人得以与天、地并称“三才”,此为人的可贵之处。而其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人心之爱,人心之爱其实就突显出了人本理念的伦理性特征。其爱从人身发端,指向与人身所勾连关涉者,包括亲人、君长、妻儿、师友等,所以可以说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人能够无所不用其爱,从爱其自身开始,到爱父兄妻儿与君师朋友等,推广到爱天下之身、爱万世之身③从爱身到爱亲,再到万物,其实很精准地表述了儒门孝道之爱的精义。也就是说,杨起元讲的人心之爱是人之孝德向万物推扩的一种体现,即如孟子所言“亲亲,仁民,爱物”。应该说这与《孝经》中圣人所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是深深契合的。。这堪称是儒家人本理念中的伦理性的极致发挥。
三、“气质之性”与人本理念的超越性
需注意到,杨起元所谓婴儿初生的一声啼哭,是天地之心的自动呈现,但是人心之爱在人的后天生活当中并不是源源不断地呈现,而人要使其能够呈现出来就需要依靠识仁工夫。那么,此处就体现了“学”的重要作用。杨起元说:“其不善爱身者,随物著念,随念忘身,愚者忘于利,智者忘于名,所忘虽异,其不能有其身,一也。等身耳,或能为天下万世之身,或不能有其身,善否若此,曷故焉?则学与不学异也。学者何也?学以求识夫仁也。……夫人之生德,凝之自性,而达之自学。”[10]190-191如果人的心念逐于物质、名利而渐忘其身,就会成为物质名利的奴隶,那么人身之贵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与上文所述陆九渊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人世间仍有善与不善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没有源源不断地开显人心之爱,亦即没有做识仁工夫。所谓识仁工夫,其实质就在于探求天地之心,即“达乎生德”[10]191。
至此,儒家人本理念就有两个重要面向可以揭示出来:一方面是由天地赋予人心的生生之德,另一方面是人以下学的工夫上达天地之心。那么可以看到,儒家人本理念除了鲜明的伦理性特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超越维度。先看下学上达的方面,传统儒家主张人贵于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能学。明代心学家许孚远明确指出:“天然自有之谓性,效性而动之谓学。性者,万物之一原;学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为其能学也。学然后可以尽性,尽已性以尽人、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而为三才,故学之系于人者大也。……先师孔子特揭学之一言,以诏来世,而其自名惟曰学而不厌而已。性之理无穷,故学之道无尽。学而不厌,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15]从天到人谓之“性”,即天命之谓性;从人到天谓之“学”,即下学上达,以尽心知性知天。由此看来,性与学是天人之间一来一往的反向关系,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天与人的关系才能完整,即人才能与天地并称“三才”。而天地之性的无限性与永恒性,决定了人的为学的无限性与持久性,以朱熹“理一分殊”的模式来讲,就是由格一事一物之理,到格万事万物的之理,乃至天地之理。此处即为人的为学的无限性与持久性的体现。可见,学的目的并不是简单获得科学知识,而是尽性,由尽己之性、物之性到尽天地之性,这是人有别于万物的特有能力,是人的主动性的极大发挥。所以许孚远的弟子冯从吾讲到“大学”的“大”要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才能彰显人独有的能学的巨大意义①冯从吾从其师说:“天地间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间惟有此学,舍此更有何事?问大学之道,曰‘大’字最当玩味。‘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生天地间,原都是大的,只因不学便小了。”儒家人本理念的重学重教传统,直至康有为仍有所体现:“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16-17]。
有学必有教,儒家人本理念中同样有着重教的传统。上文所引心学家的言论只是彰显孔子重学的一面,然而孔子在历史上更重要的是以“至圣先师”的形象出现,而这所体现的就是重教的传统。人通过教、通过学而成其为人,而能贵于万物,应该说教的作用在儒家的人本理念中完全不亚于学。教和学是相互相成之一事,如果说学是下学上达,体现的是人心之爱的推扩,那么教则反之,就是从天到人或从父到子的生养教化。在古代,对人直接产生教化作用的施教者一般有天、父、君、师四种角色②孔子自然也与教化息息相关。孔子禀受天命而成为“圣王”或“素王”,又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其自身的角色自然也就涵盖天、父、君、师多种,只是孔子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物,我们不将他与天、父、君、师这样抽象的角色概念并列。。其中对人的最根源的教化来自于天,而最重要的教化则来自于父。
天地生人,无所毁伤,帝王圣贤,无以异人者,是天地之性也。人生而孝,知爱知敬,不敢毁伤,以报父母,是天地之教也。天地日生人,而曰父母生之;天地日教人,而曰父母教之,故父母、天地日相配也。……古之圣人本天立教,因父立师,故曰资爱事母、资敬事君。敬爱之原,皆出于父,故天、父、君、师四者,立教之等也。[18]
天地的生生之德对于帝王圣贤,或者普通人,乃至禽兽草木而言,都是平等的,体现在所有人初生时形体俱全,“无所毁伤”。这一点既是心学家所着力发明的天地生德,也是理学家所主张的天地禀赋于人与万物者皆为天地之性。而在父母、君主、师长等对人施予教化之前,人在初生之后就知爱知敬,知道孝事父母,这就是天地对人的最根源的教化。这一天地之教的维度,常常被人忽略,“众人知父而不知天”,包括许多心学家都讲人初生时就能自动体现人心之爱,其实人心之爱与人心之敬并不是自动开启,也不可能自动就开启,而是需要依靠最根源的天地之教。那么,从这里也能理解虽然人与万物都平等地禀受天地之性,但人之所贵者在于人在初生之前即蒙受天地之教,有所教必然有所学,故而人天生拥有为学的能力。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天地所教的最本初的内容也是人伦之理,可以说伦理性是儒家人本理念的基本特征。天地与人之间通过教和学的方式接通起来,而这种天地之教在人看来无疑是以经验的方式所无法认知的,充分展现了天地之于人的超越性特征。超越性是儒家人本理念除了伦理性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甚至可以说,超越性是人本理念的伦理性的根基。从经文“天地之性人为贵”来看,人本理念的超越性直接与“天地之性”这一句的解释相关。毋庸置疑,我们极容易就能联想到“天地之性”是宋儒建构儒家心性论体系的重要支撑概念,而心性论又往往能够上升到宇宙论的层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儒家的人本理念是拥有宇宙论基础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即便是宋明理学将儒家的人本理念上升或追溯到天地之性的层面,却始终没有走到以神为本的地步;也就是说,天地对于人的主宰是有限度的,我们仍然有理由强调“人是目的”,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天地对于人的主宰集中体现在“生德”(以生物为心)的情况下。
所以宋儒所主张的“气质之性”就成为了“天地之性”之外的理解儒家人本理念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因为“气质之性”的设置十分圆融地解决了人与万物在共同禀受平等的天命之性的情况下,又能从宇宙心性论的层面解释人与万物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的本质原因。从而保证了儒家人本理念的超越性特征,即确保人不是一个无根的、“光秃秃”的个体,而是必然处于人伦关系当中,并且其背后拥有着天的根据。而尽管宋儒的“气质之性”的名称在晚明备受诟病,但是“气质之性”的概念无疑是宋儒极为精妙的一处心性体认。明末清初儒者对“气质之性”的非议主要在于批评宋儒的理气二元的架构,于是诸如刘宗周、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均主张先天的气质之性是纯然至善的,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作一物,其理由来自于以气作为本体,因为有理必有气,理只是气的条纹。这基本上可以说放弃了程朱所极为重视的理的真谛,无形中也消解了“天命之性”的概念。从历史儒学的角度看,明末之后的儒者逐渐丧失了天命之性的超越维度,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①可以试想,如果理气不能二分,即过度地强调有理必有气的话,那么就极有可能落入将理完全等同于气的陷阱。而当讲到的人性的时候,就会产生人性与情欲相混杂的现象。从明末清初之后的儒学心性论发展来看,确实包含着将情欲视为人性的理论倾向。这一点应该得到儒家学者的警惕。。
尽管明末清初的主流观点如此,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他的路径保证人性一元论的特质,晚明黄道周的人性论值得研究者重视。黄道周的人性一元论几乎完全异于同时代以气论为主的主流观点,他主张性就是性,气质就是气质,二者必须严分。所以黄道周实际上是保留了“天命之性”而否定了“气质之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气质之性”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凡是言说“性”字皆指“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则会受到后天积习的污染与遮蔽,所以世间之恶的来由就不是源自“气质之性”,而是后天的习染所致,此即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于是可以笼统地说,黄道周将宋儒的“气质之性”划分出气质与本性,气质与本性不可混同。如果仍以朱熹的宝珠与冷水之喻来说,朱熹认为宝珠是“天命之性”,宝珠与冷水共同构成“气质之性”,而黄道周则坚持宝珠自是宝珠,处在清水或浊水中其自身也仍是宝珠,于是将本性视为宝珠,气质作为冷水,纵是宝珠在冷水中也不可混同合称“气质之性”。黄道周由此否定“气质之性”概念的二元倾向,确保了人性一元论,即理的纯粹性,将气质严格摒除于性理之外,这实际上也继承了理与气二分的架构,甚至比宋儒更为严格。黄道周的观点之所以可贵,在于一方面像明末清初儒者确保了人性一元论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保存宋儒的“天命之性”这一重要概念②黄道周的人性论体现了对孟子性善论的坚守,并且他对历代儒者的人性论均有批评,对其所主张的人性论也有精彩的论析。拙文《黄道周对孟子性善论的坚守与诠释》有较为详细的论证,上述本文对该文的观点也有一定的补充修订。[19]。
本文以下对宋儒的“气质之性”概念的使用,将主要采取并且主张黄道周的修正方式,即把宋儒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视为先天的本性与气质,而人之不善则来自后天习染。人与禽兽草木都共同禀受平等的天命之性,但是人与万物之间确实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差别,宋儒对此差别的体认主要是主张人与万物之气禀的不同。从人与万物同具天命之性的角度看,“性则具足圆成,本无亏欠”,但是“今或以万物之性为不足以成之,盖不知万物所以赋得偏者,自其气禀之异,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性特贵于万物耳,何常与物是两般性?”[20]杨时在此所谓“性”是指天命之性,人与万物在本源上的差别在于气禀有正有偏,赋得正者即为人,赋得偏者即为禽兽草木。但是杨时一方面强调人与万物在天命之性上是同源,另一方面又主张孟子所谓犬、牛、人之性有不等,说的其实是“气质之性”,所以在讲“天地之性人为贵”时,实际上又陷入“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泥淖中①这是杨时与弟子李郁(字光祖)的问答记录,存于朱熹《论孟精义》。在问答之中,李郁还问道:“说气禀有偏正,自是容有不同,既说其体一,自是可反,何用更言‘气质之性’?”杨时则答曰:“当更思量,不可轻议他。”李郁所问其实可视为气自是气,性自是性,二者是可以分而言之的,不必偏要捏出一个“气质之性”的名称。而这个“气质之性”的概念问题,当时杨时也并无深究。[21]。
在儒学发展史上,“气质之性”的概念经由张载提出,至朱熹而获得极大的阐发,成为程朱学派心性论的重要支撑概念。这一概念无形中渗透到后世儒者对“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体认当中,几乎成为宋明理学家的确论。例如程门后学李衡参照人伦之理以观动物的行为,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当作两句读,宇宙之间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蝼蚁有君臣之义,雎鸠有夫妇之别,鸿雁有兄弟之序,仓庚有朋友之情,若此者岂非天地之性而人独为贵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22],意思是说个别动物也有部分合乎伦理的行为,但其所赋得天命之性是不全的,原因即在于受到气质的影响。再如元代吴澄作《孝经定本》,诠解云“人、物均得天地之气以为质,均得天地之理以为性。然物得气之偏,而其质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得气之正,而其质通,是以能全其性,而与天地一。故得天地之性者,人独为贵,物莫能同也”,也是同样道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吴澄在此明确将气质与性理相分,殊为难能可贵[23]。即便是陆王心学一脉的学者,虽能极力发明本心之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人与万物在本源上的差别在于气禀不同,如罗汝芳所言:“(人、物)分别则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觉与否,盖人则气清,能觉者多,物则气浊,而能觉者少也。”[15]20可见,在程朱理学的心性论框架下,气禀的理念一经确立,后世基本再无多少极为重大的阐发;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气禀不同是人贵于万物的根本所在,而对“天命之性”概念的保留也保持了儒家人本理念的超越性特征,此由杨起元一语道破:“‘天地之性人为贵’,言其命于天也。”[10]236
四、余论
对天命之性的重视,体现传统儒家对天地生生之德的崇敬。儒家的人本理念可以说是基于天地之生德的一种观念,《孝经注疏》所释“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贵也”,即突显出对天地之生德这一维度的发掘[1]33。晚明刘宗周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生也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所以事人也。……生可以该死,而溺于死之说者,反至于远生;人可以尽鬼,而溺于鬼之故者反至于远人,故曰下学而上达”,儒家从来没有放弃对死亡、鬼神的思考,但是对死亡与鬼神的思考建立在对生、对人的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深刻体现了儒家人本理念的重生重人的传统[24]。
将儒家人本理念的超越性特征追溯到终极超越者天地的层面,就应该有所止步,否则便极容易落入阳明后学的虚妄之弊。阳明后学对儒家理论的认识与阐发有时候极为精妙,但是当心学家走到将天地万物纳入人心这一步,就是产生虚妄之弊的最后一步。“程叔子以圣人为本天,本其苍苍者与?抑本其所以为天者与?若苍苍者则莫为之本矣,若天之所以为天则当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然则圣人之本天,舍人心又孰为本哉?《书》曰‘惟天生万物,惟人万物之灵’,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夫人之灵且贵者,以是心之出于皇降天命者也,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者此也,非心之外而别有天也。是心也,在《诗》曰帝,则在《书》曰皇极,曰天之明命,在《记》曰天理,在孟氏曰此天之所以与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聪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达诸伦物曰天叙、天秩,行诸政治曰天命、天讨。”[25]如果撇开胡直所言的心包天地的这最后一步,可以发现他对天的超越性的理解是十分精到的,但是心学家最终又将天地容纳入人心,形成了天人的倒置,从而产生虚妄的流弊。
总之,贵于万物的灵秀之人是天地对世间的最大恩赐。追逐于物质与名利、沉迷于死亡与鬼神,堪称是对灵秀之人本身的贬低,是一种人的自贱自欺的行为,同时也是对天地的贬低。对这一意涵,杨万里的阐发尤为高妙:
或问:“‘天地之性人为贵’,何谓也?”
杨子曰:“君子自尊其身,不敢自下于天地;自贵其身,不敢自贱于天地。非尊贵其身也,尊贵天地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