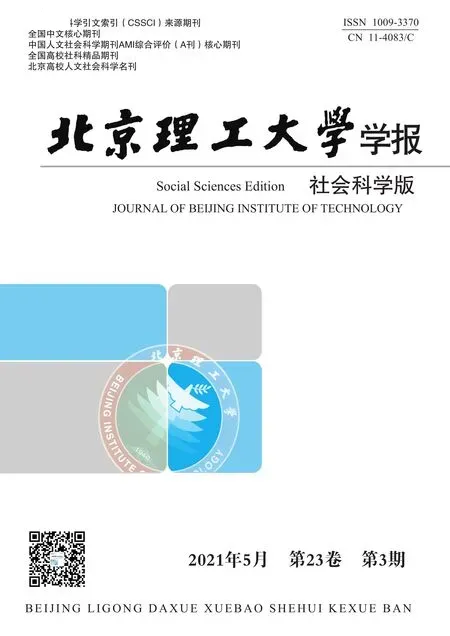演化解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发展
——结合联合国BBNJ谈判议题的考察
秦天宝 , 虞楚箫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两个着眼点
学界关于条约演化解释(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或evolutive interpretation)的争论一直存在[1-11]。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这种解释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什么情形下可以或应当进行演化解释,它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关于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关系等。在国际司法实践上,演化解释曾被国际法院①如 ICJ, 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Advisory Opinion of 21 June 1971, para.53; ICJ,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Greece v. Turkey), Judgment of 19 December 1978,para.77; ICJ, Dispute Regarding Navigational and Related Rights (Costa Rica v. Nicaragua), Judgment of 13 July 2009, para.66。、WTO上诉机构②如 Appellate Body of the WTO,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 Appellate Body Report of 12 October 1998, para.130; Appellate Body of the WTO,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WT/DS363/AB/R, Appellate Body Report of 21 December 2009, para.396。等广泛采用。早期,演化解释多出现于对国际人权、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条约的解释[7]102[12]205-206,209-211。近期,其在国际海洋法上,特别是对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关注[13-15],国内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则相对欠缺。
在国际海洋法领域,为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以下简称 “BBNJ 新文书”) 的政府间谈判进程是当前的热点议题。目前,BBNJ谈判已经进入到以文本为基础的谈判环节[16]。2019年11月,在第三次BBNJ政府间大会中各国达成的共识和所识别出的争议问题的基础上,BBNJ政府间大会主席编写了一份BBNJ新文书草案的修订版,其中囊括了很多有关BBNJ事项具体条款的表述的选择[17]。虽然现在谈判已经进入所谓的尾声,但各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尚未达成合意[18]。在此种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提出了在新文书中有目的性地使用模糊术语(ambiguous terms),包容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国内有学者将这种策略称为“建设性模糊”[19]。这种策略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新文书的生成,因为许多争议问题通过模糊术语都掩盖过去了[20]4。但是,从未来对这些条款的解释方面来讲,模糊术语的加入可能为未来对BBNJ新文书中某些条款的解释带来争议①关于语言的模糊性与条约解释的关系,参见李鸣.国际法的性质及作用:批判国际法学的反思.中外法学, 2020(3):810-811。。
在此种背景下,本文结合BBNJ谈判议题,围绕两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首先,考察演化解释在解释《海洋法公约》时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分析其对BBNJ谈判中仍具争议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的解决带来的启示和建议。其次,结合演化解释的使用要件,分析BBNJ谈判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日后可能对BBNJ新文书中相关条款的解释产生影响。在具体的讨论过程中,本文会强调这些因素与未来运用演化解释的关系。
二、演化解释的内涵、法理基础及使用要件
(一)对演化解释内涵的界定
关于演化解释的内涵,学界尚未达成共识[21]5。有学者认为,演化解释可以等同于当代意义解释。它是指“按照条约用语经过发展演变后的新含义,也就是条约解释或适用时的含义进行解释”[22]191。与之相对的是当时意义解释,具体是指“条约用语必须根据该条约原来缔结时所具有的含义进行解释”②当代意义解释也是国际法院前院长菲茨莫里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从国际法院的判决探究出的六项主要的条约解释原则之一。[2]82。还有学者则指出,演化解释只是当代意义解释的一种,它是指基于缔约者在缔约时的意图(original intention),对相关条约术语按照条约解释或适用时的新含义进行解释[3]163[8]443。在此种情形下,对该条约术语进行当代意义解释是为了体现缔约者在缔约时想要赋予该条约术语一种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含义的意图。另一种当代意义解释是基于缔约国的嗣后实践,对条约用语按照不同于条约缔结时的含义进行解释。这种当代意义解释被称为“嗣后行为解释”[3]163。它遵循的是缔约国的嗣后意图(subsequent intention),而这种嗣后意图是通过缔约国的嗣后实践或嗣后协议得以体现的[8]460。
上述两种当代意义解释方法在法理基础和使用要件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某些情形下,这两种解释方法还会带来解释结果上的差异[8]443-494。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两种解释方法进行区分。在本文的语境下,演化解释仅包括依照缔约国的原始意图,按照条约解释和适用时的含义解释条约用语。
(二)演化解释的法理基础
谈到演化解释的法律基础,关键是要厘清它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关于条约解释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③《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关于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进行条约解释应当遵循的规则,而且这种解释规则已经被相关国际判例确认为习惯国际法。ITLO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sponsoring persons and entities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 (Request for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to the Seabed Disputes Chamber), Advisory Opinion of 1 February 2011, para.57; ICJ,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Judgment of 20 April 2010, paras.64-65。。学界对这两者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争议[23]421,445[24]19。笔者认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由Helmersen[10]提出的。该学者指出,在理解演化解释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区分条约解释的要素(factors)、方法(method)和结果(result)三个概念。其中,条约解释的要素指的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中列明的“通常含义”“上下文”“目的及宗旨”“补充资料”等。解释方法则是指将上述所有(或部分)要素结合在一起,对条约进行解释的路径(approach)。而本文中的演化解释其实是运用条约解释方法对某些条约或约文进行解释而产生的后果④其他的解释结果包括静态(static)解释、扩张(extensive)或限缩(restricitve)解释、有效(effective)解释。某些解释结果之间不是互斥的,比如说,演化解释可能同时是扩张/限缩解释,也可能是有效解释。但这些解释结果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必然的。。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虽然规定了条约解释的要素和方法,但由于其用语的模糊性,依照这些要素和方法进行的条约解释可能带来不同的解释结果。具体而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规定条约解释应依其用语的“通常意义”进行解释。然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几乎所有实词的含义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在解释时到底是根据条约缔结时的“通常意义”进行解释,还是按照条约解释和适用时的“通常意义”进行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这一点上给予了解释者足够的选择空间[4]142[6]111[25]。同样,第31条第3款(c)项关于“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表述,也没有明确是指条约缔约时就已经存在的国际法规则,抑或是也包括缔约之后新增的国际法规则[26]279[27]281[28]。
国际法委员会指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关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的相关性都是建立在缔约国的意图之上[29]222。在一些情况下,缔约者会意图赋予一些条约用语一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含义。一些学者将这种意图称为“时间意志”[5]59或“时间意义上的意图”(temporal sense-intention)[30]54。这种选择背后更多体现的是缔约者想要确保国际条约灵活性的意图。通过演化解释,条约部分约文的适用范围会不断发生变化,以应对国际法与社会、科技等的发展。可以说,依照这种意图,按条约解释或适用时的“通常含义”和“有关国际法规则”进行的解释就可以被称作是演化解释。换句话说,演化解释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有关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两者并不冲突。相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演化解释提供了法律基础。
(三)判断是否可以使用演化解释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对于演化解释的使用要件,国际法院在“爱琴海大陆架案”判决中确立了由条约术语的“一般性”和条约的“无限期”性构成的使用演化解释的一般规则①国际法院在 1971 年关于纳米比亚国际地位的咨询意见中就对相关约文进行了演化解释,只是在该咨询意见中没有确立其在爱琴海大陆架案判决中所确立的使用演化解释的一般规则。国际法院在爱琴海大陆架案判决中所确立的该一般规则在2009年关于航行权案的判决中被进一步确认。此处对这两个要素的中文翻译借鉴的是曾令良教授 2010 年发表的一篇有关解释方法的论文中的表述。详见曾令良.从“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案”上诉机构裁决看条约解释的新趋势.法学, 2010(8):12。。判决指出,之所以要对1928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第17条中的“领土地位”一词作演化解释,是基于“领土地位”这一术语的“一般性”和该条约“无限期”的特性②ICJ,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Greece v. Turkey), Judgment of 19 December 1978, para.77。。
1. 条约术语的“一般性”
一般规则的第一个要素是条约术语的“一般性”。事实上,关于什么是一般性术语(generic term),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31]。国际司法机构在作出某些条约术语具有“一般性”的结论时,并没有充分阐释一般性术语的内涵。经常被学界引用的关于该概念的定义是由Higgins法官在1999年卡西基里和色杜杜岛案中提出的。按照该定义,一般性术语是指“一个众所周知的法律术语,当事方预期其内容将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③ICJ, 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 v. Namibia), Judgment (13 December 1999), Declaration of Judge Higgins, para.2。。这个定义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该法律术语的内容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事实判断);二是当事方预期这个术语的内容会发生变化(对立法者意图的判断)。但在笔者看来,既然判断术语是否具有“一般性”的目的是判断在解释该术语时可否进行演化解释,以体现立法者的意图,那么在具体的要素中再去探究术语内容的变化是否符合立法者的预期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笔者认为,判断条约术语的一般性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学上的问题,或具体而言是演化语言学的问题。其目的是判断一个条约术语的内容会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从语言学方面来讲,如果一个词的含义与社会、科技、经济等具有内在变化性的因素紧密相关,那么它的含义就很有可能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④一个词含义的变化往往是由“语言的外部要素”(language external factors)导致的。[32]4。这一观点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的报告中得到了确认。该报告使用了一个类似于一般性术语的概念——“开放或演化概念”(open or evolving concepts)。在具体的列举说明中,报告明确指出,“暗示了后续技术、经济或法律发展的术语”属于“开放或演化概念”,缔约方的义务会随时间而变化[33]415-416。
2. 条约的“无限期”
国际法院确立的一般规则中的第二个要素是条约的“无限期”。一般而言,为了确保条约的“无限期”,条约中的条款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条约抽象性的特点,在条约缔结之后,经常会发生缔约者未能预见的各种事态。在此种情况下,为了确保条约的“无限期”,对条约的部分条款就需要进行演化解释[4]143。
一些学者提出条约的目的与宗旨也是在判断是否应使用演化解释的关键要素[34]519。事实上,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体现该条约是否具有“无限期”的重要指标。这一点被国际法院在2009年关于“航行权案”的判决中予以确定⑤ICJ, Dispute Regarding Navigational and Related Rights (Costa Rica v. Nicaragua), Judgment of 13 July 2009, para.68。。在另一种意义上,判断公约是否“无限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裁判者的主观判断,而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为这种主观判断划出了一定的界限。
3. 条约的准备资料
上述提到国际法院确立的由两要素构成的判断是否使用演化解释的一般规则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批评和质疑。主要的质疑点在于通过这两个要素,解释者并没有探究缔约者的意图,而只是关注条约本身这一客观要素[35]136-137。可以看出,这还是回到了主观说和客观说这种传统的法学争论上。主观说和客观说争议的焦点在于条约解释到底是要遵循立法者在立法时的意图,还是遵循独立于立法者,存在于法律内部的合理含义[36]20-22。无论是主观说还是客观说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国际法的语境下,过于强调客观说而忽略了缔约者的意图是有违国家同意的原则的①有关演化解释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的讨论,详见刘雪红.条约演化解释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3):58-68。。不同于国内法的是,国际法,特别是国际条约的制定是以国家同意为原则。这些条约在根本上体现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家意志。如果脱离于缔约者意图进行条约解释可能会违背其背后的国家意志。因此,笔者认为,在国际司法机构确立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在判断是否进行演化解释时,还应当加入对能体现缔约者在缔约时意图的要素的考量。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条约的准备资料,亦即起草条约时的谈判记录、条约的历次草案等背景文件和讨论条约的会议记录等。如上所述,对某个条约术语进行演化解释应当是建立在缔约国的意图之上的。因此,虽然条约的谈判记录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仅被作为条约解释的一种补充手段,其在判断是否应进行演化解释时的分量则相对较重②这是因为,判断是否要进行演化解释需要考察缔约者的“时间意图”,而条约准备资料是确定这种意图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对于多边条约而言,考虑到条约准备资料的复杂性和不完整性等问题[37]15[38]1277-1278,在判断是否应进行演化解释时,并不要求找到缔约国明确同意赋予某个条约术语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含义的“直接证据”[31]101-102。只要从准备资料的“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断缔约者有这种意图,并且没有证据证明缔约者拒绝赋予该术语一种演化的含义时,在结合上述国际司法机构提出的由两要素构成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就可以对该条约术语进行演化解释。
综上,笔者认为在判断是否使用演化解释的问题上,需要考虑三个要素,而这些要素又能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条约整体的,需要考察它是否“无限期”,在考察的过程中需要分析条约的目的与宗旨;第二部分是关于条约中具体的需要被解释的条款或术语的,一是考察这个术语是否具有“一般性”特征,二是考察相关的条约准备资料以判断立法者是否意图赋予这个术语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含义。
三、演化解释是否可用于解释《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及其对BBNJ谈判议题的启示
结合上述提到的三个要素,接下来本文将判断演化解释在解释《海洋法公约》及其条款时可能发挥的作用。在判断能否对《海洋法公约》进行演化解释时,首先需要看它是否符合上述提到的第一部分关于条约整体的要件,即《海洋法公约》是否无限期,在考察的过程中,需要考量该公约的目的与宗旨。
(一)演化解释与《海洋法公约》
许多学者指出,《海洋法公约》全面规范了海洋法律关系,对海洋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编纂,建立了多元结构的新海洋制度,因此被誉为“海洋宪章”③一般认为,“海洋宪章”(a constitution for the oceans)的说法是由Tommy T.B. Koh主席提出的,这种说法也被大量国际法文献所提及。参见 Tommy T.B. Koh. A Constitution for the Oceans. President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另参见罗国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法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 2014(1):126。。《海洋法公约》是否无限期的问题与其“海洋宪章”的属性紧密相关。一般而言,对于这种宪章性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其解释过程中都要考虑条约缔结之后出现的新发展,以适应不同的新情况[39]131[40]131[41]165[13]566。在这层意义上,许多学者将《海洋法公约》称为“活文书”(living instrument),意指它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生长[14-15][42]。
关于《海洋法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在公约的序言中就明确了《海洋法公约》的制定体现了缔约各国通过该公约“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愿望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第1段及第4段。这一目的及宗旨由国际法院在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的判决中予以确定,ICJ,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19 November 2012, para.126。 对《海洋法公约》目的及宗旨的讨论,在 Robin Churchill,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edited by Donald Rothwell,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 Myron H. Nordquist et al,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A Commentary (Vol. I) (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461; 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A Commentary (C.H. Beck; Hart; Nomos, 2017), 9中有详细论述。。《海洋法公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距离现在已经近40年。它虽然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但其不能穷尽所有海洋法问题,特别是近4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43-44]。为了实现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愿望,对条约的解释必须纳入新发展的考量。
《海洋法公约》的属性及其目的、宗旨赋予了解释者很大程度上的灵活性。但是,为了确保《海洋法公约》构建的海洋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并非对所有的条款都可以进行演化解释。比如说,对《海洋法公约》中确立领海、专属经济区宽度等的条款,进行演化解释将会导致整个海洋法律秩序的紊乱。对哪些条款能进行演化解释需要进行个案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结合上述提到的关于术语的“一般性”和相关条约准备资料进行判断。
(二)对《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与联合国BBNJ谈判议题的关系
如同本文开篇所提及的,本文另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于联合国BBNJ谈判议题。因此,笔者将探讨通过演化解释1982年的“旧公约”(《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具体条款是否能对“新问题”(联合国BBNJ谈判中的争议问题)的解决提供法律基础或选择。之所以需要探讨《海洋法公约》条款对BBNJ谈判议题的影响,是因为联合国有关这次BBNJ谈判政府间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明确说明,谈判的成果必须与《海洋法公约》中的相关条款保持一致[45]2。
BBNJ谈判涵盖“海洋遗传资源”“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等多方面的问题[45]1-2。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主要讨论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构建问题。目前各国对该问题的争议仍然非常明显,特别是要不要对获取行为进行管制,如果要管制,该如何管制,以及是否要对利用这些资源产生的惠益设立惠益分享的义务,如果需要,是设立货币性惠益分享义务还是非货币性惠益分享义务等[18]7-8。为了解决各国不同立场的冲突,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以《海洋法公约》中与海洋科学研究有关的条款为基础进行下一步谈判的建议①详见第一次BBNJ政府间会议中欧盟在该问题上的立场,Elisa Morgera et al, “Summary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4-17 September 2018”, IISD - Earth Negotiations Bulletin, 第4页。BBNJ第四次预委会上,欧盟也曾明确主张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可以引用《海洋法公约》中第256条关于区域的海洋科学研究条款,第257条关于在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水体内的海洋科学研究条款。这一主张得到了Caricom和中国的支持。中国指出,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原生境获取(in situ access)应作为海洋科学研究的一部分自由进行。Elisa Morgera等.Summary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10-21 July 2017, 第 9-10 页。。在此种背景下,进一步分析《海洋法公约》中海洋科学研究的相关条款是否可适用于海洋遗传资源获取行为;以及如果可以适用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
(三)演化解释与《海洋法公约》中的“海洋科学研究”术语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探讨的是《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海洋科学研究条款在海洋遗传资源原生境获取(in situ access)活动上的可适用性问题。《海洋法公约》虽然没有给出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但通过对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得出的结论是,海洋科学研究是可以服务于商业目的的,但前提是商业利用不能是唯一的目的[46]5-6。海洋科学研究这一术语的通常含义和《海洋法公约》的上下文表明,在《海洋法公约》语境下的海洋科学研究还必须服务于“增进关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知识”的目的②例如,《海洋法公约》第240条b项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应以适当科学方法进行的一般原则与第244条有关公布和传播海洋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的义务都表明,在《海洋法公约》语境下的海洋科学研究是应当服务于科学目的的。。由于海洋遗传资源的原生境获取活动一般是既服务于科学目的又服务于商业目的的,所以该活动可能被大致纳入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③关于《海洋法公约》中海洋科学研究相关条款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可适用性问题的探讨,详见张小勇,郑苗壮.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适用的法律制度:以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可适用性为中心.国际法研究, 2018(5):15-34。另见Chuxiao Yu.Implications of the UNCLOS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Regime for the Current Negotiations on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of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第 9-10 页。。
然而,在考量该活动到底能否被纳入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时,还需要回答对海洋科学研究这一术语的内涵能否进行演化解释的问题。这是因为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在《海洋法公约》谈判时是不在缔约者的预期内的活动[47]155。如果对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不能进行演化解释,其含义自谈判到现在处于一成不变的状态,那么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这种新活动就不能被纳入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
笔者认为,对《海洋法公约》中海洋科学研究的含义是可以进行演化解释的。首先,海洋科学研究属于“一般性”术语。海洋科学研究的开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运用,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增进科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根据上文关于“一般性”术语的认定标准,可以推定海洋科学研究这一术语具有一般性的特征。
其次,《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资料表明,在该公约谈判时各国无法达成有关海洋科学研究含义的共识[48]444。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删掉《海洋法公约》草案中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定义的条款[49]26,并在《海洋法公约》中加入第251条,将关于定义的问题交由国家在该公约缔结之后,通过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的方式解决①《海洋法公约》,第251条。。
基于上述两点,可以推断《海洋法公约》缔约者意图赋予海洋科学研究这一术语一种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含义。因此在本文的语境下,关于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的活动可以纳入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条款因此也能适用于这种活动。
(四)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启示
首先,根据《海洋法公约》中海洋科学研究的相关条款,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也就是公海和海底区域,各国有权自由开展海洋科学研究活动②《海洋法公约》,第87条第1款f项;第143条第3款,第256条,第257条。。因此,在BBNJ新文书中,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原生境获取(in situ access)活动不应当设立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义务或通知(notification)义务。但是,根据《海洋法公约》第240条和第244条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条款,开展上述活动,相关国家需要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以及情报、知识的公布和传播的义务等[46]10-11。
其次,《海洋法公约》第244条关于情报和知识的公布和传播义务为在BBNJ新文书中设立有关活动的非货币惠益分享义务提供了法律基础[46]13。因为一般而言,知识的传播也算是非货币分享的一种重要形式[50]242-432[47]172。《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条款没有为缔约国创设任何货币惠益分享的义务,因此各国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也不负有货币惠益分享义务。
四、BBNJ谈判与对新文书(演化)解释的研判
演化解释作为条约解释的一种,它不仅可能在《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中产生作用,在将来还可能被应用于对BBNJ新文书(相关条款)的解释上。此次联合国BBNJ谈判是《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形成过程[51]5。一些学者已经论述过深度参与国际造法进程对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性[52]。在此种背景下,在谈判尚处于进行时的状态,对谈判中某些因素的出现(与否)及其对未来新文书中相关条款的解释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结合上述提及的使用演化解释的要件,具体分析BBNJ谈判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日后可能对BBNJ新文书中相关条款的解释产生影响。
(一)正式谈判与非正式谈判的运用
目前,BBNJ谈判中很多关键议题都是通过非正式会议进行的③在第三次BBNJ政府间大会上,对一些争议问题的谈判甚至是以“informal-informal”方式进行的。。这种谈判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为一些争议问题的解决提供更为轻松的沟通氛围。然而,它与正式谈判的主要区别在于正式谈判一般是有谈判记录的,而这些谈判记录在日后会成为判定是否要对新文书中某些条款进行演化解释的要件之一。因此各国可能结合自己国内的实际,选择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参与正式谈判留有记录,或是选择不在正式谈判中表明立场,为日后对该条款的灵活化解释和适用提供便利。
(二)BBNJ新文书中目的及宗旨的表述
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与条约的属性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些国家希望新文书在整体上具有“无限期”的特性,并主张在未来对其进行演化解释,它们可能会主张在新文书的序言中加入类似于“解决一切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的愿望”的表述。
(三)BBNJ新文书中目的性模糊术语的使用
如同本文开篇所提及的,欧洲一些国家提出了在BBNJ谈判中应用“建设性模糊”——在 BBNJ新文书中使用目的性模糊术语的谈判策略①关于目的性模糊的文献数量并不多,其中中文文献包括韩逸畴. 国际法中的 “建设性模糊” 研究.法商研究, 2015(6):171-179。英文文献主要包括Michael Byers.Agreeing to disagree: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 441 and Intentional Ambiguity. Global Governance: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2004(2):165-186; Xinjun Zhang.The Riddle of “Inalienable Right. in Article iv of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Intentional Ambiguit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 2006(3):647-662。。模糊术语的含义具有多样性,能包容国家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立场。因此,这种策略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新文书的生成,因为许多争议问题通过模糊术语都掩盖过去了。但是从未来对这些条款的解释角度来看,模糊术语的加入为演化解释提供了可能②有学者指出, “建设性模糊”能为国际法(包括规则的解释)随着时间和国家实践的发展预留充分的空间。韩逸畴.国际法中的 “建设性模糊”研究.法商研究, 2015(6):172。。这是因为这里所说的模糊术语跟上文所提到的“一般性”术语差不多是同一个概念。
具体而言,如果BBNJ新文书中包含下列术语,由于这些术语的属性,其解释就会有很大的空间:relevant(相关);sufficient(足以);the necessity(必要性);take into account all possible considerations(考虑所有可能的因素);interests(利益);the main stakeholders(主要利益相关者)等。如果一些国家想要限制未来使用演化解释的可能,那么就要尽量避免在新文书中加入这些模糊的术语。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国际司法机构在许多案件中使用了演化解释,但学界对这种解释的内涵、法理基础及使用要件目前还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国际法院确立的由术语的“一般性”和条约的“无限期”两个要素构成的一般规则是存在瑕疵的。在判断是否可以运用演化解释时,还需要考虑到有关的条约准备资料。
结合这些要件,本文提出对《海洋法公约》中的部分条款的解释是可以或有必要运用演化解释的。其中一个例证就是海洋科学研究这一术语的内涵。通过演化解释,《海洋法公约》及其与海洋科学研究有关的条款都得到了发展。具体而言,如果对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不能进行演化解释,《海洋法公约》中的相关条款就不能适用于BBNJ谈判的语境下,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提供法律选择。通过对《海洋法公约》中条款的一次次演化解释,该公约能不断获得“新生”,适应新的情形。
同样地,演化解释也可能被运用到未来对BBNJ文书部分条款的解释上。各国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确定未来在某些议题上是否存在立场转变的可能性,并通过选择谈判方式,选择新文书序言中关于目的及宗旨的表述,以及使用目的性模糊术语等策略服务于可能出现的立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