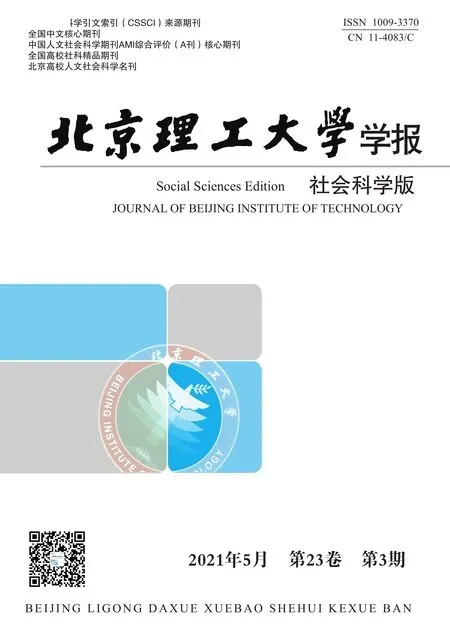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构建逻辑
龚向前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随着科技进步,全球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更加多样和广泛,但也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这必然不利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给生物多样性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与海洋划界、遗传资源等热点相比,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其中,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EIA,以下简称环评)作为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方案,在实践上充满不明确性,在理论研究上也明显滞后。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环境评价”的相关条款(第204、第205、第206条)尚缺乏具体的措施。对此,国际社会就完善和实施海洋环评规则开展了长期的研究和谈判,包括有关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 Biodiversity in area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BBNJ)新协定①2015年联大决议确认在该公约下就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BBNJ)缔结一项新协定,并要求研究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在内的议题。2021年初,第四届联合国海洋法大会又将展开讨论。,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海洋污染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凸显在各种区域性国际法律议程之中。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risdiction, ICJ)的判例表明,跨境环评的地位和意义逐步得到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认可。海底争端分庭曾认定,国际法院的具体裁决限于跨界环境影响,但其推理也可运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活动;所谓“共同资源”(shared resources)亦可涵盖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的资源[1]。作为国内法一项普遍的环境法制度,环评如何具体运用到“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或者只需简单地移植?
一、结合“国际软法”的程序主义路径
(一)作为程序性规范的环评义务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评的支持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评纳入国内法。作为一项民主、科学决策的机制,环评乃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程序,其主旨是对拟议人类活动和决策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调查、预测和评价,从而规范许可并防范风险。从表面上看,环评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实质上,“环评进程的作用不仅仅是收集和应用解决特定问题的科学知识,更多地是给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提供追求反映其特定利益的结果的机会。”[2]195在国际法上,这一点更为复杂,既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也存在着受影响社区与获利企业或群体之间的分歧,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
作为一项程序性法律制度,环评始终体现出一种自规制模式,通常并不确立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或标准。美国法院的一些早期判例指出,环评法规定的是程序性要求:相关机构应当履行评价和考虑环境影响的程序义务,而不是做出实体性标准[3]。当然,实体标准才是环境规制的主导形式,因此,各国的环评程序也日益结合了特定的实体标准,如有关空气和水质等标准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由于国际社会尚缺乏一个中央权威体系来制定和实施国际法,国际法的决策和实施背景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全球环境治理仍由国家主导。所以,环评的程序主义进路在国际法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在内的绝大多数环境条约仅仅提供一个促进共识的非常宽泛的环境目标;即便采用了实体性规则的领域,如《鱼类种群协定》(UN Fish Stocks Agreement)也只高度概括和抽象地涉及到环评的内容①京都议定书第13条要求缔约方会议“评估缔约方履行本议定书的情况及根据本议定书采取的措施的总体影响,尤其是环境、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其累积的影响”。。此外,环评制度本身也是国际法上合理注意义务(due diligence)的体现②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咨询案”中发表意见“…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 as a customary rule, has its origins in the due diligence that is required of a State in its territory.”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96 (I), p. 242, para. 29。。通常,缔约国一旦评价并通报有关项目可能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则满足程序义务,因为国际法意义上的环评本身并不能决定该国的项目是否或如何继续进行。
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所涉及利益的复杂性,将环评纳入一种程序主义的规制模式,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环评有助于扩大国家间就环境问题开展协商对话,而较少损益主权。这种实体规范上的程序性,并未损害环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首先,尽管环评并不具体涉及有关国家的项目或决策是否违法且造成了损害,但它往往包括一系列程序性的要求。例如,替代方案(措施)分析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际法上实体性标准的缺乏。在国内法上,合法性的争议可以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分权来解决。简言之,如果关于一项立法或行政决策是否合法存在争议,当事方可以诉诸法院。而国际法上并不存在这种分权制衡的体制。所以,对替代措施的检验,便事实上充当了一种国际法上的质询程序,促使启动项目(或决策)的来源国适当公开相关环境信息,照顾到相邻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在“阿根廷诉乌拉圭沿岸纸浆厂”案中,国际法院强调:程序性义务是独立存在的,即使最终未发生重大的越境损害,它们也可以被违反;同时,实质性的损害预防义务不是绝对的。相反,各国应努力防止重大越境影响时符合“合理注意”义务所需要适当的程序步骤,以避免跨境影响。这些程序步骤包括环境影响评价、通知或咨询潜在受影响的国家,等等[4]。而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裁定,由于道路建设计划确实触发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门槛,故不必审查哥斯达黎加是否有义务通知或咨询,因为它没有遵守其在一般国际法上应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5]91-97。
(二)“国际软法”充当环评的实体规范
国际法院或其他仲裁庭在判例中一再确认,如果各国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对越境环境(包括共享区域)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均应对拟议的项目进行环评。然而,《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埃斯波公约》虽然或详细或宽泛地规定了各国在环境评价上的义务,为协调处理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法律框架,但在环境影响评价的阈值(触发环评的门槛)上互不相同,因此在具体的项目筛选标准上也十分模糊,无法适应日益丰富多样的国际实践和不断发展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比国内法,国际法上的环评不仅在政治上触及到敏感的主权问题,也在技术层面存在各方面的难题。
例如,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裁定:“为履行在防止重大越境环境损害方面的合理注意义务,国家必须在着手对另一国家的环境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之前,确定是否存在重大越境损害的风险,因为这将触发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显然,国际法院将是否存在“重大损害风险”作为触发环评义务的门槛。然而,争议往往发生在是否存在重大风险,或者由谁来判定风险的存在或严重与否,以及开展的环评是否合格[5]91-97。一方面,国际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报告和专家证词,认为尼加拉瓜的疏浚方案不至于造成重大越境损害的风险,故不需要进行环评;另一方面,法院根据“项目的性质和规模以及实施的背景”,认定“哥斯达黎加的公路建设带来了重大的越境损害风险。因此,满足了触发道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门槛。”
虽然国际法院在此案中行使了自由裁量权,但仍未解答两个问题:(1)重大跨界损害风险是否存在;(2)开展的环评是否合格。对于国际法上的此类实体性判断,需要一种当事方都认可的规范或标准。然而,环评的具体实施规范与各国的经济水平和环保意识存在很大关系,故很难在国际法律文书中达成一致。因此,作为无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便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实体性标准的参照。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和原则》(Goals and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并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该文件直接提到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其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国家之间当计划的活动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环境产生重要的跨界影响时,制定互惠的信息交换、通报和协商程序”。
针对阿根廷认为乌拉圭未能满足《埃斯波公约》和《环境影响评价目标与原则》,国际法院指出,两国皆非为《埃斯波公约》缔约国,且《环境影响评价目标与原则》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不过,法院也指出,各国在依据其国内法来开展环评时必须履行“合理注意义务”[4]。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裁定中国发表的相关声明和报告“远不如其他国际法院和法庭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全面”;该仲裁庭强调,“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重要特征[6],然而对其对“全面性”的措辞语焉不详。这进一步表明,无论是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规范,均需要尽快确立国际社会接受的国际标准,从而明确最低门槛,避免任意性。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要求: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采取适当措施,要求就其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拟议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然而,如何判断“严重不利影响”和“合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则留给了2006年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包含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价自愿准则》。该准则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内容和7个阶段①这 7项包括:(1)筛选(screening);(2)范围确定 (scoping);(3)评价和评价(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4)报告(reporting);(5)审查说明(review of EIS);(6)决策(decision making);(7)监督、遵守、执行和环境审计。。事实上,“国际软法”的勃兴反映了一种对待国际法事务更加开放的态度,即:通过平衡不同的主体的利益,涵盖不同层面的合作与妥协,应对科学上不确定性较大的全球性事务。从晚近欧洲有关环评的国际判例来看,当事方可能希望依据《埃斯波公约》来裁决,但欧洲以外的“国际软法”文件,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南和世界银行有关政策等,在国际争端解决或诉讼中事实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7]。
(三)ABNJ环评的程序主义选择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海洋法公约》没有规定应统一适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②特别是,“矿山以外的海底活动(例如电缆和管道,海底设施,海洋科学研究,生物勘探,海上旅游)不存在这些要求;除倾倒和一些捕鱼以外的公海活动(例如航运,海洋科学研究,浮动设施(如波浪,核能,二氧化碳混合器));高的影响沿海国家外大陆架上的海上捕鱼活动(例如深海捕鱼对海岸带的影响)定居物种和资源,脆弱的底栖生态系统);外陆大陆架活动对公海的影响(如地震试验噪音);军事活动;海洋的新的或新兴的用途”。[8]。《海洋法公约》第206条措辞过于宽泛,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各国依据其自身能力和国内法来进行环境评价的框架。国际海底管理局、极地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不同条约机构,在环评问题上通过各自决策流程制定了不同的具体要求,从而不仅导致了规则重叠或不一致。而且,环评规则的“碎片化”无法综合考虑不同部门框架下不同活动的累积性影响。显然,发展全球性海洋环评规则,至少有三种选择:(1)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体系下,依据其第29条通过附加议定书;(2)在《海洋法公约》下通过一项类似于《基辅议定书》的“跨界环评议定书”;(3)列入《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文书。
不过,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科学性极强,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事务上,世界各国很难达成一项专门性的全球性条约。以累积性环评为例,由于累积影响途径和累积影响效应的复杂性及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累积影响评价尚未形成公认的原则和成熟的方法。不仅在一些国家存在实施困境,也并未纳入绝大多数国家法定范畴,即使是在累积影响评价工作已开展多年的美国和加拿大累积影响评价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不少问题[9]。《生物多样性公约》事实上选择了制定“国际软法”的路径。2012年该条约机构又公布了《海洋和沿海区域环评和战略性环境评价中考虑生物多样性时使用的自愿准则》,供同行审查,以便进一步完善该准则。
因此,BBNJ法律文书应进一步确立现有国际条约与判例中所明确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其中的核心义务是第204至第206条并于“直接或通过负责的国际组织观察、测量、评价和分析”环境影响或风险,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发布有关环评报告”的程序义务。当然,从世界各国环评制度的最大公约数来看,BBNJ国际法律文书除了明确协商、通知、公众参与等程序性义务外,还可以确立“重大有害影响”这一门槛值和“替代方案分析”这一核心内容。这种程序主义模式,更符合现实情况,也才可能让国际文书谈判取得进展。
从国际法发展逻辑来看,如果所要规制的风险有较大不确定性,程序规则占主导。只有当未来损害后果的高度确定性,则有可能发展出特定的实体规则。因此,关于具体技术标准,BBNJ文书只需规定一个“链接”,即在相关领域参照各缔约方所自愿接受的标准。基于条约义务确立“国际软法”标准,也更适合涵盖新兴的海洋开发活动,以规制那些尚未被有关部门性机制所规制的活动。例如,联合国大会关于海底捕鱼决议确定了针对特定活动而不是某种门槛的环评要求;针对气候变化问题,2010年第5次《〈伦敦公约〉1996议定书》缔约国会议通过了《海洋施肥科学研究评价框架》。该框架为初步评价海洋施肥科研项目建议提供了标准,并提供了详细的包括风险管理和监测在内的环评流程①包括初始评价和环境评价两个方面。其中,为通过初始评价和环境评价,拟议活动必须具有“适当的科学特性,包括履行接受“同行评审”等一系列严格标准。国家海底管理局“Polymetallic Nodules Regulations”等也确立了环境评价的义务。。
二、国家主导与国家自主决策的跨界主义模式
(一)国内法主导
在国际法上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最为理想的选择是,确立统一的国际规则、详细的技术标准以及主管的国际机构,成为协同各国行动的中枢。然而,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和信息化驱动的手段,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依赖于经济、社会上的可接受性和环境科技手段的可行性,故提出了全球环境治理上普遍存在的能力问题。如前所述,由于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自然禀赋上的多样性,各国关于环评的法律规定差别较大,特别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推进统一的环评标准尚面临能力不足等问题。自然地,各国仍将主导国际环评义务的具体实施,也即:通过国内法来规制跨境甚至全球性环境影响评价。
而且,即使订立了环评的国际标准,也必须在尊重国内法多元化的基础上确立适应性规则(adaptation rule)。换言之,尽量通过国内法确立的标准和程序来,才能应付实践中的问题。环评在跨境或国际层面实施起来将更为复杂,因为项目发起国更难全面获得境外乃至全球的环境信息,也难以对域外环境实行后续的监测和反馈,更无法取得国际共识。国际法院在“纸浆厂案”中曾指出:“由各个国家在其国内立法或项目授权过程中,决定每一案件所需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内容,考虑拟议开发活动的性质和规模及其对环境的可能不利影响”[4]。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国际法上有一项重要原则,任何国家的公法仅适用于其本国领土;反之,将其主权权利向域外扩张为非法。仅有两种例外:其一是规制国家管辖范围外全球公域的活动,如公海、极地等;其二是特定条件下允许域外管辖作为例外者②具体包括:(1)依据国籍原则,船旗国对其从事极地或海洋资源开发的公司的管辖;(2)保护性管辖,如一国对危及其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污染事故行使管辖;(3)普遍性管辖权,如损害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行为的管辖;(4) 被害人国籍原则。。如,美国国内立法和法院判决均承认环评制度的域外适用。自1979年美国有关环评域外适用的执行令发布以来[10],一方面引发了侵蚀东道国主权和实施困难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对发达国家基于域外管辖强化其跨国公司环境规制的希望。事实上,美国还通过其对外援助机构和多边发展银行来强化环评,并在判定是否进行域外环评需要综合对外投资、便利性和环保等因素。环评的域外适用进一步表明国内法的主导作用。
环评作为一项程序主义的制度,提供了利益平衡和转换的机会,以促使各国决策者能够考虑到相关的国际法义务,从而在国内政策制订上顾及不同国家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依赖国内法上的环评程序和规则,来解决跨境或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环境保护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模式,既表明了国家对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承诺,也通过将跨境或境外的环境影响等因素纳入国内决策进程,行使了跨国的利益协调功能,从而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起到实际作用。所以说,履行有关环评的国际法义务,既是由各个国家自主做出的应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也是由它们自主实施国内法的行为。
(二)国家自主决策权
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项评价拟议活动可能对环境的影响的程序”,涉及到服务两大利益攸关方的功能:其一是为决策者提供环境影响方面的信息,以便决定如何开展或管理该项目;其二是为受影响者提供参与决策的机制[11]。环评之所以从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上,最初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洲经合组织等基于非歧视原则引入跨境环境保护制度[12]。可见,在国际法上,决策者仍然应该是项目发起国,而受影响者(包括国家或居民)只是参与者;项目发起国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其他主体对项目是否实施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与当地问题的国际化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更经济有效的办法是适应当地决策进程,以便它们能够像处理类似规则的当地问题一样来应对跨境问题。”[2]195
从评价主体上来看,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些国家在关于BBNJ谈判的立场时强调受影响的公众(当地社区)应参与跨境海洋环评。《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每一缔约方须尽可能且适当地引入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并“酌情允许公众参与此种程序”。然而,尽管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国内法上具备广泛接受性,但国际法院在“纸浆厂案”中提出,有关各方并非《埃斯波公约》缔约国,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公众参与环评的指南无法律拘束力,因此,公众参与“跨境”环评并非一项法律义务。而在哥斯达黎加案中,国际法院则回避了这一问题。可见,目前,外国人参与跨境环评,主要见于欧洲地区,其他各国只须依据其国内法和习惯国际法来开展跨境环评。诚然,让外国人参与本国事务的决策,由于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过于超出国际关系的现实。
《海洋法公约》没有明确信息通报的国际组织,也没有提到应通报受影响国。对此,欧美一些学者主张在公约框架下建立协调、监督和实施海洋环境评价的国际机构[13]。然而,即便加拿大、日本、北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也强调国家在启动和开展环评以及相关决策方面的主导地位,拒绝接受第三方干预、拒绝该问题的“国际化”。主流的观点坚持“国家主权主导”和“依托国内环评”,因此,应充分顾及沿海国依据《海洋法公约》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非经沿海国同意,第三方不得对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进行环评[14]1-11。设立统一的全球环评评价标准和机构,不仅会加剧与现有不同国际条约和国际机构的重叠、冲突,也会过分超前于现有的海洋技术和环境评价能力。可见,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仍坚持国家作为环评的主体,故在《海洋法公约》下缔结新的国际协定时,应坚持这种自规制(selfregulation)模式。即便构建统一的环评国际机构,也同样应将重心放在促进包容性参与、信息通报和决策者之间互动,进而基于程序义务维护各成员国环评上的自主权。
当然,随着全球化促进相互依存,跨政府规制管理的范围和形式的急剧扩张,公私混合型机构实施的规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样,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许多规制决策需要从国内层面转移到全球层面,各类非政府组织、国内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参与决策。当前《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有关环评规则设计的挑战是,如何确立一种知情决策的完整的评审程序。其中,独立专家评审的同行评议中,不同国家代表的组成人数、投票机制非常关键。无论如何,《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开展环评,仍将坚持国家主导和国家决策的原则。
(三)基于“影响导向”的ABNJ适用范围
众所周知,海洋是较为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涉及全球公域的环境治理,需要重新思考国家责任以及国家管辖权的理论。一方面,不对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进行保护,领海或专属经济区难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不可想象,如果不对各国管辖范围内海域进行管控,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环境可以得到保护。因此,中国可考虑基于属人管辖或船旗国管辖,将国内法上环评规则统一适用于国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一切活动。这既将使中国成为一个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来统一规范领海洋跨界环评,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我们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通过适当扩展全球公域管辖权的方式来强化其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治理,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盼和整体利益。
如果我们在海洋环境行政执法权上予以统一适用,则无须再区分所谓“国家管辖或管制的海域”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有关环评的适用范围上,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如下两种方式:(1)“活动导向”是基于项目开展的地点而非环境所影响的地点确定环评适用范围,即:国际法应只调整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活动,而不论环境影响涉及到的其他区域(包括一国领海或专属经济区);(2)“影响导向”则基于项目所影响的区域而非开展的地点,即:国际法应涉及所有影响到国家管辖范围内外海域的活动,而不论项目开展的位置是领海或公海[15]。“环境影响评价应限于在国家管辖外海域实施的活动,排除沿岸国管辖范围内海域进行的活动”[14]1-11。然而,《海洋法公约》第206条并未对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和国家管辖外海域进行区分;一些地区性的海洋条约也在适用范围上同时纳入“陆源污染”;而且,至少国际法并未明确禁止域外管辖的模式。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且特别规定了“域外适用”:即在管辖海域以外,排放有害物质、倾倒废弃物等,造成管辖海域污染损害的,也适用该法。
全球公域环境治理是考验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典型领域之一。确立基于“影响导向”的国内法适用模式,将国内法上的环评规则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全球公域,既能扩大国家主权适用范围和管辖权限,又强化了各国保护海洋环境上的“合理注意义务”,且实际上巩固了各国基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自主决策权。因此,这既是贯彻国家主导和国家决策原则的重要方式,也可促进环评的国际合作。实际上,虽然中国法律并无进行跨界环评的要求,一些从事跨国项目经营的企业,已开始自愿开展跨境的环评①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为主建设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就通过招标请泰国IEM公司对项目进行了环评。。根据最新发布的《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则》,“加强对国际海域和极地的环境调查与评价。”中国最近几年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立法步骤②包括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的《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和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此,国家海洋局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配套法规,包括《南极考察活动环评管理规定》和《北极考察活动行政许可管理规定》。这些文件均涉及到中国管辖范围内海域与极地等国家管辖外海域。。其中,《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申请,应当提交环境影响报告。这实际上就是国内法在全球公域的适用。当然,这仍然需要进一步制订相关细则③与南北极的立法相比,中国在深海采矿上雄心勃勃,以增强作为全球金属供应国的主导地位,但尚未通过立法明确深海采矿环评的具体程序。这与深海采矿在商业上和科学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有关。,明确将要面临的法律挑战和政治约束。
三、区域性主义路径与全球性机制的互动
(一)欧盟法上环评规则的突破
早在20世纪70年代《海洋法公约》尚处于谈判阶段的时候,“海洋区域主义”便受到关注,并逐渐从是否需要在全球性公约中确立区域性规则,过渡到探究各个区域的合作机制。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全球性机制与区域性措施的互动关系[16]。显然,特定海洋区域有其独有的自然禀赋与生态功能,故全球性机制要具体地适用于不同地理区域和自然条件,离不开区域性条约的进一步规定。《海洋法公约》包括一项有拘束力的环评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环评义务在所有海洋区域适用,但两公约均提出了区域性办法的必要性。事实上,早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影响评估的目标与原则》这份国际文件中,就提到:“各国应努力缔结双边、地区或多边协定,以便在适当情况下基于互惠原则,就其管辖或管制下的活动可能给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造成重大影响的潜在环境影响,提供通报、交换信息和达成一致的磋商”。
这种发展首先来自于《埃斯波公约》及其《基辅议定书》与欧盟环评立法④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环境合作附属协议》及1991年《美国—加拿大空气质量协议》均确立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原则。。《海洋法公约》第206条确立了“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污染或重大和有害的变化”作为环评的阈值。这与《里约宣言》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确立的“重大负面影响”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埃斯波公约》和欧盟《环境影响评价指令》除了坚持“重大影响”的阈值外,还均以附件形式确立了“活动清单”或《范围界定指南》,以及如何判定“重大不利影响”的筛选标准。然而,欧盟指令、《埃斯波公约》和“北美环评协定”草案均较大地尊重各国主权,即:不确立统一的环境目标;由国家当局决定是否需要环评。可见,接受环评国际法规制,并不否定前述的国家主导和国家决策原则。
《海洋法公约》第206条并未明确“环境评价”是否同时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和“战略环境评价”,也未考虑“累积性影响”。而《埃斯波公约》之《基辅战略环境评价协议》,则要求对可能有包括健康在内的重大环境影响的“规划和项目草案”,开展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t, SEA)。同样,欧盟《战略环境评价指令》,要求对“规划和计划”开展环境评价。在当前谈判中,欧盟等区域性组织和国家要求以《埃斯波公约》及《基辅战略环境评价协议》为基础来解释“环境评价”,即:包括“环境影响评价”与“战略环境评价”两方面,并纳入累积环评。这种主张应从条约“演化解释”来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①基于"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包括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以及条约之“目的和宗旨来解释”。WTO上诉机构认为,“可用竭自然资源”这一术语不能仅限于非生物资源,而应被解释为包括海龟在内的生物资源;国际法院在有关“商业”这一术语是否包括“乘客运输”的问题上,也采用了演化解释的路径。。不过,尽管越来越多国家立法纳入了“战略环境评价”,一些欧洲国家根据区域国际法义务也着手开展对国家管辖外海域的战略环评,即便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也并未明确接受海洋战略环评,要将其扩展到极地深海等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就更难了[17]。
同样,基于非歧视原则,《埃波斯公约》要求域外受影响的国家和居民也参与等同于来源国及居民的环评程序。不可否认,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法公认的价值基础,公众参与和透明化乃是21世纪国际法发展的趋势,“公众参与环境评价”已经是各国环评制度的必要因素,并纳入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和海洋环境保护国际文书之中。特别是,尽管存在模糊性和争议,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公众、非政府组织和本地团体的参与作为环评的必要程序。然而,公众参与跨境或国家管辖外区域的环境影响评价目前具有不可操作性的问题,故只能作为一项无拘束力的政策倡导。如前所述,国际法院相关判例也对公众参与跨境环评持谨慎态度。
(二)区域性海洋环评制度的发展
国际法意味着国家主权权利的“交易”,国家让渡部分权利,亦获取部分权利。如果涉及具有直接利益的区域且周边国家经济社会水平相似,各国呈现出承担更大义务的意愿。如今,绝大多数区域性海洋条约都有关于环评的特别条款,确立了更加具体的义务。如,《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沿海区域公约》(《巴塞罗那公约》)的《倾废议定书》规定,地中海地区环评文件必须包括“环评的方法”“对环境(含动植物及生态平衡)的影响”等等“旨在减少对拟议活动环境影响的措施”。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公约》和1995年《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海岸带保护公约》对成员国提出了环评的要求;2012年《保护和发展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公约》还提出了订立“跨界环评议定书”的草案;《保护里海环境框架公约》正在协商制订《环境影响评价议定书》②Article 17 para. 3 of the Tehran Convention requests Contracting Parties to “co-oper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tocols that determine procedur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Caspian Sea in transboundary context”。。
相比《海洋法公约》,这些区域性海洋条约在环评制度构建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在公众参与跨界环评方面,《海洋法公约》未作明确规定,而区域性海洋条约通过具体明确的规定而有所突破。《巴塞罗那保护地中海公约》第15条要求缔约各国对公众发布有关环境状况的信息,并确保公众参与决策的机会流程,除非涉及诸如保密、公共安全或调查程序等情况。《保护和发展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公约》之《陆源污染和活动议定书》不仅要求缔约国将环境评价信息通报受影响的缔约国并与之磋商,而且进一步要求各方应根据其国家法律促进公众获取信息以及公众参与大加勒比地区污染决策过程。《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公约》规定,“各方应邀请:(a)公众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发表评论意见;(b)可能受影响的缔约方,与其磋商后提交评论报告。评价的结果应当提交公约设立的委员会以便利益相关方获取。”
与此同时,深海极地的环评制度也向前迈步。如《南极条约》选择在其《马德里环境保护议定书》中确立了更加严格的专门性环评条款,将阈值提高为“轻微或短暂的”(minor or transitory impact)的影响。在《南极条约》体系下,如果当一项活动可能超过“轻微或短暂的”标准时,则环评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EIS)将在《环境保护议定书》缔约方之间传播,以征询意见,经由咨询科学委员会(环境保护委员会)评价后送交“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南极条约》理事会机构)批准①根据《南极条约》之《环境保护议定书》,当一项拟议活动可能至多只有轻微或短暂的影响时,船旗国是最终的决策权威。。《北极环境影响评价指导纲要》(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Arctic)则以“国际软法”方式确立环评要求。此外,根据《海洋法公约》第145条,海底管理局应制定适当规则、规章和程序,以保护“区域”,故深海环境评价的国际立法也在讨论之中。国际海底管理局已发展了一套强制性采矿环评的规章,重点是采矿的勘探阶段,以及评价深海采矿潜在影响的环境法律框架。
(三)ABNJ环评机制的渐进原则
区域主义路径针对某个议题的实践,将为克服全球性海洋治理规则和制度的模糊、低效和不健全之处注入经验性动力和解决方案[18]。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承诺,中国应积极参与ABNJ环评制度的法律化,尤其是确立其程序性保证。笔者认为,中国可主动适应区域性海洋环评的发展趋势,占领新的国际道德制高点,并以渐进式方式推动法律文书的谈判签署进程。如前所述,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在关于国际海底采矿的咨询意见案中也重申:针对“共享资源”开展环评,不仅仅是成员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6条下的义务,同时也是国家在习惯国际法下的义务。其中,中国可在门槛上坚持“重要性标准”,但可有条件地接受谨慎方式(precautionary approach),即:如果存在“重大损害风险”的某种证据,即便风险不确定也须进行环评,条件是以美、日曾经联合提出的所谓“以最佳的科学证据为基础”作为折中方案[19]。
中国强调海底商业开发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取决于全球经济和金属市场总体形势,并涉及复杂的制度安排、法律责任,呼吁按照协商一致和渐进的原则制定扎实的开发规章[20]。因此,在一些具体的规则设置上,则应遵循渐进原则,即:在确立清晰的环评程序基础上,技术性规则由“国际软法”调节,逐步促成共识;关于环境目标和具体实施则坚持国内法主导和国家自主决策原则。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附属的专家咨询机构法律和技术委员会(LTC)发布了环评建议,涉及到有关专家评审机构的组成,以及公众的范围,虽然有待法律的进一步澄清。所以,对于BBNJ文书中有关国际机构的设置,可将其定位为一个科学和咨询机构,承担协调和建议等辅助职责。当前的争论焦点还涉及,如何在纳入独立专家评审和公众参与这两个被公认为“最佳实践”的程序步骤[21]?如果遵循渐进原则,则可先确立专家治理机制,留待将来关于公众参与的更多共识。
目前中国周边海域尚不存在明确规定环评的国际规则,只在一些相关的宣言、指南等软法性文件中提及。因此,中国应在区域性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发挥引领作用。首先,中国应发起南海环评合作,将信息通报、磋商等有关程序纳入到相关的多边条约之中。例如,南海沿岸国家大多存在重叠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符合《海洋法公约》第122条“半闭海”的定义,因此,根据第123条“应互相合作”,并“应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对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环保和海洋科学研究三类事项进行合作。然而,至今仍未有一个专门针对南海渔业资源养护或综合性生态环境管理的区域性组织[22]。
中国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环评技术和能力优势,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对域外实行后续的环境监测和反馈,从而获得更多区域性海洋环境信息和数据,也为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作出贡献。1985年东南亚国家联盟《自然与自然资源养护协定》草案第14条曾规定了环评条款,但至今未获得签署、生效。即便泛南海各国将来签署《埃斯波公约》,也无法解决过渡捕捞等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环评问题[23]。虽然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并没有要求跨界海洋环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如果可能对邻国或邻近海域造成重大损害,也没有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例如,根据《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准则谅解备忘录》,中国及其他缔约国明确而直接地在国际河流合作中承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②1995年,中国、蒙古、朝鲜、韩国和俄罗斯在纽约签署了该备忘录。其第1. 2条规定:缔约各方将进行联合(定期更新)区域环境分析,对经反复研究的整体地区发展规划在当地、国家、区域以至全球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联合制定区域环境调节与管理计划,以防止调节对环境的危害,基于区域环境分析及其他相关数据促进环境的改善。。此外,中国还可通过亚投行审查机制将资金支持、技术转移,推进相邻各国在确保环评信息透明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换所机制,并定期开展审议,以提高周边海洋环境质量提高。
四、结语
国家有义务确保自己管辖或控制下的行为不对其他国家海域或者国家管辖控制以外公共海域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国际法上的环评制度正不断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程序主义和跨界主义的特征。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境评估的制度构建,中国应坚持以对《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环评条款的合理解释,作为构建BBNJ国际协定规则的出发点。首先,BBNJ法律文件应进一步明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性义务,通过提取国际立法的最大公约数确立基本的要素,如将“重大影响”界定为启动环评的阈值,明确通报和磋商等义务。对于有较大分歧的事项或技术标准则留待“国际软法”规制。其次,对于环评的具体实施和审批,应坚持国内法主导和国家自主决策的原则,在国家环评适用范围上,或可考虑“影响导向”的模式。再次,中国适应区域性环评制度的演进趋势,推动国际海底区域等ABNJ环评制度激进式发展。
中国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亚太海洋共同利益的维护,故应在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双多边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可借鉴区域性海洋环境制度的新发展,结合周边区域经济技术水平和海洋环境的特征,以海洋环评这一程序性义务为突破口,促进各国在环境信息上共享和环境执法上的合作。周边国家在推进跨界环评上已具备一定法律和政治共识,一些国家是《埃斯波公约》的缔约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在考虑环评合作。可以考虑将海洋环评纳入区域性海洋事务谈判议程之中,在不损害国家主导和国家自主决策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与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跨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图书借阅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