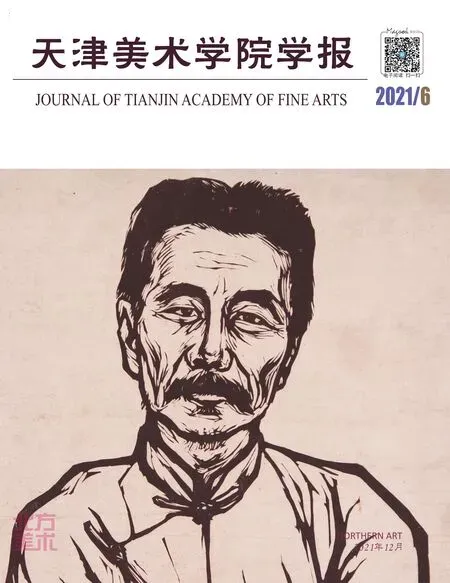“整理国故”与中国近代美术发展方向的影响研究
在美术学界,“整理国故”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使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呈现两种方向发展。而以刘海粟、林风眠等为代表的所谓现代主义美术大家,我们则不能简单地将之理解成为新文化运动下、徐悲鸿现实主义道路之外的西学对中国传统美术的改良改造,从而与陈师曾、黄宾虹为代表的中国“新传统文人绘画”截然区分开来。不管这种带有西方现代主义标签的绘画风格在表现形式上与中国传统的美术国故如何冲突,但其理念是一致的,都是以发扬“中国本位文化”为己任的,是与中国美术“整理国故”中的科学意识、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海粟、林风眠等人,与陈师曾、黄宾虹等的传统绘画,都是中国美术“整理国故”运动中的一体两面,这也使中国近代的现代主义美术之路与西方提倡“完全打破”的革命性艺术观有着质的不同。
一、“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小考
1919年,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但整理国故的实践活动,包括美术国故的整理,却要远远早于斯。“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是古籍整理,其核心在于体现和挖掘古籍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1],被认为是对中国近代古籍的一种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美术界,主要表现为美术史家对美术古籍理论的整理研究和对本位文化的保存弘扬上。保英在《丁丁画报》发刊词中说:“古法非不善也,特时代不同,趋向各异……,要使国粹发之欲明,扬之欲高。”[2]但是,“国故”确如曹聚仁所说,“处于闭国期,无‘国故’之名,隐含对抗之意”。它一方面因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被新文化中的唯物史观派大加鞭挞,称为“昏庸已极”,但是另一方面,其提出“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科学精神”,也得到了唯物史观派的认同。如李大钊、范文澜、郭沫若等都认为要以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承认国故有很高的价值存在。叶圣陶则在《国故研究者》中把国故研究进行区别,他认为研究国故的人可以分两类人,一类是有相当素养的,有检察态度的国故研究者,一类只是翻翻旧书,莫名其妙的,以“持有旧书证”为圭臬的“国故虔奉者”。[3]
新文化运动中唯物史观派是在与国故学派为代表的其他传统学派的互动与斗争中,展现了对社会守旧文化的巨大批评力。在美术学界里,表现为唯物史观派陈独秀掀起了“革旧立新”思潮,提倡中国画要采取西画写实精神,与康有为的“改良”论一起,重新审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开始注重写生、学习中西、博采众长的美术改革之路。但是,纯粹从学术研究的视野来看,唯物史观派其实是为了在学术方面占领思想阵地。1923年,郑振铎在《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一文就说,唯物史观派认为“提倡国故运动”是对新文化的一种反动。[4]也如王存奎所说:“新文化运动(唯物史观派)在理论方面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这些批判多是对类似‘阴阳符瑞’,‘一地风水’等‘吾国之俗’的文化现象的批判。”[5]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国故整理”更多是以一种价值功利性的口号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有着更鲜明的社会政治学特点。
二、国故学派与唯物史观派以科学精神对待“中国本位文化”的态度差别
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唯物史观派,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国故派,包括实践着“整理国故”精神的研究学者,都奉“科学”为圭臬。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6]对于在美术研究上运用科学,1919年10月,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中也说:“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7]唯物史观派代表陈独秀,则以一种“艺术理想”的姿态,以“断不能不采取西洋画的写实精神”[8]的科学实用主义精神,以“推动中国绘画走向进步之途”,认为在近代美术发展的道路上,“革命”是必须经历的手段和方式。[9]
而国故学派在具体实践中,要求远离社会现实,埋头古书堆,对于处于危急存亡的国难时刻,如前文所述,也确实有其诟病之处。所以,在1919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整理国故”便成为被炮轰的目标。毛子水严厉批评研究国故“抱残守缺”,傅斯年随后批评“追摹国故”者真的是愚不可及。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1924年《中国青年周刊》发文把“整理国故”者定义为一种反动黑暗势力。[10]1927年,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再发《再进一步消灭国故》一文,说要把国故“一船一船地拖向太平洋,丢到海里去……好叫他们忘洋兴叹,大哭一场”[11]。在1928年后,胡适也开始意识到国故运动在当前时局中的历史局限性,他劝青年人不要跟着一起向故纸堆去乱钻。
三、新文化运动唯物史观派与国故学派思想形成中国近代美术的两种发展方向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无论是科学技术、政治模式、伦理纲常,还是文化艺术、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先进与落后与否等,都不是仅靠“科学”这一个“赛先生”就可以决定的,关于如何对待中华民族基本人文精神出现了不同主张,新文化运动思潮出现了严重分歧。由康有为的“改良”论到陈独秀的“革命”论的中国美术发展道路,实际是由徐悲鸿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画家完成的。而国故学派“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科学精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保国”“保种”的强烈使命感和对中国自身文化的自信,“不亢不卑”(刘海粟语),在美术实践上则是由另外两类美术家来完成的。一是由陈师曾、黄宾虹等“文人画家”以传统绘画的方式,做着整理美术国故的努力,在西学东渐的大环境里甚至背负着一种“守旧”的压力,另一部分则是由刘海粟、林风眠等为代表的一批贴有“西方现代主义”标签,却处处弘扬中国国故精神的美术家来完成的。
徐悲鸿以科学写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绘画中,基本摒弃了中国绘画的文人画元素和格调,不管是在油画中表现的中国古代题材,还是用中国笔墨纸砚来描物画像,表现出来的都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的功用性精神”而不是中国东方本位的文化精神。而对中国本位文化念念不忘的则是刘海粟、林风眠等美术家,在刘海粟大量的艺术论述里,都充满着对“中国本位文化”的自豪感,在1934年1月24日的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开幕典礼上,他说:“中国的绘画,卓然在世界艺苑独树特帜而领有东方全域。……故欲观东亚近代之艺术,必须注重于中国。”[12]在对待元四家的态度、对美术写实的态度上,也与康有为的“归罪于元四家也”、陈独秀“断不得不写实也”断然不同,他在《昌国画》一文中说:“元四家以其高士逸笔,大发写意之论,其作品思想,不期而与现代欧西之新艺术相合。”[13]
这种对传统文人画的肯定和胡适的“整理国故”“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思想,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当时有很多美术学界传统文人画士,已经在践行着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和精神。譬如具有传统教育、具备坚实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又受日本近代科学知识与教育体系培养的陈师曾,除了整理大量的美术文献外,他在《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的讲演中,讲到对于美术国故的态度:“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14]周作人认为陈师曾的画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但与吴昌硕的绘画色泽浓艳、齐白石的绘画意境淳厚朴实相比,陈师曾的绘画更具有文人的书卷气。而黄宾虹对于国故整理实践,也是不遗余力, 他自民国任《国粹学报》编辑并任神州新闻时报社记者,积极组织各种团体社刊, 出版发行美术国故文献, 对美术国故的弘扬与保护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
对于美术国故,一方面是陈师曾、黄宾虹等美术史家以传统的方式维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坚守着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础阵地,另一方面则是以刘海粟、林风眠为代表,以发扬国粹为己任,不失民族基本文化精神,把中国优良的传统美术国故精神自信地推向现代主义绘画前沿,推向世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面貌。
四、现代主义美术道路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在近代,现代主义美术道路,如前文指出,是由另一类如刘海粟、林风眠等美术家践行的。他们对于美术国故,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的态度,但又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世界美术中,以图中国之美术也能屹立在世界之林。其中,如蔡元培所说,“事于整理发扬我国固有艺术,当有新颖不凡之见地与意匠。出人品者,刘海粟与黄宾虹当之无愧”[15]。刘海粟作为一个近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奠基人、教育家,其狂放不羁的性格,超强的活动能力,鲜明的艺术主张,使他的朋友圈极其广泛,无论与新文化运动中唯物史观派还是与国故派学者,也包括美术国故整理的研究者,多有密切关系往来,如黄宾虹就曾在上海美专任教过,刘海粟称其以美术“为后学提供了津梁”。
现试析刘海粟“整理国故”的思想并撷取其与陈师曾、胡适等人的交往事迹,以窺其早期现代主义绘画与“整理国故”两者影响之一斑。
(一)刘海粟绘画风格与其“整理国故”的思想
“国画复活运动”[16]是20世纪30年代美术学界“整理画故、再造文明”的新发展。美术学界的国故学派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从“写意”当中,认识到中国本地文化的优越性。而刘海粟,作为国画复活运动的引领者、参与者,一个有着以美术国故为自豪的美术教育家,处处表现出弘扬中国的本地文化、整理发展我国固有艺术的强烈艺术信念,为此,他“不怀庆赏爵禄,不顾非誉巧拙”,无论在绘画中,还是在他数百万字的艺术论述中,他都一再强调、展示中国国故美术的优越性。在其观念里,即使欧洲近代美术也是中国国故美术的小学生,石涛、八大,早三百年前就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祖师爷。但是对于西方的艺术,他也并不是如守旧派,一味排斥。刘海粟也在其《拭目待天葩》一文中说:“既要有历史眼光,纵览上下二千年的画论画迹,又要囊括中外的世界眼光,凡属健康向上可以吸收的东西,都要拿过来。”[17]
(二)刘海粟与“整理国故”代表学者的关系
1.刘海粟与陈师曾的君子之谊
陈师曾以科学态度,借日本之研究体系研究美术国故,在美术学界影响深远。李云亨说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捍卫中国传统艺术之第一人”。徐悲鸿、刘海粟与陈师曾都有君子之谊,但陈师曾与刘海粟的关系和与徐悲鸿的关系相比,明显好了很多,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陈师曾的美术思想理念也许与刘海粟会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在刘海粟的《哀新吾先生》一文中,提到陈师曾说“日三人相共,纵论志愿”,甚至陈师曾在不幸早逝(1923年)后,吴新吾还曾希望刘海粟为陈师曾作传,“嘱余为师曾作传”,可以看到两人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但徐悲鸿在其自传中,多次表现出其对刘师曾的轻视甚至心有芥蒂。1930年发表的《悲鸿自述》中,对于陈师曾仅一笔带过,说“识陈师曾,时师曾正进步时也”[18],而在《四十年来北京绘画略述》中,徐悲鸿对陈师曾的评价则更显苛刻,称“其时师曾名籍甚盛;实际师曾擅刻印而已,法吴仓(昌)硕”,“画与书略有才”。[19]但要知道,陈师曾自己曾说“平生所能画为上”[20],而对于陈师曾在美术史上的巨大成就,吴梦非称之“名满京都”;梁启超先生在其追悼会上,称其早逝影响中国艺术界甚至超过了日本关东的大地震。[21]因此,作为一个后辈晚学,相对陈师曾在当时美术学界的影响,徐悲鸿对陈师曾的“略有才”的评价与态度颇值得思索和玩味。
2.文艺界的两个叛徒
“世之举文学改新者,必曰胡适之;举艺术改新者,必刘海粟”,被称为“文学叛徒”的胡适和因“裸体模特儿”被卫道者诬为“艺术叛徒”的两个“叛徒”之间,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作为国故学派的领袖,胡适本人也是一个颇有造诣的书法家。胡适在自己的传记中说,他从小对美术就有浓厚兴趣,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选修过美术史哲学课程,还发表过滑稽画,并且他曾经的红颜知己韦莲司也是纽约一名现代派画家[22],在其文艺圈中,更不乏美术朋友。刘海粟就是1921年通过蔡元培认识了胡适。胡适作为上海美专的校董之一,1925年10月,还在美专作了题为“天才与修养”的演讲。在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还记载了钱化佛、胡适、刘海粟的“叛徒扇”的艺海掌故。在艺术观上,胡适也与刘海粟有着相同的立场,在1922年3月8日的日记中,他说:“中国美术不拘守物质上的限制,技术更自由,故能表现抽象的观念更深刻。”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关系可能只是一种“浅尝辄止”的认识关系,①但是,就刘海粟这个被认为“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徐悲鸿语)的个人秉性来说,如果真的以“认识胡适”为荣,却只能说明胡适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否则,他决不会做出如此姿态来。对于喜欢争辩出“是非”来的刘海粟,也断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失去了他自己的底线。[23]
五、余论
“整理国故”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为研究者提供了批判性思想观念和研究方向,极大地促进了包括美术学界在内的各种研究思想。它已经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本身的具体历史概念,而是变成了一种科学意识、精神体现。其以科学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国故取精去伪;另一方面,又指引中国近代美术形成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既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因素形成,也是由中国的近代美术学界的各位开拓者、奠基者,以惊人之毅力,开阔之眼界,顺应大势做出的重要贡献。
这场运动为弘扬中华优良文化,建立不亢不卑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文化精神基础,从这点意义上来讲,“整理国故”的运动不会停也不会休。
注释:
①刘伟冬认为刘、胡的关系很好,但肖伊绯认为,两人只是一种浅尝辄止的关系。参见肖伊绯:《胡适与刘海粟交谊新考》,载《钟山风雨》2020年第1期,第1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