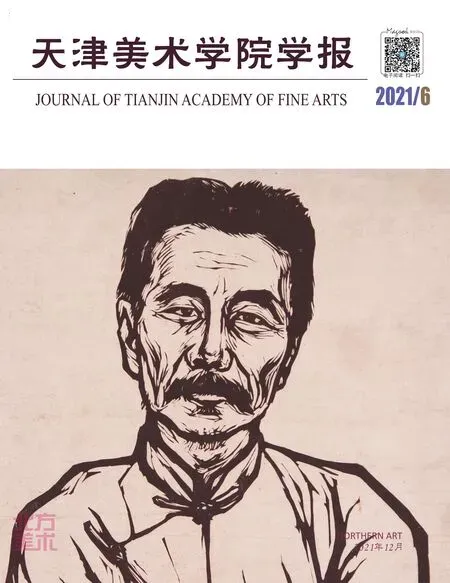媒介考古学视角下20世纪媒体艺术的产生和转变
一、有关媒介考古与媒体艺术的问题提出
在传统美术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在盛极一时的形式主义分析的背景下,材料只是艺术家创作思想的载体,物质成为美学理念的客观化。以形式及其情境演化分析为主的图像学艺术史研究中有两个假设:一方面,物质被认为是形式的从属;另一方面,物质作为艺术作品的物理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材料。这种假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媒体艺术的研究,媒体艺术研究中的核心美学信息长期被概念化为抽象和非实质性的。艺术学研究中非物质话语长期占据主导,直到今日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日益得到关注,艺术的物质性才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而以物质转向为核心的媒介考古学或可以成为新时期艺术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
“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一般是指一种以媒介物质为中心的“回溯-前瞻式”(analeptic-proleptic)的研究取向。[1]在学科不断交叉的今天,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媒介考古学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术语,一方面,媒介考古学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开创了“以客体为导向的媒介考古学”,[2]因此超越了传统媒介研究的主流叙事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媒介考古学发源于电影考古学和传播学媒介理论,又引入视觉文化研究、美术史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和思考。
目前国内涉及媒介考古学的研究仍主要以对西方相关理论的译介和阐释为主,如唐海江主译的论文集《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2018),李诗语翻译的齐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艺术与媒介的类考古学和变体学与电影》(2018),杨北辰所作的《“新物质主义”视野下的电影媒介考古学》(2018)和施畅所作的《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2019)等。国内利用媒介考古学进行的艺术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只见学者使用媒介考古学作为方法进行电影史的研究,如黄望莉、刘效廷的《媒介考古视野下的新电影史学研究》(2019)、唐宏峰的《虚拟影像:中国早期电影媒介考古》(2018)等。值得注意的是,唐宏峰在其《视觉现代性与媒介考古学——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与中国现代视觉经验》(2018)一文中提出了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理论对中国视觉艺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合理性,唐宏峰在文章中指出:“(克拉里的研究)所接近的对象更准确来称呼是一种媒介考古学……克拉里的研究对中国研究的最大启示莫过于它将那些无法被容纳于传统美术史与电影学等学科规划的媒介内容扩入思考的对象,并提供了思考该对象的理论框架和适用方法。”[3]
本文将主要使用媒介考古学理论对20世纪媒体艺术的产生与演变进行分析和梳理,并尝试用这一方法主要解释两个问题:媒体艺术是如何产生的?20世纪媒体艺术又是如何转变的?此外本文还将对作为艺术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媒介考古学进行简要论述。借助媒介考古学进行20世纪媒体艺术的研究,或有助于进一步将这一新的学术方法引入艺术学领域,并为中国语境下的当代媒体艺术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二、媒介考古学视角下媒体艺术的产生
从创作者的角度,艺术家选择使用新兴媒体作为艺术表达工具可以主要被归纳为两个原因。第一在于现代艺术失去了传统艺术对普通大众的美学影响力,随着20世纪初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这些新的艺术形态和面貌无法被大众的传统审美常识所认同。艺术批评家高名潞指出:“(现代艺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透露出艺术家对艺术媒介无力承担社会功能的失望,正是这种失望导致了更为极端的艺术与社会的疏离。”[4]而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技术作为大众媒介,可以将前卫艺术在自我隔离中解脱出来。恰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推动的媒介考古学将电影、电视等视听媒体艺术称为大众性的文化技术(Kulturtechnik),[5]媒体艺术家们希望借助大众传播媒体的公共性扩大前卫艺术的社会影响力。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也同样试图解决前卫艺术的社会无效性问题,并且为媒体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本雅明看来,艺术创作应该突破传统手工式制作的有限技术方式,从而吸引新的观众。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这些思想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等人的传播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马歇尔·麦克卢汉接受了老师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一部分理论,进一步阐释了媒介形态变化对社会变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并预测新兴媒体的出现会让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最终成为地球村。[6]26恩岑斯贝格则在1970年发表的《媒体理论的组成》(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中指出:媒体使群众参与社会和社会化生产成为可能。[7]媒介理论的发展赋予了媒体艺术以社会意义,为媒体艺术家的社会化表达提供了理论根基,也为其观念转变提出了方向性指引。
艺术家进行媒体艺术创作的第二个关键动机,在于媒体拥有创造前所未有的视觉图像和声音体验的美学潜力,换而言之,媒体艺术家认为它们可以超越所有已知类型的艺术形式。20世纪初,德国导演沃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曾经预测过一种新型艺术的出现,他认为这种新艺术与传统绘画和音乐都不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会拥有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8]很快沃尔特的预测就在20世纪30年代被立体主义画家汉斯·李希特(Hans Richter)和维京·埃格琳(Viking Eggeling)所实现,汉斯·李希特将达达主义的理论构想应用于其影像创作中,通过电影中不断变化的线条和几何图形来表达无逻辑、无秩序的影像世界,维京·埃格琳则在抽象电影作品《对角线交响乐》中将钢琴、竖琴等乐器符号化,并使其随着音乐不断快速出现和消失,极具构造主义的特点。二人均通过镜头语言的运用,使抽象图像得到不断叠加,在进行“音乐视觉化”和“视觉音乐化”探索的同时,实现了具有时间维度的象征性隐喻的艺术表达。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在对无线电艺术的探讨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认为麦克风可以人工制造出闻所未闻的声音,从而产生出更为纯粹的艺术。[9]
沃尔特·鲁特曼将这些媒体艺术的新方法视为对日益提高的媒体技术和日常感知的信息传播的反应,他在文章中指出:电报、特快列车、摄影、快速印刷等并不是艺术领域的成就,但它们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对新信息的快速获取,意味着人类个体不断地被旧认知方法所无法解释的知识所淹没,这也是人们无力接受新的艺术现象的原因。[10]这一观点得到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鲍德里亚认为: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电视带来的信息也并非它所传递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以及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11]
因此,媒体艺术家的美学表达与技术可行性问题密切相关,当艺术家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实现艺术构想时,他们就会转变为发明家,进行技术革新的尝试,从而在机缘巧合下创造出了媒介考古学者提出的“幻想媒介”(imaginary media)。克鲁滕贝格(E. Kluitenberg)曾写道: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传播介质及其功能,也要考察人们将何种幻想加诸其上——幻想媒介中介(mediate)了那些人们求之不得的欲望。[12]画家路易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在视觉艺术领域坚持菲利普·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的未来主义观念,并试图将其引入音乐领域,为此他制造了噪音发生器(Intonarumori)用于产生类似机器制造的声音;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尝试用唱片和留声机制作声音蒙太奇;沃尔特·鲁特曼则制作了胶片相机,甚至取得了相应的专利。
1919年,包豪斯(Bauhaus)创办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起草《包豪斯宣言》(Bauhaus Manifesto),宣言抹除了艺术家与工匠、理论与技术之间的界线。包豪斯宣言与媒体艺术家们的技术革新需求不谋而合,包豪斯学院内部也开始出现艺术家与技术人员合作进行的媒体艺术创作实践。20世纪20年代,包豪斯学生库尔特·施韦德费尔格(Kurt Schwerdtfeger)开发了反射色光(Farbenlichtspiele)技术,另一位学生路德维克·赫希菲尔德-马克(Ludwig Hirschfeld-Mack)则借助这一技术制作了光投影装置,通过人工机械操作,使彩色光线的移动投影形成几何图形,并使其与音乐相结合完成最终的作品。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技术,他制造了一种可以由电动机驱动的光空间调制器(Licht-Raum-Modulator)。
彼时的创新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媒介考古学尝试再度赋予这些旧技术以新奇和期待。这种在当时令人眼前一亮,而如今已经过时的创造尝试被媒介考古学者称之为“失败媒介”。美国艺术史学家汤姆·冈宁(Tom Gunning)指出:每一种新技术都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在此可以幻想未来社会会因新技术的实践而发生怎样的变革,然而当这一新技术从新奇到陈旧,它就会自我调整而进入既有的社会体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该技术的变革失败了。[13]而“媒介考古学是收藏、保存与暂留‘失败媒介’的希望空间”,[1]它站在“视旧如新”的角度,质疑传统媒介史的连续性叙事,反对以往媒体艺术发展研究中的合目的性和单一方向性。因此,媒体艺术的产生和演变历程被媒介考古学者视为一种“抵抗的实践”(practice of resistance)。[14]
三、媒介考古学视角下媒体艺术的转变
西格弗里德·杰林斯基指出:“技术不是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偶发产物,相反,技术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主体存在、意识及无意识的条件。”[15]也就是说,媒介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反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中所阐释的“一切技术都是人的延伸”,而认为媒体技术的发展影响甚至决定了作为技术创造主体的人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媒介形态技术的出现总会提出新的美学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部分是新媒介本身所固有的,例如摄影、电影和数字图像媒体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蒙太奇;另一部分则与其文化背景有关,即新媒介与既有媒介或艺术形式之间所产生的关联,例如摄影术发明推广后,艺术界开始出现了“绘画走向死亡”的观点,而电视出现后,人们对电影的未来随之产生了类似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视为是媒体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战前的媒体艺术聚焦于媒体技术的发展,艺术家们充满对新技术的好奇和期待。而随着战后媒体技术的成熟,媒体艺术开始转变为对媒介与技术的批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媒体艺术的主要形式是电影和无线电广播,那时带有技术试验性质的媒体艺术创作被视为是对传统艺术史的现代延续。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对此就有两本重要的论著,分别是1932年出版的《作为艺术的电影》(Film as Art)和1936年出版的《广播:声音的艺术》(Radio: An Art of Sound)。这时的媒体艺术家试图赋予媒体技术一些新的社会功能和含义。比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认为应该将收音机等无线电设备由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相互通讯;瓦尔特·本雅明则把希望寄托于电影中,称电影建立“人与机器间的平衡”。[16]但是这些艺术家或理论家的有关“媒体解放”的想法被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所限制,一方面,无线电和电影成为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工具,如吉加·维尔托夫、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等艺术家以及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们纷纷投身于政治宣传之中。吉加·维尔托夫很早开始关注电视技术,他认为这种将影像转变成电子信号的方法可以创造全世界工人阶级之间的视觉联系,从而很好地为共产主义服务。[17]而在与之对立的法西斯阵营中,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们同样将电视视为媒体艺术家手中传播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力量,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就曾想象将电视屏幕悬挂于飞机上,然后向远在地上的人们展示未来主义的飞行绘画(Aeropittura)。[18]另一方面,包括奥斯卡·费钦格(Oskar Fischinger)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内的逃离欧洲、移民到美国的艺术家们,也几乎没有机会继续他们的实验性创作,因为他们发现那里的媒体已经被商业控制。而同时,媒体技术的政治和商业化深刻影响了媒体艺术家们的艺术思想。
20世纪早期媒体艺术的萌芽与发展被二战打断,直至6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渐恢复才重新回归艺术家的视野。进入60年代后,媒体艺术家们开始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牢固的媒体技术系统,视听媒体基本固定为无线电广播、电影和电视,这三种媒体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了媒体艺术家的理念和实践,他们开始重新衡量媒体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电视技术的成熟压缩了无线电广播的生存空间,无线电艺术家努力为无线电广播赋予新的身份,约翰·凯奇(John Cage)试图将收音机变为一种乐器。1951年,他创作了《虚拟景观第四期》(Imaginary Landscape No. 4),这首四分钟的“乐曲”由十二台收音机演奏,每台收音机配有一名指挥和两名演奏者,演奏者一位负责调谐,另一位调节振幅及变化音色。约翰·凯奇认为如此才有可能使音乐作品的连续性不受个人品味和心理记忆的影响,也不受文学和艺术“传统”的影响,从而使声音进入时空,以它们自身为中心,不受其他潮流的阻碍。[19]无线电艺术的这种身份转变给予新一代媒体艺术家新的理念:媒介本身保持不变,只有我们的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声音为核心的无线电艺术具有“生而抽象”的特质,而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无线电艺术的面貌,当模拟信号发射系统被音频流技术所取代,无线电也逐步进入了新媒体艺术的讨论范畴。
而在电影方面,银幕的大规模生产以及摄影机的普及导致了电影制作的高度流水线化和商业化,这使得一些艺术家转向对电影和媒体社会的激进批评。字母主义(Lettrism)拥护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就是重要的“反对电影”拥趸之一,其所作的《隆迪的狂吠》(Hurlements en faveur de Sade)与其他任何形式的电影不同,该片不包含任何实际图像,只在白色和黑色的电影屏幕之间交替显示,显示白色时可以听到语言文本的对话,屏幕黑暗时则没有任何声音。居伊·德波的创作将观众带到电影放映的原始屏幕背景中,力图引领观众观察电影本质如何在时间上被感知。屏幕本身就构成了艺术,这成为他割裂电影媒介表象与本质的手段,也构成其后期“景观社会”理论的实践基础。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作的《帝国大厦》(Empire)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反电影的尝试,他放弃了商业电影中形式与内容上的夸张,以单一的镜头聚焦于单一影像,使得这部超过八个小时的影片充满讽刺意味。摄影机的技术更新为安迪·沃霍尔这一尝试提供了可能,与他早期电影中使用的波莱克斯(Bolex)摄像机只能连续录影3分钟相比,《帝国大厦》使用的奥里康(Auricon)摄像机内可以放置33分钟的胶卷。而在胶卷的使用上,安迪·沃霍尔选择了感光度(ASA)400的柯达高速黑白胶卷Tri-X,并将感光度迫冲(push processing)至1000以补偿黑暗光线下的拍摄环境。高速胶卷使黑夜中的细微变化得以被感知,迫冲处理则使得胶片更具有颗粒感,这引发了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对胶片本身的关注。
只有电视似乎仍被媒体艺术家赋予了乌托邦式的技术和社会理想,作为影像艺术(Video Art)的视觉呈现载体,它可以提供给艺术家一个开放的新艺术领域。1940年,极少主义者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与其学生共同创办阿尔塔米拉学院(Altamira Academy),并公开发表《白色宣言》(White Manifesto)。《白色宣言》中宣称:运动中的物质、颜色和声音等诸种现象,它们同时发展创造出(makes up)新艺术。丰塔纳将宣言中的理论命名为空间主义(Spazialismo),并在1952年于电视上发表了《空间运动电视宣言》(Television Manifesto of the Spatial Movement)。丰塔纳在宣言中将电视看作神秘未知的宇宙空间,并相信电视注定会更新艺术领域的表现形式。
随着电视技术重塑了社会运作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电视与观众之间传统的单向播放和收看关系被逐渐消解。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白南准(Nam June Paik)为首的媒体艺术家开始思考大众媒介与电子影像对人类思维所带来的改变。1963年在白南准的首个个展上,13台二手电视机被零落地摆放在德国帕纳斯画廊(Galerie Parnass)内,这是他首次将黑白电视机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后来在工程师阿部修也(Shuya Abe)的帮助下,白南准又制作出第一台用于电视的影像合成器(Paik/Abe Synthesizer),这一机器可以同时接收与编辑来自七个频道的信号,成为艺术与电视媒体技术结合的一项重大革命。白南准诸多的作品可以被分为三类:第一类如《电视眼镜》,是一种电视加行为而构成的身体装置艺术,第二类如《电视花园》,展现人工技术与自然的并置和共生,第三类如《电视佛》,探讨电视文化中人机关系的哲学隐喻,这些都印证了丰塔纳对于电视艺术可能性的预测。
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认为的“媒介与话语网络之间产生的紧张和冲突,也会带来媒介层面的转变”一样,[20]媒体艺术作为一种视觉信息的跨媒介叙事,其发展变化有自身内在的规律,且规律在总体上是与媒介技术形态演进相符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和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都认为:媒介发展总是包含着杂交或者融合的趋势,新媒介往往是对旧媒介的补救和完善,同时新媒介又存在新的缺陷,杨保军将这一规律总结为“扬弃”。[21]保罗·利文森在阐释其媒介演进理论时指出:“实际上,‘玩具、镜子和艺术’有这样一个主题:媒介招摇进入社会时多半是以玩具的方式出现。它们多半是一种小玩意。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完成什么工作。”[22]“然后,人们才开发它的镜子(即工具)功能。最终,它会变成一种艺术形式”。[6]40电影的发展历程可以成为利文森理论的有效例证,1888年,路易斯·普林斯(Louis Prince)拍摄的《郎德海花园场景》(Roundhay Garden Scene)放映时,观众只是为动起来的画面而兴奋不已。不久后电影被用来记录现实活动,如卢米埃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拍摄的《火车进站》(The Arrival of the Mail Train),而剪辑的技术被发明后,电影开始大规模被用来艺术创作,并成为“第七种艺术”。
四、作为媒体艺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媒介考古学讨论
西方学界已开始尝试探讨将媒介考古学引入电影学之外的艺术学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有加拿大学者加内特·赫兹(Garnet Hertz)和芬兰学者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在论文《僵尸媒体:将媒介考古学扭向艺术方法》(Zombie Media: Circuit Bending Media Archaeology into an Art Method,2012)中探讨了如何以媒介考古学作为艺术的创作和研究方法,他们提出要以挪用(appropriation)、拼贴混合物质材料和档案(collage and remixing of material and archives)为传统,发掘被认为衰败的媒体和被遗忘的理念,从而将媒介考古学从一种挖掘文本的方法(textual method)转变为探索物质材料的方法论(material methodology)。[23]西班牙学者保·阿尔西纳(Pau Alsina)和凡妮娜·霍夫曼(Vanina Hofman)则在《没有艺术品的艺术:媒介考古学视角下对媒体艺术记忆建构的反思》(Art Without Artworks: A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mory of Media Arts from a Media Archaeology Perspective)一文中通过考古学方法、变体方法(variantology)和媒体艺术的递归(recursive)三个方面探讨物质对媒体艺术美学记忆建构的影响,并强调物质研究可以成为媒体艺术研究的重要补充。[24]
媒介考古学视角下,媒体艺术的产生可以被视为一种乌托邦尝试,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开辟了新的美学可能性。而总的来看,媒介考古学视角下的媒体艺术研究,首先强调研究内容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具体表现为对艺术创作载体——媒体的技术与物质性的变革的重视,而非仅关注传统艺术史叙事中风格流派或艺术观念的更替,也非以往媒介理论中对话语场域的突出。如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深入探讨了作为物的技术是如何进入社会场域,又是如何稳定社会联结的,他的焦点在于“技术的社会形塑”(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25]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15世纪西方传统绘画材料的转变(由鸡蛋颜料变为亚麻籽油颜料)塑造了全新的绘画艺术史形态一样,20世纪媒介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媒体艺术的面貌。计算机互联网时代下新媒体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当下人工智能艺术的方兴未艾,都是技术塑造媒体艺术形态的例证。其次,与福柯(Michel Foucault)“谱系学”(Genealogy)式的断裂历史观相似,媒介考古学视角下的媒体艺术变革历程也并非直线性、连续性的。它将那些“失败”的媒介创造和艺术尝试同样纳入讨论范畴,展示了不同的媒体艺术在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被撕裂的媒体叙事,这是对传统媒介史和艺术史研究的极大丰富。
抛开既有的媒体艺术研究范式,媒介考古学中倡导的物质转向和非线性叙事将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这也是当下艺术发展的重要潮流。尽管在新媒体艺术中,无数的二进制0和1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美学意义和价值,但西方以媒介考古学为方法进行的艺术学研究仍可以为国内学者提供新的思路,而媒介考古学也有望成为未来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