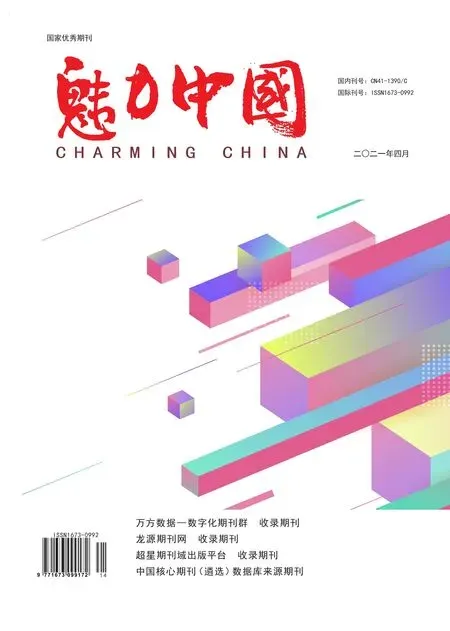浅析民族民间舞蹈表演中对于“环境意识”的运用
白富强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天津 300384)
一、“环境意识”与民间舞蹈
(一)民间舞表演中的“环境意识”
民间舞演员的“环境意识”具有特指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环境社会学中的哲学概念。其意是指民间舞演员在表演时对该民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又是民间舞演员为充分展现该民族舞蹈风格特点、传达作品意境而不断调整的自身心理活动与表演行为,协调民间舞演员与原始民族环境、民间舞演员与舞台环境相互关系的表演活动的再现性。民间舞演员对某一民族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实地体验或学习了解后,形成对该民族的基本认知,并在掌握该民族舞蹈语汇的基础上,通过有意识的联想,在头脑中拟造出该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从而在舞台环境中表演这一民族特定环境中的舞蹈时,可以使动作语汇、形象塑造与情感表达更具真实性与感染力,呈现出该民族舞蹈特有的风格特点与地域特色。
实地体验与感受各民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对民间舞演员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促成民间舞演员“环境意识”的先提条件。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迥异的民间舞蹈又是各族人民民族性格的外化形式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广大舞蹈先驱们深入地方采风学习,对各民族舞蹈元素进行了搜集与整理,并加工、提炼成较为系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教材,创作出内容多样的民族舞蹈作品,如:贾作光先生创作演出的《鄂尔多斯舞》等。
有意识的联想,是民间舞演员“环境意识”形成的必要的思维路径。在掌握某一民族舞蹈动作语汇后,达到动作语汇与对民族原始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基本认知上的关联。心理学上的联想是指,“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包括由当前感知的事物想起另一有关的事物。”舞蹈演员在非真实的民族环境(如舞台)下表演民间舞蹈之前,要对整个作品进行解读。这通常会使演员联想到曾经体验过的相似或相近的生活环境,仿佛再一次置身于曾经体验过的生活环境之中,表演时才不失真实感,从而塑造出具有鲜明性格的舞蹈形象。因此,联想在民间舞演员的“环境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民间舞表演运用“环境意识”的意义
在表演中运用“环境意识”,首先是有利于民间风格的把握。马力学教授曾对“风格”有明确的阐述:“舞蹈的风格是由于各民族、各地区和个人的不同和差异而形成的。每个民族、地区和历史演变、自然环境、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性格风格及艺人风格……它们都在每一种民间舞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民间舞蹈的风格是一个民族的标签,更是检验民间舞演员的“试金石”。笔者认为,一名民间舞演员若想掌握好某民族的舞蹈风格,除课堂的学习外,还需深入到该民族的生活背景中,实地体验该民族的各种环境因素,了解该族人民的民族性格(意识),感悟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对该民族特有的“环境意识”。从而获取舞蹈表演意境,才能在表演时更准确的掌握该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
其次是有利于对舞蹈形象的塑造。“舞蹈形象是以人体舞蹈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所塑造出饱含着主体情思的具有客体典型形态的可被人们直接感知的动态形象。舞蹈形象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解释......而狭义的舞蹈形象则主要指舞蹈作品中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并借助于音乐、构图、舞台美术(服饰、布景、灯光、道具、化妆)等其他因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在舞蹈理论和舞蹈美学的论述中,所谈论的舞蹈形象,大多指狭义的舞蹈形象,即舞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含舞蹈群体的人物形象)。”
最后是有利于“环境意识”对舞蹈作品意境的升华。“舞蹈作品的意境,从字面上解释,意是指作品所表现感情和思想,境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客观环境。舞蹈作品的意境,就是舞蹈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如前所述,民间舞演员的“环境意识”是协调民间舞演员与原始民族环境、民间舞演员与舞台环境相互关系的表演活动的再现性。触发人物情感的自然环境是营造作品意境的首要性因素,有了环境,人物才能见景生情。
二、民间舞表演中运用“环境意识”的策略
(一)培养演员的想象力
民间舞蹈的形成,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并非是为唯一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文环境对民间舞蹈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人文环境是专指由于人类活动不断演变的社会大环境,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性的,而非自然形成的。人文环境还受到原始宗教、劳动导致的动律定型、服装服饰等多方面的影响。但这些相对于在舞蹈学院的我们来说,是较为遥远的,这时候,“环境意识”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例如在舞台表演时,我们身穿民族服饰,在面对着现代化舞美和观众之时,我们身处于两种“环境”,一是当下真实发生的“舞台环境”,二是由我们心理空间所主导的“民族意识环境”。
第一种环境需要演员有足够强大的表现力,不怯场、敢于表现是最为基本的要求。而第二种甚至可以称之为“心境”的“环境意识”则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想象能力和双重视觉效应,也就是将自己置身于那个原始民间舞发生的场域内进行表演。这就需要演员在台下有足够的功力,一方面是导演的引导,另一方面是演员对表现民族特征的的理解。杨梓在《浅析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情感教学》一文中讲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情感归属于每一个民族的情感,民族民间舞无论从表演课堂还是创作课堂都应该回归“本土体验”的真实情感,因此培养内心的真实情感作为情感教学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课堂作为重要教学手段。情感教学应该从心出发,以培养学生的情感为重,在民族民间舞蹈的原生态中挖掘、寻找、想象舞蹈的真谛,切身感受中国民族民间舞本质的纯朴与热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也正是这种想象的意识,这种将图像上的、语言文字上的转化为自己真实感受的能力是一个好演员必须具备的,这是除了身体基本功以外也理应具备的演员“基本素质”。
(二)真切的感受生活
李雪梅的《地域舞蹈与生态环境——试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地理特征》研究的是民间舞蹈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以及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给予民间舞蹈之种种影响。本人认为研究民间舞蹈生成的地理环境是真实地把握一个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内在生成本质规律的关键,将地理环境作为民族舞蹈文化生成的因素之一,我们不但可以从中推出一个民族的民间舞蹈动态特征的积淀,也可以找到与舞蹈相关的一些材料的特征,如服饰、道具、场地等,这些都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而积淀了各个地域上的人类群体自己特有的符号类型。所以对地理环境的研究是研究民族民间舞风格特征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假如有采风的能力,我们应该珍惜每次这样的机会——将自己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细细的感受周围的空气、阳光等自然因素,去认真聆听老艺人对他们本族艺术的理解和传说故事,这些不仅是民间舞创作的根基,更是民间舞表演的基石。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姜铁红副院长曾说过:“民间舞蹈应该是构建在情感及环境的基础上去跳,并非仅仅依托于绚丽多姿的舞蹈动作”。基于此观点,笔者认为,民间舞演员在表演舞蹈作品时,要靠环境意识来提高情感的表现,通过情感来营造环境,这样才能使作品更具感染力,不失真实感。就以姜铁红老师为例,姜铁红老师的生存环境和在草原上的环境尽管不同,但他是在内蒙古歌舞团院里长大,在内蒙艺校学习成长,从小受到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受蒙古族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加之他多年对蒙古族舞蹈的教学经验、舞台经验,在这种环境中使他有了蒙古人的民族意识(性格)、民族文化和对蒙古舞蹈的情感,致使他在表演蒙古族舞蹈作品时更具真实感、更具感染力。所以他跳起蒙古族舞蹈来,有情有境,舞动的背景就是“环境意识”。
除了采风中感受到的生活外,在当下我们更应该注重真实生活中细腻微妙的情感体验。民间舞甚至说舞蹈是基于情感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原生态的民间舞的发生还是创作形态的民间舞蹈都是基于情感或者是情绪的激发。我们可以将感受的生活情感进行转化,使其变为某种舞台情感,例如在表演时,某种气氛对于演员来说较难把握,可以引导演员回想生活中的经历,通过回想这由亲身经历引起的情绪转化为表演情感,也是一种经常用来辅助演员找舞感的方式。
(三)“环境意识”与演员二度创作相辅相成
以上不仅是运用“环境意识”的策略,也是演员进行二度创作的基点,可以说“环境意识”与二度创作实际也是相辅相成的,“环境意识”的运用实际就是二度创作的一种方式方法,而二度创作也必然是“环境意识”发挥了作用。
二度创作是演员“空间”,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不仅会从对民族地区的“环境意识”出发,更会从根据舞台表演时的“舞台环境”做出相应的自我发挥。所以,虽然二度创作的动因具有多元性,但是不管是采风得来的还是生活经历的转化亦或是舞台上的即兴发挥,均离不开“环境意识”,二度创作也是针对不同环境下的“意识”层面的自我能动性的主体选择。
结语
想象力、感受力、创造力是一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对于舞蹈演员舞台能力的提高也是螺旋式的递进过程。对于民族民间舞蹈演员来说应该去了解生成该族民间舞蹈的成因,了解该民族的各种环境因素,了解该民族人民的民族历史及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感悟该民族的民族精神。进而能在非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表演时,通过自己对该民族各种环境因素的认知程度、熟悉程度,在头脑中快速拟造出所表现作品特定的民族环境,做到心中有“境”、以“境”起舞,从而获取舞蹈表演意境。表演时,才能更好的表现出该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才能更好的刻画出鲜明生动的舞蹈形象,使所表演的作品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
——教材内容”展示与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