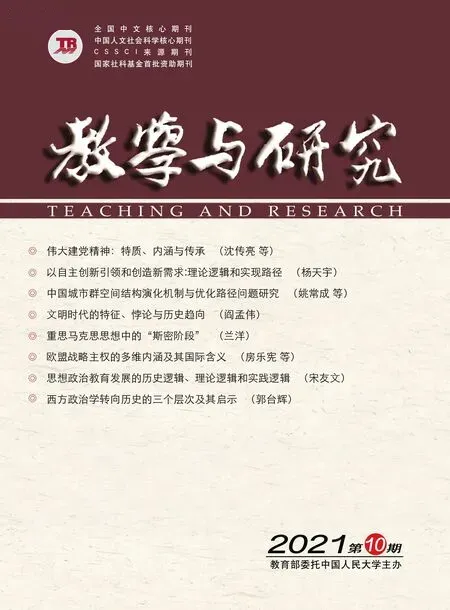以自主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杨天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意味着扩大内需的政策手段已不仅仅局限于需求端,而且也包括供给端的创新驱动。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创新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这相当于创造了新需求。(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祥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0页。从逻辑上说,市场上的现存产品容易出现需求饱和现象,而技术创新为市场引进了新产品,满足了人们对新产品的购买欲望,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需求饱和问题,的确称得上是开辟了新的市场需求。不过,技术创新是通过什么机制和过程创造新需求的,在理论上仍旧是不清楚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创新都能创造新需求。例如,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虽然对国内而言也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大多是以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的形式存在,实际上相当于拉动了国外的投资需求,而没有创造国内的新投资需求。自主创新可以避免上述问题,但自主创新创造新需求的过程仍然是不清楚的。如果我们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将自主创新划分为中间产品自主创新和最终产品自主创新,那么最终产品自主创新能否增加对上游中间产品的需求,将取决于中间产品部门是否能够为最终产品提供合适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若无法提供,则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对中间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仍然会转化为对国外同类产品的投资需求。可见,何种形式和产业链中哪个环节的自主创新能够扩大内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理论逻辑之外,以创新驱动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政策路径也需要进一步探讨。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完全可以由小微企业来完成。例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在自家车库里就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中间产品的自主创新则必须由大企业来完成。例如,乔布斯发明个人电脑时利用了当时已经相对成熟的芯片和其他零部件,而芯片等零部件的发明和制造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丰富的生产经验,绝非是几个大学生在车库里可以完成的。显然,政府鼓励最终产品创新和中间产品创新的扶持政策不可能相同,这意味着实现中间产品自主创新和最终产品自主创新的政策路径应有所区别。本文以现实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为切入点,聚焦于自主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传导机制问题,试图阐明其理论逻辑,并找出自主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实现路径。
一、文献综述
自熊彼特创新假说提出以来,已经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创新与需求的关系问题。其中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总体创新能否创造新需求,并未区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学者们找到了诸多技术创新影响消费需求的途径,如认为技术创新通过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带动消费需求,(2)肖泽群、文建龙、黄立平:《技术创新的有效需求效应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07年第3期。或者通过优化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促进消费增长,(3)黄彩虹、张晓青:《创新驱动、空间溢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2期。或者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消费升级等。(4)孙早、许薛璐:《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有的文献进一步认为,不仅技术创新可以刺激消费需求,而且消费需求反过来也可以刺激技术创新,二者是互动关系。(5)金晓彤、黄蕊:《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的互动机制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2期。此类文献的核心观点是,内需不足根源于供给端的技术创新不足,这与熊彼特的传统假说相符,但由于其忽略了中间产品创新与最终产品创新的区别,还难以对现实中内需不足的原因做出完整的解释。
另一类文献区分了中间产品创新与最终产品创新,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洞见。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指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需求互补性、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等问题,在此情况下任何最终产品环节的投资很可能一开始就受到需求不足、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缺乏的阻碍,结果导致投资失败。(6)Rosenstein-Rodan P,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1943, 53(210): 202-211.(7)[美]拉格纳·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斎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6-23页。如果我们把最终产品投资视为创新引致的投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果只有最终产品创新而缺乏中间产品创新,那么最终产品创新引致的投资同样会受到需求互补性、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的阻碍,从而无法产生成功的投资需求。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已经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了思考。例如,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8)Prebisch 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1962,7(1):1-22.(9)Singer H,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0, 40(2): 473-485.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提出的“贫困化增长”理论,(10)Bhwati J, “Immiserizing Growth: A Geometric Not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8, 25(3): 201-205.都指出初级产品的生产率增长反而会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然而,瑞典、芬兰和澳大利亚等同样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国内学者贾根良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产品部门不够发达,发达国家则拥有发达的中间产品部门。例如,芬兰和瑞典不仅出口纸浆,而且也出口伐木和造纸的机器设备。(11)贾根良: 《资本品工业的自主创新: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贾根良进一步认为,中间产品(他称之为资本品创造部门)创新可以提高最终产品(他称之为资本品使用部门)的竞争力,从而同时提高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部门的收入和生产率。以美国为例,19世纪美国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在该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就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2)贾根良:《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这一论点很有启发意义,但贾根良并没有指出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社会新需求的机制和途径。当然,基于平衡增长理论的上述逻辑也有反对的观点。例如,以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为代表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最终产品中的主导产业高速增长,可以倒逼中间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增长。(13)[美]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潘照东、曹征海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3-67页。但这种意见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中间产品和基础设施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即必须首先有基础设施和中间产品,然后才可以生产最终产品,否则最终产品生产会因为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短缺的问题而难以持续。这意味着最终产品部门的孤立增长,一开始就会因为中间产品和基础设施短缺而被迫中止,这恰恰说明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平衡增长的必要性。
总的来看,同时考虑中间产品创新和最终产品创新,要比忽略二者的区别更有解释力。不过,现有文献还没有将这个视角用于解释自主创新对新需求的引领和创造功能。本文将在区分中间产品创新和最终产品创新的基础上,深入考察自主创新如何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二、自主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理论逻辑
已有文献指出,国内市场规模对促进自主创新具有重要作用。(14)贾根良:《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本文要论证的逻辑是,自主创新本身就具有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作用,即可以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众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消费能力的贫困人口,这并不能带来市场规模。自主创新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这自然就会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这可以说是自主创新能够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最基本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别阐述最终产品自主创新与中间产品自主创新对创造新需求的不同作用。
(一)为什么只有最终产品自主创新是不够的
最终产品是指那种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在产业结构中相当于最下游产业。这个环节的自主创新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满足了消费者追求新奇的消费欲望,显然可以创造对最终产品的新需求。然而,最终产品自主创新未必能同时拉动上游中间产品的新需求。在产业经济学中,主导产业(其中多数为最终产品生产者)的增长是可以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上游中间产品的增长的,但这个规律只限于已经相对成熟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在自主创新的情况下,该规律就难以适用了。理论上讲,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特点在于,它没有已知和可测量的概率分布,是不可确定的,容易受意外事件和新事物的影响。(15)Georgescu-Roegen N.,“Methods in Economic Sci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79, 13(2): 317-328.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不确定性可以降低为概率分布为已知可测量的风险,忽略了不确定性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市场会自动快速出清,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是很容易解决的。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的提出者罗斯托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新古典主义者,但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却具有新古典主义的特征,即最终产品增长对上游中间产品增长的拉动似乎是自动完成的,无论是扩散效应中的回顾效应、前向效应还是旁侧效应,都没有不确定性的影子。然而,现实经济并不是这样运行的。如果考虑到不确定性的话,即使一个国家已经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或产业链),最终产品环节的自主创新也难以像扩散效应所预言的那样,拉动中间产品环节的需求增长。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中间产品创新的不确定性。若只有最终产品出现自主创新,那么就需要先进的中间产品来配套,这在客观上要求中间产品也出现相应的自主创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不确定性,使得最终产品自主创新难以在全产业链创造新需求。对中间产品来说,若该环节的自主创新发生在第1期,创新后的产品销售发生在第2期,那么中间产品厂商只有在预期最终产品厂商将在第2期购买创新后的中间产品时,这些企业才会在第1期进行自主创新投资。但凡是创新都有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中间产品创新肯定会成功。最终产品厂商为避免不确定性,理性的选择是不再等待中间产品的自主创新,而是购买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这就为第2期的中间产品需求带来了不确定性,迫使中间产品厂商降低第1期的自主创新投资水平。结果,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并没有增加本土中间产品的需求,而是增加了对进口中间产品的需求。
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计算机操作系统可以被视为中间产品,电脑和手机可以被视为最终产品。中国的电脑和手机厂商很有竞争力,但却没有拉动对国产操作系统的需求。事实上国产操作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发,但由于进口操作系统已经形成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国产操作系统的开发者和使用者都对该系统是否能得到更多软硬件厂商的支持(即“生态问题”)有疑虑。开发者担心用户数量不足而不愿持续大规模投资,使用者担心缺乏网络外部性而不愿使用,结果导致国产操作系统需求增长缓慢。(16)张厚明:《国产操作系统发展滞后的成因与对策》,《中国国情国力》2015年第10期。这个案例说明,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中不考虑不确定性是有问题的,最终产品的创新并不能自动地拉动中间产品需求。在成熟的传统产业中,确定性的扩散效应有可能存在,例如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可以确定性地拉动冶金工业的需求。但在新兴产业中,类似于国产操作系统开发的不确定性就会出现。若将这种不确定性纳入理论框架中,结论就将是最终产品创新未必增加本土中间产品的需求。
2.转换成本效应。若最终产品首先出现自主创新,而中间产品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自主创新,那么最终产品厂商就不得不进口国外的中间产品。而如果在此之后中间产品又出现了自主创新,那么最终产品厂商是否采用国内的中间产品,就会面临转换成本效应。转换成本由对新厂商的不确定性和从原厂商处重复购买的收益构成。一方面,如果最终产品的制造过程已经适应了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特征,改用国产中间产品将会存在转换成本,该成本的大小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若最终产品与进口中间产品的磨合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就会带来重复购买进口中间产品的额外收益。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转换成本过高,迫使最终产品厂商放弃采用国产中间产品,结果使得最终产品创新无法拉动国内中间产品需求。
例如,国产电脑之所以无法采用国产芯片,就是因为国产电脑已经在进口的Windows平台上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软件研发,如果将软件移植到基于国产芯片的Linux平台上,前期投入资金会全部损失,对企业来说是得不偿失的。(17)芮雪、王亮亮、杨琴:《国产处理器研究与发展现状综述》,《现代计算机》2014年第8期。这其实就是转换成本较高的表现。这样一来,国产电脑厂商的专利再多,也无法拉动对国产芯片的需求。转换成本也是一种不确定性,在新兴产业中,这种不确定性会更加明显。在传统产业中,转换成本并不高,如本土汽车产业放弃了进口钢材转而采用国产钢材,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成本和额外收益的损失。然而在新兴的数字产业中,由于其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技术经济特点,转换供应商的成本和额外收益都会相当大,这才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把转换成本因素纳入理论框架中,同样可以得出最终产品创新未必增加本土中间产品需求的结论。
(二)中间产品自主创新如何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由于中间产品创新的不确定性和转换成本效应的作用,最终产品自主创新的单兵突进难以有效地在全产业链创造新需求,这也为引入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提供了依据。下面我们要说明的是,由于中间产品具有强烈的外部经济效应,该领域的自主创新成功将会有利于下游最终产品的自主创新,从而在全产业链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重大的最终产品创新,都是建立在首先出现中间产品重大创新的基础上的。例如,火车和轮船的发明是建立在蒸汽机的基础上,汽车和飞机的发明则是建立在内燃机的基础上;若没有蒸汽机和内燃机,那么火车、轮船、汽车和飞机就不会出现。这些例子说明,最终产品创新是中间产品创新发生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从逻辑上说,这实际上就是中间产品的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中间产品创新对下游最终产品的前向关联效应,即中间产品部门的技术创新,可以降低中间产品价格,或提供效率更高的新中间产品。这可以降低最终产品部门的投入成本,或促使最终产品部门也出现技术创新。比如钢铁的技术进步导致成本下降,这使得以钢铁为中间产品的汽车产业成本也下降并且竞争力增强;电子行业开发出质量更高的芯片,这使得以芯片为中间产品的手机质量也提高并且竞争力增强,等等。这种前向关联效应的好处是确定性,即最终产品部门可以采用现成的高质量中间产品,不必担心创新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花费转换成本。一旦中间产品率先完成自主创新,则不但可以创造出对本产品的投资需求,而且也为下游最终产品行业的研发人员提供了创新所必需的零部件、机器设备、软件和技术标准,使得最终产品行业可以摆脱对国外类似中间产品的依赖,从而增加了最终产品自主创新的概率。最终产品的自主创新反过来又可以刺激中间产品的进一步创新,这样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就在全产业链上都创造了新需求,包括对中间产品的投资需求和最终产品的消费需求。
不过,虽然中间产品创新可以缓解创新不确定性和转换成本效应,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中间产品厂商仍然面临着创新后的产品在第2期缺乏销路的不确定性;中间产品创新需要巨额投资,这又增加了其不确定性。此外,正由于中间产品创新的正外部性,使得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企业家因此不愿投资。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产业政策应介入中间产品的自主创新过程,以尽量消除其不确定性。以消除不确定性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既可以采取间接诱导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支持等,也可以采取直接干预政策,如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三、自主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实现路径
从自主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理论逻辑可以看出,自主创新有两条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实现路径,一是最终产品部门自主创新创造了本部门的新需求,二是中间产品部门通过正外部性创造了全产业链的新需求。可见,中间产品自主创新是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关键因素,也是产业政策应重点关注的领域。
(一)中间产品自主创新需要力度更大的间接诱导政策
近几年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草根创业”,国务院也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这些政策对促进我国自主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更适合于最终产品的自主创新,对于中间产品则不太合适。乔布斯发明个人电脑可以看作是大众创业的成功案例,但是他不可能发明芯片或光刻机。作为中间产品,芯片和光刻机都需要巨额投资,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才能完成。以乔布斯当时具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使他的创造力再强大也无法完成这样的目标。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在自主创新实现路径上的区别。对于最终产品,某些天才的奇思妙想,再加上已经成熟和便宜的零部件、机器设备或软件,就足以获得成功。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飞机、电视机、无线电报和个人电脑等发明就是由一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个人完成的。所以,鼓励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政策对最终产品自主创新是非常有用的。这类政策都是通过对创新者给予某种政策优惠和补贴,甚至只需要建立平台,以利于让创新者获得市场上风险投资的支持,就可以达到激励创新和扩大内需的目的。而此类政策对中间产品是不合适的。上述优惠、补贴和风险投资支持的数额都不会很大,而中间产品的创新则动辄需要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投资,这并不是风险投资或税收优惠就可以解决的。中间产品的自主创新,需要的是大型企业的长期投入,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也主要体现为对大企业的支持,这与产业政策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完全不同。政府对中间产品自主创新的支持,当然可以包括税收优惠,但这是远远不够的。针对中间产品自主创新不确定性较高的实际情况,政府更需要做的是降低其不确定性,一是降低其创新资金和技术来源的不确定性,如财政支出资助基础科学研究和企业研发、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等;二是降低其未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如政府采购中间产品、对中间产品销售给与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国内学者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其实就是利用以上方式促进创新的。(18)贾根良、楚珊珊:《中国制造愿景与美国制造业创新中的政府干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4期。目前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政府只需要对创新者提供“种子基金”,然后由市场来选择创新的优胜者。然而,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这个观点其实更适合于那种不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只需要民间风险投资支持就可以成功的最终产品创新,而不适用于那种不确定性很高、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中间产品创新。这意味着,要促进中间产品的自主创新,政府需要对产业或企业实施力度更强的政府干预,比政府支持最终产品自主创新需要的政府干预强度大得多。
(二)中间产品自主创新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直接干预政策
教科书中提到产业政策的直接干预手段时,一般指的是审批制、配额制、许可证制等,而我们在这里要提到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直接干预手段,即利用国有企业促进中间产品的自主创新。中间产品创新的正外部性,使其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而国有企业恰恰是政府解决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而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国内学者叶静怡等发现,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大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对私有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私有企业则不具有这种作用,原因在于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大于应用研究,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弥补研发市场失灵的工具,承担了比私有企业更多的基础性研究任务。(19)叶静怡、林佳、张鹏飞、曹思未:《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作用: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许多国家都积极运用这一工具去解决基础研究密集产业的市场失灵问题,建立起大量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国有企业。(20)Hall B, and Maffioli A,“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s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8,20(2): 172-198.中国国有企业同样具有这种功能,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远高于西方国家,其在基础研究上的优势更加显著。在现实经济中,基础研究投资密集的产业,大多属于中间产品部门。自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方针后,中国国有企业已逐步退出了一般竞争性领域,目前主要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非竞争性领域,2015年底国有企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 21.2% ,但在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占比超过了50%。(21)叶静怡、林佳、张鹏飞、曹思未:《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作用: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这些领域都属于中间产品部门。不仅如此,由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有更长的历史和更多的技术积淀,因而在基础性、通用性的技术进步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22)金碚: 《技术创新离不开国有企业》,《中国质量》2015年第7期。
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和正外部性,使其可以在中间产品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可以在三个方面降低中间产品创新中的不确定性。首先,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中间产品创新,降低了最终产品部门所有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其次,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后的国有企业多为大型企业,符合中间产品创新需要大型企业长期投入的要求,这就降低了中间产品创新的不确定性;最后,国有企业在历史上通过“干中学”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也可以降低中间产品创新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具有降低创新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功能,它本身就可以被当作一种促进全产业链技术创新的产业政策。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自主创新应主要依靠民营企业。(23)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这种看法仅仅关注了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创新效率,而忽略了国有企业在宏观层面的知识溢出效应。(24)有证据表明,国有企业微观创新水平低仅仅是局部现象,并不是普遍现象。参见李政和陆寅宏:《国有企业真的缺乏创新能力吗——基于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与创新绩效的实证分析与比较》,《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2期。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这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优势。目前合适的做法是利用这种资源优势,通过支持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来实现中间产品的创新,从而发挥其在全产业链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作用。
总之,作为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起点,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而中间产品自主创新则需要高强度的政府干预,尤其是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区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角度,讨论了自主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本文的论证表明:(1)由于中间产品创新的不确定性和转换成本效应等问题,仅有最终产品自主创新是难以创造足够的新需求的。相反,由于中间产品自主创新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该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有利于加速下游最终产品的自主创新,从而在全产业链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因此,中间产品自主创新是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关键环节,国家要实施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产业政策,应该以扶持中间产品自主创新为重点内容。(2)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的,而中间产品自主创新比最终产品自主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高,因此需要高强度的政府干预和政策扶持。(3)国有企业可以作为政府弥补研发市场失灵的工具,促进中间产品部门的自主创新。
在廓清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实现路径的基础上,本文对以自主创新的方式扩大内需提出了几点初步的政策建议:第一,合理确定扶持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政府对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可以采取提供种子基金和税收优惠等形式,对中间产品自主创新则需要采取政府直接出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和采购中间产品等形式。切忌将中间产品自主创新交给市场决定,对最终产品自主创新强化政府干预的政策组合。
第二,推动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是目前中间产品自主创新的主力军,所以其创新效率对扩大内需具有关键作用。当前应进一步推广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业绩考核等已被证明有效果的改革形式,以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
第三,推动自主创新成果的转化。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的自主创新,都有一个转化为产品的过程,尤其是对于中间产品来说,这个过程消耗的资金和时间可能会更多。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可以出资建立专门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对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的过程进行补贴,尤其是要重点补贴中间产品自主创新的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