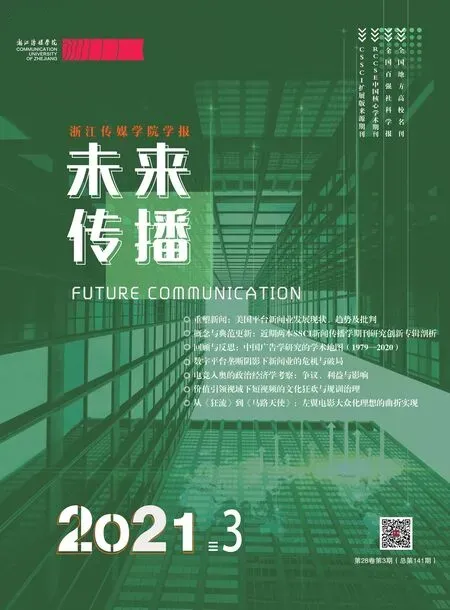作为哲学的影像空间:电影《暴雪将至》中的“异托邦”建构
王 健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理论对外部真实空间进行了“差异地学”研究,在他看来,客观存在的空间未必就是唯一的、最本质的空间,空间之外仍然存在断裂性、颠覆性、差异性的“异托邦”。在这个特殊的空间形态中,社会文化常态、权力关系被颠覆,中心价值也被解体,主体陷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因此,“异托邦”往往呈现出的是一个异类的、被漠视和遗忘的文化现象。福柯认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1]也就是说,这个另类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对立的基地。
电影《暴雪将至》将时间的坐标定位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变革的转型期,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因此,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使得影像文本中的现实空间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文化话语相抗衡的“异托邦”特质。无论是阴冷潮湿的雨天街道还是行将拆除的国有工厂都构成了一种“异质—对抗”的空间关系,空间成为影片生成意义的一个重要符号表征。《暴雪将至》作为一部集犯罪与悬疑、推理为一体的类型片,虽然延续了传统类型片的叙事逻辑,正如布雷蒙所分析概括的“叙事序列”:“可能性”(欲望、需要等)——“采取行动”——“行动结果”[2],但是,在设置情节、揭示悬念、汇聚外部张力的同时,影片更注重对社会空间内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阐释,“可能性”成为叙事环节中最重要的矢量。而恰恰正是这一“异质空间”(濒临拆除的工厂、泥泞肮脏的案发现场、不断游动的警车等)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冲突与对抗,使得主体被迫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构成了影片倾向于社会批判的文本建构逻辑。
另外,基于电影中的现实社会空间,经由叙事的表意功能、影像符号的意涵指涉,使得空间内部发生畸变,并宣告与日常生活经验下的现实空间决裂,第二道的“异质空间”由此生成。但是这个空间是一种心理补偿式的、幻觉性的“异托邦”,是异质的影像内部的文本空间。例如片中余国伟作为劳模站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但是时隔多年,却被告知当年从未举办过所谓的“表彰大会”,导演无意告诉观众真相,而是将“真与假”并置在了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内,营建出一种“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式”的内心世界,虚构与真实、时间与空间的常规秩序被颠倒,一个异类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文本空间被建构起来。
综上,影片共指涉了两种“异托邦”。第一种是功能性的物理空间也就是电影文本中呈现的现实空间,作为被划定为反常态的真实位所,直接参与到叙事流程中成为故事发生的真实场景,或者从视听表征层面上构成声画系统从而连接成电影整体;第二种是叙事流程本身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亨廷顿认为:“异质空间存在于空间之间,在空间的关系之中。”[3]电影中的现实空间与文本空间在功能层面发生关联,前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景观,所表露出的意识形态被凝聚在了影像的文本内;后者文本空间成为电影中现实空间建模的依据和参照。因此,这两种同为“异位”的空间是辩证的、耦合的,现实空间侧重于文化地理学的范畴,强调空间地理本身的特质,而影像的文本空间则是一种符号化的隐喻意指。
下文将进一步厘清电影中“异托邦”的建构逻辑,并结合《暴雪将至》文本本身去分析影片中异质化的现实空间与文本空间、电影叙事与空间的关联,从而去论证电影中异质空间的文化指涉功用。
一、 “异托邦”的建构逻辑:现实主义与“吸引力电影”
近年来,以电影《钢的琴》《白日焰火》《地久天长》为代表的一系列根植于本土文化语境、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症候的国产影片引发了国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类题材的影片通常将故事的背景定位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中,这个时间节点所呈现出的嬗变与疏离使得影像文本趋于一种对记忆与想象的解读,是一种对“无意识”的表述。“人与空间”的关系成为影像文本的建构逻辑,从而在异质、变异的空间中生成主体的生命体验,并且通过隐喻、象征的意义阐释其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分析这类影片的共性,很容易将它们归纳到具有一定社会批判倾向的现实主义电影行列,《暴雪将至》所反映的便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工人所面临的主体身份危机和生存困境,影片中呈现的现实空间在不断变革的社会进程中是滞后的、另类的,摄影机在废弃的工厂、泥泞的街道上游移。也正如当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提出的主张——“到街头去”,因为空间社区本身的物质性就使其被赋予了某种真实的、现实的意义,这种镜头下的“异质空间”也恰恰符合主体在主流社会秩序中所面临的处境。凯文·林奇指出:“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个都反映了相当一些市民的意象。”[4]因此,现实空间直接指涉的是个体和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感知、体验和记忆,它同时也覆盖了整个权力、知识体系下的社会关系,成为现实主义电影中一个概括的、综合的重要组成因素,而电影中异质的城市空间作为常规秩序的对立面也使得现实主义更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将“异质空间”与“现实主义”并置的原因在于,首先现实主义电影的认识论是感知与物质现实的同一性,而其本身的文化性使之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罗西里尼指出:“电影应当成为一种同其他手段相同的手段,它也可能比其他手段更为有用,用它来谱写历史,留下正在消失的社会痕迹。”[5]现实主义电影将视线投射在被排斥和被禁止的对象上,去观照秩序之外的空间里的边缘人群,这一点与福柯所描述的异质空间是契合的。福柯指出:“有一些特权性的或神圣的或禁忌的场所,它们服务于那些处在与其所生活的社会和人类背景相关的危机状态中的个体,诸如青春期的男女、排经期的妇女、老人等等。”[6]在异质空间中,这些特殊的人群在社会实践中被联系在了一起,也正如福柯分析“异托邦”的多样性形态时提出的危机异位和偏离,现实主义电影中所建构的也正是这种危机、另类的“异托邦”。例如在电影《钢的琴》的开始,主人公组建的乐队正在追悼会上演奏挽歌,而画面的后景俨然就是工厂冒烟的烟囱,它暗含了一种暧昧的、隐喻的空间指涉,而架构起全片主要矛盾的也正是国企改革背景下小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空间成为影片中重要的意指符号。
电影中“异托邦”的建构逻辑遵循的是福柯对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断裂”所做的思考,福柯认为:“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使存在的和不断存在的‘异托邦’发挥作用;因为在社会的内部,每个‘异托邦’都有明确的、 一定的作用。”[7]这里所指涉的“异托邦”就是由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所造成的,例如影片中的厂房、烟囱等异质空间,它们象征的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阵痛,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属性,是作为社会历史中“断裂”而存在的。包括《暴雪将至》《地久天长》《三峡好人》在内的现实主义电影,它们关注的都是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境遇,遵循的是一种小写的历史观,这一点与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是相似的,他并不拒绝关注社会的连续性,但这种“大历史”的前提必须是基于“断裂”。从这一点来说,福柯对于“断裂”“边缘”的关注恰恰是与《暴雪将至》的时代主题相契合的,这也使得影片中的现实空间具有了内部的意义,它不再是单纯的现实物理空间,更是连接着社会历史的“异托邦”。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之所以与电影具有同构性,是因为在福柯看来没有一种文化不生产异质空间。那么作为文化的电影,同样是在生产异质空间,这也由此构成了电影《暴雪将至》的“异托邦”建构逻辑,并且作为哲学的影像空间也为电影的本体研究提供了思路。
回到电影文本本身,主人公余国伟作为一名编制外的工厂保卫科协查人员一心想借“连环杀人案”展现自己的才能,从而破格进入到体制内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编制”构成了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因为“编制”在中国社会生态里象征着话语权,它使得主体在身份上拥有某种合法性。在影片空间的建构中就被嵌入了这层权力关系——例如案发现场反复游动的警车,作为一个封闭的禁区,它对外界是排斥的,是暴力、霸权的象征,人们是无法自由进入的,片中余国伟多次钻入警车,以体验和享受短暂的“编制内”快感来获得心理补偿。但是,工厂、街道所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种“编制外”的末日景观,这两种空间在影像文本中并置、叠加,权力冲突和社会矛盾在其中也由此被表露出来。我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确定不同的基地, 且彼此之间不可跨越, 更不相重叠,所以空间要经由关系而确定。[8]因此,也正是这两种极端的、各自对立的场域所表征出的空间关系建构起了这个象征权力冲突和社会矛盾、充满怪异与荒谬的“异托邦”。
可以得出结论,在这几部影片中,“空间”以独具个性的面貌传递着某种意识形态话语,经由电影语言在视觉和听觉层面上的整合,形成了风格化的或者是奇观化的“吸引力电影”。“吸引力电影”是早期的电影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不把电影看作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是看作向观众呈现一系列景观的方式,因为电影所制造的幻觉力量和异国情调可以让观众为之着迷”[9]。之所以将它们称之为“吸引力电影”,是因为尽管这几部影片被打上的标签是情节剧,但是电影空间的指涉意义是大于情节本身的,是空间中的异质,偏离建构起了电影的叙事系统。例如,《暴雪将至》的叙述逻辑并非是遵照情节线索找出杀人凶手,而是倾向对“谁造就了凶手”进行社会推理,强调社会背景的“催化”作用,以此来分析在这一“异托邦”中人的异化过程,空间就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隐喻与象征都被隐藏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中,叙事对于观众而言就不再仅仅是靠外部的情节张力来推动,更多的是依赖观众在空间内部进行感知上的探索。
电影《暴雪将至》中的“异托邦”建构方式具体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从“作者论”角度,在影像空间的建构上镶嵌了电影作者的世界观和哲学观,由素材以及个人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去生成现实空间的内部意义,就像上文列举的电影《钢的琴》,它传达出的同样是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是从“观众认知学”层面,电影中异质空间作为一种刺激性、奇观化的视觉效果,会与观众产生凝视与叙事上的关联,是观众心理决定了电影叙事意义的生成,是观众的知识建构起了叙事流程本身所构成的文本空间。此部分的论述旨在揭示电影中的“异质空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作者与观察者在情绪上共同合力的结果。这不仅有助于下文对《暴雪将至》在空间建构上进行美学与叙事分析,也有助于发掘观众心理在潜意识状态下对空间所产生的感知与理解,这是一种对空间符号的解码与破译进入到第二重文本的方法论。
二、“异托邦”的空间叙事:漫游与观察
“都市漫游者”一词最早在19世纪由波德莱尔提出,他认为漫游者是都市现代性的产物,他们在人群中不断张望、游荡,并以此为武器去对抗资本主义的“异化”。本雅明在此基础上认为,“漫游者”是在都市环境下衍生出来并具有一种社会批判意识的特殊人群。一方面,漫游者与空间是一个永恒的关系,是一群危险和偏离的个体在现代性的城市经验中以游动的视点去感知现实空间的真理游戏;另一方面,漫游者行走与凝视的漫游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作为叙事策略的话语,是通过漫游者的叙事视角生成了文本空间。
(一)漫游者与空间:感知、体验
在福柯看来,“异托邦”并非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而是联系着社会实践中某些特殊的人和事。[10]《暴雪将至》在人物设定上将一些与时代相悖的、处于危机状态的人置身于文本空间内,他们之中有保卫科科长、娼妓、下岗工人,还有行将退休的老警察,他们都是以一个“漫游者”的身份,穿梭在这个另类的、排他的空间中,包括视觉隐喻下具有时代特色的筒子楼、旧工厂、理发店、舞厅,这些空间都凝聚了令人在感知、身份、欲望上产生情感的事物,譬如男子失业导致情绪失常捅死妻子、工厂在爆破中被拆除以及舞池里男女相拥,寓意着在转型的“末日”到来前,一群危机个体在“抱团取暖”,这个异质空间所蕴含的危险性符号,都经由漫游者游动观察的视点生成了一种“漫游者”与空间紧密联系的文本机制,即以人物为视点,去探索可感的社会空间。
《暴雪将至》塑造了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漫游者形象,余国伟作为一名体制以外的保卫科干事,时常沉湎于自己“余神探”这个称谓中,试图以一己之力去侦破案件,从而进入警察编制内。他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试图用一种英雄主义的“骑士精神”去挑战现有的秩序。因此,余国伟本人就构成了一个“异托邦”,他同时构成了一个两种文化与话语并置的断裂带。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界限中,余国伟试图从被他者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抽离,进入到权力体制下的国家机器中去,即使对“杀人案”的侦查并非他的职责所在,他也尽心尽责,将被纳入警察编制的希望寄托于对此案的侦破,日常中的一举一动也俨然一副警察的模样,他手持警棍手铐,随时暴力执法,也正是通过自身建构起的心理补偿与幻觉空间来表达其对当下处境的抵抗,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反讽油然而生。余国伟本身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符号,导演尝试通过对空间环境的营造去建立起主体之间的关联,以证实世界是一种符号的“相似性”存在,贯穿全片连绵不断的雨水、广播中对“大雪”的预报,都将来自于大自然的“风暴”指向了大环境中所有人的命运,这种诗意的空间意象隐喻了社会“风暴”下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每个人都是漫游者,是空间的中介者和反思者。
“漫游者”作为一个解读现代性空间的符号指向,在影片中它们都是以一种批判的、流动性的眼光去审视城市空间中的现代性症候的,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对空间进行破坏和重建。
(二)漫游者与叙事:断裂、风格
漫游者作为叙事主体,为影片提供了一个异于常态的、与“英雄神话式”崇高美学相悖的叙事视角来实现对现实空间的重新认识;而作为叙事客体,漫游过程同样也构成了以漫游者为中心的叙事策略,空间内潜在价值与隐喻意义也经由这种叙事思维被发掘出来。下面将阐述《暴雪将至》的叙事策略并分析与之相匹配的影像风格,因为文本空间的建构也正是叙事与视听要素高度统一的结果。
《暴雪将至》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特质,这主要体现在故事的结构、情节的组织、事件的贯通上突然出现了某种“意图性”的畸变,即表层的叙事指向由外部张力作用下的“逻辑推理”迈入展示主体内心思想“异化”流程的“社会推理”,情节动力骤然地被置换为“心理冲击力”。这种叙事策略所产生的裂隙,使得影片具有了两种叙事模式冲撞后才能迸发出的“异质”景观;而这一“异质”景观也使得影片突破、超越了类型电影的“叙事神话”,转向一种触发观众深层次思考的“介入式”“沉浸式”的电影哲学观。另外,经由导演创造的视听感知空间,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声、光、环境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空间压迫感,都将观众对影片的认识纳入人物和环境的整体观范畴中,使之成为一种贯彻导演叙事意图的重要“环境张力”。
作为导演董越的处女作,《暴雪将至》无论是情节的设置,还是节奏的把握、视听的构思都是一部完成度极高的作品。但是,导演无意只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事件,而是更重视文本所产生的语境,使意义大于事件本身。整部影片都围绕着“追凶”来铺陈情节。“欲望”作为驱动文本发展的动力机制使得主人公余国伟迫切想通过侦破此案来获得认同感,这种叙事的逻辑似乎更接近一种近似“存在主义”的表述,一种主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找寻,并在这一进程中自己将自己异化。余国伟的探案过程,也正是他“异化”的过程,为了引诱罪犯,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爱人燕子,他的徒弟小刘也因他而死,这种近乎病态的渴望使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亲手葬送两条人命的“作恶凶徒”。影片的前半部分,充满了探案过程中的对抗和冲突,余国伟在这一叙事序列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独到的探案才能,案件经由他的视点变得扑朔迷离,谜底也渐次被揭开,情节所蕴含的丰富信息量使影片节奏紧张而富有张力。从余国伟指导徒弟模拟案发现场寻找线索到工厂追凶,剧情的发展在环环相扣中不断向前推进,辅之以影像中的雨水、泥土、建筑所呈现出的质感,在观众看来故事似乎要被推向“白热化”。
但是峰回路转,叙事结构由于徒弟小刘在追凶过程中的死亡发生了断裂,凶手的逃脱使得余国伟对案件的侦查陷入了停滞,这个意外性干扰因素使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强度被削弱,进而转向了一种趋于静态的内心写实,叙事的重心也由快节奏的“推理”“悬疑”位移到克制的情绪化表达上去,余国伟病态的欲望与燕子得知自己其实是诱饵的绝望,共同构成了后半部分的情绪张力,一种人物与空间呈现出的“异化”关系被凸显出来。也正是由于“情节张力”到“情绪张力”的变异,使得外力作用下的叙事调性转入体验和反思个体内心矛盾中去,影片背后深层的思想也由此得以释放。
漫游者在漫游和观察中与现实空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即便这个空间浸染了主流的权力秩序,漫游者依然可以在此过程中通过注入某些话语策略来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现实空间的“异质”特征也由此被表述出来。譬如,片中“警车”只是一个实质的空间片段,但在余国伟看来则是一个象征了权力与话语的、具有幻觉性质的“异托邦”。另外,通过畸变、断裂的叙事策略去发掘文本背后的社会伦理价值,这种以漫游者为叙事视角的实践方式直接构成了“异质”的文本空间,从而得出结论:异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弱势者的社会实践在主流社会的宏大叙事所建构的空间中造就的空间断裂带。[11]
三、“异托邦”的空间隐喻:废墟与寓言
我们在全文中不断地将福柯的哲学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影片中去分析,不是为了将其规约为一篇电影批评性质的文章,而是运用一种实证性策略,来论证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在电影研究中具有的理论价值。在下文,我们会把《暴雪将至》中所呈现的“异托邦”空间形态归纳为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废墟”,以期在符号的意指功能中,窥见偏离、荒凉的物质碎片背后所潜藏的寓意和象征,并在隐喻的意义和观众的经验意义上进入到影像深层的第二重文本。作为以影像化表达为基础的艺术,电影意象是真实性、假定性、象征性与隐喻性的统一。[12]因此,对于电影而言,表层的空间影像远非只是被作为一种叙事功能的物质载体,同样也是一种散发着社会文化性、具有深层指涉作用的表意图像。
电影透过文本的表层结构将不同的物质场景加以整合和重建,使之具有了一种隐匿的影像修辞。例如,影片中的工厂、铁路、街道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物质载体,但是如果将这些空间在叙事流程中并置和叠加,让彼此间产生联系,那么这个重构的空间身上的意涵就能够被激活。福柯认为,“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7](55)就他的观点而言,“异托邦”表达了一种一般空间所没能反映出来的文化意指,它的定位应该是并置和叠加,是在不同场所的并置和叠加中构成象征符号系统。福柯举了个例子,认为“花园”就是带有复杂叠加意义的异位,“波斯人的传统花园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在它的长方形内部, 应该集中四个部分, 代表世界的四个部分”[7](56)。所以,影片中“异托邦”的本质实则就是类似于“花园”一样的理念凝结体,是被组建的整一性意识形态载体,换言之,工厂、街道、铁路这些景观的叠加构成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历史过渡时期的缩影。我们可以将这个异质的“世界”归纳为本雅明口中的“废墟”。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论述了巴洛克悲悼剧里所充斥着的废墟意象,他把“废墟”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对象,它代表在整体意义上的崩塌,而以破碎的“寓言体”来表述,用“寓言”的方式来表达“废墟”的存在。[13]“废墟”在建筑学意义上指的是建筑物在遭受破坏后的剩余物,但是,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来看,“废墟”是一个抽象概念,象征着一个时代消逝的衰亡意象,它代表的是同一位所的文化迁移。在《暴雪将至》中随处可见的废墟景观,暗含了历史行程中的不同意义和价值观,或者是不同的历史的运作状态,在时代更迭的夹缝中,它就构成了一种既象征着衰亡又象征着新生的“异托邦”。导演通过引入一件犹如寓言般荒谬的“凶杀案”,来打破“旧秩序灭亡,新秩序建立”的和谐统一模式,从而穿透人性深层去暴露社会转型期中人的异化和疏离,并借助“废墟”来表现社会变革下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在这个怪诞离奇的“凶杀案”中,探案者、杀人者、受害者似乎都无法跳脱出宿命论的桎梏,就像余国伟不仅是探案者也是间接杀人的“凶手”,这就是寓言中典型的异化逻辑,以一种“不可理喻”的姿态来达成反讽与玩味之感。
故此,电影中“废墟”与“寓言”的关系,可以得出一个推断:“寓言”用“言此及彼”的策略来展现“废墟”的状态;而“废墟”则用一种时间的批判性分析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从而生成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隐喻和寓意。
《暴雪将至》中的“废墟”景观作为体现影片特质的重要元素,它通过象征这个时代衰亡的社会意象来透视人的生存状态,用荒芜、破碎的空间碎片来表现疏离、偏执的“寓言体”。影片为展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使用了大量具有纵深感的中景构图,将空间重新组织和编码,使得人物的生命体验与现实物象紧密地维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意涵系统。首先,“人”作为时代危机下的个体,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异质空间”,摄影机将之投射到空间意象中便构成了一种两重空间的“合成”效果,巧妙地指代了两个空间的生态关系,由此迸发出强烈的超乎声画组合意义的深层心理认知。其次,这种“合成”效果的主旨不再仅仅是为了呈现故事,而是经由这种共时性关系来强调空间自身的表现力,观众可以在这种被称为“空间蒙太奇”的并置影像中汲取更多信息,从而通过某种价值尺度对之进行思考和评说。在电影的开始部分有一组镜头,余国伟出狱后行走在残破的围墙边缘,他扭过头将视线聚焦到了过去的自己:一辆摩托车在摄影机的注视下驶过围墙,随后视野开阔起来,摩托车与废旧的工厂景观逐渐融为一体。这种模糊了现在与过去界限的“合成”方式,既是时间的延伸,也是空间的转换,在诗意化的视觉意象呈现中,凸显了“废墟”所具有的隐喻和寓意指征,对人与空间关系的思考由此也成为贯穿整部影片的问题域。
本部分引入“废墟”与“寓言”这两个概念,旨在强调一种用意识、注意、感性的方式去提炼影像中本质理念的方法论,而“废墟”与“寓言”指涉的也正是本质化的空间隐喻,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影片开头的片段,用一种“空间蒙太奇”的感知方式来领会“废墟”传达的理念。这是一种类似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这种无意识的思维定式,将影像表征的外在联系和客观联系转向内在的深层意旨。一方面,“废墟”是从影片中现实空间里抽象出的概念,它已然超出了空间地理的范畴,是理念的凝聚;另一方面,“寓言”实则就是文本空间的叙事逻辑,是一种包含了象征、隐喻的意指方式,两者在电影文本中互渗、交织,终极意义下的空间隐喻由此生成,一道“异托邦”之门缓缓开启。
四、结 语
《暴雪将至》这部电影用一种历史的叙述去思考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影片通过描写社会转型期中主体的身份危机,来营建出一个昔日的主流话语被边缘和禁止后所产生的“断层”和“差异”,也就是福柯所提出的“异托邦”。这个异质空间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下历史书写的消解,它强调少数、边缘人群的历史经验,在对现实的表述和叙事中,蕴含着大量的异质元素和策略,由此构成了影片的“异托邦”空间形式:首先表现在影像中具有特殊文化意味的现实空间;其次是经由叙事策略对客观世界进行的重塑形成的文本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升华到空间隐喻形式即“废墟”与“寓言”。这条线索同时也构成了文章的行文逻辑,即先分析电影中“异托邦”的建构逻辑,再深入到文本中阐释“异托邦”在影片中的实践方式,最后从空间实践中深化出深层的符号隐喻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