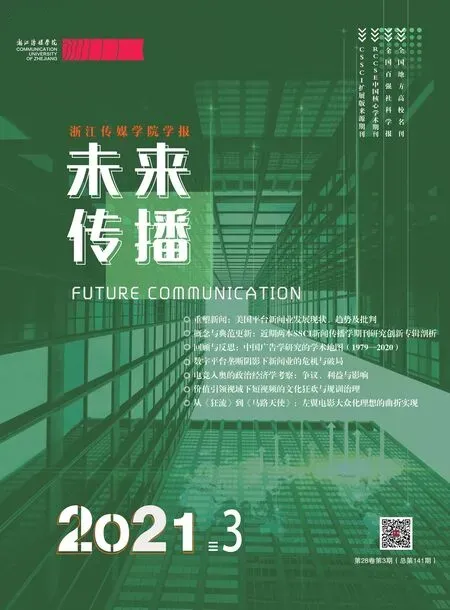当代中国舞台上的尤金·奥尼尔戏剧
韩德星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西方戏剧的引入与搬演是我国戏剧现代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动力,同时,它们也与本土剧目一起,成为我国戏剧及舞台演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搬上舞台的剧作中,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的作品无疑占有非常夺目的位置。如果从1923年2月洪深根据奥尼尔《琼斯皇》改编的剧作《赵阎王》在上海笑舞台公演算起,(1)关于《赵阎王》是不是《琼斯皇》改编本曾经有不少争议,至今依然有学者认为1930年北平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演出《捕鲸》才算是国内的第一台奥尼尔戏剧演出,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赵阎王》无疑是地道的本土化改编本。汪义群先生认为,洪深1935年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撰写的《导论》中坦承自己作品确系对奥尼尔《琼斯皇》的改编,这一公案已经了断。参见汪义群的《奥尼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288-289)。奥尼尔剧作登上我国舞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演出侧重于奥尼尔早期与中期作品,包括《琼斯皇》《马可波罗》《天边外》和《榆树下的欲望》4部剧作,以及《捕鲸》《战区内》《东航卡迪夫》《漫长的归程》和《早餐之前》5部独幕剧。演出这些剧的大多是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学校剧社,如复旦剧社、上海劳动大学那波剧社、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剧社等。他们的演出推动了当时戏剧观念的变革和我国小剧场运动的发展,为我国戏剧现代性的生成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当时我国现代戏剧毕竟处于起步阶段,无论从演出水准、社会影响力,还是从对原著的理解程度、阐释能力和改编质量来看,解放前的这些演出都存在不小的局限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原因,奥尼尔戏剧未出现在中国舞台。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全面涌入,对奥尼尔戏剧的翻译与研究越来越深入,戏剧从业者和观众在艺术审美与人文观念上都有了很大提升,具备了接受奥尼尔的前理解和期待视野,奥尼尔戏剧的改编和演出才真正步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奥尼尔戏剧演出的“狂飙突进”
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戏剧演出的黄金10年,奥尼尔戏剧的搬演也在80年代后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第一部被搬上新时期舞台的奥尼尔戏剧是其早期的现实主义剧作《安娜·克里斯蒂》。该剧最初于1982年5月至6月公演,由中央戏剧学院(下文简称中戏)表演系78级学生演出。此前一年,作为教学剧目,在该校导演系79级和78级进修班分别演出过部分片断。[1]该剧情节并不复杂,而难在“情”的演绎与表现,身为女性导演的滕岩用巧妙的构思来呈现人物细腻复杂的情感和心理演变。比如,在第二幕幕启时,原剧中摆着粗缆绳、马嚼铁的局狭脏乱的运煤船船尾被改成了干净开阔的甲板,剧中安娜穿的“黑色油布上装”换成了一件葱芯绿的衣裙,胸前佩有飘带,肩上披着长长的白纱巾,远处隐约传来小提琴演奏的小夜曲。导演有意用亮丽的色调来衬托安娜经过十天船上生活后恢复健康身心、灵魂得以净化、精神迎来新生的崭新面貌,从而与第一幕的病态、疲惫、慵懒和玩世不恭形成鲜明对照,为后面爱情的萌生作铺垫。在处理第三幕即该剧高潮部分时,导演多次使用舞台停顿来塑造人物的激烈情感反应,道具上增加了白纱巾、求婚用的鲜花、带有十字架的链条,在第二幕和第四幕中,通过抽纱巾、抢十字架来表现男女恋人间瞬息变化的情感纠结。这些细节的设计及舞台灯光、音乐的运用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风格有明显的关联性和相似度。这次演出取得了轰动效应,中央电视台给予转播,《中国日报》英文版和其他报纸曾刊登剧照和评论文字,[1](151)奥尼尔的书甚至也成了热门读物。
《安娜·克里斯蒂》首次公演就掀起一个搬演高潮,不久,上海戏剧学院(下文简称上戏)、长春话剧院、西安市话剧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话剧团等单位也将该剧搬上舞台。[2]影响较大的是1984年秋美国奥尼尔戏剧中心主席乔治·怀特来华导演的改编本《安娣》。怀特曾于1980年5月来华访问,并观看了人艺演出的话剧《骆驼祥子》,当后来中国剧作家黄宗江等人受邀访美并与他协商到北京指导一部奥尼尔剧作时,他选择了《安娜·克里斯蒂》,并建议将故事发生地点由纽约、普罗文斯顿和波士顿改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把角色改为中国人,他相信这样中国观众就会认同为旧中国发生的故事,进而产生共鸣。[3]在具体改编和演出中,安娜改为安娣(麻淑云饰),她在母亲去世后被送到了哈尔滨,其父是名叫老桂(全名郁桂峰,鲍国安饰)的福建水手,而爱上安娣的是皈依天主教的广州水手马海生(薛山饰),老妓女玛西更名为眉嫂(娄乃鸣饰)。第一幕的场景是在上海黄浦滩的一个小酒馆里,后三幕则发生在黄浦江一条驳船上。
这部剧从排练到演出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但正如怀特所说,中国话剧演员接受的训练与美国演员一样,“都出自同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统”[3](108),因此省去了不少麻烦。滕岩作为副导演,协助怀特排戏,著名美籍华裔舞美设计师李明觉负责舞台设计,服装和灯光设计师也是怀特从美国带来的专家。该剧采用了写实的布景,风格朴实明快,“舞台上看不到矫揉造作和装腔作势的表演,也没有那种空泛的抒情,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亲切动人”,鲍国安表演沉稳,富于表现力,“随时都能让观众看见这位饱经风霜的老水手的复杂微妙的心境”,麻淑云的表演“粗犷泼辣而有内心生活”,娄乃鸣善于抓住人物性格,“轻松自然地使人物活了起来”。[4]但如丁扬忠先生所言,这部戏在改编和中国化方面却有明显不足,即使人物名字中国化了,背景、故事、人物都移到中国来,“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言谈风貌,却难以做到完全中国化。在细心的观众看来,仍感到有些地方糅控不够,显得生硬,不尽符合中国生活习俗”[4](55)。究其原因,怀特在其后来的文章中谈到却并未意识到,即黄宗江先生的翻译和改编“只是改了一下人名、地名和‘老克里斯’所唱的歌词”,其余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翻译的”,[3](108)这样的改编只是抓住了中国化的皮毛,表达方式及承载的文化还是美国的,里外自然难以和谐。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上演的奥尼尔剧作还有《天边外》,1983年2月至5月由山西省话剧院演出,导演谢亢。中戏内部教学演出的《榆树下的欲望》(1983年9月)和《漫长的旅程》(即《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片断,1984年6月),导演均为张孚琛。1986年,中戏表演系82级学生毕业演出奥尼尔三联剧《悲悼》的第一部《归家》,亦由张孚琛导演。1985年底至1986年初,沈阳话剧团请张孚琛作总导演,朱静兰作导演,排练和演出了《榆树下的恋情》(即《榆树下的欲望》),这是该剧首次在国内公演。在人物塑造和表演上,导演同样采用斯坦尼的方法,“要求演员向角色靠拢,再现当时当地人物的风貌,在化妆、服装和形体设计上,下了很大功夫”[5]。扮演老凯伯特的吕晓禾一扫他在银幕上的深沉质朴形象,紧紧把握住凯勃特内心强硬而又贪婪的性格,把一个美国农场主老爹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伊本的饰演者苏金榜扮相英俊,“表演具有高度的控制能力”,“很有层次地表现了人物心理冲突的发展轨迹”。饰演爱碧的朱静兰则“善于运用眼睛、表情和声音的微妙变化,表达人物瞬间的心理”,其顺从欲望而犯罪的场面,“产生令人战栗的效果”。[5](13)该剧在沈阳成功演出后,又到哈尔滨、大连、上海、北京等地巡回演出51场,[6]几乎场场爆满,反响巨大。
当时我国戏剧舞台正热衷于演绎种种现代手法的实验戏剧,《榆树下的恋情》等剧的成功,让人们再度认识到写实主义的力量,对开始退热的现代主义也有了更多的反思与扬弃,“倾斜的舞台恢复了平衡,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风格样式并存的多元戏剧格局开始形成”[7]。
1988年是尤金·奥尼尔诞辰100周年,南京大学和国际奥尼尔学会在当年6月6日至9日联合主办“纪念奥尼尔百年诞辰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南京与上海还联合举办了“上海·南京国际奥尼尔戏剧节”,沪宁两地演出剧目多达11种。同年,在南开大学、中戏等院校也有相关研讨会和演出,该年可谓中国“奥尼尔年”,无论演出剧目和剧种数量,还是演出品质和观演效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戏剧节期间,先是在南京上演了4部剧作:由洛杉矶奥尼尔剧社演出的独幕剧《休伊》(汤姆·麦克德莫特导演),由江苏话剧团演出的《天边外》(熊国栋导演)、《琼斯皇》(冯昌年导演),以及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张孚琛导演)。其中,《天边外》作为改编本,将故事地点搬到了中国的江南渔村,用写实的手法演绎三个中国青年之间爱情与人生的凄美故事,充满浓郁的中国风情。《琼斯皇》则被改编为一台舞蹈造型剧,融话剧、哑剧、造型、音乐、舞蹈于一炉,用视觉形象来呈现原剧中由独白表现的幻象,以夸张变形的人体动作传达人物的精神苦痛,将道白压缩至十几句,并删去第一场和第八场的现实主义外框,用造型语汇替代。这种大胆新颖的创意和设计虽未必能完整传达原作意蕴,甚至导致“观众难于理解戏的具体内容,进而对一些造型语汇莫名其妙”“别说一般观众,即便是一些读过剧本的人也看不懂”[8],但其焕然一新的风格还是得到了好评,半年后参加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戏剧节,获优秀演出奖。《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则是首度在国内舞台公演,中年演员王频成功刻画了剧中的母亲形象。该剧导演张孚琛4年前在中戏导过该剧片断,但在南京演出时,由于演出时间限制,一些精彩的独白被迫砍掉,同样未能完整地将该剧呈现给观众。
上海则推出了《悲悼》(复旦剧社,导演娄际成、焦晃)、《大神布朗》(上海青年话剧团,导演胡伟民)、《天边外》(复旦剧社,导演耿保生)、《悲悼》(上戏,导演张应湘)、《马可百万》(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杰克逊·菲宾)、《尤奕》(又译《休伊》,上海青年话剧团,导演胡伟民)、《啊,荒野》(复旦外文剧社,导演白荣光)等话剧剧目,以及上海歌剧院和上海越剧三团分别以歌剧和越剧形式演出的《鲸油》和《白色的陵墓》(改编自《悲悼》第一部“归家”)。(2)这些剧目有的在5月份就已上演,如复旦的《悲悼》和《天边外》,有的则由于开排较晚,推到了6月末,如《马可百万》。在这些剧目中,《尤奕》(即《休伊》)、《鲸油》和上文提到的洛杉矶奥尼尔剧社的《休伊》是在上戏实验剧场作为内部联谊演出,不对外售票,而其余公演的剧目中影响较大的是《悲悼》(复旦版)、《大神布朗》和《马可百万》。
《悲悼》由复旦大学联合上海市总工会等单位主创,主要演员除了上海青年话剧团(下文简称“上海青话”)的娄际成、焦晃、卢时初以外,还有来自北京和佳木斯的演员,舞美设计人员来自上戏。与上戏版的《悲悼》一样,该戏也是一个压缩版,将13幕戏浓缩为8幕和一个尾声,次要人物被砍掉,时长近3小时。焦晃在剧中搬演卜兰特和奥伦两个角色,因此省掉了奥伦杀死卜兰特的一幕,在下一幕中用幕后音的回忆形式来呈现。克里斯汀娜的扮演者卢时初“应付裕如,技巧娴熟”,“讲究控制,创造的形象含蓄浑厚,很少用大动作,但善于把握戏眼与节奏,只在一睥睨、一扬首之间就把高雅外表下包藏着的欲念和热情准确地表达出来”,[7](31)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大神布朗》是上海青话为戏剧节准备的一部重头戏。在处理剧本时,导演砍去了原作的“序幕”和“尾声”,删掉了玛格丽特三个孩子的戏,角色减少到7位,情节更紧凑,矛盾更凸显。“面具”的使用是该剧一大看点,但导演并未按照原作的描述设计一个个完整的面具,而是将其简化,只截取面具中间鼻梁和脸颊部分,演员面部其余部分露在外面,方便取戴,但过多暴露面部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后半段戴恩死去以后,饰演布朗的张先衡要一身两任,在“假戴恩”“真布朗”之间来回穿插跳跃,要演出两个角色的叠加效应,表现布朗内心冲突与人格分裂的痛苦。他的表演非常成功,带动了整部戏,在上海剧坛引起不小轰动。
《马可百万》是戏剧节压轴之作,由来自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中央剧院的艺术副总监杰克逊·菲宾担任导演。该剧时间跨度大,场景转换多,角色人数也多,在所有剧目中难度系数最高。演出时,26位上海人艺的演员轮番演绎80多个角色,每次换装时间限定在20秒之内,为便于换景,尽量制作轻便易挪的布景装置。同时,在背景中悬挂一块绘有马可·波罗旅行路线图的半幕,每一场开场之前用脚印在幕上标识出他们的所到之地,再配上不同的音乐与服装风格,让观众一目了然。菲宾谈创作意图时说,他追求这种流动性,是想“在剧场中造成一种电影的感觉”[9]。丰富多彩的服饰、不断变换的异域风情、古老动人的情感故事使这部剧有了众多看点。不过,在导演理念上,菲宾意识到该剧并非真实历史故事,因此并未在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做历史主义的还原,“确切地说,整出戏描述的是一个西方人(奥尼尔)对东方人的感受及思维方式深入研究后的印象”[10],他遵循原剧“写意画的风格”,“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和地方,留给观众以思考的余地”。[10](11)
同年,纪念奥尼尔的演出还有南开大学外文系上演的英语剧《啊,荒野》,及山东艺术学院兰英、王滨导演的《追猎》(《悲悼》第二部)。1989年,四川剧作家徐棻将《榆树下的欲望》改编成川剧《欲海狂潮》,在成都成功上演,该剧在2006年重排以后影响很大(后文详细论述)。著名先锋导演牟森曾于1989年率“蛙实验剧团”在中戏演出《大神布朗》,但据笔者了解,该剧影像已难觅影踪,也未找到相关评论,仅从导演说明书中得知,该剧本欲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在1988年秋天举办的纪念奥尼尔百年诞辰演出活动,后来活动取消,该剧演出也推迟到1989年初,并且“呈现给观众的演出还不完整”[11]。
二、20世纪90年代:奥尼尔戏剧演出的瓶颈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如董健先生所说,随着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的转变,戏剧演出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时代”转为“平庸年代”,戏剧市场冷落的表象反映了戏剧灵魂的丧失,一度作为人们精神资源的戏剧被商业化浪潮和电子化娱乐逼到了狭小的角落,无论观众还是导演,对严肃戏剧的关注越来越少。与此对应,我国奥尼尔戏剧的演出也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高峰直接跌入低谷。
据笔者考察,从1990年到1996年的7年时间里,仅有《榆树下的欲望》《天边外》《悲悼》《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4部奥剧被搬上舞台,前后加起来仅6次排演。1991年和1996年,演出阙如。1995年6月,由上戏、中戏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奥尼尔学术研讨会期间,上戏和中戏分别献演了刘云导演的《走进黑夜》(根据《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改编)和赵之成导演的《悲悼》。这两部剧不但在内容上做了大量的压缩,形式上也有很大变动,前者将原本4个多小时的演出浓缩到1小时20分钟,基本上演的是原剧第四幕,形式上则采用小剧场的分区演出,把4个演员分隔在舞台上毗邻的4个演区,每人身穿白袍,头戴面具,进行无对象表演和对话。后者则把三部曲压缩在2小时之内,通过年迈的莱维尼亚对往事的回忆展开情节,并删掉了卜兰特这一角色。[12]以先锋的形式演绎经典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话剧改编的基本征候,但过分的形式化实验会对经典造成伤害,因此这两部剧的演出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不小争议。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演出大都局限于大学校园,即使公演,受众范围和影响也非常有限,与20世纪80年代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贫乏的现象直到1997年才有所改观。该年5月3日至7日,中戏、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州市文化局及中山大学外语学院等单位在广州联合主办了第七届全国尤金·奥尼尔学术研讨会暨戏剧演出周,共演出了《安娜·克里斯蒂》(广州市话剧团,王晓鹰导演)、《早点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俞洛生导演)、《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上戏,张应湘导演)、《休伊》(中戏,赵之成导演)、《天边外》(广东省话剧院,鲍黔明导演)5部奥尼尔剧作,重新点燃了观众对奥尼尔的热情,“也给略显冷清的中国戏剧界带来生机”[13]。
在以小剧场形式演出的这5部剧中,除《休伊》基本按原剧演出外,其余四部皆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编。如张应湘执导的《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将两幕多角色剧缩减为独幕两角色剧,在舞台设计上,用一个象征意味浓郁的硕大黑人面具把舞台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为表演区,后面则随剧情的发展,“时而被假定为卧室,时而被假定为另一街区,同时也是演员换装和上下场的地方”[14]。作为独幕独角戏的《早点前》,也适当删减了罗芝太太的台词,仅用一块帷幕作背景,表演则极具写意化,“演员做一个手势就表示做早餐,喝咖啡,扫地等。早点用的餐具、炊具全由演员的动作表现”[14](65)。
而最受与会学者瞩目和争议的是王晓鹰导演的《安娜·克里斯蒂》,他不但把整个四幕剧中的第一幕删去,而且对第四幕也做了较大改动。王晓鹰认为:“删掉了第一幕,使得观众对安娜这个人物的认识和接受的顺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先看到一个身为妓女的安娜变为先看到一个面对大海渴望获得心灵净化的安娜,从原来先于老克里斯和麦特知道了安娜的身世变为与他们同时知道她的身世,从原来的以旁观者的心情等待着看安娜如何向两个男人说出事情的真相变为与老克里斯和麦特一起意外地得知安娜的隐秘身世。”[15]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使演出更有悬念,而且“更能使观众如同在生活中感受现实的残酷性一样去即时感受安娜内心的惨痛,并与老克里斯和麦特一起经历情感上的巨大震撼”,从而实现奥尼尔所要达到的“‘真正真实’的悲剧性效果”。[15](13)另外,在舞台布景和人物构成上,删掉第一幕,也就过滤掉了除三位主人公以外的所有次要人物,事件和情节更加集中,而场景也只呈现为后三幕的驳船上。这种安排应和了王晓鹰对小剧场的设计思路,他和舞美王履玮在传统舞台的附台(即侧幕)开辟出别具风味的演出空间,“剧场附台原有的建筑结构诸如灯光控制平台、测光楼、直上舞台顶部的梯子、天桥等等,自然形成了演区的立体空间结构”,“这个空间中原本就有的东西诸如消防栓、电风扇、对光用的木梯、放演出器材的箱子、成捆的绳子等,都十分妥帖地成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而后放进去的镜子、洗脸池、破油桶、废轮胎等,反倒像是原来就在那里的生活细节”。[15](14)而观众的座位就安排在大舞台的台面上,周围拉上黑丝绒幕,制造夜海气氛的蓝光“不仅投向演区也投向观众区,海浪声及还穿的各种音响从四周将观众包围,一种静谧而又浓郁的氛围始终将观众与演员紧紧融为一体”[15](14)。为了达到更好的“观演共享”效果,他们甚至故意打破该剧的现实生活逻辑,在作为驳船的演区中摆放了一张美式旧台球桌,破游戏机以及飞镖盘,以营造更为浓厚的心理共享空间和氛围。在处理最后一幕时,王晓鹰试图还原奥尼尔的原意及其悲剧美学追求,一改人们一般理解的大团圆式结局,删除那些情绪欢快的台词,“删去了安娜对未来生活的幻想”,让意识到将一同出海的老克里斯和麦特“拼命地大笑,笑得很惨”,并在结尾添加了安娜和麦特之间充满忧虑和阴郁的对话。[15](14)这种安排超出了不少与会学者和观众的期待,但却与前面的人物情节设计保持了一致,更接近于奥尼尔的整体戏剧观,体现了王晓鹰追求的“残酷戏剧”美学,将生存“虚假的影子”完全剥离。
20世纪90年代末,又有三次奥尼尔戏剧演出。一是1998年底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林洪桐教授执导的《悲悼》,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在12月4日联合召开的“奥尼尔三幕话剧《悲悼》研讨会”的观摩剧目,也是北京电影学院95级表演班的毕业演出。该剧以上海青话1988年改编本为基础进行改编,将时长6小时的13幕剧作压缩至两个半小时三幕剧,在保留基本人物关系的同时,更侧重体现和阐释原剧的悲剧精神。但正如与会学者们指出的,学生因太年轻,表演上“仍显得不足与浅显”,一些关键性的戏“显得功力稚嫩”。[16]另外,因为删节与压缩大半,导致一些情节过渡不自然,有断裂感,奥林与母亲的关系、莱维妮亚的两次心理转折等都铺垫得不够。[16](92)二是1999年3月在中国青艺剧场演出的《送冰的人来了》,张驰导演,冯旭改编,系戏剧电影报社与北京某旅游公司联合出品,北京天安文化投资咨询公司制作。这是该剧首次被搬上我国舞台,但这次商演反响平平,影响甚微。第二年5月,黄磊也执导该剧,作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97级本科班的毕业戏,于7月中旬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小剧场公演,时长3个半小时。演出较好地呈现了原剧第一幕的狂欢喜剧色彩,对人物性格的演绎也比较到位,但主题的表达偏离了作家原意,侧重正能量的传达。原剧悲剧性内核在于揭示所谓“希望”之虚妄的“白日梦”性质,这也是奥尼尔时代西方悲观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黄磊有意使其更具有本土化的乐观主义人生哲学。三是1999年6月在成都由四川大学和中戏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尤金·奥尼尔学术研讨会上演出的《欲海狂潮》,由成都川剧三团演出,沿用了1989年的川剧版本,但该剧在2006年经过重新改编以后才更加成熟,并产生较大影响,为了方便,笔者也放到下一节来阐述。
三、21世纪:奥尼尔戏剧演出的突破与勃发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洗礼,戏剧的边缘化与小众化已成定局,进入21世纪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络传媒无疑加剧了这种局面。但真正夺走戏剧地盘和灵魂的应该是整体消费文化中的娱乐化倾向,这种倾向只推动了个别导演、个别戏剧在小资群体消费市场的流行,而严肃经典剧作的演出则举步维艰。另外,从第六届开始就绑定奥尼尔学术研讨会的奥尼尔戏剧演出在21世纪延续了两年以后,突然随着该会议发起人廖可兑2001年的去世以及随后会议的更名而戛然止步。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廖可兑生前曾极力倡导将奥尼尔戏剧“中国戏曲化”,这一夙愿在新世纪得以完美实现,围绕《榆树下的欲望》的戏曲化改编,中国南北的两个文化腹地——四川与河南争相展开了热闹的“竞演”,使之成为21世纪以来最受关注的一部奥尼尔戏剧。
前文曾提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成都两地就出现了奥尼尔剧作的戏曲化搬演,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川剧作家徐棻根据《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川剧《欲海狂潮》。该剧于1989年2月在成都成功上演,四年后,欧阳奋强依照同一剧本执导拍摄了两集同名戏曲电视剧,在四川省电视台“川剧苑”节目中播出。此后,《欲海狂潮》多次在川剧舞台上重演,并在1999年于成都举办的第八届奥尼尔学术研讨会期间对专家们献演。从改编伊始,徐棻就抱着革新戏曲和现代启蒙的立场,她把自己的创作定性为“探索性戏曲”,与20世纪80年代川剧《潘金莲》(魏明伦编剧)、《红楼惊梦》(徐棻编剧)等探索戏一脉相承,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借戏剧针砭人欲横流之时弊,教化大众,拓展和提升戏曲的内涵,并探索传统戏曲艺术的“变”与“不变”。因此,她既把《榆树下的欲望》完全中国化、川剧化,同时又吸收奥尼尔及西方戏剧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创造性地将剧中“欲望”这一核心命题形象化,以蓝红阴阳脸、善恶相杂的幽灵般的“角色”自由穿插、贯穿始终,“只要剧中的某个人物的某种欲望到了不可遏止时,这个形象便会出现”[17]。在故事安排和人物设置上,她将19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农庄故事置换为中国封建时代四川农村的自耕农故事,将凯伯特改名为白老头,其三子分别为大郎、二郎和三郎,艾碧改为蒲兰,增加了茄子花(即原剧中提及却并未出场的敏妮)这一人物,他们的语言、气度、唱腔、插科打诨等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原汁原味的四川风情。原剧中的对话和叙述改为演唱与宾白,原剧3幕12场的结构改为3幕6场,每场标目,使矛盾更集中,进展更迅速,原著中译4万多字压缩至1万余字,但演出时长却变化不大。出于戏曲审美和文化接受的考虑,徐棻略去了原剧清教文化内涵,把白老头塑造成性格单一、贪婪自私的白老财,并依照国人的情爱观和戏剧观修改了原剧结尾,让亲手杀死男婴又失去情人的蒲兰和报案回来发现蒲兰已死而愧疚懊悔的三郎双双自杀,让白老头火烧田庄又在抢救财物时葬身火海,这种修改虽完全改变了故事结局,也背离了奥尼尔的悲剧观念,摒弃了西方悲剧精神中敢于担当苦难的生存意志和存在的勇气,但却相当吻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与口味。
尽管这一版上演以后得到了观众、专家学者乃至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官员的充分赞赏与认可,但2006年,当成都川剧院要重排《欲海狂潮》时,徐棻再次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删去了开头的一场半戏,减少了老大、老二两个人物,使矛盾冲突以更快的节奏向前发展;二是将蒲兰塑造为第一主人公,“使该剧更合乎中国戏曲的叙事结构”[18];三是把唱腔形式由川剧弹戏变为川剧高腔,高亢激越的唱腔和天衣无缝的帮腔更好地渲染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增强了整部戏的抒情性,委婉处动人情愫,撕心处痛楚凛冽,唱词则“几乎全部重写”[18](50)。同时,演员阵容也全部更新,由梅花奖得主陈巧茹、孙普协主演蒲兰和白老财,青年演员王超饰演白三郎,并新聘导演张曼君执导。舞台设计上采用可倾斜升降的台面,需要时两边升起,中间形成一个可以让角色行走的凹槽,或舞蹈的平台,两边的台面下方设有灯光和烟雾装置,升起的台面既可以是幽暗的房间,也可以制造烈焰火海,或烘托天塌地陷的内心情状,再加上黑色背景、白光照明,以及追光的巧妙使用,大气、立体、变动的舞台空间,极大丰富了整台戏的演出效果。这些改动和创新使得新版《欲海狂潮》与旧版迥然有别,受到了更多、更大范围的观众喜爱,几乎包揽了国内戏剧界各种大奖,如2006年的“全国地方戏评比展演”一等奖,“文华奖文化剧目奖”,2007年“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中国戏曲学会奖”等。2008年4月,成都川剧院还特地举办了北京奥运演出周活动,该剧在北京保利剧院和北大百年讲堂演出。2010年,该剧在东京参加中日韩BeSeTo戏剧节演出,2014年参加土耳其安塔利亚国际戏剧节演出,后又远赴美国华盛顿、纽约、亚特兰大等城市巡演,深得国外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及热情关注。至今,该剧仍不时在国内一些省市演出,成为当代川剧长盛不衰的杰作。
另一部将《榆树下的欲望》成功戏曲化的是曲剧版《榆树古宅》,由河南剧作家孟华改编。孟华在1997年参加广州奥尼尔研讨会时,廖可兑曾嘱其将奥剧“中国戏曲化”,1999年又参加成都奥尼尔研讨会并观摩《欲海狂潮》,2000年在郑州举办的第九届奥尼尔学术研讨会上,由他改编、谢亢导演、郑州市曲剧团承演的《榆树古宅》得以顺利演出,同年11月,获河南省第八届戏剧大赛金奖,2002年应邀赴美国加州、衣阿华州、明尼苏达州等地交流演出,大受欢迎。该剧在2006年又做了调整、重排和演员更换,更名为《榆树孤宅》,应邀参加在苏州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美国戏剧研讨会(前身即“奥尼尔学术研讨会”),并在苏州、南京、徐州等地巡演。孟华谈到最初选择该戏来改编,是出于剧中悖谬的“母子恋情”,有故事,有情节,有冲突,有爱欲与贪欲、性欲与物欲相互扭结的“情感复调”结构,比较符合河南人“要有戏”“一口气看下去不起堂”的赏戏需求,但也正是这样的戏,在排练时不断遭遇质疑和指责,被污蔑为“三级片”“流氓戏”“乱伦戏”。[19]戏剧决非单纯的审美,观众与地方戏的泛道德化倾向对编演形成很大的伦理制约,“如果故事和人物是新的,也必须符合观众心目中关于美丑善恶忠奸贞淫的标准。舞台艺术语言直接塑造的人物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在道德上不被接受的形象一定不被感情所接受”[20]。考虑到接受对象的道德取向和审美趣味,孟华做了一些妥协。他将柯泰与柯龙(即原剧的凯伯特和伊本)的亲生父子关系改为非血缘的继父继子关系,“这样就大大消减了‘龙碧恋情’中的‘忤逆’指向,使柯龙为母报仇的‘仇父情结’来得更清晰、更合理,因而缓解了观众对龙碧恋情的排斥心态,增加了理解与宽容”[21]。另外,在情欲表现上,除进行戏曲程式化处理外,还将艾碧主动跑到柯龙房间求爱改为后者主动跑到艾碧房间,以冲淡‘荡妇’的行为暗示。年龄上,也将二者差距由原剧的10岁缩短至5岁。这些改动弱化了乱伦色彩,使观众一步步接受了二人的恋情,以至于最后抹着眼泪看完全剧。[21](18)
与《欲海狂潮》一样,《榆树孤宅》在舞台表演方面,无论地点场景、服装道具、人物造型、话白语式、身份称谓、风气习俗等,都实现了彻底的“汉化”改造,完全消除形式上的隔膜。用抒情唱腔带动和感染观众进入剧情,运用戏曲的虚拟性和舞台动作的程式化手法,将原剧大段的独白和舞台提示简化为歌舞动作,又穿插滑稽谐谑的插科打诨,极受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但由于剧种不同,两部改编剧还是呈现出鲜明的审美差异,最明显的是前者由于高腔的使用在抒情性上要高于用真嗓演唱的后者;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与求变上,前者也更具有先锋性;在故事编排上,二者都有重大改动,但后者无疑更保守一些,更接近原著,既保留了柯龙两个哥哥的角色,又依照原著让老头子继续活着,让男女主人公双双戴着锁链走向旭日,以“结尾的明亮化”迎合中原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尾的赏剧习惯。但也应看到,无论结局如何处理,无论怎样改变人物关系,无论如何在心理学上脱敏,以及如何因观众单一化的道德评判倾向而被迫偏离奥氏的道德立场和宗教指向,这两部戏都很好地保留并呈现了原有的悲剧性内核——永恒的爱欲之痛,它们不过是以中国人的方式(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去诠释和理解这种悲剧性,“一个完全中国戏曲化了的奥尼尔”[21](18)通过这两台戏深入到了中国普通观众的内心世界,它们亦成为难得的西剧中化(戏曲化)的成功典范。
2006年,当这两部改编戏在热闹地重排与演出时,多媒体音乐舞台剧版的《榆树下的欲望》也在“激情上演”。该剧由上戏导演系教师刘志新导演,著名话剧演员娄际成出演凯伯特,曾在1990年上戏版《榆树下的欲望》中演出过的白永成出演伊本,并兼出品人和导演,艾碧则由香港影星翁虹主演。该剧自我定位为首部“情欲悲剧”,被称为“西方版的《雷雨》”,先后在京、沪、杭等地上演,在掀起“翁虹热”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轰动和争议。作为音乐舞台剧,它不同于传统话剧的演绎模式,没有大段对白,用大量的肢体语言传达人物情感,同时,运用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手段,将多媒体影像、原创音乐、时尚服饰造型和现代舞蹈等多种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借鉴周星驰《功夫》《大话西游》等影片中的时空变幻模式,制造角色灵魂出窍的效果,以呈现人物复杂的情感变化。“新颖”的演剧形式让一些观众开了眼,在视听上觉得独特、刺激、现代,也让另一些观众难以接受,感觉台词缺少连贯性,表演不到位,多样的形式反而破坏了原剧的严肃性。而其中为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欢爱,两位年轻主演脱得只剩内衣上阵,借助一块巨型白色纱布将二人裹在一起翻转,场面长达10分钟,甚至有裸露之处,引来不少非议,认为该剧有走“情色路线”商演的嫌疑。2007年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由任鸣导演了话剧版《榆树下的欲望》,这是北京人艺首次排演奥尼尔的作品,演出风格忠于原著,关注点更集中于财产的争夺上,在感情戏上并无僭越之处,但饰演艾碧的郑天玮和饰演伊本的王雷表演得非常有激情,节奏感很强,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此后两年,该剧多次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深得观众喜爱。另外,江西省话剧团于2013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国家大剧院于2015年也分别导演过这部剧作,尤其国家大剧院版,由沈亮导演,史可、张秋歌等名演员担纲主演,次年又在大连、上海、广州、中山等地做了为期两个月的巡演,将奥尼尔的这部剧作推广给了更多的中国观众。
除了《榆树下的欲望》,奥尼尔的不少剧作也在新世纪得以搬演或重排,如2001年12月在济南举办的第十届奥尼尔学术研讨会期间,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首次将《奇异的插曲》搬上舞台,2007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张奇虹导演也执导了该剧(2008年复演10场),他们都对剧作做了大量精简和压缩,将5小时的剧作改为2个多小时,尤其后者,更是将第一主人公由尼娜改为达莱尔医生,主题也从表现尼娜的复杂情感历程转向着重表现医生在经历情感折磨后毅然投身科学事业的勇气,迎合了我国的审美意识形态。此外,2001年2月,杭州的王复民导演了《安娜·克里斯蒂》,并赴澳门参加“杭港澳戏剧分流演出”;2002年1月,上戏学生在上海话剧中心演出了《安娜·克里斯蒂》和《榆树下的欲望》片断;2003年4月,王晓鹰复排《安娜·克里斯蒂》,在北京北兵马司剧场上演;2004年2月,上海师范大学在学校东部礼堂演出了《悲悼》;2005年8月,北京大学在“美国戏剧与英语戏剧教育研讨会”期间上演了英语版《啊,荒野!》;2013年9月,上海新光剧场公演了8场由曾饰演过布朗的张先衡执导的《大神布朗》,以纪念奥尼尔逝世60周年及该剧在上海首演25周年。2013年2月,王晓鹰导演、孟华与青年编剧丛笑改编的甬剧《安娣》在宁波首演,当年11月参加在杭州举办的第十届浙江戏剧节并获奖,2014年10月赴美演出。该剧也可看作是对1984年怀特版《安娣》的致敬(王晓鹰当年曾参与此剧音响设计和演出操作),采用了同样的年代背景和地点,原来的父亲郁桂峰改为郁安家(谐音“欲安家”),水手马海生改为赵大刚,老妓女眉嫂改为梅香。同为四幕戏,不过在第一幕中减少了安娣与梅香的交流,未暴露安娣的“职业”身份,以便为第三幕的情感爆发留下足够的心理空间。同时又在第四幕开头加添了梅香的戏,让她与骤然“失去”爱情的安娣一起惺惺相惜,忘情对饮,抚慰安娣的伤痛,体现底层人的善良品格。可以看出,这种情节安排一定程度上秉承了王晓鹰话剧版《安娜·克里斯蒂》的思路。另外,该剧在安娣的“妓女”形象与性格设定、戏剧的抒情化处理等“中国化”方面也做得非常到位,让甬剧的观众不觉得隔膜与生疏。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安娜·克里斯蒂》等剧到如今的《欲海狂潮》《榆树古宅》《安娣》,我国戏剧界对奥尼尔戏剧的搬演经历了从最初的谨慎摸索到全面开花,至20世纪90年代的滞缓与瓶颈期,再到21世纪的精彩改编、彻底中国化的起伏渐变过程。显然,奥尼尔戏剧已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戏剧文化中,无论其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还是其启蒙性、批判性的人文思想,都为我国的戏剧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乃至中西的文化碰撞、文化误读以及自作主张式的“纠偏”都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改编和接受的主体,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奥尼尔,修正奥尼尔,同时也被他所修正。也许,人们离那个真实的奥尼尔还有一段距离,也许真实的奥尼尔永难抵达,但正是这种距离感和难度才会让人们不断滋生出新的审美期待和创造冲动,进而将他的经典剧作不断搬上我国的戏剧舞台,一再借他人的故事叩问自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