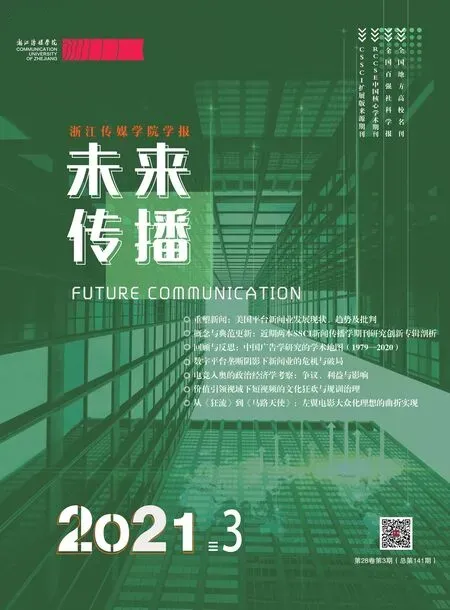浙商现象和影视浙军之间的双向互动
王 锋
(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影视浙军”这个提法始于2002年。2004年,《人民日报》发表《浙江制造叫好又叫座,影视浙军在壮大》的文章,从影视的机制、数量、基地、获奖、投资、效益等方面分析后认为:“浙江已经成为全国电视剧生产数量最大、投资最多、得奖较多的省份之一”[1]。事实上,浙军影视在每个阶段都有引领时代的影视作品。以电视剧为例,1980年代,既有《鲁迅》《济公》这样的地域文化特色浓郁的单篇短剧,也有《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大地震》等开时代风气的长篇佳作。1990年代,既有《九斤姑娘》《大义夫人》《梨花情》等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越剧电视剧,又有《中国神火》《中国商人》《中国空姐》等描绘时代潮流的影视系列;2000年以后,影视浙军齐头并进,一直走在攀登高峰的路上,如电影有《捉妖记》《大圣归来》,电视剧有《天下粮仓》《至高利益》《中国往事》《十万人家》等年度力作,尤其是2010年以后,就创作数量而言,浙江电视剧排全国第一、电影排全国第二;就质量而言,浙军影视于2020年度出品的《外交风云》《急诊科医生》《可爱的中国》《绝境铸剑》《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等5部电视剧获得当年飞天奖,在16部获奖电视剧中占比近三分之一;在海外,浙江出品的影视剧也受到了欢迎,如2014年出口电视剧175部7639集;2015年《虎妈猫爸》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播出,成为中国内地首部全球同播的华语电视剧;2016年,《传奇大亨》首次获得戛纳电视节官方展映资格,这是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最高级别。对于影视浙军现象,浙江大学范志忠教授做了概括:“就像浙江人生活的步伐一样,从这里‘走’出来的影视剧同样肯担当、有活力、识变通。通过几年来在创作生态、品牌培育等方面的‘深耕细作’,影视浙军,已经找对了路。”[2]
影视浙军的崛起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2016年,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寿剑刚精辟概括了浙江成为中国影视副中心的六个生态因素,即“开放的政策、灵活的体制、火热的土地、深厚的文化、充裕的民资和谦卑的政府。”其中之一的民营资本尤为活跃。据统计,“2019年,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省65.5%的生产总值、74.4%的税收、61.5%的投资、79.8%的外贸出口、87.4%的就业岗位。在2019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92个企业上榜,连续21年居全国第一。”[3]民营资本的迅速发展,从生产总值、税收投资、就业岗位,企业影响力等方面真正实现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的全球化覆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影视具有高投资、高风险的商业属性,恰好和浙商敢为天下先的内在精神相契合,再加上开放的政策和灵活的机制,民营经济参与见证了影视浙军从起步到崛起的发展历程,两者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
一、浙商现象与影视浙军的相互促进
浙江处于内陆和大海的汇合处,山多田少,资源贫乏,灾害频发,经常遭遇台风袭击、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在与自然的斗争实践中,人们开发工商业成为谋生的重要手段。经过世代传承与发展,在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浙江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温商为代表的“浙商”迅速崛起,形成了温州模式,随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建立商圈是浙商的显著特色,如由温商、甬商、台商、越商、婺商、杭商等名字就可见一斑,甚或“浙商”本身就是地域的缩写。而以地域为特色建构起各大商圈的主业,形成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精的产业分布格局,如温州皮鞋衬衫、宁波服装家电、台州精细化工、绍兴化纤、金华五金家电小商品、杭州丝绸等都是产业的龙头,创造了各个商业领域的“第一”,赢得了“无浙不成商”“天下第一商”等诸多美誉。
浙江作为首批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企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依据浙商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中得到了体现。改革初期,在电视剧刚刚兴起之际,浙江就拍摄了“改革三部曲”,其中《女记者的画外音》(1983)就是根据“双燕衬衫厂步鑫生”为企业家原型改编而成的。当时正处于公司改制的初期,步鑫生有一套“手段灵活,求真务实”的管理方式,“不请示、不规范,讲管理、看效益”,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扭亏为盈的成效,盘活了企业。经央视播出后,改革者的形象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明确了关注当下、关切现实的创作方向。此后,浙江活跃的民营资本赞助拍摄成为影视创作的常规模式,如《远洋船长和他的妻子》(1984),就是温州电视台和民间资本合作完成的。这部以温州船员的生活为内容,以温州为背景的电视剧,获得电视金鹰奖单本剧第一名,首开民营资本投资的先河。
进入1990年代,浙江的民间资本实力更加雄厚,为影视剧的繁荣奠定了经济基础。1994年的《喂,菲亚特》,就是由“浙江真空包装机械总厂和国有温州味精总厂分别投资10万元”[4]协助拍摄完成。当时的回报方式没有现金,只在每集的片尾出现“本剧演员皮鞋由‘浙江霸力皮鞋厂’提供,协拍单位:温州味精总厂、浙江真空包装机械总厂”等字样。但这种不求回报的协助拍摄的方式,为浙江赢得了声誉,“浙江好拉赞助”在影视圈广为流传。随后,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开始了联合创作,如华新影视公司创作的《绍兴师爷》(1999)等。
2005年8月8日,《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公布,为民间资本进入影视创作领域打开了通道。浙江的民间资本为影视剧的创作夯实了经济基础,影视剧的成功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两者结合,促进了影视浙军的繁荣。一方面,以浙江制造为主题的影视剧佳作频出,如《海之门》(2006)、《温州一家人》(2012)、《向东是大海》(2012)、《温州两家人》(2014)、《鸡毛飞上天》(2017)等都获得大奖;另一方面,电影《智取威虎山》(2014)、《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我和我的祖国》(2019)、《中国机长》(2019)等年度力作的背后,都有浙江企业作为出品方或者联合出品方,以广厦集团、横店集团、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民营公司对影视投资的深度介入和众多影视作品的集中获奖,标志着影视浙军的全面崛起。
二、剧里剧外自然统一的浙商形象
吴越之地,历史悠久,文化醇厚,自越王经历卧薪尝胆、五国争霸之后,吴越刚烈好斗、尚勇轻死之风盛行。《汉书·地理志》就说:“吴粤(越)之民皆尚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刘子》云:“楚越之风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5]既有卧薪尝胆的柔慧,也有剖腹自刭的刚烈。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吴越之地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一直沿袭至今。
(一)柔慧
浙江地处江南水乡,面朝大海、十里荷花、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旖旎风光,孕育了浙人柔慧的性格特质,“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6]。在封建社会,浙人通过灵活多变的“小本生意”,避开与政府利益的直接冲突,如在《向东是大海》中,恒通钱庄就有“十不准”店规,祖训的头条就是“不得与官府做”,其原因也借剧中人物之口阐释到位:“生意的对象是物,是指对物的态度,无非是人无我有、人次我好、人贵我廉,做到了自然就有信誉;交易的对象是人,是指对人的态度,无非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巴结有权势的人,然后用权来换钱,权贵是靠不住的,是断头生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浙商柔慧的性格得到全面的展现。如《喂,菲亚特》第一个跑出租的丁志方,《画外音》第一个鞋厂改革,《温州两家人》第一个聘请克林顿总统做代言广告,《鸡毛飞上天》的首建海外中转仓。这些众多第一背后是敏锐发现商机的智慧。正如费孝通曾对浙江温州经济所作的评论那样:“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的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7]经过世代的沿袭,柔慧已经内化为浙江商人的优良传统,一直沿袭到现在,如浙商总是在众多不起眼的小百货中发现独到的商机,成就义乌小商品市场。
浙商柔慧的性格还体现在对影视题材的处理和投资判断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就在当年,浙江制作完成了讲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商界风云的《喂,菲亚特》《中国商人》等电视剧。电影方面,有根据当年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改编的《湄公河行动》(2016),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改编的《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根据2018年四川航空真实事件改编的《中国机长》(2019)等。年度力作的背后,都有浙江企业作为出品方或者联合出品方的身影。
(二)刚烈
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资源贫瘠、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浙江与天争、与海斗的尚勇好斗之俗;再加越王勾践厉兵秣马、称霸天下的政治引导,夯实了尚勇轻死的刚烈之风。
性格刚烈体现在日常行为中,常见的就是一旦认定的事就会坚持到底,绝不回头。《温州一家人》中的周万顺为了开采石油,经历了住羊圈、吃剩饭、下跪磕头等各种苦难,甚至卖掉了祖屋和房产,导致众叛亲离、妻离子散依然初心不改;《十万人家》中的沈万家对彩丝项目的研究,经过长期的研发终于成功,虽被认定没有多大价值,依然持之以恒;《鸡毛飞上天》的主人公抵押所有财物开发海外中转仓。几乎所有浙江商人成功的背后,都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定决心。
在关键时刻,即使面对生死的威胁,浙人也不畏生死,勇往直前。《女儿红》中的周万泉,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坚决不当日本操纵下的商会会长,最终宁死不屈,以死明志。而《向东是大海》中周汉良的表现更加令人敬佩,拿着椅子坐在了法租界几十杆枪口的前面,在日本租界的门口公开叫卖中国水泥,在爆炸声中和日本大佬同归于尽,在每一次的斗争中,周汉良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是浙人刚烈性格的终极体现。
(三)刚柔相济
尽管影视剧中刻画的人物性格各有侧重,但整体而言,刚柔并济是浙江商人典型的精神内核,也是浙商影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质。《鸡毛飞上天》中的陈江河就是代表。陈江河和骆玉珠夫妇在最初的创业阶段,就是从鸡毛换糖的摆地摊开始,到做拖把、运猪料、卖袜子、贩五金等众多百货的小生意起步,逐渐壮大成为玉珠集团。在开拓海外仓时,遭遇了黑帮的绑架和对手的算计,玉珠集团也因此一夜破产。但陈江河并没有被击倒,而是隐居幕后,等到时隔多年以后,抓住儿子再次购买海外仓的时机,列举出当年的罪证,迫使当年的对手阮文雄辞职服输。这样的“灵活变通”,既符合生活实际,也是《喂,菲亚特》《温州一家人》《向东是大海》等主人公共同的性格特征。
浙江影视的每部作品都是刚柔相济的传神再现,并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十万人家》(2008)以盛产桑蚕丝绸的钱塘小镇为背景,通过沈氏企业从家族管理转向现代企业的历程,彰显了沈万家等杭州商人的 “灵活多变、求真务实”;《温州一家人》(2012)的周万顺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商人依靠个人努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创业历程,女儿周阿雨则代表了中国第二代商人在国外自由竞争中的跨国贸易,共同构成了改革大潮中商业发展和商人命运的发展史,彰显了周万顺等温州商人的敢为人先、永不放弃;《向东是大海》(2012),以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为背景,周汉良在和对手范小恩、董芝恒的竞争中,在和日本外敌的较量中,不断壮大钱庄生意,发展民族产业,彰显了周汉良等宁波商人的诚信经营、开拓进取、不畏牺牲。整体来看,浙商性格有着高度统一的精神内核,既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刚猛气质,也有灵活多变、勤俭持家的柔慧特质。
绝大多数浙商题材影视剧都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从内容来看,从商贩起步,再到家族集团,后转型互联网电商,再到“一带一路”跨国贸易,都在各个地区的商业题材影视剧中有所表现,合在一起,构成了浙江商业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剧中的人和事是“浙商”的艺术再现,而“刚柔相济”的性格特征则是“浙商现象”的动力核心,两者互为表里,相互印证。
三、浙商文化是影视题旨的源头活水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浙江商人一直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涌现出众多的传奇人物和鲜活故事,成为《温州一家人》《十万人家》《向东是大海》《女儿红》《鸡毛飞上天》等影视剧的人物原型。浙江商业影视剧在热播的同时,也传达了独具特色的浙江文化,“文明的积淀与文化的助推才是成就当代温州现象的最深刻根源;也只有在浙学传统的真谛中才能揭示浙商传统的本质精神。”[8]总体而言,浙江的商业文化,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时代发展的文化精髓,成为影视剧题旨要义的源头活水。
(一)义利并举、实事疾妄,发扬经世致用、立业报国的爱国精神
浙江历代先贤,如越国时期范蠡的“散财济民”,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钱王世家的“保境安民”,永嘉学派的“通商惠工”,永康学派的“义利并立”,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等经商实践和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浙东学派的“义利并立”的财富观,为浙江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石,历经世代相传,已经根植在浙江人的血脉基因之中。义利并举这一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有三个层面,即义在利先、利在惠民、义利并举,这也成为所有浙江商业影视剧的核心题旨。
首先是义行天下。白居易诗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观念,也是长期以来民众对商人的传统看法;但浙商将“义”字放到首位,无疑是对商人德行人品的看重。在《向东是大海》中,恒通钱庄的老板董如海在选择接班人时,放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董芝恒,选择上门女婿周汉良,其原因就在于看重女婿的品性德行。类似的诸如《十万人家》选择接班人沈万家、《女儿红》酒业大亨周万泉选择女婿孙南笙,其决定都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从剧情来看,老辈的选择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其次是利在惠民。惠民,从小处来看,就是回报于民,就是让在交易的过程中,如《鸡毛飞上天》中多次强调“四进六出”的经商理念,让双方都获利;《在远方》中,当姚远发迹之后,每年都回家发放红包,回报养育过他的父老乡亲;《十万人家》中,沈万家推行股份制让所有员工都享受到“红利”。这都是惠民的具体做法,就是经世致用的具体呈现。而从大处来说,就是立业报国,从范蠡开始,这种情怀胸襟和爱国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女儿红》中周万泉在开枪自杀之前说道:“我周万泉一生敬商圣范蠡智以保身,更敬其忠以报国,我今天可不能像范蠡那样在败鳞残甲的亡国之中含垢忍辱,以曲求全,但我周万泉可为了我族之尊严,不惧生死。老夫就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唤取同胞们的爱国热情,这样老夫就死而无憾了。”在现实中,类似的做法屡见不鲜。如据第一财经网报道,“万向集团公司捐出截至2018年度审计报告的资产,成立一个新的慈善信托——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以支持新技术研发和高端人才教育” ,“涉及市值超过145.54亿元”。[9]
最后是义利并举,《向东是大海》中周汉良捐出财物抗日,挂起了“恒通钱庄”的牌匾,《女儿红》中绍兴酒业和日军的抗争到底,都诠释了义利并举的题旨要义;相对来说,《十万人家》(2008)通过三兄弟的不同道路对义利并举的艺术演绎更具有代表性。沈氏集团以丝绸起家,当遇到贸易壁垒时,丝绸业面临产业转型的经营困难,导致分家。老大沈万忠“丢卒保车”,丢弃了十万蚕农的丝绸行业,转向了房地产,最后崩盘;老二沈万全“断尾求生”,为了来钱快做起了仿冒名牌生意被法院封停;老三沈万家革新缂丝技艺,接受下岗女工,不惜代价,研发彩丝技术,接盘三万蚕农,实行生死与共的股份制,终将丝绸产业发扬光大。老大背信弃义,老二重利轻义,老三重义轻利,三者不同的结局对比,揭示出商业文化的精髓,只有义利并举,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市委书记送给沈万家的对联:“义利兼顾,工商为本”,横批“饮水思源”,不仅是沈万家义利并举、工商为本的经商理念,也是经世致用、立业报国的传神写照。
(二)恪守诚信、知行合一,发扬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杭州著名的老店胡庆余堂有两句经典的店规:“真不二价,价二不真”和“虚和无人晓,诚信有天知”,形象地昭示了浙江商人恪守信义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以来,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浙商对诚信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历程。
《宋史·地理志》记载说两浙路人,“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10]这种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做法并不鲜见。1987年8月8日,5000多双“温州制造”的假冒伪劣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公开烧毁,这在《喂,菲亚特》《温州一家人》等剧中都略有提及,而在《鸡毛飞上天》中有更深刻的艺术表现。义乌陈家村以陈大光为首冒充港商贩卖伪劣皮鞋服装、五金电器等商品后,假冒伪劣之风盛行,从而导致消费者不敢买,售卖者收不到钱、厂商无法生产的恶性三角债,严重影响了义乌信誉和市场发展。邱英杰顶着各方压力,将没收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在义乌商城当众烧光。正如邱英杰谆谆告诫陈江河所说:“商人眼里不能只有钱,要有信用,心里永远要有杆秤,否则鸡毛永远别想飞上天。”
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武林广场的大火,开启了警醒浙江商人恪守诚信之路。时代在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这在众多的影视剧中都有表现,如《女儿红》中女儿陈、鉴湖情、绍兴春等酒业的质量更新,《十万人家》中的沈万家长期研发彩丝项目,《在远方》中私营快递和邮政之间服务质量的竞争等,全方位地说明了开拓创新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是《鸡毛飞上天》的剧情设计,将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也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轨迹进行了艺术呈现:在创业阶段,利用废弃的棉布头做拖把赚了钱;力排众议引进了日本的先进的提花机设备,救活了濒临倒闭的国有瓦厂;离开袜厂之际,就注册了“玉珠”百货的商标,为做大玉珠集团埋下了伏笔;为了占领欧洲市场,产品质量达到欧洲的高标准,主动和德国厂家做合资品牌,共创品牌。面对国际竞争的危机,陈江河打开欧洲市场,不惜变卖所有资产去做海外中转仓,终在电商崛起之后变成了现实。陈江河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拓创新的发展,代表了众多义乌商人,也是浙商,甚或中国商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轨迹,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三)求真务实、达观通变,弘扬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
“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的“四千”精神和“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是浙江商人求真务实、达观通变的传神写照。纵观《温州一家人》《向东是大海》《鸡毛飞上天》《在远方》等众多剧中主人公,在创业之初,都经历了捡垃圾,做纽扣、卖皮鞋等小本经营和夜餐露宿、跌宕起伏的摸打滚爬;而在发达之后,依然是节衣缩食、勤俭持家的常人本色。
《喂,菲亚特》剧中,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和人物,分别是以丁志方为首的私人出租车和以赵秉忠为代表的鞋厂改革。以丁志方为代表的个体户,看中了菲亚特的小巧灵活又便宜实惠,适合温州当时狭窄的街道,利于解决拥挤的交通,于是就做起了中国第一个私营出租车司机,从第一辆车牌号00518开始,发展到遍布温州大街小巷的4000辆,当时,全国只有6000辆,这成为温州一道亮丽的黄色风景和一代人的生活烙印。以赵秉忠为代表的国有厂厂长,面临效益低下、工资发不出的困局,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施“独立自主”的管理权,“自由调动”的人事权,“按劳分配”的财权,重视科研人员,启用皮鞋新款式的研发,扭亏为盈,开创了国有厂市场化改革的先河。该剧通过一公一私的双线叙事,艺术地呈现了温州率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
加入WTO后,面临全球化的竞争,国内外的贸易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温州两家人》的剧情就是复杂环境背景下展开的。以侯三寿和黄瑞诚为代表的温州商人做出了一系列敢为人先的首创,如邀请克林顿当形象代言人来树立企业的高端品牌形象,在南非投资两千万美元建太阳能厂,季诚集团和MGX公司长达6年的反倾销案官司最终胜诉等经营案例,都展现出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和竞争格局。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了《喂,菲亚特》中的鞋厂改革,第一个私人出租车的“温州模式”;在WTO的接轨中,《十万人家》面临家族企业向股份制企业的转型升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鸡毛飞上天》搭上了“一带一路”出口贸易的国际班列;在电商崛起之后,《在远方》展示了现代物流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科技角逐。显然,影视剧中的浙江商人在每个阶段每个领域的开拓创新,就是浙江商业的变迁史。从吴越时期的商圣范蠡开始,到清末民初《向东是大海》中的周汉良、《女儿红》中的赵一荻,再到新中国《十万人家》中的沈万家,《在远方》中的姚远,勾勒出了浙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践行义利并举、立业报国的浙江商业的文化史。
四、影视浙军繁荣之下的反思
浙商带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影视浙军的繁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体向好的局面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资本活跃,投资风险巨大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浙江经济得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民营经济发达,为影视的发展夯实了经济基础。资本充足,使得影视投资活跃,这主要表现在影视制作单位的数量上。1998年,华新影视,也就是今天的华策影视成为浙江省第一家民营公司,到了2004年,全省影视制作机构有186家,2020年,制作机构的数量则达到了3000多家,仅次于北京,平均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在增加。浙江经济基础雄厚,投资踊跃,但也埋下了众多影视公司面临倒闭的残酷现实。以2015年影视作品总量的数据为例,电视剧66部2906集,影片57部,动画片55部,平均8家公司制作1部作品。 在世界范围内,从影视比较成熟的德法英美等国来看,他们影视公司的数量都比较少,如美国的八大电影公司,韩国的四大电影公司。公司少,行业比较集中,规模大,产量高,抗风险能力强,生产10部电影只要2部盈利就能维持生存。与之相比,小公司平均产量小、抗风险能力低、专业化程度弱。可以预见的是,浙江这种小作坊式的影视创作现状将会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发展而逐渐集中,而过程会以多数倒闭、少数兼并、个别壮大等方式实现规模化运作。
(二)资本逐利,影视质量堪忧
活跃的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从客观上支持和促进了影视的创作与发展,如《潜伏》《黎明之前》《美人鱼》《捉妖记》等影视剧都有影视浙军的身影;而影视精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如《阿凡达》《泰坦尼克号》《捉妖记》等都是十年磨一剑,这也是艺术创作的固有属性,《红楼梦》就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资本逐利的特性也使影视艺术创作的质量令人堪忧。刘勰曾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但现在很多公司是“为利造文”。其中,最有警示意义的就是煤老板陈卫民。2011年和2012年,他先后分别投资千万元以上拍摄《乱世情缘》《没有承诺的爱》,但都没有和观众见面,导致了自杀的悲剧。“陈总对影视拍摄流程、电视剧发行周期、宣传策略的不了解,导致了投资的失败。很多浙江以前做实业的老板选择投资影视剧,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老板或是被圈内人骗,或是做出的东西不专业,反正盲目投资的,我没见过一个赚钱的。”[11]从2009年至今,浙江每年新增100多家影视公司,在资本涌入影视的大潮中,众多影视作品难以保证艺术质量。
(三)制作粗糙,缺少工匠精神
影视的制作粗糙,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作机制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影视创作普遍采用的是独立作者制,即编导演等主创人员由一个人来主要负责;如华策公司就和刘恒、麦家等编剧签约,这也是影视业界流行的做法,但这种创作体制也有弊端,容易固定,难以全面,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相比,美国、韩国等都已经采用非常精细的职业化分工,即对剧本创意、框架结构、人物设置、对白、桥段、噱头等各个细节,都采用专门团队来负责。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是保证影视质量的前提。采用精细的职业化分工,革新影视创作机制,是浙江影视持续做大做强的未来之路。
五、结 语
影视作为当代文化的显学,在改革前沿的浙江得到了孕育和发展。影视浙军的发展一直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浙军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影视浙军从最深和最广阔的层面契合了观众的审美诉求,引领了影视艺术创作的时代潮流,意味着浙商现象和影视浙军之间达成了同向共进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