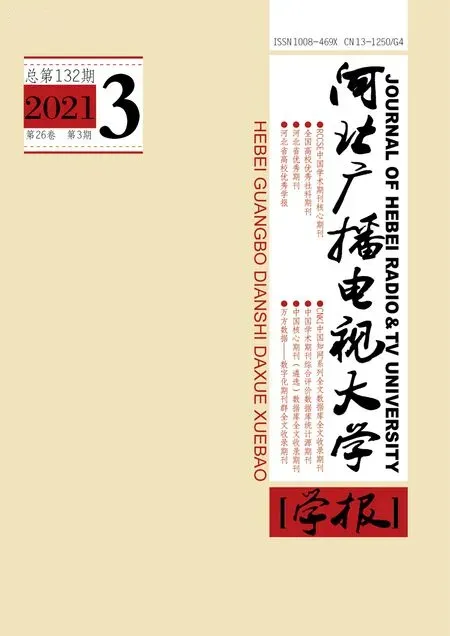庚子事变中基层官员的艰难应对
——以定兴知县罗正钧为中心
梁 娴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罗正钧(1855—1919),字顺循,号劬庵,湖南湘潭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任职于陈宝箴幕府,后在其举荐下赴直隶任官,历任抚宁、定兴、清苑知县,天津知府及山东提学使等职。辛亥鼎革后,不应袁政府出仕邀请,闭门著书。著有《船山师友录》《左文襄公年谱》《劬庵官书拾存》《劬庵文稿》等图书传世。罗正钧于庚子年初到任直隶定兴县知县,京师陷落前数日被解职。他关于义和团的记录大部分集中在庚子年阴历三月至五月间(1)下文若无特别说明皆使用阴历纪年。(1900年4月至6月),收录于《劬庵官书拾存》中,反映了义和团在直隶快速壮大到清廷对外宣战的大致情形。彼时的直隶基层官员作为连接统治者与人民的纽带,既要承受政府高层决策游移的伤害,又须应对团民的威逼,其经历展现了清末乱局中基层治理的复杂面相。迄今学界对罗正钧在庚子事变中的表现研究较少,笔者认为以罗正钧的经历为视角观察庚子事变中的国家与人民,以及理解一批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在清末的政治表现有着积极意义。
一、纷扰与焦虑
庚子年三月到五月中旬,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快速发展壮大,并蔓延到京师。慈禧太后此时对于义和团是剿是抚尚无定见,但因为戊戌政变、己亥建储等一系列事件对列强已怀仇恨态度,所以对义和团只采取了有限的“严拿首要,解散胁从”(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页。的做法,实质上纵容了义和团的扩张。因此这两月间军民冲突不断,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四月,定兴毗邻的涞水县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涞水教案”。教案起于高洛村的民教积怨,在团民攻打教堂后引来官军镇压。清军将领杨福同在涞水石亭镇被团民所杀,团民随后向北转移占领顺天府的涿州城,并毁坏了涿州附近的铁道、电线。清廷闻讯后命聂士成麾下杨慕时、邢长春等将领保护铁路,随后派赵舒翘、刚毅等前往涿州视察。这是官方对义和团公开招抚、利用其对抗列强的前奏。定兴所处的位置四通八达,在义和团声势愈加壮大之时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首先是高洛村团民转至定兴境内烧毁仓巨村教民的房屋,教民被迫转移。然后是境内大沟村团民与新城县团民联合烧毁北河铁路大桥,以图切断在高碑店与团民开仗的杨慕时部与援军的联系,此举招致邢长春部队围剿大沟三村以捉拿团首,并由罗正钧将团首田和顺擒拿并枭首示众。他苦涩地形容自己这两个月来“无日不办理拳案”,是在“舌焦笔秃,如防欲溃之堤,日夜惴惴”(1)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的压力与疲累中度过的。
罗正钧的身心俱疲与朝廷剿抚不定、表里不一的政策有着莫大的关联。朝廷给直隶地方官下达的命令是要对义和团尽量劝谕解散,而不是严厉镇压,这种口头上的劝导和训诫实际上很难起到实效。罗正钧从就任起,就多次尝试过对团民进行劝导,但收效甚微。如正月二十二日,“官绅同赴书院,见牛家庄、老李村各会首,劝谕勿学拳,不听”(2)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3页。,四月二十一日,“王副戎与县公同邀议仓巨拳民事,令解散不允”(3)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1页。。即使团民暂时性的散去,也会很快再次聚集起来。罗正钧尝试过深入团民云集的村庄,与当地士绅一起竭力劝谕解散,“各村董来署禀称,各股业经走开,必可无虞”,甚至“卑职登车时,村民拳众跪送者且数百人”(4)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看似取得了不错效果,但之后不久团民又蠢蠢欲动。这样温和的政策不仅没能使团民放弃练拳,反而让他们感受到朝廷政策的偏向,愈加无所顾忌。在与团民的密切接触中,罗正钧对于义和团的看法也急转直下。在三月间,直隶境内拳会已不少,但大规模的暴力抗官事件并不多,因此彼时罗正钧虽认定义和团属邪教无疑,但毕竟事出有因,“惟其以仇教为名,愚民积受欺侮”(5)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才导致义和团发展壮大起来,民教相仇才导致恶化的局势,不难看出此时的他对义和团是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的。但当石亭戕官、涿州被占、铁道被焚等一系列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后,罗正钧的认识便发生了变化,他对于义和团的评价急转直下,并请求上司乘其尚未坐大,赶紧派兵将其剿灭。罗正钧并非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剿,而是在目睹了义和团的暴力行为升级后方转变了其应对态度。
此时作为直隶地区的中层官员,罗正钧上司的反应也耐人寻味。直隶按察使廷雍在涿州事发后令罗正钧“会同营汛防军严加防范,外匪阑入,即行捕拿”(6)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语气相当严厉。保定府知府沈家本在仓巨村被焚后多次询问仓巨村拳民的后续情形,令罗正钧严防情势反复,可见其对镇压义和团的重视。表面看来,直隶地区高层对于义和团的发展相当关注,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他们执行的仍是朝廷“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谕令,实际上对于义和团的弹压措施是“审慎而有限”(7)黎仁凯、边翠丽:《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的,总的来说并没有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相比于罗正钧等基层官员,中层官员与朝廷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于朝廷风向的把握更为准确,直隶中层官僚彼时的注意力放在了揣摩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态度,甚至有些官员希望借此获得端王等新贵的赏识,因此一方面要求下属对义和团实力剿办,另一方面又不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上司的做法让罗正钧颇为不满,面对上司的问责,他不无负气地回禀道,没有军队的支持,自己的工作始终是徒劳的,“惟大兵压境,决于一发;官吏空文,实难以有效”。望眼欲穿等来军队的支援,结果却奉命只保护铁路,他也会忍不住对上司直言“匪既注意毁道,则保道应先剿匪。宪台自有主持,无俟卑职之渎陈也”(8)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但人微言轻,他的抗议并不能扭转高层的决策。
对于如何解决义和团的问题,连罗正钧的下属艾声都明白用武力解决并非不可能,“中国兵力虽弱,然灭此拳民如摧枯拉朽”(1)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页。。可以想见,若采取得力的军事措施,直隶境内义和团不难荡平。吊诡的是,直隶境内并不缺少可以用来弹压义和团的军队。罗正钧上任以来就有多支队伍奉命来定,如四月十七日,“亲军马队营官副将王公占魁,带马队八十名到县”(2)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9页。等等,兵力上并非十分缺乏。然而军队的行动却受到了极大限制,他们奉朝廷“迅往弹压,妥为解散”(3)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页。之命而来,往往只能在暴乱已发生之后才能捉拿团首,没有被赋予提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权力。更有甚者,朝廷派来保护铁路的部队甚至只专职保路,并不以剿团为目的。多重束缚之下,军队的行动效果在直隶便大打折扣了。
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在庚子之乱中不仅起到的正面作用有限,还会因为军纪不严滋扰地方、激起民愤,这一问题在定兴显得尤为突出。被派来保护铁路的邢长春部队便与罗正钧发生过多次冲突。最初起因是邢部入城“强易市物、擅入民宅”,有一名营勇甚至“强奸民妇”(4)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页。,被团民捆送县衙,但邢军拒绝接受罗正钧的处罚。随后又“兵至大沟、两合庄等村,先问财主,继索食物,该村团民诣县署请撤兵,否则开仗”(5)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3页。。罗正钧虽然需要军事支持,但邢部若继续留在定兴只会使局势愈加复杂。他只能禀明上司廷杰,请求将邢部撤回高碑店,定兴则自行保护铁路。为此他得罪了邢长春,还受到了廷杰的斥责,甚至差点丢了官职,“奉藩宪严电申斥不应请撤兵……县公赴省请交卸”(6)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4页。。
调离邢部的请求未被批准,邢长春与罗正钧之间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冲突。邢军为捉拿大沟村团首田和顺,并未告知罗正钧就前往大沟村围剿,波及周围三个无辜的村庄。罗正钧赶到后与邢长春争执,“三村断不可令无辜被剿,某系地方官,请予限三日责某交田和顺,如逾限无人,参革刀锯,壹唯公命”(7)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虽不排除罗正钧美化自己形象的可能,二人之间交锋的激烈亦可以想见。罗正钧是在努力维持义和团与官方力量脆弱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一旦被军队打破,定兴必将陷入暴力与混乱之中。
在义和团快速壮大的阶段,直隶地方官员大多要面对“上游之牵掣,匪徒之阑入,客兵之骄横”(8)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齐齐压来的局面,其艰难烦扰可以想见。而作为主剿派,罗正钧等人需要承受更多心理的焦虑,他们眼见朝廷决策表里不一、上司领导无所作为却无能为力,只能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尽量维持地方的稳定,拖延陷入乱局的时间。
二、无助与悲愤
到了五月中旬,朝廷的决策在联军进逼的压力下走向明朗化。十四日,英国军官西摩尔率联军两千人分批自天津赴京师护卫使馆,此举并未事先取得清廷的同意。慈禧太后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预备开战的措施,载漪、启秀等顽固派接掌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董福祥此前已率领甘军进驻京城。揣摩到朝廷的意图,直隶总督裕禄的态度也在五月中旬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十六日开始,他便拒绝出兵剿灭义和团(9)阮国桢:《津乱实纪》,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页。,随后还派兵保护天津城内三义庙的拳坛。战衅已开,正式宣战只是时间问题,对于义和团的公开承认也呼之欲出。十八日,刚毅视察涿州完毕回到京师,刚毅在涿州的见闻促使慈禧相信团民可作为对抗列强的力量,也成为清廷走向宣战的重要推手。
然而直到此时,清廷对地方官员仍没有承认其抚团的决定。刚毅等宣称到涿州是为安抚义和团而来,谕令团民“妥为解散,各安生业”(1)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5页。,若各村首事能解散团民,朝廷还会给予奖励。甚至到了二十一日,朝廷“虽有谕旨,仍责成地面拿首要,解胁从,无‘剿捕’字样”(2)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7页。。因此军队与团民依然有暴力冲突,而罗正钧还在积极地组织县城绅民防御义和团的进攻。虽然基层官员未必对朝廷的态度没有感知,但毕竟因为信息获取的滞后被抛在了极其被动的地位。如刚毅回京时调走了此前奉命保路的杨、邢等部队,定兴一下失去了可依靠的军事屏障。罗正钧此时还不清楚朝廷的态度已发生了极大变化,因而向上司表达了自己的不理解,“连日正奉各军实力剿办之谕,不知何以忽撤各军”(3)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页。?清军撤走后,涿州的团众立即四下行动,首先沿途烧毁铁道,直到定兴边境。随后入境拆毁了定兴火车站,还扬言进攻县城。城中守备空虚,老百姓人心惶惶。罗正钧多次请求上司派军队来护卫县城,而此时的省城保定已是“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5年版,第304页。的混乱局面,没有人敢于在风口浪尖上再言剿团,自然不会有援军到达。见多次请兵不至,罗正钧只能自行募勇守城。因为铁路被毁,交通与通讯皆中断,来自朝廷的讯息也断绝了。一面是义和团来势汹汹,一面是守备空虚的孤城,既无援军也无消息,这便是处于朝廷决策转变关键期的直隶地方官的真实处境,其中的焦虑、无助可以想见。
五月二十一日,联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台。二十三日,朝廷下令裕禄召集“义勇”,将其“编成队伍,以资捍卫”(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八国联军侵华卷》(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公开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二十五日,发出“宣战诏书”,决心“大张挞伐,一决雌雄”(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八国联军侵华卷》(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并专谕嘉奖团民为“义民”,号召各方督抚效仿裕禄在天津办法将拳民组织起来御敌。直到三十日,定兴官民才收到二十五日的上谕,它将直隶基层官员抛在了更为尴尬、危险的位置,尤其是罗正钧等主剿派。得到朝廷公然的认可后,六月初开始,团民行动更为激烈,甚至公然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此时天津地区的团民不仅与总督裕禄分庭抗礼,还“在街前行走时,若遇官弁坐轿者必喝令下轿,骑马者必喝令下马,且必脱帽旁立,不从者,则挥刀恐吓,怒目相加”(7)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官威扫地无余。乘此大势,多股团民涌到定兴衙署来找罗正钧“秋后算账”。艾声《拳匪纪略》记载道,“六月二日,大沟拳民王洛要即王老耀,因县公诱获田洛养(田和顺),挟仇报怨。本日率拳入城,勒罚县公白米二百石”(8)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9-460页。,此前被邢长春部围剿并捉得团首的大沟团民来向罗正钧寻仇,他们先向过境的顺天府尹王培佑状告罗正钧滥杀平民,随后还持械涌至衙署,“该村众贪索不已,恫喝万状,并称卑职所出示谕,不应称拳为匪。其意直欲寻仇,与卑职为难”(9)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罗正钧因为此前将团首田和顺枭首,此时便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第二日,“牛家庄拳民,因正月间查禁时,县公拘一人,给黑狗肉面一碗食之,遂破其法。今来城内寻县公复仇,纠周各庄老李村聚众百余,持械并舁鸟机炮两尊,来杀县官,势极其凶悍”(10)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其寻仇理由如此荒谬,但直到罗正钧交上罚金,并率“官绅齐赴东林寺叩头,拜坛谢罪”(11)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才得以暂时平息。罗正钧自认为在处理拳案时他做到了公平,“民习拳以仇教,因以仇官。予自问未尝袒教,于民无怨,故无所惧也”(1)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因此他倔强地坚持自己对团首的处置没有过错,即便这样,他依然要承受团民的打击报复,成为朝廷政策失当的替罪羊。
更为尴尬的是,朝廷此时要求地方官联络各团,将团民组织起来抗击联军入侵,罗正钧也只能遵从,初十日,“城内官绅公请四乡各团齐集书院,好言相慰,藉免侵凌”(2)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0页。,同时还派遣下属至各村访问义和团,查其实效。但以罗正钧过去与团民的仇怨势必不能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上有朝廷的重重压力,下有团民来势汹汹,其艰难烦扰可见一斑。罗正钧在六月初向上司递上辞呈,刚由按察使升为布政使的廷雍,为了表明自己支持义和团的媚上态度,请求撤换了坚决主剿的一批官吏,如安平知县何子宽、饶阳知县汪宝树、涞水知县祝芾等,罗正钧也位列其中。七月初十,罗正钧去职,凄然离境。艾声记录下了罗正钧离开时的情景,“公饯旧官罗公于南关外,惨然而别,练勇及各村团民送者千余人,刀枪林立,数百年未见有此气象。然乱象也,有心人隐痛之”(3)艾声:《拳匪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3页。。罗正钧等主剿派官员被要求去职既是个人选择,也是朝廷坚决开战、撤换主剿官吏的结果。上至总督,下至县令,主剿派或被去职,或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抚团开战,局势逐渐不可控制。罗正钧离境后不久,京师陷落。
罗正钧等地方基层官员中的主剿派,因为对义和团的态度使高层不喜,势必难以及时把握高层决策的变动,便处在了极其被动的地位。在朝廷转而招抚义和团后,又成为团民宣泄怒气的对象,实际上是代替朝廷承受了政策游移的恶果。随着庚子事变的平息,这些在夹缝中得以艰难生存下来的亲历者开始了积极的反思。
三、审视与忠诚
庚子之乱平息时罗正钧已为一介布衣,他这样记下自己的感受,“通国之辱,盈庭之耻,回首凄然,肝肠欲裂”(4)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这种强烈的耻辱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共同感受。时过境迁后,罗正钧等有识之士对这场大难进行了反思,他们站在更高的高度审视乱局之中的国家与自身,而这种思考也必然影响着他们后续的人生轨迹。
朝廷对祸乱的招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尘埃落定后难逃历史的审判。罗正钧也看清了朝廷对义和团表里不一的真面目,“虽示禁之檄屡下,而意存护惜,唯以解散为辞”(5)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让事态发展一发不可收拾。他分析朝廷之所以不大力剿办义和团,原因之一在于被表面现象蒙蔽,混淆了民、匪之间的区别,“当事犹窃窃议之,盖始终误于认匪为民也。其时匪实畏兵,故倡为激变之说,期去兵以肆其所为。朝野惛然,竟莫能辨”(6)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他认为政府高层身在庙堂,无法了解义和团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无法认识到其复杂性,而与团民大量接触的地方官对于他们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是人微言轻,无法左右大局。事后他也了解到朝廷纵容义和团的深层意图,即端王等顽固派欲借义和团之力行废立阴谋,“盖是役端邸欲借以遂苗刘之谋,十八日刚相归而决议,而荣相依违其间以成之,遂以贻中国复亡之惨祸”(7)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页。。政治阴谋才是义和团酿成大乱的根本原因,他在了解到这一层真相之后咬牙切齿地骂道,“参之肉真不足食也!”(8)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除了对高层决策者的批判,他对于上司的懦弱和骑墙态度也大力抨击,“当事者视京津不加严禁,不复敢言用兵,惟日责地方官解散,希冀无事,以为敷衍之计”(1)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他指出了专制政体的一大害处,即官员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百姓负责,他们也是庚子之乱的帮凶。罗正钧借此机会宣泄着自己数月以来的屈抑与痛苦,批判着上至庙堂下到地方的当政者,但对于仍掌大权的慈禧太后颇有顾忌。他只能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君子如怒,乱庶遄已”,又“君子信盗,乱用是暴”(2)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页。,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相比于对朝廷的失望,罗正钧对自己在庚子之乱中的表现却是比较满意与骄傲的。直隶不乏义和团戕官辱官的现象,而他认为自己即使面对凶恶的团民也是极有威信的,他回忆了几个团民对其礼敬有加的场面,如“新城沈各、白沟各处拳匪至北河者殆将千人,红巾黄带弥满村市。予凌晨乘专车至北河,竭诚开谕,已允散归。临行拳众罗列跪送,欢呼好官。前烧涿良铁道,至高碑店定境,亦呼定兴好官,相戒勿烧。盖尚以仓巨一案未尝袒护教民也。回署鹿杏侪学尊迎谓曰:今日真可谓黄巾罗拜郑康成矣”。(3)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他自己分析拳匪尊敬他的原因就在于他处事公平,未曾袒护教民,因而得民心。不仅拳民对他尊敬,治下的老百姓更是对其十分爱戴,如“城中居民恐予有失,竟日万众乘城探望。薄暮予归,环集慰问”(4)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等官民祥和的场面屡屡出现。虽不能考证以上情形属实还是罗正钧的自我美化,但作为坚决的主剿派,他能相对公正地处理拳教冲突,一定程度上平息人民的愤怒,治下没有发生严重的暴乱,值得收获百姓与历史的肯定。
然而仅停留在反思层面是不够的,彼时的中国已是千疮百孔,罗正钧等思想较为趋新的士大夫在庚子事变后也积极寻求振兴国家、洗刷耻辱的良方,他在庚子年后的表现也成为清廷革新自救的缩影。他本身是学者型官僚,弱冠时就以文才闻名湖湘,曾为醴陵渌口书院山长,为官后常购置图书、建造书院,大力劝学。有感于拳民“惟其愚实由上之无教”(5)罗正钧:《劬庵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坚定了他大力发展教育的决心,因此后半生乘清廷推行新政的大势,投身于新式教育事业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赋闲在家的他受湖南巡抚俞廉三之命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请派学生赴日本习专科之学,湖南之选派留学生自此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立学校司,电调罗正钧往直办学,他向袁世凯建议“教育贵普及,而以中小学堂为本,然必先造就师资,而后中小学能刻期举办”(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7页。,于是被任命为师范学堂总办,是为直隶创设师范学堂之始,四年后中小学堂渐次林立,引得山东、河南等省选派人员来观摩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保定府知府,次年任山东提学使。他在山东除整饬师范学堂,设立中小学堂外,还广购图书,创办山东图书馆。著名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评价他道“君子因机立教,予将以斯道觉民也,泽之所及者广矣,何必以私与里子弟哉!”(7)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8页。,一语道破了他欲借兴办教育启发民智的理想。
然而历史的效果往往不以人的动机为转移。文化上的大力西化消解着儒家传统的影响力,人心日益浮动,成为促使清朝走向灭亡的思想基础。罗正钧在清朝覆灭后分析了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戊戌、庚子内衅迭生,法度益以堕坏,于是游学小生猎取肤末,奋臂倡言,遂乃土苴六经,排斥礼教,凡非功利之说率目为空文无用。其说又一切讬之外人条教名词,举仿效之,习非成是。上下相奖,诬浅学之。夫先无以自立,蔽于所闻,而狂迷失守,遂若中国之书可以尽废,其害中于人心视焚坑之烈殆尤过之。昏怓叫嚣,国以随覆,而大乱相寻莫知所届”(1)罗正钧:《辛亥殉节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页。,庚子之乱后他对国家仍抱希望,然而文化道统的废弛却让他无法不悲观了。罗正钧等开明士大夫本身是大力倡导近代化教育的旗手,然而传统文化迅速失势的残酷现实却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结果,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现代化语境之中,“传统”往往带有鲜明的贬义,然而现代化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传统即陈旧,现代即正义。对传统进行单一化的贬斥,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罗正钧在辛亥鼎革后回到湘潭老家闭门著书,拒绝袁世凯政府的出仕邀请,成为众多逊清遗老中的一员。无独有偶,直隶地方官中比他更为知名的吴桥县令劳乃宣同样选择了归隐山林。作为庚子事变中坚决的主剿派,他们所受的屈抑比他人更多,然而他们却选择了对清廷恪守忠诚。除了对自己长期生活的王朝怀有留恋,他们更想坚守的应该是作为人生信条的儒家道统,以及作为文化道统传承者的那份自我价值。面对庚子事变后“由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在震荡中的解体”(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这一残酷的现实,罗正钧等逊清遗老们致力于史学、刻书藏书等文化事业,以一己之力希图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对抗历史的大潮。如何评价这种悲壮的坚守?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回答。
四、余论
罗正钧在庚子年间的经历是一批基层主剿官员的缩影,他们上不能左右时局,下不能保境安民,时时刻刻承受着中央政策游移带来的痛苦,而士大夫匡扶社稷的社会责任感更是让他们在目睹乱局之时饱受心理的煎熬,这不能说不是人生的一种悲哀。但福祸相依,离开政治舞台的他们反而在文化与思想领域长袖善舞,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更有价值的财富,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庚子之变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大到国家和朝廷,小到基层官员甚至是平民百姓,无不受其影响,故而从中择取相应的角度予以深刻的剖析,便显得不可或缺。本文只是初步尝试,未来的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