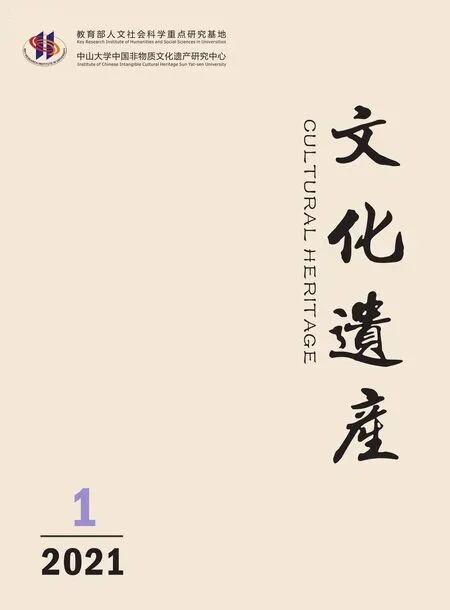论元杂剧中“开”与“开呵”之区别
李 妍
元杂剧文本中,“开”作为宾白提示语之一,多被认为是宋金以来伎艺演出中“开呵”的省文。如孙楷第先生道:“宋元以来伎艺人上场表白语谓之‘开呵’……省其文则曰‘开’,如元刊本杂剧凡上场白皆标‘开’字是。”(1)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28页。黄天骥先生亦说:“考诸宋金杂剧,演员上场时,往往是有‘上开’的提示的。这‘开’,就是‘开呵’,或写作‘开和’‘开喝’。”(2)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另外,在《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元曲释词》等工具书中,“开”的条目下也都有“开呵”后省略为“开”的记载,等等。但将文本中“开”的用法与“开呵”的形态、功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事实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元杂剧选本中,“开”有着自身的发展体系,元明版本对“开”的用法并不相同,甚至到万历年间,《元曲选》中已经不再出现“开”的身影,其用法与选本编者的编选原则关系密切。而“开呵”作为伎艺表演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出现则是演出艺术发展的结果,“开”与“开呵”之间并不存在文本对演出艺术的呈现关系。因此,本文将分别对“开”与“开呵”进行探讨,从形态、来源、实施者等方面入手,区分二者的差异。
一、“开”的形态与用法
“开”作为宾白提示语之一,在《元刊杂剧三十种》《改定元贤传奇》《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阳春奏》及《杂剧选》等元杂剧选本中多次出现。但在用法上,元、明选本之间却存在差异,且到明万历年间臧懋循编刻《元曲选》时,已经不再将“开”作为人物上场的提示语了。因此,对元、明选本中“开”的形态进行分开讨论,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其用法上的变化。
(一)元刊本中“开”的形态
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出现“开”的剧本有十九种,是现存元杂剧选本使用“开”最早且频率最高的版本,通过对其研究,可以看出“开”在元杂剧文本化过程中的早期特征。
首先,“开”的实施主体皆为剧中角色,但呈现出的用法却不完全相同。其中,正色“开”37次,净、外、驾、杂等外脚“开”31次。当实施者为正色时,“开”通常出现在一折开头正色首次登场处,提示形式包括三种:a、“正末(旦)……上,开”,如“末抱监背剑冒雪上,开”(3)《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页。;b、“正末扮……上,开”,如“正末扮杜如晦上,开”(4)《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67页。;c、“正末引(同)……上,开”,如“正末引卜儿上,开”(5)《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94页。,“正末同老旦上,开”(6)《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67页。等。这些提示语代表正末开场的同时,也简介了脚色上场时的人物及环境状态,提示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转换,并引出其他脚色上场。而与正色不同,外脚“开”的位置并不只限于在每折的开头,曲子之间也可以“开”,提示形式亦与正色存在差异,如剧中常用“……上,开了”“……开,一折”“……上,开住”等,做为外脚“开”的提示语。虽然外脚所“开”内容大部分省略不提,提示语也较为简单,但结合文本可以看出,无论实施主体是正色还是外脚,他们都属于杂剧剧情冲突中的一员,“开”的内容自然也是构成故事剧情的一部分。
其次,“开”的内容通常包括三种形式。最为常见的是自报家门,并介绍故事背景及相关人物,如《新刊关目诸葛亮博望烧屯》第一折:
(末扮诸葛上,开)贫道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于南阳邓县,在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有一冈名曰卧龙冈,好耕锄陇亩。近有新野太守刘备,来谒两次,于事不曾放参。盖为世事乱,龙虎交杂不定。正每日向茅庐中松窗下,卧看兵书。哎,诸葛,几时是出世处呵!(7)《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80页。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剧的主要人物及相关背景,为之后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议论天下形势,并请诸葛亮出山的剧情发展作出铺垫。
二是梳理故事剧情的发展,如《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第二折:
(正末骑竹马上,开)奉官里圣旨,差老夫五南采访,巡行一遭,又早是半年光景,今日到家,多大来喜悦。(8)《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45页。
此时,“开”大多出现在套曲与套曲之间,而非正色首次登场之时,其内容对后续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解说作用。
另外,“开”的内容还包括唱念韵文,如《新刊关目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第三折:
(正末扮渔夫上披着蓑衣摇船上,开:)月下撑开一叶舟,风前收起钓鱼钩。箬笠遮头捱日月,蓑衣披体度春秋。俺这打渔人好是快活!(9)《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77页。
这种形式类似于人物的上场诗,用以说明人物的身份、心情或描绘当时的情景。与上述两种内容相同,它们都是剧中人物用以介绍或推动故事发展的方式之一,并非独立于剧情之外。
以上可以看出,元刊本中对“开”的使用并没有太多的规范。不同的脚色在剧首或剧中都可以用“开”来提示人物的登台念白,其内容没有固定格式,皆是剧情的一部分。“开”的用法与戏曲文本中另一常见的宾白提示语“云”十分相似,不仅自报家门、梳理剧情、唱念韵文等“开”的内容常出现在“云”的提示之中,且“云”也可以同“开”一样,用在一折的开头代表开场,如《新刊关目张鼎智勘磨合罗》(正末同旦上,云):“自家李德昌便是。妻刘氏,有个小孩儿,嫡亲三口儿,在这河南府居住,开这个绒线铺……”(10)《古今杂剧三十种》,《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47页。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二者都无甚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云”的使用范围显然比“开”更为广泛,这也成为在明代元杂剧文本化过程中,“开”逐渐被“云”所取代的主要原因。
(二)明选本中“开”的形态
明代中后期,元杂剧的演出逐渐衰落,但随着文人的关注,使得刊刻元杂剧文本的行为日益流行,于是,大量元杂剧选本在此时出现,编选者们对元杂剧文本进行了改订与整理,同样,对“开”的用法也会作出规范,使其呈现出与元刊本不尽相同的形态。
首先,与元刊本相比,明选本使用“开”的频率有所下降。与《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出现“开”的剧目多达三分之二不同,明选本更多是用“云”作为人物开口念白的提示语,甚至在出现“开”的同时,也会用“云”与其叠加,以“开云”的形式提示之,如脉望馆本《关云长千里独行》第一折首:“冲末曹操同张文远上,开云”(11)《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二十七),《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与元刊本一样,在提示人物开场时,明选本中“开”和“云”的用法并无差别,于是,随着元杂剧在明代的不断文本化、规范化,“开”便逐渐被“云”所替代,直至臧懋循编《元曲选》时,对各种本子进行“参伍校订”,统一采用“某某云”的形式作为宾白的提示语,“开”则彻底从元杂剧文本中消失了。
其次,明代选本中新增“冲末”担任“开”的实施者。“冲末”不见于元本,目前最早出现于《改定元贤传奇》剧首或某折的折首,在明传奇中,“冲”有冲场的含义,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记:“冲场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12)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页。这与明代元杂剧选本中“冲末”往往首先登台开场的行为保持一致。关于“冲末”是否为脚色,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从文本中看,“冲末”所扮演的皆是剧中人物,如“冲末扮裴尚书引夫人上”(13)《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十),《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冲末扮赵大舍引郑恩上,开”(14)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125页。、“冲末袁绍领卒子上,云”(15)《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十四),《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类,以“冲末扮某人”或“冲末+某人”的方式出现,但这些人物只在剧首或折首登场时由“冲末”扮演,剧中再次出场时便改为由其他脚色担任,如上例裴尚书、赵大舍等角色便是先由“冲末”扮演开场,随后在剧中又由“孤”“外”所担任,即“冲末”与这些脚色在剧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了同一个人物。此外,“冲末”还可以直接代表某个脚色上场,如脉望馆本《看财奴买冤家债主》剧首:“冲末扮正末同旦儿俫儿上”(16)《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十九),《古本戏曲丛刊》四集。,《状元堂陈母教子》楔子:“冲末外扮寇莱公引袛从上”(17)《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九),《古本戏曲丛刊》四集。等,表明“正末”“外”等脚色都是以“冲末”的身份登台开场的。可见,“冲末”并没有固定的扮演类型,且只出现于剧首或折首,此处用于开场的脚色、人物皆可被称为“冲末”,它虽然代表剧中人物,但与元杂剧的脚色之间却存在着区别,并不能算是脚色之一,而由“冲末”担任“开”的实施者,其职能便是代表不同的脚色进行开场。
最后,“开”的内容逐渐程式化,大多由“上场诗+自报家门+介绍剧情(或剧情梳理)”三部分组成,如《改定元贤传奇》本《西华山陈抟高卧》中:
(正末道扮上,开)术有神功道已仙,闲来卖卦竹桥边。吾徒不是贪财客,欲与人间结福缘。贫道姓陈,名抟,字图南的便是,能识阴阳妙理,兼通遁甲神书。因见五代间,世路干戈,生民涂炭,朝梁暮晋,天下纷纷,隐居太华山中,以观时变。这几日于山顶上,观见中原地分,旺气非常,当有真命治世。贫道因下山,到这汴梁竹桥边,开个卦肆指迷,看有甚人到来也。(18)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第125页。
这是明选本中人物上场时典型的宾白形式。“上场诗”由两句或四句的韵文组成,内容大多与说话的人物有关,或介绍说话人物身份,或描述性格、抒发人生感悟等。它并非是明本中的新增内容,如前文所述,在元刊本中也有类似的韵文出现,但《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舞台演出的脚本,更偏重曲辞而忽略宾白,故包括上场诗在内的大量宾白在演出时多由演员自由发挥,并不常见于元刊本之中,然而在戏曲口耳相传的授艺方式下,上场诗的内容与用法趋于固定,到了逐渐文本化的明选本中便成为人物开场时的惯例。
二、“开呵”的用法与来源
关于“开呵”,最常见的资料便是徐渭在《南词叙录》中的记载,即“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今戏文首一出,谓之‘开场’,亦遗意也。”(19)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46页。于是,很多学者便把元杂剧文本中的开场提示语“开”等同于“开呵”,且将其看作为“开呵”之省文。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王万岭先生指出“元杂剧的‘开’与宋杂剧的‘开呵’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并且认为“徐文长是因为研究‘南词’才顺便解说‘开呵’的,他的解释没有针对‘北曲’。”(20)王万岭:《元杂剧的“开”与“节目主持人”无关——与黄天骥先生商榷》,《戏曲研究》2002年第1期。那么,“开呵”与“开”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开”又能否被当做“开呵”的省文呢,我们可以通过对“开呵”之形态、来源的探讨,作出比较分析。
现存文献中,“开呵”一词较早见于金末元初之时。商政叔的【一枝花·叹秀英】中记道:“为妓路刬地波波,忍耻包羞排场上坐。念曲、执板、打和、开呵。随高逐下,送故迎新,身心受尽催挫。”(21)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9页。宴乐演出中,在乐床上做排场的女艺人,除了唱曲之外,还负责“打和”“开呵”等。有学者认为“打和”即“开呵”(22)黄天骥先生在《从“引戏”至“冲末”——戏曲文物、文献参证之一得》中道:“打讹即打和,也就是开呵。”,其实不然。“打和”一词在北宋时便已出现,如《东京梦华录》中“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2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101页。“和”即应和、唱和,此处是指对参军色念致语口号的应和,另南戏《琵琶记》第十七出中也有“我唱你打和”的记录:
(净云)呀,倒被你听见了,也罢,我唱你打和。
(丑云)使得。
(净云)孝顺还生孝顺子。
(丑云)打打咍莲花落。
(净云)忤逆还生忤逆儿。
(丑云)打打咍莲花落。
(净云)不信但看檐前水。
(丑云)打打咍莲花落。
(净云)点点滴滴不差移。
(丑云)打打咍莲花落。(24)《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这些都可看出“打和”是对他人念唱的一种回应与配合,但“开呵”却非如此,以下几则材料对“开呵”的形式、内容进行了直接的描述。
《水浒传》第三十六回:
宋江分开人丛,挨入去看时,却原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枪棒。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枪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口里开呵道:“小人远方来的人,投贵地特来就事。虽无惊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远处夸称,近方卖弄。如要筋重膏药,当下取赎。如不用膏药,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赍发,休教空过了。”(25)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6年,第449页。
第五十一回:
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呵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26)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中),第640页。
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予闻清源,西川灌口神也。为人美好,以游戏而得道,流此教于人间。讫无祠者。子弟开呵时一醪之,唱啰哩嗹而己。(27)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28页。
院本《园林午梦》:
[开和]轮转心长不动,争长竞短何用。拨开尘世闲愁,试听园林午梦。
[末扮渔翁上]……(28)《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下),《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首先,能够“开呵”的伎艺十分多样,它并不仅存在于杂剧演出中,杂耍、诸宫调、祭祀、院本等不同的表演方式均可“开呵”。其次,在内容上,“开呵”的功能包括请求赏赐、引导人物上场、帮唱衬词、宣赞开场等,实施者皆是以剧外之人的身份主持和引导节目演出的,内容游离于所衔接的伎艺演出之外,不能左右表演剧情的发展。最后,“开呵”大多出现在表演的开场之前,虽也有例外,如上例《水浒传》中,实施者是在“使了一回枪棒”之后,才张口“开呵”以求赏赐的,但其内容及功能并没有随着出现位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现有资料中,“开呵”这一称谓出现于元代前后,但其对应的行为、职能却与宋代的教坊乐语具有一致性。在宴乐表演中,乐语的基本结构由十五个部分组成,通常会根据宴会的繁简程度进行删减、组合。如《东京梦粱录》“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
第五盏御酒……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乐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小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2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第101页。
文中“作语”“问小儿队”“勾小儿队舞”“进口号”“勾杂剧入场”“放小儿队”等,都是教坊乐语常用的程式。“作语”即念致语,它与“口号”都用于宣赞颂扬,大多为德美祝贺之词,且早在唐朝便已经有与其相似的表演形式,如陈旸《乐书》中记:“唐时谓优人辞捷者为‘斫拨’,今谓之杂剧也。有所敷叙曰‘作语’,有诵辞篇曰‘口号’。凡皆巧为言笑,令人主和悦者也。”(30)陈旸:《乐书》卷一八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842页。,虽然具体形态上有所差异,但它们可被看作为宋乐语中“作语”“口号”的前身。另“勾小儿队舞”“勾杂剧入场”“放小儿队”等,则具有串连演出的作用,以王珪的《集英殿乾元节大燕教坊乐语》为例:
《勾小儿队》:“玉宇风微,觉纤埃之不动;金徒漏缓,知瑞旭之初长。尧樽纔泛于九霞,禹会正趋于离万玉。宜诏髡髦之侣,来陈舞羽之容。上悦天颜,教坊小儿入队。”
《勾杂剧》:“翩跹长袖,适停逸缀之文;曼衍都场,未尽多欢之具。宜荐滑稽之戏,以资恺乐之情。徐韵宫商,杂剧来与。”
《放小儿队》:“舞茵徹绣,暂收画鼓之声;宴斝浮香,渐转绿槐之影。歌沛风而甫歇,咏沂水以将归。再拜天阶,相将好去。”(3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勾”“放”是引导节目进行上场或下场,一般出现在表演前后,对演出作出调度与安排,多由参军色诵念,有时也由队舞班首代劳。综合而言,乐语是通过参军色念致语、口号,并与小儿班首、女童班首相互问答的形式,来宣赞颂扬、引导节目上下场演出的,将其与伎艺表演中的“开呵”相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在职能上的相似性。
而这种演出方式的相互借鉴,源于教坊与民间演出的互动与交流。不同于唐代,宋时教坊与民间的联系颇为频繁,不仅节日典庆时会召集民间艺人入宫承应,且伎艺精湛的民间艺人还会被征入教坊,同时,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教坊艺人也会流落民间。艺人的流动使得教坊与民间演出可以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在表演方式上达到相通的效果,故而,教坊乐语所代表的行为与职能在民间演出中出现便不足为奇,如上文【一枝花·叹秀英】中:“为妓路刬地波波,忍耻包羞排场上坐。念诗执板、打和、开呵”(32)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第19页。,“做排场”即在演剧过程中,由女艺人在舞台旁作出的辅助表演,而“念诗执板”“打和”“开呵”等形式,便可看作对宋代教坊乐语的继承。
同时,与参军色负责教坊演出中的勾入、勾出相对应,引戏色承担了民间杂剧表演时的引入、引出。引戏是宋金杂剧中的重要脚色,如《梦粱录》中所记道:“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33)吴自牧:《梦粱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90页。所谓“引戏色分付”,便是指引戏“盖在做院本场中为导引或赞相之人”(34)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403页。,其宣赞开场、解说剧情并引导人物上下场的职能与“开呵”相契合,故而引戏可以看作宋金杂剧演出时“开呵”的实施者。
引戏是杂剧的戏班成员,并非是剧中角色,它负责引导角色上下场,是独立于演出之外的。如散曲《庄家不识勾栏》中:
【四】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不多时引出一伙,中间里一个央人货。裹着枚皂头巾顶门上插一管笔,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知他待是如何过?浑身上下,则穿领花布直裰。
【三】念了会诗共词,说了会赋与歌,无差错。唇天口地无高下,巧语花言记许多。临绝末,道了低头撮脚,爨罢将么拨。
【二】一个妆做张太公,他改做小二哥,行、行、行,说向城中过。见个年少的妇女向帘儿下立,那老子用意铺谋待取做老婆。教小二哥相说合,但要的豆谷米麦,向甚布绢纱罗?(35)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第31页。
这首散曲保留了金末元初勾栏演出的情形。其中“引出一伙”的女孩就是引戏,她负责将演员引上台前,类似于教坊演出中的“勾杂剧入场”,演员上场后,先由“央人货”负责插科打诨,“做寻常事一段”即杂剧中的“艳段”,接着院本、杂剧的演出便正式开始了,引戏将演员引出后,并没以剧中角色的身份加入表演。另外,在明代《鹦鹉洲》传奇第六出串演的《傀儡梦》中,引戏对人物动作、剧情的解说也可以使我们看出,引戏在演出中是以司仪职能独立于戏外的。
到元杂剧时期,虽然在剧本中未见对“引戏”的记载,但他们也是实际存在的。如元代山西运城西里庄墓杂剧壁画东壁所绘六人中,左第二人身着圆领长袍,腰束带,戴幞头,与宋金戏曲中的引戏扮相相吻合,手中的竹竿更是对“参军色执竹竿子”的继承,其职能便是负责开呵、收呵,对杂剧演出的上下场作出指导。
可见,“开呵”在不同伎艺中的形态,与元杂剧文本中“开”的用法有着明显的区别,且通过对“开呵”所代表的职能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从宋代到金元时期的教坊、民间演出中,始终有“主持性质”的脚色存在,具体到元杂剧中虽缺乏对“开呵”的直接记载,但负责引导表演上下场的脚色显然与元杂剧文本中“开”的实施者有所不同。
三、二者的区别与“开”的成因
经上文论述,可以明显看出“开”与“开呵”在实施者、内容及职能等方面上的差异。
对元杂剧而言,“开”是剧中人物登场时对所念宾白的提示,其内容是构建、推动剧情的一部分。元明选本中,并非所有剧本都用“开”作为宾白提示语,一些剧本甚至没有出现“开”,而是用“云”“念”等提示人物念白,将这些提示语进行对比,可知“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只出现于折首或每折中人物初次登场时,具有象征性提示开场的意味。那么,用它提示开场时是否带有表演性质的伎艺程式呢?通过对同一剧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些杂剧在元本中用“开”作为提示语,到明本中的同一位置时,却会用“云”将其代替,如《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马丹阳三度任疯子》等,还有杂剧在某些版本中存在“开”,而其他版本却没有,如《改定元贤传奇》中,《玉箫女两世姻缘》在剧首使用了“开”为提示语,而到《杂剧选》、古名家本中却都将之省略。这种提示语之间可以相互替换且随机出现的用法,从侧面表明“开”和“云”一样,都仅仅是文本中对脚色开场说白的提示,并不包含特殊的演出伎艺。
但与“开”不同,“开呵”的实施者则是以剧外人的身份来主持、引导杂剧演出的,其内容游离于剧情之外。在元杂剧中,与“开呵”用法相近的是“按喝”,“按喝”即在杂剧表演的精彩之处“按住开呵”,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第四折,正末扮司马相如上场,唱【越调·斗鹌鹑】“巍巍乎魏阙天高”(36)《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四五),《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时,“外按喝上”,暂停了演出进程,开始以第三视角向观众介绍故事大意,并作一番感慨后,表演才再次展开。“外”便是装外,胡忌先生通过《水浒全传》记载“装外”的装束与职能,认为“装外”便是“引戏”。可见,“按喝”与“开呵”都由“引戏”实施,其职责皆在于引导、协调杂剧的演出,“开呵”一词也并非仅为文本中的提示语,而是代表了演出的一部分,与“开”“云”等用于介绍人物身份、发展剧情的提示语并不相同。
因此,可以看出“开”与“开呵”的关系,即“开呵”出现于杂剧演出开始之前,用以引导、指挥演员登场,而“开”“云”等则是在元杂剧文本中作为人物“诵诗通名姓始末”的提示语,开场并展开剧情。既然文本中的“开”并非为“开呵”的省文,那么,关于“开”为何在元杂剧文本中出现,我们可以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编选中推断一二。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目前可见使用“开”最早的元杂剧选本。从编选方式来看,其重曲词而轻宾白,除了部分正色的宾白之外,外脚宾白几乎被全部省略,常用“某某云了”“某某开了”等提示语带过,故元刊本也被当做是为演员或观众提供杂剧唱词的脚本,并不能反映元杂剧演出前后的表演程式。“开呵”在杂剧开演前进行,有吸引观众、介绍剧情的定场功能,其表演内容与实施者的身份都独立于杂剧剧情之外,于是,在编选元刊杂剧时并没有将其记录在内。文本中,人物初上场时出现“开”,便是元刊本省略了“开呵”之后,对读者进行的开场提示,即代表正式演出从此处开始的意思。其次,除了剧首,剧中也会出现提示语“开”,这与元杂剧的表演形式有关。杂剧演出并非一下演完,为填补演员换装而出现的舞台空闲,元杂剧中常会穿插歌舞、杂耍等伎艺,而演出继续时也会重新“开呵”,如前文《司马相如题桥记》中的“按喝”。但杂剧文本中一般不会对这些伎艺演出进行记载,也通常会省略掉“按喝”这一程式,为了提醒读者,便会在剧中重新用“开”作为开场提示语,其性质当与在剧首使用的并无差异。但《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刊印较为粗糙,且又非成于一时一地,所以对杂剧的编选原则就自然不同,因此也就造成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的杂剧有“开”,但一些杂剧中却没有“开”的情况。
综上所述,“开”与“开呵”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关联,二者分别代表了文本中开场宾白的提示语和演出前的一种表演程式。将“开”看作为“开呵”的省文,显然是用欣赏演出艺术的心态关照文本化元杂剧的结果,而未真正辨明它们的具体形态与职能。戏曲的演出与文本之间固然存在一定关联,但对于元杂剧选本而言,它们有相对独立的编选原则,其刊刻目的也并非是为了还原场上的艺术形式,因此,在对元杂剧进行研究时,理应清晰文本与表演形态间的区别,以避免出现对演出艺术在文本呈现上的认知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