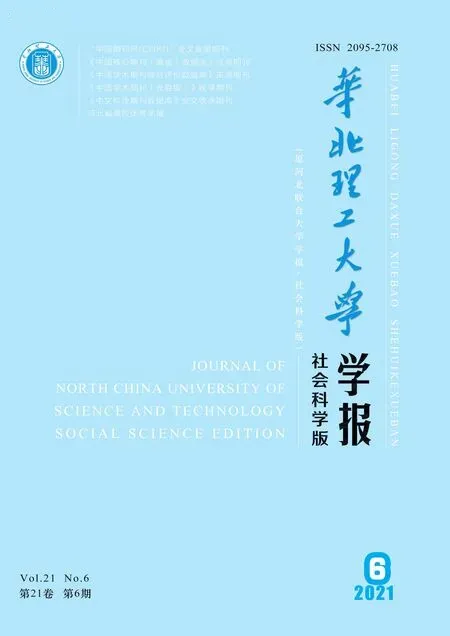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绿色翻译的生态属性及价值取向探析
罗迪江
(1.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广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引言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起始于21世纪初,它的兴起与发展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为理论基础,确定了以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为研究对象,是对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向“生态转向”转变的翻译问题的生态范式研究。在此意义上,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是与其对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研究同步进行的,而其生命力在于它总是能够努力追求以更新的思维方式来把握翻译发展的脉络,并尽可能为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互生共存提供了新的演进方式。这种新的演进方式就是作为生态翻译学新形态的“绿色翻译”应运而生了,作为绿色翻译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也就相伴而行了。这样就可以考虑将此思维范式作为理解翻译现象的思维方式,以此视角来揭示翻译实践活动的共生法则,把握翻译的本质及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因此,从绿色翻译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基本特征等方面着手来对绿色翻译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述绿色翻译在翻译学领域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意义。
一、绿色翻译的生成逻辑
绿色翻译研究起源于生态翻译学但限于方法困境与关注度低而处于停滞阶段。绿色翻译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围绕着新时代的热点议题与难题求解而需要重新审视与考察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只有厘清绿色翻译的发展逻辑,我们才能认识与把握绿色翻译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性。绿色翻译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形态,其产生是解决当代翻译的工具性与功利性等非生态化问题的必然结果。如果将绿色翻译置于翻译学的发展趋向背景中看待,它是当代生态翻译学和复杂性思维范式发展的结果,其出现具有自身内在的生成逻辑。首先,翻译的工具性与功利性是绿色翻译生成的直接原因。翻译的本质特征在“文化转向”中被不断弱化,并且在弱化的过程当中出现泛文化主义的盛行。翻译即操纵、改写、背叛等理念盛行于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翻译的工具性、功利性、自我性等等随之而来。可以说,当下翻译研究普遍存在着一些困惑,陷入各种“转向”的执迷,功利性思维大行其道,生态翻译价值观仍存在着较大偏差,“这不仅不利于我们真正把握与实现翻译的价值、评价翻译的地位,不利于我们把握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创造性”[1]。在工具性与功利性驱驶下,诸如“暴力翻译”、葛浩文式的“连译带改”翻译、“食人主义翻译”等等都呈现出明显的“非生态化”问题,给文学译介或翻译实践带来了生存危机:“通过翻译进行改头换面,甚至任意梳妆打扮,不仅是对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伤害,而且有违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理念,与通过翻译实现双向交流的目标背道而驰”[2]。这就为绿色翻译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解决工具性、功利性等“非生态化”问题提供了绿色理念。绿色翻译是以完整的绿色价值而不是单个语言作为基本的实践理念与分析参考点,有助于避免翻译实践陷入功利主义,进而使翻译实践回归于绿色意义与绿色价值[3]。
其次,生态翻译学是绿色翻译生成的理论来源。生态翻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伴随的是翻译研究的绿色理念、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的涌现,这就向翻译研究提出了绿色发展的要求。当代翻译学的研究格局正趋向多元化与碎片化而导致翻译研究中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处于一种割裂状态,从而使翻译实践陷入“非生态化”问题的泥潭。当我们对“非生态化”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翻译的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翻译的绿色化与合法性就会成为我们重新审视的基本议题。“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尊重原文,这样的翻译是合法的吗?对原文不断地修改、修订甚至是改编,这样的翻译是合法的吗”?[4]从整体上说,翻译的合法性是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相关的,它旨在从绿色理念的视角上去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考察文本的生命状态与审视翻译的生态整体,使翻译具有生态化与绿色化而获得翻译的合法性。
第三,复杂性思维范式是绿色翻译生成的内在驱动力。翻译研究的原文中心论与译文中心论,其所遵循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或二元论思维范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割裂对立,促使译学界对两大转向的翻译观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意识到应对以往的翻译观进行扬弃,从而形成生态翻译学新形态的翻译观——绿色翻译,加之生态翻译学和复杂性思维范式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动摇了原有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既为绿色翻译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解决翻译研究遭遇的“非生态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二、绿色翻译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对于绿色翻译的定义,国内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导致其概念还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当然,本文对“绿色翻译”的认识,源于从生态翻译学的“译者生态、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三生”议题开始,“讲的是以‘生’字为线索展开研究和论证阐述,表明‘生’是生态翻译学发展之基石”[5]。换言之,绿色翻译是以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为和谐共生体而获得对翻译现象及其过程的“生存·生命·生态”理解与说明。失去三者中任何一方,另一方就不可能得到整体性地理解与说明。绿色翻译的这种互存共生反映了绿色翻译的存在本质是和谐共生。透过这种和谐共生,我们不难把握绿色翻译的内涵:绿色翻译是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形成的一种互存共生、和谐统一的生态关系。因此,绿色翻译的定义包含三个层面:(1)就译者生存而言,绿色翻译是以译者的生存境遇为前提,以“生态人”的身份考察文本的生命状态而实施翻译的绿色行为方式。(2)就文本生命而言,绿色翻译是以和谐共生为视域关注文本的生命状态,探讨译本“自我”的诞生、延续、成长是如何在“他者”异域中生生不息。(3)就翻译生态而言,绿色翻译是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可见,绿色翻译将成为一种贯通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形成了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
基于此思维范式,绿色翻译具有以下本质的特征:(1)共生性。绿色翻译意味着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译者生存只有在共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成为真实、完整的“生态人”;文本生命只有在共生中才能“适者生存”、“生生不息”;翻译生态只有在共生中才能“焕然一新”。共生是“和而不同”,是“自我”与“他者”的共存。(2)实践性。绿色翻译并不预设固定的对等性原则,而是把翻译的可能性奠基于具体的绿色实践之上,使得绿色翻译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成为可能。可以说,实践性是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本质属性。从译者的角度来看,译者之所以成为绿色翻译的“生态人”,就在于基于绿色理念的实践性,一方面扬弃译者主体的纯粹主观性,增强译者主体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力争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另一方面扬弃文本的确定性而寻求文本在异域中的诞生、生成、延续与成长。因此,绿色翻译的实践性本质要求在绿色翻译实践中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去把握与认识翻译过程,任何单纯地把翻译仅仅理解为“生存”、“生命”或者“生态”,进而选择简单性思维范式,是不可能真正通向正确理解翻译的认知途径。(3)动态性。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是一种动态方法论,其根源在于翻译实践活动的动态性。换言之,绿色翻译不是以二元对立的简单性思维范式为其前提的,而是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为导向,强调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交互性的存在,译者的翻译行为终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生成过程。在此意义上,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是一种绿色性的动态关系,文本生命向译者生存展示其“生生不息”本性;反过来译者生存不断地探寻文本在异域中如何“适者生存”,由此认识与理解文本的生命特性与生态特性。(4)开放性。绿色翻译是由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构成的翻译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不是由同质的、一元的单元构成的封闭系统,它是在开放性的生态系统中,实现译者、文本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在这个和谐共生体中,则更是“自我”向“他人”开放的生态系统,它“蕴涵着翻译的多样统一、动态平衡、整体关系以及翻译的生态、文本的生命、译者的生存的相互交叉渗透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而又整体的动态关系”[6]。(5)系统性。首先,绿色翻译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对翻译行为相关因素的文本考量,必须引入文本自治性、生成性与成长性的考量,更依赖于对翻译主体及其创造性、伦理性、生态性等相关因素的译者考量,同时包含翻译过程所涉及到的翻译生态场与翻译环境的考察。因此,绿色翻译的本质是多元系统化的。其次,绿色翻译的价值是生态化的,它不能在单一或孤立的意义上进行考察,而是应当将其置于翻译生态系统之中加以生态化地审视与探讨。因此,绿色翻译系统性地趋向于翻译研究的可持续性。再次,绿色翻译是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确定的复杂性思维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及其现象进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才能获得其内在的运行机制与有效性限制。
纵观绿色翻译的五个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其中共生性是绿色翻译最根本的特征,显示了绿色翻译之为绿色的本质特征,也是最能体现绿色翻译有别于传统翻译的关键所在;实践性与动态性是基于共生性得以展开,强调了绿色翻译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开放性与系统性则是对共生性的进一步阐释,凸显了翻译生态系统的包容性。当然,这五个特征并不是绿色翻译所独有的,其他翻译观或多或少也具有这些特征。分析绿色翻译的这些特征并不是为了单纯从绿色翻译的生成逻辑与基本概念层次对翻译研究进行描述,而是为了强化我们对于绿色翻译的理解,并以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为切入点对传统翻译提供了必要的批判与反思,从而确立此思维范式应有的描述力与解释力。
三、绿色翻译的生态属性与价值取向
绿色翻译是随着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既是生态翻译学的新形态,也是翻译研究的新形态。因此,对绿色翻译的认识与理解离不开对生态翻译的认识与理解。按照对绿色翻译的内涵及概念所做出的阐释,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来论述生态翻译与绿色翻译之间的关联。其中,广义而言,绿色翻译与生态翻译具有一致性的内涵关系,即是在翻译活动中对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共生的生态化认识的总和。狭义而言,绿色翻译主要是涵盖了译者对翻译所持有的生态意识、绿色理念与绿色行为层面的内涵。因此,从这个层面对生态翻译与绿色翻译的关系进行论证的话,我们发现绿色翻译是生态翻译的具体化与实践化,并且为生态翻译的发展提供具体的实践路向。可以说,翻译研究的发展离不开绿色翻译的推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渗入翻译研究的领域,可以内化为人们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
(一)绿色翻译的生态属性
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求“真”的开放性过程,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西方和中国对认识翻译、定义翻译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程,并且在未来的研究中仍将继续[7]。绿色翻译表现为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存在,正是朝向“真”发展而显示出新的魅力,它既是翻译发展的原初状态,也是翻译求“真”的最高存在。
第一,绿色翻译本质上追求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共生与多样统一,它通过纠正工具性对于生态价值与价值理性的不恰当的排挤,并试图以复杂性思维范式将翻译的工具性与价值性有进行有机整合,转变译者行为的单向性追求,警惕与避免翻译行为的工具性与功利性。确实如此,翻译的单向性定位是传统翻译简单性思维范式造成的,而绿色翻译是基于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进行的,是一个多维度、多向度的动态过程,追求翻译的可持续性与生命力。绿色翻译不仅要考虑“如何翻译”问题,也要考虑“译本如何被接受”的问题,更要关注译文本在异域中是“如何适者生存”的问题。可以说,绿色翻译的本质是生生不息,是译者的生存、文本的生命与翻译的生态及其三者相互作用的和谐共生。
第二,绿色翻译为翻译研究趋向描绘了一种全新图景,即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互生共存与和谐统一,促使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建立在译者、文本、翻译生态环境这三者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绿色翻译因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而显现出翻译自治性与翻译成长性的统一。自治性优先考虑文本,使文本成为翻译活动的本质力量,使自身在异域中或说“异的考验”中凸显翻译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特征。简而言之,翻译自治性是一个不断显露阶段性的历史过程。成长性使翻译有了“适者生存”的延续与发展的生态空间,使翻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生态系统,而是一个自我向他者开放的生态系统。绿色翻译的本质就是自治性与成长性的统一。此外,绿色翻译又因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而体现出确定性与非确定性、译者主体与译者责任、他者与自我、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第三,绿色翻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实践方式。实践作为译者自我塑造、自我确证的生存方式,决定了译者作为绿色翻译的“生态人”。译者作为“生态人”的行为方式就是要求译者在考察与思考与原文、译文、翻译群落(包括原作作者、译文读者、赞助商、委托人等等)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生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态实践思维方式[8]。一方面,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构成了翻译生态系统而具有“生态场依存性”,译者要兼顾翻译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译者是具有创造性与适应性的主体,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的“生态场依存性”并不是限制译者的全面发展,使得译者能够在翻译生态系统中“随心所欲不逾矩”,从而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绿色理念与绿色行为。这种翻译的绿色行为是以生态化与绿色化为基准,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理念与绿色行为,它既能推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和谐性生存与创造性生存的统一,又能推进文本在“异的考验”中“适者生存”、“和而不同”,促成文本生命的“生生不息”;又能促进翻译生态环境成为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有机土壤。因此,绿色翻译所提供的绿色理念与绿色行为,它的着眼点是一个整体性的生态考量,是译者、文本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命运共生体。
(二)绿色翻译的价值取向
绿色翻译是建构在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基础之上,而绿色翻译的和谐共生需要体现在翻译价值取向的有效定位与广泛认识。绿色翻译的产生,是源于生态翻译学的迅速发展与生态翻译理念的持续拓展,而翻译的绿色价值观演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有着多元的发展指向。总体来说,翻译的价值观可分为三个阶段:文本中心主义价值观、译者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
第一、文本中心主义价值观。它是以对等性原则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开启的,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价值观。这就“极大地推进了翻译学的学科创立,将翻译问题探索从经验主义的泥潭带出,为翻译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一系列亟待解答的问题”[9]。一方面,它需要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概念与结构进行精确地理解与说明,在理解与说明过程中尽力地避免翻译文本中语言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语言学范式就是强调“文本”的唯一性及其意义的确定性,厘清语言的混乱性,语言的使用与表征能够获得正确的、清晰的理解,从而为翻译推理的无限理性提供了可行性与现实性。由于文本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了文本是衡量翻译的尺度,文本与译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被曲解,最终导致文本与译者之间关系陷入了二元对立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可以理解为语言层面上的危机。
第二、译者中心主义价值观。译者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由文化范式驱动的,其目的就是要寻找回被语言学范式遮蔽的译者及其“主体性”问题。因此,主体性问题是语言学范式之后翻译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推动文化转向产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在“主体性”确立的初期,这种价值观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主体性的过渡张扬与膨胀,它也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译者中心主义价值观对译者创造性的过分张扬让文本成为了被译者操纵、改写、背叛与主宰的对象,文本因此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与译者也因此失去了自我,文本与译者再次陷入了极度分裂的状态。
第三、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就是指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和谐共生的绿色价值观,就是由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指向的绿色价值观。绿色价值观之所以在翻译研究中具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偶然的。对翻译研究的两大转向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首先,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将文本与译者割裂开来,然后由文本中心主义价值观向译者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转变,这种基于“有序、分割、理性”的简单性思维方式是失效的。其次,倘若把译者放置于无限的主体性之中去解决翻译的主体性问题,从而使翻译行为趋向任意性与功利性,那将消解译者自身的创造性与本真性,因而也是不适当的。那么,单纯地从文本的视角或译者的视角去看待翻译问题,都有着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因此,要求解翻译研究存在的难题,一方面需要进行复杂性思维范式,使不同研究视角趋向均有一个可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并相互关联的整体综观;另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阐释基底,在这个基底上各种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翻译理念可以互生共存。到目前为止,倾向于认为,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所导向的绿色价值观能获得这种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获得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获得译者、文本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统一的阐释基底。换言之,绿色价值观在复杂性思维范式的意义上具有自身存在的地位与功能,在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意义上给出翻译实践活动的整体性趋向确定了现实可能性,它对于翻译研究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与价值论趋向,对于翻译研究趋向生态意识、绿色理念、绿色价值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思维范式实现了“三生”问题上译者与文本、翻译生态环境的融合,深化了翻译问题的本质研究,因而在翻译研究中具有更加突出的作用。作为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绿色翻译的解释建构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之上,诉诸了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的分析方法,究其实质乃是对基于“有序、分割、理性”简单性思维范式的突破与超越,促使翻译实践活动真正建构在具有生命活力的绿色行为方式之上,其所展示的作为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和谐共性的本质特征,内在地规定了绿色翻译的生存化、生命化与生态化。因此,绿色翻译事实上是以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方式在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形成一种融合性的绿色价值观解释,它是对传统翻译价值观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建立了符合翻译研究发展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积极的价值观层面的指引。用绿色翻译的方式去认识与理解翻译就成为翻译研究新思维范式的必然选择,其完全合乎绿翻译本身蕴含的绿色意识与生态责任[10]。因此,综观翻译研究的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绿色价值观的凸显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与时代迫切性的趋向。
四、结语
翻译研究的两大转向以及价值观的发展历程,使绿色翻译更自觉地突出了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作为一种复杂性范式的地位与作用,并通过这种复杂性范式的展开和实现去分析翻译价值观的演进并选择绿色翻译价值观作为未来发展的趋向。事实上,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是在生态翻译学的深入探讨中突显出来的,并试图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作为重要议题进行研究以求得翻译研究的整体性综观。同时,翻译研究的两大转向的深刻教训在于,它们执迷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没有充分把握翻译的整体性与复杂性,没有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和翻译生态的分析整合起来,而是将它们分别地割裂开来。绿色翻译正是将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绿色理念、绿色价值与绿色行为的指引与导向。可以说,绿色翻译既是扩大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也是一个有效的复杂性研究范式,它能够进一步增进翻译研究的包容性、生态化、复合性与开放性,导向一种更广义的生存·生命·生态思维范式,从而包容各种不同翻译观内在的统一性和共同的价值。
——简评《中国法治的范式研究:沟通主义法范式及其实现》(郭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