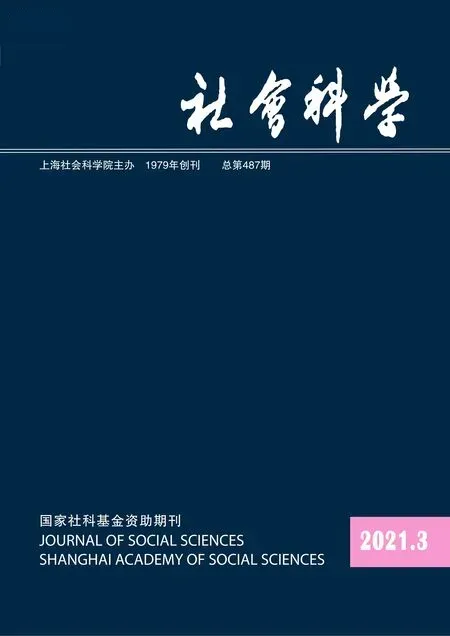何谓时间分析的“本体论差异”*
——重衡当代英美时间哲学之争的根本问题
陈群志
“时间”论域属于“形而上学”似乎没有异议(1)参见Alyssa Ney, Metaphys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138-169; M.J. Loux and D.W. Zimmerman,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11-256; L.N. Oaklander, ed.,Debates in the Metaphysics of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p.1-128; C. Williams, “The Metaphysics of A- and B-Time”,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46, No.184, 1996, pp.371-381。,而“时间”的“本体论”之争倒是另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争论分析或描述“时间”的路径或方式的差异,那么显然是基于“方法论”(methodologically)的角度来思考,而非“本体论”(ontologically)的地位问题。在西方学界,“时间本体论”的探究也有一些直接成果,无论是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界皆有关注,目的是要考察构成“时间”的“根源”为何。(2)参见A. Chernyakov, The Ontology of Time: Being and Time in the Philosophies of Aristotle, Husserl and Heidegger,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02; L. N. Oaklander, The Ontology of Time,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4; D. Dieks, ed.,The Ontology of Spacetime, Oxford: Elsevier B.V.,2006。
不过,具体到我们要讨论的当代英美时间哲学中的A-理论与B-理论之争,“本体论”问题就仅限于其“构成”到底是源于“A-系列”还是源于“B-系列”。如果把“时间”视为一种“秩序”,那么对“时间”的分析就必然要走向“关系论”;如果把“时间”视为一种“流逝”,那么对“时间”的分析免不了会走向“生成论”,时间分析的“本体论差异”就是依此形成的。在此之中,时间的“本体论”之争自然也属于“形而上学”领域,同时还伴随着“方法论”的考量。
一、“时间本体论”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开始反思,就会发现,时间的诸种因素从根源上来自于对它自身的追问,时间的本性是什么?不过,实际上,自麦克塔加(John M.E. McTaggart)论列以来,首当其冲的问题当属时间的“实在性”和“非实在性”的争议。依他的描述,很多近代的哲学家都否定了时间的“实在性”,并给出了各自的论证。(3)参见John M.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Mind, Vol.17, No.68, 1908, p.457。以至于他的学生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早期的名文《神秘主义与逻辑》(1914)中甚至言道:“时间的非实在性是许多形而上学体系的一个基本学说。”(4)[英]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及其他论文》,贾可春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页。这种阐述显然是受了乃师的影响,只是罗素并不赞成如此观点,他明确表明:“那些关于时间是非实在的及感官世界是虚幻的这一论点的论证必须被视为谬误。”(5)[英]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及其他论文》,第22-23页。
罗素是典型的B-理论家,支持时间“关系论”的理路,但却不像其追随者奥克兰德(L.N. Oaklander)那样试图从“本体论”角度来澄清和界定时间“关系论”不可分析和无法还原的根本特性。当然,在否决麦克塔加的“非实在性”论证的这一条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不言而喻,如果时间的“实在性”得不到确立,也就无所谓“本体论”问题了。如此看来,提出“时间本体论”问题,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反驳麦克塔加的结论,另一方面可以为自己的立场进行“底层”辩护。
依奥克兰德的设想,时间的“本体论”分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立“时间关系”(temporal relation)(以B-理论为标准)作为“原初的”和“最终的”时间之形而上学本性。(6)L.N. Oaklander, The Ontology of Time, p.18.而如果依据“时间生成”(temporal becoming)(以A-理论为标准)是做不到的,它不是确定时间之实在性与客观性的基础。然而,麦克塔加如此说道:
当然,如果我们把另一个系列正确地称之为时间系列,那么这个问题就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哪里有时间,哪里就有变化。然而整个问题在于它是否是一个时间系列。我的争辩是,如果我们把这个A系列从时间的元初(primafacie)本质上去掉,就只剩下一个无时间性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变化顶多是一个纬度系列(a series of latitude)(按:如依据本初子午线所经过的纬度而来的时间系列)所允许的变化(按:亦即不能算是变化)。(7)J.M.E. McTaggart,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Vol. II, ed. C.D. Broa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15.
这里所谓的“另一个系列”指的是A系列(动态时间系列),亦即后来据此发展起来的A-理论。依麦克塔加的论述,“时间”与“变化”是不可分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古义。(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3页。但实际上,他与亚里士多德思路相反,只是运用归谬法而已,最终宣称“时间”、“变化”与A系列都不是真实存在的。(9)J.M.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p.470.不过,仅就这一段话来看,麦克塔加至少部分承认,A系列是“时间”内在固有的“时间性存在”,是“时间”的“元初”本质所在。如果从“元初”的表述出发,“时间本体论”就必须在此意义上才能给予说明。
奥克兰德当然不会认可这种论调,在“时间本体论”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开始点:即麦克塔加之所以能逻辑性地论证时间是非实在的,是因为其认为“时间流逝”(temporal passage)或“时间生成”自相矛盾。所谓的“时间流逝”或“时间生成”,是指沿着一系列“瞬间”(moments)和“事件”(events)的“现在”运动。在这一点上,梅勒(D.H. Mellor)、奥克兰德、包德维(R.L. Poidevin)等赞同麦克塔加有关A系列(A-理论)不真实的“悖论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只是没有接受他的结论,因为他们认为B系列(B-理论)足以说明时间的“实在性”,并能够依此对时间进行形而上学的奠基。(10)H. Mellor, Real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L.N. Oaklander, Temporal Relations and Temporal Becoming: A Defense of a Russellian Theory of Tim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L.N. Oaklander, “McTaggart’s Paradox and the Infinite Regress of Temporal Attributions: A Reply to Smith”,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25, 1987, pp.425-431; L.N. Oaklander, “McTaggart’s Paradox Defended”, Metaphys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tology and Metaphysics, Vol.3, No.1, 2002, pp.11-25; R.L. Poidevin, Change, Cause and Contradiction: A Defense of the Tenseless Theory of Time,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1.与之相反,施莱辛格(G.N. Schlesinger)、卢卡斯(J.R. Lucas)、史密斯(Q. Smith)等则主张B-理论(非时态理论)的观点要让位于基于我们自身之“体验”而来的时间观,亦即时间的“实在性”也当取决于A系列(A-理论)的特性,A系列能被视为一种“本体论”认知。(11)G. Schlesinger, “How Time Flies”, Mind, Vol.91, No.364, 1982, pp.501-523; G. Schlesinger, “The Stream of Time”, in L.N. Oaklander and Q. Smith (eds.), The New Theory of Time, pp.257-285; J.R. Lucas, The Future: An Essay in God, Temporality, and Truth, New York: Blackwell, 1989; Quentin Smith, Language and T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问题:时间的“实在性”如何确立?只不过,随着学者们探究议题的深入,“实在性”的问题已然不再是主要关注点,关注点转换成了如何建构时间“本性”的构成,亦即对“时间本体论”的追问。显而易见,在“本体论”问题上,上述两种时间理论的争论各有立场,难以融通。笔者倒以为,这有点像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或许二者是可以共存的。
当然,争论在所难免。对于麦克塔加和一些A-理论家的那种把A-时间视为“元初”本质的观点,梅勒和奥克兰德的批评与反驳在B-理论家中算是比较有力些的。(12)D.H. Mellor, Real Time I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7-18; L.N. Oaklander,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taphysics of A- and B-Tim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Vol. 26, 2001, pp.23-36.总体来说,奥克兰德给出了多个方面的理由来为B-理论辩护,其中他更关注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即时间哲学的形而上学奠基问题:B-理论具有“原初的时间关系”(primitive temporal relations),而A-理论没有“原初性”,也不谈“时间关系”,这是B-时间与A-时间的根本不同之所在,亦即形而上学的差异。很显然,奥克兰德作出这样一个“奠基性区分”的大体想法,是受到罗素和布劳德(C.D. Broad)的影响。(13)L.N. Oaklander, The Ontology of Time, p.24.因为他们二者都主张,“时间关系”是不可分析的最原初的“时间本质”,它是“非时态的”,不能用“时态谓词”来加以界定,也不能被“还原”或“转换”为“时态属性”。(14)B. Russell,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Monist, Vol.25, No.2, 1915, pp.212-233; C.D. Broad, “Time”, in J. Hastings, ed.,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inburgh and New York: T. & T. Clark and Scribners, 1921, pp.334-339;
至此为止,基于“本体论”而言,A-理论家和B-理论家对“时间”的思考似乎已经转换成了“生成论”和“关系论”哪个更“原初”的问题。从问题的提出来看,要区分时间存有的不同性质很重要,同时还要分辨清“A-生成”和“B-关系”在英美哲学中的特定所指。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时间理论之争不能被看作莱布尼茨和克拉克论战的延续,因为那虽然是牛顿的“绝对时间论”与莱布尼茨的“关系时间论”的分歧,但实际上他们对待时间的态度都比较偏向于“空间化的时间”。(15)参见[德]莱布尼茨、[英]克拉克:《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120页。“空间化的时间”探究并不是“纯粹性”地研讨“时间”,这与A-理论以及B-理论的初衷不相同,虽然说也有些许交叉的地方。缘于此,我们还需要追溯“本体论差异”的来源。
二、“生成”与“关系”的差异溯源
“时间”必有“本体”吗?抑或“时间”需要“本体”吗?对此问题的回答并不容易,可能需要我们重新界定“本体”的具体含义。如果这个“本体”指的是“本性”的话,那么“时间”当然有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在追问它。(16)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21页。可是,如果这个“本体”指的是“实体”的话,那么就还必须弄清“实体”的所属,到底属于“观念的实体”还是“经验的实体”,但这是从古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旧问题。
如何能更确切地追溯这种“差异”呢?如何在“实体”(也就是“本体”)的另一方把握它们呢?我们知道,观念论者笛卡尔(Descartes)重视“实体”概念,他强调“时间”是一种“观念实体”或“思想实体”,而不是一般的“实体”。简言之,“时间”是以一种“观念实体”存在于“思维领域”中的。不过,笛卡尔也同时强调了“时间”的“变化”,如其所言:
如果我们注意到时间的本性或事物的持续(duration),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掩盖这一证据的明晰性。因为时间的本质是这样的:它的各个部分并不相互依存,也从来没有共存过。(17)Descartes,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in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1, trans.,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D. Murdo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00.
我们对持续、秩序和数也将有非常清楚的理解,只要我们不把任何实体的概念错误地加到它们上面。相反,我们应该只把一件事物的持续看作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我们认为事物是继续存在的。同样地,我们不应把秩序或数看作是与有秩序和有数的事物相分离的任何东西,而应该把它们仅仅视为我们思考所讨论事物的方式。(18)Descartes,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in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1, p.211.
为了测量所有事物的持续,我们将它们的持续与能产生年和日的最大且最规律的运动的持续进行比较,而称这个持续为“时间”。然而,就一般意义而言,除了一种思想方式(a mode of thought)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加于持续之上。(19)Descartes,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in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1, p.212.
在笛卡尔这几段论及时间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一方面认为“时间”是一种“思想方式”,它不是一般的“实体”,而是犹如秩序和数一样的“观念实体”;另一方面他主张“时间”不应与事物相分离,它具有“持续性”,但它的各个部分不能“共存”。与之相同的是,经验论者休谟(David Hume)虽然轻视“实体”概念,但也强调了“时间”或“持续”的各组成部分无法“共存”,在他看来,“共存”只能属于空间意涵的“广延”而非时间意涵的“持续”。
时间有一个和它不可分的特性、可以说是构成了它的本质,即时间的各个部分相互接续,而且任何一些部分不论如何邻接,也永远不能共存的。一七三七年和今年一七三八年不能同时出现,根据同样的理由,每一个刹那和另一个刹那也必然互相区别,不是在后,便是在前。因此,时间的存在确是由不可分的刹那组成的。因为,如果我们永远不能把时间分割到底,而且接续其他刹那的刹那也不是完全单一不可分的,那就会有无数共存的刹那或时间的部分;这一点我相信会被认为是一个明显的矛盾。(20)[英]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4页。
时间或持续是各个部分组成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便不能想像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持续。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些部分不是共存的:因为各个部分的共存性质属于广延的,这也就是广延和持续的区别之点。时间既然是由不共存的各个部分组成,而一个不变的对象既然只能产生共存的印象,它就产生不出能够给予我们时间观念的任何印象。因此,时间观念必然是由可变的对象的接续得来,而且时间在最初出现时绝不可能和这样一种接续现象分开。(21)[英]休谟:《人性论》上册,第49页。译文有所改动。
然而,依怀特海(A.N. Whitehead)的阐述,他不同意笛卡尔和休谟描述时间的一个基本前提:时间的各组成部分有“不可共存”的“本性”。显然,这种“时间个体”的“独立性”假设,实际上否决了时间的“连续性”事实,虽然他们都谈到了“持续”概念,并且把“持续”概念理解为“时间”。为此,怀特海言道:“经验包含着生成;生成意味着某物在生成,生成着的东西包含着转变为新颖直接性的重复。”(22)[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5页。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时间生成”的描述在“过程哲学”中获得了支持。
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跟它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这就是说:一个事件把跟它同时发生的事件的样态作为现时达成态的展示而反映在本身之中。事件也有过去。这就是说该事件在自身中把先行事件的样态反映出来,并作为记忆混入自身的内容中去。事件还有未来。这就是说,这一事件在自身中反映出未来向现在反射回来的那些位态。换句话说,它反映出由现在决定的那些样态。因此,事件便有预示作用,就像下面这两句诗所说的一样:无垠寰宇,先知梦魂萦来日。这几句结语对任何形式的实在论说来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认知界中,有过去的记忆,有目前的体现,也有对未来的预示。(23)[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4页。
在英美哲学家中,对“时间生成”这一路向进行过深刻论述并表示了极大致意的,怀特海当属典型代表,只是后来一些学者认为他的时间论过于形而上学而较少谈及。然而,他在《过程与实在》这一名著中明确说道:“结论就是,在每一个生成活动中都有某种具有时间性广延的东西生成;但这个生成活动本身却不是广延性的,因为它并不是像已生成的东西的广延可分性那样,可分为先前的生成活动和后来的生成活动。”(24)[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第109页。笔者认为,从怀特海出发,至少可以把“生成活动本身”视为“共存领域”的“时间本体”,而这个“时间本体”并不是基于“关系”得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把怀特海视为一个“A-理论家”实际上并不失他的本意,虽然他生前从未参与A-理论和B-理论之争。(25)参见A.N. Whitehead, The Concept of Nature, p.48。
很有意思的是,怀特海的学生罗素走的却是另一个路向,他主张“时间关系”是“最原初的”(primitive)和“不可分析的”(unanalyzable),本体性的“时间关系”与物理性的“空间关系”之间具有“不可还原”的“性质差异”(qualitative difference)。在先和在后的“关系”是基于“客体与客体”的“关系”,因而不需要蕴涵任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的A-理论属性。(26)参见B. Russell,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Monist, Vol.25, No.2, 1915, p.227。与罗素一样,还有一些学者如早期的布劳德(27)参见C.D. Broad, “Time”, in J. Hastings, ed.,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pp.334-335。、奥克兰德(28)参见L.N. Oaklander, “The Russellian Theory of Time”, Philosophia, Vol.12, 1983, pp.263-292。、肖特(J.M. Shorter)(29)参见J.M. Schorter, “The Reality of Time”, Philosophia, Vol.14, No.1-2, 1984, pp.321-339。等人都持有类似观点。
既然如此,那么罗素对“生成”与“关系”的定位是如何描述的呢?在早期的论文中,罗素一方面反驳了麦克塔加等人有关时间的“非实在性”论证,另一方面又明确表达了“时间生成”构想的那种“过去与未来的感觉差异”并不是“内在的差异”,而是相对的主观的差异,因而属于“实际愿望的暴政”,是需要克服的。
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对过去的情感如此不同于对未来的情感,那么我们立即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差别的原因总体来说是实践上的:我们的愿望能够影响未来,但不能影响过去;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我们的力量,而过去则不可更改地固定下来了。但是,每一个未来都会在某一天成为过去:假如我们现在真实地回望过去,那么当它曾经还是未来时,它一定恰恰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而且,从目前所看到的未来一定恰恰就是当它已经成为过去时我们将会看到的那个样子。因此,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那种被感觉到的差异,并不是内在的差异,而只是相对于我们的:对于客观的研究而言,它就不复存在了。而且,知识领域中研究的客观性完全就是行为领域中作为正义与无私而出现的那种公正的品性。任何希望真实地看世界的人,若在要思考中免受实际愿望的暴政,就都必须学着去克服在对待过去与未来的态度上的差别,并以一种综合的眼光去勘查全部的时间之流。(30)[英]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及其他论文》,第23-24页。
不难看出,罗素认为没有所谓的“时间流逝”,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时间的本质属性,时间的本性只能基于“先后关系”。这个观点和立场,直到他后期的思想中依然如故,“很明显,时间涉及的是较早和较晚的关系;一般认为在我们经验过的事物里没有一种只有瞬间的存在”(31)[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3页。。罗素是最典型的B-理论家,他与布劳德不一样,布劳德一生多次改变自己对时间的看法,而罗素活了近百岁,其时间观却一以贯之。
追溯罗素时间观的渊源,远的要数莱布尼茨(32)参见[德]莱布尼茨、[英]克拉克《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第18-19页。,近的当属布拉德雷(33)F.H. Bradlery, Writings on Logic and Metaphysics, J.W. Allard and G. Stock, e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4-131。。对于莱布尼茨的“关系时间说”,罗素虽有批评却深表同情。(34)[英]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9页。而对于布拉德雷提出的源自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关系”理论,罗素则是极力反对的。(35)参见N. Griffin, “Did Russell’s Criticisms of Bradley’s Theory of Reations Miss Their Mark”, in G.Stock, Appearance versus Reality: New Essays on Bradley’s 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53-162。布拉德雷的主要观点表达在出版于1893年的著作《表象与实在》(36)参见F.H. Bradley, Appearance and Reality: A Metaphysical Essa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之中,但罗素认为,布拉德雷的有关“关系”的学说是一种“内在关系论”(the doctrine of internal relations),这种学说尤其无法解释“非对称性”(37)参见[英]罗素《数理逻辑导论》,晏成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3-51页。的“关系”问题。(38)参见B. Russell,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03, pp.218-226。因此,罗素自己提出一种“外在关系说”(the doctrine of external relations),在他看来,这正是确定“在先”与“在后”之“关系”的根源所在。(39)参见[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7-56页。而且,根据当时的论争情况来看,“关系”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俨然成了“新黑格尔主义者”(neo-Hegelians)和“新莱布尼茨主义者”(neo-Leibnizians)的根本分歧。(40)T. D. Laguna, “The Externality of Relation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20, No.6, 1911, pp.610-621; H.T. Costello, “External Relations and the ‘Argument from Missouri’”,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8, No.19, 1911, pp.505-510; G.A. Tawney, “Transcendentalism and the Externality of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11,No.16, 1914, pp.431-436; E.H. Hollands, “The Externality of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11, No.17, 1914, pp.463-470.“外在关系说”虽然起先是从数学与逻辑的角度来谈的,但正是在这种“外在关系说”的基础上,罗素的时间观才得以有其本源的确立性。(41)参见F. Wilson, “Burgerskijck, Bradley, Russell, Bergmann: Four Philosophers on the Ontology of Relations”, Modern Schoolman, Vol.74, No.4, 1995, pp.283-310。许多年以后,追随着罗素,奥克兰德对“时间生成”与“时间关系”进行了一个完全对立的区分。(42)L.N. Oaklander, Temporal Relations and Temporal Becoming: A Defense of a Russellian Theory of Tim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对此,他曾言道:
对罗素而言,关系不能被还原为它们项的一元属性。尤其是,时间关系乃是指它们的项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a先于b,即使a和b都无法示例任何A-属性。接续这个简短的关系问题讨论,我认为,A-时间和B-时间之间的根本不同在于,A-理论没有而B-理论有原初的时间关系(primitive temporal relations),这种关系依据时态谓词不可定义(indefinable),依据时态属性不可还原(irreducible)。(43)L.N. Oaklander, The Ontology of Time, p.42.
如此看来,“生成”与“关系”的差异有其渊源的不同,也有其纠缠之处。我们借由对“时间本体”或“时间本性”的追问而走向了“本体论差异”的一些说明,在这些说明中,有立场的呈现,有缘由的探究,有争议的澄清。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揭示时间理论之争的原初诉求,在随后的具体论述中,此议题将会越来越明朗。
三、“本体论差异”的两个区分标准
若时间的“本体论差异”能够得以确定,那么依据A-理论家与B-理论家的争论,我们至少得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设想:
第一,“时间生成”与“时间关系”的分别应该如何安置。因为这个议题到如今已不是莱布尼茨时代的那种“实体论”还是“关系论”的形而上学争端,而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重新架构问题,它决定着时间系统的独立性地位。
第二,“永恒存有”与“流逝现在”的分歧应该如何界定。“瞬时”的存有与否自古以来就是时间哲学中的争议论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现在”有无“尺度”(44)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27页。的问题,在麦克塔加那里则是怎样理解“似是现在”(specious present)(45)参见J.M.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pp.472-473。的问题。
第三,“时态属性”与“非时态属性”的分叉应该如何取舍。显而易见,任何对时间的界定都会使用“时间术语”。在西方语言系统中,“时间术语”定会牵涉“时态”与“非时态”的属性,因而对于时间论题语句的时态和语义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此一来,与细节并行的可能不是所作“区分”的“确定性”,而是它们的“不确定性”。简而言之,分别、分歧、分叉的“界限”似乎很难明朗。比如,我们也可以说,“生成”是一种“关系”,“流逝现在”是“永恒的”,“时态”与“非时态”能相互转换。因此,如果要将“本体论差异”的区分标准予以更定性的解析,我们不妨用两条直接的准则:
(1)A-理论的标准是“感受时间”或“体验时间”的存有;
(2)B-理论的标准是“客观实有”的“物理时间”的确立;
若依罗素早期的设想,“A-标准”可称之为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关系”(time-relations),“B-标准”可称之为客体与客体的“时间-关系”,前者是主观的“心理时间”,后者是客观的“物理时间”。(46)参见B. Russell,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p.212。这种设想的优点是简明清楚,缺点是过于简单。不过,笔者在此想先取其优点,来看看是否能够探寻区分标准的作用。
我们首先从“A-标准”出发来思考一下,依照这个标准的理据,B-理论难以解释“感受时间”或“体验时间”的存有。尽管有些B-理论家压根就不承认任何“感受时间”或“体验时间”的“实在性”,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需要多此一举进行“解释”。然而,我们讨论问题的态度不应该是直接“取消问题”或“回避问题”,而是得就事论事。那么,“A-标准”真就毋庸置疑了么?显然不是。
麦克塔加得出的结论是,A系列是自相矛盾的,但人们为何会相信“A-特性”(过去、现在、将来)能够应用于现实呢?并且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还“日日相见”呢?很多人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受到了“体验的心理特征”(47)参见P. Turetzky,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24。的作用。例如,我们会受到感知、想象、回忆、期待、恐惧等不同性质的心理行为影响。由此而来,可能恰如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所表述的那样,我们相信“直接感知”有一个特性即“现在”(presentness),“回忆”有一个特性即“过去”(pastness),“期待”有一个特性即“将来”(futurity)。于是,“时间”就成了一种内在心灵的延展。(48)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3-256页。不过,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基于“体验的心理特征”而来的“体验时间”的“感受”并不具有确定性,只能造成对“时间本质”的“误导”。
的确,依麦克塔加所言,把“直接感知”、“回忆”、“期待”之类的心理行为特征置于“事件”之中,那么“现在”的一切事物都会与“直接感知”相应,“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事物则分别与“回忆”和“期待”相应。然而,正因如此,有学者依麦克塔加之意指出,这里已然犯了好几层的错误:
首先,犯了把“客观”置换为“主观”的错误。也可以说,是把“体验”的“主观性特质”误置成“事件”的“客观性特质”。于是,我们相信“事件”可以被区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但“事件”本身是确定的。“就时间而言,存在着这样的矛盾——A系列的诸特性互不兼容,但每个项都是如此。除非这种矛盾得以解除,否则时间观念必定会因其无效而遭拒绝。”(49)J.M.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p.470.
其次,犯了把“质性差异”置换“相位差异”的错误。所谓“质性差异”就是指“直接感知”、“回忆”、“期待”之类不同的心理行为的本性差异,这里的不同不是“量”或“关系”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相位差异”指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时间中的不同相位,实际上是相对而言的。麦克塔加说:
在任何瞬间我都有某些感知,也有对其他知觉的回忆,再有就是对他者的期待。直接感知自身是一种与回忆和期待这些感知有质性差异的心理状态。基于此,我们相信,当我具有感知时,这种感知自身就有一种特性,而当我具有这种感知的回忆或期待时,其他的特性就会取代原来的特性——这些特性被称之为现在(presentness)、过去(pastness)和将来(futurity)。当有了这些特性的观念后,我们将之应用于其他事件。所有那些与我当下具有的直接感知同时发生的一切,都被称之为现在,并且甚至于在根本没有人具有直接感知的情形下,也将会视为现在。与之相同,那些与我们回忆感知和期待感知同时发生的行为,就被认为是过去或将来,而且这些会再次延伸到没有任何我当下的回忆和期待之类的感知是与之同时发生的诸个事件中。但是,在整个区分中,我们的信念源自于[直接]感知与期待感知或回忆感知之间的区别。(50)J.M.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p.471.
明了这些含义之后,如果我们把“主观体验”中心理行为的“质性差异”(直接感知、回忆、期待)误认为就是时间构成中的“相位差异”(过去、现在、将来),那么自然就会造成混淆与矛盾。
最后,犯了把“似是现在”作为被感知的“事件”本身的“现在”的错误。“似是现在”这个术语最早可能是在心理学领域由学者克莱(E.R. Clay)使用,后被威廉·詹姆士(W.James)引证才有更多讨论。(51)参见W. James, “The Perception of Time”,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Vol.20. No.4, 1886, pp.377-378; also see W.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2013, p.609。它表达了“现在”的不确定性,只因“现在”总在变成“过去”,因而“现在”只能是“似是而非”的“现在”。现在我们假设,“时间经验”总能把握一个即刻的“时间间隔”(temporal interval),即能够把握一种“似是现在”。那么“感知”就会在“似是现在”之中的“时间间隔”里发生改变。结果很显然,在“似是现在”中,“现在”就不可能是同一个。“‘似是现在’会随情况而改变长度,并且对在相同时段的两个人而言,这一‘似是现在’可能会不同。”(52)J.M.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p.472.如此我们所体验之“事件”的“现在”状况就可能是“过去”,“过去”状况就可能是“现在”。于是,“事件”的“感知”将兼有“现在”和“过去”。这当然是有问题的。(53)参见P. Turetzky, Time, p.125。
在我看来,麦克塔加对“A-标准”的质疑有他自身的目的,但这并不表示,“A-标准”就无法作为“本体论差异”的区分准则。我们已提到过,A-理论家施莱辛格给B-理论家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设法解释我们内心中最深的情感。奥克兰德明确说,这是B-理论家必须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54)参见L.N. Oaklander, The Ontology of Time, pp.33-34。在笔者看来,“A-标准”是存在的,而且“A-标准”也是可靠的。因为,B-理论确实无法解释“体验的连续性”、“人格的同一性”、“意识的统一性”、“意志的自由性”等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假定有两种时间:一种是“普通时间”(ordinary time),另一种是“元-时间”(meta-time)。这个“元-时间”能够给出“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之间的合理关系。因此,在此意义上,它也能统摄“A-标准”和“B-标准”。
现在,我们不妨依“B-标准”为思考点,来考虑一下“本体论差异”问题。按照“B-标准”,A-理论所确立的时间描述“太主观了”,没有成立的可能。罗素甚至说:“认为时、空是存在于我的心中的那种思想上的闷气使我十分憎恶。”(55)[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第54页。也正因如此,他很早就确立自己B-理论家的立场,基本认同以“客观实有”的“物理时间”为标准来建构“时间关系”理论。那么,这个“B-标准”在麦克塔加的描述中居于何种地位呢?它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已然知晓,罗素最先反对麦克塔加的时间论证。不过,笔者认为,罗素早期的反驳见解比较弱,不太具有说服力。(56)参见陈群志《麦克塔加与分析哲学学派的时间理论之争》,《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并且,他的有些看法并不完全恰切,似乎还有不够深入之处。在此,不妨以麦克塔加的两个附属性观点作为例证。
首先,在《时间的非实在性》(1908)这篇论文中,麦克塔加已明确指出,B系列作为一种永久的关系,一个固定的静态关系,没有变化,因此它无法代表时间的本性。因此,他认为B系列不能脱离A系列而存有,但B-系列能够从A-系列衍生出来。“只有当给予变化和矢向的A系列与给予永久性(permanence)的C系列(C-series)相结合,B系列才得以出现。”(57)J.M.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p.464.。但是,C-系列只有“秩序”而没有“时间”,因而可以说是一种“非时间系列”。“如果我们宣称事件M和N 是同时发生的,这就等于我们宣称两者在时间系列中占据了同一位置。那么,其中就包含着一些事实,因为我们将现实感知为事件M和N,而两者的确在一个系列中实在地占据着同一位置,不过这一系列不是时间系列。”(58)P. Turetzky, Time, pp.125-126.可能正因C系列的解释方案并不典型,而且或许也没有这个必要,后来在收入《存在的本性》(1927)中时,这一论文中有关描述C系列的部分就没有再使用了。(59)参见J.M.E. McTaggart,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Vol. II, pp.9-31。
其次,麦克塔加后来还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A-特性”(A-characteristics)是一种“关系”(relations)而非“性质”(qualities)。(60)参见J.M.E. McTaggart,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Vol. II, p.19。这个观点在1908年的论文中并未提及,想必他对A系列有新的想法。因为在此之前,麦克塔加没有认为A系列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些“特性”是一种“关系”,现在却指出“A-特性”所具有的“关系”要胜于“性质”。这当然是一个新的转变。不过,他又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一般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找出这样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61)参见P. Turetzky, Time, p.125。若依麦克卢尔(R. McLure)的研究,这个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62)参见R. McLure, The Philosophy of Time: Time before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p.157-163。
回过头看,麦克塔加对“B-标准”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他没有否决B系列的存有,而是认为B系列的存有当以A系列为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实际上,时间的“客观性”自然无可置疑,这在A-理论家也并不否认,关键在于B-理论家如何确立它的标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罗素也好,奥克兰德也罢,这些典型的B-理论家之所以能够坚信“B-标准”,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作为支撑点,那就是爱因斯坦的新物理学时间观。笔者归结爱因斯坦的基本观点为三条(63)参见陈群志《从爱因斯坦到海德格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9日。:
(1)相对论引起了空间和时间理论的根本变革,空间和时间只能结合为“空间-时间”这样的四维连续区才能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他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Britannica)(1929)所写的“空间-时间”条目的最后指出:“如果不用坐标系(惯性系)来做参照基准,要断言空间中的不同点上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那就毫无意义。由此得出的结果是,空间和时间融合成为一个均匀的四维连续区。”(64)[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8页。
(2)空间和时间理论受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初步修改,这种修改依据惯性原理认为“空间-时间连续区”在物理上具有客观性质。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如果从牛顿的立场来看,“时间是绝对性的”(tempus est absolutum)和“空间的绝对的”(spatium est absolutum)这两个表述能够协调一致。然而,狭义相对论则应当说,“空间和时间的连续区是绝对的”(continuum spatii et temporis est absolutum)。(65)参见[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42-243页。不过,必须明白,就其能够用静止的时钟和物体进行度量而言,“空间-时间连续区”虽然仍然能够保持着“绝对性”,但是,就其取决于所选择的惯性系的运动状态而言,它又必然具有“相对性”,缘于运动能够对物体形状和时钟运行产生影响。
(3)空间和时间理论又在广义相对论中得到了进一步修改,在这个修改中,爱因斯坦引进了相对于惯性系加速的坐标系,从而在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引力场”理论。依据“引力场”理论,它否认了“空间-时间连续区”具有欧几里得的几何特征。由此而来,只有通过把“空间-时间”坐标同描述“引力场”的数学量结合起来才能给出“度规”(metrics)的实在性。(66)参见[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42-247、250、274-375页。
如果我们去看罗素在《物的分析》一书中对时间(也包括空间-时间)的理解,可以发现到处都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子。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罗素的“时间关系”理论在此获得了进一步的物理-数学界定。“在广义相对论中,时-空以两种方式出现:首先,作为一种提供四维顺序的东西;其次,作为一种产生关于‘间隔’的度量的概念的东西。两种方式都是‘点’之间的关系,但在数学上都被看作微分关系。”(67)[英]罗素:《物的分析》,贾可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6页。与之相应,依据“B-标准”,爱因斯坦与罗素在这个断言上没有太大差异。如爱因斯坦所言:
在我们看来,个人的经验是排列成一系列的事件的;在这个系列里,我们所记得的单个事件显然是按照“早”“迟”的判据排列着的,而对这个判据却不能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对于个人,存在着一种我的时间,即主观时间。这种时间的本身是不可度量的。(68)[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39页。
我们清楚,每个人都有共同的感官经验,因而也就能够借由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各自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在爱因斯坦看来会自行排成一个系列,并且在此系列中有“在先”和“在后”的次序。于是,时间的这个部分就如此形成而不能进行再分析,因为两段不同的时间的确无法同时存有。而那种对“我”而言的“主观时间”自然也可以谈,只不过爱因斯坦认为这就是有“在先”和“在后”次序的“经验”。换言之,爱因斯坦虽然不像麦克塔加和B-理论家那样,把“在先”和“在后”这些时间术语给予“客观时间”,而是认为“主观时间”是这样形成的,但他的实质意涵还是“客观的”。就此而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还指出这种“主观时间”是“不可度量的”,却属于“时间的本身”。倘若如此,爱因斯坦又如何界定“时间”呢?
物理学的时间概念同科学思想以外的时间概念是一致的。因为后者来源于个人经验的时间次序,而这种次序我们必须作为事先规定了的东西来接受。人们经验到“现在”这一瞬间,或者更准确地说,经验到目前的感觉经验同(以前的)感觉经验的回忆的结合。那就是感觉经验所以像是形成一个系列,即那个由“早”、“迟”来表示的时间系列。这种经验系列被认为是一个一维连续区。经验系列能够重复,因此能被认识。它们也能作不完全精确的重复,这时,某些事件可以被另一些事件所代替,但对我们来说,经验系列仍不失其可重复的特征。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了作为一维构架的时间概念,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用经验来填满。同一个经验系列适合于同一主观时间间隔。
从这个“主观”时间过渡到科学以前思维的时间概念,同下面这样一个观念的形成相关,这观念就是认为存在一个同主体无关的实在的外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客观的)事件就同主观经验对应起来。在同一意义上,把经验的“主观”时间归属于一个与之对应的“客观”事件的时间。所不同于经验的是,外界事件和它们在时间上的次序必须对一切主体都是成立的。(69)[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76-377页。
爱因斯坦在撰写“空间-时间”词条时,他是先界定“空间”,然后再界定“时间”的,上述所引就是他界定“时间”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他对“空间”的界定非常详细,如果仔细阅读这个词条,可能会有的感觉就是,似乎讲完“空间”以后不需要再专门讲“时间”了。因此,实际上,爱因斯坦界定“时间”所写内容非常短,而且大部分在叙述相对论以前的时间概念,也就是上引文中的解释。依照如此解释推论,如果“个人经验的时间次序”对所有人都有效,都是同一的,那么“时间”的“客观性”就能够获得成立。不过,爱因斯坦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忽略“空间”的突出作用,要不然无法理解“同时性”这个概念。职是之故,爱因斯坦进行了根本的变革,就像前述基本观点中已揭示的那样,“时间”必须与“空间”融合形成一个“四维连续区”才能获得其绝对意义。
论述至此,我们不难发现,爱因斯坦所讲的“主观时间”实际上就是一种“客观时间”,因为他标识其为“一维连续区”(70)[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76页。,有着明显的先后关系。如果说“空间-时间”的结构是决定物理学的根本,那么我们必须说,这种基于物理学思维的以“空间”为原初地位的“空间-时间”论是悬在B-理论家头上的“幽灵”。由此,才能够完成“本体论差异”的“B-标准”和“A-标准”之间的区分。
四、简要总结与新的疑难问题
如何分析与描述时间,原则上需要一种模型。因此,借由对“麦克塔加问题”的辩驳,A-理论与B-理论的时间分析模型也就得以在英美哲学世界逐步形成,并延续至今。(71)参见陈群志《麦克塔加与分析哲学学派的时间理论之争》,《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然而,我们还需要追问:除了试图解决麦克塔加提出的“时间悖论”以外,是什么样的基本问题使得他们争论不休呢?笔者比较倾向于A-理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绝对排除B-理论的设想,尤其牵涉自然科学时间观的设想。不过,B-理论存在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B-理论家(非时态论者)需要设法解释或解决“变化”的问题。因为在此问题上,A-理论家已特别指出,B-理论(非时态论)无法说明“变化”,因为如果只是依据“时间部分”(temporal parts)或“事件”(events)来表述一个“事物”的“变化”,那么实际上并无“事物”的“变化”。
第二,B-理论家必须设法解释或解决何谓“时间的现象学”问题,亦即什么是在“思想”或“体验”中被给予我们的时间方式。(72)参见L.N. Oaklander and Q. Smith (eds.), The New Theory of Tim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79-375。“对过去的情感”和“对将来的情感”为何会出现不等价?(73)参见[英]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及其他论文》,第22-24页。更重要的是,依B-理论家,一切“事件”都同等实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实在性”是均衡的。但有些A-理论家认为,对“将来”的“体验”只是“可能性”,亦即“将来”是一种“可能性的开放区域”而已。因此,如果“将来”是真实存在的,那么B-理论家必须说明我们的“体验”在创造“尚未存在”的“将来”中发挥着何种作用。(74)参见L.N. Oaklander, The Ontology of Time,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4, pp.31-34。
第三,A-理论家施莱辛格提到了一个困境:非时态论者(B-理论家)必须设法解释或解决非时态的观点能否与我们对时间最深切的感受(deepest feelings)相一致。(75)参见G. Schlesinger, “The Stillness of Time and Philosophical Equanimity”, Philosopical Studies, Vol. 30, 1976, pp. 145-159。比如,一个“基本情绪事件”,像“我现在有一种对将来的焦虑”或“我现在有一种对过去家乡生活的怀念”之类,这些“事件”都是B-理论家比较难处理的。简言之,如何认知“感受时间”是很关键的。
第四,还有一个遍及所有的重要议题:非时态论者(B-理论家)需要设法解释或说明“B-时间”为何不存在时态属性,这不仅是一个时间形而上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语言哲学的问题。因为A-理论家认为,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时间指示词”(temporal indexicals)的“语义”就蕴涵着时态属性(A-特性)。
上述四个难题可以简括为:变化问题、将来问题、感受问题、语言问题。笔者认为,与此相关,“将来问题”要在化解“变化问题”或“感受问题”中讨论,而“感受问题”实际上是对“经验/体验”的不同理解,而这方面A-理论的确更具说服力。总之,从时间分析的“本体论差异”中生发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细致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