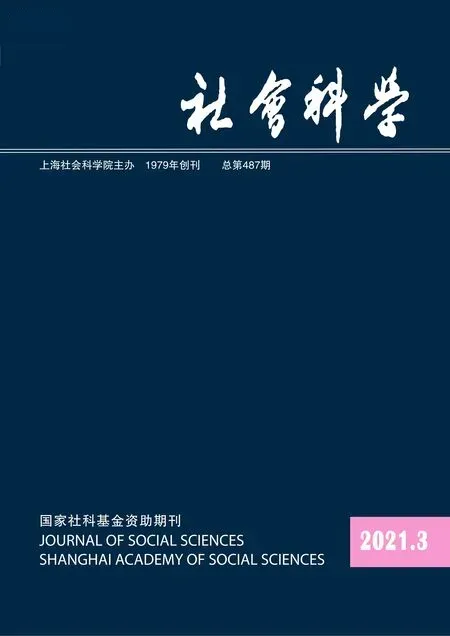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空间想象
陈舒劼
小宇宙中只剩下漂流瓶和生态球。……在一千米见方的宇宙中……几只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环境中静静地漂浮着,有一条小鱼从一只水球中蹦出,跃入另一只水球,轻盈地穿游于绿藻之间。(1)刘慈欣:《三体Ⅲ》,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513页。
看着那蓝色的星球,我像是看着母亲的瞳仁,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我哽咽着说:
“是的,孩子,那是地球。”(2)刘慈欣:《超新星纪元》,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这时,在人类无法去到的天空中,聚满了亿万双叹为观止的眼睛。(3)韩松:《高铁》,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空间想象的特质,可从上述三段引文中略见一斑。这三段引文分别来自三部小说的结尾:刘慈欣的《三体Ⅲ》和《超新星纪元》,以及韩松的《高铁》。《三体Ⅲ》——同时也是整个“三体”系列——终结于这段人造小宇宙的全知视角描述之中,而《超新星纪元》和《高铁》则贡献了一组视线相反的空间关系:从地外的宇宙空间回观地球母星,以及在似乎驰骋于大地上的高铁中发现宇宙中未知的他者。宇宙可以是造物的艺术,也可以在视角的差异中显示不同的面貌,这是类型赋予科幻小说的权力。当然,这些都只是三十余年来,科幻小说空间想象复杂性的冰山一角。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人类空间技术不断发展,构成了三十余年来科幻小说空间想象繁荣的现实基础,探知星海不必再寄情于遐思。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空间转向”思潮逐步成形并向哲学、文学、历史学、建筑学、城市和区域研究等人文学科蔓延,带动了作为文化思潮的空间意识的兴起,至今依然汹涌澎湃。空间是一种方案、一种关系,“实质上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充满政治性和矛盾性,“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4)[法]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6页。在科学技术推进和文化意识形态变化的大语境下,空间既拥有了独立的文化形象,又成为诸多意识形态交锋的载体和镜像,是科幻小说值得深耕的沃土。“当代空间理论侧重研究的是,文学艺术在文化表征实践过程中如何运用表现、再现、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揭橥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文化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5)谢纳:《空间转向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三体”系列小说结尾处的这颗简单的人造“小宇宙”,就携带着丰富的意义内涵和历史信息。显然,近三十年来科幻小说的空间想象中必然存有许多问题待发现,如同隐于夜空里的星。
一
科幻小说肯定不是首先关注空间的文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人类的空间意识与时间意识同样拥有远久的历史。“人类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我们生来就占有空间。”(6)[美]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文学的空间意识在源远流长的地方美学传统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地理环境对地方文化和生活于其中的文人的影响,最终通过作品独特的美学面貌反映出来,《诗经》十五国风的分类就是个清晰的例证。这种观念在历史中得到了许多附和,刘勰所提出的“江山之助”已经成为中国古典史学的重要命题。(7)陈未鹏:《宋词与地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地理空间是特定的气候、种族、宗教、语言、民俗的载体,多种因素的合力以地理环境之名左右文学创作,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和泰纳对此观点没有多大不同。斯达尔夫人的一个论断是:“德、法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都证明了这一分歧;莱茵河的永久疆界分开了两个文化地区,它们和两个国家一样,是互不相干的。”(8)[法]史达尔:《论德国》,载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19页。简而言之,“塞北秋风烈马”、“江南春雨杏花”几乎可被视为理解某种美学风格形成的思维定式,许多作家因此被与某个具体的地理空间对应起来。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贾平凹的商州、李锐的吕梁山脉、苏童的香椿树街,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乔伊斯的都柏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等等,莫不如此,尽管这些地理空间本身早已完成了程度不等美学的转化。
近三十年来科幻小说的空间想象需要面对这份传统文学的遗产。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地方叙事的美学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科幻叙事中是否依然得到延续?至少从 “冷湖奖”存在的事实来看,科幻文学并不排斥这种逻辑关联。作为中国第一个以地理命名的科幻文学奖,“冷湖奖”在其“第四届征文公告”明确将地理标志作为内容元素提出:“凡作品中包含以下地名元素中的任意一个均可投稿:冷湖、火星营地、俄博梁雅丹、石油小镇废墟、赛什腾观测站、火星一号公路。”(9)https://mp.weixin.qq.com/s/c75RjXz4HBI-KcrPkuq96Q,2020-10-18.这些地名隐约勾勒出某种独特的地方风景,曾获此奖的小说《冷湖之夜》的描绘是:连绵起伏的山脉、亘古不变的沙海,“隐隐能看到巨型雅丹群的轮廓,风从天然形成的土堡间呼啸穿过”,“唯一缺少的便是人烟”(10)王诺诺:《冷湖之夜》,载杨枫、迈克·雷斯尼克编《冰冻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9、93页。。然而小说似乎无意从这地理风貌中精雕细琢出某种属于冷湖的苍凉粗犷之美,叙述迅速地拐上科学幻想的主车道,驶入一个过滤掉了地方风情的时空循环之中。相比于冷湖地区,长铗的“奉家山”同样偏远。处于两省交界的奉家山用卫星接收器作装猪食的锅,区隔现代文明的态度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这个小山村的特点是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山村景象,白天风景怡然而夜晚诡异狰狞。白日里奉家山的景象“无疑是值得嵌入相框的,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夕阳余晖的斜射下,发出琥珀般的光芒,梯田外是一块葱绿平底,点缀着白墙黑瓦的村舍”(11)长铗:《麦田里的中国王子:长铗科幻小说选本》,成追忆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入夜之后的奉家山祠堂鬼气萧森,门洞若骷髅之鼻孔,古柏似垂手的僵尸。怡人和瘆人不和谐的并存需要科学的解释,几笔风景点缀犹如细长的叙事导火索,还是为了点燃小说“普朗克常量异动”的构想。从地方风景的生成逻辑看,长铗笔下的“昆仑”与“奉家山”不过是同体的两面。小说中的昆仑是什么?大地的中心,神话的源头。昆仑本无定所,当漫长跋涉后众人突然于远方的天地合一处发现独特的空间存在时,昆仑即由特异的景象得到指认。“一道金色的光芒,从那昂藏于天地的擎天一柱涌出,蔓延、席卷,直至吞没整个世界”,“它通体金光闪闪,掩映在诡谲奇伟的云海之中,若隐若现,遥不可及”,整体结构如“层峦叠嶂,珠玑楼饰,拔地而起”(12)长铗:《麦田里的中国王子:长铗科幻小说选本》,成追忆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185页。。似近实远、神圣而又似可描述的矛盾感,造就了昆仑的神秘之美,可这难以复现的空间景观,最终又被科学解释的重力拉回了现实地面,昆仑就是外星智慧的空间交通工具。
问题出现了。科幻小说在承继传统文学的地方美学建构逻辑时,似乎总是无意于这种地方美学的深耕。粗线条地勾勒出某种地理空间环境的特色,贴上几个形容词作为标签就草草收工。冷湖是孤寂的大漠,奉家山是封闭的山村,地域风情是科技想象的花边。作为科幻核心要素的科学性,往往要求科幻想象具备现实性和可理解性,多少挤压了地域美感的经营。这种矛盾不难理解:如果人类基因突变,湘西和伦敦一样危险;如果心怀恶意的外星人降临,冷湖或巴黎没有区别。地域空间的美学营造就这样悄悄地让出了科幻小说的舞台中央,但与此同时,新的战场也在不断开辟。
二
试图替代地理美学描绘的,是科幻想象对空间形态多样性的探索。读者会发现,近三十年来科幻小说对空间本身的兴趣明显上升。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上天入地,已经不能满足近三十年来科幻小说的好奇。
地球的舞台如此逼仄,容不下异星入侵、怪兽出没、星舰启航、陨石撞击、恒星撕裂、光速跃迁、黑洞漂移之类的大场面,科幻想象本能地要求撑大空间。在《基地》《银河英雄传说》《银翼杀手》这样的科幻经典里,光年在感觉上不比手臂长多少。《银翼杀手》中仿生人自述他见证过人类难以置信的场景,星际战舰在猎户座的侧翼熊熊燃烧,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空间足够宏大才能容纳如此壮观的景象。刘慈欣在“三体”三部曲中的系列描绘,如水滴摧毁人类两千余艘恒星级战舰的末日之战、整个太阳系的二维化、“黑暗森林”设想和“宇宙安全声明”等,也都远超过了地球空间的尺度。跨出地球或太阳系的空间想象,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俯拾皆是。科幻空间想象的超大尺度,是否产生与传统空间叙事的差异?宇宙空间内的星际交往,是否就是现今地球村逻辑的简单放大——恰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那样?并非如此。叙事空间的扩大使科幻小说具备独特的美学表现方式,刘慈欣用极具内在张力的“宏细节”概念强调了空间扩大的意义。他认为:“在科幻文学将触角伸向宇宙深处,同时开始了对宇宙本原的思考时”,大量出现了以宇宙尺度为标准的“宏细节”,“宏细节”不仅是“科幻小说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最能体现科幻文学特点和优势的一种表现手法”,还“对科幻小说的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创作者们得以“先按自己创造的规律建成一个世界,再去进一步充实细化它”。(13)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载《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111页。空间扩大涉及到诸多社会关系和自然规律的重新理解及建构,其复杂性远超过单纯的物理扩张,这是类似于客观世界的新“创世”。因此,至少刘慈欣部分小说中的空间微缩,也可以理解为“宏细节”逻辑的产物。刘慈欣的空间缩微不是将叙述视角扩大,而是改变了作为叙述对象的空间的形态。《微纪元》中人类缩小至10微米左右,“三体”三部曲结尾处陆天明送给程心的“647 号宇宙”,都涉及到了小空间内社会关系变化甚至重造的多种可能。
空间变形的现实场景与空间的放大缩小相比,离传统的文学想象更远。莫比乌斯环——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的一种空间形态,成为顾适的《莫比乌斯时空》和长铗的《六四七号公路》的情节骨架。《莫比乌斯时空》用英文的“结束”作为开头、“开始”作为结尾——这显然是形式与内容相契合的安排,在短篇幅内以莫比乌斯环式时空为中线,用克莱因瓶式感觉结构、人机结合体、虚拟共生技术等编织出一个在轮回时空中努力自我拯救的故事。《六四七号公路》的空间叙事则更富有现实烟火味,莫比乌斯环式的空间结构服务于以飙车的方式抓捕逃犯的情节安排,空间反转导致人体左右侧功能对换的科幻设定也无足轻重。
从空间变形的烈度来看,《莫比乌斯时空》和《六四七号公路》的莫比乌斯式空间是静态的设定,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和七月的《biu一声就这样消失》 则展示了空间剧烈变形的过程——“折叠”。《biu一声就这样消失》专心致志地描画了南京折叠形变并消失的过程:“偌大的南京城就像是被烈日烤化后随意揉起来的一个糖球。南京长江大桥挂在西北的天际,直通云霄,混浊的长江如一火车站边旅馆久未清洗的窗帘,遮挡了西北的天空,窗帘上还能见蠕动的小虫,惊恐疯狂地鸣着汽笛。东面,馒头形紫金山高高卷起,像被巨人扭成一颗螺丝钉,盘旋弯转拧成一个倒U形,顶端钻头一样刺进了秦淮河,夫子庙被漂浮在天空的东南面,像一面旗一样摇摆不定,而夫子庙一边的中华门瓮城却出现在西边,上下颠倒,惊慌的行人头朝下的站在倒悬的路面。南京城所有的一切扭曲在一起,如无数海市蜃楼层层相叠。”(14)七月:《biu一声就这样消失》,载成追忆编选《像堕天使一样飞翔:七月科幻小说选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南京市最后化为谜团:一小块荒地,歪斜地插着写着“国家级景点——南京”字样的木牌。或许是过于陶醉在南京折叠变形的细节想象之中,小说的叙事基本没有迈出空间变形的物理属性范畴,放弃了空间折叠的社会属性。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倒是在空间变形的物理范畴之外挥毫泼墨,从城市折叠场景描绘的对比就能看出。南京折叠是物理空间的整体变形,长江、紫金山、秦淮河概莫能免,而北京折叠明确地体现为“六环内”城市建筑的翻转重组。“晨光熹微中,一座城市折叠自身,向地面收拢。高楼像最卑微的仆人,弯下腰,让自己低声下气切断身体,头碰着脚,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再次断裂弯腰,将头顶手臂扭曲弯折,插入空隙。高楼弯折之后重新组合,蜷缩成致密的巨大魔方,密密匝匝地聚合到一起,陷入沉睡。然后地面翻转,小块小块土地围绕其轴,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另一面,将另一面的建筑楼宇露出地表。楼宇由折叠中站立起身,在灰蓝色的天空中像苏醒的兽类。城市孤岛在橘黄色晨光中落位,展开,站定,腾起弥漫的灰色苍云。”(15)郝景芳:《北京折叠》,载《孤独深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第9页。北京折叠是彻底的、可控的人工操纵,既是现实的组成又是现实的镜像。不同阶级的利益分配和诉求冲突决定了空间折叠的方式,老刀和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卑微而顽强的努力,不过是为了抗拒阶层固化进程中代际遗传性不断增强的趋势。让养女上有文艺培训的幼儿园、与上层空间的女孩恋爱、试图摆脱包养式的婚姻、坚决捍卫自身阶层空间的纯洁性,这些期望相互联接又相互排斥,驱动着北京折叠永不终止的运转。《北京折叠》是空间观念矛盾性的生动注脚:空间应该“被理解为不仅是政治、冲突和斗争的场所,也是被争夺的事物”(16)[美]菲利普·E.魏格纳:《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地点和文本性批评》,载[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可想而知,空间的冲突和斗争也引起了诸多科幻空间叙事的兴趣。
三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时曾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铺开,就是资本逻辑试图逐步征服直至泯灭地方意识的过程,传统地域小说所标榜的地方特性,成为抵抗资本逻辑的战斗堡垒。资本空间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在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传遍四方之时,进一步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并使之激化。《共产党宣言》对此的生动概括是: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二十世纪中后期“空间转向”所产生的当代空间理论,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地理学在新历史条件中相遇的产物,“空间”物理属性之外的文化政治属性得到高度的重视,其本体性和异质性也得到凸显,空间变动不居,“由此,人类自身即其它事物的形成以及对各种存在事物的思考、解释或批判都成为了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交织与对抗的场所,而不具有了唯一性。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在发掘这种异质性空间的过程中寻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9)刘进:《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科幻的空间想象,就是各种关系相互纠缠、各类冲突此起彼伏的最好沙盘。
科幻空间想象的冲突性,最浅层的表现就是空间被理解为占有的对象。面世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郑文光《战神的后裔》,讲述了一群志向远大的青年改造火星的努力,无论是火星沙尘暴、宇宙射线辐射、黑洞吞噬,还是建设中的挫折乃至人员的伤亡都没能动摇他们征服火星的决心,这群在“战神之星”上奋战不息的人因而被称为“战神的后裔”。小说注意到,仍有一些个人的忧伤情绪混杂在昂扬的集体意志中,但这些负面情感如同火星的恶劣环境一样仅是征服对象,火星的空间并没有展示出它的复杂性。这种情况在刘慈欣2002年发表的《吞食者》和宝树2012年发表的《安琪的行星》里,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两部小说在内容上差别很大,但拥有一个共同点:注意到被征服的空间的复杂性。《吞食者》里的吞食帝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挫败人类文明的抵抗,庞大的环形飞船实现了对地球整体空间的吞食。可人类失败却决绝的抵抗在长时间后显现了效力,吞食者文明元气大伤,以吞食空间为途径的进化前景阴影重重。空间的征服和抵抗彼此生产,这其中有少许世事循环的感叹,更有进化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无情。宝树的《安琪的行星》在将行星“ΣX-6470-2”作为爱情礼物的甜蜜故事背面,隐藏着巨大的反讽。在地球文明的空间内部,“安琪的行星”是爱情争夺战的工具,但作为“ΣX-6470-2”而言又是有异星生命形态的空间载体。这颗行星到底是被地球人所命名,地球主人可以无视这异星生命的存在,以爱的名义将其彻底清除。“无论在这个星球的任何角落,我都找不到可以喜欢它的地方。诚然,主宰这个行星的准智慧生物表面上和人类有几分相似,但空有人类的狡诈和愚蠢,却全无人类的灵气。”(20)宝树:《安琪的行星》,载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安琪的行星》,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39页。主人傲慢的口吻令人联想到西方殖民者对第三世界的空间优越感,联想到西方世界种种以“自由”“民主”为幌子的意识形态输出和征服。“ΣX-6470-2”星上的生命无法发出申述甚至是悲叹,空间冲突中的许多关系维度,也可能就像这般无声而待发掘。
“想象是各种可能的空间世界的肥沃资源,那些世界能够预示……形形色色的话语、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物质实践。”(21)[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科幻想象擅长以科幻作为工具搅动现实空间的既有格局,许多问题早已超出了“进化——落后”“征服——屈服”“保护——破坏”“科学——进步”之类的思维模式的处理能力。陈楸帆的《荒潮》就是呈现出开放性问题意识的小说,小说中“硅屿”这座全球化浪潮中的电子垃圾之岛,同时也是诸多冲突的旋涡中心。代表国际资本方利益的斯科特很快发现“有两个硅屿”——新富阶层和垃圾人的硅屿,而双方似乎均对所生存的硅屿漠不关心甚至是厌恶。“本地人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多赚一天算一天;外地人也不关心,他们只关心早一天赚够钱,回老家开个杂货店做点小买卖,或者盖个房子娶个媳妇。他们讨厌这座岛,没人关心岛的未来会怎样”(22)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第18-19页。。冷漠与厌恶预示着硅屿社会空间的复杂性,没有任何阶层或群体对硅屿表示认同。随着叙事的推进,生态问题的跨境处理、资本的全球性渗透、人机结合体时代的抵抗可能、地方宗族与身份认同等问题都被融混编入赛博格的叙事语境中,硅屿空间的多层性和多义性得以多视角展示。电子垃圾牵扯着这个岛屿世界的利益网络,垃圾女工、政府官员、家族势力、国际资本等,在岛屿的现实空间、网络空间和认同空间内相互冲突又彼此牵制,而这“只是个开始”(23)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第313页。——小说结尾已然预示着硅屿的更多变数必然上演。“空间,更具体说是社会空间,就不仅仅是一个事物、一种产品,相反它不但包容了生产出来的事物,也包纳了事物的共时态的、并行不悖的、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它是一系列运作过程的结果,所以不可能被降格为某一种单纯客体。”(24)陆扬:《空间何以生产》,《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1期。此时,仅作为被征服的客体的空间早已烟消云散。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也可以在空间的主体性层面上得到理解。读过小说的读者不可能忘记宇宙社会学的黑暗森林法则,它宣告,如果宇宙空间有不止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宇宙空间中各文明关系的本质就是“先暴露者先灭亡”。无论各文明的具体形态为何,宇宙空间的社会学不改其坚硬与简洁,矛盾始终主导着空间的存在。《荒潮》中陈贤运对陈开宗说:“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社会,那就是丛林社会”(25)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第33页。,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当然,“三体”系列在解释空间矛盾性的本质时还能将其形象化,空间的降维打击就是明证,整个太阳系被二维化为一幅没有厚度的卷轴。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科技手段对空间形态做出了什么样的改造,矛盾性从不缺席。矛盾性无处不在,因此也可以说“宇宙中除了空间之外什么都没有”(26)刘慈欣:《球状闪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刘慈欣的《赡养人类》只是将穷人简单地区隔到自给自足的微型循环胶囊房中,就呈现出极致化的资本主义想象:房外的所有空间内容——空气、草地、水——全部都属于富人的私有财产,每一口呼吸都值得争夺。
四
网络打开了空间的新面相。从空间物理形态的变形与重组,到空间作为冲突斗争的场所和被争夺的事物,空间想象的丰富性次第展现。网络作为巨大的变量和增量加入到了空间的科幻想象,其根基在于网络有力地改变了社会现实。“当一个新的因素加入到某个旧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旧环境和新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全新环境”,约书亚·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27)[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网络改造现实空间,同时也自成新的空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老百姓开始进入互联网世界时,鼠标、硬盘和现在看起来已经笨重不堪的显示器所指向的神奇世界令人耳目一新。网络社会的崛起迅速而又全面,曼纽尔·卡斯特强调:“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2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9页。,新的社会运行逻辑和新的网络数字技术合力,动摇了许多原本稳固的认知。主体、真实、身份、物质、实践等一系列重要概念都需要重新修订。
王晋康的《七重外壳》提出了对数字虚拟技术大规模运用后的忧虑。在无孔不入的虚拟技术覆盖下,“真实”这个被反复讨论的多义之词已经很难在日常概念的层面上被识别,当亲眼所见、亲手所触的生活用具都可能是网络虚拟技术的造像时,柏拉图对艺术模仿现实、现实模仿作为至高真实的“理式”的“真实”概念讨论已经无关紧要了。网络数字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习以为常的许多真实感觉可能经过了虚拟技术的过滤——恰如“语言转向”突显了语言的存在。“主体的现实接受和再现均无法摆脱语言之网的控制”(29)南帆:《文学理论十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这个判断中的“语言”完全可以替换为“网络虚拟技术”。《七重外壳》的主人公甘又明面临的挑战是必须识别出自己是否处于虚拟之网的空间中,他所采用的方式就是仔细捕捉虚拟现实在细节呈现上的漏洞,比如自己喝了大量的水却长时间不用如厕。可当这种逻辑被推向极限时,甘又明发现他永远无法从关系的参照比较中停下来,所有的呈现和感知都要质疑:“我已经剥掉了六层SHELL,谁知道还有没有第七层?”(30)王晋康:《七重外壳》,载《养蜂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如果继续深究,他马上就可以怀疑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也是网络虚拟技术的造物,关于主体、真实、身份等讨论的复杂性在网络技术的介入下再度升级,可靠的认知支点在哪里?
网络数字技术的能力远不止于制造某些逼真的表象。《黑客帝国》联通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间的方式令人难忘,个体意识通过拨通的电话摆脱了对肉身的依赖,进入另一个充满危机却又更接近真相的虚拟世界。克服具身性亦即克服空间的分割性和时间空间之间的关联,网络空间近乎极致化的自由将焦点都集中在了内部的关系上。七月的《像堕天使一样飞翔》弥漫着些许《黑客帝国》的气息,主人公李雅亚“是为数不多能将网络信号和神经信号无缝对接的人,可以随意地利用自己大脑直通网络内部,也能利用无线网络信号影响他人的大脑”(31)七月:《像堕天使一样飞翔》,载成追忆编选《像堕天使一样飞翔:七月科幻小说选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她为逃脱追杀进入城市上方的平台时发现了许多昏睡的人,但昏睡者们的意识合成的城市管理程序在决定着城市乃至于人类的命运。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手或麻烦制造者都是网络技术携带的可能性,网络技术可能带来类似《1984》式的社会控制,也可以抵抗现实压迫的利器。陈楸帆的《荒潮》以近乎魔幻的方式,将受网络病毒感染后的反抗者小米的主体意识与大型机械人相联通:“只是一闪念,她便凝跃到那尊杀戮之神面前……意识的触手如同柔韧海草,蠕动着渗入那堵墙,寻找着缝隙及复杂咬合的机关……源于意识深处,带着电流的无形触须温柔拂过数以亿计的神经元,扰动晶蓝色的波纹,沿着三维拓扑荡漾开去……小米的意识在机械人与人类两具躯壳间快速切换”(32)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第121、122-123、126页。。感染网络病毒与实现自我拯救,在诸种利益缠斗不休的硅屿空间中,奇异地合成一体。谢云宁的《太阳知道答案》里,宇宙高等文明之间形成“云网络”状态,云网络能“抹去了物质世界固有的浮华光影,让所有个体都能自由平等地驾驭自己的生命轨迹”,但仍“充斥着艰险与争斗”(33)谢云宁:《太阳知道答案》,载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成都往事》,万卷出版公司 2019年版,第269页。。网络无论是自成空间还是作为影响现实空间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表现为简单的技术行为还是呈现为高等文明间的共存状况,它始终对斗争与冲突保持开放。
日益深刻地卷入现实的复杂斗争之时,网络数字技术还是否容许遁世隐居存在?放下手机不仅是个人意志力的考量,它涉及到现代技术进程的不可逆性。网络数字技术不是蜡烛或投石机,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用大明星查尔斯以结束生命为代价退出网络直播的事例说明,脑波传递等网络技术方式既得到整个资本主义方式的支持,也是令人欲罢不能、开启未知未来的“真正技术奇点”(34)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载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金陵十二区》,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55页。,它不存在退出的程序。茨平的《住进玻璃瓶里的人》像是《人人都爱查尔斯》的反证,凯迪拉布奋斗三十一年只为住进“足不出户,就可以工作、赚钱、养家、还房贷、支付各种费用”,还能“有效地保证了空气的清新,水和食物的安全”的实为闭合内循环系统的玻璃房(35)茨平:《住进玻璃瓶里的人》,载江波等《末日卷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195页。,却死于孤独、软骨症和资本主义的冷漠。遵从网络技术逻辑的凯迪拉布和试图反抗它的查尔斯最终殊途同归,那么以某种网络技术对抗网络逻辑是否可行?王侃瑜的《链幕》试图探索这一问题。性格内向的陈淮喜欢链幕技术带来的“身处其中,却不完全融入其中”的感觉,希望“向前伸手就可以触碰到链幕之外的世界,抱紧自己则可以独守自己的空间”(36)王侃瑜:《链幕》,载《海鲜饭店》,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可陈淮在链幕技术即将成功、人工智能可实现替人社交之时死去,链幕技术胎死腹中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以网络技术对抗网络的空间运行机制,宛如拔着头发离开地面的努力。
五
空间物理知识、空间理论和地理批评、网络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相互融汇,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无论空间形态如何变幻,不平等、不公正、不均衡、不静止的权力关系及其构成方式始终是科幻文学想象应跟踪的焦点。理想的科幻想象将秉持这样的立场:被区隔的空间、被生产的关系、无法被看见的人,都与我有关。《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这样的社会学调研指出,网络数字化技术离不开人类劳动的参与,但无论是配合还是抵抗,许多劳动力都隐而不见。尽管物理学上“最新的观点认为,与我们相联系的宇宙并非只有一个,而是许多个,他们相互平行,被称为多元宇宙”(37)[意]托马斯·马卡卡罗、克劳迪奥·M.达达里:《空间简史》,尹松苑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 251 页。,但何夕的《六道众生》和刘慈欣的《纤维》这样的作品都认为平行宇宙间仍发生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没有脱离关系而存在的空间,只有看不见、被遮蔽或被简单化理解的空间。就科幻想象而言,“大”空间不应出于单一的物理维度考量,而应当是权力关系复杂多样的指代。《三体Ⅲ》结尾处的“小宇宙”,其内部社会关系尚未萌芽、作为未来大宇宙组成部分的可能性又未展开,这是它“小”的根本所在。同理,《超新星纪元》中刘静的书名“大如果”之所以可称“大”,就是对空间社会想象丰富性的肯定。发现空间的丰富性、分析空间构成诸要素的生产与相互作用、思考面对空间的价值立场,这是追问星光闪烁的“小宇宙”所包含的“大如果”的过程,也是科幻小说空间想象的魅力所在。
从星光熠熠中看出彼此的交相辉映,需要重新召唤总体性的视角。星空即是是总体性的地图,这是卢卡奇《小说理论》开篇的经典想象。“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人们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的火,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世界与自我、光与火,它们明显有异,却又绝不会永远相互感到陌生,因为火是每一星光的心灵,而每一种火都披上星光的霓裳”,“存在和命运、冒险和成功、生活和本质,就是同一概念。”(38)[匈]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19-21页。总体性意识并非简单地逆转个体视角,而是尽量以复杂关联的认知方式组织科幻想象。某种科幻想象进入特定的空间,意味着旧关联格局的逐步风化解体和新体系在纠缠中的萌生。“整个空间的关联性都在破碎重组,……那些看似消失的空间去了哪里,这些重新构成的空间关系是怎么维持”(39)七月:《biu一声就这样消失》,载成追忆编选《像堕天使一样飞翔:七月科幻小说选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才是耐人寻味之处。如果抛开网络类型文学“金手指”式的强制设定,那么科幻小说中的某种新奇技术的诞生,一定需要面临复杂的社会化接受和运用进程,而研发与接受之间的空白,就是诸种关系缠斗的空间。
当然,科幻想象中总体性视角的重建,离不开价值认同的讨论或伸张。不平等、不公正、不均衡、不静止的权力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的对话、合作、妥协、冲突中,相对应的价值空间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风平浪静。苏贾认为,讨论空间正义不可或缺:“空间正义可以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一个经验分析的焦点,一个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靶子。……正义的地理学或者空间性是正义自身的构成性的、内在的要素,是正义和非正义何以社会化构成并随时间进化的关键部分。如此看来,寻求空间正义就变为基本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40)[美]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有研究就认为,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朋克类型应将重心转向内部空间的探索,在超越肉身的局限性之时将“共情能力、友爱与亲密关系视为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和追求”(41)王一平:《赛博朋克小说中的赛博空间与新生命形态:论吉布森的“蔓生三部曲”》,《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呼唤社会的公正和谐和人际间的友爱共情。有时,对空间正义的追求甚至包容了科技想象某种程度上的硬伤。《北京折叠》中北京的独立翻转折叠,所需要的能量和轴承系统是无法得到现有科技支持的,但这种知识硬伤并未影响到小说斩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传达出的对资本权力区隔的警惕和恐惧,很大程度上击中了现代人空间焦虑和价值诉求的靶心。韩松的“地铁”“高铁”“医院”等系列主题的科幻小说,在将宇宙空间同质化、斗争模式简单化之时,通过回忆、错觉、怀疑、梦境将科幻想象浸泡在浓郁的诡异氛围中,传达出对现代社会强烈的不安感和忧患意识。“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迁的世界里,空间构造物如何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42)[英]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97页。,需要科幻想象个体视角和总体性意识的相互协调,并在此过程中彰显美学的魅力,预防空间想象诸多的物理形态或内部关系的趋同化。
科幻想象一直充满好奇地注视着空间及其外化形象,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里的黑石、《与罗摩相会》中作为空心圆柱体的“罗摩”,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却又难以对其内涵给出定论。科幻研究同样应将科幻的空间想象作为始终的异质象征加以关注,推敲每个“小宇宙”中所包含的“大如果”,并以“首先并始终是历史的—社会的—空间的存在”的立场,“单个或集体地主动参与到历史、地理、社会的建构或生产——‘形成’——中去”(43)[美]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 93 页。,开启更高维度的科幻空间认知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