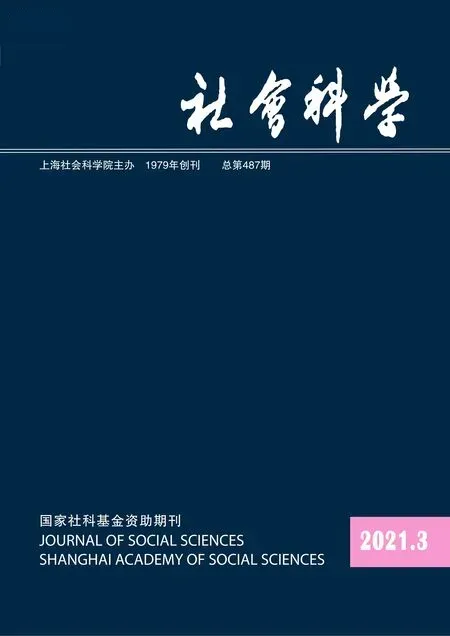自我知识的资格:基于“事”的构成主义*
徐 竹
引 言
与获得他心知识(knowledge of other minds)相比,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通常不需要主体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对意向态度——诸如信念、愿望、意图等——的告白(avowal),例如“我相信这是真的”,一般是被默认为有着第一人称的权威(first-person authority),这就是对“相信”的态度作自我归赋(self-ascription)。认知资格(epistemic entitlement)就是信念成为知识的可靠保证(1)认知资格是一类认识上的保证(epistemic warrant),被保证了的、有资格成为知识的信念在正常情境中通常为真。参见Burge, Tyler,“Perceptual Entitlemen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67, No.3, 2003,pp.505-506。,“有资格成为知识”通常并不保证实际的知识状态。作自我归赋的信念通常也有资格成为知识,但自我知识的资格似乎就能够保证知识状态,而不像他心知识那样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这至少是“表面上的”(prima facie)特殊性。
构成主义(constitutivism)主张,这种“表面上的”特殊性有实质的根源,认知资格保证了自我知识具有区别于他心知识的透明性(transparency)与权威性:所谓透明性是说认知者实际持有的意向态度本身蕴涵了对该态度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high-order belief),而所谓权威性则是反过来,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本身也决定了认知者实际上持有该态度。(2)Bilgrami, Akeel,Self-Knowledge and Resen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89.与此相对的是认知主义(cognitivism)观点,这种观点主张自我知识在“表面上的”特殊性并不蕴涵认知资格上的实质差异:自我知识也像他心知识一样需要经由观察和推理,而我们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判断是非透明的更不具有权威性,那么基于同样的认知资格,自我知识也没有特殊的“第一人称权威”。认知者对意向态度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与实际持有的相应态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在构成主义者看来,这恰恰表明了认知主义对自我知识资格的严重误解。
一、构成主义的两个论证
在自我知识理论的当代论争中,休梅克(Sydney Shoemaker)一直致力于批评认知主义的这种误解,即所谓“独立存在论证”(distinct existences argument):
内省性的信念与觉察必须被看作是作为觉察对象的那些心理状态所导致的结果。而原因与结果之间只能是“独立的存在”,正如休谟教导我们的,独立的存在之间只能有偶适的关联。(3)Shoemaker, Sydney,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225.
如果高阶信念与一阶态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至多有偶适的(contingent)关系,那么认知者只能通过知觉与推理得知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即便有认知能力的正常发挥,也仍然可能受偶然的认知运气(epistemic luck)影响,而作出错误的自我归赋。知觉知识的资格就是这样。知觉能力的正常发挥能使知觉信念具备认知资格,但这并不能保证赢获知觉知识。设若认知者身处不正常的光线条件中,又或是像“假谷仓案例”(Barn Façade case)(4)当代知识论中讨论的假谷仓案例有如下形式:张三带着儿子开着车在公路上奔驰,儿子一指远处的一处建筑物,问是什么,张三看了一眼,说那是谷仓。张三视力正常,而且他们所看到的那个也的确是谷仓。但张三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车正驶入一个叫做“假谷仓县”的区域,这里前前后后有很多假谷仓,看起来很像真的,但只是一幅立体感很强的图画,远远看去完全无法分辨。如果稍微错过去一点儿,张三他们就会碰到假谷仓,而只是碰巧当时看到的是真谷仓。那样偶然进入极易产生虚假信念的环境中,那么即便有认知资格,认知者实际上也并没有真正的知识。
所以,如果自我知识的资格类同于此,那么也会存在偶然的认知运气,阻碍了有资格的信念成为自我知识。休梅克称之为“自我蒙蔽”(self-blindness):主体有这样一些意向态度,并不蕴涵任何对其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即自我知识不再是透明性的。但“自我蒙蔽”并不等于任何使透明性不成立的情况。如果主体的自我认知机制存在缺陷,譬如说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的病患,那么他的一阶态度当然有可能不蕴涵高阶信念,这却不是“自我蒙蔽”。仅当透明性不成立的原因是认知资格以外的偶然因素时,才是自我蒙蔽。在休梅克看来,如果“独立存在论证”成立,那么自我蒙蔽就一定是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能证明自我蒙蔽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认知主义就必不能成立。
概言之,休梅克反对自我蒙蔽的论证具有如下的形式:
(1)S具有某个心理状态p,可以是现象意识、知觉状态或行动意图等;
(2)如果S有状态p,那么S就必须具备对p来说是必要的能力P;
(3)S是自我蒙蔽的,即S的认知能力正常却不知道“我有状态p”;
(4)如果S的认知能力有缺陷,则他可以有能力P却不知道状态p;
(5)如果S的认知能力正常且不知道“我有状态p”,则他缺乏能力P;
(6)由(2)(5)得知,如果S的认知能力正常却不知道有状态p,则他实际上没有状态p,而这与(1)相矛盾;
(7)由(4)(6)得知,当S不知道自己有状态p时,要么是他认知能力有缺陷,因而有能力P却不知道状态p,要么是他认知能力正常却缺乏能力P,因而也就没有状态p;
(8)S不论处于(7)的哪一种情况,都不是自我蒙蔽的。
不难看出,这一论证中最关键的一步是(5):在休梅克那里,自我蒙蔽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当认知能力正常发挥时,假如某个心理状态对主体不透明,那么主体就实际上缺乏形成该心理状态的必要能力,因而他就实际上就没有此心理状态。这是因为,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与作为其对象的意向态度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构成性的关联:自我知识的资格本身就要求意向态度总是已经蕴涵了对它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而这就保证了透明性特征,拒斥了自我蒙蔽的可能性。
为了解释人们拥有某些高阶信念的行为,即那些对他们的一阶信念的信念,他们唯一需要的只是那些一阶信念加上正常的理智、理性和概念能力,而完全不需要赋予他们某些额外的东西。(5)Shoemaker, Sydney,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nd Other Essays, p.239.
这就是休梅克的构成主义版本。按此,自我知识的认知资格完全不同于知觉知识:在信念具备自我知识资格之后,没有什么偶然的认知运气能造成“有资格无知识”的情况。而认知资格之所以能保证知识状态,是因为主体实际的意向态度与对其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发挥相同的因果作用(6)Shoemaker, Sydney,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nd Other Essays, p.243.。正如戈尔德曼(Alvin Goldman)后来批评的,经典功能主义者既然认为一阶的心理状态将会自动地产生相应的高阶信念,那么“究竟如何断定自己是否有某个心理状态”的问题,就完全处于他们所能解释的范围之外。(7)Goldman, Alvin, “The Psychology of Folk Psycholog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16, No.1, 1993, p.22.这一论断也适用于同样是经典功能主义者的休梅克,但功能主义并非构成主义的自我知识理论的必要前提。
伯奇(Tyler Burge)就提供了一种非功能主义前提的构成主义,论证说自我知识的资格来自于认知者的“批判性推理”(critical reasoning)能力:
批判性推理的能力及其与之必然匹配的对理性规范的接受,要求某些心理行为和状态必须可以被认识和回顾。可知的可回顾性(knowledgeable reviewability)就特别地要求有与之相关联的某种独特的认知资格。它要比知觉判断中包含的资格更强。在相应的第一人称判断与其判断主题为真之间,必须有一种可待解释的、非偶适的理性关联。(8)Burge, Tyler, “Our Entitlement to Self-Knowledge: I”,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96, 1996, p.98.
首先,批判性推理的能力要求自我知识具备权威性。所谓的“批判性推理”就是认知者能够修正自我原有态度的反思。这种修正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对态度的反思性判断可以直接调控被反思的态度本身——这意味着两者之间也是构成性的而非偶适的关联。在伯奇那里,认知资格意味着规范得到满足,而规范是表征功能完成度的标准(9)Burge, Tyler, “Perceptual Entitlement”, p.513.。那么,“如果认知者缺乏判断自己态度的资格,那么他就不能接受某些理性规范,正是它们决定了人们应该如何调控那些作为反思对象的态度。如果反思并未对那些态度作出任何理由背书(reason-endorsed)的判断,那么反思与被反思的态度之间的理性关联就会不复存在”(10)Burge, Tyler, “Our Entitlement to Self-Knowledge: I”, pp.101-102.。一言以蔽之,自我知识的资格是对态度展开反思的先决条件。
自我知识之所以具有权威性,认知资格本身即足以保证知识状态的赢获,在伯奇看来,这就等于主张对态度的自我归赋不会犯“蛮横错误”(brute errors)。所谓蛮横错误,就是具备认知资格的信念仅仅因为认知运气而产生的错误。态度的自我归赋虽然可能出错,但这只是因为主体认知能力未能正常发挥,却不是蛮横错误(11)Burge, Tyler, Cogni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Self-Knowledge, Interlocution, Reasoning, Refl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88-189.。
自我知识的资格与蛮横错误不相容,同样来自于批判性推理能力的要求。设想一下,如果高阶信念的认知资格不能保证该信念是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态度的信念可能犯蛮横错误,那么在相同的意义上,我们对自己所持态度的反思结论就不能“直接调控”被反思的态度本身,这就将使我们的态度反思不再是真正“批判性的”。一言以蔽之,高阶信念与一阶态度之间的构成性关联、自我知识的资格对实际知识赢获的保证,归根到底都立足于被反思的态度可以直接受批判性反思的调控,而蛮横错误恰恰取消了这种“可直接调控性”。然而,这种“可直接调控性”的确可以不成立,例如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的认知者作出了错误的自我归赋,正是因为他的高阶信念并不能实际修正自己的一阶态度。对此,伯奇的解释是,我们不能把非批判性推理造成的态度误认为态度反思的结论。自欺的认知者显然并没有真的在作批判性推理(12)Burge, Tyler, “Our Entitlement to Self-Knowledge: I”, p.104.,因此他本来就缺乏认知资格,而非在具备资格的基础上犯了蛮横错误。(13)当然,构成主义者还可以采纳不同于伯奇的解释,例如坚持“可直接调控性”在自欺发生时依然成立,高阶信念本身并未出错,只不过是由它调控形成的态度与其它潜在的一阶态度之间不一致,所以造成了认知者作出错误自我归赋的“假象”。参见Bilgrami, Akeel, Self-Knowledge and Resentment,p.143;Coliva, Annalisa, The Varieties of Self-Knowledge, Palgrave Macmillan,2016, p.198。
反之,如果“可直接调控性”成立,那么自我知识的状态总是已经由认知资格保证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可错的”。具体说来,“相信p”是认知者的一阶态度,它回答了“p是否是事实?”的问题;相应地,认知者的高阶信念“相信我持有信念p”,回答了“在相信p、非p与悬置判断之间选择哪个更合理?”的问题。而伯奇实际上主张的是,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总是直接调控了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这其实是理性主义的标准理想,并不总是合乎现实,因为对这两个问题的信念慎思(doxastic deliberation)完全有可能分别独立展开,得出并不一致的结论。换言之,认知者有可能既同意“应该相信非p”又断言“p是事实”。这被称为“认识上的意志薄弱”(epistemic akrasia)(14)Hookway, Christopher, “Epistemic Akrasia and Epistemic Virtue”,In A.Fairweather, L.Zagzebski,Virtue Epistemology: Essays on Epistemic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89-190.。如果认知者是意志薄弱的,那么即便批判性推理能力得到了正常发挥,高阶信念仍有可能犯蛮横错误,因为它并不能直接调控一阶态度,从而认知资格就不能保证有真正的自我知识。
所以,伯奇版本的构成主义虽然不像休梅克那样受功能主义的制约,但以“批判性推理能力”来界定自我知识的资格,就受制于理性主义的标准理想,从而也就无从应对认识上的意志薄弱。与此相反,认知主义完全承认蛮横错误的可能性,因为自我知识本来就没什么特殊的认知资格。
二、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对称性
与构成主义不同的是,认知主义者认为,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并不蕴涵认知资格上的实质差异。就认知资格而言,自我知识与他心知识并无不同。我们在何意义上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就在同一意义上了解我们自己。因此,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实质上是对称的。那么,这种认知对称性为什么会至少在“表面上”造成自我知识的特殊性?这就是认知主义所致力于解答的疑惑。
认知主义的论证汲取了来自认知科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的证据。自笛卡尔主义以来,自我知识的特殊性往往被归因于某种只能采取第一人称视角的“特权通道”(privileged access),具体说来就是内省(introspection),由此界定了某种比他心知识更优越的认知资格。然而,实验证据表明,人们在内省中常常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做出错误的归因,并不真的比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更可靠(15)Nisbett,R.E.,Wilson,T.D.,“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Vol.84, No.3, 1997,pp.231-259.。在日常情境中,要认识他人的心理状态,我们通常需要观察他人行为,然后基于某些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定律作出推理与预测。例如,“人渴了就会喝水”是常识心理学的定律,那么看到张三拿起水杯喝水,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论他正体会到口渴的感受。而发展心理学的证据表明,3周岁以下的儿童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认识自我的,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对称性至少是儿童心理发展早期的事实。
认知主义的“理论论”(Theory-Theory)观点是,自我知识的资格是基于常识心理学的推理和预测,从而也类同于他心知识的资格。因此,认识自我的心理状态就类似于提出一种解释自我心智的融贯理论。当然,3岁的儿童还没有构建理论的能力,但他们对自我的认识至少在一些关键环节上类同于理论解释:例如他们会假设某些不可观察的实体——信念、欲望等心理状态,并且以定律来联结这些实体。这样构建起来的“心智理论”同等地适用于自我与他人。(16)Gopnik, Alison,“How We Know Our Minds: The Illusion of First-Person Knowledge of Intentionalit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16, No.1, 1993,p.10.
但是,随着儿童心理成熟度的提升,自我知识资格似乎就不再需要经由类似理论的推理,而是越来越展现出某种更为直接的、区别于认识他人的途径。对此,理论论者回应说,这并不是说理论性的推理不再发生,而只不过是由于太过“精于此道”所产生的“技能错觉”(the illusion of expertise):
成年人现在就可以运用心智理论的所有理论工具,包括意向性的概念在内,以便得出关于他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推理与结论。这些推理将会产生某种带有特定复杂现象特征的心理体验。在技能的影响下,我们有可能完全觉察不到自己在做这些推理,而把那些复杂的、负载理论的体验解释为对我们的心理状态的直接感知。(17)Gopnik, Alison, “How We Know Our Minds: The Illusion of First-Person Knowledge of Intentionality”, p.11.
这就为自我知识“表面上的”透明性与权威性提供了一种认知主义的解释。然而,正如戈尔德曼所指出的(18)Goldman, Alvin, “The Psychology of Folk Psychology”, p.26.,这并不能解释何以我们在他心知识上就不会产生类似的技能错觉。如果自我知识的特殊性仅仅是推理技能娴熟的错觉,如果自我与他人在认知上还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本应该在认识他人时也可能有同样的“错觉”才对。但实际上,“即便我们有时熟知他人的行为,于是我们对他心的认识也不再像一个生手科学家,而更像是一个行家里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依然想要让自我知识的路径区别于他心的认识路径”(19)Bilgrami, Akeel, Self-Knowledge and Resentment, p.17.。所以,自我知识的特殊性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发掉。
戈尔德曼不仅指出了理论论解释的局限,而且认为理论论的局限性就在于忽视了现象特征与意识体验的作用。心理状态的现象特征是它在第一人称的意识体验中呈现出来的样子,这普遍存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心理状态中。我们不仅在知觉经验中把握花朵“如此这般艳丽的红色”,而且甚至从最抽象的概念性思想中也能够体会到独特的现象特征——例如在做几何证明题时也有对某种独特“确定感”的意识体验。不论是自我知识还是他心知识,都建立在对心理状态之独特现象特征的把握上。所不同的是,自我的心理状态可以被直接地体验到,而要预测他人的心理状态却必须依赖于某种心理模拟机制:“先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情境中,然后再决定自己会做何事或有何感受”(20)Goldman, Alvin, “The Psychology of Folk Psychology”, p.27.。
在认知主义的“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观点中,仅就对意识体验的依赖性而言,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的确是对称的;但自我知识的特殊性也并非全然错觉,因为对自己当下心理状态的意识体验的确是特殊的——可与之相对比的是认识过去的自我,以及认识他人的心智,都需要借助想象的情境模拟才能“间接地”获得相应的意识体验。在这里,“想象的模拟”替代了“基于常识心理学的理论推理”,因为认识他人的心理状态只需要“引入某个想象的情境,作为对某一内在心理机制的输入,然后再产出某个相关的输出状态。即便你不知道任何描述机制的定律,你的机制也仍然能‘模化’或摹仿目标人物的机制”(21)Goldman, Alvin, “The Psychology of Folk Psychology”, p.27.。
模拟论解释的合理性取决于把握现象特征的意识体验的地位。困难在于,任何包含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的心理状态都不仅有现象特征,也要有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而在现象特征与内容之间并没有保持足够敏感性的对应关系。例如,我在相信勾股定理与相信“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时可能具有差不多强度的“确定感”,那么我如何能仅仅通过现象特征上分辨所模拟的心理状态究竟是关于勾股定理的还是有关“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的?如果要为模拟论辩护,那戈尔德曼就得主张有这样一种能够从现象特征上分辨内容的心理模拟机制,而这似乎只是一种不太有希望的设想。(22)Nichols, S.,Stich, S.,Mindreading: An Integrated Account of Pretence, Self-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98.
既然理论论与模拟论都有内在缺陷,那么将两者综合起来或许能做得更好。在斯蒂奇(Stephen Stich)与尼克斯(Shaun Nichols)看来,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都要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探测,即把所获知的心理状态归赋给某人;二是推理,即用已知的心理状态信息预测先前或未来的心理状态、行为与环境。(23)Nichols, S.,Stich, S.,Mindreading, p.151.按照这一区分,理论论实际上就是以推理来完成探测的任务,模拟论则是相反,试图以探测去做推理所应做的事。然而,并没有什么理由保证这两个任务要由同一个机制完成,为什么不尝试由两个机制分别完成这两个任务呢?
他们主张,认知者除了有常识心理学的推理之外,还有对自我心理状态的监控机制:认知者对这一机制输入自己的各种表征状态,如信念、愿望、意图、想象等,而它输出的是对这些信念、愿望、意图与想象的自我归赋:“我相信p”(24)Nichols, S.,Stich, S.,Mindreading, pp.160-161.。首先,监控机制并不是对现象特征的意识体验,而是直接针对表征内容的监控,所以也就不存在模拟论那样的困难。其次,它也不需要把自我知识的特殊性解释为“技能错觉”。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知识的确可以区别于他心知识,因为我们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监控机制,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则只能靠推理。3岁以前的儿童之所以表现出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的对称性,是因为他们那时还过于依赖推理的机制,缺乏调用监控机制的能力。随着认知能力的增长,儿童也会逐渐摆脱对推理机制的依赖,而从监控机制获得的信念自然是以不同于观察和推理的方式获得成为真正知识的资格。(25)Nichols, S.,Stich, S.,Mindreading, pp.171-172.因此,认知主义的监控机制理论(Monitoring Mechanism Theory)就兼具理论论和模拟论各自的优势:一方面,基于常识心理学的推理保证了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对称性;另一方面,对自我心理状态的监控机制独立于推理机制之外,解释了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
但即便如此,认知主义的根本问题似乎仍然存在:由监控机制塑造的认知资格究竟能否保证赢获实际的知识状态?如果它类同于他心知识的资格,那么被监控的一阶态度与监控机制输出的高阶信念之间就仅有偶适的关联,认知资格本身无法保证认知者实际具有自我知识。因此,坚持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对称性,就仍难以解释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如果监控机制保证了自我知识的资格不同于他心知识,具备认知资格即保证了自我知识的赢获,而与蛮横错误不相容,那么就的确解释了“表面上的”特殊性,但却放弃了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对称性,也就离开了认知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构成主义的门槛。一言以蔽之,既要坚持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对称性,又要解释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这对认知主义来说简直是无解的。
三、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
我们对构成主义与认知主义各自的得失稍作检讨。构成主义主张,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反映了认知资格上的实质差异:自我知识的资格区别于知觉知识或他心知识,因为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与实际的意向态度之间是非偶适的、构成性关系,自我知识的资格本身就保证了知识状态的赢获,而不会像知觉与他心认知那样有蛮横错误的可能。但构成主义不能解释“认识上的意志薄弱”,因为这恰恰要求实际持有的态度可以不受反思判断的直接调控。相反地,认知主义主张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对称性,具备认知资格的高阶信念也有可能犯蛮横错误。但是,认知主义的困难在于,如果不放弃这种对称性,转而诉诸认知资格上的实质差异,似乎就很难解释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
就一般知识而言,资格得自于认知能力的正常发挥,知识状态却是能力与环境相配合的结果。一个正常知觉产生的信念总是已经具备了成为知识的资格,但它要成为真正的知识,就需要环境因素与之配合,而不能是反常的光线条件或“假谷仓”案例那样的环境。而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似乎意味着,知识状态本身仅仅要求认知能力的正常发挥,而无需顾虑偶然的运气。在构成主义者看来,这当然意味着自我知识要求特殊的认知资格。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构成主义与认知主义都默认自我知识的资格具有某种普遍性,即立足于某类普遍的认知“能力”。如果我的高阶信念是“相信我现在口渴”,那么这一定是基于产生高阶信念的普遍能力,而非由某一类情境塑造的特殊能力。但是,也有很多自我知识的确依赖于情境的塑造,这往往是“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26)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并不限于对心理状态的自我知识。实践的自我知识(practical self-knowledge)即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任务导向的;考虑复数主体“我们知道”的情况,集体性自我知识(collective self-knowledge)也大都是任务导向的。——认知者并非专题性地开展认识自我的活动,而是在某类实践事务的应对中,根据任务本身的要求而认识了自我的意向态度。那么,相应的认知资格就必须得自于主体为了应对实践事务而发展出来的特定能力。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在侦破一起凶杀案的过程中,侦探认为被害人的丈夫小王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且对这一信念作自我归赋:“我相信小王是嫌疑人。”那么这一自我知识就是受任务导向的。首先,它并不是专题化认识自我的结果。侦探正在做和想要做的并不是“认识自己究竟相信什么”,而是“侦破案件”。而在这一任务导向下,自我知识的确是必要的,因为假如侦探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相信“谁是嫌疑人”,他也就无从确定自己接下来该如何破案。因此,自我知识虽然不是认知者的任务目标,但却是应对这一类实践事务所要求的东西。
同样的自我知识也完全可以不由实践事务导向。如果一个完全不懂如何破案的外行人,边阅读侦探故事边检视自己的信念,他也可以知道自己“相信小王是嫌疑人”。此时,这个外行人对信念的自我归赋就是没有任何任务导向的单纯报告,是专题化自我认知的成就,从而也区别于侦探在破案的任务导向下获得的自我知识。当然,会有人批评说,两者毕竟断定的是完全相同的信念内容,因而“有无任务导向”似乎是非常外在的区分,无论是在构成主义还是认知主义的意义上,这都不会造成自我知识资格的差异。
然而,这种差异的确存在,因为“有无任务导向”决定了指称自我信念的不同方式,或可约略概括为“从物/从言”(de re / de dicto)的差异。所谓“从物”的方式就是直接指向对象本身,不论其所处的具体描述;“从言”的方式则一定是从对象所处的具体描述下来思考对象,从描述的涵义通达指称对象。例如,“太阳系的行星数是偶数”,在“从物”的意义上就等价于“8是偶数”,因而也必然为真;但若“从言”地看,两者并不等价,因为仅就“太阳系的行星数”的描述涵义来看,它也可以是9。所以“太阳系的行星数是偶数”并非必然为真。
类似地,侦探和外行人尽管做出了内容相同的自我归赋:“我持有‘小王是嫌疑人’的信念”,但他们对各自信念的指称方式是不同的。对外行人来说,这是专题化反思自我的结果——无论是构成主义者推崇的批判性推理,还是认知主义者主张的监控机制,总之专题化反思都要直接指向信念本身,而并不取决于呈现信念的具体描述,所以都是“从物”的方式。与此相反,侦探却是在“从言”地指向自我的意向态度。在任务导向下有意义的并不只是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而是要从某个特定描述中知道自我的态度。换言之,与对自我的专题化反思不同,侦探从来都是在具体描述下相信“小王是嫌疑人”的:例如,这究竟是意味着“小王身上的疑点不能完全排除”,还是“小王的嫌疑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交叉印证”,抑或是“尽管证据与之相左,但仍然倾向于相信小王是嫌疑人”?这些未必明述的,可以仅仅是被默会地把握了的信念描述,构成了侦探获得自我知识的必由路径。因为侦探的这一自我知识乃是受破案任务导向的,而对信念态度的具体描述不同,所要采取的情境策略也就会有相应的差异。
一言以蔽之,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的资格,就得自于处理实践事务的能力。这也为反观构成主义与认知主义各自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如果意向态度的自我归赋受实践事务的具体导向,乃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那么,构成主义与认知主义都有必要表明自己如何能适用于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
四、基于“事”的构成主义
立足于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构成主义亦不同于休梅克与伯奇的论证版本,而是一种基于“事”的构成主义。它对自我知识资格的界定就不再是批判性推理的能力,而是处理实践事务的能力。这样做的好处是,认知主义解释的部分合理性就被吸纳到构成主义的框架中,既能解释“认识上的意志薄弱”与“自欺”的可能性,又能够界定自我知识“表面上的”特殊性。具体说来,基于“事”的构成主义仍然以认知资格与知识状态之间的构成性关联为理想目标,而认知主义主张的那种与蛮横错误相容的自我知识资格,则仅仅是某种有待于改进的状态,并且也正是在这一“可提升性”的意义上,自我知识区别于他心知识与知觉知识。
如前所述,伯奇的构成主义论证的主要问题是,囿于理性主义的标准理想,无法解释“认识上的意志薄弱”。在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中,认知者的确可以是“意志薄弱的”。设想侦探对归赋给自我的那个信念的特定描述是:“尽管证据与之相左,但仍然倾向于相信小王是嫌疑人”。如果仅仅按照批判性推理,基于证据评估的结论是“可以合乎情理地排除小王的嫌疑”。然而,即便侦探明明知道这一结论,他也仍然选择把“小王是嫌疑人”的信念归赋给自己,这就是典型的“认识上意志薄弱”,因为侦探实际的信念抉择并没有受批判性推理的调控。构成主义主张的那种“可直接调控性”在这里就不能成立。
构成主义的可能回应是,这意味着侦探做出了非理性的信念选择,因此丧失了自我知识的资格。但是,侦探的选择未必是非理性的,反倒恰恰是因为他破案的经验老练娴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谨慎采信基于有限证据的推理。尽管他还没有具体的证据来挫败那些排除小王嫌疑的证据,他也仍然选择相信嫌疑不能排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经验丰富的侦探不仅有认知资格,而且还要比那些初入行的、拿到一点有限的证据就开始发挥“批判性推理能力”的新手探员更有资格真正知道自己“相信什么”。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批判性推理能力”并不适宜于界定认知资格——仅仅面向“批判性推理能力”的可直接调控性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标准理想,但在任务导向的情况中,“可直接调控性”的来源并不仅仅是批判性推理的能力。经验老练的侦探也不是一个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的老顽固,他知道修正自己的态度有时是必要的,只不过这种修正的力量并不得自于有限证据的推理,而就是处理实践事务的能力——“做事”的能力。破案就是侦探所做之“事”,这不仅要求批判性推理的能力,而且还需要恰当的直觉和洞察力,以及综合把握环境要素的能力,等等。正是基于综合的“做事”能力,人们才能以恰当的描述“从言”地呈现自己的信念,也就是在任务导向下具备自我知识的资格。
那么,在认知者处理实践事务的能力意义上,认知资格与知识状态之间是否具有非偶适的、构成性的联系?如前所述,构成主义主张对态度的自我归赋并不会犯所谓“蛮横错误”,即认知资格保证了知识状态的赢获。那么,这是否也适用于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这意味着,只要具备“做事”的充分能力,只要在认知资格上无所缺失,就一定不会在自我知识上出错?
在认知主义者看来,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是对称的——既然他心知识与知觉知识都不能免于“蛮横错误”,那么自我知识也一定不会例外。例如,在任务导向的情况中,即便是具备充分“做事”能力的认知者,也仍然有可能发生自欺。设想一个已经具备独立破案能力的探员,有可能受一系列与小王的犯罪嫌疑相左的证据影响,其实际的破案行为表明他并不真相信小王有嫌疑,但当被问到“小王是否有嫌疑”时,他还是会像那个经验老练的侦探那样,给予肯定的回答。因此,这个侦探陷入了自欺,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出错了。
当然,在构成主义者看来,这仍然不是蛮横错误,而只是表明发生自欺的侦探并不真正有“充分的”做事能力。与此相比,娴熟老练的侦探大概就不会自欺,他一旦相信小王有嫌疑,在实际办案策略中就会做到知行合一。但是,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门槛就被不恰当地提高了:“做事”的能力本应是底线要求,“娴熟老练”通常不是“做事”能力的必要条件,而是远远超出底线要求的卓越表现。相应地,以其为认知资格的自我知识也应该是某种更有价值的知识状态,或接近于自我的理解(self-understanding)(27)伯奇也谈到了“自我理解”的概念,但在他看来这与自我知识并没有实质区分,两者都与蛮横错误不相容。参见Burge, Tyler,Cogni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Self-Knowledge, Interlocution, Reasoning, Reflection, p.188。但是,在对“理解”的当代知识论讨论中,的确已经有很多论证主张,理解是比一般知识更有价值的认知状态。参见Kvanvig, J.L.,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88。按此,自我理解理应是比一般的自我知识更有价值的认知状态。与明智(self-wisdom)。在这个意义上,原来立足于“批判性推理”的伯奇版本的构成主义,可以被重构为一种基于“事”的构成主义:由处理实践事务的卓越能力所界定的认知资格,的确保证了认知者总是具有任务导向下的自我理解与明智状态,而不存在发生蛮横错误的空间。
但是,发生自欺的侦探也已经具备“做事”的能力,因而他对自我态度的信念已经有认知资格,那么就必须承认这里发生的的确是蛮横错误,这正是认知主义的合理性所在。“做事”的能力不能保证知识状态的实际赢获,因为由此而断言意向态度的高阶信念尚不足以成为构成自我实际态度的条件。在理性主义的标准理想中,对态度的反思判断可以直接调控自我的实际态度。但在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中,作自我归赋的高阶信念得自于“做事”的能力,而非批判性推理的能力。但即便是充分的“做事”能力,也未必已经达到由这种能力来实际地决定自己持有何种态度的境界。所以,基于“做事”能力的“可直接调控性”,并不是自我知识资格的底线要求,而是为卓越自我理解与明智的资格体现。
如果卓越的“做事”能力与更高价值的自我知识状态之间可以是非偶适的构成性关联,那么蛮横错误的可能性,就应该被视为一种有待于改进的现状,可以随着“做事”能力的精进而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不难设想,有破案能力的侦探会变得越来越娴熟老练,越来越懂得如何恰当地规避自欺与意志薄弱,从而让任务导向下的自我知识越来越接近于自我理解与明智的状态。而对于他心认知与知觉经验来说,原则上始终有可能发生蛮横错误,其认知资格就不会像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这样具有“可提升性”。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知识的特殊性并不只是“表面上的”,而是的确要求不同于他心知识或知觉知识的认知资格。
结 语
“任务导向”当然不是自我知识的普遍特征,但以“做事”能力来界定自我知识的资格,却有着普遍的意义。俗话说“少不更事”,这往往是指对自我和他人皆欠缺了解的状态,而在“事”上磨练得愈久,能把握之“事”愈多样,就愈能在“做事”中理智清明地对待自我。“事”哲学的新近讨论也呈现了这一义理脉络。自我知识资格的“可提升性”正是奠基于“做事”能力由潜能向现实的转化,因为“本然的机能……要成为现实的能力,便离不开人所从事的不同活动”。杨国荣指出,这正是引入“事”的概念的优势所在:
这种发展并不仅仅以抽象的观念衍化为其形式,而是实现于人所做的多样之“事”:“事”不仅涉及“做什么”,而且关乎“如何做”,在把握对象和变革对象的过程中,人既在“做什么”的层面与世界发生关联,也在“如何做”的层面锻炼和提升自身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的能力。(28)杨国荣:《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对任务导向的自我知识及其认知资格的讨论,既与上述评论交相印证,也可以反过来对“事”哲学本身作出评价和补充。立足于认知资格的可提升性,“事”概念的引入着眼于自我的培养,自我更多地是被当作在经验中拓展能力的对象,而非具有能动的构成作用的主体。构成主义特别强调这个面向,尽管这不应该等于由态度的反思判断直接调控意向态度本身,但在基于“事”的构成主义中,由“做事”能力形成的高阶信念也应该成为做事者实际持有态度的构成条件。只有在由处理实践事务的能力决定的认知资格中,人们才能真正对自我实现一种极富价值的理智把握——这是一种身处事中而明智果决的自我理解,超越了仅仅诉诸理性能力的抽象理想。如果这是人类生活共同的经验沉淀,那么它理应成为自我知识理论的题中之义。基于“事”的构成主义正是循着这一方向的建构性尝试。